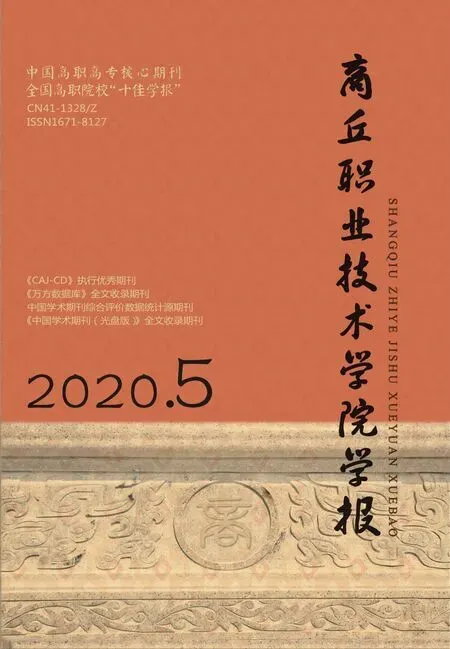墨家思想与中国现代化
陈小刚
(中共平塘县委党校,贵州 平塘 558300)
一般认为现代化的标志是产业革命,即走向社会化生产方式。这种线性理解和经济视域,忽略了现代化的综合过程性,即国家现代化并非纯粹的经济指标(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还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思想和价值理念。随着全球现代化不断推进,中国现代化所遭遇的“西方”乃是一种资本主义①,这使得中国现代化理论日益突出。在“多元现代性”和中国实践的基础上,已然明确中国之现代化的关键点在于政治经济体制和文化传统,即经济建设与思想道德的现代化。所以传统文化和古典思想在现代社会能否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思想资源,核心在于古典智慧与现代化的适应、协调、契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结构之关键部分和“世之显学”的墨家,从发轫至今历经“显学”“式微”“绝学”“重光”的千年嬗变,产生了新墨学、新墨家,这足以说明其不息之生命力和广泛适用性,特别是近现代以来,墨家以其深刻的哲学洞见和民主、科学因素成为连接东西文化的桥梁,为中国现代化注入了学术活力,传播了思想价值。墨家思想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在于其融贯中西、古今转型,实现自身的现代转向。在思想—实践中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问题—视域中实现墨学研究范式的变革和墨家思想的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以“十论”为核心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产生密切关联。这种关联性为当代国家治理提供了政治上的尚贤、善政,社会伦理上的尚同、兼爱、公义、法仪,经济利益上的交互利、兴利除害、节用,生态价值和道德因果的顺天之意,精神文化生活上的非乐非命、和谐世界的非攻、国家安全的守御之治理体系和古今对照、中西合璧的“尚贤—民主”“尚同—自由”“兼相爱交相利—理性经济人”“法仪—法治”等文化主张,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
可以说,在“中体西用”的时代背景和“返本开新”当代要求下,如何有效协调传统文化与现代诉求之间碰撞冲突,使其相对契合,意义十分重要。这样一种创造性继承、创新性发展的实践理路导引传统文化(特别是伦理价值和思想文化)的现代化转向,为中国现代化提供文化价值。所以结合思想—实践、问题—视域进行现代性考究,可以发现,墨家思想之于中国现代化,可以提供物质生产(经济—生产)现代化、制度设计现代化(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的治道体系)、人的现代化(思想道德与综合素养)的理论镜鉴和哲学理念。
一、墨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循史而观,中国现代化离不开“西方”“西学”的介入,其介入使得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产生思想碰撞与冲突。作为应对文化挑战、连接东西文化桥梁的墨家思想,于历史文化和思想实践中,以其广博深邃的理性哲思、民主元素、科学元素和人民性、实践性、逻辑性特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伴相随,彼此之间萃取思想精华,实现其与时俱进和现代转向的特性。
西学东渐以来,中西文化相互遭遇、碰撞、融贯。“纵览古今,横贯中外”的学术思想风气,创生了“兼容并包”的开放思想观念和学术环境。在现代化进程中,墨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遇、会通、融贯、互促,既是学术、思想问题,也是历史、文化问题,更是理论、社会问题。墨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历史视域出发,关联了近现代史、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哲学史,从文化维度透视,涉及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社会结构而论,遍及政治、伦理、经济、宗教等各领域。
历经“显学”“式微”“绝学”的墨家思想[1],在清末民初迎来重光和勃兴的际遇,由于时代思潮的影响和社会转型的变革,它成为应对西方文化挑战(冲突、碰撞)的有力武器。其具体表征为苦行救世与救亡图存的社会现实需求(墨子“十论”之救世扶偏理论、止楚攻宋之身体力行义举)相暗合、“民主”成分利于思想启蒙(公私、兼爱、尚贤)、“科学”内容与西学近似②、援墨济儒与革命精神塑造(儒家仁爱,墨家兼爱;儒家贵和,墨家尚同;儒家尊礼,墨家非乐)。起初,学人以西学中源论对待接受西学,具体表征为西器、西政、西教等层面(尤以黄遵宪为代表极倡此说),其重要来源之一就是墨家思想。墨家思想,不仅厚植了融合中西的思想文化土壤,更为助推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思想观念。
于此视野之下,墨家思想与东来之马克思主义产生会通、融贯、互促,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一些基础。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在充分认知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之上,深刻解析、合理汲取本土文化,将其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贯通,助推促就马克思主义的扎根、发展。可见,这种“中国化”进程的关键在于萃取、融合传统文化之精要。兼济儒道的墨家,以其显学地位和深刻洞见,不仅历史地与马克思主义交汇,更为耦合其闪光因素,显扬其古典智慧,提供了有益路径。具体表现为:一是墨家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影响;二是共产党人对于墨家思想的扬弃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意义;三是墨家思想、墨家精神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具体表征;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墨家思想与时俱进的价值意义。
墨家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影响,体现在社会历史、内容结构、思想观念和人物事件中,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加以理解:(1)历史维度:历史进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涉及清末民初、五四时期、延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等时间范畴;(2)主体思想观念维度:墨家思想观念与马克思主义观念的会通与融合,其民主、科学因素以及人民性、实践性、科学性特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3)人物事件:墨家思想对共产党人(部分典型代表)的影响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作用。
一是历史进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清末民初,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西方理论学说[2]与骤然勃兴的墨家思想的初步会通、融合,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奠定了一些基础条件。早期,马克思主义作为“舶来品”进入华人视野比较零星、模糊,经格义而触类比量、与古典文化交汇,出现了“墨学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同论”③“墨家平民观(农与工肆之人)与马克思主义人民观(被剥削、被压迫者)相暗合”。五四时期,十月革命曙光照亮了进步知识分子的内心,不断传入的马克思主义于“黜儒尊墨”的思想文化与学术氛围中,渐被接受。墨家思想作为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路径,既得到不断新解阐发,亦使得墨、马二者融通契合。一批共产主义者一方面高扬身体力行、苦行救世的墨家精神,另一方面知行于革命实践中④。延安时期,墨家之伦理精神、朴素唯物主义和民主主义等思想得到了深入而广泛研究,其中的唯物主义成分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重要思想资源,其对延安精神的形成和党风廉政建设产生重要影响,墨家思想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达到相当高的水准。新中国成立以来,墨家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社会的发展亦发挥着作用和影响。起初,其与政治关系密切,融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意识形态中,而后是“实践论”(三表法)、“民本观”(尚贤义政)、“和谐观”(兼爱非攻)、“经济伦理”(交相利)等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文化养分,作用于社会主义建设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
二是墨家主体思想观念与马克思主义相类相通。为劳动大众代言的墨子,所开创之墨学与马克思主义有着许多类似和相通之处。基于对人类历史的考察可以发现,东西方哲人们都以不同形式思忖普遍的共性问题。墨、马都有一个基本的预设立场:“农与工肆之人”的墨家与“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都代表社会下层劳动群众的普遍意愿,维护劳动者的正当权益,表达天下百姓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诉求。墨家倡行的“兼爱”“赖其力则生,不赖其力则不生”“余力相劳,余财相分”“兼以易别”分别与马克思主义中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学说中按劳分配、人人劳动的理念,人人互助、财产公有的平等精神,消灭剥削和私有制等内容类同。墨家同情并重视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倡行“兼相爱,交相利”,马克思关怀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剥削者的疾苦和利益,前者关注、重视自我之利(兴利以满足生存发展)、天下利(利天地人),后者重视个人在生存和发展中应有之利、人类之利。墨家思想蕴含的朴素辩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有类似之处,后来“唯物史观”墨学研究成为学界一大趋势。《墨子》中载录的科技知识与尚贤兼爱思想,蕴含着科学(science)、民主(democracy)因子,成为连接中西文化的重要纽带:“尚贤”“兼爱”之中暗含“平民主义、庶民主义”因子和民主思想元素,意在使社会下层劳动者获得解放,成为国家的主人(天民),享有应有之社会地位;《墨辩》中的自然科学和逻辑学思想,与“西学”更为相近,其所提及的数学、物理学和逻辑学思想多与近代科学相暗合。于墨家思想中所表现出一种深刻的人民性、实践性和理论性,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质相吻合。以“兼爱非攻”反对攻伐,除天下害而兴天下利,为民创生良性的生存发展环境;主张尚贤使能,实现“官无常贵,民无常贱”的人民主权地位;倡行交相利而节用(加费而不加于民则止),既让“寒者得衣,饥者得食,劳者得息”,又保障民众合理的利益。这些兼爱兼利天下的思想观念,体现了人民性特质。墨家从“本、原、用”的经验立场出发,强调知行的标准在于契合“古圣王之事”(历史经验)、“百姓耳目之实”(民生实际)、“发以为刑政,观其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实际效用),总结出历史经验(间接性)、实际检验(百姓的直接经验)和实际效果相结合的检验原则,具有实践论特质。《墨经》中“墨辩逻辑”(如名实、推类等)和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展现了古人独特的心智活动与认知方式,表达了重理性、遵逻辑的一面。这三种思想特质,与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观、实践论、科学性具有相类之处,促进了墨、马相通融贯。
三是墨家思想对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共产党人向来注重吸收借鉴传统文化,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一些共产党人在宣扬墨家政治、社会、文化价值的同时,自身思想观念和道德品质亦受到墨学及墨家精神的熏陶影响。墨家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初入中国及其早期传播中,促进认知西方文化和认同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一些共产党人和党的理论家的思想学说体系中,不同程度地吸收借鉴墨家思想。特别是在延安时期,党的领导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还对墨学进行了较为细致和独到的探讨,其研究成果对于加强党的建设以及助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者,李大钊认为新事物必然能够战胜旧事物。这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虽不可等同,但足可说明学人吸收墨家朴素辩证法思想因素,以深度研究辩证法。蔡和森由墨家接受马克思主义、深受墨家精神影响。萧楚女、邓中夏等人高扬并身体力行墨家苦行救世精神,投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延安之际,毛泽东、张闻天、陈伯达、艾思奇、范文澜、郭沫若、侯外庐、吕振羽、翦伯赞等共产党人以唯物史观为指引,详细而深入考究墨家伦理精神、朴素唯物主义等思想,总结出其唯物主义成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重要思想资源。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党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风貌和延安精神的形成与墨家思想、墨家精神密切关联。这种关联既包含对共产党人的深刻影响,亦作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青年毛泽东注重劳动、讲勤苦、求实效的思想观念,与墨家主张的“力”(劳动、实践)、“强”“兴利除害”等思想相一致。可见,作为传统文化主体结构之一的墨家思想,不仅成为共产党人认知、接纳、阐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古典思想文化沃土和伦理基础,更磨炼着共产党人思想理念、人格品质和身体实践,为认同、接受、发扬马克思主义和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精神动力。
显然,墨家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文化土壤和理论基础。在东西方文化碰撞冲突之中,墨家思想以其主体“十论”、民主、科学因素和人民性(平民性和民本性)、实践性、科学性等思想特质与马克思主义贯通融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墨家思想以不同形式作用于思想—实践、人物—事件之中,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提供文化沃土。同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发展和丰富,使得墨家思想的研究发生历史性变革,促进了墨家思想的现代化转向。
二、墨家思想的现代化转向
在思想—实践的历史进程中,墨家思想步入了古今对照、中西贯通的现代化转向。在这种现代化转向中,既有西学的介入,亦有自身的转型。既包括古今研究范式变革的墨学现代化,也包括问题视角的时代研究,共同促进了墨家思想可持续发展。于此,范式之变革的“古墨学——今墨学(新墨学)”和创诠法、适应性之生命力的“墨家——(现代)新墨家”就应机随缘而生。

对此,可简约回顾一下墨学研究的历程。乾嘉至晚清,主要是《墨子》文本的重新发现与整理时期,该时期以传统小学研究为主,特别是孙诒让《墨子间诂》这奠基之作,使得《墨子》文本“厘然复其旧观”“尽还旧观”。从中华民国建立至五四时期,是《墨子》价值的重新发现与诠释时期,主要是援西入中,从考据之学(以校注为主)转向义理之学(以诠释为主),出现“国人家传户诵,人人言墨”的复兴盛况。20世纪30至60年代,墨学研究全面展开,学术理论“更专业化、更精细审慎、更踏实沉稳”,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尤其是《墨辩》《墨经》之复兴。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重新启动的墨学研究得以进一步深化,凸显现代化和国际化趋势。
纵观近代以来,国家之现代化很大程度上与外部影响有关。于此,援西入中、融合中西是传统学术在近现代的基本发展趋势,即所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见王国维先生《观堂别集》国学丛刊序)。从中不难看出,以儒家为核心的经学在遭到批评和冲突(原因是儒家缺乏“民主”“科学”元素)的同时,亦进行着自身的现代性改造和发展;而且子学与西学的融合更促进着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诸如老庄之“自由”、墨家之兼爱平等科学、名家之逻辑,都与西方现代主张相类。循着这个角度,我们重点考察从“显学”到“绝学”再到“复兴”之墨学研究及其对传统学术现代化的影响,可以发现复兴之墨学起初不仅与西方思想相会通,更有甚者坚持“墨学西源说”。此中真意,实乃以西学体系为参照的墨学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乃是由其研究方法的现代化所致。西学的注入和西方治学方法的引入是墨学发展的重要动因。在自觉或不自觉的借鉴中,促进了墨家思想自身及其研究范式的现代化,具体表征为:(1)借助西学知识体系,先秦墨学中长期隐晦难解的内容被初步揭示出来,并与现代精神相融合。诸如墨家之自然科学知识、朴素民主思想和逻辑学思想的显现,都得力于转型时期的墨学研究。(2)西学为镜,墨家思想体系结构被赋予了现代特征。传统墨学的思想体系带有古典学术的综合性特征,其虽没有分门别类,但也受到了正统儒学的限制。现代之研究则参照西方学术体系对《墨子》进行分门别类阐释,并揭示不同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极大地丰富了墨学的思想内涵。(3)墨学不再是经学的附庸,而是成为一门独立的、专门的、系统的学问,构成了中国近代乃至现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现代性趋势,使得墨家思想与西方思想文化“遭遇”(碰撞)更加剧烈。不仅墨家思想研究现代性更深入,而且西方思想本土化更明显,其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墨家思想文化现代化就是典型。它们相伴相随,彼此之间萃取思想精华,实现自身的与时俱进。
于此,墨学不仅有了“征易”的现代性特质,而且有了在“西方”“西学”体系介入下的“状变”。可以说,这种现代化在于其研究范式转化,典型标志是古今范式的分野⑤;治墨者大致可分为两种范式和三种定向。墨家思想历经了“传统”与“变革”相互交替的范式,“传统”即古墨学、朴学,“变革”即新墨学、解释学。在这种范式转变的历程中,大致可分为三种定向,即古典朴学研究模式、墨学发微模式、新墨学(家)模式。它们涉及考据、义理、墨学史、元墨学⑥等研究。当中墨学的现代性改造占据了主导,成为墨家思想现代化的重要阵地。且在学问的生命(墨学自身内因发展)和时代的生命(全球化外因作用)的视域下,以墨家之时代精神价值、现代应用伦理和学术交流合作表征的墨家思想研究进一步现代化[4]。
墨学的这种现代化,促成了一个有别于古墨学但又本于它的“现代新墨学”(区别于近代复兴之墨学)发轫。这种墨家思想文化的创造性、创新性转化发展,是文化繁盛的时代要求。学界有儒学—新儒学、道学—新道学之研究热潮,而对墨学—新墨学的研精阐微可谓少有问津。无论是在“易本原、道本根、儒主干”的思想分野中,还是处于儒释道三家互济的文化结构中,墨学、墨家都是被忽视的对象。其根源在于两千多年历史文化中“显学”变“绝学”的中衰现象和不被统治者接纳的“冷宫”遭遇。但思想文化传承发展的断裂(表层、现象上的断裂)并不意味着其价值的“香消玉殒”,千年中绝的墨学与近现代史上的“重光”“复兴”,已然确证了其不息的生命力和时代适应性。实质而论,墨家仍旧潜藏着现代社会所需之理论资源和价值宝库,诸如兼爱互利之人文精神与《墨经》之科学理性精神,以“十论”为核心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现代化价值理念以及和平主义、整体主义、平等主义的世界观,有待进一步现代性和建设性的理解、挖掘和继承。
基于这种建本开新的使命,学界一直在进行不懈努力。墨学研讨日渐繁盛,墨学基本问题得以有效解决,奠定了新墨学复兴之基,墨学研究成果不断丰富(丛书、专著、论文),墨家思想的现代性透视更加深入。这种以墨学为研究对象、以现代科学理论为工具、将墨学和时代需要相结合,日渐成为实现创立新墨学的目的。复兴成为当代一门“显学”,与以西方为参照系来讨论墨学、把墨家的观念学说当作印证西方的实例,或者证明西学在中国是“古而有之”的近代墨学复兴有着本质区别。现代新墨学是在开放、包容的学术氛围中,与中国传统文化其他方面(诸子百家)、西方文化交流对话,面向人类在当代社会生活所遭遇的普遍性问题,重新阐发墨家智慧。
长久以来,学界持有这样的论调:发轫于欧洲社会的民主制度和科学,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中并不存有二者的元素;进而推之以这种非民主性和反科学性,不能建构民主体系和独创现代工业化。并非中国文化中没有民主与科学因素,而是具有这些因素的墨家、名家等文化资源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作为传统文化结构中不可或缺的墨家思想,借以民主因素、科学特质和理性精神,可以助推中国现代化,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文化资源。科学发展的根基在于逻辑学与认识论(理性认知)。学界总结了“效”(效法)、“辟”(类比推理)、“侔”(直接推理)、“援”(间接推理)、“推”(归纳演义)等墨家逻辑认知体系。杨武金认为“墨学在根本上体现为一个从批判的武器即逻辑工具出发,构建了以兼爱思想为核心、以科学精神为引领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相契合的科学理论体系”。孙中原通过对《墨经》的分析,创造性诠释墨家具有现代价值的科学精神,包括“摹略万物之然”的实证原则、“所若而然”的方法思想,以及“巧传则求其故”的理论意识[5]。这些都显示了墨家迥异于重政治伦理而轻科学技术理论传统的科学性⑦,有力地回击了新儒家诸如牟宗三先生对于墨学复兴的嘲笑。墨家“兼爱”“尚贤”“尚同”表征的人本、博爱、平等、民主思想,具有走向民主的可能性。因此,出于儒而又异于儒、非于儒而又济于儒的墨家思想,以民主因素和科学元素为中国现代化助力,是可能的。
墨家思想的这种现代化转向,在于墨学研究与中国经济社会的密切关联。现代中国正处于走向工业化、商业化市场经济的转变时期,确立与之相应的价值观念、法理原则和基本公德是必要的。在面对全球话语问题上,不假外取而内求于传统文化,寻求相类似的观念作为根基,具有理论性、实践性的“兼相爱,交相利”墨家伦理就是不可忽视的宝贵资源。与此同时,在应对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灵与肉、文明与文明的冲突时,墨学中存在着有待进一步挖掘的文化资源,如“顺天志”“阴阳和”的生态之道,“兼爱、公义”的生态之德,“交相利”“节用”的生态之利,都是难能可贵的普遍原则[6]。在全球化进程中,墨学能够对接全球伦理,提供普世原则。以往我们只将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西方思想的“你们愿意别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别人”相提并论,却忽略了墨家思想的世界意义。区别于孔子“负”而“不伤害”主张和西方思想积极而“负”的教导,墨家之“兼爱、非攻、交利”提供了“柳暗花明”的新思路:既包含儒家“消极无伤原则”,又规避西方思想“潜隐地强加于人”。
可见,墨学的现代化必然要在古今中外的比较视野中显现。就连墨学现代化的开拓者梁启超、胡适等人,也不得不承认西方现代哲学对墨家思想的现代转化是有益的⑧。借用现代哲学来研究中国古代学术的会通之路,想要达到古墨学与现代哲学的“视域融合”,就应从社会实践的迫切需要和问题意识出发,观察、透视墨学,探索将其潜存之抽象普遍的文化价值和具体的文化价值转化为现实价值。这种继往开来、古今对照、中西合璧,实现墨学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墨家思想的生命力(可持续发展和永恒价值)的关键。在借鉴、借助西方现代哲学探究、解释墨家思想的同时,以墨家思想阐释现代西方哲学,得以寻求比较研究和方法论突破、解决时代课题和全球问题的古典方案。显学之墨家力主兴天下利除天下害,倡导超越时空、普遍平等的兼爱。墨家思想于全球化背景下,凸显出一种强劲的生命力,具体表征为在全球伦理(兼爱、非攻、交相利)、国学体系(新子学)等方面的价值意义。当今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问题,在墨家思想中都有其相对应的古典智慧和参考方案。可以说,从全新的视域和方法重新诠释和转化墨家思想,乃是一种必须。
为了实现墨家思想的可持续发展,志在复兴墨学的新墨家,对墨家文本进行现代解释,寻求回应现代问题的文化资源。拓展对《墨学》原典、文本的理解与释义空间,实现从“义理、辞章、考据”之校勘、训诂、音韵、翻译、“分门述学”到“意义-义理”的全新解读。新墨家大而全、小而细地对墨家的各种基本概念与学说的意义解析,厘清文本的原始意义和文字意义,说明作者意、文本意和精神意,进而在现代社会价值层次上创造性转换和引申,即从文字—文本—文化转化墨家有益于现代化的意义。这种类似于“五谓”创诠法⑨和语言分层理论的方法,可以促进墨学现代化。
但现代新墨学、新墨家,应注意到当前墨学之还原性研究(墨经校解、以墨解墨)、“旁观者研究”(墨子还原、以我论墨)、“现代性研究”(墨学与当代社会、以时论墨)潜隐的问题。在承认此三种研究范式有点的同时,不得不警醒可能走向的误区:还原性研究是开展墨学研究的基础和前提,但过于强调原意(以此为中心),则会自我设限,食古不化;旁观者研究提供了多维视野和参考价值,但过于个人立场化,则违背原文,失去墨学实质;现代性研究,凸显墨家思想的生命力,既能为时所用,又能传承文化,但过于实用,墨学则会工具化,牵强比附者影响墨家本来之健康发展。故墨家思想的可持续发展,应着眼于学问的生命和生命的学问,着眼于生命的认知和实践。以往墨学研究者,多将墨学视为“对象”“材料”(刻板的文本),治墨者与其对话就变成了思想者与文本间对话,此时墨家只得听“我”说。而后治墨者意识到墨家思想应值得尊重,将其视为“你”,开展了主体间(思想者与思想者)的对话。这种生命与生命(“他—你—我”)关系的交互,意在实现“文本—材料—义理—生命”的转向。
依此而论,墨家思想的生命力在于“人能弘道”。此与历史文化和社会事实存有一定矛盾性:世之显学的墨家,秦汉之后逐渐式微,几近湮没。在2000多年的历史传承中,治墨者可谓寥若晨星。于清代繁兴之前,仅有晋之鲁胜、唐之乐台等可考,真可谓名副其实的“绝学”。如此墨家之“道”又何传呢?基于中国哲学思想和传统文化结构性、整体性考察,可以发现表象上的墨家“绝学”,实则深刻影响着中国古代思想史发展和认知方式嬗变,其对儒家(孟荀)、道家(庄子)、法家(韩非子及其法术主张)思想和古代逻辑认知(名家及其名辨思潮)影响颇深。因为“任何学派的思想观念、哲学概念不仅会与其共存的其他学派的哲学发生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关系,而且还会同其之前和之后的哲学观念发生沿袭与变革、吸收和剔除的相互关系”。从“道待人传”到“道乃心传”的学术生命力和思想发展视域看,即便是赴义蹈死、墨者自衰,墨家所创新的思想文化和价值体系(类似于“道”)并未中绝,而是潜藏于民间和各家学说之中,一直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
三、墨家治道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耦合
国家治理,是人类社会长期发展历程中极为重要的议题。无论是传统治道,还是现代治理论,都是关涉治国安民的学说原理、普遍原则和根本方法。作为“务为治者”的墨家,主张“尚贤尚同、节用节葬、兼爱非攻、非乐非命、天志明鬼(人格象征)”,力求由乱而治实现天下治、天下利、国家富、刑政治(善政)、人民众、阴阳和。这不仅是传统治道思想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潜藏着内容丰富、结构完备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治理体系和古今对照、中西合璧的“尚贤—民主”“尚同—自由”“兼相爱交相利—理性经济人”“法仪—法治”的治理主张,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
政治上的尚贤、善政,社会伦理上的尚同、兼爱、公义和法仪,经济上的互惠交相利、兴利除害,思想文化上的非乐非命,生活意向上的节用节葬,价值保障上的顺天之意,展现了墨家丰富的治道思想资源和系统的治理结构(治理体系)。这种传统治道思想和治理体系的完整生命力不仅在于发挥了治国理政的历史作用,更在于能够推进当代国家治理实践。“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故而推进现代化全新维度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应“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适宜、合理、充分汲取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治道养分和国内外成熟的治理经验。作为传统治道思想之关键、东西文化之桥梁的墨家思想,与治理现代化密切关联,不仅可以提供政治尚贤、社会尚同、德行兼爱、交往互利的价值取向和时代启示,亦体现出深刻的人民性(天志、兼爱)、实践性(“三表法”和经验主义)、理论逻辑性(认知方式和科学性)思想特质。此乃墨家治道思想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耦合的理论资源,需要阐明二者的关联处与契合点(包括治理目标、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显扬墨家治国理念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哲学启示和积极价值。
目标导向与价值定位,是国家治理的关键所在。其不仅是国家治理的起点,亦是国家治理的归结点,更是关乎贯穿国家治理起点到归宿全过程的精神动力。一般认为,经济繁荣、技术发展、人民幸福、公民文明以及国力强盛,是国家现代化给人的基本印象。这也恰好是国家治理的目标价值所在。国家治理的理想状态,就是“善治”。墨家开宗明义地强调“察乱之起”而治,实现天下治、国家治、刑政治、乡(邑)治。这种“善治”包含两个层次,即横向上的“十论”所确立的治理目标和纵向上的立体治理价值。在横向上,墨家对于当时之政治实践、社会实存、经济发展、环境问题、文化导向进行了深刻的哲学反思,提出了“择务而治”的“十论”来治理国家各个方面的问题。政治上尚贤、义政以实现“官无常贵,民无常贱”的“善政”,与今之民主民本理念相类;社会伦理上兼爱、公义、法仪,与今之德治、法治、正义思想取向相通;经济利益上兴利除害、节用节葬,与今之可持续发展、生态消费根本目的相符;精神文化上非命、非乐,与今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实质相同;人天关系上,尊天(客观)事鬼(道德因果),与今之尊重自然、顺从自然、利用自然的生态伦理观内涵相符。在纵向立体价值上,在天之整体层次上,以“天邑”、“天民(臣)”观念引导“非攻—和谐”“守御—安全”(类似于今之全球治理取向);在国家层次上,以“十论”“择务而治”,实现天下治,天下利,国家治、国家富、社稷安;在政府层次上,“赏贤罚暴”,官长各从其事,实现“刑政治”和义者之“善政”;在社会层次,坚持“爱、义、利”统一,使君臣父子兄弟等交互主体间兼爱互利而和谐;在百姓层次上,“爱利百姓”根治“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使其“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从而实现“人民众”(富、贵)和“百姓安”。墨家所确立的这些横向、纵向综合目标和价值体系,与当今国家治理现代化“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和全球治理“共存共荣”的目标存有相同之处,可以为当代国家治理的提供借鉴。
国家治理的本质表征,在于“治理目的、过程、体系、结构和制度”中。可见,国家治理是系统工程,必须通过系统思维,进行结构性、整体性地理解。欲实现天下善治,就应建构与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众意愿相协调一致的治理体系。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关键内容的治理体系现代化,乃是基于历史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渐进、改进、内生演化的结果”。倡导“十论”治国的墨家思想,建构了系统完备、结构清晰的治道体系,将有利于深刻理解古典治道传统与治理特色,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文化养分。墨家的治国方案,在政治上主张贤能政治和义政,实现“善政”;在社会伦理上强调“尚同”为要,推崇兼爱、公义与法仪;在经济利益上倡导“交相利”原则,发展“天下利”,以利于“天、地、人”;在精神生活上力主“非命非乐”,构建“力”“强”“安—足—节—和”的生活理念;在人天(人与自然)关系上突出人格意义、符号象征之“天志”的监督和赏善罚暴功能,建构利于“天、地、人”整体生态价值和道德因果保障。以法治、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特质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同样也包含了“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结构体系。传统治理体系与“五位一体”的制度体系,虽然在内容上存有差别,但其中亦有相同的形式与原则。具体表征为政治上“尚贤—民主、义政—民本”,社会上“兼爱—德治、法仪—法治、公义—正义”,经济上“兴利除害—可持续发展、节用—生态消费”,精神文化上“非乐—艰苦奋斗、非命—自力更生”,生态上“天志—生态之道”。此外,从天之兼性、整体性、平等性出发,主张“非攻”而国家间和谐,强调“国之备、守御”而国家间安全,这与当代呼吁共存共荣的全球治理体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是内在一致的。
国家治理乃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治理主体(人民)按照法律法规政策处理国家事务和社会问题,从而实现特定价值目的的社会活动。这种实践性表征出:无论是“天下治”的善治目标,还是“尚贤义政、尚同兼爱公义法仪、交相利兴利除害节用、非乐非命、天志明鬼(人格象征)”式“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治理体系,运行而有效,方显价值意义。这就关乎国家运用治理体系治理国家的能力,即国家治理能力。墨家思想的“力”“强”“行”,要求的不仅是为政者(天子、诸侯、士君子、乡长)或官长、正长),更有“农与工肆之人”(这些普通民众在墨家贤能政治架构中,他们可以参政)。因为在墨家那里,他们都是天下善治的主体,都必须“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尊天(法)事鬼(道德因果)”,实现天下治、天下利、天下和,这就是墨家对国家治理能力的强化。特别是对于“士虽有学”的为政者(公权代理者)而言,“行为本”应用“十论”所确立的治理体系,既要“择务而治”国家之“昏乱”“贫弱”“憙音湛湎”“淫僻无礼”[7],又要“察乱之起”而“兼”(全面、整体)治。这种专项治理与统筹兼顾的综合能力就被凸显出来。墨家认为,贤能既是为政之本,更是治理能力的关键所在。因为力强则治、力强则富、力强则贵、力强则众,反之则乱、贫、贱、寡。在治理能力提升上,墨家主张“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按照才能类型和处理信息能力大小来授予官爵,要求恪尽职守(“早朝晚退、听狱治讼、收敛关税”)兢兢业业、利国利民,做到修身为本(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
四、结语
概言之,“轴心时代”的古典智慧考量着人类社会的基本问题,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当代经济社会发展。我们现在所能想到的,无不是以往的哲学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思忖探究过的。“墨之至者”墨子以其平民思想家、军事战略家、古代科学家的崇高地位和其墨家思想中的民本性、和谐性、兼爱性、互利性、生态性、人文性、科学性等特质,表现出永恒的生命力。在文字—文本—文化—文明的整体性学问生命中,古今对照、中西合璧的“返本开新”,方显墨学现代化和墨家思想可持续发展的愿景。墨家思想作为国家治理哲学(治道思想),是一种“实然—应然—理论”的理性反思和哲学建构。这种治道思想,不仅可与现代治理思想、中国社会现实(social fact)内在衔接,而且能为中西治道思想合璧、古今治理思想-实践对照奠定文化基础。
注释:
① 这便是韦伯所论述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以及主流的中国文化缺乏那种精神(韦伯命题)。但被传统文化长期忽视的墨家思想中的类似于西方清教徒的内容:强调兴利除害、强本节用(节葬)、力强则富贵治平,是推进中国现代化不可或缺的经济伦理资源。
② 《墨辩》中的自然科学和逻辑学思想,与“西学”更为相近,是“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其所倡言的数学、物理学和逻辑学思想多与近代科学相暗合。
③ 严复以为“至于墨道,则所谓社会主义”(王拭:《严复集》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57页)。梁启超以为“墨子之政术,非国家主义,而世界主义社会主义也”“墨子之生计学,以劳力为生产独一无二之要素,其根本概念,与今世社会主义派别所持殆全合”。(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7页。)
④ 陈独秀、李大钊援墨批儒,为时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和有利的学术环境。蔡和森由墨而入马克思主义,既强调墨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融通与契合,亦对墨学进行了发挥和阐扬。萧楚女、邓中夏等人高扬并身体力行墨家的苦行救世精神,投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
⑤ 所谓古今分野是指新旧墨学研究范式的转化。公元前5世纪墨学产生,到20世纪初孙诒让《墨子间诂》定本刊行,历经两千多年的墨学研究,归入古墨学、旧墨学阶段。20世纪初近现代以来,由梁启超、胡适领军的墨学研究,呈现崭新的范式,用现代语言和科学方法,古今中外融会贯通,在继续提高《墨子》文献校勘训诂、资料整理水平的基础上,阐发墨学深层义理。把这一时期的墨学研究归入今墨学、新墨学的阶段。(孙中原:《古今转型 中西合璧——墨学的持续发展和比较研究》,《职大学报》2011年第04期。)
⑥ 元墨学是墨学的元研究,是现代学者对墨学的超越和整体研究。孙中原先生从研究主体、主题、成果、形态、语言、层次、方法等层面揭示了古今墨学的元性质:主体(先秦墨家—现代学者)、主题(战国课题的墨学应对—现代课题的墨学借镜)、成果(战国课题的墨学答案—现代课题的墨学镜鉴)、形态(古墨学论著—今墨学论著)、语言(古代语言—现代语言)、层次(第一层次元研究—第二层次元研究)、方法(古代哲学方法—现代哲学方法)。(孙中原:《古今转型 中西合璧——墨学的持续发展和比较研究》,《职大学报》2011年第04期;孙中原:《墨学现代化、新墨学和元墨学》,《哲学研究》2006年第1期。)
⑦ 孙中原先生认为“这就是一部古代缩微的百科全书,以浓缩的形式,有意识地进行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的建构”。《墨经》的科学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重政治伦理实践、轻自然科学技术理论的倾向大相径庭,而与古希腊哲学家重视探索自然奥秘的科学精神酷似。
⑧ 只有那些在比较研究中有类似经验的人,才能真正领会西方哲学在帮助我解释中国古代思想体系时的价值。(胡适:《先秦名学史》,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⑨ 傅伟勋创造性诠释学分层法:(1)实谓:原典实际上说什么,原典校勘考证,提供真实可靠材料。(2)意谓:原思想家想要表达的真正意思,原典训诂、语义分析。(3)蕴谓:原典思想的深层义理、多层诠释学蕴涵。(4)当谓:原思想家应当说的,原思想体系表面结构的深层结构,创造的诠释学者为原思想家说出应当说的。(5)创谓:为解决原思想家未完课题,现在须创新地说什么,从批判继承者转化为创造发展者,救活原有思想,消解原有思想内在矛盾难题,突破创新,为原思想家完成创造性课题,从事中外思想传统对谈、交流,培养创新力量。(傅伟勋:《学问的生命与生命的学问》,南京:正中书局,1998年版,第228-240页。)
⑩ 朱传棨先生认为“墨家学说的精神影响着主流学派。应该看到孟子‘性善论’及民本思想受到了墨子《天志》中‘天民’思想、《尚贤》中‘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哲学认识论上,墨子思想的影响更为深远。墨家‘三表法’中强调经验对于检验认识真理的重要性,在此之后荀子的‘符验’、韩非子的‘参验’到汉代扬雄的‘有验’和王充的‘效验’、‘证验’,乃至宋代以后的‘有验’思想,均受墨家‘三表法’的深刻影响”。(张清俐:《在现代视域中重新发现墨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5月刊。)
——评《中国现代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