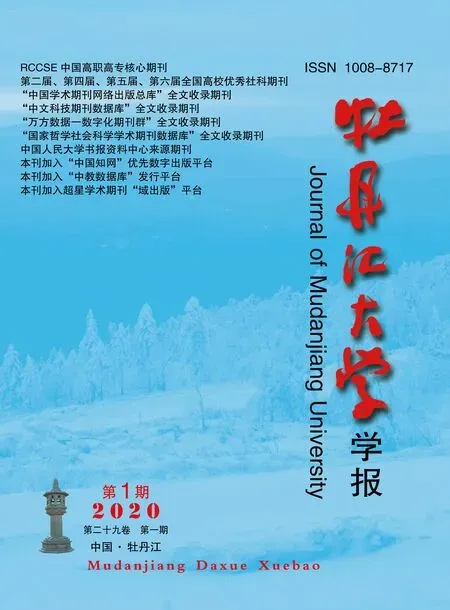无法逃脱的罪恶与救赎
——试析王十月《人罪》的底层叙事视野
张建华
(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榆林学院文学院,陕西 榆林 719000)
王十月的作品被许多评论家称为“打工文学”,[1]因为他没有站在道德和文明的高度俯视底层群体的生命进程,而是零距离描述他们的悲欢离合、风云变幻。但是,王十月创作又不能仅仅以“打工文学”一言蔽之,因为他的叙事视野是宽阔的,是超越“密室写作”的“旷野写作”[2]。这种视野兼具叩击现实的勇气和悲天悯人的情怀,且意图以每一个人都无法逃离的命运意象向人们传达一种信念——“希望点亮那复活的小小的火”,亦即希望在悲凉的人世浮绘图上留下一抹温暖的亮色。谢有顺先生指出:“一个作家,如果没有对现实境遇的卷入和挺进,就意味着他未曾完成对存在的领会。存在是最大的现实。看到了这一点就知道,把王十月的写作简单地归结为打工文学或者底层文学,其实并不合身。他的确关注了属于他的那一部分现实,但通过这一渺小的路径,王十月要探查的,还是现实背后的那些人生,有着怎样的黑暗和亮色。”[3]许相全先生认为,在当前“底层文学”处于僵化停滞的时期,将底层文学置于更高的维度进行考量是一个必要的举措。并且指出,当前学者把底层叙事特征大致分解为三个层面,即:谁说,说谁,如何说。[4]这正是《人罪》通过其底层叙事视野着力要表现的内容。
一、底层人物
一个作家,目光所及,其实就是他心灵关怀所指。王十月的目光始终是指向底层的,从这个维度切入,我们把王十月的作品称为“底层叙事的舞蹈”应当是可行的。
《人罪》一如既往地关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他们是无言的,沉默的,但是他们的命运书写却是庞大的。这里有生活困顿不得不依靠摆地摊谋生的小贩陈责我,有出身贫寒靠个人奋斗进入城管队伍的吴用,有冒名顶替多年来一直被罪恶感压迫的法官陈责我。这里的每一个形象都并非完美,但一定是立体的。他们都被命运的鞭子不停地抽打着,被岁月的风霜不住地侵蚀着,在不知名力量的播弄之下痛苦不堪。一切看似不平,一切却又顺理成章。
法官陈责我是一个回乡知青的后代,其母陈春梅在当年上山下乡的革命浪潮中被命运之手裹挟到农村,满怀激情地嫁给一个当地的农民,以表达自己的革命决心。可是,在“后来的漫长岁月中,陈春梅的人生目标就是逃离农村。她对农村的反感,就像当初她对农村的热爱一样真切而炽热。……离婚在那个时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于是,陈春梅渐渐接受了这人生的现实,将梦想寄托在儿子赵城身上”。[5]从兹可知,生在农村的赵城——也就是后来的法官陈责我从小就知道,他是肩负着读书上大学做城里人的重任的。这实际是法官陈责我和小贩陈责我命运对调的直接原因,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一系列的故事,改写了县一中校长陈庚银、真假陈责我以及杜梅和孩子、吴用等人的命运轨迹。赵城读书很用功,且在他舅舅陈赓银掌管的学校学习,自然更受关爱。可是他上高二时,其母陈春梅得了严重的肺病,吐血很厉害,这让他无法安心读书,因此高考落榜。陈赓银因为担心妹妹的病情,所以做了手脚,扣留了乡下孩子陈责我的录取通知书,将自己的外甥赵城更名换姓送进了大学。这就是故事的开端,也是悲剧的引子。法官陈责我接受了城市的召唤,同时也拉开了这出大戏的帷幕。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不是十恶不赦的角色,但是他们通通被这一事件牵绊其中无法自拔。正如王十月自己在《人罪》后的创作谈里所说:“《人罪》中,每一个人最后都无路可逃。”[6]法官陈责我因为内疚,上大学后不敢谈恋爱,不敢跟外界过多接触,唯有埋头读书以赎回自己真正的尊严。他如愿以偿考上了法学研究生,毕业后成了一个克己奉公秉公执法的好法官。而舅舅陈赓银更是一个一身正气、成就了许多乡下孩子梦想的好教师好领导,被众多学生深深爱戴和尊敬。但是人可能就一个不经意的错误会毁灭其一世英名。随着时间推移,外甥赵城狸猫换太子之事在老校长心头慢慢隐去,可偏偏小贩陈责我无意之中刺杀了同样出身微贱的城管吴用,且法院正巧让法官陈责我主审此案,这就将一桩沉埋多年的隐情挖掘了出来。法官陈责我将这件事告诉陈赓银之后,老人顿时“手心里全是汗水,胳膊软得提不起一丝劲,两条腿也发软”,然后他去了三十里外的青山镇——小贩陈责我的老家,在那里他看见了家徒四壁的陈责我旧居,乡邻们也纷纷为陈责我辩护,且有一个邻居很神秘地告诉他当年陈责我被人顶替的传闻,这无疑像在陈赓银的心上狠狠抽了一鞭,将他的内疚和自责逼到了死角。陈赓银从青山镇回来首先找到现任校长——他的学生,且是他一手提拔的同僚,替小贩陈责我的儿子陈一飞办了头等奖学金8000元,然后让另一个学生——李总包揽了陈一飞的上大学费用。这样他“心里的不安又减了三成”。
再说小贩陈责我。他高考落榜(被法官陈责我调包)后做过木匠并因此患了慢性苯中毒,再无法从事这一职业。他有一儿一女,儿子读书跟当年的他一样出色,为了不让儿子过早辍学,他买了辆三轮车批发水果,与妻子在城区零售,可是得提防城管,“好不容易赚点钱,被抓一次,一个月就算是白干了”。这种形势逼迫他们不得不跟城管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不得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城管要强行没收他赖以为生的三轮车,在冲突过程中,陈责我被一个协管员用钢管打破了头,三轮车自然被没收了。他数次讨要未果,并且“在案发前两天,曾到城管队讨要他的三轮车,遭到了城管队员的羞辱,几个城管队员轮流扇了他耳光,还将他绑在烈日下晒了一个小时,并扬言让他滚出这城市,否则见一次打一次”。陈责我从小安分守己,读书好学,即便穷困不堪也舍得给卖艺的可怜兄妹捐一笔“巨款”,半辈子老实巴交,连鸡都不敢杀。可在这次事件中,他却作出了让人难以理解的举动——举起手中的水果刀偷袭了城管吴用并使其毙命。尽管他本意并没想致人于死地,因为“据他交代,他只想扎一刀就跑”,但事实上他把自己和儿女以及吴用可怜的母亲和怀孕的女朋友推向了不见底的深渊。
吴用也是出身社会底层,有一个摆地摊供其读完大学的母亲。他靠自己的努力当上了城管,居于“城管阶级”中间一层,本无须去街上与小贩们斗智斗勇,且有其母的小贩经历在先,他实际上从内心是同情小贩的,因此要求那些“临时城管”应当“文明执法”。这却招来那些粗暴执法的临时城管们的讥刺甚至起哄。在此情形下,他被迫上街执法,试图用自己的方式“讲道理”,可是在小贩们的无情嘲弄下,他失去了耐心,指挥临时城管“暴力执法”,从而引火烧身,失去生命,将可怜的母亲和有孕在身准备马上结婚的女友丢在了冰冷的尘世。
从小说看去,这些人没有一个是歪瓜裂枣,都是本心善良愿意安分守己只求一生平安的普通百姓,可是生活如同一个巨大的漩涡,每一个人都身不由己被卷入其中,只能对某些血腥保持沉默或者共同维护一个谎言。这就是王十月对底层人物形象的诠释。
二、底层精神
何谓底层精神?借用李环宇的话说:“底层精神指城市底层人物的灰色形象及其悲剧性,而这种悲剧性又通过城市底层人物寓言式的自我救赎,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7]究其实质就是通过描述底层人物的悲剧命运来彰显小人物在苦难中表现出的最可贵的宽容、善良、坚韧等特性。在这一点上,王十月的表现无可非议,因为他本身曾经是这些底层人物的一分子,切身体会过他们的艰难与苦寒,所以他对这些底层人物精神的把握是精准而透彻的,常常令人血脉偾张无法自已。
一个陈责我出场而千万个陈责我在苦难的生命途程中哭泣哀号的情景被写得纤毫毕现。这就是王十月刻意表现的底层精神的张力。王十月在《人罪》里如是说:“法官陈责我站在窗边,深吸了一口烟,看着窗外,窗外是热闹而繁华的都市,阳光耀眼,他站在阴凉的办公室看着外面的世界。他知道,此刻,就在下面的街道上,还有无数小贩陈责我、打工仔陈责我、农民工陈责我……他们在街头讨生活,在工厂的流水线上讨生活,在建筑工地上挥汗如雨讨生活……而他,法官陈责我,却站在这蓝色的玻璃幕墙后面,吹着空调吸着烟,如同看一个与己无关的世界一样,看着这苦难众生。法官陈责我内心涌起了不安。他也是农民的儿子,许多年前,若不是一纸录取通知书将他送进了大学,然后考研,现在,他将是那烈日下苦难众生中的一员。”这一段议论,正是法官以及其他处于审判者地位的陈责我们的良心嘶鸣。
无论是因公无辜丧命的吴用,还是悲愤之下无意中杀人的小贩陈责我,他们无疑都是善良而隐忍的。虽然身处社会底层,他们并没有因此堕落,依旧恪守自己的道德底线,对社会和他人寄予的,仍然是同情悲悯,而非刻骨仇恨。这种底层精神,是比金子还珍贵的品格,是灰暗生命中一星半点的亮光。也是王十月在所有的打工文学作品中一再凸显的基因。
吴用在当了城管之后,并没有沾沾自喜,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母亲也是靠摆地摊供自己读书的。他当了城管,母亲很高兴地说:“再也不用怕城管抓了,因为我们家就出了一个城管。”吴用发脾气了,觉得自己当城管母亲当小贩很“吊诡”;觉得自己工资不低,父亲又有一份收入,劝母亲再别去摆地摊,母亲却坚持要为儿子再奉献一些余热。吴用生气了,说母亲这样让自己很没面子。母亲“沉默了许久”,终于答应儿子不再摆地摊。当其母不再出摊,吴用“心里却难受了”。作者用这一细节突出吴用内心疼爱母亲、知恩图报的品质。小贩陈责我在冲动之下挥刀刺向吴用,本是尊严屡次被践踏后的泄愤行为,但是阴差阳错,吴用因他一刺而命丧黄泉,他立马被推上了道德和法律的审判台。小说在处理陈责我认罪伏法的过程中有一些合情合理的变化,一开始,“他并没有表现出积极的认罪态度,而是认为城管该杀。当他得知被害人是刚毕业的大学生,特别是得知被害人的母亲也曾经是小贩后,他蹲在地上嚎啕大哭。他在受审时并未提及自己被众城管扇耳光晒太阳羞辱的细节,甚至在律师韦工之一再表示愿意为他做死缓辩护时再三声明:“现在他每一天都活得很痛苦,一想到那个被他杀死的孩子他就想死。”韦工之有意提醒他,主审他案件的法官也叫陈责我,并且跟他是一个县一年参加高考的,暗示他回想当年高中是否有两个叫陈责我的学生,小说写道:“据我所知,你当时读高中时是班上的尖子生,结果却连普通大学都没有考上。如果你当时考上了,你的人生将从此不同。韦工之相信,这样的暗示,足以让小贩陈责我抓到救命稻草。但是小贩陈责我却摇了摇头,说他当时没考好,这是命。”这一段描述不动声色地将小贩陈责我的精神境界抬高到了令人仰视的地步,没有狡诈,没有疑虑,事出有因,其情可悯。人性之善,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让人不禁为小贩陈责我放声一哭。
其他围绕这一事件展开的人物,虽非严格意义上的底层群体,但是其精神指向是偏向底层社会的。他们同情身处重重碾压中的下层百姓,关心他们的疾苦,能够竭力为他们的立场摇旗呐喊。法官陈责我的妻子、报社主任杜梅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她出身较好,因为职业关系一直抱有极高的正义感和使命感。故事的结尾,杜梅来到了小贩陈责我的坟头,“坟头已长出了鲜嫩的苦艾,站在他的坟前,她深深地弯下了腰。……她知道,她这辈子都无法赎清自己的罪”。这一场景,也将杜梅的形象升华为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完美女性,面对谎言和亲情,她只能选择保护亲情维持谎言,可是她为自己无法逃脱的罪责深深忏悔,真诚地逃离。这是一个更加光彩夺目的精神形象,这种精神更是有意义的,它是小贩陈责我生命的声援者,也是其苦难的见证者,它必将在引导人们为社会底层人民生命和尊严辩护的路上开放出炫美夺目的精神之花。
而舅舅陈赓银何尝不是一个对底层社会抱着关怀和同情,并且一直秉持着做人的良心的好人呢。只是,在一母同胞的妹妹软硬兼施下,他违心把自己外甥变成“陈责我”。起初他也担心过,并且屡次悄悄地观察那个真正的陈责我,发现“陈责我学了木匠,结了婚,小日子过得还成。于是,他心里就获得了安慰”。这里的陈赓银更是无辜的,一个无辜却无法逃脱的罪人。
王十月以客观冷静的笔调描写的底层群体无处不在的苦难,以及在苦难浸染中仍然坚强、温暖以及悲悯的底层精神,正是千万个陈责我身上所凸显的高贵品质。
三、底层叙事风格
谢有顺在《现实主义者王十月》中说:“这些年来,尖刻的、黑暗的、心狠手辣的写作很多,但我们却很难看到一种宽大、温暖并带着希望的写作。可见,作家的灵魂视野存在着很大的残缺”,“他身上所焕发出来的理想主义精神,常常令我心生敬意:他也写自己的经验,但他的心事,通向的往往是这个时代‘主要的真实’”。[8]他提倡我们这个时代应该有更多的有良知的作家象王十月一样书写“主要的真实”。陈思和说:“一个作家,充塞他的创作空间的,应当仅只是人类心灵深处从远古以来就存在的真实情感,这古老而至今遍在的心灵真理就是:爱、荣誉、同情、尊严、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如果没有了这些永恒的真实与真理,任何故事都将无非朝露,瞬息即逝。”[9]
王十月说,我写小说是为了赎罪,因为,我是一个罪人,我从没放过自己。他不但审视他人,也审视那个灵魂深处的自我,所以他看似淡然的作品就有了不一样的高度。
因为这一种视野的观照,王十月的作品呈现出活灵活现的生活本身,为他所熟悉和热爱的底层人民所写,且表现出一些固定的书写风格和技巧,《人罪》亦然。具体表现有三:
第一,口语化的语言风格。《人罪》是底层社会现状真实的描摹和临写,所以作者为这样的叙事场景设置了最平民化的叙述语言,首先,这种叙述语言可以更准确简练地描述事实,其次,这种语言范式也最容易为平民化风格的读者认知和喜爱。比如,描写陈赓银退休后子女接他们去北京享福,“他们去住了两个月,死活不住了,说受不了北京的空气”。描述杜梅第一次看见狱中的小贩陈责我时,王十月这样写:“他差不多就是一根呆木头,脸如死灰。”这里,“死活不住了”“呆木头”都是典型的劳动人民的语言,自然会为他们所喜闻乐见。陈赓银得知小贩陈责我杀人一事后马上去了陈责我的家乡,提及此事,一群乡民围着他为陈责我喊冤抱屈,一个老人说:“你是领导,能给法院说说么?陈责我是好人呢,打小就是好孩子,心软得很,鸡都未曾杀过,怎么就狠下心来杀人了?”另一个说:“还不是被逼的。你说他这样的人都杀人了,那得有多大的委屈。”这些语言,全是将生活原汁原味地再现笔端,使得整个文章平民意味十足。
第二,最贴近的读者群。“底层叙事”的主要读者群除了专业人士,还有文学爱好者以及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广大劳动者,而最可能被这种故事震撼和吸引的应当是劳动者。因为专业人士和文学爱好者们对于作品所描述的生活是“隔”着的,并不能全方位体验被生活盘剥和压榨的劳苦大众最深的苦楚和渴望,不能贴心窥探他们最隐秘最原始的心灵旅程,所以当王十月在《人罪》里毫不拖泥带水地将吴用以及小贩陈责我的处境再现给读者时,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引发这些最贴近读者的共鸣,从而使文学的社会功能得到更好的发挥和阐释。小说有一处详细描述小贩陈责我的外貌:“法官陈责我从卷宗中拿出小贩陈责我的照片,那照片是在预审时留下的。一张正面照,一张左侧照,一张右侧照,背景布上还标有身高”,“那是一个黑瘦的男人,眼窝深陷,胡子拉碴,看上去一点也不像四十岁的人,倒像是六十有余了”。这样一张充满苦难痕迹的脸,必定是王十月再熟悉不过的面孔,所以写来丝丝入扣,读起来才会令人动容。
第三,鲜明的矛盾冲突和巧合设置。《人罪》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叙述特征,就是在故事情节上有意为之的矛盾冲突设置。因为普通民众在阅读口味上更倾向于读大悲大喜、巧合立体的类似于古代拍案惊奇之类的故事,王十月在书写上显然照顾到了这一种阅读趋向。
具体而言,作者设置了几对主要矛盾体,即:被审判者和审判群体的对立,城管吴用和自己摆地摊为生的母亲的对立,以及小贩陈责我和法官陈责我的对立,城管吴用和小贩陈责我的对立,以及城管吴用和临时工们的对立。这些矛盾体的存在既很好地串联起故事使之脉络清晰,又用戏剧性的矛盾设置毫无悬念地抓住了特定的读者群体,使之怀有一睹为快的阅读期待。
就《人罪》而言,王十月的确是一个称职的作家,他并非精通结构的奥妙,因此其结构未免有松散或急缓不均的现象,但是他懂得尊重读者,重视读者的阅读心理,而非某些新生代作家没完没了地自我陶醉自我安慰的絮语和自以为是的卖弄笔法。这也许正是王十月的小说在众多“打工文学”中脱颖而出的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