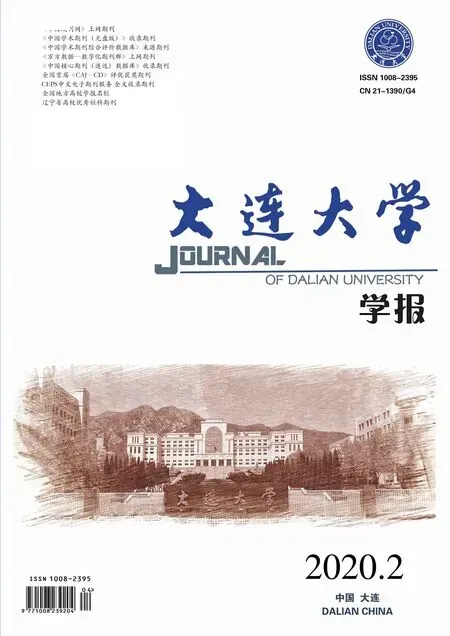《西游补》与禅宗“三境界”
高日晖,金田妮
(大连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622)
一、引 言
禅宗自达摩祖师传入中国,经历了六祖慧能的兴盛,唐宋时期的繁荣,发展到晚明时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一股力量,其思想对晚明社会文化影响体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政治上禅宗经过唐宋以来的发展演变,已逐渐成为士大夫面对社会现实矛盾时,一个有效的逃离之法,明清之际在文人士大夫中“弃儒入禅”之风盛行,并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和社会影响。其影响表现在思想上,禅宗对“心学”的影响极大,“心学”的创始人王阳明曾访问禅宗门派的50多个寺庙,认为心学的核心理论“心即理”“如佛家说心印相似”,进一步阐释“致良知”为“真圣门正法眼藏”,认为其精神与人人本有,在于内心觉悟的禅宗思想基本一致[1]。对书法与绘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审美导向上,更重视非理性,讲求直观体验,意在创设境界,突出艺术本位与创作者个人风格的协调一致性。禅宗对文学的影响具体表现在明末名著《西游记》上,小说中强调“心性”是修行的根本,整部小说实际上是围绕着孙悟空心性修炼的历程来叙述,孙悟空起初未识心性,从菩提老祖学来一身本领,便开始卖弄本事与天地争斗,铸成大错后被如来押于五行山下,直到唐僧将他解救出来,始是他明心见性的萌芽。西行路上,孙悟空的心性虽偶有迷茫,如在“真假美猴王”故事中,真假美猴王的出现则是贪图享乐和潜心修炼两种内心的矛盾挣扎。随着西天取经的功德圆满,孙悟空的心性修炼也达到了臻于完美的境界,最终修成正果,被封为斗战胜佛。自《西游记》始,神魔小说风靡一时,成为人们争相模仿的小说题材。神魔小说因其富有玄幻色彩的故事内容,更易于融入某些宗教观念,神魔小说《西游补》也不例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禅宗思想的影响,小说中的各种世界是孙悟空从心而发形成的幻境,其中主人公不断探索,悟其真性的心路历程,正与禅宗的三境界相契合。
二、禅宗“三境界”说
《五灯会元》卷十七中记载:“吉州青原惟信禅师,上堂: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大众,这三般见解是同是别?有人缁素得出,许汝亲见老僧”[2]。
禅宗青原惟信“三般见解”是表征“悟”的三个阶段,也就是揭示“悟入”过程的三种境界。“境界”一词本出自佛教用语,佛教境界指人的六根及其所对之对象,而境是其中最虚空的一个。作为人心的刹那逗留之地,它指心灵的某种非理性的状态,它是最直观或直觉的[3]。自青原惟信禅师提出这一理论后,学者们便广泛地认同了禅宗“三境界”的理念,许多佛教研究著作和论文都对此进行阐释和解读,并引用此理论进行相应学科的研究。目前来说,对“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这一理论的解释主要可分成两种趋向。一种是叶威廉先生《中西诗歌山水美感意识的演变》的观点,此观点是基于道家语言观背景而阐发的。尤以学者皮朝纲的研究最为突出。他认为禅宗三般见解是循序渐进的过程,是禅宗修炼开悟需要历经的必然过程,并引用了铃木大拙的“桶底破”理论来理解这三种境界,起初的“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只是以无智的素心对客观事物进行简单认知,随之悟道渐深,到达第二阶段,不再单一的接受所感知到的世界,而是从认识的哲学思维角度出发否定一切,寻找事物之间的联系与意义,在此之后的第三阶段,人的认识从意识心转变为智慧本身,便能处于自然山水之中却能展开超越自然山水之外的心境[4]。另一种是从纯粹禅悟的角度,对日本学者阿部郑雄所提观点的认同和证明。阿部郑雄认为第一阶段,山水之间既有肯定性又有区别性,以自我为中心,把山、水和其他一些事物与“我”区别开来,以无明心认识山水;第二阶段否定了第一阶段山水的二元对立,认为“万物皆空”;第三阶段是通过否定“无分别”而被认识到的“分别”,认识到自然山水的自主存在,不可得本身就是真我。这两种禅学解释中,赞同前者观点的人较多,如南怀瑾,傅邵良,萧丽华等[5],后者观点援引者较少,吴言生在他的论文《禅宗审美感悟论》中曾有过详细的论证。
纵观前人学者对“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解释,结合各家学说,笔者认为,禅宗三境界表达了禅宗独特的审美感悟,此三境界可以理解为未悟、初悟、彻悟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包涵了人对自然山水认识的二元对立,是以天生稚心和未受熏染的无明心观世界的未悟阶段。第二阶段,主要是对客观世界的彻底否定,并突出心识的地位和作用。第三阶段,否定一切后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拥有超脱物外的心态和认识本真的智慧。此三个阶段就是禅宗“开悟”的全过程。
三、《西游补》与禅宗“三境界”
小说《西游补》中,禅宗“三境界”的理念贯穿于孙悟空出入梦境的整个过程,与小说的内容联系紧密。
禅宗的第一境界,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这一境界,存在着主观与客观的二元性,惟信禅师运用了一种辩证思维的逻辑阐释,把山水判然区分, 既有山是山,水是水的肯定性,又有山不是水,水不是山的区别性。小说第二回中孙悟空突然闯入新的大唐境界,看着绿锦旗上“大唐新天子太宗三十八代孙中兴皇帝”这些字和一如大唐的宫廷,一头雾水,仅凭着自己已有的思维和经验判定眼前看到的一切,却辨不得大唐真假,说明此时的孙悟空还停留在事物的表面显现上,只是“见山是山”。唤不来值日功曹,就挥着金箍棒乱舞乱跳,这些行为都是他自我的本性体现。不过,同时,他又明白“山不是水”的道理,能凭借先有的意识做出简单的判断,从而让自己挣脱思维的困境,区分出“我”与山、水,以及周围的一切人、事,处于一个相对理性的平台上。第三回遇见“踏空儿”后,孙悟空听他们讲述凿天的缘由,以及对自己过往的指指点点,本已失去了耐性,气得“金睛暧昧,铜骨酥麻”,直想挥棒就打。然而,转念之间,又回过神来反思,认为所发生的事与师父无关,定是妖怪小月王作祟的结果,得以将思维中的世界与现实世界暂时分割,实现了“物”与“我”的对立。在对“山水”的观察中,始终以未开悟的“自我”最直观地去看待万事万物。孙悟空从最初的打杀一干男女怕师父责罚,到闯入大唐境界、遇凿天之人,再到误入万镜楼窥视万千世界,都只是以己目观察周围的一切,产生未经修炼的真实反映和感受。小说第二回,一个手拿一柄青竹帚的宫人,一边扫地,一边口中自言自语道:“呵,呵!皇帝也眠,宰相也眠,绿玉殿如今变做‘眠仙阁’哩!”此处用一个宫人的口吻,直击社会政治的黑暗面,对皇室的奢靡腐败,朝中大臣崇尚享乐,整日庸庸碌碌的社会风气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辛辣的讽刺。再如,小说第四回,孙悟空从万镜楼的“天字第一号”视角看到科举放榜时儒生的人物百态,将众多人物集合在一个画面当中,突出其各具神态的反常动作和语言,字里行间“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将科举制度对文人士子的毒害完全揭露出来,给予科举制度一个强有力的抨击。小说主人公处于思维的幻境中,却处处如现实生活一样真看真感觉,这是来源于朴素“原我”的感受。之所以孙悟空的想法简单直率,也是因为他此刻持有着一颗未受熏染的无明心。小说的第一回,师徒四人在行进的路途中,孙悟空眼见红花,就直言牡丹花红,不假思索,以先天纯见为立世的标准。而师父早已跳出生活的藩篱,不为事所累,不为情所困,因此答说“不是花红,是心红”。此时的孙悟空未看破其中奥妙而不解其意,因此要想获得大彻大悟必须经历冲出迷雾的禅悟过程。
第二境界,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此境界既没有区别性又没有肯定性,只有否定性。禅的渐进悟入,既是对相对知识及原始未开悟“自我”的否定,又在否定中突显意识的觉醒。在小说《西游补》中这种否定性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对自身皮相的否定。孙悟空初闯入万镜楼,发现其中有千般景象,却“无自家影子”,代表了孙悟空自我的迷失。因此,在纷繁复杂的各个世界中,孙悟空对自己没有清晰的认识,只有通过不断否定自我而获得成长。在小说第五回中,孙悟空受利益的驱使,来到古人世界,发现自己的外在皮相完全改变,由一个猴性和尚,变成了一个倾国倾城的绝世美女虞姬,与绿珠小姐,西施夫人等人喝酒吟诗。后来成功地哄骗住了楚霸王,杀了真正的虞姬,费尽心机讨好楚霸王想要得到关于驱山铎的线索。孙悟空完全否定自身外貌而委身成另外一个人,将自己的内心隐藏在另一个皮相下,这种变化看起来只是孙悟空的小聪明,其实暗藏着的是对“自我”的一种否定。孙悟空所处之境为心魔臆想的幻境,因其过度的追求而迷失了自我,他有意识地蒙蔽他人的视觉,从外在表象上否定原生自我,本为获取更大的利益,但事实上毫无任何进展,小说的这一情节也暗合了“自性迷则万事皆空”的思想。其二是对自我身份的否定。小说第八回,孙悟空硬生生被小鬼拉入未来世界,当了一天的阎罗判官,审判秦桧之罪时,怕自己慈悲和尚的样子没有威严,还特意换了一身阎罗坐堂行头,成为了铁面无私的审判者形象。小说中用了两回的篇幅描写审判秦桧的经过,列举秦桧的一条条罪行,并施以各种阴间的酷刑惩罚,表现了主人公对奸臣叛国求荣的愤懑之情和对岳飞一类爱国忠臣的崇敬。但过程中全无寻找“驱山铎”的主线内容,说明孙悟空已经完全认定了自身审判官的身份,早将自己和尚面的慈悲掩饰起来,试图在幻境中审判和惩戒奸臣,有意识地干预社会政治,改变当时的政治生态,为心中的是非忠奸做一个公正的裁决。还有一次自我身份的否定出现在第十五回,孙悟空见师父做了将军,就混在乱军中过了三日,身份变成了六耳猕猴模样的孙悟幻,身世也成了“自从大圣别唐僧,便结婚姻亲上亲”。小说《西游记》中也有关于六耳猕猴的叙述,孙悟幻可以说是世俗化了的孙悟空,充满着原始本性的影子,而此处孙悟空身份的改变其实是失了本心的结果。其三是对自我认知的否定。小说第十一回,辗转回到青青世界时,行者偶然听说师父在饮虹台上喝酒听戏,一路追踪,暗地观察,见师父与小月王交好,又与翠绳娘洒泪诀别,点兵将做了将军。在戏文中,就连孙悟空自己都被封了丞相,过上了妻儿相伴的风光日子。在青青世界发生的一切,都超出了孙悟空的认知。师徒四人恪守规戒,不远万里去西天取经,如今却留连于世俗情爱,在俗世享尽荣华富贵,一系列不可思议的奇闻湮没了他们的初心,也是对所见所闻的最大否定,此刻意乱情迷到达了顶点,亟待拨开云雾,识得本真。小说中孙悟空由表及里,将自己层层剥离,处处否定。孙悟空在思维的求索之路上历经波折,也在过程中反复迷失和自我解救,可不管用尽多少功夫,一切终是幻梦一场,如泡沫般破碎,不过其处于混沌迷茫之时的感悟,为后来的彻悟打下了基础。
第三境界,见山仍是山,见水仍是水。指的是达到佛道最高境界,看破一切世俗,回归本心,此时不再是初见山时的“自我”,而是开悟后的“真我”。小说第十回孙悟空在葛藟宫幻境中,曾有过一次找寻“真我”的自我解救,但俗尘未了,心结未开,所以只是暂时的脱困,并未识真性。直到小说的最后一回,孙悟空因五旗色乱而烦乱,被虚空大师点破,如梦初醒,终看清人生恍惚不定,迷惘虚妄,三千大千世界不过一瞬。心物本为一体,且相互贯通,任何仅“执于事”或“契于理”的执着一边均是不识“自性”[6],就是悟空说的“心迷”。突破困境后就如沙僧所说,妖魔皆被扫尽,世界朗朗清平。孙悟空的种种经历完全是自己思想的一种虚化,与《西游记》不同的是,他不再需要对抗来自外在的各路妖魔鬼怪,而是需要面对自己的内心。而这里的心魔也不再只局限于儿女情欲,借铎、寻师、除奸等,任何的执着欲念都会成为束缚人的枷锁。小说中的孙悟空和鲭鱼精,本是同时出世,但却一善一恶,究其原因,是由于其能否抽离世俗的羁绊,明心见性所致。鲭鱼精未曾开悟,因此为世俗所累,迷人自迷;而孙悟空梦醒开悟便会成佛成圣。所谓“成佛”,便是自我认识的觉醒:“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7]。孙悟空的梦醒是他自觉悟道的结果,是存在于他内心斗争之后的一场洗净和升华,使他能够去抛弃那些愚痴迷妄的思想,能够远离贪欲爱憎,怀着一颗大彻大悟后的平常心,重新审视自己眼前的一切。“见山仍是山,见水仍是水”,只不过观山水之人已经大为不同,如今看待所有事物都是淡然而通透的,正像小说的最后一句所言,“范围天地而不过”,天地虽大,彻悟人之心却能容下,这反映出开悟之人包吞宇宙的气度与胸怀。
四、结 语
明代末期阳明心学思想和禅宗思想不断融合,且都强调发自内心的修行,在小说《西游补》的创作中也有所体现。比如孙行者既有道教的祖师和佛教的唐僧,也想拜岳飞为儒教的师父,以及“花不红是心红”“心迷时不迷”等这样的语句。第十回葛藟宫中悟空自救,寓意人心的两面性,这里的自救也是求其放心的一种表现形式。这都受到了当时注重个体精神自由风潮的影响。《西游记》之后,出现了神魔小说的滥觞,这一时期的社会思潮也更趋于内心世界的探索和宗教观念的融合,相对于世情小说和演义小说,神魔小说的义理性更强,更容易在奇异诡谲,变幻无穷的小说内容中掩藏深刻的内涵。小说《西游补》以幻入境,以情贯穿,不仅讽刺了当局政治,批判了现实生活,更在情节架构上蕴含了世事虚幻,万物皆空的禅宗哲学,从而升华了小说的思想内蕴和艺术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