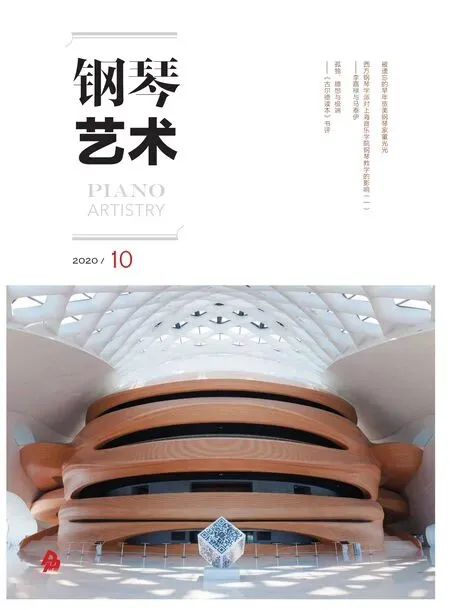致敬与感恩
——评“广东风格钢琴曲第一人”夏里柯的钢琴作品(下)
文/ 梁茂春

万里思乡赤子心
这一节,我想谈一谈夏里柯在中国香港谱写的四首拉脱维亚风格的钢琴曲,具体是指:《第一狂想曲》(作品6),作于1921年8月;《第二狂想曲》(作品7),1923年2月;《两首拉脱维亚叙事曲》(作品21),作于1930年。
按照创作时间的先后顺序,本应以上列作品的先后来分析。但是由于他的两首“狂想曲”的体裁较大,艺术上亦更加全面,所以我先分析比较通俗、简练的《两首拉脱维亚叙事曲》,而将两首《狂想曲》作为“压轴”的曲目来欣赏。
这些作品中,流淌着这位拉脱维亚流浪音乐家的“万里思乡赤子心”。
《两首拉脱维亚叙事曲》(作品21)
这是两首拉脱维亚音乐风格的钢琴小品,连续演奏。1948年出版于美国,作品题献给“M. K.”。
例7 《两首拉脱维亚叙事曲》之一

例7的前两小节是前奏,第3小节的右手奏歌谣性主题,在降E大调上。第二行乐谱倒数第2小节开始是左右手“卡农式”复调,非常精致。整首“如歌的慢板”是带再现的复三部曲式,都建立在这一主题的各种变奏形态上。
中段速度稍快较为兴奋、活泼,调性转到降G大调上。中段结束处是全曲的高潮。
再现时又回到降E大调。主题作进一步的变奏,织体显得更加丰富,情感更加深沉、内敛,歌声逐渐走向遥远,在ppp音量中结束。
例8 《两首拉脱维亚叙事曲》之二

这个主题最显著的特点是重音的非常规处理,这使这段音乐带有了强烈的舞蹈律动感。A段即在这八小节的音乐中变奏、发展。音响从p开始,逐步发展形成高潮。
B段是对比性的中段。这段的音乐主题是长气息的下行旋律,以“柱式和弦”伴奏,像是激烈的舞蹈中间一个喘息、缓冲的段落。
然后又回到A段的再现,最后在fff特强音响的热烈、旷达的舞蹈中结束,音乐犹如燃烧着的火焰!
这两首叙事曲相连起来,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艺术整体,是拉脱维亚民族的深情之歌和激情之舞。它们是拉脱维亚民族生活的画卷和精神的展现。
《第一狂想曲》(作品6)
夏里柯的《第一狂想曲》于1924年在美国出版。夏里柯在乐谱上写着“为纪念李斯特而作”及“采用拉脱维亚民间曲调,李斯特风格”。伟大的匈牙利钢琴家、作曲家李斯特诞生于1811年,夏里柯是为李斯特诞生110周年而谱写这首《第一狂想曲》的,以表达对李斯特的崇敬,同时也深刻表达了夏里柯对拉脱维亚的思念和深沉的爱。
《第一狂想曲》结构庞大,是自由的多段体曲式,全曲大体上可以分为六个段落。
例9 《第一狂想曲》

例9是《第一狂想曲》的第一段——序奏,乐曲开头即是狂风暴雨般的高潮!、、的不规则节拍转换加强了音乐的不稳定性;fff和ffff的强大音量,上行小三度和五度的“号角式”旋律,成为《第一狂想曲》贯穿始终的“特征音调”,体现了拉脱维亚民族桀骜不羁、勇于战斗的性格。
联系拉脱维亚国家独立的经历——这个民族经过了无数次艰难曲折的斗争之后,终于在1918年获得独立,仅仅三年后,远在中国香港的夏里柯即于1921年以《第一狂想曲》直接表达了他对祖国独立的庆祝。从那暴风骤雨般的音乐中,我们可以直接感受到拉脱维亚民族历史的声音。
这段音乐似乎是表现对民族历史的深情赞颂和对苦难遭遇的深沉回顾,充满了内在歌唱性,力度基本上控制在p的范围,与序奏中的强烈音响形成鲜明的对比。又出现了一段拍的阴郁、低沉的旋律,仿佛在追忆不堪回首的历史,又似乎是沉重的哀悼曲。这段深沉的音乐,表现了作曲家内心深处那种“故国在云端,天路隔无期”的无奈和惆怅。
例10 《第一狂想曲》

又经过一个长休止后,乐曲进入第四段——“摇篮曲”段落,速度是小行板。夏里柯在这里专门采用了拉脱维亚作曲家E.梅尔宁盖利斯的一个旋律,温馨、委婉的曲调,深深寄托了作曲家对民族、对祖国未来的美好向往和良好祝愿。
第五段音乐回到第一段的“号角式”音调和暴风骤雨形象,这是《第一狂想曲》的再现段落。
当狂风暴雨再次平静之后,音乐进入了一个长大的进行曲段落,首先出现“急板”音乐,这像是一大段快速的群众性的胜利进行曲。力度从pp开始,经过p,突然进入fff,形成强大的冲击力,音乐推向昂扬恣肆的总高潮。
夏里柯的《第一狂想曲》通篇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是一首爱国主义的嘹亮颂歌。钢琴发出了管弦乐队的交响音乐效果,贯穿着强烈的交响性和斗争性。从结构上说,作品汇聚了多个音乐主题,有变化、有重复、有对比、有统一,类似一部浓缩了的多乐章交响音乐。如果有作曲家能够将其改编成管弦乐队的体裁,一定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夏里柯的《第一狂想曲》是拉脱维亚独立初期的一座音乐的纪念碑。
《第二狂想曲》(作品7)
夏里柯的《第二狂想曲》于1926年出版于美国。夏里柯在乐谱上标明“基于拉脱维亚民间曲调”。
《第二狂想曲》的曲式亦很庞大,也是自由多段体的狂想曲结构。乐曲开始是全民胜利狂欢的场面:群情振奋,豪情万丈。有激情的歌唱,有热烈的铜管乐合奏,有群众的欢呼和呐喊,音乐荡气回肠(见例11)。
例11 《第二狂想曲》

音乐一开始就将情绪推向了高潮。第一行乐谱右手弹奏的旋律有群众歌曲的特点;第二行乐谱中加顿音记号的曲调,像是一首热烈的军乐队曲。这两个音乐主题贯穿了全曲,
第三段音乐是一段“变奏曲”,速度类似行板。主题在E大调上,拍(见例12)。
例12 《第二狂想曲》

变奏曲的主题变化出现了多次,开始时音乐纯朴,转而变为华丽,继而发展至情绪猛烈,钢琴带有炫技特点。
接着是一段在号角声引导和衬托下的“群众进行曲”,最后是雄伟壮丽的结尾,这一段音乐始终持续着最强的音量(fff——ffff)。音乐材料回到序奏中的两个主题,但是经过了巨大的变化和发展。音乐循环往复,乐风雄朗豪迈,壮阔悠远。全曲在“全民欢腾”般的狂热气氛中结束。
以上简要介绍了夏里柯的四首拉脱维亚音乐风格的钢琴曲,尤其是两首大型的“狂想曲”,以鲜明的音乐形象,直接表达了夏里柯强烈的、发自内心的爱国热忱。这几部作品体现出了拉脱维亚民族和国家历史的声音,表达了作曲家难以割舍的“拉脱维亚情结”,那是夏里柯内心的真实呈现,值得引起人们充分的注意。
拉脱维亚这个民族在历史上多灾多难,饱受欺凌。早在13世纪初就被德国控制,18世纪又被俄国占领,20世纪又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1918年,拉脱维亚独立后不久,夏里柯就到了中国香港,他于1921年和1923年先后谱写的两首狂想曲,无疑是他对祖国独立后发出的欢呼声,是他发自内心的爱国热情的真实流露。
2018年是拉脱维亚独立一百周年。夏里柯的《第一狂想曲》和《第二狂想曲》,是拉脱维亚独立之初的时代声音,是应该进入拉脱维亚音乐史的。无论从拉脱维亚国家历史来看,或者从拉脱维亚音乐史来看,这两首钢琴曲都有它们特殊的历史意义。它们与夏里柯1930年谱写的《两首拉脱维亚叙事曲》,都充分表现了夏里柯对祖国的热爱和思念。从这些作品中,能够明显地感受到深藏在夏里柯骨子里头的拉脱维亚民族精神。我不知道这些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创作于中国香港的钢琴作品,有没有引起夏里柯的祖国和人民的关注?是否知道这些产生在中国香港的“拉脱维亚钢琴曲”?是否了解在万里之外,还有一位拉脱维亚钢琴家为自己的祖国谱写了这些深情而动人的音乐?
百年乐史须感恩
夏里柯的历史资料目前远没有收集齐全,我的初步研究工作,得力于中国香港钢琴家蔡崇力的鼎力支持。蔡崇力是夏里柯亲授的钢琴学生,他保存了夏里柯大部分的曲谱资料,这些资料可以说是我研究的基本资料。其他有关夏里柯的零星史料、曲谱、照片、报刊评论等,又得力于我的朋友宫宏宇教授和学生白一冰的帮助,他们利用当代网络的优势,补充了一些很珍贵、难见的曲谱和资料,但是,可以说都是碎片化的历史信息。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尚有许多工作可做。
现在初步收集到的夏里柯钢琴作品还有:《诗》(作品2)、《变奏曲和赋格——贝多芬主题》(作品10,为双钢琴而作)、《小步舞曲》(作品15)、《变奏曲——日本歌曲主题》(作品25,1944年作于澳门)、《纪念册的一页》(作品32之1,为双钢琴而作)、《古老的俄罗斯波尔卡》(作品32之2,为双钢琴而作)。
本文只重点分析了夏里柯的“广东风格钢琴曲”和“拉脱维亚风格钢琴曲”,其他风格的钢琴作品还没有涉及。
中国有句古话“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是中国优良的传统品格。当一个人横遭逆祸,处于穷困潦倒、逼仄煎熬之中时,有好心人给了一滴解渴的水、说了一句同情的话,这就是恩情,值得你用涌泉来相报。这正是伟大的中国文化中重视感恩的传统,值得永恒地传承。
本文“序诗”中的“百年乐史须感恩”这一句话,想表达的主要意思是:中国的百年钢琴发展史也要感恩夏里柯这位拉脱维亚钢琴家,应该向他表示深深的历史敬意。
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才是有希望的人;一个懂得感恩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一个懂得感恩的国家,才是有希望的国家。
夏里柯在中国香港改编这一批广东音乐风格的钢琴作品时的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钢琴创作尚处在“初生期”,甚至还不懂得钢琴作品还可以“说中国话”或“讲广东话”。当20世纪初夏里柯在圣彼得堡接受音乐教育时,他受到了俄罗斯民族乐派如柴科夫斯基、里亚多夫等作曲家的深刻影响,即作曲家要重视和倾听民众的歌声。他在中国香港、澳门地区认真倾听、熟悉、记录了街头巷尾的广东民歌和小曲,并努力把它们用钢琴表达出来。夏里柯所做的这一努力,比中国作曲家自己做的要提早了十来年。他不但将广东音乐改编为钢琴曲,还在钢琴独奏音乐会上经常演奏,并且在国外的音乐出版机构出版了这些作品,有的作品乐谱还再版了多次,这足以反映他的用心是多么良苦!
这里再介绍一则1932年发表在新加坡报纸上的音乐评论,是关于夏里柯钢琴独奏音乐会的。这篇乐评说道:“拉脱维亚钢琴家夏里柯昨晚在新加坡基督教男青年会举行最后一场音乐会时,令东方与西方音乐再次相遇。跟前几次音乐会一样,他显示出自己是一个技巧非凡的钢琴家。”这场独奏会,前半场以演奏西方钢琴作品为主,夏里柯弹奏了巴赫、贝多芬、门德尔松、肖邦、李斯特、斯克里亚宾等人的作品,而后半场则是以演奏夏里柯自己改编的广东音乐风格钢琴曲为主,他相继演奏了 《中国南方幻想曲》《旱天雷》《雨打芭蕉》《柳摇金》《寡妇的悲哀》《饿马摇铃》——再次掀起了听众巨大的兴趣。
请注意,这场音乐会举办的时间是1932年5月4日,地点是在新加坡。中国钢琴曲创作中民族风格成熟的标志性作品是1934年产生的贺绿汀的《牧童短笛》《晚会》《摇篮曲》等。这里产生了一个有趣的“时间差”:当内地的钢琴创作的民族风格尚未成熟的时候,在香港地区却有一批夏里柯改编得相当成熟的“广东风格钢琴曲”,并已经在东南亚地区开始产生影响了。
夏里柯也曾经在广州多次弹奏过他改编的这批作品,黄锦培教授曾写道:“20世纪30年代曾有西方钢琴家夏里柯弹过一些广东音乐的钢琴独奏曲,并于50年代到广州演奏过《双飞蝴蝶》等曲目。”
因此,有理由称夏里柯的这些作品是第一批在海内外产生了影响的“广东风格钢琴曲”。
最初探索广东音乐风格钢琴曲的中国作曲家,是吴伯超和陈洪。吴伯超(1903——1949)在1935年根据广东流传的小调《思春》改编为同名钢琴曲;陈洪(1907——2002)于1936年发表了他根据广东小曲《玉美人》改编的同名钢琴曲。这是中国作曲家尝试创作“广东风格钢琴曲”的滥觞。从时间上看,都在夏里柯的创作探索之后。
中国作曲家创作的“广东风格钢琴曲”,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进入了第一个高潮期,产生了马思聪创作的《三首舞曲》(1950)和改编的《粤曲三首》(1953),陈培勋改编的《广东音乐主题钢琴曲四首》(1953——1954),以及黄容赞创作的钢琴曲《狮舞第一号》(1955)等影响广泛的钢琴曲。而夏里柯在20年代就改编过的《旱天雷》《卖杂货》《水仙花》《梳妆台》《双飞蝴蝶》的旋律,仍然还是作曲家们争相改编的首选曲目,这不能不说是夏里柯引起的历史的余波涟漪,由此可见夏里柯的深远影响之一斑。
所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称夏里柯是“广东风格钢琴曲第一人”。我们应该对他表示真诚的敬意!
历史证明,真正有价值的音乐,必定出乎对人的热爱。夏里柯的这批广东风格钢琴曲,正是表现出了他对中国人民的热爱,对广东音乐的热爱,因此具有永久的历史价值。
由于夏里柯本人是一位优秀的钢琴家,所以在他的这些作品中,钢琴的特长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挥,也就是说,作品中“钢琴化”的处理做得比较好。
当国内的钢琴创作总体水平还处在“ 拜厄”“849”“299”初级阶段的时候,夏里柯却谱写出了一批具有专业音乐水平的“广东风格钢琴曲”。夏里柯以他敏锐的感觉,率先踏上了“广东风格钢琴曲”这个历史阶梯,因而对“广东风格钢琴曲”的催生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历史真的充满了偶然,须知一个外国人要深入了解广东音乐有多么困难!
历史随风而逝,夏里柯的这一段历史并没有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被充分关注过,更没有引起过重视。而当历史尘埃落定之后,夏里柯就成了历史研究中的一个缺失环节。好在夏里柯的这一批钢琴作品都在中国、美国、英国等地出版过。将这些“碎片化”了的历史乐谱重新“打捞”和集中之后,夏里柯的模糊存在可以通过这批乐谱、资料得到一定的再现和复活。
此外,也许没有人知道,拉脱维亚的一段音乐历史曾经在中国香港走过。拉脱维亚的文化界、音乐界是否有人知道,曾经有一位拉脱维亚的儿子,在浪迹天涯的旅途中,谱写出了一批对拉脱维亚表现出真诚爱国情怀的钢琴作品,这些钢琴作品直接表现了夏里柯的潜意识——隐藏在心灵深处的爱国、思乡情愫,表现了夏里柯“身在香港澳门,心系拉脱维亚”的真实情感。聆听夏氏狂想曲,何人不起故园情?它们也应该是拉脱维亚音乐历史的印记,作品创作至今已经将近百年。它们应该回到拉脱维亚,让拉脱维亚音乐界知道这位流浪的拉脱维亚音乐家的历史贡献,让拉脱维亚民众能够听到一位拉脱维亚儿子“沦落天涯”时留下的赤子之音,感受到他作为“拉脱维亚公民”的赤子之心。
我在本文中曾初步分析了夏里柯的两首叙事曲和两首狂想曲。虽然夏里柯一再强调,他的作品“采用拉脱维亚民间曲调”或“基于拉脱维亚民间曲调”。但由于我对拉脱维亚民间音乐毫无了解,因此无法对作品的民族风格和意韵作出精确的分析。我真的非常期望能够有拉脱维亚的音乐家来对夏里柯的作品进行更加深入和具体的音乐阐释。(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