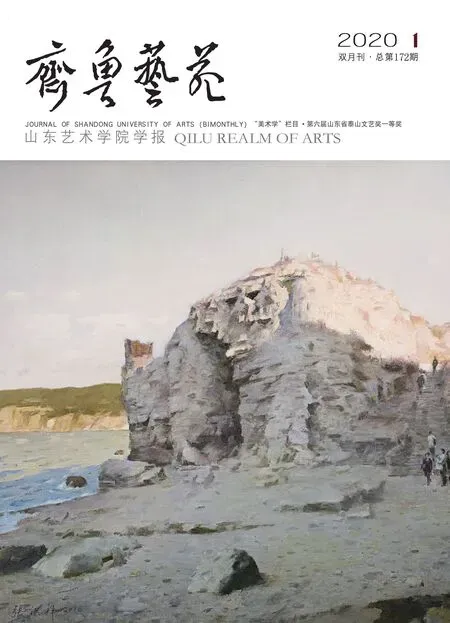皖南陶瓷元素在合肥地铁空间中的介入研究
张 毅
(池州学院艺术与教育学院,安徽 池州 247000)
皖南特指安徽境内长江以南的区域,源于唐代江南道,雏形于宋代,定性于民国皖南行政署,是区域概念,也是文化维度。其位置地处长江沿岸,是南北文化的交汇点,中国文化的繁盛地。这里工艺美术多彩丰富,成就辉煌,体现了思想前瞻开放、科技人文丰盈的特征,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造就了影响中国的程朱理学、新安画派、徽州医学、徽派建筑、徽州版画、徽州古戏台、徽剧(京剧前身)、皖南陶瓷艺术等精彩纷呈的皖南文化,体系完整,内容丰厚,特征昭彰,对人们生活习性、思想情感以及中国工艺文化的特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皖南工艺美术长期趋稳,表达方式多样,具有典型性、辉煌性、丰富性的特征,为研究中国工艺美术的衍变历程提供了大量的史料。其中皖南陶瓷遗存丰富,造型和装饰齐备,都是精美之作,它集中映射了皖南区域人们独特的审美观念和造物技艺,是中国陶瓷工艺发展史上重要的文化印记。将皖南陶瓷文化在公共空间传播和创新,不仅是文化传承路径,更是紧跟大国工匠的步伐,探究其设计手段和展呈表现,促进地域文化资源与当代设计进行互促,将两者交融后加速安徽经济与文化的腾跃发展。
一、皖南陶瓷元素与艺术特征
1.皖南陶瓷的历史渊源考释
皖南文化是横跨黄山、芜湖、马鞍山、铜陵、池州、宣城等六市根基上滋生——孕育——繁荣,显现出极度的一致性:无论在造物理念、思想旨趣,还是在艺术造型、装饰语言、动态之美等方面展露出民族美学相近的特性,这种宽泛的一致性具有高贵文雅、典范趋同、和谐相生的世俗情结。
中国陶瓷是中国先民用丰富的生活知识和精确的工艺技巧创作出集实用与审美为一体,集科学与艺术,集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为一体的文化风貌,它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需求和审美情趣,它用多变的型体,雕饰细节纹身,表现出强烈的名物风情,是国人引以为傲的工艺美术作品。真正意义上的瓷器在东汉起始至隋唐出现繁茂,形成以浙江越窑和河北邢窑为代表的“南青北白”局面。两宋时期,官窑、民窑相继勃兴,各地瓷窑在造型、装饰上都有独创性的成就,玉壶春瓶、梅瓶、葫芦瓶、提梁壶、诸葛婉等是前所未见的新品种。特别是以景德镇为代表的“青白瓷”的出现影响甚广,涉牵安徽、湖南、浙江、湖北等区域。据考古发现,安徽两晋时期发现墓葬为50有余,且主要分布于皖南。这些丰富的史料对于研究皖南地区墓葬形制与陶瓷的业况提供了重要的价值。特别是当涂太白乡纪年墓、和县纪年墓、寿县纪年墓、南岭长山村M1墓中青瓷的种类与数量史无前例。出土的青瓷多以实用器和明器为主,包括碗、罐、壶、钵、仓、磨盘、俑、动物为主。其釉色多为青黄、绿黄、青绿、米黄、豆青为主,做工简陋、釉色浑浊,有掉釉和开片的特点。安徽典型的寿州窑则以色彩瑰丽的黄釉一举成为唐代七大名窑之列。其窑系当属南方青瓷,流行施用化妆土,表层为透明的玻璃质釉,釉面光润,开小片纹,釉色以黄色为主,有鳝鱼黄、蜡黄、黄绿等色泽,釉层厚薄不均,釉色浓淡不一,有剥釉现象。这种由隋代青釉改烧唐代黄釉的改良,形成了唐代寿州窑的时代风格,其诱因是还原焰革新为氧化焰的烧成气氛的结果。寿州窑造型、色彩及装饰有佛教倾向,由青瓷向黄瓷转变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与寿州窑比邻当属宣州窑。民国黄矞在《瓷史》认为:“宣州瓷窑,为南唐所烧造,以为供奉之物者。南唐后主尤好珍玩。”唐代末年由于长期战乱,导致北方先民大量南迁,在迁徙过程中带来了丰富的制瓷技艺,宣州境内濒临长江、水阳江、青弋江,这里有丰富的高岭土、瓷土,从而造就了宣州窑的蓬勃发展。其色质为青黄,既有北方陶瓷的粗犷,又有南方瓷器的细腻。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安徽芜湖繁昌柯家村、姚冲窑、半边街窑、骆冲窑等窑址组成的繁昌窑在挖掘规模和数量上独占鳌头,是典型的专烧青白瓷的大型古窑址群。繁昌窑是五代始烧,南宋初年停废,2001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瓷窑遗址其标本多为青白瓷、卵白釉瓷及酱釉瓷,瓷器有碗、盏、盏托、碟、温碗、执壶、炉、盂、粉盒、器盖、瓷塑小动物等器型,种类繁多,粗细、横直、长短、弯曲不同轮廓线组合不同形体,有的修长秀美,有的短硕稳重,光怪陆离,气韵天成。这些瓷器造型规整、制作精良、工艺水平极高,以至于成为目前大家研究度极高的著名瓷窑遗址。
2.皖南陶瓷元素建构与艺术特征
皖南工艺美术的历史积厚流泽,绵延至今,而陶瓷作为工艺美术特定的审美对象,皖南窑场环设,商贾云集,号邑巨镇,既是陶瓷制品的市场,也是瓷器的集散地,消费与市场繁荣,自身特有的造物工艺、图案纹饰与地域文化相补相长、工致有余,形成了独有的生活审美。皖南陶瓷元素给人以视觉上的物态形象,陶瓷元素的风格与时代合乎逻辑,密不可分,长江沿岸的高岭土为皖南陶瓷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将北方白瓷与南方青瓷进行文化提炼、技艺相长进行把握和审视。无论是唐代的寿州窑、宣州窑还是宋代的繁昌窑造型多来源于对浙江越窑的器形模仿,也有对唐代金银器借鉴,特别是陶瓷执壶短流、莲瓣纹首饰器的仿效。黄釉为表征的寿州窑,釉色以氧化焰烧成,釉色多以蜡黄及黄绿釉,釉下多施泥质胎衣,成玻璃状,粗制断面,有气孔和铁质斑点,多数使用化妆土,但并不牢固,有剥落现象。而作为宣州窑色泽则呈现出白釉及酱釉特征,以大宗日用品为主,其器形和成型工艺都与越窑有异曲同工。繁昌窑目前最新研究成果共识为中国青白瓷起源较早区域,釉色偏黄或偏青,有开片黑色斑点,开片处呈现翠绿色,精细化程度较差,圈足处多为砂质颗粒,其风格与宋代景德镇青白瓷相近。
皖南陶瓷元素的提炼是多元化视觉形象的综合体,它是安徽先民的内心写照,其建构是陶瓷文化对视觉的集中反馈,皖南陶瓷是民众民意反馈的重要管道,它以艺术化的方式把握文化的价值尺度。
皖南作为古代吴越文化的重要领域,物产丰盈、地形多变,在公元4世纪初(晋末)、9世纪末(唐末)、12世纪初(宋末)三次朝代更迭和三次大规模的人口变迁,中原望族大规模迁入皖南,经过与山越人的宗族混居,产生了一个以中原汉族为主的移民社会。中原人士带来了当时北方最先进的制陶技艺,特别是钧窑、汝窑等皇家御窑文化,经皖南嘉山秀水的陶冶,形成了中华文明史上一道独特的历史文化景观,也是中国瓷器的重要的发源地之一。目前,考古挖掘百余座陶窑遗址与文化遗存,从实物情况看,皖南的陶瓷青白瓷数量为最,兼有黄釉、酱釉、青花、五彩。器物造型多采用轮制,造型规整,方圆适宜,胎质色泽莹润,白中泛青,青中显白,透明度不高,胎壁厚重。虽整体烧造技术不及景德镇青白瓷,但它却是北方的漏斗形匣钵和底垫、垫圈装烧具组合的泛用者,采用一物一器仰烧法,也有个别的支钉叠烧技术,瓷器内壁和器底无法施釉的露胎,形成了品种有消长,产量有起伏,产区有转移,质量有优劣的特征。作为皖南的民窑体系,多数器物作为民众的日常功用,如“碗、盘、碟、盆、炉”等,彩绘瓷多为花卉山水、游鱼花鸟为常见题材,经工匠的巧手,用不同的技法,表现出不同的神情意态与器型巧妙结合,因器施画,花叶纷披,俯仰有致,姿态各异,地域特征鲜明与文化色彩浓郁。
从目前挖掘陶瓷遗存看,皖南陶瓷多数是唐宋遗风,自然是承传了唐宋陶瓷的艺术特征:以多彩釉色、多变造型取胜。装饰方法为传统工艺的延续(刻、印、划、剔、贴、嵌、彩绘等)。装饰题材丰富多变,厚重雄健而趋于清新流丽,表现出挥洒自如、简练有致,精绝的设计意匠和高超的技艺完美融合,造就了皖南陶瓷的独特神韵。
二、皖南陶瓷元素的影响因素及在合肥地铁空间的介入分析
1.皖南艺术思维对陶瓷元素的影响
皖南地区艺术精彩纷呈,有其独立的历史溯源和精神底蕴,通过考古文献和文化遗存,可以得出皖南陶瓷的形成受到了该地域文化的教化。皖南陶瓷通过唐代孕育、发展、勃兴、颠覆、衰歇不仅具有中国文化轨迹属性,更表现出文化的延展性,在某种水平上表达出全国性的艺术特征和文化缩影。
民俗思想的文化表象。作为民窑产出的皖南陶瓷,表现内容和设计造物彰显了皖江地区的文化特性,浮现出求真务实、格调雅致、社会风尚、题材富厚的特质,这种文化现象是民俗思想的真实表现,是对皖南历史把握的依据和载体,是工匠精神的衍生品和审美观。特别是徽文化的浸染,作为典型性、辉煌性、丰富性的地方特色,在明清社会上处于热点、显赫一时的学派,一跃成为中国三大地方显学之一,特别是受儒家思想浸深的程朱理学、新安画派、徽州版画都对皖南陶瓷有深刻影响。
宗教思想与图式吉祥的概括抒发。皖南跨越两山一湖,陶瓷文化深受佛教文化影响至深。特别是九华山宣扬普度众生、善恶美丑、邻里和谐的宗教教化是人类共有的标尺,在考古的皖南陶瓷艺术遗存中展呈丰富。例如,繁昌窑的观音瓶的大量出现,侈口,短颈,丰肩,肩下弧线内收,胫部外撇,浅圈足,器型修长,线条流利;在九华山出土的青花瓷器中,多数出现了佛教题材的莲花、地藏王图式,瓷质细微,争奇斗丽,是典型夸耀地藏王的丰功伟绩艺术品。吉祥图式也是陶瓷元素装饰的重要资源,在选材、构图、工艺、造型上紧扣莲花、菊花、巧竹、腊梅的自造君子旨趣,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审美设计的核心形态,是对文化的开放性和多元论进行了深刻的解读。黄山太平湖出土的五彩花瓶,胎制细润,色彩柔和淡雅,通体腹部四分,皆为士大夫追随的“竹菊梅兰”四君子图式,线条有力,鲜明透彻。这种影响尺度已经悄然改变了我们的文化品质和精神内涵。
2.皖南其他文化对陶瓷元素的浸染
徽州版画是伴同徽商经济发展在文化意识形态上的艺术载体,总明代起首,呈现多维度的景象,是当代中国印刷与出版行业的开端,于今依然名扬天下。以精巧、清秀、富丽为表征的徽州版画艺术为皖南陶瓷的题材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根养,线条细发如丝、苍劲有力、刚柔同济、色彩强烈、泾渭分明,也突出了皖南绘画的特质。徽州版画最大的贡献是对皖南陶瓷的色彩感化。青花五彩作为明代代表性陶瓷品种之一,其特征是粗犷豪放、浓墨重彩、自由奔放,突出色彩对比,与徽州版画的构图和设色是异派同源。
黄山画派是摹写黄山及周边山水容貌为风格自觉建构的皖南派系,他们师法自然,将徽州美丽的自然风光绘于纸绢,挥洒自如、无拘无束。而作为新安画派的代表人物查士标、汪之瑞、孙逸、黄宾虹、张君逸,善用笔墨,貌写家山,借景抒情,表达自己心灵的逸气,画论上提倡画家的人品和宇宙之气浑为一体,形成中国绘画最高品评的“气韵生动”,绘画风格趋于枯淡幽冷,具有鲜明的士人逸品格调,在十七世纪的中国画坛独放异彩。新安画派最大功勋是染指了浅绛彩瓷,品类齐全,粗细兼备,程门、王少维是代表人物。浅绛是山水画中以水墨勾画初形,采用浅色赭石、花青为色料的山水、花鸟画。将浅绛用在彩瓷上也是勾勒浅彩,画面色浅温润,古雅端庄,也是以摹写山水花鸟为特色。这种浅色典雅的美学思维就是新安画派的精髓所在,这种艺术形式至今影响景德镇的瓷画艺术,对推进千年瓷都瓷器的极盛有推波助澜之功。
徽商文化也是皖南陶瓷的繁盛的决定力量和终极原因。徽商被人称誉“儒商”,“贾而好儒”是徽商特色,经营范围“北达燕京,南至广粤、获利颇赊”,其雄厚的经济财力缔造了皖南陶瓷发生的条件,徽商经济创造了皖南艺术发生的动因,甚至决定皖南艺术的内容与形式。徽商走南闯北,行动轨迹类似游牧,而对身上所能携带的器物进行了多次的考量思辨。发现瓷器既方便携同又品味兼具,于是陶瓷便成了他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当功成名就之时,回乡将外地优质的瓷器技艺进行改良,特别是清末明初景德镇陶瓷外销推动有一半皆属于徽商的功绩,他们对陶瓷艺术的反馈和输出,无疑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成就了皖南陶瓷的技艺革新和艺术价值。
3.皖南陶瓷元素在合肥地铁空间中的介入分析
主题应用。皖南陶瓷是安徽工艺美术的典型代表,作为造型艺术和装饰艺术并重,呈现的语汇是多样的、丰彩的。创作源泉源于皖南匠师对陶瓷的精深取舍,对文化意识和生活审美的多维创造,其运用也与社会形态和大众的审美接受有关。安徽是产瓷大省,合肥又是安徽文化的集中颂扬地和展示地,将千年的皖南陶瓷元素应用于合肥地铁空间,是大众所需、人心所向。它是皖南文化植入公共艺术空间之中,顺承国家“工匠精神”策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再造、承传、创新的重要途径。屏风千百年来一直作为入口屏障,它的沿革是影壁文化的室内传承载体,是地域文化的展示窗口和自信介质。合肥是目前安徽唯一的地铁同行城市,作为省会,徽风皖韵的理论浪潮仍然生活在其文化延长线上,无论是思考框架,还是我们正在面对的历史命题,都能看到徽文化影响的轨迹。合肥地铁入口作为彰显安徽文化的重要区域,设置皖南陶瓷屏风意义显著,如将寿州窑、宣州窑、繁昌窑等瓷片在屏风的外部贴饰以及彩绘,自然形成工艺美学与地域文化设计元素的和谐共生。建筑具有“跨时代性”“亲时性”的特点,即表现出它对时代的亲和性,又表现出它对时代的跨越性,“当随时代变”,陶瓷也不例外,虽然皖南陶瓷在唐宋达到高潮,属于那个时代和民族,环境特殊,依存于特殊的历史和其他观念的目的,它是时代的影子。在当今,将其重新烧造,采用了当代新的陶瓷技术、新的思想、新的语汇,让其陶瓷文化既有空间意义的协调,又有时间意义的和洽。这种多维度的立体设计,会将大众的视觉步入皖南境域,有历史穿越之感。
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肥东)人,北宋名臣。包拯廉洁公正、立朝刚烈,不攀权臣显贵,刚正不阿,且决判英明,勇于替百姓伸冤,自古就“包青天”“包公”雅号,是中国清官的代表典型,而合肥作为故乡,廉政文化自然是地铁重要表现场域,这种与中国目前宣扬的“诚信做人、清白为官、踏实做事、勤政为民”的中华传统美德、正端风气相契合。目前,合肥地铁1号线,地铁车厢内部已经在“包公园站”充分利用陶瓷自身的视觉符号将包公的脸谱及卡通形象应用之中,给人以警示作用和传递徽剧形象(京剧前身)作用,即传递了廉政文化、徽剧历史,又将陶瓷艺术进行结合,达到了物质与精神、技术与艺术、材料与造型、工程与审美完美统一。
其次,几千年来,忠孝文化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它是伦理准则的要求,又是宗教信仰的敬奉。皖南文化中对忠孝的记载史书多达几十部,特别是宋代儒家文化集大成的朱熹将《礼记·大学》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植入徽文化,如将徽文化中忠孝文化在陶瓷载体上呈现可能历史厚重感更强。这种孝道文化在当代通讯设备发达、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社会现象相继出现后,意义非凡。陶瓷作为生活的衍生品和必备物,如果将陶瓷彩绘将合肥的“三国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安庆的黄梅戏”、“池州的傩戏”等皖南文化充分在合肥车厢内部进行展示流通,不乏也是艺术的创新。
个体应用。当代设计是文化展示的不竭动力,设计的文化性并不是“文化”的单一属性。文化性是“知识与信息”、“历史与传承”、“能力与学习”三位一体的综合体现。当代设计艺术仅仅有“文化性”是不够的,还应有“技术创新”与“文化创新”,就是我们过去所说的“传承与发展”。地铁中的环境导视系统的设计需要独立创新的设计思路、精益求精的制作工艺及完善人性的服务,是一种多元的产业结构。将皖南陶瓷元素符号寓意之中,不仅仅是展示城市多元文化,更是城市文明的重要表征,相信结果将是意境美妙,文化情调独具。
壁画是在建筑物墙体进行装饰的艺术载体,是建筑空间设计的重要媒介。它通常是带有主题性、教育性、装饰性等特点,在公共空间中强调的是与环境相融汇,既体现“规格化”、“程式化”的理性原则,又取得了“灵活性”、“多样性”的艺术效果。地铁空间是人流聚散地,也是文化展示区,由于人们的审美需要在壁画的材质、设色、内容上进行革新创造,地铁内部空间的文化衍生则是重要内容。由于公共空间的特殊性,合肥地铁空间在陶瓷壁画选择上,适宜高温釉下彩装饰壁画,在皖南陶瓷中寿州窑、宣州窑、青白瓷则是上乘之选。色泽明快、颜色多变与地铁空间的氛围相得益彰,既强调了装饰美感又增进了艺术气息。将皖南地区神话故事、文化典故、人文风情及生活情态通过陶艺壁画进行公共艺术展示,将社会—人—空间进行文化串联。
地铁承重柱是地铁站空间的重要依托,它给予的是另一种崇高,承载着空间屹立不倒的坚强使命。它的存在方式是特殊的,是与周围环境和谐共生的结构形态。如将陶瓷艺术语言对柱式进行局部装饰,广泛吸收皖南陶瓷的装饰手法和雕刻精华,将陶瓷构筑成形象简洁、色泽艳丽、抽象性强的语汇,将合肥古城的历史韵味和艺术内涵充分展露。
合肥地铁空间设计是安徽文化的博物馆,是徽文化各种要素构成和创造的空间场域,是徽文化自身展呈的重要路径。在众多的徽文化中,皖南陶瓷的艺术演绎更有多元性。地铁中的照明设施是复杂的、多变的。但有的照明设施则是装饰的,渲染气氛的作用。将这些陶瓷设计成灯具式样让其发挥艺术的功能性,则是设计的亮点之一。徽州自古就有三雕(砖雕、石雕、木雕)艺术,且列入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将雕刻艺术与陶瓷的玲珑瓷结合应用更是皖南陶瓷在工艺美术上的创新与传承。可以紧扣主题站点,进行陶瓷灯具设计,既强调了照明物质功能,又体现了审美的情感关怀,这种地域特色显著、文化的辨识性高的造物思维是我们应该提倡的。
动态应用。随着互联网+进入人们的生活视野且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与静态的符号元素相比较,多维动态的符号互动更具有优势可言。合肥地铁是新型科技和设计理念的多维度产物,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是审美观念和文化展示的舞台。多媒体发展和交互设计的融合在地铁空间规划中举足轻重,LED屏幕展示、手机APP、iPad、电视具备了视觉悦目、携带便捷、易读性强的特点。如果充分利用多媒体平台优势,将皖南陶瓷进行历史梳理、考古动态进行更新、陶瓷竞赛进行展示,相信皖南陶瓷的文化与学术价值将会得到深层次的探索和全方位的发展。
三、结语
皖南陶瓷元素的形成集中体现了古代先民的造物智慧与审美情趣,它完美融合了陶瓷的材料特性和精湛的制瓷技艺,加之独到内敛的装饰审美,是中国传统陶瓷技艺的代表。当代设计师深刻认识到皖南陶瓷艺术所承载的审美意图和人文意识,是安徽本身所特有的产品审美和情感需求,需要被人们重新关注和推崇。
皖南陶瓷介入合肥地铁空间设计规划,是对中国传统文脉的承传与呼应,积极弘扬“工匠精神”,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中国造物设计的整体水平。以全新的姿态和当代新视野,将地域文化与传统技艺关系进行合理整合,保护传统艺术,做到人与造物产品充满灵性。今天,我们重提传统文化就是要回归精致文化的本位,改变整个国家对文化传承发展的态度,让地域文化百花齐放、共生和谐,用文化自信接受新的机遇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