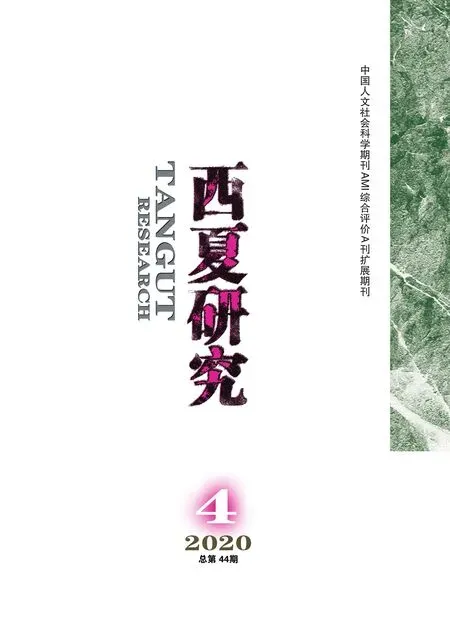破地狱与生净土:唐宋时期尊胜信仰与观音信仰结合流行现象探析
□陈凯源
一、问题的题出
唐宋时期的佛顶尊胜陀罗尼信仰(以下简称尊胜信仰)和观音信仰,向来受学者关注且著述颇丰。在大量相关文献、石经幢及造像中,反映这两种信仰结合流行的物证屡屡被发现,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已引起不少学者的注意。刘淑芬关注到尊胜经幢上兼刻其他经咒的情况,并指出尊胜经幢并刻《大悲咒》的情况最多[1]74-75。李小荣《敦煌密教文献论稿》中最早提到敦煌文献中存在《大悲启请》和《佛顶尊胜加句灵验陀罗尼启请》的合抄本,注意到《大悲启请》中将《千手经》主尊释迦牟尼换成了阿弥陀佛,并提及在宋雍熙四年(987)李恕尊胜石幢中《尊胜启请》和《大悲启请》并书的情况[2]85-87。刘永增《敦煌石窟尊胜佛母曼荼罗图像解说》一文提到东千佛洞第7 窟和莫高窟第465窟中存在尊胜佛母与十一面观音作为主尊无量寿如来的胁侍而出现的情况,认为与当时的密教信仰以及宋代法天译《佛说一切如来乌瑟腻沙最胜总持经》(以下简称《最胜总持经》)有很大的关联[3]29-45。高秀军《敦煌莫高窟第55 窟研究》认为尊胜信仰与观音信仰在满足信众现实需求、法门较为简易和具有破地狱功能方面有共通之处,并进一步总结“二经变都注重对人间现实苦难或死后世界的救度拔苦”[4]228。张亮《四川大邑药师岩新发现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及相关问题讨论》一文对四川大邑药师岩的尊胜经变的画面进行考释,并指出药师岩K7-2 这种千手观音、尊胜经变、尊胜大悲幢的组合,构成一个考虑到“现世免恶死— 死后不堕地狱— 来生得福报”的整体[5]71-81。黄璜《剑川石窟石钟寺第8窟释迦、观音和尊胜佛母组合造像刍议》以石钟寺第8 窟造像为重点讨论了观音和尊胜佛母为胁侍的造像组合,以及瓜州东千佛洞第7窟和莫高窟第465窟的此类组合,认为这种组合是依据宋代法天译《最胜总持经》,并受到当时佛教忏仪的影响,“观音负责现世利益的需求,而尊胜佛母专司度亡”[6]15-21。以上学者的论述注重从某一个点讨论这一问题,对于唐宋时期尊胜与观音结合流行的梳理还留有相当大的余地。尊胜信仰与观音信仰是如何发生联系并在数百年间结合流行的?笔者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二、文物遗存与文献资料中尊胜与观音两种内容的结合
(一)8至10世纪石窟中尊胜与观音的结合
在莫高窟的洞窟里,有多例尊胜经变和观音经变同时出现在一个洞窟里的现象。敦煌石窟保存了8 铺尊胜经变[7]429-431和29 铺观音变相①。莫高窟盛唐第217 窟,该窟主室南壁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以下简称“尊胜经变”),东壁为观音经变。同为盛唐的第23 窟也存在这种情况,窟顶东披绘制了尊胜经变,南披绘制了观音经变。对于第217 窟主室南壁与第23 窟窟顶东披的这两铺经变,过去一直被认为是法华经变,直到下野玲子《莫高窟第217窟南壁经变新解》[8]21-32一文发表后,学界开始改变过去的看法,认为这两铺经变并非此前所说的法华经变,应是尊胜经变。
若按照过去的说法,《观音普门品》作为《法华经》里的一品,法华经变与观音经变在同一洞窟中出现合情合理,但如今尊胜经变与观音经变同时出现,它们之间有着什么样的联系?除了盛唐时期的洞窟,北宋时期营建的莫高窟第55窟也存在尊胜经变与观音经变对称出现的情况,该窟主室北壁西起第一铺为尊胜经变,南壁西起第一铺为观音经变。此外,四川大邑药师岩摩崖石刻发现了一铺9 世纪末至10 世纪中叶建造的尊胜经变,该铺尊胜经变与千手观音、浮雕经幢刻于同一龛内,且三者无打破关系,显然是有规划地同时开凿[5]71-81。可以看出,在8 至10 世纪的敦煌和四川石窟中,存在着尊胜与观音图像一同绘制的情况。同样,我们在文献中也发现了尊胜类经典与观音类经典合抄的情况。
(二)9 至10 世纪敦煌文献中尊胜与观音的结合
敦煌藏经洞中保存了四件将尊胜类和观音类经典合抄一起的文献,分别是S.2566、S.4378V、S.5598 和HHT040。其中,S.2566 和S.4378V 是有题记纪年由比丘惠銮抄写的写经,两件写经的题记如下。
S.4378V号写经尾题:
比丘惠銮今者奉命书出,多有拙恶,且副来情,谨专奉上,伏乞受持,同沾殊利。时己未岁十二月八日江陵府大悲寺藏经内,写《大悲心陀罗尼》《尊胜陀罗尼》同一卷了。[9]497
S.2566号写经尾题:
比丘惠銮今者奉命书出,多有拙恶,且副来情,谨专奉上,伏乞受持,同沾殊利。时戊寅岁一月十七日在沙州三界寺观音内院,写《大悲心陀罗尼》《尊胜陀罗尼》同一卷毕。[9]507
对S.4378V题记中“己未岁”和S.2566 题记中“戊寅岁”的具体年份,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己亥岁为公元899 年,戊寅岁为公元918 年;二是认为己未岁为公元959年,戊寅岁为公元978年。②两件写经的具体年代虽无定论,但可以确定它 们 应 是9 至10 世 纪 的 写 经。 除S.2566 和S.4378V外,李际宁指出藏经洞还保存了第三件比丘惠銮抄写的写经,即世界民间藏敦煌文献HHT040。将HHT040 与S.2566、S.4378V 两件写经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这三个抄本的书法笔迹相同,应该都出自一人之手,抄书者就是比丘惠銮[10]11。那么HHT040 的抄写年代也应与S.2566和S.4378V号写经相近,即同为9至10世纪。
S.2566 和S.4378V 均抄写了《大悲启请》、《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神妙章句》、《佛顶尊胜加句灵验陀罗尼启请》以及《佛顶尊胜加句灵验陀罗尼》。HHT040写经抄写了《大悲启请》、《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神妙章句》以及《佛顶尊胜加句灵验陀罗尼启请》,其中《佛顶尊胜加句灵验陀罗尼启请》后半部分已经丢失。另有敦煌文献S.5598③,抄有《大悲启请》、《无障碍大悲心陀罗尼》以及《佛说加句尊胜灵验陀罗尼神妙章句》。以上四件文献均包括两个主要内容:一是《大悲启请》、《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神妙章句》和《无障碍大悲心陀罗尼》,实际上都是《千手千眼观音经》的衍生内容;二是《佛顶尊胜加句灵验陀罗尼启请》、《佛顶尊胜加句灵验陀罗尼》和《佛说加句尊胜灵验陀罗尼神妙章句》,实际上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衍生内容。可见,现存的9至10世纪的四件敦煌文献也存在将尊胜经内容和千手千眼观音经内容合抄在一起的情况,这种现象实际上在唐宋时期的石经幢上更为多见。
(三)7至11世纪经幢中尊胜与观音的结合
建造经幢是尊胜信仰中最主要的一项活动,《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以下简称《尊胜经》)提到:
若人能书写此陀罗尼,安高幢上,或安高山或安楼上,乃至安置窣堵波中。天帝若有苾刍、苾刍尼、优婆塞、优婆夷、族姓男、族姓女,于幢等上或见或与相近,其影映身,或风吹陀罗尼幢等上尘落在身上,天帝彼诸众生所有罪业,应堕恶道地狱、畜生、阎罗王界、饿鬼界、阿修罗身恶道之苦,皆悉不受,亦不为罪垢染污。[11]351
唐代尊胜信仰流行后,各地僧徒广树经幢,现保存下来石经幢上刻得最多的是《尊胜经》和尊胜陀罗尼。除《尊胜经》外,经幢上也会出现兼刻其他经咒的情况,其中以刻《大悲咒》④为最多[1]667-669。如唐永昌元年(689)至天授元年(690)邢台开元寺建造的尊胜陀罗尼与大悲咒合刊幢[12]68-73,唐大和九年(835)洛阳白居易宅院造的“佛顶尊胜大悲心陀罗尼”经幢[13]102-111,唐咸通十年(869)沈仕达等人在归安县(今浙江省湖州市)天宁寺造大悲尊胜幢[14]329,后梁贞明三年(917)郑义在许州(今河南省许昌市)龙兴寺所造的经幢[14]546,后唐同光三年(925)宝鸡李茂贞墓中的梵汉《尊胜经》和《大悲心陀罗尼经》合刊石经幢[15]52-60,北宋景德二年(1005)郭重显等人在其亡父母坟墓东南建尊胜大悲经幢[14]576,辽代大安二年(1086)北京房山居云寺经幢造的经幢[16]126。可以看出,在7 至11 世纪的石经幢中,《尊胜经》或《尊胜咒》与《大悲咒》合刊一幢的情况非常多,甚至出现了“尊胜大悲幢” 或“大悲尊胜幢”的称呼,反映了这时尊胜和观音两种信仰结合流行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石经幢中尊胜和观音两种信仰结合的情况,并不是局限于在某一地区才出现,而是一种在南北方各地均有出现的全国性现象。在11世纪时,将尊胜和观音两种信仰相结合又出现了新的方式。
(四)11至13世纪初造像中尊胜与观音的结合
宋代法天重新翻译了《尊胜经》并命名为《最胜总持经》,法天译本与唐代《尊胜经》最大的差别在于,由原来的世尊让帝释天教善住天子念诵佛顶尊胜陀罗尼,转变成观世音菩萨因乐闻此一切如来乌瑟腻沙最胜总持法门,而请无量寿如来宣说经典。法天译本对尊胜信仰最大的发展是规述了尊胜佛母形象,使单纯的陀罗尼信仰发展成具体的尊胜佛母信仰[6]15-21。《最胜总持经》中写道:“于像两边画观自在菩萨、金刚手菩萨,手执白拂,于像上面画净居天人降甘露雨。”[17]409尊胜佛母两侧应画观自在菩萨与金刚手菩萨,但在一些石窟造像中,尊胜佛母却与观音作为主尊佛的胁侍菩萨一同出现,如东千佛洞第7 窟中心柱东面绘有尊胜佛母曼荼罗,与之相对应的位置绘有十一面观音菩萨曼荼罗,而中心柱中央为无量寿佛,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两侧的尊胜佛母与十一面观音就有着胁侍的功能和作用。剑川石窟石钟寺第8窟主室外左侧浅龛、主室左内壁、主室外右侧浅龛三处的造像内容相同,主尊均为释迦佛,两侧胁侍为尊胜佛母与观音。莫高窟第465窟西天井也出现了主尊为无量寿佛,两侧胁侍为尊胜佛母和十一面观音的“一佛二胁侍”组合。这些例子可以说明,在法天重新翻译《尊胜经》之后,出现了人格化的尊胜佛母和观音(或十一面观音)作为胁侍成组出现的情况,并将《尊胜经》的宣讲者由释迦牟尼置换成无量寿佛,相应地图像中无量寿佛也取代释迦成为尊胜佛母和观音的主尊。尊胜和观音两种信仰结合流行,由最初的经变相辅、文字合抄转变成了尊胜佛母和观音菩萨作为无量寿佛胁侍的新形式。
通过以上对唐宋时期出现的尊胜与观音结合流行现象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两种信仰结合的时间与空间轨迹。一是尊胜和观音两种信仰结合从7世纪末开始出现,并一直延续,时代越晚这种情况案例越多,并在11世纪时发生了一次形式上的革新。二是两种信仰结合的情况,并不是地域性现象,而是一种全国性的普遍现象。赖鹏举指出:在敦煌石窟中,经变、佛传等是表达每个洞窟“造像思想”的重要工具与单元。不同类型的经变都各有其思想内涵,洞窟中不同位置及不同经变的组合,可以看出开窟高僧的造像思想。[18]1-4因此,洞窟绘制什么题材的壁画以及壁画的具体布局都蕴含着特定思想主题。同样,文献中尊胜类和观音类经典汇抄在一起,经幢上《尊胜经》(或《尊胜咒》)与《大悲咒》同刻一幢以及造像上尊胜与观音作为胁侍出现的现象也必有其特定功用和意涵。在不同场合中尊胜与观音结合的现象未必只是单纯的巧合,更有可能是开窟者、抄经者和造幢者有意而为,这就预示着这两种信仰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并能表达出特定的思想主题。
三、尊胜信仰与观音信仰结合流行的原因
《尊胜经》主要讲述了佛为善住天子免除七返恶道之苦而为其说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中提到人们诵持此陀罗尼能灭除造重大恶业者“一切罪业等障”,短命者可以延长寿命,有大恶病者除病,还能免受“堕恶道地狱、畜生、阎罗王界、饿鬼界、阿修罗身恶道之苦”[11]350-352。《尊胜经》有灭罪业、祛病、增寿及免堕恶道的功能,但其最主要的功能是破地狱。在唐代,人们特别注重此经的破地狱功能,这应与当时地狱观念的普及有着密切关系[1]9。早在东汉末年安世高翻译的佛教经典中已经有不少关于地狱的经典,如《佛说罪业应报教化地狱经》、《佛说十八泥犁经》等。佛教地狱观念传入中国后不断加深对中国民众的影响,到唐代地狱观念更是深入人心,其带来的直接影响是人们对地狱的恐惧[19]473-474。善导大师曾为弟子讲地狱诸苦,众弟子闻后,“心惊毛竖,怖惧无量,恐畏残殃不尽复还流浪”[20]430。吴道子在景云寺画地狱变相时,“京都屠沽渔罟之辈,见之而惧罪改业,往往有之,率皆修善”[21]4。在地狱观念的影响下,对唐人而言,他们除了注重祛病、增寿、净除一切恶业等一些现世利益外,更希望的是如何避免死后堕入地狱。而《尊胜经》所宣扬可净除地狱等恶道之苦及其破地狱的思想,恰好满足当时人们希望消除罪业、免堕地狱的心理,因此该经也起到了拯救众生的功能。所以,尊胜信仰的主要意涵应是拯救众生免堕地狱。
观音是大乘佛教主要信奉的菩萨之一,中国本土的观音信仰最早出现在三国时期,此后历代不衰,到宋代已有了“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的说法。据唐代伽梵达摩《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以下简称《千手经》),观音菩萨能使众生安乐,除病增寿,灭除一切恶业,远离一切诸怖畏,满足种种所求。同时,诵持《大悲咒》可不受十五种恶死,得十五种善生,“灭无量劫生死重罪”,延长寿命,医治各种疾病[22]106-111。可以说,《千手经》中所提到的诸多功德都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姚崇新、于君方认为观音信仰的主流意识是观音的现世关照,并将观音信仰的意涵归结为现世拯救[19]480-485。笔者认同二位学者的观点,但笔者认为观音信仰意涵不仅在于现世拯救,它还包含了接引众生往生净土的内容。
随着净土宗在中国民间的广泛流行,净土观音信仰在民间获得热烈响应,唐宋时期净土观音信仰在中国扎根,成为唐代以来民间极其流行的一种信仰形态[23]362-386。《千手经》载:
诵持大悲章句者,临命终时十方诸佛皆来授手,欲生何等佛上,随愿皆得往生。诵持大悲神咒者,若不生诸佛国者,我誓不成正觉。若诸人天诵持此陀罗尼者,其人若在江河大海中,沐浴其中众生,得此人浴身之水沾着其身,一切恶业重罪悉皆消灭,即得转生他方净土。[22]109
这说明诵持《大悲咒》能往生净土世界。唐代西方净土信仰广泛流行,在“净土三经”《阿弥陀经》、《无量寿经》以及《观无量寿经》中,观音主要有三种角色。其一,观音菩萨在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座下的上首菩萨,与大势至菩萨一样胁侍于阿弥陀佛身边,合称“西方三圣”,其任务是协助阿弥陀佛说法并作为接引菩萨接引众生前往极乐世界。其二,其相身可供信众观想,由此引导众生往生极乐净土,如《观无量寿经》的十六观中,第十观就是观观世音菩萨。其三,观音菩萨为阿弥陀佛的一生补处菩萨,未来将会成为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如前所说,李小荣注意到了《大悲启请》中将《千手经》主尊释迦牟尼换成了阿弥陀佛,这种情况应是在当时西方净土信仰的影响下而产生的,由此可见观音信仰与净土信仰是紧密结合的。因此,观音信仰的意涵应有两方面:一是关注现世利益的现世拯救,二是接引众生前往西方极乐世界。
对于尊胜与观音这两种信仰在唐宋时期不同场合中多次结合出现的情况,石窟造像中并没有明确的榜题或题记记载其原因,但我们能在经幢上的造幢记中找到两者为何结合流行的一些线索。唐咸通十三年(872)胄曹参军沈□尊胜大悲幢记载:“伏恐先孝府君在生之日,或有业障未得解脱,愿承此功德,永离幽□。”[14]330后唐天成三年(928)常庭训造的尊胜大悲幢上写道:“伏为先亡妻孙氏发愿造尊胜大悲幢子一所,伏愿亡妻生居净土早获人天,每近西方之极乐。”[14]595北宋雍熙四年(987)李恕造的经幢上的铭文写道:“盖闻怀罪集福,莫急于《尊胜陀罗尼》《大悲心真言》。”[24]380宋嘉祐七年(1062)张师皋大悲尊胜幢铭记载:“弟子张师皋普为四思三友,法界含识,受持诵读,救拔轮回苦,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14]621。从经幢上的记载来看,人们建造在尊胜经幢上兼刻《大悲咒》的主要目的是消除罪业、超度亡灵进而往生净土,而《尊胜经》和《大悲咒》恰好能满足人们的这些需求。
唐宋之际,佛教经忏信仰兴起,在尊胜经幢上开始出现七字一句的启请文,启请文中有“启请”、“稽首”、“回施”等佛事仪轨中经常出现的术语。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四件尊胜类和观音类合抄文献里,也抄有如经幢上出现的七字一句的启请文和佛事仪轨中经常出现的术语,其抄写年代正是佛教经忏信仰兴起之时,那么这些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尊胜类和观音类经典合抄文献很可能是当时敦煌寺院僧人在经忏法事活动中所使用的经典。前已提及宋代法天翻译的《最胜总持经》与唐代《尊胜经》最大的差别在于,由原来的世尊让帝释天教善住天子念诵佛顶尊胜陀罗尼,转变成观世音菩萨因乐闻此一切如来乌瑟腻沙最胜总持法门,而请无量寿如来宣说经典。东千佛洞第7窟和莫高窟第465 窟中,尊胜佛母与十一面观音作为无量寿如来的胁侍这种造像组合,应受到法天译本的影响。黄璜认为法天再译《尊胜经》时应受到当时佛教经忏信仰的影响,加强了观音在经中的地位,使观音和佛顶尊胜陀罗尼以及尊胜佛母信仰衔接起来。观音与尊胜佛母的造像组合起来就起到了满足现世利益和度亡的作用[6]15-21。
如果说以上的分析尚未能充分解释说明尊胜与观音结合出现的原因,那么在黑水城发现的尊胜类与观音类经典合刻文献就明确指出了这两种信仰结合出现的原因及两者之间的关系。黑水城里发现了汉、藏、西夏三种文字的《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和《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其中汉文本和藏文本的这两种佛经均是合刻在一起,而西夏文本既有合刻本又有单行本[25]81-85。值得注意的是,在部分刻本后面附有西夏仁宗皇帝于天盛元年(1149)所作的发愿文,里面记载:
御制《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并《胜相顶尊总持》后序发愿文
联伏以神咒威灵,功被恒沙之界,玄言胜妙,力通亿劫之多。惟一听于真签,可顿消于尘累。其于微密,岂得名言?切谓《自在大悲》冠法门之密语,《顶尊胜相》总佛印之真心。一存救世之至神,一尽利生之幽验……故《大悲心感应》云:若有志心以至心诵持《大悲咒》一遍或七遍者,即能超灭百千亿劫生死之罪,临命终时,十方诸佛皆来授手,随愿往生诸净土中。若入流水或大海中而沐浴者,其水族众生占浴水者,皆灭重罪,往生佛国。又《胜相顶尊感应》云:至坚天子诵持章句,能消七趣畜生之厄。若寿终者,见获延寿。遇影占尘,亦复不堕三恶道中。授菩提记,为佛嫡子。若此之类,功效极多。朕睹兹胜因,倍激诚恳,遂命工镂板雕印番汉一万五千卷,普施国内……
大悲神咒玄密语,胜相顶尊佛心印。七趣之罪尚能去,胜缘往生净土中……
天盛己巳元年 月 日
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谨施⑤
发愿文里明确提到,诵持《大悲咒》能灭百千亿劫生死重罪,临命终时,十方诸佛接引随愿往生净土,《胜相顶尊感应》则有消七趣畜生之罪,不堕三恶道的功能。代表尊胜信仰的《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和代表观音信仰的《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是西夏时期两部较为流行的经典,而西夏仁宗皇帝正是看重观音信仰中的灭罪及接引众生往生净土和尊胜信仰的不堕三恶道的功能,遂发愿雕印这两部经典以普施西夏境内。
在佛教里,净土是菩提修成之清净处所,为佛所居之处,与净土相对的是地狱,而地狱则为罪恶众生死后所生之地。大部分佛教信徒在日常生活中拜佛、礼佛、抄经造像、崇敬三宝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死后不堕入地狱、摆脱六道轮回进而往生净土世界。同样,他们在思考临终关怀问题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对现实生活的关怀。尊胜信仰强调的是灭罪、度亡以及拯救众生免堕地狱的意涵,满足了人们希望死后不堕地狱的期望,而观音信仰则从与人们息息相关的现世利益出发,照顾到了祛病、消灾、延寿等各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观音信仰还包含了人们最为看重的内容,即接引众生前往西方极乐世界。如此一来,两种信仰分工合作,既关注到了人们在世时的现世利益,又提供了死后免堕地狱和往生净土的保障,实现了从地狱向净土的转换。这两种信仰互为补充、紧密结合,对人们生前和死后的忧虑及苦难都进行了圆满的解救。因此,尊胜信仰与观音信仰功能上的互补性及人们对二者的整合是两者在不同场合下多次结合出现的重要原因。
四、小 结
唐宋时期佛教呈现出社会化的特点,人们信仰佛教的主要目的是祈求佛菩萨能满足他们的各种愿望,只要能达到这一目的,在人们心中任何宗派和神灵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人们都会共同信奉礼拜。尊胜信仰和观音信仰在功能上的互补,既满足了人们希望“永离一切诸病”、灭“一切罪业等障”等各种现世利益,又免除人们死后堕入地狱的恐惧心理,更重要的是尊胜信仰“地狱救赎”与观音信仰“往生净土”的功能,圆满地解决了人们生前死后的各种顾虑,给予了人们最大的心灵慰藉。因此,数百年间人们热衷于将这两种信仰结合起来,以期同时得到两者共同庇佑。
注释:
①罗华庆指出敦煌石窟中观音普门品变与观音经变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作为法华经变的一品,没有脱离法华经变的主题而独立;观音经变则已经脱离了法华经变而独立存在,形成以表现观音为主题的经变。详细论述参考罗华庆《敦煌艺术中的〈观音普门品变〉与〈观音经变〉》,《敦煌研究》1987年第3期。本文讨论的对象是观音信仰,因此将观音普门品变与观音经变视为一个整体,即两者均是观音信仰下的产物。
②平井宥庆、牧田谛亮等认为己未岁为899年,戊寅岁为918年,参考周一良《唐代密宗》,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第303页;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第497页。池田温、张先堂等认为己未岁为959年,戊寅岁为978年,参考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第497页、第507页;张先堂《古代佛教法供养与敦煌莫高窟藏经》,《敦煌研究》2010年第5期。
③郭丽英认为S.5598虽未记年月,但从其内容和字迹判断,该写经应为10世纪末至敦煌藏经洞封闭前的写本。参考郭丽英《佛顶尊胜陀罗尼的传播与仪轨》,日本《天台学报》特别号,2007年。
④《大悲咒》即《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的简称,特别指其中的《大悲心大陀罗尼神妙章句》。参考李小荣《敦煌密教文献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92页。
⑤引文主要参考俄藏黑水城文献TK164、TK165的汉文本和俄藏инв.№6796(6821)号西夏文本的汉译本辑录标点而成。参考段玉泉《西夏文〈自在大悲心〉、〈胜相顶尊〉后序发愿文研究》,《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