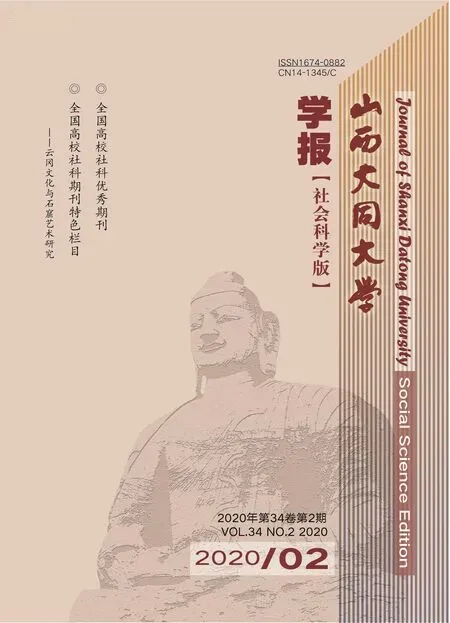中古地域集团学说之用于汉末吴蜀研究综述
王 勇,李 皓
(山西大同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山西 大同037009)
一、引言
中古时期地域集团学说之滥觞于20 世纪三四十年代陈寅恪提出的“关陇集团”理论,为后学研究中古时期的政治问题,特别是涉及权力斗争的问题时,联系、比照现实,更容易看清历史事件的本质提供了新的视角。随后,陈门弟子及其他的诸多学者均对这一理论或深入挖掘,或提出商榷,促进了这一学说的发展。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类似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几已成为研究中古史的基本路径。之前,范兆飞、仇鹿鸣等学者均已对此类学术成果作出学术性的总结,但仍主要集中于“汉—魏—晋”的学术梳理,或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研究综述,对于汉末吴蜀则着墨甚少。有感于此,故以汉末吴蜀的政治史事为基础,以中古地域集团学说为线索,对此近百年政治史史事的研究作一综述。
二、中古地域集团学说之用于汉末研究
东汉末年,朝廷混乱,各地烽烟四起,汉政府已摇摇欲坠。尤其是公元189年董卓进京以后,政局更是变得动荡不安。方诗铭继承其师陈寅恪中古地域集团学说的理论方法对汉末西部并州集团与凉州集团的分合、东部袁绍与曹操集团的内讧进行了研究,并要求引入“集团”这一概念对历史事件进行深入剖析。
在此时期,率先登上历史舞台的便是以董卓为首的凉州军阀集团,该集团骨干均为凉州籍,又带有极强的人身依附关系,因此带有明显的集团性和地方性。凉州军阀集团操弄朝政、纵横陕洛关陇,其活动一度构成了中原和西北地区政治局势的主格,也波及到了西北民族关系等方面的演变。董卓纠结凉州各方势力,在平定羌胡叛乱中崛起,更吸收大量羌胡人士,接纳了以吕布为首的并州武人集团,极大提升了自身实力,从而在汉末乱世中得以迅速成长,得以入主中原、主持朝政。但也引发了与关东党人集团的对抗,形成了汉末第一次不同集团之间的对抗,其实质似是关西武人与关东党人文士之间的对抗。
对于凉州武人集团的考察,方诗铭具体分析了凉州军事集团的领导阶层和士兵“成分”,得出其领导阶层的“凉州人化”和士兵阶层的“羌胡化”,大大增强了该集团的凝聚力和战斗力。[1]李纪言在《汉末关西诸部兴亡述论》中探讨了关西诸部联盟(凉州武人集团)的四次分裂:一是凉州官军与并州官军的分裂。二是凉州官军与凉州叛军的分裂。三是凉州官军内部的分裂。四是白波军与凉州官军之间的分裂。王北固在其文章《凉州兵团在三国史上的特殊地位——从马超助刘备取蜀说起》中则通过时空观念来界定“凉州兵团”,从灵帝中平六年(189 年)至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 年)分为四个阶段:一是董卓;二是李傕、郭汜、樊稠;三是张绣;四是马腾、韩遂。前两个阶段是其对东汉政权的摧毁,后两个阶段则是其为曹操、刘备所用,成就霸业。赵立民在《论汉魏之际的武人研究》中,进一步划分为:第一层次:“凉州三明”——皇甫规、段颖、张奂,努力寻求武人士人化,维护和支持东汉王朝;第二层次:皇甫嵩、董卓,二人一人扶汉,一人乱汉;第三层次:牛辅、李榷、郭汜、段煨、张济等在董卓亡后再次祸乱天下;第四层次:马腾、韩遂为汉末割据势力,后投降曹操;第五层次:张绣、马超、马岱、姜维,除张绣降曹外,其余均归属刘备。
对于并州武人集团的考察,方诗铭探讨了其形成、发展直至灭亡的过程。以丁原、吕布为首的并州集团和董卓的凉州集团同为何进所依靠的两支力量,后董卓诱吕布杀丁原,并吞并州集团,但由于董卓轻慢吕布,加之以胡畛为代表的凉州集团与并州集团不相容,被王允等士大夫利用,吕布遂击杀董卓,与凉州集团决裂,其后,形成了吕布、张辽、张杨三人组合的并州军事集团(三人各有地盘),最终吕布、张扬被杀,张辽降曹,并州集团灰飞烟灭。赵立民对这一集团的研究则将其分为了三类,即丁原、吕布和张扬、张辽。
与西部凉州集团和并州集团的分合相对应的是东部地区袁绍集团与曹操集团的斗争。方诗铭考察了袁绍集团的具体情况,指出袁绍集团应在冀州形成。袁绍因与董卓不和,出走冀州,其后经过发展形成了以荀谌、辛评、郭图等为代表的颍川集团和以审配、田丰、沮授等为代表的河北集团。并依靠这两个集团相继夺取幽、并、青三州之地。但在官渡之战之中、之后,由于袁绍未能解决颍川、河北两智囊团之间,以及家族内部之间的矛盾和火并而最终走向消亡。
方诗铭对于曹操集团的考察则主要限于初期。曹操早年在洛阳期间,即和袁绍、张邈、何颙、许攸等人结成了以袁绍为首,或以袁绍、曹操两人为代表的袁、曹政治集团,以反对宦官。后董卓进京,袁、曹不得不出走,分别前往冀州与陈留。其后,曹操在袁绍的支持下相继出任东郡太守,兖州刺史,并相继剪除威胁兖州的内外势力,取得了兖州的绝对控制权。在此期间,袁、曹双方暂掩矛盾,携手合作。之后双方矛盾才逐渐公开化,并在官渡之战后得以最终解决。而袁、曹集团的合分也深刻地影响着天下大势。
三、中古地域集团学说之用于蜀汉研究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王仲荦先生指出“焉入川时,亲戚故旧,跟着他的人很多,形成一个政治性的集团......这一政治集团就是依靠‘东州兵’作为他们的主要武装力量。”[2]因此形成了以刘焉、刘璋(焉子)为首的“东州集团”。但随着刘焉等外来势力的发展,引发了益州地主的不满,双方火并,虽最终以刘焉的胜利收场,但此后的十几年间双方矛盾始终存在。随后,以张鲁为首的五斗米道盘踞汉中,严重威胁益州,以张松为代表的益州土著地主集团企图借助外来势力(荆州刘备)推翻刘璋,而刘璋也想借助外来势力对内镇压益州土著地主集团,对外打败张鲁。在这样的情况下,刘备便带领以诸葛亮为首的荆州集团进入益州,随后又占据汉中、荆州一部,建立了蜀汉政权。因此,蜀汉政权实为刘备的荆州集团、刘璋的东州集团和益州(巴蜀)土著豪强集团共同构成。
20世纪八十年代初,田余庆在其著作《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中,“根据蜀国统治集团组成状况及其变化,探索诸葛用人背景......”在用人问题上对蜀汉政权的集团构成进行了分析与考察。指出当时支持刘璋的势力为陆续进入益州的南阳、三辅人为主的“东州人”及其他外来人;两种益州势力,一为原仕洛阳、后随刘焉回籍的益州官僚;一为益州本地的土著豪强。而刘焉正是与其形成了相互利用、相互依存的关系才得以在益州立足。也因此形成了以刘焉、刘璋的东州集团为代表的客(新)与以益州土著豪强集团为代表的主(旧);以及刘备集团进入益州以后,融入刘璋旧部的客(新)和以益州土著豪强集团为代表的主(旧),且存在于蜀汉政权的始终。
随后,一些学者在以上的成果上进一步进行研究,黄昊在其文章《蜀汉荆州集团与益州集团》中认为,蜀汉政权除刘备身边起家功臣以外,其立国得益于荆州集团和益州集团的支持。白杨、黄朴民在《论蜀汉政权的政治分化》中则指出,蜀汉政权是由“刘备微时便跟随其征战南北,漂泊四方的兄弟级人物组成”的草莽势力,如关羽、张飞、赵云、糜竺、简雍等;“寄寓荆州刘表期间,所延揽、笼络、收买的荆襄人物”的荆襄势力;进入四川后,所接纳的刘璋部分旧属与益州当地豪强、士人的益州势力;带领部曲投奔刘备的一些实力人物,即外附势力四大部分组成,另有雷近芳、贾海鹏等将其分为故旧集团、荆襄集团、巴蜀集团与甘陇集团。
在探讨蜀汉政权内部各集团关系的问题上,各家皆有其见解,其相同之处多着眼于各不同集团之间的合作,故笔者拟就不同之处进行对比展示。王仲荦认为刘备及其继任者在益州统治的稳定,在于对各集团人员的使用均照顾到。如原有的“荆楚群士”:诸葛亮、霍峻、陈震、刘邕、董恢、辅弼、邓芝、蒋琬等。刘璋旧部即原来的东州集团:法正、李严、吴懿、董和、董允(董和子)、费祎、刘巴、吕艾等。而对于益州土著地主集团则一方面拉拢有用人才,如杨洪、何袛等;另一方面又严厉打击不稳妥的人物,如彭羕、张裕等。田余庆认为前期有刘焉、刘璋东州集团与益州土著集团的对立,后有刘备集团(融合了东州集团)与益州土著集团的对立,而这其中则包含有刘备荆州集团与刘璋东州集团的合作与融合。
田余庆在探讨废黜李严原因时即指出,废徙李严是“解决新人旧人之争的关键”,是秉承以荆州派为主、极力拉拢东州士,共同压制益州集团的用人路线的具体实施。张承宗、郑华兰在《蜀汉人士与蜀汉灭亡》一文中也指出,蜀汉的用人路线为“坚定地依靠荆州地主集团,团结和信任东州地主集团,排斥和控制地使用益州地主集团,并且不让后者进入政权的中枢机关。”朱子彦在探讨荆州集团的代表人诸葛亮选择接班人问题时,也指出诸葛重用襄阳大族出身的马谡,相继培养荆州集团的蒋琬,东州集团的费祎,甚至是曹魏降将姜维,而对于益州集团出身的马忠、张巍等却不予重用。而在探讨孟达败亡原因时亦认为孟达在蜀魏之间的反复与败亡实为蜀汉政权内部荆州集团与东州集团的斗争的牺牲品,是荆州集团借打压孟达来限制东州集团的发展,要求维护荆州集团的主导地位。[3]
在不同集团之间的矛盾问题上,黄昊认为荆州特殊的地理位置,聚集了大量中原地区避难名士,他们思想开发,要求建功立业。而益州集团所处的“益州地区受盆地影响,相对闭塞,益州人士心态保守......具有很强的排外性。”因此双方矛盾重重,在刘备托孤之后开始激化。虽然荆州集团的地位仍高于益州集团,但双方实力的转化已不可避免。在蜀汉后期,由于两大集团的内斗,蜀汉政权已十分衰弱,而此时益州集团已占据主导地位,并推行其“亡国主张”,最终得以实现“蜀人治蜀”,彻底瓦解荆州集团。白杨、黄朴民认为蜀汉政权内部存在着“刘备早期的草莽势力与后来吸收的士大夫阵营的矛盾,以及荆襄势力与益州势力的矛盾,而后者正是贯穿蜀汉政权灭亡始终的线索。”
四、中古地域集团学说之用于孙吴研究
在将中古地域集团学说用于东吴的研究中,田余庆可谓是居功崛伟。田氏将此说用于东吴研究以前,就已从新旧、客主剖析蜀汉政权的政治势力与人事斗争,还考察过曹魏政权中的青徐豪霸问题,提出过自己独到的见解。然其在东吴研究上用力更深,提出了两个地域集团:外来的淮泗集团、本土的江东集团。同时认为这两大集团的逐渐走向融合,而融合的方向正是东吴政权的江东化。[4](P262-327)孙策过江之初,实为代袁术征伐,其率领的军队也是以淮泗人为主体,之前又曾攻击刘瑶,故不受江东大族的待见,尤其是吴郡人士。加之孙氏本身并无强大的宗族势力,孙坚死后又短暂依附于袁术,使得孙氏势力更为衰弱,因此在孙策平定江东,孙权治理江东期间,对于陆续加入的淮泗集团和江东大族这两股势力必须加以倚重,而淮泗集团作为最早跟随孙氏的势力也必然成为其“心腹”。
在集团的分野这一问题上,大多数人还是基本认同田氏对于淮泗集团与江东集团的划分的。高敏认为孙权统事之初所重用和依靠的仍是淮泗武人集团中人物以及北方流寓江东的士人地。但与此同时,孙氏父子也在加强其宗亲势力,借以巩固权力,故实际上孙权当政之初是北方地主集团(淮泗武人集团和北方流寓江东的士人地主)与孙氏宗亲之间的联合执政,而矛盾也恰恰在此时开始显现并激化。孙权当政时期,通过平定山越、开疆拓土等战功使孙氏宗亲获得“世袭领兵、世袭领郡及食奉邑、自置长吏等特权......使孙氏集团成员变成了世官、世将型的特权地主阶层,并与江东地主融合,引起江东地主集团同北方流寓地主集团在权力分配方面的矛盾斗争。[5]王令云在《试论孙吴时期淮泗集团的兴衰》一文中则认为,淮泗集团与江东大族在政治目标、经济利益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淮泗集团要求积极进取,开疆拓土;而江东大族则只要守土自保,以维护自身在江东的地位和利益。
在双方的矛盾演化过程中,对于曁艳案、吕壹事件、二宫之争最为典型。庄辉明在其文章《暨艳案与吕壹事件再探讨》中,认为此三案为孙权在位期间两大集团的激烈冲突与较量,是彼此力量消长的产物和表现。王令云、翟清伟均认为这是孙权为消除日益崛起的江东大族的威胁,平衡各方势力而制造的矛盾冲突。但与这些观点相反,朱子彦在探讨二宫之争时否定了两大地域集团在此期间的矛盾,认为两大集团虽分属南北两个地域,但并无大的利益冲突,还进一步指出有吴一代的党争仅仅存在于孙权执政后期,无地域之分,应为太子党与鲁王党之争。[6]
在两大集团之间,若隐若现的穿插着孙氏宗亲的身影。高敏从地域的角度考察,认为其当属于江东集团。王令云也基本持此观点。翟清伟则认为孙氏当属外来势力,与淮泗集团当为同一势力。
在两大集团的矛盾对立与融合发展中,始终还是以融合发展为主流的,也就是田余庆所言的“江东化”,即孙吴政权与江东大族的结合,或者说是以淮泗人为主体的政权转变为以江东人为主体的政权。在实行过程中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建安末年以前,群吏爪牙兼用江东人;在建安末年至黄武年间,顾、陆先后成为当轴主政人物;黄武年间及以后,全面的江东化。“孙吴政权完成了江东地方化,大大巩固了政权。”王令云、翟清伟均认同田氏东吴江东化这一观点,不过二人更强调这一过程中淮泗集团由于远离故土、人才凋零、以及政治斗争中遭受打击而逐渐衰落;与此同时江东集团的日益崛起也引起孙权忌惮,并加以打压,试图平衡双方势力。
对于孙吴政权后期,即孙亮、孙休、孙皓时期的相关研究极少。由于孙权安排的辅政大臣是以诸葛恪为首的淮泗人士,故江东大族深受打压,但已不可改变孙吴政权的基础是江东大族。随后代表孙氏宗族势力的孙峻上台,但此时淮泗集团、孙氏宗亲、北方流寓士人等均受到沉重打击,江东大族的势力却在逐渐回升,因此淮泗集团不可避免的走向末路。
综上所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学者对于孙吴政权的研究基本上仍是在田余庆的成果之上,整体成果不大,亦因此可见田氏于孙吴研究之功力。
五、中古地域集团学说在海外的应用及其商榷
海外对于汉末及吴蜀的专门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汉末和蜀汉,可谓是凤毛麟角,而孙吴相对多一些,不过也大都包含在江南六朝的研究之中。笔者所见,对于中古地域集团学说的应用有渡边义浩《孙吴政权的形成》、《孙吴政权的展开》两文。在日本八九十年代的学界,延续之前京都学派对于六朝贵族制、豪族共同体等理论,以及森正夫、谷川道雄等人所提倡的地域社会研究外力的刺激下,始有渡边氏之文。其文章详细考证了在孙吴政权中北来的名士与江东的名士之间的关系,及其与孙吴政权的关系,以及在孙吴政权的建立、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
地域集团学说作为研究中国中古史,尤其是政治史的一把钥匙至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学界臻于鼎盛。于此同时,批评的声音随之出现,岑仲勉考察了太宗朝25 名宰相的籍贯出身,发现其中有18人并非出自关陇地区,而主要分布于江左、河东以及江南等地区,并进而得出早在隋朝中后期就已开始打破关陇集团。[7](P166-168)黄永年在岑仲勉研究的基础上,将籍贯出身的考察扩展至隋朝中央,唐高祖时期的宰相、太宗凌烟阁功臣,断定关陇集团的存续时间只限于西魏北周时期,杨坚建隋后开始松动,逮炀帝杨广时,即正式解体,李唐初年早已不复存在。[8](P154-182)辛德勇继承其师黄永年的观点,大胆指出“在研究北朝隋唐史时,搞出‘关陇集团’这样的名堂,并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甚至可以说是多此一举的事情。”认为“集团学说”或“集团分析法”是在“文革”结束以后特殊时期语境的产物,加之对陈寅恪的敬仰,遂在八九十年代大行其道。台湾学者黄炽霖通过统计数据的方法研究孙吴地方行政官员的地域分布及政治派系时也得出了与田余庆等人所用地域集团学说不同的结论。[9]
与上述学者相对应的是,仍有大量学者支持这一学说,并进行深化。在雷艳红的《陈寅恪“关陇集团”说评析》、李万生的《说“关中本位政策”》两文中,提出关陇集团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岑、黄二人只注重了其狭义的一方面,而忽视了广义的关陇集团。范兆飞在关陇集团的问题上将其核心要素概括为“ (a)西迁胡人;(b)胡化汉族;(c)割据关陇地区;(d)与江左、山东对峙;(e)物质和精神上的融合之道。”同时又将中古地域集团进一步细化,“将之分为两种类型:山川流域型和行政区划型。”在地域集团中“隐然包含着文武、胡汉、质文、东西、南北等多重二元对立的概念”,同时还要考虑到“地域集团中的人物关系、角色认同及身份变迁”。[10]仇鹿鸣认为陈寅恪于中古史的最大贡献正在与其所提供的研究范式,即“运用政治集团说,结合地域、社会阶层、文化等诸多因素的观察分析,勾勒出两个或多个互相对立、制衡的政治集团,并以此作为了解中古政治史演变主要线索的研究方法。”并指出将研究建立在史料批判的基础之上,无证不信,溯本清源,更好的挖掘史料的内涵;在方法论上不能过度依赖政治集团的研究范式,要有所反思,充分考虑其背后政治、社会和文化三方面的因素。[11]
六、结语
综上所述,陈寅恪所发明的地域集团学说,犹如一把钥匙,打开了探索中古时期纷乱历史的大门:万绳楠提出曹魏时期的谯沛集团与汝颍集团,王仲荦提出蜀汉政权的荆楚集团、东州集团和益州土著集团,田余庆提出孙吴政权的淮泗集团和江东集团,蜀汉政权的外来新人与益州旧人,东晋政权的侨姓士族和吴姓士族,以及南北朝各政权之中的集团势力对抗等等,促进了中古史研究的发展。但自进入21世纪以来,该学说的弊端也日益显露:政治集团缺少准确清晰的定义、集团之间的简单二元对立、论证逐渐固化,导致中古政治史研究出现“边缘崛起,中心陷落”的不利局面。
对此,范兆飞认为,“中古政治史的研究,需要在使用地域集团学说的时候,保持足够的清醒,注意其适用的范围和边界......如以陈寅恪关陇集团理论所包含的要素而言,学人多从地域和家族入手,未能充分关注陈氏强调外来势力关中化的要素。田余庆的孙吴政治史研究,契合关陇集团的五个要素,尤其强调江东化的历史进程,卓然成为不朽之作。又如学人提倡的史料批评当然重要,但史料开拓同样不可或缺......或从社会阶层的纵断面进行分析探讨,或从地域集团的横断面进行分析探讨......需深入挖掘的是:地域集团的载体——地域单元的边界选择(可考虑以方言区为准),和地理空间及乡里社会的互动关系,以及地域集团的政治人物作为自然个体所擅长的方言、经历的身份变化和角色转换。”[10]
概而言之,一是从地域集团学说这一范式出发,要充分考虑到地域政治集团的政治、社会、文化、经济、等因素,尤其是地方化这一极易被忽略的要点;同时还要考虑到地域划分的多样性,或东西、或南北、或山川河流、或行政区划等,尝试从不同角度进行划分、组合,以发现其共性或特性,从而进行研究。二是关于史料的问题,要求我们广泛挖掘史料,如出土文物、墓碑墓志铭、古人笔记小说、家谱,甚至是口述影像资料等,只有通过详尽的考证,才能建立起详实的立论基础,进而通过精当的分析,从而洞察历史的幽隐,并归纳抽象,建立新说新论。三是充分利用各种理论方法,如布罗代尔的三时段理论、李开元三层次史学层次模式理论、建构主义和解构主义、计量史学、比较史学、跨学科交叉研究等史学研究方法进行实证性研究,挣脱传统的束缚,进而拓展中古政治史研究的议题、边界与内容。凡此种种,利用地域集团学说的中古政治史研究仍可以拥有一片新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