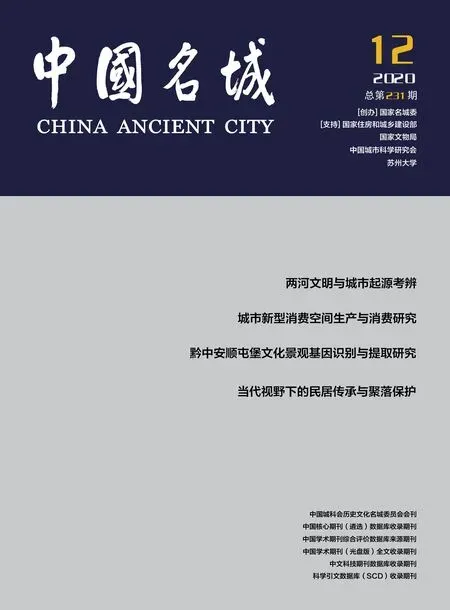两河文明与城市起源考辨
曹昌智
导语
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有着45.5亿年的邈远历史,大约250万年以前地球上才开始出现人类。从那时起,人类由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举步,经历漫长而又艰辛的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终使蛮荒世界迎来文明的曙光。文字发明、金属工具制造、城市诞生、礼仪制度建立和国家出现,标志着人类步入文明社会,从而带来亘古通今的城市演进与兴衰。
1 脱胎于邈远原始村庄聚落的早期城市
大量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和考古发掘表明,人类文明产生于公元前3500年,距最初非洲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africanus)进化成具有思维能力的智人,远隔7万多年。那时候地球上相继出现的人类文明几乎都集中在了北纬30。附近的欧亚大陆和海域。这是个被称为最适宜人类生存活动的亚热带和温带过渡区,得益于大自然的禀赋。大自然是生命之源,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正如马克思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1]
人类依靠大自然赐予的陆地和海洋分别创生了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农耕文明的主要发祥地分布在西亚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两河流域,非洲北部的尼罗河流域,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河、恒河流域以及东亚的黄河、长江流域。这些区域气候温和,而且陆地资源来自大江大河长年累月形成的冲积平原和沉积平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用于农业灌溉的水资源丰沛,适宜农作物生长,作为最早出现的人类文明,被冠以“世界大河文明”之称。它们分属于世界著名的四大文明古国,即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古代中国(图1)。
人类最早正是从四大古老的国度迈进了文明社会的门槛,具备了由脱离新石器时代野蛮状态的社会行为和自然行为所构成的文明要素特征,不仅在劳动中创造了语言,而且先后发明了古巴比伦楔形文字(Cuneiform script)、古埃及象形文字(Pictograph)、古印度印章文字(Seal character)和古代中国的甲骨文(Oracle bone script)。与此同时,人类还发明了金属冶炼技术,制作出各种青铜器具和工具,并且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上,随着分散定居点及聚落演化的嬗变,渐渐孕育了城市文明的胚胎。主导这一规律性变化的内生动力,是新石器时代农耕经济发展带来的农业剩余产品,以及由此引起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那次社会大分工使得手工业同农业分离,也将城市文明的胚胎从原始村庄聚落发育成以手工业为中心的早期城市。于是手工技艺开始变得专门化,商业贸易也成了专门的行当,人类社会由此产生了阶级和阶层。
美国著名城市理论家、社会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从对远古时代村庄的观察研究和文献考证中发现:尽管新石器时代的村庄因物质环境阻隔造成与世隔绝,沉湎于自我封闭的生活方式,文化近乎静止僵固,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以致村民秉持自我满足的心理状态安身立命,但是包括物质结构和组织结构在内的早期城市胚胎构造却已存在于村庄之中。他认为,“城市的建筑构造和象征形式,很多都以原始形态早已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村庄中了:从更晚一些时期的证据中还可推断,连城墙也可能是从古代村庄用以防御野兽侵袭的栅栏或土岗演变而来的。……村庄的秩序和稳定性,连同它母亲般的保护作用和安适感以及它同各种自然力的统一性,后来都流传给了城市。”[2]换言之,城市脱胎于远古时代的村庄。当村庄聚落孕育的城市文明胚胎及其萌芽随着人类社会进化到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诸多文明要素从雏形到逐渐成熟和完备,也就使得原有的村庄实体产生了质的变化,发展为具有城市功能的复杂结构。诚然,远古时代的村庄演化嬗变为城市,经过了极其邈远的渐进过程。人类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创造了文化,处于萌芽状态的城市是文化的一种外在表征。在人类文明社会到来之前,城市物质结构和组织结构的胚胎构造发育生长日臻成熟,显现出与城市功能匹配的空间形态特征。
这些萌芽状态的城市最早出现的年代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那时的城市已初见雏形,只不过规模较小,形态多样,尤其在人口职业构成、聚居规模和社会管理的功能上还没有与村庄形成本质的区别,并且缺少复杂的大型宗教礼仪建筑和交易集市,也没有建立起足以管控处理复杂社会中和秩序、安全和效能等相关问题的国家制度,因此按照国际社会判定人类进入文明状态的标准,处在萌芽状态的早期城市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只不过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氏族社会农村聚落中心。

图1 世界大河文明分布图
美国杰出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指出,“人类必须先获得文明的一切要素,然后才能进入文明状态。”[3]他所说的“文明的一切要素”,自然不仅是指城市空间形态及其文化的外在表征,而且包括文字的发明与使用、金属冶炼术的发明、器皿工具的制作、礼制建筑的建造、城市手工业和商业职能的形成、阶级社会的产生以及国家制度的建立等等。尽管这些要素在不同部落、不同地域、不同国家出现的时间或早或晚,各种要素出现的顺序有先有后,然而在进入文明状态以前的每一个阶段中,随着人类的发展步步向前,诸多文明要素的孕育成长必然处于并行的过程,直到一切要素完备。因此判定文明是否形成,早期城市的物质结构和组织结构是否过渡到文明时期,应当综合分析进入文明状态的一切要素是否完备和成熟,而不是仅凭单一文明要素妄下结论。例如只有文字发现或者只有萌芽状态的城市形态特征,还不能简单地断定进入了文明状态,创造了城市文明。这对探索城市起源和世界上最早诞生的城市至关重要。长期以来,包括学术界在内,观点和论述莫衷一是,症结就在于没有清晰界定文明要素和文明状态之间的区别。
事实上,对人类文明和城市起源的研究曾有一个再认识的过程。正如英国历史学家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和美国历史学家卡尔顿·海斯(Carlton J. H . Hayes)合著的《全球通史——从史前文明到现代世界》所言:“早先,人们曾经一度认为是尼罗河哺育了人类最早的文明,但是现在人们一致认为人类文明诞生之地是苏美尔。在基督教的圣经《旧约全书》中说到的希纳国,指的就是这里。”[4]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S. Stavrianos)的著作《全球通史》同样说:“有一时期,人们曾认为文明的摇篮是尼罗河流域,但现在一致同意,最早的文明中心是苏美尔,也就是《旧约全书》中的‘希纳国’(Land of Shinar)。”[5]人们之所以从再认识中获得重新判断,主要基于20世纪初两河流域特别是苏美尔古城遗址考古发掘的新发现,证明人类文明要素之一的城市最早诞生在两河流域,并不在尼罗河流域的埃及。然而彼时苏美尔城邦林立,究竟哪座古城始建年代最早,学术界也不乏争议。按照苏美尔人的传说,公元前4500年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埃利都(Eridu)已经具有相当规模,人口可能多达5 000人。这座古城由一座泥砖神庙和围绕在神庙四周的许多泥砖房屋组成;社会上层聚居在神庙周围,手工业者居住在外围,所有的农民生活在远离神庙的地方[6]。但是迄今考古发掘未发现埃利都具有文明社会完备的城市功能,就本质特征分析,它依旧属于从原始村落型仪式中心逐渐成长起来的城镇。这种现象在野蛮社会高级阶段向文明社会过渡时期相当普遍。
1877年摩尔根出版了足以震动西方史前史学界的重要著作《古代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评价摩尔根的这部鸿篇巨制“像达尔文的著作对于生物学那样具有决定意义”[7]。在这部论著中,摩尔根指出,“在回顾人类进步过程时,可以注意一点,那就是:在低级野蛮社会中,各个部落常住的家是用栅栏围起来的村落。在中级野蛮社会中,开始出现了用土坯和石头盖造的群居宅院,似于一个碉堡。但到了高级野蛮社会,在人类经验中,首次出现以环形垣垒围绕的城市,最后则围绕以整齐叠砌石块的城郭。”[3]马克思和恩格斯赞同摩尔根关于远古时代村庄聚落向城市进化的观点,“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过渡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8]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被认为是法国著名史学大师,声望显赫为史学界难以超越,在西欧学界也享有崇高地位。他从文明的角度,总览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对城市的属性作过专门研究论述,在其巨作《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中明确说:“文化和文明之间这些区别的最明显的外部标志,无疑就是存在和不存在城市。在文明阶段,城市大量存在;而在文化之中,城市仍然处于萌芽状态。”[9]布罗代尔所说的文明阶段和此前摩尔根所说的文明状态是一致的,都把原始村庄聚落具有的早期城市文化表征与进化到城市文明的标准区别开来。
2 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在两河流域诞生
迄今国际社会对于人类文明史、古代社会史和全球城市史的研究不过100多年的时间。在过去一个很长时期内,由于受认知世界历史的能力局限,以及在判断人类文明标准上存在很大差异,所以对城市起源和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城市所持学术观点和见诸文字的表述众说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直到通过对近代考古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成果的不断求证,人们的认识才渐趋一致。
前述两部《全球通史》都提到人类文明的诞生地希纳国(Land of Shinar),在中文版《新旧约全书》和《圣经》以及多种版本的《圣经故事》里,又译作“示拿地”(shinar)。《圣经》描述上帝创世过程,说上帝让洪水清除了地上所有的深重罪孽,然后吩咐挪亚和其家人走出方舟,开始新生活,叮嘱他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大地。洪水过后,挪亚3个儿子的后裔分赴各地建邦立国。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于是就在那里住下来。这片被《圣经》称作“示拿地”或“希纳国”的平原,正是位于两河流域诞生苏美尔文明的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即今伊拉克南部。
美索不达米亚在希腊语中意为“两河之间的土地”,是学术界称作“新月沃地”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冲积平原,也是原始村庄向城市演化嬗变的理想环境。两河均由土耳其东部山区发源,自北向南穿越高山丘陵,进入地势较低的平原,下游交汇在一起,注入波斯湾。两河之间的南部地带由于常年洪水冲积形成三角洲。这方自然禀赋优厚的土地广阔平坦,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沼泽和湿地,成为哺育人类早期文明的摇篮。
公元前5000年以前,苏美尔人就已经在这里定居,最早把原生谷类、大麦和小麦培育成可食用的农作物,开始饲养家禽、牛羊,还利用沼泽水域捕获丰富的鱼类、野禽和小猎物,使新石器时代的劳动产品有了剩余,提高了原始村庄的生活、生产技术水平,进而在向城市演化聚合中,实现了原始的新石器时代部落从文化到文明的飞跃。大约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3000年,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城市体系。苏美尔人开启了以两河流域文明著称的人类文明,其标志性特征是城市起源和诸多城邦国群聚。苏美尔人率先创造了城市,催生了城市文明。在美索不达米亚被沼泽和湿地分隔的平川谷地上,建起若干个独立的城邦(city-state)。每个城邦以城市为中心,连同周围的乡村构成城市国家,形成小国寡民的鲜明特征,对世界城市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欧洲文明发祥地希腊的城邦兴起就源自这里(图2)。

图2 两河文明地理位置示意图
两河文明时期,国家最基本的单位是城市。城市周围是大片的农田和复杂的水系灌溉网。这与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256年中国商周时期的众多诸侯国颇为相似:城是诸侯国和城邦国的主体,所以城也有国的称谓,一城即一国,一国即一城,营城与营国有着同样的含义,均标志人类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制社会,也都出现过群雄争霸的局面。所不同的是,中国古代诸侯国以家庭为核心,以血缘为纽带,尊奉祖先崇拜、嫡长子继承和分封制度,是一种家国同构的社会形态;而苏美尔城邦却是以各自共同的族群和地缘建立起来的城市国家,敬畏崇拜自然神灵。在诸侯国代表王权政治的主要建筑是宫室、朝寝、标志宗法血缘政治的宗庙以及专事天地崇拜仪礼的社稷,宫室居中而立。苏美尔城邦中最权威的建筑莫过于供奉守护神明的大神庙和代表王权政治的国王宫殿。神庙体现城邦国的权力中枢,置于城市最主要位置,祭祀所有神明中地位最高的主神。国王以下是祭司阶层,由祭司主宰城市,主持宗教仪式和管理寺庙社区,以神的名义控制所有公共资源和剩余劳动产品的分配。社会结构除了国王、祭司和武士以外,还存在着由神庙共同体中的“专门人员”、自由农民和奴隶构成的3个阶层。那时的“行政机构、社会机构和经济机构已发展到足以处理(不论如何不完善)一个复杂社会中与秩序、安全和效能有关的问题”[10]。这些城邦国规模较小,大多以运河、界石分割属地,围绕城市周边的疆域十分有限。为避免周期性洪水灾害的袭击,城市选址基本都在大型台地上。苏美尔最具典型意义的重要城邦当数呈三足之势,相距较近的乌尔(Ur)、乌鲁克(Uruk)和拉格什(Lagash)。令人惊叹不已的是,起源于两河流域的城邦国和诞生在黄河流域的诸侯国地隔遥远,分属西亚和东亚,在自然地理环境完全不同、毫无信息联系的两大地域,竟然有着高度相似的创造城市文明的智慧。这足以表明人类从原始社会迈入奴隶制社会的进化过程,有着几乎同等的社会认知能力和思维方式的规律性。正如摩尔根指出的那样:“人类的经验所遵循的途径大体上是一致的;在类似的情况下,人类的需要基本上是相同的;由于人类所有种族的大脑无不相同,因而心理法则的作用也是一致的”[3]。
3 发现苏美尔人创建的第一座城市——乌尔
公元前3000年,两河流域苏美尔城邦林立,乌尔古城是这些城邦里最先建造的城市,也是苏美尔人的乌尔王朝都城。《圣经》中希伯来人的祖先亚伯拉罕就诞生在乌尔。乌尔城址位于幼发拉底河下游的穆盖伊尔,在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东南约300 km。这座古城最初规模并不大,保存下来的遗址也不完整。美国著名城市史和城市问题研究权威乔尔·科特金(Joel Kotkin)在《全球城市史》中,援引澳裔英籍考古学家戈登·蔡尔德(Gordon child)所著《历史中所发生的故事》,说“这些城市聚落最早可以上溯到公元前5000年,但按照现代甚至是古典的标准来衡量,其规模都比较小,甚至到公元前3000年,巨大的乌尔‘都市’也不过150英亩(60.7 hm2),居住人口24 000人左右而已。”[11]考古研究则认为古城人口约在34 000人,古城附近还居住着大约20万村民。这些来自考古发掘的分析表明当时乌尔古城的人口达到了相当规模。
自1922年开始,英国考古学家、曾指导过中东地区许多遗址发掘工作的伦纳德·伍雷(Leonard Wooley)来到伊拉克,率领大英博物院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联合考古队,对古城遗址进行了12次考古发掘。发现的城墙遗存属于乌尔第三王朝的乌尔纳姆时代(《苏美尔王表》所示公元前2047年—公元前2030年)。考古报告描述:“整个城墙看起来是一个椭圆形,它大约四分之三英里长,半英里宽。”[12]即南北长约1 207 m,东西宽约804.67 m。四周环绕8 m高城墙,城墙外麦田一望无际,幼发拉底河从乌尔古城流过。在城西、城北的幼发拉底河与运河岸边各设一个港湾。古城不远处分布着乌尔王朝的王室墓葬群(图3)。关于古城最初建造的年代,出土的泥砖和碑板铭文没有记载,只有反复出现的“重建”和“修复”字样。但是从第三王朝古城遗址地层下叠加遗存发掘,发现了约在公元前2800年的乌尔第一王朝古城遗存,还有更早时期的城墙遗存,约在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3000年。乌尔古城郊外的一座神庙里还有一块安尼帕达石碑,记载的乌尔城邦历史最晚可追溯到公元前31世纪[13]。乌尔第一王朝时建筑物平面非常完整。城内有3个主要区域:最东部的角落是一个长20.75 m、宽18.60 m的矩形开阔庭院;西北部是一长排房间;东南部是个独立建筑物。第一王朝的神庙靠着塔庙的东角,平面布局简单,保存完好[14]。

图3 乌尔第三王朝古城平面图
古城整体格局分内城和外城两部分,由厚厚的防御墙分隔。内城中心区是圣城,圣城拔地而起,上面矗立着雄伟的神殿、王宫和高耸巨大的阶梯式塔庙。周围建有实施经济社会管理的税收、法律等官署,还有商业设施、手工作坊和仓库等。外城为一般平民居住和奴隶栖身之地,划分为不同的功能区,其间以道路或者运河分隔开。主路和城墙平行,采用陶片铺就。一些与主路相互连接的街道,有些规整有序,有些崎岖狭窄,延伸进拥挤的商店、旅店、住宅、礼堂、锅炉房、学校、厨房、盥洗室、作坊。住宅区每处房址由12个两层高的房舍组成,平面非常完整,墙体用粗糙的土坯泥砖。房舍建筑有休息室、接待室、厨房、盥洗室。所有房舍围绕一个中心庭院而建,外墙并不开窗,而是借助院内天井自然采光。房址周围环绕木质走廊,留有一些通往二层房间的通道[12]。由于两河流域缺少建筑石料和木材,可供烧砖的燃料也极其匮乏,因此建筑大都采用夯土构筑,或用软泥晒干而成的土坯砖块砌筑墙体,外墙用泥或石灰泥抹面。屋顶大都平缓,用棕榈树枝干作椽,上面覆盖草席和泥层。
在乌尔古城,最具苏美尔城邦时代文明表征的当属圣城18.55 m高的一座4层巨型台阶上的通天塔,传说是《圣经》里挪亚后裔建造的巴别塔的原型。在塔庙建筑神殿内,祭祀着被奉为保护神的月神南纳。伍雷推测这种阶梯式的方正塔庙起源于苏美尔人。原本居住在山区的苏美尔人崇拜山神,来到美索不达米亚冲积平原后,通过建造巍峨的人工塔庙代替他们祭拜神明的圣山,将塔庙视作天堂的象征,因此把塔庙的一切,包括建筑轮廓、建筑颜色等等,都和天堂、天体顺序以及天体性质对应起来[12]。后来塔庙的形制成为两河流域城市形态的普遍特征。到了公元前27世纪的埃及古王国时期,法老左塞尔建造的第一座的金字塔采用了同样一种形制,为埃及金字塔时代的出现开创了先例。通过研究乌尔古城遗址发掘出来的建筑遗存,可以发现苏美尔人建造神庙、大塔、宫室、庭院时,已经开始运用圆柱、拱廊、拱形圆顶等基本建筑艺术形式,建筑风格简洁平直,对墙面和门窗进行艺术加工。这也形成了两河流域传统的建筑特色[15]。虽说至今没有一部著作能够精准地展示出这座古城的完整格局和历史风貌,然而法国建筑师、考古学家、当今古代城市复原图制作领域的巨擘让-克劳德·戈尔万(Jean-Claude Golvin)还是尽其所能绘制复原图,去想象它的风貌(图4)。

图4 乌尔古城复原图
考古与文献相互印证可见,乌尔古城具备了进入文明状态所必需的一切要素,作为远古时代人类的一个伟大创造,催生了地球上的城市文明,从此产生了搏动不息的城市命脉,这无疑是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这座世界上最早诞生的城市真实呈现了奴隶制城邦社会等级制度和社会生活的基本文化特征,仅从王后墓穴出土的一块被伍雷称为“乌尔旗”的通体镶嵌图案的神秘饰板,也能看到乌尔社会运作的模式以及早期经济繁荣和军队作战得胜的场景。不仅如此,乌尔古城还在自然环境资源利用、城市规划理念和总体布局、建筑设计中数学几何把握、文化艺术,以及建筑材料和建筑构造采用、建筑施工技术等方面,开创了人类文明的先河。不无遗憾的是,这座引领人类迈进城市文明门槛的古城连同往昔的辉煌早已化作历史尘埃。因文献资料阙如,人们只有通过发掘古城遗址,进行考证和综合分析研究,把那些片段的和破碎的信息织补起来,才能描绘出其脉络和概貌,解析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和遗产特色。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特征属于城市文明,体现在城邦集群式地出现。其中苏美尔人的乌鲁克城在众多城邦中同样发挥着先驱作用,被誉为“众城之母”,乌鲁克城位于乌尔城东北50 km。关于乌鲁克城的描写主要来自苏美尔人口头流传的《吉尔伽美什史诗》。这部最古老的史诗以楔形文字书写在12块泥板上,广为传播。据此,不少西方考古学家认为乌鲁克是人类最早的城市,认为苏美尔王表中确有吉尔伽美什其人,史诗描述的乌鲁克古城特定空间和形态特征足以令人可感可信。美国著名考古学作家布莱恩·费根(Brian Fagan)在《世界史前史》中记述:“公元前4000年时乌鲁克城面积已达2.5 km2,城内密布着成群的房屋、窄巷和庭院。金字塔建筑群及其卫星神庙成为乌鲁克人全部生活的中心。到公元前3500年,这座城市已发展起一套完善的管理体系”[6]。悉尼大学古典学教授理查德·迈尔斯(Richard Miles)研究了首批城市的出现,说:“在公元前约3000年的巅峰期,乌鲁克曾是4万—5万人的家园。城墙的周长将近11 km,环绕了方圆6 km2的土地。……在那段岁月里,乌鲁克人修建了至少十几座甚至更多的宏大建筑——神庙、宫殿、礼堂,无人能确定是何种建筑,但尽皆形态各异、规格不同。”[16]还有一些学者持同样观点,却又都没有直接考古实证支撑乌鲁克城始建年代的确在乌尔城之前。探秘两河流域文明遗址始于20世纪初德国的考古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取而代之,派伦纳德·伍雷爵士率领大英博物馆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联合考古队,继续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乌尔与欧贝德一带发掘,终于有了惊人的发现,揭开了乌尔古城神秘面纱。接着美国学者克拉默(S.N.Kramer)在1956年出版了《历史从苏美尔开始》,第一次将苏美尔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呈现在世人面前。
苏美尔人创造的城市文明也使楔形文字得到了充分发展,在长达2 000年的漫长岁月里,楔形文字成为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唯一的文字体系。人们将芦苇削成三角形笔尖,在湿泥板上刻画出各种表意的楔形符号,进行商业交流、行政记录、沟通、教学以及文学艺术创作。乌尔的城市文明还在古代城市规划和政治、土地、宗教、祭祀、数学知识上多有建树,尤其创造了杰出的数学运算成就,以致从那时起西方的所有文明都继承了古巴比伦人的“十二进制”的计时方法[10]。直到游牧部族闪米特人侵入,两河流域归于阿摩利人建立的强大的古巴比伦王国,乌尔古城和苏美尔文明随之消亡。
从乌尔城邦诞生时算起,迄今时空跨度5 500多年。在这地老天荒的漫长岁月里,人类建造城市的活动从来也没有停止过。这些大小不一的城市比比皆是,不计其数,散落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此消彼长,竟没有人能够说出确切的数字。消失的城市已然成为历史,而历史城市消失带走了这个世界多种文明太多的记忆,也带给了人类太多不解之谜。因此探索研究历史城市消失的规律,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人类文明,成为时代召唤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