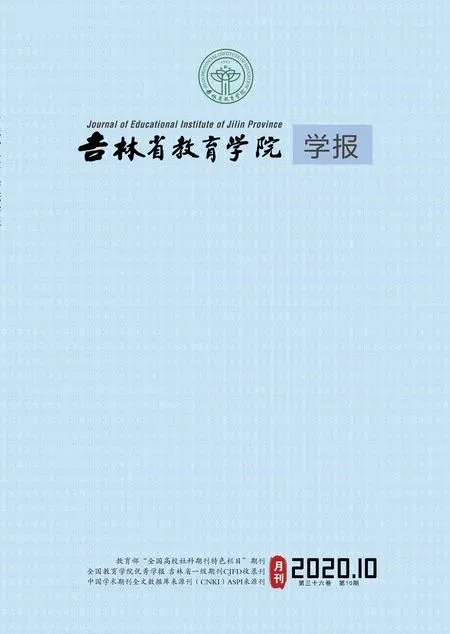用小说建构历史:《神圣的渴望》中的奴隶贸易书写
郭海霞
(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201306)
巴里·昂斯沃斯(Barry Unsworth,1930—2012)是当代英国文坛大师级作家,卓越的英国当代历史小说家,主要作品有《兽皮》《帕斯卡里之岛》《秃鹰之怒》《石女》等17 部小说。《帕斯卡利岛》获1980 年布克奖提名,并被搬上荧幕;《戏中人》获1995 年布克奖提名;《神圣的渴望》(Sacred Hunger,1992)一出版就引起了广泛关注,并与加拿大作家迈克尔·翁达杰的《英国病人》共同获得了1992年的布克奖。《神圣的渴望》以令人振奋的航海大冒险,性格鲜明的人物群像将读者带入18 世纪邪恶贪婪的奴隶贸易历史中。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力图使文学批评具有现实维度的努力受到人们支持和尊重,伊格尔顿、威廉斯、詹姆逊等主张重新开辟文学研究的历史途径。作为这种主张的回应和具体实践,新历史主义认为,文学也可以作为历史文本,帮助读者重回历史现场,体验历史。本文从新历史主义角度入手,揣摩小说奴隶贸易书写时使用的地名、船名和人名,发现小说中的故事、人物与真实历史形成的映射,探索小说的文本历史性和历史文本性以及大写历史的小写等,挖掘小说文本的深层结构和隐喻系统,揭示其隐含的英国与非洲和美洲贸易关系的真相及其幽深的政治和经济目的。同时,本文以奴隶贸易书写为点,以历史发展为线,研究英国小说中奴隶贸易书写与世界历史演进的互动关系,揭示大西洋奴隶贸易书写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
一、奴隶船 “利物浦商人” 号
与传统的历史主义不同,新历史主义解构了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的传统观念,在文学研究中引入对 “文本的历史性” (historicity of texts)和 “历史的文本性” (textuality of history)的双向关注。新历史主义认为,对历史的认识应该从历史的本体和对历史的认识这两个方面进行。本体意义上的历史,即人类所经历和创造的所有事实已经逝去,人们现在所了解的只能是经过语言加工过的历史。因此,历史与文本都是具有想象因素的存在,都是叙事的产物,如海登·怀特所说: “历史的语言虚构形式同文学上的语言虚构有许多相同的地方。”[1]英国当代历史小说家们在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历史与文学的交融关系与新历史主义者的思想不谋而合。[2]在《神圣的渴望》中,小说与历史水乳交融的关系得以充分展现。小说以序言中老奴隶卢瑟为线索引出了小说所叙述的非洲奴隶贸易这段历史: “他总是在述说:讲述一艘利物浦的船,在船上当医生、永远活在他心中的白人父亲” 。[3]大西洋奴隶贸易是最著名的三角贸易,即牵扯到三个区域或港口的贸易。其贸易路线起源于现在的欧洲,欧洲殖民者用船载着兰姆酒、武器和棉布等来到西非(这段航程被称为出程),用这些货物交换大批奴隶,然后将奴隶运往美洲卖掉(这段航程被称为中程),最后购买美洲殖民地的银、砂糖和棉花等带回欧洲(这段航程被称为归程)。大西洋奴隶贸易是造成黑人除了分布在非洲同时也分布在其他大洲的主要原因,给他们带来了奴役和苦难,并导致了非洲的落后与贫穷。正如小说的叙述者告诉读者的那样:奴隶贸易是 “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商业冒险,其规模之大迄今都难以想象” ,它将会 “改变历史,带来死亡、堕落和利润” 。[3]
英国的奴隶贸易与海外扩张紧密相连。英国的海外扩张之路自都铎王朝统治时期就已开启,其后的英国统治者们也都对海洋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他们不仅大力发展海外贸易、抢夺制海权,还以国家的力量支持和鼓励各种殖民扩张和海盗行为,将拓展海外贸易、争夺海上霸权与开发殖民地三者紧密结合,互为作用,铸就了英帝国的繁荣与强大。而这其中的海外贸易就包括了奴隶贸易,即以奴隶作为商品的贸易。英国自1660 年到1821 年先后成立了4 家经营非洲奴隶贸易的特许公司,最初公司对奴隶贸易拥有垄断权,但是到了1698 年,其垄断权被取消,所有商人都可以进行奴隶贸易,但要缴纳货物值10%的税金。1712 年,英国政府废除了收税金的办法,从此,英国所有臣民均可自由参与贩奴,使英国的贩奴活动达到了高潮。商人们纷纷投资,普通老百姓也纷纷集资从事这项冒险而有暴利的贸易。在小说中的第一部分,英国商人肯普信心满满地告诉聚会上的宾客们,非洲贸易有利可图,1752 年可能成为最佳、最兴盛的时期: “既然战争已经结束,既然皇家非洲公司已经丧失特权及其垄断经营权,既然我们可以去非洲从事贸易而无须向伦敦那些该死的无赖支付税金……”[3]肯普的话反映出当时英国商人对于非洲奴隶贸易的热情。这也是肯普愿意花大价钱自己造船来从事奴隶贸易的原因。
由此可见,中世纪末与近代初的英国历史和奴隶贸易密切相联,可以说,奴隶贸易是英国历史的重要部分。对奴隶的捕捉和贩卖似乎成为了人们普遍参与和发财的行动,这一点从英国的经典文学作品就可窥一斑。例如,鲁滨逊早已以原始积累时期资产阶级创业者的真实形象深入人心,而人们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个人物印证了英国积极参与贩奴活动,而贩奴是它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这一事实。在《鲁滨逊漂流记》第一章,想发财的鲁滨逊以60 西班牙银币的价格卖掉了他的黑奴,并与他熟识的商人和种植园主们兴致勃勃地谈论贩卖黑奴的事情,并计划装备一条前往非洲海岸——几内亚的船,因为几内亚海岸可以买到或换到大量黑奴, “在巴西,当时正需要大量的黑奴劳动力。我谈到这些情况时,他们总注意听着,他们尤其注意的,是有关购买黑奴的情况,因为在当时,干黑奴这一行当的人还不多,而且干的人必须得到西班牙、葡萄牙国王的特许状,带有国家垄断的性质,所以被贩卖到巴西来的黑奴数目不大而价格高昂。”[4]在笛福的另外一部作品《辛格顿船长》中,主人公有一次看到一条船在海上漂泊,好像无人驾驶,航行过去登船一查究竟,原来是一船黑奴,因为受不了白人的虐待,全体起义,战胜了白人,但不懂驾驶方法,只能随风漂泊。辛格顿船长取得了这一船黑奴,便航行到南美,卖得个好价钱,发了一大笔横财。
新历史主义将主观和客观、真实和虚构、事实和故事之间一直存在的界限打破了,使前者和后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小说中,肯普造的船被命名为 “利物浦商人” 号,这与当时的历史形成映射,具有深刻的文化历史内涵。历史上,英国有许多港口参与了奴隶贸易,最重要的有3 个,伦敦(1660—1720)、布里斯托(1720—1740)和利物浦(1740—1807)。而且,在1799 年之后只有从这3 个港口出入的船只才能进行奴隶贸易。直到16 世纪中叶,利物浦还只是一个人口只有500 人的小镇,到1650 年英国内战后,利物浦贸易和居民人数才开始缓慢增长。1699 年,利物浦商人的第一艘奴隶船进行非洲航行。1715 年,利物浦建成了英国第一个船坞,而奴隶贸易的利润帮助它迅速繁荣起来。1698 年,英国取消特许状后,从利物浦开出的贩奴船多如牛毛,利物浦港和奴隶商人获得了丰厚的利润。有人形容,利物浦的主要街道是用非洲奴隶的锁链开辟出来的,楼房的墙壁是用非洲奴隶的鲜血粉刷的。到18 世纪末,利物浦控制了欧洲41%、英国80%的奴隶贸易。从1748至1784年,平均每年有60条船从利物浦出发去非洲贩奴。正是由于与奴隶贸易相关的海上贸易的兴旺,18 世纪利物浦的人口增长最为迅速,80%为外来人口的移入,20%为自然增长。1708年,它的居民有7000 人。到了1773 年,它的人口超过 34000 人。到 1801 年,它的人口达到 77000 人。[5]正像小说中所说: “利物浦的未来取决于非洲贸易”[3],如果没有奴隶贸易,利物浦就不会从一个小乡镇变成大城市。
二、作为 “贵重商品” 的奴隶
昂斯沃斯尤其擅长对历史的还原,他以冷静的眼光观察和描述了英国人参与的这段世界历史。《神圣的渴望》体现出他丰富的历史学、人类学和经济学等方面的知识。小说的历史性在于它关注18世纪的奴隶贸易历史,客观真实地展现了这一时期英国及非洲等的社会特征和生活原貌。小说的叙述者告诉读者: “黑人是贵重的商品,”[3]因此,船长瑟索要确保每个买到的奴隶在交货时的身体状况是最佳的。奴隶贸易早在古代奴隶社会中各个奴隶主之间即有发生,然而在现代的奴隶贸易中,为什么非洲人(黑人)成为 “贵重商品” 遭受奴役并被贩运到美洲,而不是其他种族的人?
当美洲的殖民地需要大量劳动力时,欧洲殖民者也曾想过将大量输送白人到美洲做契约工,但是由于诸多原因而未能实现。首先,在黑死病之后,欧洲人口增长缓慢。其次,14、15 世纪,欧洲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资本主义萌芽出现,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多经济机会,因此欧洲人不需要去海外谋生。第三,战争使欧洲的军队需要招募大量人员从军,如欧洲的八十年战争(1568—1648)、三十年战争(1618—1648)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640—1688)等都招募了大量男性平民,而战争的后果是人的死亡。最后,去美洲的路费昂贵,海上航行的安全性也令人担忧,而且白种人到了美洲也很难适应那里炎热的气候。美洲本土的印第安人也曾是欧洲殖民者考虑的劳动力,但是,印第安人对欧洲人带来的传染病几乎没有抵御力,例如对于欧洲传染过来的天花,当地人毫无免疫力,造成人口大量减少,加之他们对故土的依恋使西班牙和葡萄牙人放弃了对他们的奴役。
非洲黑人本身居住在热带地区,因此比较适合美洲的炎热气候,而且亲戚和血缘关系也似乎不那么强烈,还有非洲社会本身的一些因素使欧洲人最终选择大量贩运非洲人到美洲。[6]昂斯沃斯的《神圣的渴望》就如一部详实而形象的历史书,真实地呈现了18世纪奴隶贸易过程中的各种历史元素。小说告诉我们奴隶的来源: “一些是战争的俘虏,其他人是家庭奴隶,现在被他们的主人卖掉来偿还债务或是作为结婚嫁妆的一部分” ,但是 “还有一些是被当地的奴隶商人抓住的” 。[3]非洲当时由很多部落组成,各部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战败的一方有很多俘虏都沦为了战胜方的奴隶。所以欧洲人可以很容易地买到大量奴隶,另外,欧洲人带着自己生产的工业品如武器和棉布等去非洲购买奴隶,而他们带来的经济利益使非洲人之间产生战争,也有的部落为了通过卖出奴隶获利而故意挑起战争,因此,白人对奴隶的需求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战俘的产生,这些战俘作为奴隶被卖掉。然而,当战俘也无法满足对奴隶的需求时,袭击和掠走手无寸铁的农民就成为了一种常规。[6]这也使得非洲大量可耕种的良田成为荒地。
然而,作为 “贵重商品” 的奴隶在贩奴船上并没有得到精心的对待。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从16世纪延续至19世纪,为时约350年。据统计,在16世纪末和17 世纪贩奴船上奴隶的平均死亡率是20%,到了18 世纪末期才降到了10%以下。[6]在奴隶贸易中,英国一直占居着重要的位置,它虽然不是最早贩卖非洲黑奴的国家,但是它后来却成为最主要的奴隶贸易国家。据估计,从1662 年到1807 年,英国商人贩运了大约310 万非洲奴隶到英属殖民地以及北美、南美和加勒比海地区,最终有270 万抵达目的地,也就是说其中有40 万人在贩运过程中就饿死、病死或由于其他原因死亡了。贩奴船只拼命超载,因为装载的奴隶越多,贩运者的利润越大。昂斯沃斯在小说中描述到: “现在奴隶的数量迅猛增加,在甲板下的加固间,他们的居住区域恶臭无比。”[3]贩奴船上的饮水、伙食和卫生条件极差,奴隶们忍饥挨饿,口干舌燥,疾病流行,并遭受船长和船员的虐待,女奴还会遭到船员的强奸。在船上缺的是粮食,多的是疾病,卫生设施形同虚设,洗漱、排泄物容器全挤在居住区:
黑人因食物匮乏身体衰弱了许多,很多人还染上了痢疾,他们所承受的苦难是骇人听闻的。不久,他们的房间就变得闷热难耐。由于缺乏氧气,禁闭的空间令人窒息,再加上这么多人紧密地挤在一块儿,他们不停地呼吸、流汗、排泄,整个房间臭气熏天。他们的住所净高不过两英尺,栖身的木板并未刨平,当他们在闷热窒息的黑暗处无助翻滚时,粗糙的板面从他们的背上或是体侧撕下一层皮。每逢狂风过后,帕里斯都能听到他们的呼救声和发狂的哭喊声,有时还能看见窗栅上冒着热气。
……在帕里斯看来,这个地方就像是地狱般的屠宰场。房间的地板布满了血迹和黏液——这是痢疾造成的——地板打滑,每走一步都充满危险。[3]
贩奴船的确就是 “漂浮的地狱” 。1796 年,一艘利物浦的奴隶船因为风暴而导致航行在海上拖延太久,这个过程中有128 名奴隶饿死,6 个月的航行结束时只有40人存活下来,船主也因此获得了保险赔偿。[7]奴隶在流行病发生时出现一些症状,或是食物或水不够时,往往会被扔进大海以获得保险赔偿金。1781 年,一艘 “桑格” 号(Zong)奴隶船由于航线错误造成缺水,船长和船员将113 名奴隶活着扔入大海。同样的情形下,《神圣的渴望》中的贩奴船船长瑟索也是这么做的,因为他知道 “因所谓自然原因而在船上挣扎的货物一文不值,而因充分良好的理由被抛入大海的货物则属于合法投弃物,可以从保险公司索赔百分之三十的市价” 。[3]
三、 “神圣的” 渴望
《神圣的渴望》中,对于肯普以及像他一样的英国奴隶贸易商人来说, “利润” 是 “神圣的渴望” ( “sacred hunger” ), “它能证明所有一切都是正当的,使所有的目的神圣化” 。[8]在他们看来,丰厚的利润能使所有罪恶的意图合理、合法,正如他们所从事的奴隶贸易。对于读者而言,这也许令人感到迷惑:敬畏和赞美上帝的欧洲人,在从事惨无人道的贩奴活动时竟是如此的平静和从容,并认为他们所做的是 “神圣的” ,这难道不有悖于基督教义吗?当置身于欧洲海外扩张、海外殖民的那个疯狂年代,这种被称之为 “神圣的” 渴望也许更容易理解。正如叙述者在小说中所讲: “这个时代,追求个人财富被认为是天生的美德,因为这会增加整个社会的财富和福利” 。[3]文本和历史的关系向来是历史主义研究的中心问题,以格林布拉特、海登·怀特等为代表人物的新历史主义颠覆了文学只是机械反映历史的观点,强调文本能动地参与历史的重新改写和阐释。 “文学不再被认为是历史知识表达的一个媒介,而是某特定历史时刻具有活力、创造力的一部分。而历史也不再被认为是僵硬的事实,或文学产生的背景。两者作为社会权力结构中的话语,互相交流和对话。”[9]通过小说,昂斯沃斯向读者描述了一种难以为现代人所接受的罪恶渴望。同时,这部小说彰显出作者对于18 世纪英国商人对于金钱的非人性追求的强烈讽刺和批判,以及对于奴隶贸易残酷性的直白揭露和痛斥。
欧洲殖民者在长期贩卖黑人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套一本万利的奴隶贸易制度。据统计,一次三角航程所需的时间平均下来是18个月,奴隶贩子最高可获得80%以上的利润。[10]尽管西方的历史学家们对于贩奴的平均利润率一直争论不休,有的认为是30%~40%,而有的则认为只有7%左右[11],但是获利丰厚是肯定的,否则横跨三大洲的奴隶贸易也不会繁荣一时。英国的奴隶贸易不但供养着西印度群岛的英国奴隶主,还在数个世纪里为英国本土的投资者、制造商、商人和工人带来了可观的收入。玛丽安·格温在其文章中写道: “传统观点认为英国的奴隶贸易促进了商业精英阶层的崛起,但最近的研究更强调指出,奴隶贸易的利润被地主们又投入了实业和庄园的建设,英国各地的平民团体如纺织工、矿工、冶金工人和食品生产者也从中受益。”[12]英国从贩奴贸易中不仅获得了大量利润,积累了资本,扩大了生产,而且非洲奴隶市场对廉价工业品的巨大需求促进了18 世纪后半期工业上的一系列发明,使英国产业革命得以实现。同时,贩奴贸易也促进了英国大城市的兴起,利物浦就是代表之一。确如马克思所说: “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就没有现代工业。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了价值,殖民地造成了世界贸易,而世界贸易则是大机器工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13]
奴隶贸易使欧洲奴隶贩子从中赚了大量钱财,促进了欧洲的繁荣,使美洲获得迅速的发展,然而给非洲带来的灾难则是空前绝后的。奴隶贸易是非洲历史上一段最黑暗的时期。首先是由于奴隶贸易所引起的战乱,加速了非洲文明古国诸如贝宁、刚果等国家的瓦解,阻碍了一些新的民族国家的形成;其次,奴隶贸易决定了非洲经济畸形发展的趋势,因为在大型奴隶买卖转运地区,人们抛弃了传统的手工业与农业,积极投入奴隶贸易,非洲农业、手工业发展受到阻碍;再次,奴隶贸易夺走了无数非洲人的生命,其中包括在奴隶贸易战争、奴隶商队及 “中段航程” 等各时期死亡的人数。人口流失也使非洲大部分地方一片荒凉。
虽然18世纪的笛福还在为贩奴活动呐喊助威,但是19 世纪末的康拉德已开始谴责白人在非洲的掠夺和屠杀,当代作家昂斯沃斯更是勇敢地正视这段历史并大胆地揭露和批判它。笛福一生的活动是多方面的,他的文字工作就包括了政治、经济和文学等方面。然而,他的基本思想和主张却不复杂,那就是 “一切为资本主义发展,为资产阶级利益”[12],因此,他是典型的新型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认为贸易是社会进化、国家富强的根本原因。他的口号是: “贸易就是一切。”[14]1711 年,笛福发表《论南海贸易》(即An Essay on the South-Sea Trade,这里的 “南海” 是指中、南美洲及其周边海域),支持英国在西印度的殖民和贸易扩张,同年英国成立了 “ 南海股份公司” (South Sea Company),开展南美及西印度的特许贸易。 “而最初向英王威廉三世提议成立公司的正是笛福的朋友威廉·佩特森。”[15]笛福的贸易思想和殖民主张充分体现在《鲁滨逊漂流记》和《鲁滨逊漂流续记》等小说中。作为一名商人,在资本主义的拜金浪潮中,笛福 “把商海情结变成虚构文学的灵感源头和基本内容” 。[16]即使是在历经死亡的恐惧之后,主人公鲁滨逊依然保持着对海外贸易的痴迷,并毅然决然地多次登上征途,这正反映了当时整个英国社会对海外殖民扩张的热衷,证实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对海外财富的渴望和对陆上权利的神往。
小说中,当 “利物浦商人” 号进入非洲的时候,读者的视界就与康拉德《黑暗的心》形成了超时空的链接。康拉德的《黑暗之心》描述了英国人在非洲所从事的象牙贸易,伴随这种贸易的仍然是对于非洲人的剥削和奴役。虽然这个时期奴隶贸易已被废除,但是非洲黑人仍然像奴隶般和动物般地被对待: “六个黑人排成一排,吃力地沿着那条小道往上爬去。他们都直着身子慢慢走着,头上顶着装满泥土的小筐。……每个人的脖子上都套着个脖圈,把他们全拴在一起的铁链在他面前之间晃动着,有节奏地发出哐啷声” 。[17]这些人正在修建铁路, “所有那些人干瘪的胸脯一起随着气息起伏,使劲张开的鼻孔翕动着,无神的眼睛全都望着山上。”[17]他们不是罪犯,而是 “让人完全合法地从海岸深处各个角落里弄出来” ,若生病了,失去工作能力, “才能获得允许” ,爬到树荫下慢慢死去。[17]康拉德在小说里呈现的似乎是地狱里的场景,给人一种他本人也深深体会的 “强烈的‘噩梦般的感觉’” 。[17]而英国殖民者前往非洲,所做的这一切包括对于黑人的奴役都源于一个目的: “为了赚钱” 。[17]这种强烈欲望,即所谓 “神圣的” 渴望,使他们变成暴力及贪婪的魔鬼。在他们的掠夺奴役下,非洲丛林里村舍凋蔽,饿殍遍野,一片阴森恐怖。
《神圣的渴望》中奴隶们在被送上船只运走之前会被关在贸易站的地牢里。送上船后,他们被戴上镣铐,关在甲板下的底舱。小说中对 “利物浦商人” 号在装满奴隶后起航时的描写令人难忘:
当船接触到深海区滚滚海浪时,船移动的节奏发生了变化,在散发恶臭的黑暗狭窄的底舱,奴隶们知道他们失去了回家的全部希望,因而忧伤绝望地大声呼喊。呼喊声经由水传到停泊区的其他船只,那些船上被关在底舱的奴隶听到了呼喊声,便用狂野的呼喊和尖叫回应。所以,对于沿岸村庄里醒着躺在床上的人们和孤独的渔夫来说,黎明前有一段时间,黑夜里回荡着恸哭声。[3]
很多黑奴上船后尽管挨鞭打也拒绝进食,希望饿死,因为 “他们认为死后就可以回到自己的国家” 。[3]生病和饿死的黑人被扔出船外,抛入大海。从《神圣的渴望》中读者明白了英国贩奴商人所享受的锦衣玉食的生活是如何用悲惨而痛苦的奴隶的生命换来的,正如小说主人公帕里斯绞尽脑汁地思考着 “俘获奴隶和他表弟伊拉斯谟·肯普购买一条新领带或者他姨夫举办晚宴之间复杂的交易链条” 。[3]另外,对于这位表弟来说, “美德仅仅意味着裁剪精致的服饰、令人骄傲的仪表,以及银行里的金钱” 。[8]通过昂斯沃斯的小说,读者深深地了解到贩卖奴隶的英国商船上充满了黑奴的血泪,而奴隶贩子所谓 “神圣的” 渴望,事实上是邪恶而无耻的,因为它是以非洲黑人的奴役和苦难为代价的。
四、结语
文学与历史、现实与虚构、事实与故事是交织杂糅在一起的。小说和历史一样, “都是一种叙事,都具有文本性和人为建构性” ,两者的区别在于,小说的叙述 “更注重个人主体对历史的理解和重新阐释”[2]。昂斯沃斯对《神圣的渴望》的创作可谓别出心裁,他自由地穿梭在小说与历史之间,以所处时代的眼光完成了对文本再现历史的想象、反讽与批判,以虚构文本丰富了新历史主义的探索形式,从个人故事和小写历史入手,拓展了历史反思的维度,因此,文学与历史的深刻关联充分体现在这部小说中。本文提醒读者要充分注意英国的海外贸易,特别是奴隶贸易的开展伴随着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是建立在掠夺基础上的。通过对《神圣的渴望》中奴隶贸易书写以及文本历史性和历史文本性的研究,本文希望有助于唤醒人们的历史意识,实现文学与历史的互动,启发人们从政治和经济视域阅读文学作品、观察历史和现实,并培育大众对不合理的体制和思想的批判精神和变革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