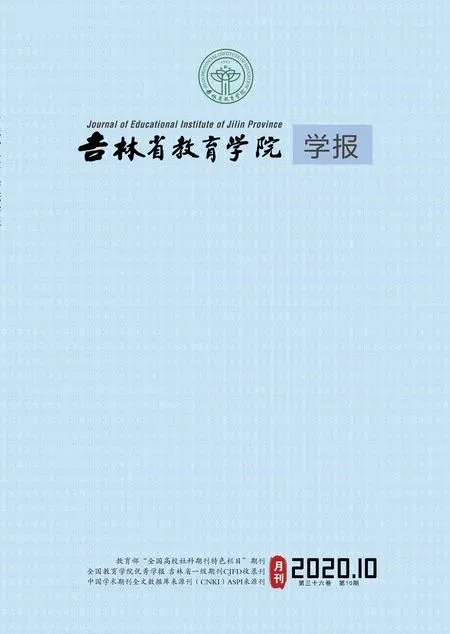论鲁迅对国民奴性心理的批判
陆妙琴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基础部,陕西咸阳712000)
“国民性” 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众多的现代文学作家在其作品中反复书写这一主题,如鲁迅、老舍、沈从文、林语堂、茅盾等,而鲁迅的文学书写在国人心中产生的影响尤为广泛而深远。纵观鲁迅一生的创作,对国民劣根性的深入挖掘和猛烈抨击贯穿了他几乎全部的作品。而鲁迅最为痛心疾首、深恶痛绝的莫过于存在于国人灵魂深处的奴性。鲁迅在他的作品中不仅无情剖析了国人的奴性,而且冷峻地挖出了国人奴性心理形成的历史文化根源。疗救国人的灵魂,使其成为 “真的人” ,是鲁迅创作的终极目标和毕生的追求。
一、鲁迅对国民奴性心理的批判
鲁迅认为 “尊个性而张精神” ,也即人的个体生命的精神自由是 “人” 之成为 “人” 的本质,是衡量人是否具有 “‘人’的价格” 的唯一绝对标准。只要人的个体生命尚处于物质的,特别是精神处于被压抑的状态,没有获得个体的精神自由,人就根本没有走出 “奴隶” 的状态。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鲁迅痛感个人在我国文化传统中被压抑、扭曲、虐杀的境遇,他振聋发聩地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观点,中国百姓向来就没有争到过 “人” 的资格,至多不过是奴隶,两千年的封建史,就是一个老百姓永久做奴隶的时代—— “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1]鲁迅指出, “中国的百姓常把做奴隶当作一种奢望,甚至是一种享受,一旦有哪一位统治者满足了这一令人感到悲哀的要求,他们自然就万分喜欢了。”[2]鲁迅在其作品中,力透纸背地揭示了国人奴性心理的种种表现。
逆来顺受,苟安于命运和现状, “甘心做奴隶” ,不思反抗是国民奴性心理中最鲜明的特征。长期积淀的奴性心理使得中国百姓对于统治者俯首帖耳,唯命是从,唯唯诺诺,不敢逆天反上,无论遇上什么不公、打击都能忍受,听天由命,安分守己,对一切事情无不驯良。
在《灯下漫笔》的开头,鲁迅回忆民国初年国家银行发行钞票,因其携带便利,摆脱了白银黄金的沉重累赘,信用日见其好。当时人们都喜欢用钞票而渐渐少用银元。但袁世凯复辟期间,钞票不断贬值,商民不要钞票,百姓购买东西多给商民钞票心有不甘,用钞票换铜元换不来,到亲戚朋友处借现钱借不来,用本国钞票换外国银行的钞票也换不来,最后只能钞票折价换现银,先是六折,最后七折,人们包括作者却千方百计地将钞票换成银元,没有丝毫不满,反倒 “非常高兴” 。鲁迅由此引出了对 “人” 的价格贬值的思考, “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欢喜”[1]。百姓明明吃了大亏,却显示出满足。国民隐藏在灵魂深处的一种普遍的奴性心态——苟安现状、不思反抗、自我满足、自我陶醉由此可见一斑。
《明天》里的单四嫂子 “是一个粗笨的女人” ,她勤劳、朴实,温柔善良,丈夫早逝后,对社会没有任何怨言,也没有任何非分之想,始终遵循着封建礼教 “从一而终” 的观念,不敢改嫁,独立乐观顽强地生活,只想靠自己的一双手养活自己和儿子。她深更半夜就开始张罗第二天的生活,常常纺棉纱到深夜。失去丈夫后,因为有儿子在身边,她觉得纺出的棉纱 “寸寸有意思,寸寸都活着” 。她把所有的寄托、全部的希望都押在了儿子宝儿身上。然而厄运却一再向她袭来,她唯一的儿子宝儿生病了,求签、许愿、吃单方,可宝儿的病丝毫不见好转,最后她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庸医何小仙身上,但宝儿最终还是不幸夭折,单四嫂子最后一点儿希望也随之破灭了。单四嫂子就是这样一个命运极度悲苦的人。但当一连串的不幸和打击向她袭来时,她没有任何的不满和反抗,而是一味遵从封建道德教条,安分拘谨地守节,甘心情愿地任人摆布自己的命运,逆来顺受,对命运顺从、屈服、幻想,以此来减少自己的痛苦,通过所寄托的梦幻般的 “明天” 去实现那永远无法兑现的梦。
习惯于被统治、被压迫,驯良、顺从的奴性心理同样存在于《故乡》中的闰土、《药》中的华大妈、《阿Q正传》中的阿Q身上,他们都安于命运,安于现状,过着得过且过的日子,兹不赘述。
国民奴性的第二个特点是卑怯懦弱,屈从于强权与暴力。旧时代的中国百姓精神沦丧,生命力委顿,胆小、懦弱,不敢冒犯欺凌他们的权贵,对暴力和强权无条件地服从,不怨、不怒、不争,消极避世,甘心为奴。对此鲁迅做了入木三分的揭示: “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1]“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屡见不鲜的。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哪一面,但又属于无论哪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1]可见,在暴力和强权下,百姓即使是当奴隶也是乐意的,甚至还害怕当不上奴隶,对暴力和强权有的只是屈服和盲从,根本无意、无力反抗。
国民奴性的第三个特点是怕强欺弱,狡诈无赖的主奴意识与两面人格。鲁迅在《忽然想到·七》中对此有精辟的概括: “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3]鲁迅说: “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3]鲁迅还透辟地分析了国人主子和奴才的两面人格: “一方面逆来顺受,自甘卑贱屈辱贫寒而不自知;另一方面,一朝得势,便以贵凌贱,以富凌贫,加倍压迫自己的同胞。中国只有两种人:主子和奴才。以奴性自处的人,得志时是主子,骄横跋扈,表现出兽性的残忍;失意时是奴才,摇尾乞怜,惟主子之命是从,分取吃人的余羹,现出奴的卑微和无耻。”[4]他在《论照相之类》中说: “凡是人主,也容易变成奴隶,因为他一面既承认可做主人,一面就当然承认可做奴隶,所以威力一坠,就死心塌地,俯首帖耳于新主人之前了。”[1]他在《谚语》中进一步指出: “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动摇的。”[5]
欺软怕硬、狡诈无赖的主奴心理和两面人格在阿Q 身上有着突出的表现。阿Q 在狼面前就变成了羊,在羊面前就又变成了狼。他在赵太爷、假洋鬼子面前显现出空前的软弱,真可以说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他被赵太爷打嘴巴后,不敢争辩,只用手摸着左颊。假洋鬼子扬起哭丧棒要打,他不但不反抗,反而在 “等候” ,主动接受惩罚。鲁迅在《阿Q 正传》中是这样描写的: “不料这秃儿却拿着一支黄漆的棍子——就是阿Q 所谓哭丧棒——大蹋步走了过来。阿Q 在这刹那,便知道大约要打了,赶紧抽紧筋骨,耸了肩膀等候着,果然,啪的一声,似乎确凿打在自己头上了。”[1]这里充分显现出阿Q 的奴隶性。但在比他更弱的人面前,阿Q 会寻找并抓住一切机会施暴凌辱,又表现得十分霸道—— “他打不过王胡,惧怕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却去欺负小尼姑,以求得心理的平衡;赵太爷害他丢了生计,他却去小D身上发泄不满;当革命到来,他不准小D 革命。狡诈无赖、怕强欺弱的两面人格是如此矛盾而又统一地体现在阿Q身上。”[6]
人主失势成为奴才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鲁迅在《南腔北调集·谚语》中提到的孙皓和宋徽宗了。孙皓在位时极其残暴,随心所欲地杀戮臣下和宫人,降晋后对晋武帝俯首称臣,摇尾乞怜,令人不齿。宋徽宗也是中国历史上凶残暴戾的 “人主” ,靖康二年被金兵俘虏后,备受侮辱,可他毫无气节,不知廉耻,甘心为奴。主奴性又是如此矛盾地统一在孙皓和宋徽宗的身上。
国民奴性的第四个特点是愚昧、麻木、迷信、不觉醒。鲁迅在其诸多作品中塑造了这类人物形象。鲁迅对这类人物是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对他们的精神状态感到深深的焦虑和悲哀。《祝福》中的祥林嫂就是一个愚昧麻木、自我意识迷失的典型形象。她深受奴性自尊的戕害,最后连做一个奴隶的资格都失去了。她受封建礼教思想和迷信思想的毒害很深,面对悲苦的人生命运,看似有过不平和反抗,但她的反抗也正是她的可悲之处。她的一切反抗都是在维系封建礼教,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获得封建秩序的认可,从而使自己做稳奴隶。她的反抗其实是对封建礼教的顶礼膜拜,因此,她越是在维系封建礼教的轨道上前行,则越是对自我价值的背叛。这就决定了她反抗的结果只能是成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而对这一点,她是不自知的。她以死抗争婆婆的逼嫁,为的是维系 “好女不嫁二夫” 的封建礼教信条。世人认为她再嫁是罪恶,她自己也始终以再嫁为耻,精神恍惚萎靡,心怀恐惧。为了摆脱再嫁的罪恶感,她乞求于迷信,幻想通过捐门槛摆脱罪孽。虽然对于鬼神之说她有所怀疑,但这并不能表明她已觉醒,而是她欲生不能,欲死不敢心理状态的反映。祥林嫂把封建礼教思想和迷信思想当作救命的稻草,反而使自己陷入恐怖的深渊。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也是杀害自己的凶手之一。
愚昧、麻木、不觉醒,自我意识泯灭的奴性意识不仅仅体现在祥林嫂身上,《明天》里的单四嫂子也是一个无知、迷信、严格遵从封建礼教信条的典型,失去丈夫后,儿子成为她的精神支柱和全部希望,但当儿子生病时,她不去找医生诊治,却求神拜佛,相信妖术,在虚幻的梦中追寻所有的期冀,贻误了时机,她的封建迷信思想不仅害了儿子,也断送了自己的希望。还有《故乡》中的闰土,呆滞、麻木、不觉醒,默默承受剥削和压迫,屈服于等级制度,将生活的全部希望完全寄托于神佛、迷信。
二、鲁迅对国民奴性心理产生根源的思考
鲁迅不遗余力、全方位地批判了国民的奴性心理,但他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穿越历史的重重迷障,把解剖刀深入到国民奴性心理产生的根源上,并且得出了令人折服的结论。
在鲁迅看来绵延至今的封建等级制度是培植奴性的历史土壤。鲁迅在《灯下漫笔》中引用了《左传》昭公七年的一段话: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1]君臣父子,尊卑有序,这种森严的等级制度,是旧中国处理人与人关系的最高原则和行为规范。鲁迅慨叹道: “我们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1]国民的奴性就是在封建等级制度的沃土中发芽培植起来的。封建等级制度腐蚀了整个民族的精神,使人们陷入奴隶的深渊而不能自拔。
鲁迅认为封建专制主义的暴力对人的精神奴役是国民奴性产生的又一个根源。正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暴力对人的精神奴役,造成了国民的愚昧、苟且。长期处在封建暴力统治和精神奴役下的中国百姓,饱受重压和杀戮,从来没有享受到做人的尊严和权力,统治阶级 “将人不当人” ,对人的权利进行肆意践踏和剥夺,统治者把人治成了死心塌地的奴才,希望老百姓是羊,虽死也应该是羊,使天下太平,彼此省力。
鲁迅认为封建主义文化思想、历代统治者的愚民政策,对国民奴性心理的形成也有着巨大影响。中国封建社会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文化形态。儒家文化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当它形成君臣父子、长尊幼卑的道德谱系,与道教、佛教文化合流,并蜕变为历代统治者奴役民众精神的工具时,就逐渐丧失了积极的价值,日益成为阻滞社会进步的消极因素。鲁迅指出,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 “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1]鲁迅看穿了正是这些古旧的 “文明” 造成了国民的不觉悟。鲁迅在《老调子已经唱完》中说: “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7]这种违悖人性的 “主子” 文化,只会扼杀人的自由意志和创造精神,断然培育不出健康向上、高尚圆满的现代人格。鲁迅还说: “愚民的发生,是愚民政策的结果”[8],历代统治者的愚民政策将民众麻痹为不死不活的状态,令他们甘心永远做奴隶。历代统治者以儒释道三教兼济,互相补充、融汇,在这种 “硬要民众当奴才” 的主子文化的欺骗和压制下,民众 “失了力量,哑了声音” “就只好永远箝口结舌,相率被杀,被奴” 。[8]
三、鲁迅批判国民奴性心理的终极目的
鲁迅深入批判国民的奴性心理,揭出其产生的病根,终极目的在于根除奴性和根治奴性,使国民人格得以健康、健全发展,先 “立人” 后立国。
“立人” 是鲁迅毕生的追求,无论是1907年前后其立国必先立人思想的确立,还是 “五四” 时期重新确立启蒙思想,再到1930 年接受阶级论思想,都是其立人思想的不断修正、完善与实践。鲁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鲁迅希望国人都具有人格,而不是 “奴格” 。
鲁迅认为,要 “立国” ,必先 “立人” ,唯有 “立人” ,才可 “立国” ;不 “立人” ,不 “尊个性” ,不根除奴性,就无以立国。他在1908 年写的《文化偏至论》一文中指出: “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鲁迅认为欧美之强,根本在人,中国之衰,根柢也在人。国家要想繁荣富强必须先立人。 “立人” 和启蒙是救国的根本和关键。鲁迅的 “立人” 思想从一开始就与民族、国家、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鲁迅看来,要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人的解放,个性的解放是前提、基础。中国人只有摆脱了封建专制压迫,从愚昧落后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从精神的禁锢和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得 “人各有己” 的现代独立人格,才能实现 “中国亦以立” 的民族复兴理想。反之,如果国人的奴性未得到根除,精神依然处在被奴役、被压迫、不自由的状态,那么,不但个人的发展无从谈起,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发展也无从谈起。
“立” 和 “破” 是鲁迅立人思想的两个维度,不破不立。 “破” 就是对国人奴性心理、国民精神缺失的批判,就是打破封建社会制度对人的束缚,健全人性,寻回人性的尊严; “立” 就是国民精神的重新建构。方法就是 “尊个性而张精神”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 “立人” 与 “立国” 的统一。
鲁迅深感中国数千年的封建专制文化是国民奴性不断滋生的土壤,封建专制主义的暴力,封建主义思想、历代统治者的愚民政策,严重地束缚、压抑了人的精神个性,泯灭了国民的个人意识,造成了国民的愚昧、不觉醒,形成了国民根深蒂固的奴性心理,使国民失去了作为真正的人所应有的健全人格和精神自由,但清除国人思想和精神上的渣滓,根除奴性,实现人的精神的解放,完成 “人” 的革新,国人人格的重塑,只是 “立人” 的手段, “立国” 才是 “立人” 的最终目的。鲁迅希望通过 “立人” 使人实现全面、彻底的解放,使人成为理性的、独立的、自由的、真正的个体。只有使国民走向人的全面发展,使人的精神获得真正的独立、自由与解放,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充分享受做人的资格,获得人的尊严,享有民主、平等与自由,成为具有现代文化意义上的人,才能够使国民真正走向觉醒,改变国民的精神状态、培养国民的健康人格和良好的文化心态,诞生民族的精神支柱,使整个民族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最终通过立人达到立国的目标。[9]
总之,鲁迅是一切奴隶道德和奴隶文化最坚决、最勇敢、最彻底的叛逆者,他毕生的创作都在批判国民的劣根性,尤其是奴性心理,并思考其形成的历史文化根源。他毕生都在为国民性改造而努力,他终生都在探索国家和人民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