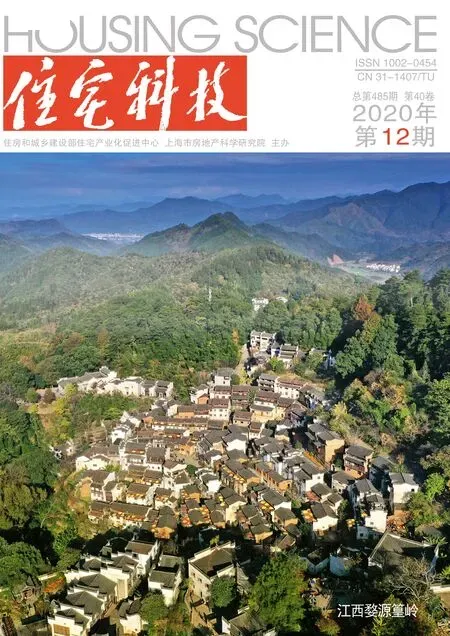上海中心城区老旧住区可持续更新策略研究
SHI Wenbin SUN Tongyu LI Yong
1 研究背景
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城市建设由增量扩张转为存量更新的背景下,中心城区老旧住区的改造更新成为迫切需求,探索老旧住区的可持续发展策略对优化城市环境、提升住区品质、改善居民生活、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逐渐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重要议题。
上海中心城区存在着大量的老旧住区,分布面广且数量较大,这些既有住宅建筑及环境日益老旧,与上海国际化大都市城市风貌形成较大反差。为了改善居民生活,提升公共空间品质和城市风貌,上海市于2016年发布了《上海市15 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导则》,标志着上海城市更新的工作重点开始转向社区综合品质的提升;老旧住区更新也从单体建筑的修缮改造逐渐转向整体片区的宜居性改造更新,从“涂脂抹粉”的外立面美化工程逐渐转变为增强社区功能的系统性更新。老旧住区改造更新的目标是:通过空间的集约化、高效化的改造更新,带动社区产业、社区文化、社区服务等多个层面的全面提升,使其拥有多样化的舒适住宅、更多的就近就业空间、低碳安全的出行、类型丰富且便捷可达的社区服务,以及绿色开放、活力宜人的公共空间[1]。
老旧住区的改造与市民生活的基本需求息息相关,上海市政府十分重视老旧住区的更新问题。早在1999年,上海市就全面开展了既有住宅“平改坡”工程。为了兼顾城市风貌和市民生活需求,上海颁布了《上海市旧住房综合改造管理暂行办法》(沪府发〔2005〕37 号)、《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1 版)、《上海市建筑面积计算规划管理暂行规定》(沪规土资法〔2011〕678 号)、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住宅设计标准》(DGJ 08—20—2013)等相关政策法规,在规划管理层面对老旧住区的改造更新做了相关的规定和要求。同时,上海市也在2013 年颁布了《本市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工作规划管理意见(试行)》,对既有住宅进行适老化改造。2020 年7 月20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对老旧住区更新数量、制度和时间节点的要求,强调发展制度框架、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的重要性[2]。虽然各级政府都对老旧住区的更新问题十分重视,也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配套政策,但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不少矛盾与瓶颈。大量自发改造的需求与目前条块化的规划管理模式,是老旧住区改造更新过程中的基本矛盾,也是难点所在。老旧住区改造更新是城市建设存量更新的主要载体,也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涵。本研究将针对上海中心城区老旧住区进行实地调研和访谈,挖掘出老旧住区更新中存在的基本问题和矛盾,并结合国内外相关的理论与实践,提出老旧住区的可持续更新策略。
2 上海中心城区老旧住区更新的现状及问题
上海中心城区老旧住区存量较大,其中新式里弄230 万m2、旧式里弄513 万m2、简屋6 万m2、一类职工住宅7 664.65 万m2和二类职工住宅7 750.56 万m2[3],构成了中心城区住区的主要城市空间肌理。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地价高涨,加上缺乏正规的管理流程,老旧住宅的加建和改建现象尤为突出,也往往伴随着公共空间环境混乱,并引发交通、消防、治安、卫生等一系列问题,亟待合理引导和控制。总的来说,上海老旧住宅的改造更新由于其独特的历史原因,呈现面广量大、成因复杂、矛盾多样、管控难度大的特征。
2.1 老旧住区的基本类型
根据上海城市发展独特的历史阶段与特点,住宅的类型主要可分为3种:第一个类型是19 世纪60 年代—20 世纪50 年代上海开埠后形成的里弄住宅,是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的具有上海特色的住区形式,具有较强的保护价值;第二个类型是20 世纪50—90 年代大量建设的工人新村,由政府主导建设,形成了上海中心城区基本的住区肌理,是上海半个世纪以来的城市空间记忆;第三个类型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住宅建设市场化后,建设的商品房住宅[4](图1)。
上海里弄住宅由于其独特的风貌与历史价值,多为历史建筑保护的范畴,因此,在更新改造过程中所面临的产权问题更为复杂,在更新审批的流程上也与其他旧住宅有所不同。20世纪90 年代以后建设的商品房住宅居住品质尚可,居民改造更新的需求和意愿尚不急迫;而工人新村住宅作为上海中心城区住区肌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大部分住宅建筑都接近50年的建筑结构设计使用年限,居民改造更新的需求和意愿较为迫切。本研究主要关注这类20 世纪50—90 年代建造的具有一定典型性的老旧住区。
2.2 老旧住区更新的现状
本研究对虹口区的曲阳社区、杨浦区的鞍山社区、普陀区的曹杨社区、徐汇区的田林社区进行了集中调查研究。这4 个社区以工人新村住区为主,居民的改造更新意愿强烈。通过现场调查与居民访谈,目前,上海中心城区老旧住区的基本现状表现为:①住宅建筑破旧,楼栋设施老化;②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不全,缺乏休闲健身设施和适老化设施;③消防通道不规范,消防设施及水、电、路灯、座椅等市政设施破旧;④公共活动空间不足,社区绿地利用率低;⑤ 停车位紧张,多占用人行道路停车;⑥自发改造现象普遍,其中,底层院子加建、屋顶加建和外扩阳台现象较多(图2)。

图1 上海中心城区(内环以内)旧住区分布情况
老旧住区一般为多层建筑,建筑密度大、间距小,且成片布局,公共空间局促;社区公共空间以线性的街道空间为主,缺乏城市空间节点;社区配套服务以商业零售为主,缺乏文体设施。由此可见,老旧住区更新的现状不仅难以满足居民生活品质提升的需求,也影响了中心城区城市风貌的进一步提升。
2.3 老旧住区更新的难点
老旧住宅的自发改造现象较为普遍,其目的多为增加私有居住面积,导致对住区公共区域的侵占。由于居民私自改扩建,对结构问题不够重视,部分加建阻挡了消防通道,造成安全隐患。老旧住区大量的自发改造现象是历来规划管理工作的难点,也是其更新过程中的瓶颈所在,这主要是由于更新机制和流程尚不完善。
(1)目前,城市规划管理缺乏对“存量更新”部分的管控机制和流程。在老旧住区更新项目中,开发和申报主体以政府和地产开发企业为主,缺乏针对小规模企业和个人的改造机制和申报流程,老旧住区的更新难以调动更广泛的社会资源和资本。
(2)在具体的改造更新项目中,用地性质变更困难,缺乏变更机制和流程;同时,中心城区土地开发强度管控严格,住区容积率难以提升,从而产生土地溢价。
(3)对开发强度和土地性质的管控缺乏弹性机制和协商平台,也是大部分老旧住区更新项目难以推进的主要原因。
3 老旧住区更新的理论及实践
老旧住区更新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其作为城市更新重要的组成部分,一直备受学术界关注。自20 世纪60 年代以来,伴随着对现代主义的反思与批判,一大批学者和从业者开始思考城市更新问题,产生了各具代表性的更新理论,同时,也在世界各地进行了大量实践。
3.1 老旧住区更新的理论借鉴
现代主义城市功能分区的空间模式饱受批判,而小尺度多样性且功能混合的空间模式则越来越受到推崇。简·雅各布斯提出城市更新应考虑多样化的社区模式,采用小规模渐进式的更新方式,形成功能混合的社区,以促进城市的活力[5]。柯林·罗提出城市更新应尊重城市历史空间肌理,进行“有机拼贴”式的微更新而非大拆大建,应保留城市的历史记忆[6]。Davidoff 提出了“倡导性更新”理论,指出城市更新需要广泛的公众参与[7]。吴良镛先生在对中外城市发展历史和规划管理制度充分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有机更新”的理论,强调城市更新应符合自然生长规律和有机更替原则,顺应城市内在的秩序和规律而进行发展[8]。
近年来,学者们在住区空间改造和更新机制两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1)老旧住区更新应尊重城市历史肌理,主张采用适当的规模及合适的尺度对城市进行渐进式更新;并着力打造公共空间,激发社区活力。老旧住区公共空间改造涉及的物质环境要素框架包括活力与多样性、绿化、交通、新老建筑融合、旧建筑物质现状、新形式的塑造、利用与再利用潜力等方面的内容[9];社区绿色基础设施的更新产生风量和温度变化,从而改善社区公共空间微气候,改善城市地面环境并减弱城市热岛效应,降低城市能源消耗[10]。
(2)城市的规划管理应具有弹性,以满足城市空间自组织发展的要求,有效引导居民对旧住宅的自发改造行为。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地方自主性更新的出现及演变,对地方利益相关者具有重大意义,使其与当地文化产生连接,为社区更新创造价值;同时,也使居民对当地社区整体空间的发展更为关注[11]。
综上,老旧住区更新应符合有机更新原则,在尊重城市记忆和住区肌理的前提下,有效引导住区空间的自组织发展,重塑社区公共空间,完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激发社区活力,实现老旧住区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3.2 老旧住区更新的实践经验
早在20 世纪60 年代,在小尺度多样性、小规模渐进式等理论共识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就开启了大规模的城市更新进程,也积累了许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实践经验。
3.2.1 城市历史风貌与居住需求扩容之间的矛盾
经历了历史发展的城市中心区往往留存着大量的历史建筑,对这些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老旧住区进行更新,尤其需要采取审慎的态度。中心城区也存在着大量的居住需求,如何解决城市历史风貌与居住需求扩容之间的矛盾,是大部分老旧住区更新中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
例如,维也纳的屋顶改造策略便提供了有益的尝试和借鉴。为了解决维也纳中心城区居住面积短缺的问题,维也纳市政府鼓励并引导屋顶加建改造,并制定相关的建筑规范和规划审批流程。规范要求:屋顶加建部分具有适当的体量;要严格遵守建筑退界要求,不遮挡原有光照,并与周边建筑相协调(图3、4)。在这一政策的鼓励和引导下,维也纳通过屋顶加建,在保证城市历史风貌延续的前提下,每年可增加25 000 个屋顶住宅单元,大大缓解了住房紧缺的压力[12]。可见,积极的引导可以有效杜绝老旧住区中违章搭建等自发改造现象;通过统一的规划管理,使自发改造有序进行,并与城市风貌相协调。
3.2.2 公共空间品质的提升
老旧住区的公共空间品质提升也是其更新中的重要议题。比利时根特市于2012 年启动了“生活街道”项目,以解决机动车占据步行街道、社区公共空间品质欠佳等问题。生活街道项目的开展由居民主导,在政府部门的监督下进行审核。居民在共同设计和改造社区的过程中,形成了更为紧密的社群关系,同时,也鼓励设计师创造性的发挥设计思想,打造高品质的社区公共空间(图5、6)。可见,居民作为社区生活的主体,是社区公共空间改造的主要动力来源。这些自发改造的需求在相应的政策和机制保障下,可以形成一个共建共享的社区更新格局。

图3 维也纳城市更新中的屋顶加建

图4 维也纳屋顶加建剖面示意图
3.2.3 配套设施问题的解决
中心城区老旧住区的集中化、功能单一化、配套服务设施不足等问题,是其更新中亟待解决的问题。20 世纪80 年代起,柏林国际建筑展(IBA,1984—1987)提出“在内城中居住”的口号,海默尔(H·W·Haemer)认为对柏林中心城区的老旧住区改造应遵循“谨慎的城市更新”原则,提出必须从当地居民利益出发,尽可能达成设计师、居民和开发商之间的统一意见,研究居住单元平面,开发新的居住模式,尽量增加广场、绿地公共空间等具体的空间改造建议,对柏林内城进行全面复兴;同时,也制定了公众参与的住区改造决策模式,设立了专门的服务机构来统筹和实施住区改造的具体工作[13]。柏林的内城复兴计划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柏林中心城区的历史建筑,提供了大量的住宅,缓解了住房供应的紧张。HackescherMarkt 改造项目是其中的成功案例,其前身是20 世纪早期的大型四合院住宅建筑,更新后形成了8 个公共空间,其中,咖啡馆、电影院、艺术画廊、餐馆和品牌商业的入驻让它成为了一个高人气的目的地[14](图7~9)。

图5 “生活街道”街景

图6 “生活街道”街景
3.2.4 自下而上的改造动力和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导
城市中心区老旧住区的更新需要自下而上的改造动力和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导共同推动和实施。例如,20世纪80 年代,美国纽约在《纽约市区划决议》(New York City Zoning Resolution)制定了统一的土地使用审查程序,形成了公众参与的土地开发审查流程,为纽约的旧城更新提供了开放的、弹性的政策保障机制;同一时期,日本倡导的“新公共”政策,在政府的推动下,为公众提供了更多参与社区营造的机会和途径,社区居民、政府、社团及非盈利组织之间形成了一种开放的合作关系,共同促进老旧住区的更新。这些实践经验对上海中心城区老旧住区的更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图7 1996 年改造前的Hackecher Markt

图8 改造后的Hackecher Markt

图9 Hackecher Hofe 项目改造平面图
4 老旧住区可持续更新策略
在老旧住区的更新中,应综合评估当地居民的基本需求,保护城市记忆与空间肌理,激发城市活力,优化老旧住区更新审批流程和实施机制,实现精细化的可持续住区更新目标。针对上海中心城区老旧住区更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难点,结合国内外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本文提出以下4 个老旧住区可持续更新策略。
4.1 规范化的空间改造
老旧住区的更新应规范引导居民自发的改造行为,关注公共利益平衡问题。上海中心城区老旧住区的自发改扩建现象,其基本动因是增加居民居住面积。从实地调研的情况来看,可以显著增加居住面积的手段有:底层院子封顶加建、顶层屋顶加建及外扩阳台等。目前,这些居民自发的改扩建,缺少相应的规范化管理,导致城市风貌的不协调。针对这些改扩建现象,在满足建筑技术规范(尤其是结构和防火规范)的前提下,相关政策可以对其放宽要求,进行规范化的管理和引导。例如:①在经过结构评估及不影响原有日照指标的前提下,可以进行屋顶加建,扩展居住空间;②在不侵占消防疏散通道的前提下,进行底层院子的封顶扩建;③在统一协调居民意愿后,可以进行加装电梯等适老化设施改造(图10)。
4.2 公众参与的公共设施提质
针对上海中心城区老旧住区建筑物老旧、基础设施破旧、公共空间不足、公共服务配套设施缺乏等问题,更新时应对其周边城市区域的空间资源进行统筹安排,打造功能混合社区,提升社区公共空间品质。具体的实施策略可以分为以下3 个方面。
(1)市政基础设施的改善和提升,如改造水电管线,开辟公共活动场地,增设停车设施等。
(2)挖掘“被遗忘”的闲置空间,包括老旧住区中使用效率低下的公共绿地、闲置用地、危旧构筑物等,通过系统化的改造,赋予其新的公共性功能,打造社区菜园、休闲健身空间等居民喜闻乐见的功能形式,激发社区活力,提升居民对社区生活的依赖度。
(3)探索功能混合的可能性,推行开放住区模式,实现老旧住区公共资源的整合和共享。例如,修建立体停车库、共享停车位,改造社区公共广场和绿地,实现公共空间资源的优化配置等;充分利用垂直空间,通过符合规范要求的屋顶加建等方式,打造屋顶花园,在有条件的开放空间区域布置地下停车场;同时,也可以引导社区公共空间在不同时段的功能共享,如公共活动场地和停车场地的分时共享等。
4.3 多方融合的更新机制
老旧住区更新应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以政府为主导,达成居民、开发企业和第三方非盈利机构等不同参与主体的合作与共赢。以居民个体和小微企业为主体的小规模渐进式老旧住区更新模式尚未得到充分重视,创新社区的更新机制显得十分重要。规划管理应以政策规范和疏导为主,推动以居民个体和小微企业作为申报主体的老旧住区更新流程和机制,提升居民参与度,实现社区自管自治,以激活老旧住区更新的自组织机制。该机制下,居民可根据专业的设计、咨询和评估来进行自组织更新,由政府机构对改造更新进行规范化的引导与审批,并由社区公示更新方案,在达成共识后,便可以进行自发改造项目的实施(图11)。通过这种居民的规范化自主更新模式,老旧住区的风貌更新将具有更多的可能性,强化居民与社区的归属感,提升社区的多元化与活力,创造出具有未来感的新式旧住区。

图10 老旧住宅自发改造规范化引导策略

图11 多方融合的更新机制
4.4 资金反哺的经济运营模式
老旧住区更新也需要充分考虑经济可持续性。资金是不可忽视的部分,通常,城市更新的资金来源依赖于政府投入或开发商投资,政府资金往往有限,不可持续;而开发商资金一般只有在一定规模开发时才会投入,且以盈利为目标,不适用于小规模的社区改造和非盈利性的公共设施改造。本研究提出,将居民自发改造过程规范化后收取的资金进行统一管理,设置成社区基建基金,并用于反哺社区公共设施的改善优化,这是一种将私人改造获利溢价资金反哺社区更新的经济运营模式。这种模式由于鼓励居民自主进行改造,规模适当,不会造成大拆大建,是一种谨慎更新的模式;同时,也激发了老旧社区更新的内在动力,达成多方共赢的局面。通过这种创新型的经济运营模式,实现社区可持续更新(图12)。
5 结语

图12 社区资金反哺运营模式
上海老旧住区更新是目前上海城市发展面临的重要议题,对改善居民生活、彰显城市特色风貌、优化建成区公共环境、重塑城市魅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老旧住区的更新问题纷繁复杂,涉及多层面的机制、流程及利益平衡问题,单一部门和机构难以解决,需要上至政府管理部门,下至居民个人及各类社会企事业机构的支持。只有统筹全社会的资源和力量,才能推进上海中心城区老旧住区更新工作的可持续发展。本研究结合国内外的住区更新理论和实践,提出规范化的空间改造、公众参与的公共设施提质、建立多方融合的更新机制和资金反哺的经济运营模式四个方面的老旧住区可持续更新策略,以期激活社区活力,营造高品质社区生活,修复城市风貌,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