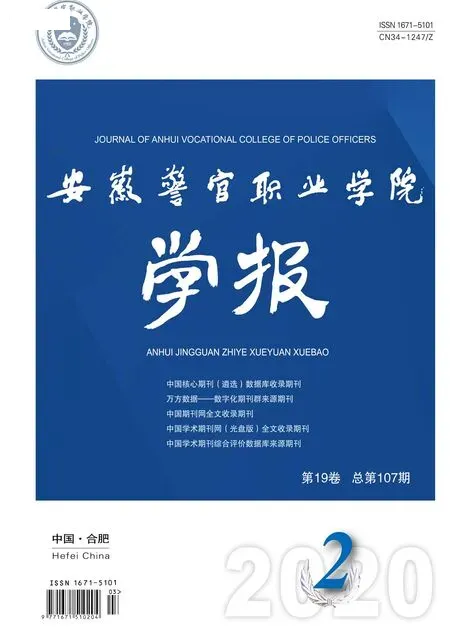网络背景下侮辱罪的流变及刑法应对
李 韬
(东南大学 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一、问题提出
我们首先看一下几则案例:
案例一:2016 年4 月, 知名艺人王某在其新浪微博上发布声明,称其妻子马某出轨宋某。 王某的声明发布后,引起了舆论广泛的关注,网友评论中绝大多数都是谴责马某的出轨行为,且用语多含有极强的侮辱、人身攻击成分。 一时间,对马某“当代潘金莲”的称呼在海内外不胫而走。
案例二:A 在酒店里往B 的嘴里撒尿, 并带有炫耀的意思,拍下了视频传给C 看,C 将该视频转发到了一个微信群里, 致B 喝尿的视频扩散,A、C 的行为能否构成侮辱罪?
案例三:2013 年12 月,蔡某因怀疑徐某在其经营的服装店试衣服时偷了一件衣服,将徐某在该店的视频截图配上“穿花花绿绿衣服的是小偷,求人肉,经常带只博美小狗逛街,麻烦帮忙转发”的字幕后,上传到其新浪微博上。 蔡某的行为引发了网友对徐某广泛的人肉搜索,徐某的个人信息、家庭住址、所在学校等信息全部曝光,网友对徐某的批评和辱骂也在不断蔓延,同时徐某在生活中也遭受了来自老师、同学等的非议。 两日后,徐某跳河自杀,蔡某也随之被警方抓获归案,并最终被法院以侮辱罪判处有期徒刑1 年。
案例四:2015 年1 月19 日23 时许, 姚某在绍兴E 网论坛以网名“蓝月伊人”的名义,发表“对绍兴交警关于网民称交警骂街事件的调查存疑” 一帖。2015 年1 月20 日16 时23 分许,陈某以网名“城西小师爷”的名义,在“蓝月伊人”发帖内跟帖,以“狗、SB”等侮辱性语言,辱骂姚某在绍兴E 网论坛使用的网名“蓝月伊人”。 2015 年1 月20 日16 时30 分许,被告人陈某又以网名“城西小师爷”的名义,在绍兴E 网论坛发表“蓝月就是一个戏文唱过头,自我感觉太好,好到没有朋友”一帖,同样以“狗、SB”等侮辱性语言,辱骂自诉人网名“蓝月伊人”,该帖截止删帖点击数达5943 次,回复数达104 次。 后姚某向公安机关报案,法院最终判决陈某无罪。
以上四则案例是网络时代背景下与侮辱罪有关的案例, 相似之处在于行为人的行为均导致了对方的名誉遭受了重大的损害,但是,由于其中掺入了网络的因素,与传统侮辱罪的认定存在区别,行为人是否构成侮辱罪具有值得探讨的空间。“网络因素的介入,改变了组成犯罪的‘原料’和‘元素’,导致了犯罪的构成要件要素的变异,包括犯罪对象、犯罪行为、犯罪目的和犯罪结果等方面。 ”[1]以上四则案例折射着网络背景下侮辱罪所发生的新的变化, 如何加以应对,值得我们研究。下文将就侮辱罪在网络背景下发生的流变展开梳理,并分析其应对之策,同时会就上文提到的案例展开评析, 以期合理规制网络背景下的侮辱罪。
二、侮辱罪在网络背景下的流变
根据《刑法》第246 条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 情节严重的,处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前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侮辱罪,是指使用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败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 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 当今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也给刑法领域的传统犯罪带来了诸多变化以及归责上的挑战。如在网络背景下,传统犯罪的犯罪总量与不法程度较之在物理空间实施的同类犯罪呈现几何级增长、犯罪预备行为的不法属性发生异化、犯罪参与的刑事归责面临障碍等[2],这些问题与挑战考验着刑法教义学在网络背景下的应对。 侮辱本质上就是导致他人社会评价降低、名誉受损的行为,其词义具有广泛的伸缩空间,与网络相遇,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刑法问题, 侮辱罪在网络背景下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侮辱罪特殊主体的出现
在网络背景下, 实施侮辱行为的主体出现了新的情形,首先是拥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由于会受到舆论广泛的关注, 其一言一行在网络空间中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力。 如同样是披露某项有损被害人名誉的事实,如果单纯在现实生活中口口相传,限于时空因素, 所扩散的范围以及对被害人名誉损害的程度可能并不严重。而网络社会则不一样,由于网络的传播效应,某一项事实公布到网上之后,很快就会广泛扩散,为相当大范围的人们所知,而如果披露事实的主体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公众人物, 无疑又会进一步加大信息扩散的程度, 网络媒介加上公众人物自身所具有的广泛关注度, 使对法益侵犯的可能性上升了至少两个台阶, 同时公众人物基于对自己身份的认识, 对于自己所发布的信息所带来的广泛扩散进而严重毁损对方名誉的后果, 即使不是抱有积极追求的态度,至少也存在放任、听之任之的间接故意,因此并不排除对其进行规制的可能性。 但是,在决定是否规制时, 还涉及到保护公众对公众人物的知情权的违法阻却性事由的问题, 如何衡量其与对被害人名誉保护的利益关系,以及在进行规制时,如何加以具体认定,均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另外一类特殊主体是积极参与网络侮辱行为的网民。发生在现实空间中的传统侮辱罪,往往是特定的一人或多人实施加害行为,比较容易判断加害方,但是在网络侮辱中,参与“网络暴力”的往往是不特定且数量庞大的网民, 他们共同参与到了对被害者的侮辱之中, 共同导致了被害者名誉严重受损的后果, 但是事实上不可能对数以万计的所有参与侮辱行为的网民均进行处罚,于是,“法不责众”的现状与对被害人名誉的保护成为了规制网络型侮辱罪当中的另一对矛盾。或许有人会认为,不需要处罚所有参与网络侮辱行为的网民, 虽然网络上参与侮辱言论的网民人数众多, 但由于侮辱罪的成立有“情节严重” 的要求, 并不是每个人的情节都达到严重的程度, 因此只需要处罚那些侮辱情节达到严重程度的积极参与者即可。 但是, 如何划定积极参与者的范围,仍然是一个问题。
(二)侮辱罪实行行为的变化
发生在现实空间的传统侮辱罪中, 侮辱行为表现多是泼洒粪便, 扒衣服等形态, 具有一定的物理性、现实性,而网络空间中侮辱行为的表现形态则迥异于现实世界当中, 不需要有直接面对面的身体接触, 加害者相隔万里, 只需要在网络空间中进行打字、转发等特定的操作,即可以实现对被害者的“隔空”侮辱,可以说传统侮辱罪的实行行为在网络空间中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具体到侮辱罪的认定上,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根据刑法规定,侮辱罪的成立需要满足“公然”的条件,现实生活中传统的侮辱样态,由于侮辱行为一经完成,通常侮辱他人人格名誉的后果也已造成,行为的公然与结果的公然几乎是同时发生, 因此在侮辱罪的“公然”性要件上没有特别的认定困难。 但是,网络背景下的侮辱行为由于多是“隔空”进行,且由众多侮辱行为积累而成,并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发酵,最终导致了使被害人名誉严重受损的后果,由此导致在侮辱行为与侮辱结果之间往往存在着一定的时空距离,行为的“公然”与结果的“公然”并不重合,因此也就有了以何者作为“公然”标准的解释问题。
同时,与侮辱罪的“公然”要件密切相关的,还有对于网络空间中的传播行为的定性问题。 由于网络的虚拟性,网络空间中不可能实施泼洒粪便、撕扯衣服等物理形态的侮辱行为, 其主要的表现方式只能是通过网络言论的方式, 而网络的突出特征即是其极强的传播扩散性, 网络侮辱言论正是借助了网络这一媒介,才得以广泛扩散传播,并由此产生了极大的危害性。因此传播侮辱信息的行为,对于侮辱信息的扩散及对被害方名誉的损害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由于侮辱罪的成立要求“以暴力或者其他方式公然侮辱他人”,因此,在网络空间中传播侮辱他人的视频或者转发侮辱他人的信息等行为, 能否属于以其他方式公然侮辱他人呢?如前文中提出的案例三,将他人私发的侮辱性的视频转发到微信群中导致视频扩散,此类传播行为,是否属于侮辱罪的实行行为呢? 值得深思。
同时, 侮辱行为与侮辱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认定问题, 也是网络背景下侮辱罪实行行为方面涌现出的新问题。发生的现实空间中的侮辱行为,通常会直接伴随着侮辱结果的发生, 侮辱行为与侮辱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需要特别的认定。但是,网络空间中的侮辱行为, 由于主要表现为言论犯罪的形式, 行为人单纯在网络空间中所发表的某一条侮辱性言论, 其本身尚不足以产生对被害人极大的名誉损害,正是借助了随后众多网友的评论、转发等传播行为, 才使其危害性上升到了值得以侮辱罪进行规制的程度。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否认定初始侮辱行为与最终侮辱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以及认定的话以何为标准, 也成为了网络背景下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三)侮辱罪定量标准的困局
在网络背景下, 侮辱罪出现的变化还包括定量标准的难以厘定。由于根据刑法第246 条,成立侮辱罪需要具有“情节严重”的要素,因此侮辱罪的定量标准,也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侮辱罪在网络背景下认定“情节严重”的困境体现在:一方面,网络侮辱的行为表现方式不同于传统的泼洒粪便、 扒拉衣服等从外观上便具有明显侮辱性质的行为,需要结合其所发表的文字、图片、语音、视频等的内容加以判定, 因此增加了认定情节是否严重的难度; 另一方面, 在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层面上,立法机关和最高司法机关也没有就侮辱罪“情节严重”的认定给出明确的标准,虽然2013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网络诽谤解释》第2 条将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 浏览次数或者转发次数、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精神失常、自残、自杀等严重后果以及2 年内曾因诽谤受过行政处罚,又诽谤他人作为诽谤罪“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但这主要是针对治理网络谣言、规制诽谤罪而言的,对于侮辱罪并不能够完全的适用。如关于《网络诽谤解释》中将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或者转发次数作为“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之一,这与诽谤罪作为捏造事实以毁损他人名誉的犯罪是相互适应的, 但是对于主要通过侮辱性的意见表达或者披露有损被害人名誉的事实以进行贬低毁损他人人格名誉的侮辱罪却未必适用,侮辱信息的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或者转发次数并不能够完全反映出侮辱情节的严重程度, 必须结合侮辱信息的具体内容以及相关人物对被侮辱者的社会评价, 才能准确全面地体现出侮辱的程度。
三、侮辱罪流变背景下的刑法应对
既然如上文所述, 在网络背景下, 侮辱罪在主体、实行行为以及定量标准层面上都发生了流变,如何回应网络所带来的挑战, 就成为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 对此,针对侮辱罪在主体、实行行为以及定量标准上所发生的变化,本文作出如下针对性的回应:
(一)特殊主体的认定
1. 在网络空间中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对于他们在网络空间中发表侮辱他人言论的行为,笔者认为,规制时需要结合其身份,就其在网络空间所具有的影响力加以判断。(1)由于公众人物在网络空间和现实生活中具有的影响力, 其所发布的侮辱性的内容必然会引起广泛的关注,为人所周知,故侮辱罪的“公然”要件得以满足。(2)关于侮辱性言辞的内容,如前所述,由于网络型侮辱罪主要是一种言论犯罪, 因此判定行为人是否进行了侮辱行为必须结合其言辞的内容。如果是高度人身攻击、侮辱性的言论,自然可以作为侮辱罪进行处理;值得思索的是,如果言论本身并不是侮辱性质的言辞, 而是披露了某项虽然真实但如果广为扩散则会具有毁损涉事方名誉可能性的事实, 如上文中所提到的艺人王某披露其妻马某出轨的案例,是否该当侮辱罪?首先需要明确,侮辱罪并不限于直接辱骂他人的意见表达,在侮辱罪与诽谤罪之间的关系上, 不能简单地认为侮辱罪属于意见表达,诽谤罪属于事实陈述,如此理解的话,由于诽谤罪仅限于不实的事实披露,因此无法将披露了真实的事实, 但严重毁损对方名誉的行为纳入刑事法网, 因此侮辱罪本来就应包括侮辱性的意见表达和披露真实但毁损他人名誉两种类型。 因此,艺人王某披露其妻马某出轨的案例中,即使王某公布的是真实的事实,其妻确实出轨,也并不会排除侮辱罪的成立空间。 而是否成立侮辱罪,笔者认为,应该综合考量以下几点因素:该事实的性质,即如果广泛扩散是否会严重损害被害人名誉; 公众人物的社会影响力大小, 其关系到所发表的言论可能受到关注并进而扩散的程度;以及更为关键的、在公众知情权与被害人名誉保护之间的权衡,对此,如果公众人物所披露的事实关系到社会公共利益, 应该认为保护公众对此所享有的知情权要重要于被害人名誉的保护,反之,如果该事实完全属于个人私事、家庭纠纷, 应该认为公众对此并不享有值得刑法保护的知情权,其应该让位于被害人名誉的保护。
2.积极参加者主体的认定。 笔者认为,首先应该将参与主体限定为积极参加者, 对于只是少量地评论转发的主体,没有必要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只有积极在网络空间进行评论、转发等行为,才具有严重损害被害人名誉的可能性,也才可能达到侮辱罪“情节严重”的要求,而如何认定“积极参加者”,可以参考郭玮博士所提出的几点考虑因素:[3](1)数量标准。首先可以将《网络诽谤解释》中的同一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或者转发次数作为认定“积极参加者”的标准之一, 亦即网民将始发者的侮辱信息转发或者是加工评论后所发布的信息,如果其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或者转发次数达到《网络诽谤解释》中的标准的话, 可以认定为其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侮辱信息的接收者, 而是实质性地促进了对被害人的侮辱程度,具有以侮辱罪规制的可能性。 不过,次数的统计具有一定的纰漏性, 并且单纯以次数作为衡量积极参与侮辱行为以及对被害人的侮辱的程度, 可能还并不算周延, 因此需要考量其他的标准加以综合认定。 (2)开辟新的传播平台。 鉴于网络上存在诸多传播平台,同时不同平台的用户并不完全一致,因此如果行为人将侮辱信息的始发者所发布的信息, 转而发布到其他平台, 可以说是为侮辱信息的扩散开辟了新的传播平台,相当于新的始发者,同样具有规制的可能性。当然,在进行规制前需要衡量参加者开辟的新平台的社会影响力、传播力的大小,如果新开辟的平台受众不多、社会关注度较小,则并没有实质性地升高被害人人格法益被侵犯的危险,反之,如果新平台的社会影响力较大,则具有规制的必要。 (3)进行人肉搜索。 “狭义的‘人肉搜索’是以网络为平台,以网民为资源,逐渐获取某个人或某些人的信息,然后分析整理这些信息, 最后找出这个人并确认某个人信息的过程。 ”[4]人肉搜索本身就是一种严重侵犯被害人隐私权、进而侵犯被害人名誉权的行为,同时由于其披露曝光被害人详细个人信息资料, 使侮辱行为从网络空间延伸进入到了现实世界, 大大提升了对被害人名誉的侵犯程度, 因此进行人肉搜索行为的主体, 具有被认定为网络侮辱行为的积极参加者,进而以侮辱罪进行规制的可能性。
(二)实行行为的认定
如前文所述,基于侮辱罪在网络背景下的特点,认定侮辱罪的实行行为时重点应该是对于侮辱罪“公然”要件的理解、对于传播行为的定性以及对于侮辱行为与侮辱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认定,对此,笔者将作如下分析:
1.关于侮辱罪的“公然”要件。 对于“公然”的理解,刑法理论界存在将“公然”理解为“行为的公然”还是“结果的公然”的对立,前者认为侮辱罪的“公然”是指行为的公然,即侮辱行为必须是公然进行,面向不特定或多数人;后者则认为,侮辱罪的“公然”是指结果的公然, 即使侮辱行为是针对特定人或者少数人进行的,只要具有传播的可能性,也应认为属于“公然”。 但是,“结果的公然”的观点并不合适。 首先, 根据文理解释,“以暴力或者其他方式公然侮辱他人”解释为行为上的“公然”明显要比解释为结果上的“公然”更易于解释;其次,“结果的公然”的观点容易导致行为人是否成立侮辱罪由他人的传播意思所决定,这并不妥当;另外,只要具有结果上的公然性就可以成立侮辱罪,可能导致个人闲话、日常言论也构成侮辱罪,不当扩大了侮辱罪的处罚范围。[5]因此,“结果的公然” 的观点不足为取。 而在网络空间中,鉴于网络的传播效应,仍应坚持以“行为的公然”作为侮辱罪的认定标准, 否则可能导致很多在进行时尚不具备公然性的侮辱行为, 却由于他人的广泛传播而产生了公然侮辱的结果的, 从而成立了侮辱罪,这样便不当扩大了侮辱罪的处罚范围。 亦即,侮辱行为必须发生在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网络空间之中,如果只是私发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或者只是在好友人数较少的朋友圈中发表侮辱性的言辞, 虽然也不排除具有扩散传播的可能性, 但出于限制处罚范围的考量,不应认为是在进行公然侮辱。
2.由于网络的传播效应,传播行为也可界定为侮辱罪的实行行为, 其可以认定为公然侮辱的一种方式, 亦即, 即使本人没有直接在网上发布侮辱信息,但若积极参与侮辱信息的扩散,也应属于侮辱行为,因为其实质性地提升了被害人被侮辱的程度,因此一些如转发视频信息到人数较多的微信群、 朋友圈或者微博、论坛等网络平台等的传播行为,也属于公然侮辱他人的情形, 如果极大地提升了对被害人名誉的损害,也应纳入规制的范围。如本文中的案例三,传播撒尿视频的B,就应构成侮辱罪。也就是说,网络空间中的侮辱行为,既可以是直接发表言论、视频等,也可以是传播言论、视频。 同时言论视频的内容,既可以是侮辱性的意见表达,也可以是披露对被害人名誉不利的真实事实。
3.在侮辱行为与侮辱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认定上, 考虑到网络背景下初始侮辱行为与介入侮辱行为在对侮辱结果的发生上均可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笔者认为,可以借鉴日本学者山口厚教授对因果关系的理解,“因果关系应该理解为实行行为的客观危险性向构成要件结果现实化的过程(危险的现实化)。 ”[6]即,判断实行行为与构成要件结果有无因果关系,需要判断行为的危险性的大小,其是否向结果现实地转化。因此,对于网络背景下侮辱行为与侮辱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应分别考察初始侮辱行为与介入侮辱行为对侮辱结果产生的危险性的大小。 如果初始侮辱行为本身危险性较大, 对侮辱结果的产生发挥着重要作用, 应当认为初始侮辱行为与侮辱结果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反之,如果初始侮辱行为本身尚未实现对被害人人格名誉的公然侮辱, 被害人最终遭受名誉严重损害的结果主要是由广大网民的人肉搜索、谩骂评论、转发传播等行为所造成,则应当认为初始侮辱行为与最终侮辱结果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如上文中的案例一,行为人蔡某将被害人徐某在其店的视频截图配上“穿花花绿绿衣服的是小偷,求人肉,经常带只博美小狗逛街,麻烦帮忙转发”的字幕后发布到网络空间,由于蔡某提供了被害人的外貌截图以及行为特征, 并教唆网友进行人肉转发, 可以认为蔡某对被害人名誉遭受严重损害并最终自杀的结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法院最终以侮辱罪判处蔡某有期徒刑1 年没有问题。 而在案例四中, 由于陈某所侮辱的只是姚某在网络论坛的虚拟身份,由于“侮辱网络虚拟身份的行为应当具有公然性,且必须同时及于使用者的实体人格,即他人能够根据虚拟身份推断出被害人的现实身份, 并可能降低其外部名誉或贬损内部名誉时, 方可成立侮辱罪。”[7]而根据陈某侮辱的情节,社会公众尚不能从姚某的虚拟身份直接推断出其现实身份, 因此其初始侮辱行为本身并未实现对被害人人格名誉的公然侮辱,即使其后如果有网友的转发、搜索等行为并导致被害人遭受人格名誉的严重侮辱,应当认为,也不应该归责于初始侮辱者姚某, 故本案法院的判决也是正确的。
(三)定量标准的衡量
关于侮辱罪的定量标准,首先,由于网络侮辱行为不同于传统的侮辱行为, 主要表现为一种言论犯罪,从其外观无法直接识别侮辱性,因此必须结合其内容进行判断。 即网络侮辱言论的内容需要是对被害人进行人身谩骂、 攻击或者披露有损于被害人名誉的事实, 且如果广泛传播具有严重损害被害人人格名誉的危险性。 其次,如前文所述,由于侮辱罪不同于诽谤罪,不可以把《网络诽谤解释》中将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或者转发次数作为“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套用到侮辱罪之中,实际被点击数、浏览数、转发数等数额标准,一方面难以避免统计上的纰漏, 另一方面也不能准确全面地反映出被害人被侮辱的程度,因为侮辱的认定不同于诽谤,不是单纯的事实真伪的判断问题, 而是需要纳入一定的社会评价。 因此,对于网络侮辱“情节严重”的判定,笔者认为应采取多元性的衡量标准,以准确全面反映出侮辱的程度。 具体可以参考以下四方面的因素:被害人方面可测量的损害、加害人的规模、传播平台的性质、传播的时长。
首先是被害人方面可测量的损害。 由于侮辱罪是一种侵犯人格名誉的犯罪, 被害人在人格名誉上所遭受的损害往往是难以准确测算的。但是,如果这种人格名誉上的损害转化成了现实空间中可测量的损害,如侮辱行为造成被害人或其家属自杀、自残或者精神失常,可以认为侮辱行为在量上达到了“情节严重”的要求。 当然,在这一方面由于介入了被害人方面的因素, 因此需要准确认定侮辱行为与被害人方面可测量的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 对这一问题可以归结到对侮辱行为危险性的判断问题上, 前文已作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其次是加害人的规模。 单个加害人孤立地进行侮辱,在网络空间产生的影响可能并不是很大,但如果加害人汇聚成了具有一定组织性、 专业性的群体进行对被害人的谩骂攻击,其危害性便要急速上升,其典型便是网络水军。 “网络水军接受客户的委托,为其宣传造势,美化自身,攻击他人,经常会直接或间接地侵犯他人的名誉。 ”[8]如果行为人雇佣网络水军攻击侮辱他人,由于加害人规模庞大、侮辱信息传播速度飞快, 很容易对被害人的人格名誉产生严重损害。
传播平台的性质也是值得考虑的一个因素。 考量网络背景下侮辱行为对被害人的侮辱程度, 离不开侮辱信息的传播程度,而信息传播所依赖的平台,又在促进信息的传播扩散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如果信息传播平台只是在网络空间中没有太大影响力、关注度不高的小微型社交网络, 其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自然远远抵不上新浪微博、百度贴吧、天涯论坛等已经经营多年、 在网络世界中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关注度的大型传播平台, 因此判断侮辱行为的情节程度, 也需要将侮辱信息传播平台的性质纳入考虑之中。
最后是侮辱信息传播的时长。上文提到,虽然侮辱信息传播所依赖的平台, 会影响到侮辱行为的程度,平台影响力越大,侮辱程度一般越强,反之亦然。但与此同时, 侮辱信息传播的时长也是影响侮辱程度的一个重要变量。鉴于网络的动态性,网络空间中的信息一直处在不断的传播扩散之中, 原来发布在小众平台上的信息, 随着时间的推移发酵也可能扩散到大型平台上,并产生严重的危害性,同时侮辱信息的传播时间也直接影响到其影响力和关注度,因此判断侮辱行为的严重程度, 也需要考量侮辱信息传播的时长。 司法工作者在具体判断网络侮辱行为是否达到“情节严重”的定量标准时,需要将以上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全面判断侮辱行为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