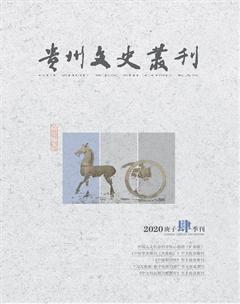姚华赋学观及其现代学术意涵
唐定坤
摘 要:姚华的赋学具有西学视野、实践创作、艺术学映照的立体视角,值得从转型时期学术的“现代性”视角加以抉发。其内容主要体现在赋体源流、赋与其它文体的关系、论赋取向等论述中,较之传统在考镜源流、统摄观念、文体发展、创作实践四个方面具有现代意味的转变。他治赋学注重深度和广度相融合的系统性,出脱经学最为彻底,昭示了转型时期吸收西学的“现代性”治学观念;而其基于文艺创作体悟和客观研究所整合出来的价值判断与独特论断,在建构民族独立的赋学话语体系、启发现代赋学研究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姚华 民国赋学 传统 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I2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20)04-78-86
作为中国文论的有机组成部分,赋论一直和其它文体论一样,呈现出创作服务于理论的特征,因此若论其学则必然兼顾其创作。传统赋论大致以唐为界,唐前固然以古赋为中心,唐后则在理论言说上兼融一切赋体,在“法”的创作论倾向上则以律赋为主,创作亦然。到了晚近民国之际,由于受西学的冲击,学者的治学观念产生了巨大变化,传统创作功底之“厚”遇合西学观念之“新”,致使其研究在传承中出现了明显的新变特征,具有丰富的现代学术意涵和重大的学术价值。刘师培、姚华、章太炎、刘咸炘等学者可谓赋界代表。近来有学者陆续注意到民国学者的赋学贡献,而于专人研究则只注意到赋论相对较多的刘师培和刘咸炘1,对创作、赋论篇幅相对较少却胜义纷呈的章太炎、姚华等人则付之阙如。贵州姚华(1876—1930),字重光,号茫父,早年曾留学日本,是民国时期“旧京城的一代通人”,以书画鸣于世,实则举凡诗、词、曲、文、赋、金石颖拓、双钩绝学等创作无不喜好;作为学者的一面,则在金石学、小学、书画、文学尤其是曲学研究等方面都颇有成果,其著述收入自订稿《弗堂类稿》中,近代名流如梁启超、陈师曾、鲁迅、梅兰芳、郑天挺、黄秋岳等皆对之倍加赞誉。姚华赋论主要体现在“博涉广营,根柢雄厚”2的系统之作《论文后编》中,且多被选著收录3,另外曲学名著《曲海一勺》中也涉及一部分;实际上姚华还是民国学者赋作最多的人,按其“生性嗜辞赋,惜未得传者”4的记录,可知他对己作的自负,他不仅手抄六朝小赋而加以摹写,且“每一赋成,必写为画”1。因此,其赋学具有西学视野、创作体悟、艺术学(含金石书画文字之学)映照的立体视角,在吸收西学观念、摆脱传统赋论经学本位等方面都有特别的体现。其中的主要观点及其所蕴涵的现代学术意涵,不仅是描述民国赋学史的重要内容,而且对于今天的赋学研究方法,也具有一定的参照意义,值得加以抉发。
一、姚华赋学的具体内容
目前关于姚华的赋学研究,都呈现在通论性著作中,如何新文等著《中国赋论史》、许结《中国辞赋理论通史》、孙福轩《中国古体赋学史论》等专著中都有所提及。但因概论赋史而甚简略,有必要首先对姚华的赋学内容进行钩沉,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赋源。关于赋的起源,历代赋论受班固“赋者,古诗之流也”2的影响,而追溯于《诗》,刘勰则更进一步扩容此说:“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3不仅继续将赋的源起纳入《诗》学源流系统构造,而且从文体上关注到了《楚辞》的作用,将荀子、宋玉看成“爰锡名号”的标志性人物。姚华之说表面上承自刘勰,实际上大相径庭,他认为“诗有比兴,与赋为三,荀书演赋,其体益广。《楚辞》递兴,继生宋玉,赋始敌诗,以授汉人”,于是得出“赋有三本:其一承《诗》,其次拟荀,其次宗楚”4的认识。并且,源出“三本”之说仍有主次,即“三百篇之《诗》,言其敷陈,亦称曰赋,然未尝独名一体。荀子赋篇,其始创矣;体制初成,演而未畅,此诗之广也”5。《诗》和荀子皆不是关键的因素,宋玉才是汉赋的决定性人物,“宋玉之所为,则斟酌楚屈原、赵荀卿,调和况荀平屈,所纳较多,厥涂遂广”6。这是以宋玉开汉大赋一脉为主的赋源建构,既不同于班固的“诗源说”建构,也不同于刘勰的荀宋“爰锡名号”“蔚成大国”说。
(二)赋体流变。虽然姚华论赋主要以宋玉一脉为主,但“三本”之源不可忽略,所以在流變上姚华跳出了《汉书·艺文志》次四家赋的说法,而另行建构了一种“发为枝柯”的流变体系:“孔臧、司马迁仅能为荀之质,其馀名者,皆屈宋之流也。然为屈原者,贾生一人而已;司马相如则为宋玉,而扬雄、班固、曹植三分其军。其远祖庄生者,厥惟阮籍,顾后无嗣者。六代之际,相承递变,陆机、潘岳、谢庄、鲍照、江淹、庾信之属,醖酿陈篇,孕育新制,遂启唐风,更著功令,于是赋古今之目,较然分焉。”7姚华重点考察屈宋一脉,注意每一位赋家的取法流变。此外他还特别提到“庄周本攻儒术,特好为诡谲,其辞若仙,而不为赋”,这是对孙梅《四六丛话》所引项安世之说的辨驳,不过他仍从精神气质的角度将之与屈赋并为“庄骚一脉”8,所以在讨论赋体之流时特意提到“远祖庄生者”的阮籍,足见其考辨源流而能鞭辟入里,明析体格而能通达兼顾。至其描述六代古赋之变以开出唐律赋,指明受秦观论赋的影响,虽然此论祝尧《古赋辨体》、吴讷《文章辨体》等都已先论及,但姚华仍有不同的辨说:“当古赋渐变 ,律赋未起,转徙所经,或谓骈赋《四六丛话·叙赋第三》,强为分别,反加紊乱。”9他认为孙梅《四六丛话》中“骈赋”的称名“语邻重叠”,“骈”指向句式之骈,而赋何尝没有专求骈句的子类,所以双重指向并不能标示出这一过渡时段的赋体,是不精确的,这一深入的辨体仍属卓见,至今似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三)赋与其它文体的关系。文体交互影响论也可以说从属于赋的源流部分,为了方便理解,我们单独提出。姚华的论述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骚赋关系。汉代以来在目录学上虽骚赋有别,刘勰《文心雕龙》“辨骚”“诠赋”更别为两篇,但因赋“拓宇于楚辞”的关系,历来在称名上往往等屈骚于屈赋,或称楚辞,其中关系,鲜有能析言之者。姚华以为:“自屈原赋《离骚》,南国宗之,名篇继作,通号《楚辞》。《楚辞》者,楚人之辞也。虽‘凤兮‘沧浪,已载前籍,而骚尤深远,其辞若跌宕怪神,其思则缱绻恻怛,……原所为不一篇,大都相类。及宋玉变而广之,溢以为赋。自尔赋家,大抵兼攻《楚辞》,《楚辞》家所为,亦多与赋不别。”1这就从三个方面将二者的关系讲清楚了:屈原之作“于诗为别调,于赋为滥觞”2,真正影响赋的是宋玉对屈骚的“变而广之”,这已见前述;赋家因为骚的“滥觞”关系而“兼攻《楚辞》”,站在这一角度则可称骚为赋;反过来,楚辞家所作则与赋不同,这是因为“楚辞高古”而“体若多纷”,《楚辞》以下的诗词歌赋等后起文体只能“援以自益”3。二是诗赋关系。在他看来,“律赋既行,古赋衰歇,格律拘束,不便驰驱,登高所能,复归于诗。于是李杜歌行,元白唱和,序事丛蔚,写物雄伟,小者十馀韵,大者百馀,皆用赋为诗,汉人所未有《项氏家说》。清人律赋,往往有以五七言相间成篇者,或竟体七言,亦以为赋,虽出庾信,特律所不许,罕觏名篇”4。他将古赋的衰歇和律赋的兴起、唐诗的兴盛三者结合起来作通盘考察,发展了项安世之说,具有一种宏阔的文体综观视野和通达的文学观。三是赋文关系。如他论宋代文赋:“宋文以笔为文,作赋亦或由之。欧苏所制,号出荀子,亦杂庄生。”5这是论文体的交越互用。又考察论体文的特征是“析理”,追求“理胜事徹,笔振其辞”,故而历代文人“论多不善”,“论著之家,往往不兼辞赋”“唐宋以来,赋不逮于古,而论则多畅”6。正是以诸种文体的特征来互为参照,发现彼此的短长和作家的文体拘执,此一论断既承自曹丕《典论·论文》中作家才性和文体匹配之说,还蕴涵了文章辨体和近代西学注重思辨的视角。
(四)评论及论赋取向。姚华的论赋取向是在对赋家和赋体的评论中体现出来的。他对赋家的直评虽不多,然实有精彩的见解,如谓屈原之作“其心则诗,言则庄也”“不受桎梏,自成闳肆”7极为精当。又谓荀子之学“源出西河,粹乎《诗》《礼》之传,及其为文,则辞正而旨约,志闲而气肃,《礼》坚其中,《诗》被其外,赋之质者也”8,虽承自张惠言“其原出于《礼经》”9之说,然更为综切。评价律赋则较详细:“今赋试于所司,亦曰律赋,时必定限,作有程式,句常隔对,篇率八段,韵分于官,依韵为次,使肆者不得逞,而谨者亦可及。自唐迄清,几一千年,强绳墨于场屋,或规矩于馆阁,其制益艰,其才弥局。”10显然是以批评为主。又论文赋:“宋文以笔为文,作赋亦或由之。欧苏所制,号出荀子,亦杂庄生,或以为文赋,则又文质殊观,名实反戾矣。”11与律赋一样,评价不高,足可见出作者论赋宗法六朝以前的古赋,唐以后的赋则非其所取。
(五)赋作。民国学者大都理论兼及创作,如章太炎、黄侃、姚华三人更有严肃的赋作,这也是他们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姚华赋作在民国知名学者中最多,这与他本身好于文艺创作有关,《弗堂类稿》所收文字,不包含书画艺术,仅诗、词、曲、文赋就占十六卷,述学文字才十五卷,其创作要占一半以上篇幅,总量不亚于王国维,可以说他也是民国知名学者中最好文艺创作的人。其集中共收录了十六篇赋,包含骚体赋一篇,即《述德赋》,以自述家世为主,不脱文人宪章祖德的传统;大赋两篇,即《朽画赋》和《双钩书赋》,前者带有小学家气息,后者以散体大赋形式而作,皆取书画题材;咏物小赋最多,含《诘鼠赋》《原鼠赋》《并蒂芙蓉赋》《文蛇赋》《凤尾鞭赋》《晚香玉赋》《晚香玉后赋》《晚香玉别赋》《晚香玉馀赋》《洋晚香玉赋》计十篇,其题材具有画家取物的独特视角,尤以晚香玉得其喜爱,为其反复书写,在写法上则注重体物的抒写和品格的点染,正是咏物赋本色,又《并蒂芙蓉赋》则取六朝骈美之赋的写法;抒情小赋两篇,即《闵灾赋》和《夕红赋》,前者是写日本地震,后者是为周大烈的印“飘零夕照红”所作,率能抒情;律赋一篇,即《蝇丑扇赋》,是作者“年十七试于学使者”的“冠军”之作1。又其《雨窗琐记》:“余夙嗜面具钩脸之术,……曾作《后都剧赋》,敷陈其事,仅成三百言而中辍。”2今集中未收此赋,可见姚华赋作实际上不止这十六篇。通观他的赋作可以总结为两点:一是具有艺术的眼光,取材以书画为中心,应和于他作为书画家的主要身份。二是在体制上和清代以降注重律赋不同,具有普遍的尝试性,十六篇兼取诸体的赋作正是他“生性爱辞赋”的明证;同时这一诸体并写的行为,不同于晚清以来学者及同代章太炎、黄侃等人的创作,这反映了他当时与众不同的文化守持心态,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下文再细论。
二、有别于传统的四个转变
综观以上姚华的赋学,较之于传统而言呈现出一种时代论学的转变,我们可以从四个维度上去分别考察,进而探索其独特的赋学特征和民国赋学的时代面目。首先,就考镜源流的角度而言,具有从诗源说到三源说的转变。章学诚论目录学从刘向、刘歆父子处总结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并同时意识到这作为一种方法论早已推及于论诗文3。推及于赋的产生则主要体现为班固的“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的经学源流建构,“或曰”之说表示推测,欲将赋体看成《诗》之流变,故称之为“《雅》《颂》之亚也”4,下经刘勰补足《楚辞》及荀况宋玉的过渡作用,形成了影响最大的“诗源说”。这带给历代赋论最大的影响就是以《诗》衡赋,形成了不离经学本位的源流叙事及评价标准。近代学者已然发现,诗源说其实并不能体现赋体的产生,即便刘勰的补足扩容也稍嫌混杂,如许结先生就称班固之说为“赋用论”5。实际上姚华变之为“其一承《诗》,其次拟荀,其次宗楚”的三源说就已著先鞭,在省思诗源说时描述清楚了此中的主次影响和远绍旁收的关系。首先姚说别出了《诗》的经学纠缠,按其“三百篇之《诗》,言其敷陈,亦称曰赋,然未尝独名一体”,便指出了《诗》中之赋只是手法而未独名一体,并不构成真正的源流关系,因此“雅颂之亚”的说法在文体特征上便无法立足。再者“荀子赋篇”“演而未畅”的强调,指明了荀赋立体只能算“体制初成”,不可扩大其在赋体形成方面的影响。表面看这是刘勰界定荀子“爰锡名号”的旧说,但实际上清人纪昀特别注意到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总赞“赋自诗出,分岐异派”是“侧重小赋一边”6,他论赋坛十杰,最少是大小兼顾了的;而姚华论荀子之赋乃“诗之广也”,因为“源出西河”而“礼坚其中,诗被其外”,故还不能与诗相敌,可见最少在形成赋体的因素中,荀赋并非关键。关键节点上的人物则是宋玉,他承前启后的功能正在于向前则“斟酌楚赵,调和况平”,从而广开赋体,致使“厥涂遂广”,而能向后“以授汉人”,形成“赋始敌诗”的局面。确认宋玉定体的关键地位,显然是以汉大赋为正体,因为宋玉《风赋》《高唐赋》无论在“王对玉问”的主客问答还是王曰“试为寡人赋之”的导引上,还是在铺陈的手法上,都下开了汉大赋的写法。据此上溯楚辞一脉,则可以界定屈骚“于《诗》为别调,于赋为滥觞”的地位,从而最终形成以大赋发展为中心,余皆旁支影响的赋体源流论。从赋论史上看,大约以章学诚最先跳出诗源说,而认为赋起源出于诸子各家,兼收多元而自成“一子之学”7,只是章说太过庞博而难摄主次;当然亦不乏论家捐弃荀子之说者,如谢榛称荀赋“不可例论”1,程廷祚称“君子略之”2,同代章炳麟称“诗与赋未分离也”3;至于宗骚之说亦代不乏人,如刘熙载称“骚为赋之祖”4,刘师培亦不同意诗源说,且从文本细节上去寻找赋“咸出于骚”5的依据,毕竟过于琐屑而未抓住主要的一面。姚华特别强调宋玉的作用,可能出自程廷祚和王芑孙,但二人都未脱开《诗》学源流说,姚说则在于弃荀而主宋,并且明晰了屈骚的“滥觞”作用,这就在赋体生成论上兼顾了主次远近的因素,形成了《楚辞》滥觞、宋玉定型、旁涉《诗》和荀子这一演变清晰的赋体生成论。
就统摄观念来看,具有从宗经观到“文质观”的转变。我们知道,古人论文章之学皆有着“依经立义”的传统,王逸论《楚辞》“依经立义”6,刘勰《文心雕龙》立“宗经”为文之枢纽,这就很容易导致论家以经学为统摄观念来对文体的生成进行源流建构;就赋而言,刘勰谓“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7,皇甫谧《三都赋》序谓“昔之为文者,非苟尚辞而已,将以纽之王教,本乎劝戒也”,所以班固“古诗之流”的赋学建构实非个案。这当然源于中国强大的儒家经学传统。姚华虽是清末最后一代参加科举考试的士人,但他留学日本曾专门提出以“新知识真学理”攻错传统文化的“中魂西才”之说8,故能完全出脱经学的影响。如前论他称《诗》中之赋“未尝独名一体”,便是无视班固以来经学的评价视角。更为精彩的是他对屈骚的评价:“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其心则诗,言则庄也。楚隔中原,未亲风雅,故屈原之作,独守乡风,不受桎梏,自成闳肆,于诗为别调,于赋为滥觞。”9完全跳出了传统评价《楚辞》的“依经立义”之说,将屈骚看成“独守乡风”而“未亲风雅”的“别调”,正是这一出脱经学的判断,才让他摆脱了历代纠缠不清的骚赋关系论,建构起了兼顾远近主次的赋体生成论。但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姚华的赋学研究有破有立,他在出脱经学的同时还能以“文质观”为论文学的统摄观念,取而代之进行系统的赋体源流建构。他根据章学诚“六经皆史”之说得出“一切之文子孙于史”,故而“凡为文者,必于史取则”10,赋予了孔子“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的新理解,并得出“均文质者,莫三百篇若”的结论,由是建立起了文质视角的文体流变论:“《诗》亡而文质分,赵得其质,楚得其文。况平之后,悉授于汉,一谓之赋。”11这已完全不同于传统宗经观念下的经史源流论,从源头影响来看,荀赋因为“礼坚其中,《诗》被其外”而从属“赋之质者”,宋赋则因“所纳较多,厥涂遂广”而从属于“赋之文者”,两皆为刍型而以宋赋为要,影响于汉,才自足为一体。依照“文章应时而生,体各有当,古俗浑朴,简略泰甚,踵事增华,乃益趋繁”的发展规律,汉赋立体正以“京都巨制,动累篇幅,循其繁也”12。即是说,汉赋是《诗》文质论“文”的一端的新发展。此说真于前人未尝梦见也,颇有现代学术的发展观,即學术越发展越宏肆深沉,文学庭庑从轴心时代向后则越加广大,这是完全符合文体的发展规律的。嗣后他批评宋代文赋“以笔为文,作赋亦或由之。欧苏所制,号出荀子,亦杂庄生,或以为文赋,则又文质殊观,名实反戾矣”。“文赋”从赋的层面看,乃主于荀赋得其“质”失其“文”,于是名实不合,混淆文体,殊为不当。这正与前说一脉相承,以“文质”说为统摄观念纵论文体。表面上看,以“文质”说论赋袭于前代,如汉扬雄曾有“辞胜事则赋,事胜辞称则经”13的宗经贬赋之说,清代刘熙载也有局部的分疏:“屈子之赋,贾生得其质,相如得其文。”1但姚华之说有质的不同,一是既跳出经学本位的影响,同时看到了《诗》的作用而显得通达可观,二是他以之为统摄观念具有系统的现代学术方法论品格,这一点我们后文再论。
第三,就文体发展来看,具有从一体流变到诸体影响的转变。从学术理路上讲,宗经观念的消解意味着研究对象的客观化和平等化,所以在文体发展的考量上,自然不再如传统大都是以一体的流变为中心来加以讨论,而是平视诸体、注意到彼此之间的交互影响。姚华著《曲海一勺》大彰清末以来地位颇低的曲体地位,论及“战国既降,诗分为三:骚、赋、乐府,并成鼎足。”2就是平视诸体的通达论断。又因为他论学有综合的眼光和“贯穿”群籍的工夫3,在此基础上论赋体流变,就特别注意到诸体之间的互动。最为明显的是论唐后的赋史:
律赋既行,古赋衰歇,格律拘束,不便驰驱,登高所能,复归于诗。于是李杜歌行,元白唱和,序事丛蔚,写物雄伟,小者十馀韵,大者百馀,皆用赋为诗,汉人所未有《项氏家说》。清人律赋,往往有以五七言相间成篇者,或竟体七言,亦以为赋,虽出庾信,特律所不许,罕觏名篇。然赋者,古诗之流,亦不能斥其非也。4
讨论律赋注重和古赋、诗的互动,注意到“用赋为诗”和以诗入赋的情况,注重考虑到了左右周边的交互影响。许结先生便特别称赞这里诗入赋和赋入诗“不能斥其非”的态度,是“缘自对文学发展整体流变的把握,属于打破文体限囿的新的文学史观”5。所赞甚是。又如比较论赋二体:“论以析理,……夫笔易以求工,事理艰于所畜。故来文人,论多不善。而论著之家,往往不兼辞赋,其以此耳。”“唐宋以来,赋不逮于古,而论则多畅。”亦一脉相承,俱体现了注重诸体影响的宏阔视野。
最后,其创作实践具有从主于律赋到诸体尝试的承变。赋学史上唐宋以来就存在着古律之辨,清代形成以李调元为首的律赋派和以张惠言为首的古赋派,但这仅是学理场域的论辨,实际上在创作中仍然以律赋为主,这与科考律赋取士的传统有关;不过一流的文人则兼作多种赋体,有论者称之为“古律融通”6。姚华旗帜鲜明地反对律赋:“时必定限,作有程式,句常隔对,篇率八段,韵分于官,依韵为次,使肆者不得逞,而谨者亦可及。自唐迄清,几一千年,或绳墨于场屋,或规矩于馆阁,其制益艰,其才弥局。”7他从创作上对律赋体制限制作家才性的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与前代反对律赋的论家之说大致相同。所以他所作的十六篇赋中,只有一篇是律赋,正是少年应试之作,此外诸体皆有所尝试。他成年时国家已取消了科举制度,又因留学日本具有了广阔的文学视野,所以弃律取古便不足为奇。但另一方面,这也与他生性好艺术的取向有关,他的艺术创作与其学术研究具有等量甚至超量的地位,所以其创作在艺术学的映照下就明显具有一种独特的近代文人趣味,而远较同代学人为重。这既不太同于章太炎、王国维等致力于以学问为主,从而会产生中西文学观的冲突,所以也就没有了关于赋体创作“文学性”8的焦虑感;又因为“学问不关乎科第”9而不同于前代一流文人兼取诸体的功利性考量。同时,此中所蕴含的创作心态反过来对他的赋学论断又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一点要待深入考察姚华赋学的价值才能彰显出来。
三、从治学观念到学术价值
以上简单钩沉姚华不同于前人论赋的四个转变,不难发现其间蕴含着一定的现代学术意味。现在我们更进一步,分析姚华赋学背后的学术观念,揭示其学术价值,藉以补足姚华赋学丰富的现代学术意涵。首先,从治学观念来看,姚华治学注重深度和广度相融合的系统性,昭示了转型时期具有“现代性”的学术品格。上论姚华以“文质观”取代传统宗经之说,对赋体源流的叙述便具有明显的系统性,实际上这种治学观念是贯穿于他的整个治学的。他的曲学名著《曲海一勺》虽以论曲为中心,却能将文体的源起和变迁与社会时代联系起来,并且能从横向的文史和纵向的诗词曲关系去立体考察曲的地位和功能,从而建构起一种“诗统”理论,具有明显的系统性1;所以其中虽偶一言及于赋,仍多洞见。姊妹篇《菉猗室曲话》 虽系考证之作,仍具系统性。而《论文后编》开篇即谓:“文章流别,自挚虞以来,言者众矣,然其流虽晰,而其源或略,至使来者茫昧,故复并而论之。”以下据章学诚“六经皆史”之说而论文,认为“一切之文子孙于史”,围绕《诗》《书》的有韵无韵分途钩连战国以下的各类文体,引论纷呈,枝繁叶茂,形成“因实递进,以次条缕”的系统文体源流。这种系统建构在广度和深度的融合方面特别突出,如谓文体源起《诗》《书》,并非守持“宗经”的观念建构,而是因为“书契既兴,文字觕成,吉金贞卜,始见殷商,虞夏书迹虽不可见,然孔子删《书》,起于《尧典》,……文章之原,必稽于此。《书》本史也,而载‘赓飏之词,其流为《诗》三百篇”。以下再分论“屈宋相继,衍为辞赋,始独占文坛”2的赋学一脉。这里隐含了金石学和书画文字学、现代文体学的知识谱系,故在具体考察赋时能在诸种文体间出入综观,如此论述,不仅具有章学诚“文体备于战国”3的宏观视野,而且能较其“一子之学”的赋论更加细密深邃。张舜徽对此大加赞赏,认为该书“条述文章流别,备论各类体例,斟酌古今,语皆有本,尤非贯穿群籍,洞明著作原委者不能为”4。“各类条例”兼取“古今”,自是一种学术取径的广度;“贯穿”“洞明”则无疑指一种具有深度的系统性。如果仅论赋学融合广度和深度的系统性,姚华应当属于民国学者的第一列人物,其《论文后编》论赋的立体视角是可以比肩于章太炎《国故论衡》、刘师培《论文杂记》和《文说》的,所以他论赋的源起,赋与诗的关系皆能体现出一种“新的文学史观”。这种治学恰恰昭示了晚近转型时期吸收了“现代性”的治学观念,可为代表。按现代学术与传统学术的不同就在于“吸收了新的学术观念与方法”,在晚近新文化运动前夜,由西学中的“历史的眼光”“进化的观念”所影响的“学术系统化、体系化”,正是最明显的“新”学标志;姚华本有深厚的乾嘉小学功底,他1905年留学日本时特别提出要以“新知识真学理”攻错传统文化又建立起了广阔的学术视野和现代学术思维,所以他这一建立在深度和广度基础上的系统治学观念,与同代人章太炎、刘师培、王国维等的治学观念皆相近似,无疑体现了转型时期学者治学的“现代性”品格5。
其次,从学术价值上看,姚华客观研究而不失创作体悟所整合出来的价值判断与独特论断,具有赋学研究的方法论启示。姚华这一代民国学者大都因为受西学的冲击,能脱出传统经学的影响,而对研究对象持一种客观平等的态度;但同时又因为他们旧学功底深厚,研究不脱创作,两相整合而所得出的论断就具有“了解之同情”6而能胜义纷呈。就出脱经学的影响而言,大致以姚华和章太炎最为彻底,比之刘师培论赋强调“诗为赋源”和“咸出于骚”,其实更具有新学的品格。如他称“文章应时而生,体各有当”7,据此而评骘《诗》、赋及赋的子类、诗的体制特征,所谓“诗分为三:骚、赋、乐府,并成鼎足。然骚赋别行,而乐府独隶诗系”,便是完全脱出经学平视诸体的客观论断。但他论赋的唐前古赋取向,批评律赋“使肆者不得逞,而谨者亦可及”“其制益艰,其才弥局”是站在创作的角度而洞见律赋体制的利弊的,论文赋的“文质殊观”亦然。从主体的研究思维来看,创作给研究提供了一种标准,同时与客观研究两相整合,其所作出的价值判断和学术论断必然容易契合于文本的自足审美和文体的动态特征。这种既具客观研究这一现代学术观念,又具有创作体悟而冷暖自知的实践视野,应该是民国学人大都所共有的学术秉性。如章太炎称“小学亡而赋不作”1、刘师培称“自唐人以律赋取士,而赋体日卑”2,黄侃“用便程式,命题贵巧”“或谓赋至唐而遂绝”3,皆与姚华之说相桴鼓,有着近似的学术判断理路。只是民国著名学者中以姚华最好文艺创作,具有融涵金石书画文字之学的艺术学视野,以此来考察他据“体各有当”论赋源取宋玉一脉的大赋为主而不嫌“动累篇赋”、论文体源起不主宗经却能看到“文章之原,必稽于《诗》《书》”,论文体变迁中,赋体在宋玉手中生成“别子为祖”的大宗、论“自曲之興”而“骚赋”等“无当于史材”4,等等,实多蕴含着独特而精彩的见解。大抵白话文运动以后破旧推新、古不如今等“革新”观念成为学界主流,逐渐致使学者视传统文学为纯粹的客观研究对象,而去古代文学的语境渐远,于是朱光潜“不通一艺莫谈艺”5的体认警戒渐次淡化,当代学者看待一切古代文学材料大都以客观的史料学价值平视之,由于缺少传统文学理论服务于实践的践行品格,于是既不能作蕴含实践体悟性质的价值判断,亦少了很多切近古代文学动态特征的学理论断。如论章太炎为赋史上的“最后一位作者”6、评价姚华等宗唐前古赋为“保守”或“复古”7,便或多或少囿于白话文运动以来所谓的“革新”观念。两相映照,可以见出姚华及民国学人论赋所带给今人的方法论启示。
不仅如此,姚华赋学还具有重新认知赋学而正本清源的价值,有利于建构民族独立的学术话语体系。我们知道,传统赋学受执于宗经观念和科举制度的实用性倾向,历来在三个方面最具争论:诗源说,骚赋关系,古律关系。姚华的治学观念因为注重西学的系统性和客观研究取向而能完全出脱经学,亦不失创作的体悟;但同时他与章太炎一样并不因为西来的文学观去削足适履,而是坚持在述学中守持一种中国文学的自性,他们可能是基于西学东渐语境的民族主义而作如是观,今人或谓恋旧,实际上以今天的观点来看,这种在转型时期的借鉴和守持恰恰有利于建构起民族独立的学术话语体系。我们看他在这历代最具争论的这三方面都有精彩的论断,能跳出传统旧说又具有现代学术视野下的总结性。他在赋源论上能跳出班固“赋者,古诗之流也”的经学建构,提出以宋赋为主而远绍旁收的三源说,形成为今人所击赏的“屈辞滥觞,宋赋定体,直开汉赋为然”8体制演变叙事,正本清源而契合赋以手法立体的语用事实;同时还能以系统的“文质观”来论其流变,却又不废《诗》《书》在“文章之原,必稽于此”上的作用,显得系统、客观而通达。他别出诗骚关系,认定“楚隔中原,未亲风雅”,即见王逸以来的“依经立义”之说是一种人为依附;同时认定“楚辞高古”“体若多纷”使得后代诸体“援以自益”,所以只能作为赋之“滥觞”,正是从他论“文体变迁,纯出自然,古人偶创,后争效之,众体竞作,群目乃生,古虽不别,今实居要”9的文体原则推导出来的,这背后完全是一种现代的文学发展史观,符合文体的实际发展。他径取古赋以大赋为主而直陈律赋之弊,虽承自前人但其中所蕴含的治学观念已然不同,主要是基于创作实践和客观研究相整合后的文體认知。今人长久以来都接受了西方文学的审美抒情内核说,而多以之为评价标准论历代赋之高下,实际上这颇不符合文章学“体各有当”的传统;姚华称《诗》“无长言”“由其简也”,而赋有“动累篇幅,循其繁也”,取古赋而以大赋为主,如果对照章太炎断大赋“奥博翔实,极赋家之能事”,而未尝“动人哀乐”10,并以此为据明确反对鲁迅所借用的西方文学定义11,则不难见出这些论断颇有正本清源的功能,蕴含着丰富的本土学术话语,有利于建构民族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
最后我们也必须要指出,姚华赋学具有丰富的赋学史料价值,是民国赋学史乃至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姚华赋论连并其十六篇赋作,与同代章太炎、刘师培、黄侃、刘咸炘等学者的赋学一样,都是民国赋学的重要内容。民国赋学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这是由晚近的特殊语境所决定的,晚近西学东渐决定了前沿学人新旧观念的冲突和激荡,他们的赋学既具有传统的总结性,又具有新学品质,其中所反映的学术观念和学术转型态势更值得关注,对今天的学术研究来说不无禆益。学界近年来在关注民国赋学时虽给予了姚华一定的位置,但或自文献的视角作资料的钩沉和叙述,或自革命文学的立场视之为“保守”;实际上姚华在同代学人中最注重文艺创作,出脱经学最彻底,论赋学所具有的广阔视野和系统观念亦具典型性,其赋学多有经典话语而具独特识断,特别是他与同代民国学人的赋学中所蕴含的现代学术意涵,正是民国赋学最精华的部分,而值得我们重加观照。
Abstract:Yao Hua's theory of Fu School has a three-dimensional perspective of western vision, practical creation and art vision, which is worthy of explor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ty” in the academic transformation period. It's content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discussion of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Fu sty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u and other styles, and the orientation of Fu. When it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 which has some modern meaning changes in the original mean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extual research, the concept of domin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style and the practice of creation,etc. Yao Hua's research had the systematic on the integration of depth and breadth, and the most thorough departure from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which showed the “Modernity” on an academic concept of absorbing western academics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Yao Hua's valuable judgment and unique arguments, which had been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literary creation and his objective research are of great value in constructing an ethnically independent discourse system of Fu studies and enlightening modern Fu studies
Key words:Yao Hua;Fu studie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radition;Modernity
责任编辑:黄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