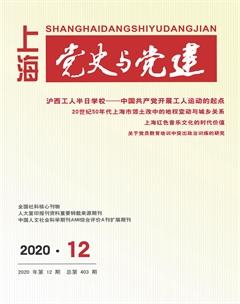沪西工人半日学校
邵雍
[摘 要]沪西工人半日学校是中共党史上第一所工人学校。从1920年秋至1925年春,校名多有变化,包括上海第一工人补习学校、工人补习学校、工人识字班和工人夜校补习班。具体经办人先后为李启汉、陈为人、嵇直、孙良惠与刘华等,邓中夏、李立三、项英等人也参与过该校的实际教学。该校是党开展工人运动的起点,是1925年二月罢工的策源地。在党的领导下,办校人员经过艰苦摸索,成功找到了联系、发动工人阶级的具体途径,使党牢牢扎根在工人群众之中。沪西工人运动最终发展成为席卷全国震惊世界的五卅运动,从而为全国工运的开展提供了上海方案。
[关键词]沪西小沙渡;工人半日学校;中国共产党;李启汉;孙良惠;刘华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0)12-0003-08
沪西小沙渡工人半日学校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工人运动的起点,但与外国语学社、平民女校的研究相比,成果较少。就目力所及,迄今为止只有沈以行等著《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三章第一節及第六章第四节有所论述,以及《强大师资打造的沪西工人半日学校》(作者华校生,《党史信息报》2020年8月5日)一文。本文所讨论的沪西工人半日学校是个泛指的概念,包括上海第一工人补习学校、工人补习学校、工人识字班和工人夜校补习班,时间从1920年秋至1925年春。
一、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沪西工人半日学校与上海第一工人补习学校
小沙渡地处上海西郊,是日本资本家开办的纱厂最集中地区,这里有日资纱厂十几家,雇用中国工人2万多人,是上海纺纱工人最多的地方之一。[1]日资纱厂的工人工资低,工时长,还时常遭到日本监工的打骂欺压。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不久,就派李启汉来这里从事工人运动。
李启汉,湖南江华人,上海外国语学社社员,最早的团员,后转为党员。1920年8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创办了专门向工人进行马列主义宣传的通俗刊物《劳动界》周刊,并选派李启汉去沪西小沙渡筹办工人学校,组织纺纱工会。李启汉听说沪西小沙渡地区的数万纱厂工人曾在1919年的“六三”大罢工中大显威风,如将马克思主义带到他们中间,必将如虎添翼。他感到劳动人民没有文化,很难接受马克思主义。因此,他沿用上海各校学生举办平民教育的经验,于1920年秋在小沙渡槟榔路北锦绣里3号(今安远路62弄178—180号),开办了一所工人半日学校。当时李启汉借了日资内外棉九厂三间两层砖木工房,将楼下改为教室,里面只有黑板与二十来张没有油漆过的白木桌凳,夜间还有一盏油灯照明上课,教学设备极为简陋。楼上则作为办公室和夜间教师的宿舍。而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创办的全国第一所工人学校”[2]。
邓中夏在所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说:“组织工人工作是从一九二一年开始。”其立论根据是“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北京党部开始在长辛店开办劳动补习学校……共产党上海党部在一九二一年亦开始做组织工作,首先在沪西小沙渡。此地是上海纱厂集中区域之一。着手也是开办劳动补习学校。”[3]他的结论是“长辛店和小沙渡两地都是中国共产党最初做职工运动的起点”[4]。大量资料显示,中国共产党在各地的早期组织地位并不相同,上海是发起组,北京是支部;筹办劳动补习学校,上海是1920年秋,北京是1920年冬;实际开办时间,上海是1920年秋,北京是1921年元旦。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正式成立伊始,就着手组织工人的工作。小沙渡劳动补习学校开办时间早于长辛店,因此,小沙渡才是中国共产党最初做工人运动的起点。
张国焘回忆:“一九二○年,各地中共小组成立后,即着手在工人群众中展开活动。上海工运工作一直是由李启汉负责的。”[5]而在小沙渡协助李启汉办工人半日学校的,还有上海外国语学社学员陈为人、雷晋笙、严信民等。补习学校选用《劳动界》等作为课本教材。陈为人先后在该刊上发表了《我底劳动力哪里去了》《今日劳工的责任》《劳工要有两种心》《天冷与劳工》《上海工人游艺会成立大会记》《劳工歌》等文章和诗歌,揭露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在《我们底劳动力哪里去了》一文中说,“那般资本家,什么老爷们、太太们,小姐们一点没有劳动,他们偏偏有那丰富的衣食,高大的房子,美丽的器具使用”,而我们做工的人,“倒反不及那般坐吃的资本家有那样好的衣穿,好的吃食,好的房子住,好的器具使用,我们有时还连一碗糟米饭都没有吃”。最后他指出,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我们底劳动力,都被那般资本家强盗去了:那好的衣,好的食,都是我们用劳力去换来的,却被资本家劫去了”。[6]陈为人在《今日劳工的责任》一文中呼吁劳苦工人团结起来,共同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兄弟们呀!我们要减轻我们的劳苦,要增高我们的生活,要脱离资本家的奴隶,要得到那‘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的乐境,这是我们自己的责任,要我们自己努力去做呢!弟兄们啊!我们的责任既是这样大,我们为什么还要饮恨吞声的服从那资本家,不去实行社会主义,不去打破那资本家的阶级?”[7]《劳工要有两种心》也指出:“我们不要以为受苦是我们的命运。若说到命运,我们何以都是一样命运呢?天天起来都是不能转运吗?单独资本家都是好命吗?要知道我们这样的受苦,都是资本家陷害我们的,虐待我们的。资本家要我们做值一元的工,他只给我们一角,其余九角,他都得了去了。”[8]上述这些为《劳动界》周刊写的稿件也就是陈为人在半日学校上课的内容。
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陈望道也常深入到沪西小沙渡路(今西康路)一带工人集中居住地区,在工人补习夜校即半日学校上课,把政治内容结合到教学中去,重点在于启发工人的阶级意识。陈望道的讲课内容也是同一时期他发表在《劳动界》的文章要点。陈望道批判了当时社会的“真理”是“做的饿,逛的阔,忙的出力当下贱,闲的游荡作高尚”[9]。“越不做工的,穿的衣服越好,吃的东西越讲究,住的房子越阔气。越不做工的,穿的衣服越一箱一箱地堆着烂,吃的东西越一碗一碗地有得倒,住的房子越一间一间地闲着做蜘蛛窠、蚊虫府。做工的做煞,还是个得不到他们闲着抛了的一点剩余。”[10]而工人“今天做,今天才有饭吃:明天闲,明天就没有粥喝……每天做十四五点钟工,日里忙煞,夜间倦煞,就使有家庭,也没有家庭的乐趣”[11]。
因为缺乏经验,事前没有做好宣传动员工作,尽管学校设在工人区,但报名上学的工人却寥寥无几;加上是义务教学,不收分文,经费困难,到十二月初天气寒冷,更少有人来读书,只好提前放假。
李启汉并没有因此气绥,为了便于和工人交谈,他下苦功学会了上海话,并设法打入青帮组织,利用帮会关系结交工人。体察到工人做工时间长,工余来读书十分疲劳,他决定适当开展文娱活动,用以吸引更多工人来上学。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同意李启汉把工人半日学校暂时改为上海工人游艺会。经过多方联络,1920年12月19日下午,工人游艺会借白克路207号上海公学开成立大会,到会二百余人。[12]李启汉担任大会主席,报告开会宗旨及进行方针。他说:我们工人“从前只是各人苦着,饿着,我们想要免去这些困苦,就要大家高高兴兴的联合起来,讨论办法”。他强调工人不仅要得到一些娱乐,对于“什么金钱万能,劳工无能,我们都要改革,打破!”[13]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杨明斋、沈玄庐等也以来宾身份在会上发表讲演。杨明斋鼓励工人“输入知识”,“活泼精神,强健精神”。[14]沈玄庐强调劳工组织团体的重要性,指出:“工人是替世界上谋幸福的人……这样神圣不可侵犯的工人,竟被资本家压迫了!真是可恼!我们此时应当要去抵抗他,我们此时就应要有团体。”“从前工人没有自悟的原因,都是为着迷信所误……我们赶快打破他!”[15]
工人游艺会寓教于乐的策略起到了一些作用。1921年春半日学校重新开学,报名上学的工人有所增加。日商内外棉五厂青工黄桂生,当时只有17岁。他听人说锦绣里办了一个新学堂义务教工人学习,觉得新鲜,便在一个厂休日,约了几个小兄弟一道去锦绣里打探。走到学校门口,看见几个穷哥儿坐在里面听留声机放京戏唱片。李启汉老师笑着招呼黄桂生等人进屋,逐一询问黄桂生他们的姓名和生活情况,接着拿出一只足球,请大家到外面荒场踢球。回教室休息时,有的工人提出每天做工12小时,白天没功夫读书。李启汉说,白天没有功夫读书,就晚上来读,如果做夜班,就在下午读,只要大家愿意读,什么时候来都可以。学校可以多开几个班次。他还鼓励大家说,工人要尊重自己,力求进步,不要因为社会上一般势利眼看不起工人,就灰心丧气,一定要人穷志不穷。黄桂生就这样进了工人夜校,后来成为罢工的积极参加者。[16]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半日学校的学生增加到20多人。在此基础上,李启汉帮助工人组织沪西纺纱工会,并推举学习最认真、热心为大家办事的日商同兴纱厂工人孙良惠为负责人。孙良惠是听了李启汉的课后才开始懂得工人受穷苦的根源,积极参加革命斗争的。他曾代表沪西纺纱工会,几次参加纪念五一节的筹备活动,散发传单,并到浦东日华纱厂声援罢工工人。工人半日学校被租界巡捕房查封后,他仍常到李启汉的住处请教。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作出的第一个决议就是开展工人运动,明确将此作为党的首要任务。8月,党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以后,就把沪西工人半日学校扩大为上海第一工人补习学校。当时报名的有200多人(其中女生20余人),经常到校上课的约有30余人,分为两班。日班工人上课时间是19时至21时;夜班工人的上课时间是7时至9时。教授内容有政治常识和工会组织等一些有关问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李启汉、李震瀛、包惠僧等轮流去教课,李震瀛担任校长。[17]帝国主义势力对此极为仇视,1921年秋,公共租界巡捕房查封了该校。
李启汉因形势需要,离开此地去支援香港海员罢工,又领导了浦东日本纱厂、上海邮局等工人罢工。1922年6月,租界巡捕房用“煽动罢工”“破坏治安”等罪名,逮捕了李启汉。“会审公堂”判他3个月徒刑,期满后逐出租界;同时不准劳动组合书记部编的《劳动周刊》出版。7月间,劳动组合书记部也被查封。7月18日,上海第一工人补习学校被迫停办。
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续办的沪西工人补习学校
1922年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书记张秋人委派嵇直去小沙渡续办工人补习学校。嵇直在劳勃生路(现名长寿路)一家安徽人开的木材行楼上租了一间房子。他以“代书书信,不受分文”、个别访问等方式,办起了工人补习班,一开始只有4个学员。嵇直再三向他们说,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我们劳动人民学起来没有味道。他进行教学的是大家在现实生活中看得见,听得到,又能用得着,而且与自己皆有切身利害关系的“活”教材,大部分是从《新青年》《向导》和《劳动周刊》中找来的,有时也就地取材。“安源煤矿工人俱乐部”“香港海员工人大罢工”“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等等都是讲课的重要题目。嵇直每星期讲3课,在每节课中,凡说到地名时,必定打开地图,指出方位,使人一目了然。而有些词句(如“为反对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而斗争”“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啊”等),除扼要解释清楚外,还写在纸上,教学员抄写。这样,工人每上一课都能增添一些有关工人阶级的新知识,认识一些生字或知道一些地理常识,对此大家都尚满意。[18]
后来鉴于来补习的工友逐渐增多,经组织同意,嵇直吸收了徐玮来分工合作;凡住在劳勃生路以北和宜昌路的,就到徐玮住处的补习班上课;而住在劳勃生路以南槟榔路(现名安远路)和海防路的,仍到嵇直住处上课。此时,孙良惠听说嵇直在工人补习班上的课与李启汉曾经对他讲的道理差不多,特地前来探望,并乘机打听李启汉的消息。1922年初冬以后,孙良惠常来工人补习班,他上课时带头发言,用自己的体会和工人语言,帮助教师解释问题;有时还带着他的朋友们来听讲。后来孙、徐被吸收入团,与嵇直一道组成了团支部。这两个补习班的共同缺点是工友们流动性太大,有时来得多,有时来得少。与学校有联系的人数比以前多了,但联系并不巩固,且仅限于男工。当时在小沙渡的一些工厂,发生过各种类型的劳资冲突的事件,但很快被压制下去,扩大不起来。[19]
1922至1923年全国工运潮期间,上海也举行了一系列罢工斗争,但因未能建立起强固的工人组织,共产党组织并没有在工人群众中扎下根。据1924年5月统计,上海只有党员47人(包括在党中央机关工作的党员),还是以学界为主要发展对象。上海地委向中央扩大执委会议报告说:“我们所作的工人运动是没有钻到里面去,只立在工人群众外面的,所以作几次失败几次,到现在还是等于零,这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的很大错误。”报告还认为我们的同志“作运动的经验原来很幼稚”,因此,“希望中央能在别处多调几个有经验的同志来”。在全国第一次工运高潮中成绩卓著的工运领袖安源的李立三和武汉的项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调来上海工作的。而安源工运的经验之一是从创办平民学校、职工夜校入手,条件成熟时,进而组织工人俱乐部。项英则是参与创建京汉铁路总工会的干将。中共上海地委当时强调困难,力争支援,称工运“到现在还是等于零”的说法实际上是有失偏颇的。仅仅从党领导的工人补习学校来考量,当时已不是只有沪西一所,而是在各区推开。很难讲各区办校人员全是“立在工人群眾外面的”。当然,与李启汉相比,嵇直、孙良惠等人“作运动的经验原来很幼稚”的。
1924年春,党组织决定在适当地点另找一所比较宽畅些的房子,把两个补习班合并成为“小沙渡沪西工人补习学校”,分日夜两班上课,以便工友学习,并在课余安排一些文艺活动。与此同时,分别在工厂里设法建立职工小组。于是,孙良惠在槟榔路小沙渡路口德昌里(今安远路278—280号)租下一套新建三间平房,两间作为日夜班课堂,一间作为文艺活动所。所需桌凳乐器,主要也是由孙良惠和几个热心的工友向左邻右舍、亲戚朋友临时借用,或从自己家里拿来。这样,来上课的人明显多了,并且又都不像从前到教员宿舍那么拘束。每天下课后还总有人留下来,或谈话,或下棋,或弄乐器。每当市团委要在本区内散发传单,或在什么地方集合参加什么运动,团支部总能带着一些工人去执行。[20]
据1924年初去补习学校学习的内外棉五厂工人姜维新回忆:“说是半日学校,其实我们上课只有两小时。教科书是学校发的,老师也不一定照课本讲,主要是进行阶级教育。一起读书的大约有几十个人。”[21]教书的有项英、孙良惠、邓中夏等,还有一些轮流执教的大学生。但是他回忆的校址和模样与嵇直讲的不一样,称:“学校在劳勃生路以南,东京路(今昌化路——引者注)以东。学校的房子是个矮楼房,上课在下面,办公在楼上。听说是孙良惠找的房子。”这个说法在《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得到采纳。但姜维新只是个普通学员,对校址的印象肯定不如具体经办人嵇直深刻;再者,姜维新所说“以后学校发展为俱乐部,来的人更多了。刘华来教了约一个月,即发生二月罢工”也有问题。俱乐部是1924年8月底成立的,9月间刘华就奉命到校工作了。从那时起到次年2月,足足有5个月。可见,“刘华来教了约一个月,即发生二月罢工”的说法明显有误。姜维新当时就学的补习班的地点很可能是嵇直在劳勃生路以南的住处。不过,嵇直只租借了该处楼上,楼下待考。
从1924年4月开始,中国共产党利用国民党左派或共产党员所掌握的学校课堂,逐渐在上海的沪西、沪东、浦东、吴淞、南市、闸北、虹口等处办成了7所职工夜校。[22]与项英同时调来上海加强工运的李立三除了亲自负责吴淞区职工夜校的教学,还每个星期轮流去各个职工夜校上课一次。他到沪西工人补习学校讲过“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等课。在李立三等人自编课本里有这样的内容:“上学校、念念书,农工不是生来粗。”“富人坐在家中吃鱼肉,农工劳苦作工喝薄粥,富人哈哈笑,农工个个哭,不分东西和南北,富人笑,穷人哭。”[23]
三、沪西工友俱乐部开办的工人识字班和工人夜校补习班
1924年5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工人运动新的任务,批判了二七大罢工以后党内出现的取消工人运动的倾向,决定加强党对工运的领导。会后,中共中央工会运动委员会书记邓中夏仍在上海负责领导工人运动。他召集有关同志了解情况,分析上海工人罢工斗争很少获胜的原因,要求上海党组织采取措施,加强对工人群众的宣传教育、大力发展工人党员和牢固建立党的基层组织,以实现党对工人运动的有力领导,计划在沪西工人补习学校的基础上筹建沪西工友俱乐部。
同年夏天,项英对嵇直等人谈了在学校现有的基础上成立“小沙渡沪西工友俱乐部”的设想。8月31日举行俱乐部成立大会时,项英、刘华、顾秀、江元清等30余人到会,公举孙良惠为主任,嵇直为秘书,陶静轩为交际委员。孙良惠宣布沪西工友俱乐部的宗旨为“联络感情,交换知识,相互扶助,共谋幸福”[24],并请项英写成横幅,张贴在俱乐部的中堂。随即举行第一次委员会,议定:(一)征求俱乐会员,会员资格暂定经过两人介绍并每月缴纳会费一角;规定会员互相保密,不对外公开会员姓名。(二)开办工人识字班,工人夜校补习班,入学的人不限定会员,凡是工人均可入学,一律不收学费;聘请刘华、顾秀、江元清等担任教员,均为义务,并指定干事、失业工友刘贯之常住俱乐部。接着进行募捐,作为俱乐部的经费。[25]
俱乐部成立不久,嵇直調往外地,党组织派刘华接任秘书,分管俱乐部的宣传和组织工作。1923年11月入党的刘华,时任上海大学生会执行委员、上海大学平民义务学校执行委员。他白天到内外棉第七厂(原上棉二厂)当勤杂工,借勤杂工可以到处流动的条件,广泛接触工人,把各处工人如何反抗资本家的英勇斗争事迹讲给大家听。他还编写了一些鼓词和顺口溜,用这种工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来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与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反动本质。有一首鼓词写道:“兄弟姐妹们,睁眼望望真,帝国主义资本家,不做工来专门剥削人,拿我们当牛马,做活儿养他们。青年工友们,我们要翻身,齐心协力,打倒他们,工厂归工人!”[26]晚上,刘华和邓中夏等人在沪西工友俱乐部同工人们谈心、上课。他在工人夜校补习班的讲课入耳中听,讲到工人受剥削压迫时,许多工人流出了眼泪。刘华向大家介绍安源工人斗争的先进经验时说:“我们纺的棉纱,一根根拿在手里,一拉就断,要是拧成一股粗绳,任他大力士也拉不断。我们工人就要团结起来,拧成一股又粗又长的绳索。这样,就能捆住帝国主义、资本家的手脚,解放我们自己。”“我们眼前的任务,就是要象安源那样,把工人都组织起来,加入俱乐部,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希望你们尽力团结各厂工友,准备斗争!”[27]在刘华的悉心帮助教育下,许多工人很快就参加了俱乐部的活动,有些还成为骨干力量。
邓中夏也常到沪西工友俱乐部的工人识字班与补习班讲课,讲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讲“剥削”一课时,有个工人不解地问:“工人做工,老板给工钱,从来就是这样,工钱和剥削有什么关系?”邓中夏严肃地说:“工钱,不是老板‘给工人的,是工人出卖劳动力得来的,是工人劳动创造出来的财富中的一小部分。”他扳起手指头,给工人算起他们劳动创造出来的大部分财富哪里去了:“比方说,一个工人一天干活十二个小时,纺出十斤纱。按照市面价格,十斤纱可以卖十块钱。除掉纺十斤纱花费的成本、机器折旧等六块钱外,剩下的四块钱,就是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工人只能拿到两角钱,剩下的三块八,全被老板装进腰包,这就叫剥削。”工人们听后恍然大悟。[28]学员姜维新回忆说:“俱乐部成立后,形式上仍上课,但我们一些骨干分子每天忙着开会、宣传,已不能安心听课。组织上常把一些通俗宣传品(包括画刊)和《向导》一起发给我们,这样,我们向工人宣传就方便多了。”[29]
小沙渡沪西工友俱乐部成立后,工人踊跃要求参加识字班,因房子太小,虽然按一小时一班分成好几个班,仍难满足工人的需要。补习班也同样应付不暇,因为补习班只开两班,乘着识字班空出的时间上课,所以更觉紧张。担任教学的几位同志,每天都是忙得吃饭时间都不易空出来。邓中夏就找在沪西工友俱乐部做具体工作的共产党员个别谈话,勉励他们;又在《中国青年》第十三期上发表《胜利》一诗:“哪有斩不除的荆棘?哪有打不死的豺虎?哪有推不翻的山岳?你只须奋斗着!猛勇的奋斗着,持续着!永远的持续着。胜利就是你的了!胜利就是你的了!”项英则建议改变工作方法,一方面继续识字班、补习班,一方面开办讲演会,宣讲故事、时事以及有关工人利益等事项。由于讲演会地点随时决定,容纳人数较多,内容可以多种多样,很受工人欢迎,其功效超过了识字班。
就这样,沪西工友俱乐部成了工人读书、听讲,接受阶级教育的大课堂。工人们把接受党的教育称之为“听道理”,要求参加俱乐部的一天比一天增多。孙良惠首先在同兴纱厂组织几个小组,不到40天,该厂工人秘密加入俱乐部的就有300多人。内外棉三厂、四厂、九厂、十五厂和日华纱厂等日本纱厂也陆续组成了俱乐部小组。到1924年年底统计,有19个纱厂建立了俱乐部的秘密组织,俱乐部会员将近两千人。内外棉七厂工人顾正红、内外棉十五厂工友陶静轩、内外棉五厂工友王有福、同兴纱厂工友郭尘侠等,后来成为上海工人运动中的中坚分子。
沪西工友俱乐部在上海工人运动历史上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共产党的组织是从这个俱乐部开始打进产业工人群众中去的。党在同兴纱厂以及内外棉三厂、五厂中都是在工友俱乐部会员中选择和培养积极分子,然后发展入党,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的。这样,党在沪西工人中扎下了根,“使沪西小沙渡成为五卅时期上海工人运动的策源地”[30]。当代学者李良明认为,项英“在沪西平民学校和工友俱乐部的工作,直接为上海二月罢工奠定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31]。1925年,作为五卅运动预演的二月罢工就是党依托沪西工友俱乐部开展起来的,沪西日本纱厂2万余工人参加。同年5月15日,共产党员顾正红因带头反对日本资本家关厂威胁被当场枪杀,由此引发的持续抗争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索。
四、研究五卅运动一定要从沪西工人半日补习学校讲起
邓中夏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对小沙渡评价偏低,宣称“其影响当然不及长辛店,但在中国职工运动运动史上仍有它的意义”[32]。这是可以商榷的。要知道五卅运动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和指挥的一场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席卷全國并且具有世界影响的反帝爱国运动。包括长辛店、安源在内的全国其他地方的罢工都没有搞成如此大的规模。这是因为:第一,上海工人阶级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领头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是一样。其次,中国共产党诞生后长期驻在上海,其对上海工运的领导最为直接。第三,“万事开头难”,各地情况不同,在上海开展工运有不同于长辛店、安源的环境。经过初步探索,上海找到了党联系、发动工人阶级的具体门路:工人补习学校——工人俱乐部(工会)——在工人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而工人补习学校是整个工作链条中的第一环,“否则,这种学校就无需存在,可予以解散或改组”[33]。研究五卅运动,一定要从沪西工人半日补习学校讲起。
从1920年秋至1925年春,沪西工人半日学校的名称多有变化,包括上海第一工人补习学校、工人补习学校、工人识字班和工人夜校补习班。开办的组织分别为共产党、青年团以及沪西工友俱乐部,其中的关键人物有李启汉、陈为人、嵇直、孙良惠、刘华,邓中夏、李立三、项英等人也参与过该校的实际教学。虽然校名及具体经办人多有变化,但中国共产党一直领导着该校。因为青年团以及沪西工友俱乐部是党直接领导的,李启汉、陈为人、嵇直、孙良惠、刘华、邓中夏、李立三、项英都是共产党人,有的还是党的高级干部。从这个意义上说,该校的师资是很强大的。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办工人补习学校本身并不是目的,目的是要以此为场所与媒介,宣传革命思想,教育工人,“提高工人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成立工会的必要”[34]。因此,在工人补习学校进行的宣传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宣传,它必须因地制宜,结合实际与工人的切身问题,从身边事、眼前事、伤心事说起,注意对日常生活中各种实际问题的解释,尽量避免过于艰深或过于空泛。过于艰深,超过工人的文化水平,则学员难以理解;过于空泛,不能使他们感觉切要。两者同样会浪费宝贵的教学资源,达不到预设的教学效果。与北京长辛店的工人补习学校[35]一样,沪西工人半日补习学校本着宣传本位、组织优先、任务中心三大原则,日常教学也是围绕着“工人为什么穷”“怎样不再穷”展开的,与工人群众的生活状况与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无论是教本还是现场讲解都是度身定制的,文字通俗,语言生动,引人入胜。该校启发式的互动教学融知识性、趣味性、思想性于一体,贯彻了反压迫、反剥削、求解放的斗争逻辑,有利于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与使命感,具有起点低、立意高、易接受等特点,工人群众听得进、记得住、用得上。其经验具有适用性、可操作性,便于复制推广,为民主革命时期的工人运动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上海方案。
总之,小沙渡沪西工人半日补习学校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工人运动的起点。在纪念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重新审视中国共产党最初开展工人运动走过的路,是很有教益的。
参考文献
[1][33][34][3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50.7.7.14—18.
[2]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创立之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148.
[3][4][30]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14—17.17.17.
[5]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168.
[6]我们底劳动力哪里去了[N].劳动界第14册,1920-11-14.
[7]今日劳工的责任[N].劳动界第15册,1920-11-21.
[8]勞工要有两种心[N].劳动界第18册,1920-12-12.
[9]真理底神[N].劳动界第9册,1920-10-10.
[10][11]平安[N].劳动界第2册,1920-08-22.
[12]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日报(1920-12-20)[A].上海市档案馆,U1-1-1128.
[13]上海工人游艺会成立大会记[N].劳动界第20册,1920-12-26.
[14]工人游艺会的益处[N].劳动界第20册,1920-12-26.
[15]劳工组织团体的重要[N].劳动界第20册,1920-12-26.
[16]姜沛南.五卅运动前后沪西工人的革命斗争[M]//文史资料选辑:1978年第二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2—3.
[17]“一大”前后: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55.
[18][19][20][21][24][25][29]五卅运动史料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283.284—286.287.294.276.288—289.294—295.
[22]沈以行,等.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卷[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170.
[23][30]唐纯良.李立三全传[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67.69.
[26]五卅运动编写组.五卅运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12—13.
[27]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七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61—62.
[28]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三十五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25—26.
[31]李良明.项英评传[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31.
本文系上海市哲社规划“党的诞生地史料挖掘与建党精神研究”专项“历史视野中的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研究”(2019ZJD0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贾 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