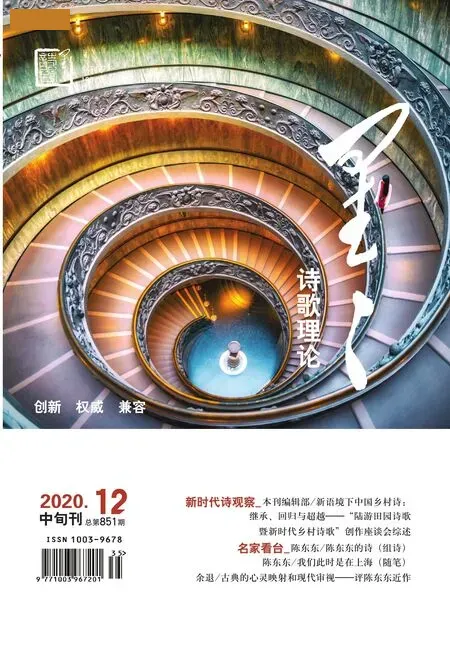“征文体”观点摘要
南 鸥 宗 城 白瀚水 苏美晴 阿 剑 吴 辰 周水寿 周 航
南鸥(诗人,诗歌评论家):直至今日,我从未参加过一次诗歌赛事,但是我对所谓的“征稿体”的创作是理解的,是赞同的。其实,所谓的“征稿体”古今中外都有之,只是近年在我国诗歌现场比较普遍,从去年开始在诗歌现场大有燎原之势。据经常参加“征稿体”赛事的朋友们介绍,他们建有专门的微信群,经常分享诗歌赛事的消息,彼此交流参赛获奖的心得,并有向专业化和集群化发展的趋势。从主办方来说,为了打造自己的文化品牌,借用诗歌这种大家喜闻乐见的文学样式来注入文化内涵,浇铸灵魂内核,以此提升本地区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充分发挥诗歌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灵魂作用,既弘扬了传统文化,又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当然是大好的事情。从积极参赛的诗歌写作者来说,如果严肃点说,是他的权利;创作上说,也可以得到一定的锻炼;从世俗生活意义上说,奖金可以弥补一下生活上的开销,又可以赢得一些关注,或者对于职称和工作调动等等世俗的诉求,都是无可厚非的。从文化的生态上说,这是一个多元的时代,多元是我们时代的历史趋势与总体特征,每位诗歌写作者的写作都应该受到应有的尊重。参赛者写什么,怎么写?完全是他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诗人创作出人文精神与艺术品性完美统一的作品,是每一位诗写者的共同追求。客观地说,“征稿体”在创作中确实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并不是说“征稿体”就不可能写出优秀的作品,这恰恰是对作者的认知经验、艺术表现力的一种考量。而“征稿体”是否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完全取决于作者所选择的视角、诗意的开掘、语言的艺术表现力等方面,并不是由所谓的“征稿体”这样的文本类别所决定。
宗城(青年评论家):征文体诗歌古已有之。李白、韩愈等大诗人都写过征文体,用以换取高额润笔费或者仕途便利。为什么现在它成了一个问题?其实,不是征文体这个文体本身不好,而是当征文体泛滥,成为诗坛的一股流行风气时,征文体造就的内容空洞、阿谀奉承之作泛滥,也就成了不可回避的问题。征文体诗歌泛滥,助长了诗人投其所好的风气。诗人为了拿奖,必然会揣摩主办方的用意,这样的诗歌美则美矣,终究改不了拍马屁的嫌疑,这个嫌疑就决定了诗歌不纯、不真,在意境上落了下品。写作者在平常的训练时会告诫自己:要爱惜自己的笔墨,学会拒绝。拒绝什么?就是拒绝会伤害你品性、磨损你文字质感的任务。固然,这是一种理想状态,人世间大部分旅人,为了生计,都难免弯腰乞讨几回,但切忌把弯腰作为常态,不要为了金钱,就丢失了自己对文字的要求,否则久而久之,你会失去自己曾经敢于飞翔的能力和勇气。一个诗人能走多远,看的不只是他的技巧,还有他这个人的心性。伟大的诗人,往往拥有一颗敢于挑战陈旧语言、打破常规的诗心。虽说征文体诗歌它本身是合法合理的,但如果它泛滥,成了文化生态里我们无法忽略的那臃肿的存在,我们就会发现大量陈词滥调占据了诗坛,诗人们交出的作品变成一只只温顺的宠物,它们貌美、娇羞,就是没有一颗勇敢的心。当一种存在泛滥成陈词滥调,批评家就理应指出问题,而不是视而不见,和和气气地加入一场大合唱。而对诗人来说,既然诗歌本身就是反抗陈词滥调的艺术,那么诗人也肩负有责任,创作出新鲜的语言,保有诚挚与勇气,而不只精明世故,成为物质所驯服的仆役。
白瀚水(诗人):我是一个没有发表过什么作品的基层作者,谈到征文,我想这可能也是很多征文作者写征文,以及征文体形成的原因——为了活着,作者的尊严被暂时放到了一旁,词语变得澎湃激昂,没什么主动的情感,只有对征文的敬业和词语上的宣泄。
据我所知,我不是个例。写征文的人大多都很苦,有些人甚至以此为生。所以当征文体这件事情被拿出来,作为一种反文学的文本进行批判时,我觉得我很惭愧。我没有坚持一个作者的本心,在征文写作中写了很多有违内心的文字,但是同样,我也是征文体的俘虏,是被束缚的人。也是因为,我需要活着。如果不提文学,只讲生活的话,征文体是很多底层作者的出路,是普通作者得以挣扎于文学边缘的理由。当如我一样的作者,在已经基本放弃了文学理想以后,如果转战征文,既能得有些文字的恩惠,也能继续坚持写作,也不失为一种特殊的对文学的坚持。虽然在大多数征文作者眼里,征文并不是文学,而是和广告语、宣传语类似的语言表达形式,如果非要把征文归类到文学,其本身的存在意义可以忽略不计。至少目前,这样的情况不可能得到根本扭转。如果想彻底摆脱征文体,那么现在最可能实现的办法就是彻底取缔征文,让文学完全回归刊物,但也有可能因此完全堵死大部分基层作者快速的上升之路,使写作圈彻底固化为“名家的文学”或“世家的文学”。换句话说,征文体虽然可恶,却是寒门书生唯一的出口,雷同古时的应试,八股文之存在。
苏美晴(诗人):其实我是16年下半年才接触征文,写征文我还是一个新手。个人认为既然有征文,就应该有人参加。一个征文活动举办了,没人写,那主办方举办征文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写征文,我没觉得有什么可丢人的,相反,在写作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查阅资料,了解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我不是言辞夸大,因为我是一个残疾人,几乎很少出门,写征文满足了我对外面世界的好奇,有朋友问我写征文有什么窍门,其实我想说的是没什么窍门,跟高考一样,有时候比高考还难,竞争力很大。从时间与体力上来说,其实写征文很累,中奖率很低,但你如果能坚持下去,一定会有收获的。其次,你要先学会写好诗,才能写征文。你连诗歌都不会写,还写哪门子征文?所谓的征文体,它必须带有鲜明的个性,而不是纯诗的共性,要有鲜明的地域性。最后不要斤斤计较,写作本身才是最快乐的事情,要有初心。你要来参与,就要保持一种良好的心态,才能保持住对征文的一往情深。
阿剑(青年诗人):似乎各个专业从业者都有一种天然冲动,在自己头上笼罩一层高蹈而自由的荣光。我们当然知道并非如此。真正的诗者,大部分还须“为稻梁谋”,还须像对待一份职业与工作一样,被“征文”、被私人定制、“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这既是文艺的经济属性体现,也是诗者的社会属性所必须。就像《诗经》风雅颂三百余首,既有先祖颂歌,神鬼祭祀,也有贵族宴饮,更有渔猎婚恋等黎民之事。一个真正的诗歌时代是需要兼容并蓄的。更为重要的,如果我们抛弃个人的偏狭,站在一个基于大数据统计的视角来审视文艺创作,就会发现,只有更大的因数参与,更多的声音共振,才能形成时代的最强音。就像史铁生说,“我希望未来的写作是所有人的一期假日,原不必弄那么多技巧,几十亿种自由坦荡的声音是无论什么技巧也无法比拟的真实、深刻、新鲜。”那么,为什么不选择拥抱更开放的时代与世界,拥抱当下最汗水淋漓与满面尘土的现实呢?为什么不去写草原诗歌、边陲诗歌、少数民族诗歌、打工诗歌、草根诗歌、工业区诗歌、房地产诗歌、电商诗歌、新媒体诗歌呢?为什么不让征文体诗歌成为当下活泼泼写作新时代的一部分呢?我相信各种形式与力量的文化活动,会形成一种缓慢而深沉的力量,去芜存菁的力量,在众声喧哗之中,在纷繁复杂之中,最终会凸显出这个时代最敏感、最精致也最具灵魂的声音。
吴辰(诗人、青年评论家):提起“征文”,人们的态度总爱走两个极端:有人热衷于“征文”,甚至产生了“征文专业户”,凡“征”必有文,乃至将其作为文坛的投名状或者零花钱的提款机;有人一提起“征文”便一脸嫌弃,认为所谓“征文”只不过是利益交换、诗坛黑幕、投机野心的集合,那些“征文体”都是些速朽的垃圾。那么,文要不要“征”?
我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当然要征!“征”本身就是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诗歌的传统。两千多年前,周天子居庙堂之高而想要了解江湖之远,于是令诸侯献诗、王官采风,遂有《诗》三百。可以说,《诗经》里的篇什之所以能够保存到现在,与“征文”这一形式是分不开的。至于兰亭诸贤集当日之诗,昌黎先生平生擅为碑文,也未尝不可以视作是“征文”之筹。我认同征文,却不代表我认同“征文体”。征文而有“体”,本身即与征文的精神向悖。什么一旦成了“体”,自然难免固化,而征文本身即是一种向着当下和未来展开的文学活动,以“体”写出的征文显然已经难以呈现出时代的丰富和复杂,以陈迹去书写新篇,新的也便成为旧的了。尤其是诗歌,《诗经》以来的诗歌创作实践已经证明了诗是可以“征”,且有必要去“征”的,但是,却不曾有过某一种诗歌体例是专门为“征”所打造的。征文,尤其是征诗,本应该是个人体验与时代精神碰撞出的火花。诚然,在征文、征诗的具体实践中,有一些固定的书写路数能更引起评审专家们的兴趣,也由此产生了一些争议颇多甚至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乃至事故,但因此就去否定征文、征诗的意义,则未免有些因噎废食。而那些由于一两次征文、征诗不得而将这一文学组织形式全盘“黑幕化”的人,则需要多去读读鲁迅先生的著作了。
周水寿(青年学者):当我们谈论“征文体”诗歌,我们其实谈论的是场域性的诗歌活动,是在为当下的诗歌圈生态局部命名。征文比赛至多提供的是展示、比拼的擂台,而非诗意的参建要素;而诗歌文本的竞相迸发多半为景观化的生活图解。值得辩护的是,诗人应征的背后原因复杂,不是单面化的。于诗歌的发展而言好处也极为明显,那些极佳的文本会在大浪淘沙后面世,并因诗性的光辉获得更多的瞩目,这不单是对参赛者的肯定也是对某种审美标准的强化。“征文体”的流行是与当下传播手段的流体化、碎片化相互叠加而存在的。潮涌式的大小诗歌征文通知,暗合的恰恰是现代性中(特别是电子媒介时期)信息所要制造的“震惊”体验。在此之际,诗歌正以这种符合时代氛围的方式“刷存在感”,诗人们在以微信为代表的网络平台上频繁聚集,更是“征文体”诗歌存在的一种常态;二者有着相似的面孔。这两副面孔亦有着类似的表情,欢笑热闹的背后,是难以掩饰的焦虑(或为名利焦虑或为诗歌的处境焦虑)。尽管群聚下的诗人们找到了荫蔽的阴凉地,但是如何面对这个火热的时代,他们的“群聚”能带来何种新的诗学维度,这值得思考。或许文本的缺失,是征文举办的诱因,也是征文活动想替诗歌界掩饰的彷徨。某种程度上,“征文体”正以自身为媒介,架构着当下部分诗人与世界交流的方式,而这种方式是否妥帖,引起了大家的谈论——这是诗歌该有的自省。
周航(学者、评论家):对于“征文体”诗歌,我的看法是大可不必贬低,它的出现有其社会和时代的土壤,我们应该顺应和适应诗歌在不同时代的表现,肯定其中可能生发的积极性意义,而非只盯紧一些负面性因素不放。首先,“征文体”诗歌走出缘情传统,与社会发生了一次较为综合的接触与融合。简单地说,诗歌在现代传播媒体发达、社会各大元素高度交错与融合的当今,不再只是个人低吟和言志的单向表现或手段,而是体现出不同层次的模糊、杂糅和混血的特征。其次,“征文体”诗歌的论争,是精英和大众、雅与俗、出世与入世等二元矛盾认知的又一次相遇。存在的未必就一定合理,但存在过我们却无法抹掉,之所以存在必有其产生的土壤,不妨宽容待之,正确思之。正如我们不会冒然去全盘否定战争年代的墙头诗、枪杆诗一样。最后,“征文体”诗歌说到底是个体创作和公共空间的一次尝试性的接触。古有唱和雅事,有命题作诗之趣,其实与征文体均有相似之处。诗歌的个体性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公共性不巧联姻,甚至成为大众文化消费意义上的一股潮流,其盛况令人瞠目结舌!其间的确产生过一些负面性影响,但大可不必大惊小怪!诗歌以这种方式切入社会、生活、经济、新闻等领域,总比养在深闺无人识要好得多,总比被动地、无边地被边缘化好得多。况且,诗歌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进入社会公共空间,以这种形式重构一个新的诗歌公共空间,我们又何必去求全、何必去苛求完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