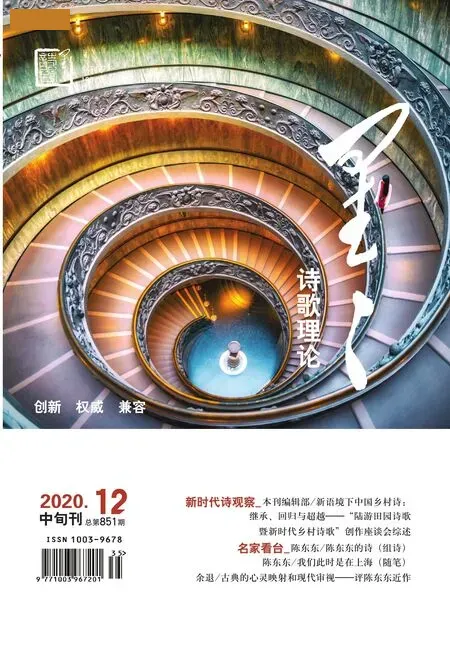在缺钙的世界里倔强突围
杨 克
项建新少年时已经崭露文才,写诗逾三十年。近年他诗学观念陡然转变,不再满足于曾经的抒情、唯美或辞藻,而是对创作拥有了更大抱负,他提出诗歌写作需要“大不同的视角,很高级的表述,白描式的行文,意料外的点题,很奇巧的隐喻,最终让隐喻引发折射,这样的诗歌是可以映射社会现实,洞穿历史未来的。在这样的认知下,我们可以自由地与宇宙、自然、人类、自我,开展对话”。真能达到如此境界的诗歌,可谓是哲学家、小说家和诗人的三位一体,近年来的作品恰好见证着他处于创作转折期、上升期的蜕变与爆发。特别是在专业写作者钙质流失的文化氛围中,他倔强地怀着逆庸常潮流而动的赤子之心、傲骨之气,努力于诗坛边缘野蛮生长,默默而准确地捕捉着时代脉搏,深挖着个体命运和文化本髓,确实可叹可嘉。
项建新天马行空、毫不谦逊的风格跟坊间其他温文敦厚、低吟浅唱的诗集大相径庭,提示着读者需要拥有如尼采所言“一口好牙和一个强健的胃”,才能消化这样毫不取悦传统与他人的精神食粮。对于人、世界和宇宙的描述,他拒绝墨守成规,“地球/是宇宙的一座牢狱/人的出生/是灵魂被判决入狱/先把灵魂锁入躯壳/再用地球引力束缚住/哪天刑满释放/ 人就死了/灵魂就再次获得自由”(《地球牢狱》),“人们都说/地狱在地下/天堂在天上/我却相信/天堂在地狱的下面/只有穿过了地狱/最终才能抵达天堂”(《地狱和天堂》),“流星/像精子般射向地球/就会有一颗卵子/在地球这个子宫里/经过撞击/孕育出一个新宿命”(《流星》),不羁跳脱的文字给予读者莫大的视觉和心灵冲击,而又跳脱了中国文化主要关注历史的窠臼,像当代西方文学那样,眼光投向外太空或未来,具有科幻色彩。复杂的生活阅历和学识结构,为他注入了多元的生命体验,能在更广阔的外部世界和更深邃的心灵空间两个维度自由延伸,而且他的思辨并非凌虚蹈空,而是根植于现世、肉身和理性,“醒着的人/穿过黑洞/就做起了梦//梦着的人/穿过黑洞/就过起了人生”(《黑洞》),“时间/是万物生长/刮动的风//时间/是推动宇宙运转的/力”(《时间》)。即便在思考终极问题时,他仍延续着华夏哲学的务实特质,交融着当代科学的文明意识,将传统与现代、理性与神秘性加以整合,“宗教成了爱因斯坦的最终归宿/他最后认识到有某种东西/是我们无法洞察到的/只能以某种最原始的形式/才能把握那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我们的华夏先民/早把宇宙及之外的一切力量/归之于无极/它既不是上帝/也不是宗教”(《归之于无极》)。这些苦思炼成的文字,就如一座巨大的射电望远镜,向浩渺神秘的宇宙投射出人类清澈而敬畏的目光。这些作品篇幅不多,但在题材的开拓上,功莫大焉。实话说,我很少在其他人诗集里读到类似内容的书写,或许应该归功于他的新闻和从商阅历,炼成了严谨犀利的理性和冷静独立的批判力,其思维世界始终扎根大地,又面向人世和可知的未来豁然敞开。
不过更为重要的是,他以广袤的社会视野和敏锐触觉将芸芸众生纳入笔下,描绘出一部形神具备的市井风情录。他以戏谑的情调写下了关于黑股票、血腥足球赛、假神医、李咏之死、诗人与诗、朗诵比赛、滥拜佛、山寨组织、食品安全、跟风鼓掌的观众等社会题材。这些作品从个体生命出发,透视社会、洞析人心,并始终保持着诗人应有的先锋精神,传递着批判、忧患与悲悯大爱,甚至偶尔混搭着幽默与俏皮,通过无数碎片化镜头的组合串连,捕捉并呈现出寻常百姓五味杂陈的生活状况。他也聚焦于某个凡人,刻画其人性闪光点,既能以接地气的口吻赞扬一位亲民勤劳的基层公仆,也能传递出特殊工作者的内心善良与谋生意志(《陪唱姑娘》《活着不易》)。至于社会繁华表象下的阴暗角落,比如重庆坠江公交、中国式彩票等,义之所至,他也金刚怒目,独抒己见,唤起我们对于生存与灾难、正义与罪恶、善良与贪婪等基本命题的重视与思考。而对于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他向世人提出了灵魂拷问,“对此 我心疼/却不内疚/因为需要内疚的是/有些山/有些水/有些空气/有些灵魂”(《有个表弟快要死了》)。他并没有滞留于单纯悲伤或义愤,纠结于政治社会层面的追责或批判,而是更深地看到了普遍人性中潜藏的怯懦。这些关于人世间的诗歌,捕捉的或许只是一人一事一景,折射的却是群体生存和个体灵魂的矛盾与调和,他以沉郁内蕴又蓄势待发的文字,致力于表达斑斓多姿、充满矛盾而统一的真实生活,延续着新文化运动以来诗人的独立精神,又恰如其分地回避了激越与反叛,达到了特立独行和传世共鸣的平衡。
对于这么一位目光执着游弋于人心世相的诗人,项建新笔下的植物描写,自然不是鸟语花香的纯粹景物攀写,通读下来,你会赫然发现他所写形形色色的植物和动物,依然是人类思想言行的投射与外化。对于植物,他往往寄寓了人性种种善意与美德。他以棉花、蒲公英种子、南瓜、龙葵、多肉、狼毒花、榕树等寻常植物为话题和契机,不动声色地抒发了对人情世故的感悟。他笔下的每一株无言、无名的植物,既焕发出与作者同样的傲岸超拔的灵魂,又始终令读者可亲可感,感受到透亮流畅和醇厚深远的微妙张力。反观他笔下的动物则截然相反,讽喻了人类历史和社会中一些我们熟视无睹的不义和荒诞。《狗》从洛阳周天子车马遗址里殉葬犬的遗骸重构当年活埋现场,抒发出他对人性阴暗面和罪恶的透析。“我无数次展开想象/当年往坑里填土的时候/活着的小狗一定满心恐惧/拼命寻找能让自己活着的地方/刚开始填土时/由于泥沙不会立刻填充到车下/马车下的空间/便成了他们片刻苟活的藏身之地/然而这藏身之地也是极其脆弱的/四处逃窜的小狗们/很快纷纷窒息而死/……在这几乎接近地面的地方/在这几乎接近生还希望的地方/人类用这块石头重重砸在头部/在一声刺穿苍穹的凄厉叫声中/小狗终止了生命/我们至今应该可以看见/它眼神中对人类的疑惑/愤恨无助乃至绝望”,近年诗坛极少有这样令人不寒而栗、而又不得不正视的作品。
因此他笔下的无论动物和植物、自己和世人,在诗学意义上得到一视同仁的打通、并存和共融,不单蕴含着哲学与思辨,更加以精细的语言化和形象化,共同塑造出一位复杂、睿智而细致的诗人主体。通读全书后重温开篇他的《自序一条从龙门山跳出的鱼》,一首近乎3D水墨动画片的自喻诗,更加感同身受。他就像一条拥有奇遇的鱼,从南方小溪、小河逐渐游入大江、游向北方乃至大海,领略过同类未曾见识的风光,却始终对故乡念念不忘,“因为鱼始终很明白/自己不仅是/一条喜欢大海的鱼/更是一条/从龙门山跳出的鱼”。返乡意识,是人类历久弥新的精神源动力,是诗歌应对生存困境的自然反应。特别是他身处传统与现代、工业与信息时代的社会转型,混杂着写作与从商的两栖身份、自由审美与功利实用的思维切换,这种身与心、己与物的紧张状态形成了巨大的生存焦虑,但也提供了持久的精神动力,促使他在现实世界和精神国度之间努力寻求回应、突围和超越。
项建新作为保持了钙质的诗人,是大时代大转型社会里难能可贵的梦想践行者和价值守护者,为当代汉语诗歌输入生机勃勃的创造性活力。他以其复杂的人生际遇、深邃的精神追求,抗衡着个人和理想在现实处境中被侵蚀、被扭曲的命运,低调而执着地以其作品、其言行乃至整个生命,向芸芸众生和广袤苍穹宣告着文学何谓、诗人何为的永恒命题的个体答案。
■附:项建新诗两首
回 乡
眼看一壶水
被带离到他乡
我能设想
当它想家了
就会化为白云
一路飘到故乡上空
以雨的方式回乡
如果一个人
迁徙到异乡
当他想家了
我无法确定
他的灵魂
会以怎样的方式回乡
读 雪
我害怕冷
却年年期盼大雪
每当站在大雪里
把雪花放在手心
故乡就会来到心头
年复一年
读雪也成了我的爱好
读的雪越多
就越相信
每朵雪花都有她的来历
读的雪越多
就越相信
原来
大雪纷飞的样子
就是故乡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