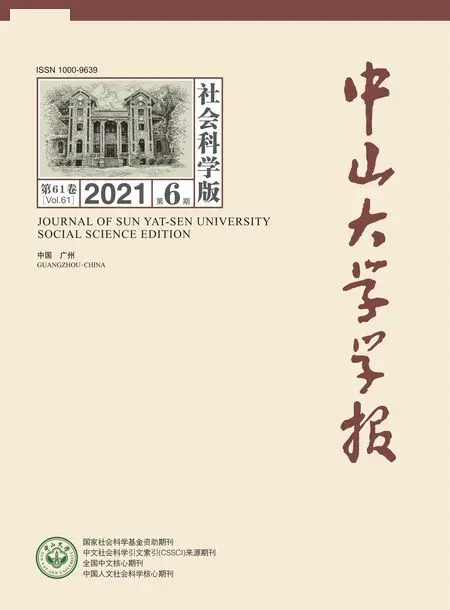辛亥革命前后康梁在国内的谋划活动*
安东强
康有为、梁启超组织领导的政治团体是清末中国政治舞台的重要力量,也是孙中山所领导革命运动的重要对手方。在清末十余年间,双方因宗旨、政见、思想的分歧,在国内外多个场域下爆发公开的论战,甚至也有秘密暗杀之举,欲将对手除之而后快。尽管两个政治阵营的个别人,如梁启超与孙中山一度曾有联合,最终也走向歧路,彼此之间的斗争与仇恨,甚或超过与清政府之间的斗争。1905年,康有为命令康同璧谋划暗杀孙中山,还称“宁我事不成,不欲令彼事成也”①桑兵主编,於梅舫、陈欣:《孙中山史事编年》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472页。。次年,梁启超致函康有为又谓:“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②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73页。这些论述正是康梁一派与革命党之间紧张关系的真实写照。
迄至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康梁一派的主张与活动仍以革命党为主要对手,其联络各省、鼓吹“虚君共和”及接触袁世凯(联袁问题,康梁二人态度上亦有差异)等举措,希望在历史的大变局中掌握政治的主动权。此前已有研究者对辛亥革命时期康有为、梁启超一派的政治主张与活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尤其是关于“虚君共和”的来龙去脉及背后的政治意图与学理纠葛③陈长年:《辛亥革命中康、梁一派的政治活动》,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湖南省历史学会编:《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李永胜:《清帝退位前夕梁启超与袁世凯关系》,《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赵波:《“虚君共和”说和辛亥年康梁一派的应变举措——〈新中国建设问题〉解析》,清华大学2001年硕士学位论文;桑兵:《辛亥康有为的虚君共和论》,《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王庆帅:《以衍圣公为虚君:康有为在辛亥鼎革之际的一项政体设计》,《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9年第3期。。本文依据近年来影印出版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及新出书信等资料①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此书为当年丁文江等人编纂梁启超年谱的稿本,后续《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油印本)及《梁启超年谱长编》均在此基础删削而成。本文所引梁启超等人书信的文献,若《梁启超年谱长编》已收录,则仍征引《梁启超年谱长编》一书;若为《梁启超年谱长编》所无、而为《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所有,则径引《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从而凸显该书“新材料”。,结合当时报章杂志,拟对辛亥革命前后康梁在国内的谋划活动进行细致而深入的梳理,以期呈现辛亥革命复杂多元的历史内涵。
一、续开党禁
由于党务发展和开赦党禁的挫折,梁启超在1910年5月有“家事、党事、国事无不令人气尽”之慨,对清朝统治颇为悲观,称:“大乱之起,决不能出两年之外,恐四万万人死去一半,然后新机局乃开耳。将来收拾残山剩水,责任终在我辈。”②《致梁启勋》(1910年5月28日),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20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41页。所谓“四万万人死去一半”,是梁启超此前批评孙中山革命主张之语。这表明在时局困顿之际,梁启超也不得不将打破旧局、开新机局的希望寄托于革命,只是仍然自信最终由他们“收拾残山剩水”。
1908年至1911年间,康有为、梁启超急于谋开党禁,固然缘于国内预备立宪运动的高涨,希望回国执政坛之牛耳,也与保皇派在海外筹款密切相关。当1909年“开禁之议,近复大炽”之际,梁启超致函其弟梁启勋称:“兄年来于政治问题研究愈多,益信中国前途非我归而执政,莫能振救,然使更迟五年,则虽举国听我,亦无能为矣;何也,中国将亡于半桶水之立宪党也。”③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93—494,515,526页。其迫切的心情和自信的姿态于此可见一斑。此后徐勤给梁启超的信则称:“美洲欲筹款之法,非开禁不可。”④丁文江、赵丰田 编:《梁启超年谱 长编》,第493—494,515,526页。因此,康梁差遣同党一方面暗中结交清室亲贵疏通,一方面联络立宪派呈请呼吁,耗费了无数银钱而筹谋的开赦党禁运动虽然轰动一时,但是在载泽等人的阻挠下,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在辛亥前一年开赦党禁受阻之后,时在北京活动的潘若海函告梁启超此事仍大有希望。他从亲贵载涛处获知,此次资政院提议请开党禁之所以未通过,是“政府对于院奏非不以事实为然,乃不以院为然,故稍停顿,即另寻题目作文章”,大约“开年后必有明文”⑤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93—494,515,526页。。按照载涛的讲法,清廷不是不想开党禁,而是不希望通过资政院来提议开党禁。因此,借助新的途径或借口来解除党禁,则成为康梁在辛亥年亟需思考的问题。
辛亥年开年不久,时在美洲的徐勤即致函梁启超,告知海外党务困疲,请再度谋划开党禁的事宜。他称:国内“开赦党禁”之事为袁世凯所阻,“闻之气短”,海外商务失败,“人心摇摇,大局岌岌,几如一篇枯窘题,无从下笔,只有日受辱骂呵斥而已,奈何奈何”。“今日欲补救之,只有再为运动,一面在老广处打点,一面在各省同志会签名要求开事,并运动各省督抚。”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9册,第4399,4403页。同日,徐勤还致函在京的伍宪子,称:“开事既有阻力,则此间无说话可讲,弟亦畏见人面矣。盖今日起死回生之药,舍开事实无法也。然既有所阻,则万无坐待之理。”⑦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9册,第4399,4403页。可见康梁一派海外党务只得借助解党禁来重振了。换言之,解党禁既关乎康梁等人的政治命运,又是重振党务、海外筹款的“起死回生之药”。
保皇派海外事业陷入困境,很大一个原因是海外投资的失败。一为墨西哥革命的影响,此前投资墨西哥的产业均濒临破产,且短期内无法出手;二是从香港贩运至纽约的古玩字画未能如愿获利;三是开党禁运动的受挫,此前为开禁筹捐的款项又需偿还。种种压力之下,徐勤焦头烂额,频频向梁启超抱怨,称:“今禁又不开,商务又一蹶不振,人心大去,无面目以见人。偶一见之,除辱骂外无他事。仆生平不知造何冤孽,而日受此奇困奇辱,真真不值矣。”欲求海外党务,一言以蔽之,“舍开事别无他策”①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9册,第4432—4433,4435,4407、4406,4467,4465页。。在此形势下,徐勤仍认为“使开事之议不至中变,则游埠行乞数千之款,亦不患不能筹也”。更为甚者,徐勤指出康有为及梁启超的信用“在美洲已尽失,只有开事实行后,或可复之”②清 华大 学国学 研究 院、中 华书 局编辑 部编:《梁 任公 先生年 谱长 编稿 本》第9册,第4432—4433,4435,4407、4406,4467,4465页。。言外之意,若康梁无法完成开赦党禁之举,他们在美洲的信用则将坠入万劫不复之地。
关于开赦党禁的阻力问题,何擎一从在北京活动的伍宪子处获得一些传闻:一是袁世凯以金钱贿赂宫廷及庆亲王奕劻,二是造谣惑众的革命党人,三是表面赞成而暗地里施手段的章宗祥、陈邦瑞、陆宗舆等人,四是“不见其反对之迹,而人言其甚为反对者”的名士郑孝胥、汤寿潜、张謇③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28页。。也就是说,朝野上下俱是反对开赦党禁之人,连革命党都与之“互为利用,务达其目的而后已”。康有为也以此为托辞,称“北事多沮,愈大则忌者愈多”,同时指出最大阻力还在于庆亲王,“不去庆父,鲁难未已,惜无力为突人之举动”④清华大学国学研究 院、中华书局编辑部 编:《梁任公先生年 谱长编稿本》第9册,第4432—4433,4435,4407、4406,4467,4465页。,流露出无可奈何的心情。
在开赦党禁一再无望之时,保皇派投资墨西哥的产业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几乎尽毁,“数年以来,无事不败,即银行、地皮数十万不动产,亦出意外,为乱党所毁,同事皆死”⑤清华大 学国学 研究院、中华书 局编辑 部编:《梁任公 先生年 谱长编 稿本》第9册,第4432—4433,4435,4407、4406,4467,4465页。。徐勤固然希望“再运动开禁事”,因“不开禁,会事尽散也”,但态度也趋于激进,要求回国实行暗杀活动:“满贼罪大恶极,纵不革命,亦当实行暗杀主义,乞速觅人来交代,弟即返,五步之内以颈血溅满人,于愿足矣。”⑥清 华大学 国学研究 院、中 华书局编 辑部编:《梁任 公先生 年谱长 编稿本》第9册,第4432—4433,4435,4407、4406,4467,4465页。他态度转而激愤,所谓要返回国内“五步之内以颈血溅满人”,无疑与汪精卫面对革命困顿之际不惜北上刺杀摄政王载沣之举类似。至于“纵不革命”之语,潜在之意也想到了以革命手段破除旧局,与梁启超愤言待革命来开启新机局的主张不谋而合。这或许反映出在辛亥革命前夕以革命打破旧局逐渐成为某种共识。
有意思的是,就在康梁一派对开赦党禁一筹莫展时,革命党人在广州的暗杀和起义活动提供了重议开赦党禁的新机。广州将军孚琦之死与两广总督署被革命党人攻击之举,固然没有实现革命的终极目标,却引起朝野轰动。1911年5月4日,在京活动的徐佛苏函告梁启超称:“开赦之说,前本有因,但前函所陈稍有推助,故曾嘱令娴公子必转递台中,冀以耸动彼方,不知果已递到该处否?至如近日,开赦之说又有生机。闻阁制不日发表,枢垣谓发表后,其第一义即当召赦,此言颇确。但飘蓬之政府果能其所见否?粤中近出两案,亦是造因之一法,当静以待之。”⑦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9册,第4446页。《梁启超年谱长编》虽收录同日徐佛苏函,但删去此段落内容。“粤中近出两案”,即4月间广州连续爆发的温生财刺杀孚琦之案与后来所称的黄花岗起义。
无独有偶,时论亦披露这一传闻。5月20日,《大公报》刊载《开除党禁又有转机》的要闻,称:“开除党禁一事,上年资政院曾经具奏,其折留中未发。现监国因广州党患迭起,恐非剿除所能净尽,拟即开诚布公,弛去党禁,以遏乱萌而资利用。昨特将上年资政院请开党禁之折,发交阁议。闻总理大臣庆邸对于此事亦颇赞成。其中原因,盖为驻京美使于数日前曾进忠告,谓现在各省乱机四伏,若不速筹变通办法,诚恐乱无已时,殊为可虑。庆邸亦以为然,故近来政界多谓此事已有转机。”⑧《开除党禁又有转机》,《大公报》1911年5月20日,第4版,“要闻”。开赦党禁的转机居然来自政敌的推动,不知梁启超获闻此消息后心情如何?
在时论看来,清政府重议开赦党禁,“但知开除党禁,可弭目前之祸,而不知致力于根本问题,恐党禁虽开,乱萌终未易遏”。何谓根本问题?须知党人来源问题:“党人之发生,由于政治之不良,政治之不良,由于专制之遗毒。俄之有虚无党,意之有无政府党,日之有暗杀党,胥以是也。证诸吾国往事,则尤有信而可征者。”由此可知,“党人之宗旨固不在倾覆国家,而在改良政治”,因此清政府应改变此前数年“阳骛立宪之名,阴长专制之焰”的旧辙,不得“以纸片上之宪政欺党人,以欺天下”。就此而论,清政府若不在根本问题上进行改革,既开党禁,“政府所持为笼络人心之具”,“应召而来者,不过似是而非之么么小丑,彼渠魁首领依然思乘隙而入,达其推翻政府之目的”①《开除党禁之根本问题》,《大公报》1911年5月20日,第3、4版,“言论”。。此论基本可以反映朝野上下对清政府实行立宪的期待,固然与康梁一派的政治目标有所差异。
尽管迫于各方压力,清政府有重议开赦党禁的传闻,可是实质性进展却迟无音信。6月28日,徐佛苏还在给梁启超的信中称:“弟近日焦思苦虑,不知以何方法而能开党禁也?”②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51页。7月25日,报界探知内阁大臣在召见时虽奏对赦免党人的政策,并提出“如蒙殊恩赦免,当即量为录用,拟先委办各项实业,俟有成绩再行量才畀以行政、外交上之重要差缺”,但此事重大,要待召集御前会议时由国务大臣讨论后才可发表③《阁臣另起召见奏对赦免党禁》,《大公报》1911年7月25日,第3版,“要闻”。。据称,此次重启开禁之议,缘于两广总督张鸣岐的鼓动,其意不过是“因该省匪党势大,无法剿除,故特献此议,以为笼络之计”。8月间,张鸣岐曾有公文寄至内阁,请宽赦党人,所议“种种办法,颇为中肯”,但奕劻阅后,只是将其藏入袖中,“回府内详加核夺”④《张鸣岐条陈开除党禁》,《大公报》1911年8月6日,第4版,“要闻”。。
由于开赦党禁的传闻异辞,好事的《大阪朝日新闻》记者专程赴康梁在须磨的住所,询问“以特赦是否属实”。康梁二人表示并不确定,“果然,吾辈洵喜甚”。梁启超称:“若使君所闻电报为真,吾辈应绝叫时机之到来也。吾辈在外已十余年,常不忘国事,奖励同志,直至今日者,时机果到,当大有所为矣。”⑤《新闻记者之访康梁谈》,《顺天时报》1911年7月21日,第2版,“中外汇报”。可以说,康梁对外并不讳言对党禁解除的期待,只是对于消息真实与否仍取审慎态度。
之所以迟迟未定论,显见开赦党禁之事既有主持甚力者,也有阻碍者。8月2日,时论披露内阁总理大臣奕劻的态度,称:“开除党禁,现虽议及,然将来实行与否,尚未可知。故须严守秘密,勿得预为宣泄。”又对民政部有所布置,称:“宽赦党人一说,关系重要,须暂缓议办,如国民有为此项问题开会集议,希即严行禁止,以防上书请愿,转滋诸多不便。”⑥《开除党禁仍守秘密主义》,《大公报》1911年8月2日,第4版,“要闻”。后来,传闻清政府又密商此事,担心“若延至资政院开会后,恐议员仍行鼓动,尔时准驳,反至两难,莫如赶于开会前颁布恩旨”,再令资政院诸人群议办法,“各大老亦颇赞成”⑦《密议开除党禁之时期》,《大公报》1911年8月13日,第4版,“要闻”。。至9月间,经内阁会议,仍将开赦党禁与否的问题延后处置,“开除党禁之利害,现已再三核议,将来能否实行,在朝廷自有权衡”。但资政院开会在即,若将此问题交院会议,“势必众意纷纭,转无定见,因决计不交院议”,且谕令资政院两位总裁李家驹、达寿,如果届时有议员提议此问题,应“直言拒驳”⑧《开除党禁决计不交院议》,《大公报》1911年9月6日,第4版,“要闻”。。以后见之明看来,大势将去,清政府仍欲秘密行事和禁止民众开会请愿,不免为将倾的统治大厦再加了一把推力。
时隔一月之后,10月10日,武昌枪声响起。经过革命浪潮及清政府内部军政人士的推波助澜,开赦党禁之议终获确定。10月27日,于邦华在资政院提出“弭乱策”数案,经三数人讨论之后议决:“一、罢亲贵内阁,二、将《宪法》交院协赞,三、解除党禁。”汪荣宝称将此议“作为三件具奏案同日呈递”⑨赵阳阳、马梅玉整理:《汪荣宝日记》,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243页。。29日,由资政院总裁世续等领衔奏请速开党禁,以立宪国实行宪政通例及爱惜人才为理由,“不可不速开党禁”。至于开党禁的人员范围,包括“凡因戊戌政变而获咎者,与前后因犯革命嫌疑惧罪逃匿者,以及此次乱事虽被胁附而自拔来归者”⑩《资政院总裁世续等请速开党禁以收拾人心折》,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93页。,均在被赦之列。其中自然包括了康有为、梁启超诸人。
至于康有为、梁启超获闻此谕又是何种感想,值得玩味。黄可权致函康梁时称:“党禁开矣!几经曲折之问题,一旦解决,何幸如之。虽以后国家之局势未可遽知,要之,其为革新之一段落,无可疑也。此次开禁,系出于他力,非出于政府之诚心。”①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9册,第4518,4493页。“他力”之说,显然系革命之势,而非康梁之谋。这对于康梁此前苦苦筹谋开赦党禁来说,无异于一种讽刺。对于党禁骤开,康有为也赋诗二首,以表其迹,一为:“千秋伤党锢,禁网至今开。自是昊天下,宁因兵变来。流涕苏马赦,伤旧滂膺哀。感叹乌头白,艰难归去来。”二为:“十四年于外,流离万死间。子卿伤白发,坡老指青山。国事亦多变,神州竟未还。惜哉迟岁月,念乱泪潸潸。”②吴天任:《康有为年谱》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87,484页。所谓“自是昊天下,宁因兵变来”之语,大概可以反映康梁师弟二人的心境。数月之后,康有为又有“党禁久迟,吾几死”之语③《康有为致梁启超》(1912年2月4日),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往来书信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43页。。
姗姗来迟的开赦党禁上谕已不足以引发康有为、梁启超欣喜若狂了,因为武昌战事以来的革命形势已发展到全新局面,于康梁而言,也是要履行“收拾残山剩水”责任的时机了。
二、秘密联络
自1899年保皇会成立以后,除了次年轰轰烈烈的庚子勤王运动以外,康梁一派的组织活动重心是在海外,其在国内的影响主要通过三个途径:一是以言论影响朝野上下,诸如《新民丛报》《时报》《国风报》的创办与影响;二是秘密结交权贵,借助清政府的政治斗争翦除政敌与开赦党禁;三是在鼓动与呼应国内立宪运动,借朝野的呼声打破党禁的枷锁,从而联合志同道合的团体组织政党,使海外与海内联通一气。于康梁而言,固然是要借助国内军界、政界与舆论界的力量,于国内朝野而言,其接受康梁的联络,无非也有借助康梁政治威望及海外影响的意图,彼此之间均有在政治上借水行舟之意。
在开赦党禁遭遇重大打击之后,辛亥年阴历五月,康有为移居日本,与梁启超会聚一地,同住神户须磨的双涛园,后在临海处建造一个小楼,名曰天风海涛楼。在徐勤看来,虽然海外党务惨淡,但是康梁师徒会合,“十年奔走,身世飘零,良可痛矣。然尚得于患难之时,追随函丈晨夕讲求,亦幸事也”④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9册,第4518,4493页。。师弟二人阔别8年之后重聚,“相对如梦寐”,时有诗酒酬唱之乐,梁启超还亲手抄写康有为诗集,以珂罗版影印二百册行世⑤吴天任:《康有为年谱》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87,484页。。
与此同时,梁启超仍在积极为徐佛苏在国内组织宪友会、经理《国民公报》事出谋划策。梁启超还在与徐佛苏的通信中述及康有为政学的高见,获徐佛苏等人赞叹:“知南佛老年精进,旁通寰球政学,真天纵多能也。弟于座间即以大示与鄂议长汤化龙、闽议长高登鲤一阅,均惊佩失色。盖弟等视公之好学敏求,已如仰视泰斗,而公文谓南佛之精进为意料之所不及,则弟等更如游、夏之不能有赞词。”⑥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51页。这或为梁启超为康有为争取日后宪友会的党魁铺路。毕竟多年以来,国内立宪派与梁启超联系密切,颇有待开党禁后举梁为党魁之意。至于对康有为,国内立宪派诸人还是有所保留,这于民元国内组党时的情形即可见一斑。
梁启超与徐佛苏筹划开赦党禁固然挫折重重,可是作为一个重要党派,对国内政局的影响不应局限于此。辛亥年也是中国多事之年,因中外交涉不利,瓜分之说再次腾诸报章。主持保皇派美洲党务的徐勤频频接到各埠询问:“吾党进行之方当如何,仆无以应之。盖立宪耶,则迫不及待;革命耶,则更速其亡;暗杀耶,则从何下手?从种种方面研究,几如一部十七史,不知从何说起耶。吾党为中外人所仰望,今危急如此,使寂寂无闻,无以副人望而张党势,乞与长者速定方针驰告,以便布告各埠而安人心。”徐勤甚至提出,欲救危亡,或可仿照庚子年在上海开一个国会,“传布十八省,以处置北京政府,或合各省志士求独立之法”①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9册,第4439—4441页。。就目前寓目的史料而言,尚未见康梁如何因应此事。此时康梁仍沿续此前运动开党禁的途径,意图利用亲贵之间的倾轧,发动宫廷政变。他们在禁卫军广布党羽,耗去此前捐募的款项,同时活动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希望收为己用②陈长年:《辛亥革命中康、梁一派的政治活动》,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湖南省历史学会编:《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下册,第538页。。
至武昌战事骤起,康梁虽迅速有所策划与布置,但整体判断却颇失良机。梁启超认为:“武汉之乱,为祸为福,盖未可知,吾党实欲乘此而建奇功焉。”康有为则判断此次变乱有可能“不期月而亡国”,“以法国鉴之,革党必无成;以印度鉴之,中国必亡”,“所幸武汉之事,出自将军黎元洪,而汤化龙参之,皆士夫也,或可改为政治革命”。经康梁商定计划,定为“用北军倒政府,立开国会,挟以抚革党,国可救,否必亡”的方针,此外则联络运动各省,“但得一省倡之,他省必从之,然后稍有时日,足供我布置,布置一定,则各省复合为一,此反掌之功”。当梁启超起行回国之际,又定下和袁、慰革、逼满、服汉的八字方针③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53、557、552、555、558,593页。。所谓“用北军倒政府,立开国会”之策,实际上仍是沿续此前发动宫廷政变与谋开党禁的策略。
至于联络各省的活动,诚如研究者所论,一是梁启超亲赴奉天一带运动,因形势变化,且有不测之险,只得返回日本;二是分派要人奔赴山东、广东、云南等地进行活动;三是差遣盛先觉赴上海接触章太炎和宋教仁等革命党人,兜售其“虚君共和”的主张;四是通过蓝公武和罗惇曧在北京运动邮传部大臣梁士诒和资政院总裁李家驹;五是与袁世凯的试探与接触④陈长年:《辛亥革命中康、梁一派的政治活动》,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湖南省历史学会编:《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下册,第541—549页;李永胜:《清帝退位前夕梁启超与袁世凯关系》,《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由于袁世凯复出后基本上掌握京师的政权和兵权,使得康梁一派原本的计划胎死腹中,因此梁启超只得返回日本,再谋进取的策略。
其实在梁启超动身前,远在美国的徐勤便认为梁启超此行“必难成,且甚险”,建议康有为“切勿再倡存皇族”之说,因“满人气运已绝,若复抗舆论,存皇族,必为全国之公敌”,“以失人心,而散会事”⑤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53、557、552、555、558,593页。。可惜乃师未听从其建议,仍提出“虚君共和”论以维持清室。康有为苦心炮制的“虚君共和”主张,虽有一时反响,终为各方所弃⑥参见桑兵:《辛亥康有为的虚君共和论》,《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除上述诸人的活动之外,尚有数人的行踪值得注意,特别是徐佛苏在此期间的活动。徐佛苏本为梁启超在国内奔走开赦党禁、组织政党和推进立宪运动的重要联系人,在获知梁启超有回国计划之后,曾一度到天津,将在北京主编的《国民公报》交由蓝公武代管。徐佛苏此行欲与梁启超会合。潘若海曾在致梁启超的秘信中称:“念四日抵津,晤佛苏,云公将至,连日在车站相候。至念六日,佛苏得公电,知不来。仆乃晋京,在长公处小住数日。本定与佛苏日来,因佛苏有事济南,故仆先返沪相候。”⑦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9册,第4615,4615—4616页。由此可见,徐佛苏与梁启超之间有电文往来,可惜今未得见。揆诸梁启超的行踪,他于11月6日动身回国,约徐佛苏在天津相会,后因梁启超因故不能入关赴津,遂致电徐佛苏取消行程,徐于“念六日”(11月16日,即九月二十六日)获电。值得注意的是,潘若海函中同时称:“前者北行之政策,仆至今未能深悉,恐仍道旁筑室之谋。今日无论政策若何,非有真实力量,必无幸成。”⑧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9册,第4615,4615—4616页。由此可知,徐佛苏与潘若海可能并不知晓梁启超赴奉天之行的深意。
徐佛苏所收梁启超的电文中应不止有取消原计划的内容,或尚有命他南下赴济南及上海之行。潘若海函中称徐佛苏“有事济南”,即指徐佛苏在天津要南下接应此前派人运动山东的事宜。徐佛苏在山东的活动情况,未得其详。但是当时奉康梁之命与侯延爽同在山东活动的麦孟华,在此期间曾有一函致梁启超,询问:“佛苏东否?望必请其至此一商,东事非谓绝望,然必熟察情势,乃可着手,断不可卤莽耳。”根据麦孟华的观察,国内形势瞬息万变,即如山东局势,他和侯延爽的书信刚送走,山东局势已尽变:“孙抚已取销独立,或言为军队反对,或言实政府主使。要之,此事已见明发,无论如何,必不能着手,当即电止勿行,计达典签。今日局势瞬息百变,在东时所筹画指望者,至此后情形已异。”①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9册,第4624、4621,4622—4624,4619—4620页。从后来的行踪来看,因留在山东已不足以改变孙宝琦的立场,徐佛苏便与麦孟华、侯延爽一同赴上海。
身在国内活动的潘若海、徐佛苏等人的意见颇为一致,即函中所称的“今日无论政策若何,非有真实力量,必无幸成”,所以他们南北奔波,除打探各方真正意图外,最主要的还是为康梁联络“真实力量”,无论是军界还是政界均可,从而实现海外与海内两重势力的整合与新生,成为可以直接影响国内政治走向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远在海外的徐勤亦持同样的意见,因为其党对于辛亥变局“向无预备,致为他人捷足,党势顿衰”,所以建议康梁“运动唐翥臣先生,图琼州,据一隅以观天下之变。并用林承先招生番练兵,以进取中原。今日惟有兵力乃可有势力,有势力乃可有发言权”②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93页。。进而言之,“有发言权”才能贯彻其党政治意图,否则各种政治主张只会是虚言而不能有切实的影响。
按照麦孟华的总结,康梁所持的应是在南北之间的“第三主义”,因此在政局尚不明朗的时候,“吾党既持第三主义,此时万不可有所偏倚,若一落边际(如从雪舫言而东行之类),则虽欲为第三者,势必逼而成为第二者,而代人受敌。一着稍错,以后便不能自拔,千万不可轻举妄动”。故而主张“必当审慎以观其变”。同时也奉劝康梁不要急于发表政见,尤其是康有为,“长者之文,更宜缓发。此时吾人无政见发表,亦不至遂失人望。而当此狂醉之时,一言稍有轻重,彼狂醉者持以相攻,则哗然和之,便足令我落边际,故不可不慎也”③清华 大学 国 学研 究院、中华 书局 编 辑部 编:《梁任 公先 生 年谱 长编 稿本》第9册,第4624、4621,4622—4624,4619—4620页。。这或许即是指康有为那一系列的《救亡论》及《共和政体论》等文章。
相较而言,徐佛苏、麦孟华等人在国内活动,对局势的认知应比康梁更深切一层。麦孟华虽建议康梁不急于发文,并非持保守主义,而是期望向务实方面努力。他认为:“今日事变方始,必非一半年所能收拾。吾辈最苦绝无凭借,必须拉合一二有力者(若策正同此意,即其策不行,仍必须向此着力),假其力以为藉手。既无自力,不得不假他力,专意从此着想,必尚有可乘之机。”④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9册,第4624、4621,4622—4624,4619—4620页。正因为“绝无凭借”,所以联络各省有实力者的行动不宜迟缓,麦孟华等人由北至南的秘密联络要人最显得格外重要,此后他接触岑春煊、谋取广东,正是此意图的具体表现。
徐佛苏抵上海后,曾有一函致梁启超,称:“抵沪后,和议大就绪。既由国民会议决定君民问题,则将来民胜自无待论。根本既已决定,其他之重要问题虽多,然南北两面,以后只有协议而无戎机矣。弟前日来沪之意,原系就和议成否两面而定办法。倘和议不成,则吾辈之责任重,而挽救方法亦当极速;倘能成,则只注重联络各党派,建组一大政党而已。”关于建党问题,作为梁启超在国内奔走的关键人物,在党禁已开、和议就绪的新形势下,无疑是徐佛苏等人接下来活动的第一要义。可是他们“在沪无甚活动,虽曾多见党中要人,皆未暇多言建党”。在徐佛苏看来,“南方汲汲组织临时政府,以统一目前,而善后事宜端绪千万,不暇与吾辈议党”,因此未来“联建党基以北方为较要”。事实上,徐佛苏在上海期间,“寸步有人监察”,因“平日讲宪政著名之人,在南中行动不能自由”,故而难以行事。经与麦孟华商议,徐佛苏先于1912年1月3日乘船返回北京,麦孟华继续留在上海活动。他们议定“抵京后与龟山等商妥,三五日之后即具情电达”,以定梁启超之行止⑤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97、568页。“龟山”指袁世凯一方的杨士琦。。
总而言之,在武昌战事爆发之后的数月之间,康梁一派无论是抛出“虚君共和”的主张,还是秘密联络各省的活动,均未收到实质性的成效,无非是在某些政治立场与选择上与各方逐渐获得一些共识。这些共识能否成为具体的政治实践,均取决于康有为、梁启超是否回国、何时回国、回国后如何做而定。
三、回国的分歧
康有为和梁启超是推动戊戌变法的重要人物,在政变后流亡海外十余年间,仍然通过策动勤王、暗通权贵、传播新知与新学等多种形式影响国内政局和知识界。在辛亥革命的历史大变局中,由于党禁开赦和南北和谈,康梁何时回国以及以什么身份回国,无疑是有可能改变当时政局的重要因素。
1911年11月3日,《大公报》披露清政府电令各出使大臣查探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行踪,“并详探其对于此次党禁开后具有着何感情,迅即电复”①《电查康梁等之行踪》,《大公报》1911年11月3日,第2张第1版,“闲评”。。如果传闻无误,看似查探行踪和感情,实际上清政府关注的是他们三位党魁的回国问题。
各方对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三人回国的期待有所不同,自不待言,即以康梁而论,也有不小的差异。11月16日,袁世凯在北京组织新的责任内阁,任命各部大臣,以梁启超为法部副大臣,未到以前由定成暂行署理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7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04页。。在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看来,新内阁中“最可惊讶者,则授梁启超为司法部副大臣之事。梁为康有为党最著名之人”,“著书甚多,尤以律学为最”③陈国权译述:《新译英国政府刊布中国革命蓝皮书》,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77页。。至于袁世凯为何愿意接纳梁启超入阁,而非康有为,朱尔典未作评析。
时在北京与袁世凯一方接触的蓝公武致函康梁称,自袁世凯组阁后,京城官场大老及一般士大夫“渐成一种心理”:极望康梁回国与袁世凯联合。又称:袁世凯“所以仰望二先生出山者,有二故:一欲借二先生以收罗人才,挽回舆论;一望二先生联络华侨,整理财政。惟项城颇惧南海先生,将来权在其上,故尚踌躇未决。而沧江先生则深愿其归国,且有副大臣不愿,则以大臣与之之说。”④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9册,第4601页;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79页。也就是说,按照蓝公武的观察,袁世凯是惧怕康有为权在其上,才只借其名望,对梁启超则可付之副大臣乃至大臣。不过此说也可以有另一种解释,即希望替康有为挽回一点颜面。
康有为如何面对这种尴尬?不得而知。若仅以某部大臣来安置康有为,或许未免低估了康有为的器局。但若说康有为没有政治欲望或官瘾,则又高估了康有为的为人。事实上,康梁还是因为梁被任命法部副大臣之事而心生嫌隙。在同处须磨双涛园的一次冲突之后,康有为毫不客气地讥讽梁启超称:“知汝羽毛丰满,又学博名高,应退让以寻常友朋相待,则岂敢于大名鼎鼎之汝、□为副大臣之后,而致其冒渎干涉者哉?”⑤《康有为致梁启超》(1912年2月4日),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往来书信集》,第643页。借“副大臣”讥之,或可见康有为对此事的不快。
因此,无论是从政治大局把握,还是从私情顾虑,梁启超既不可能立即回国就袁内阁的副大臣之位,但又不会断却了与袁世凯一方沟通联络乃至合作的可能。蓝公武、罗惇曧、徐佛苏等人在京与袁世凯一方反复试探与沟通,即为例证⑥李永胜:《清帝退位前夕梁启超与袁世凯关系》,《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
事实上,不仅袁世凯内阁想要请梁启超回国任事,民军方面也有请梁启超归国起草组织临时政府文件的提议。12月2日,《申报》载广西军政府电称:“组织政府,关系事巨。由各省派全权委员赴鄂联合组织,固足以昭郑重。然无硕学鸿儒为之起草,恐仍难期周密。”他们提议梁启超,“才学久为中外所仰望,拟请各军政府联衔延聘,专事起草,庶几组织完备。一经宣布,可免纷更。各都督如以为然,希从速电请鄂军政府聘定为要”①《都督府电书一束》,《申报》1911年12月2日,第2张第2版,“本埠新闻”。。不过此事未见下文。
梁启超在11月赴奉天之行落空后,便不再轻言回国。对于梁启超此行,其门人吴冠英于12月14日致函称:“迩者奉天之行,外间已纷谓先生将教赵督借俄兵以平革军,沪上及粤中各报攻先生者已累日矣。此时若再有被外人误会之事,使一般人视为众矢之的,群转锋以相向,则不特所谋事将归无成,而于国家亦无所裨,李陵所谓杀身无益,适足增羞,此时之举动,万不可不慎之又慎也。”从而提出自己的看法:“默观目下中国之时势,窃意先生之出山,实非其时,若数月后乎,则时势逼人来,先生虽欲高卧,恐亦为舆论所不许矣。”②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94、596,597—598,598页。这固然是基于南北和谈前局势不明朗的观感。
待到徐佛苏等人在上海观摩南北和谈之后,他们一度认为梁启超应当准备回国北上为妥,因“昨谕沧已开缺,则项城容纳沧之意见可知,故沧万不能不北往以结之”。“沧”即指梁启超,“以大势言之,公等与项城自当引为政友,虽未必能冶为一炉,然亦无极反之事”③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94、596,597—598,598页。。1912年1月初,徐佛苏从上海返回北京,可能在接触了袁世凯方面之后,又建议梁启超暂勿回国。他与蓝公武会面晤谈,二人均“不主张二先生即时回国”,但关于康梁接下来应行的政策,徐佛苏主张应“拥戴满朝于满蒙”和“欲任公改唱共和”,便遭到蓝公武的反对。蓝公武主张:“二先生宜一无举动,静观时局之变;即欲改趋共和,组织党派,亦宜由在京者为之。盖时至今日,即欲改趋,既不能取信于人,徒多一番猜疑耳。”④《蓝公武致康有为、梁启超》(1912年2月),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往来书信集》,第708页。这自然是鉴于此前康梁高唱“虚君共和”论所引发的被动结果。
作为一个政派的党魁,在重大变局中“一无举动”,不免引发党众的不满。关于归国问题的重要性,梁启超也深知之,却也有许多难处。在奉天之行后,梁启超曾向康有为上书,指出“今日第一义在先决吾党行止”,对于奉天之行“总有不能释然者”,因为始终面对的是袁世凯。他提出几个问题:一、满人果可与共事否?二、即能共事,其利害若何?三、我辈果能得全权如今袁氏否?四、袁倒后我乃往乎?抑先往乃与各团共倒之乎?五、我即能得全权,如今之袁氏,能否得天下之贤才相与共事?六、北军究竟能战与否,实属疑问。在是否回国的问题上,“现在海内同志无一人不以沉几观变相勉,我若骤出,恐最亲信之人亦且量而后进”,“党中不欲吾辈轻出,几成舆论。若排众议而往,必尽失党人之心,以后谁与共大事者?”大概此时康有为是主张梁启超回国,冒险入北京,抢夺北京政府的主导权,梁启超则怀疑此事不可行。他所列的上述问题,即针对此方针而言,同时对于康有为对时局的论断已有异议,毫不客气地称:“师所论或亦有之。然遽断其必如是,得毋太武!汉阳复后,英日出而调停,此众目所共见者。英美商团请逊位,其建言书亦见各报,何由尽指为伪?吾师论事论学,凡既标一说,则一切与己说反对者,辄思抹杀之,论理学所谓隐匿证据是也。似此最易失其平。”⑤《上康有为书》(1911年11月后),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9集,第218—219页。仔细分析,康梁之间的分歧不仅在于是否回国,而且还在于回国后执行什么方针。梁启超大概认为康有为指授的方针在此时已无可行。
1912年2月3日,张浩、梁炳光、冯翼年、何天柱等人经过两个月的商议,致函梁启超,表示大局已定,“逊位之事发表在即”,“吾党不欲登舞台则已,如其欲之”,必须早与袁世凯联手,才能达其目的,理应当行之事:一、回国“迅赴北都,以谋进行,万不可瞻顾徘徊,又贻后时失机之恨”;二、政见改弦易辙,“再作大文字一篇,以发表最近之政见,斡旋前文,自完其说”,“政见本随时而变迁,不足为病也”;三、与康有为分道扬镳,“如佛决不以为然,出其专制之力来相阻格,则各树一帜,各行其是,万不可再屈以求合”。理由是“吾辈已过中年,宁堪再误”⑥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94、596,597—598,598页。?
按照当时人的年岁算法,梁启超正值四十,步入不惑之年。就在此时,康梁师弟因家事、党事、政见发生了一次冲突。梁启超给康有为的信中直言:“数月来谈事动生扞格,自银行、货币、财政等而已然,每谈一次,归则患首痃。”“大抵与师论事,无论何人决不能自申其说。师固非有心拒人,且未尝不力劝人以尽言,然人则断无能言者,无如何也。”指出康门弟子中谨厚者屈己以从,狡黠者面谩以营其私,“师平昔事无大小,举措乖方之处,不一而足,弟子亦不能心悦诚服,无如何也”。因此他自称“不适于任事”,“日来槁木死灰之念日益加,亦将从此不复问国事矣,还读我书亦可以自全其天”,同时也请乃师“复还讲学之旧,相与弦诵”①《上康有为书》(1912年),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9集,第221—222页。此信无月日,因其中提出“日来动生龃龉,全非因薄物细故”之语,故暂置于此。。因师弟意见分歧,遂致自退于读书自全和不问国事,自非有使命担当的政党党魁所应为。之所以如此,亦可想见二人政见分歧日深与争议日烈。
此次冲突大概深深刺激了康有为。2月4日,他写了一篇“数万言”的长信责斥梁启超,一方面将保皇派海外商务失败与开党禁不利的事,几乎全推在梁启超推荐的叶恩身上,但又言“吾一切与汝共事,互有得失,吾亦从不肯诿过于人。试问商败至今五六年,吾曾有一言以用叶委过于汝否?”“若当时破除情面,拂汝大怒而不受叶,则商务无今日之败,亦无命案,且必开党禁矣。”另一方面自认虚己虚受:“盖必自知为错,乃知认之;若自不知之,从何而认?伪为之乎?亦何益也!惟汝太不知吾性,吾家人则知之最详。盖吾于小事无日不曰千错万错,至大事乎,则自武汉后至行者为总统,吾料事未明,无日不自责其误而不中矣。”②《康有为致梁启超》(1912年2月4日),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往来书信集》,第642—644、646页。康有为甚至引曾、左之变与同室操戈的典故,可见当日冲突之烈。
看着昔日两大政敌袁世凯和孙中山都在辛亥革命的政治舞台上风生水起,康梁的政治压力与日俱增应是不争的事实。当康梁因应辛亥革命的种种举措不仅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陷入政治上的被动,其压力无疑更是难宣泄。康梁此番政见冲突,无疑就是种种压力之下的巨大宣泄,只是这种宣泄未能团结面临分崩离析的政党,反而适得其反。可以说,从南北议和到清帝逊位两个月的时间里,康梁师弟在讨论回国与否、如何回国的问题上白白浪费了政治时机。
2月13日,即清帝逊位诏书发表的第二天,冯翼年、梁炳光致函梁启超,陈请“不可不速决定”的两大问题:一、速与袁世凯合作,“发表政见,组织政社,收拾北方士夫及南方不附同盟会之诸派,可以成一极大极强之团”;二是速做政党之事,“此后中国必成为政党世界”,应积极扩张党势。同时致书汤觉顿,称“近来同人政见往往不同”,“函请主人速定大计,未审阁下以为然否”?对于这些说法,康有为直接在“政治世界”上批语“吾恐即复为专制帝政耳”③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10册,第4704、4706,4713—4714,4820页。。这显然印证了信中所言的“近来同人政见往往不同”的说法,或者已然是他们党人的共识性问题了。
从帝制到共和的历史变革,康梁一派在国内的组织与活动未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不免引起海外党众的质疑。徐勤来书建议康梁要注重海外关系与影响,称:“各埠纷纷追问党事,弟子亦穷于对付。吾党此后与各埠如永绝关系,则虽百函相问,置之不理可也。但吾党方当进行内地之时,藉海外之力方长,万难遽绝,以资对党。况十余年所办各事,无一事不藉海外之力。”这番话反映出徐勤远隔重洋之外的痛心与无奈,所历数庚子年以来的海外筹款对于国内组织活动的重要支撑,谅非虚言。可是数年来苦心经营的党务事业,不仅在国内未见成效,还在革命的浪潮下发生“同志之在海外海内受人辱骂、残杀、焚毁、斥逐之事”④清 华大 学国 学研 究院、中 华书 局编 辑部 编:《梁 任公 先生 年谱 长编 稿本》第10册,第4704、4706,4713—4714,4820页。,不知党内领袖又有何颜面直面海外党众父老呢?
康梁一派在辛亥革命期间举措失败的结果,不仅进一步暴露了内部的政见分歧,而且引发了同仁对政党的检讨与反省。麦孟华毫不客气地说:“吾党向来最误者,在无一定之政策,摇摇不定,一日百变,故至今无成。今不可不决定大计,定一政策,勿蹈前者之覆辙也。”⑤清 华大 学国 学研 究 院、中华 书局 编辑 部 编:《梁 任公 先生 年 谱长 编稿 本》第10册,第4704、4706,4713—4714,4820页。“无一定之政策”的责任,无疑在于党魁,隐然指向康有为及梁启超。所谓“勿蹈前者之覆辙”,自然是要向过往划清界限。
无独有偶,在获知清帝逊位的消息后,徐勤检讨本党失利的原因时亦称:“吾党十余年来办事,绝无条理,绝无实效。粤沪诸君实心办事者,又鲜其人。当此革命之大风潮,吾党则寂然不动,此不特局外者为之轻视,即会中之最热心者,亦为厌冷矣。即我辈设身处地,亦如是矣。”他对于康有为来电所称“缓归,内地无事可办”,表示自己在美国停留本是要“维系人心”,但“徒招耻辱”,愤愤而言称:“弟子决一月即归,如无事可办,则蹈海而死,以了此余生而已。”①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10册,第4839、4837—4838页。作为康有为的两大弟子,梁启超表示今后欲读书以自全,徐勤则要蹈海以了余生,真不知乃师作何感想?
余 论
徐勤所言的“当此革命之大风潮,吾党则寂然不动”,恰恰与当时孙中山及革命党人在国内的政治影响形成鲜明对比②安东强:《辛亥革命时孙中山在国内的政治影响》、《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寂然不动”或许只是结果与表象,康梁在此期间自然并非不动,只是种种盘算先后落空,从而造成过程与结果均呈现出全面失败的历史面相。
康梁一派在辛亥革命时期坐失机宜,犹豫不决,眼睁睁看着昔日的政敌孙中山与袁世凯成为南北政局的要角,且在斗争中实现了在中国肇建东亚世界第一个共和国。这种鲜明的对比落差,于康梁而言,当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待到梁启超1912年10月回国之时,在家书中则称:“都人士之欢迎,几于举国若狂”,尤其是要和此前孙中山、黄兴入京时的欢迎情形相比,“日来所受欢迎,视孙、黄过数倍”,且谓“彼等所受欢迎会不过五六处,吾到后已十余处相迎矣”,“要之,此行为国中温和派吐尽一年来之宿气”③《致梁思顺》(1912年10月24日、1912年10月29日),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20集,第17—18页。。关于所受欢迎情形的种种描述,可以窥视梁启超毫不掩饰的自得之意。与其说“此行为国中温和派吐尽一年来之宿气”,毋宁说是梁启超本人一举扫尽辛亥革命一年以来政坛失利的阴霾。
至于康有为,则在几年后将辛亥革命时期所撰写的文章编订成集,取名《不幸而言中不听则国亡》,提示国人那些民国诸多乱象均在他的预见之中,从而凸显他的先见之明④桑兵:《辛亥康有为的虚君共和论》,《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93页。。历史的批评者和建设者固然都可以留名史册,古今多少大事也都可以付于笑谈中。然而中国历史自辛亥革命之后,帝制已然为陈物,共和则勃然新生,历史的大势终如孙中山所言:“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