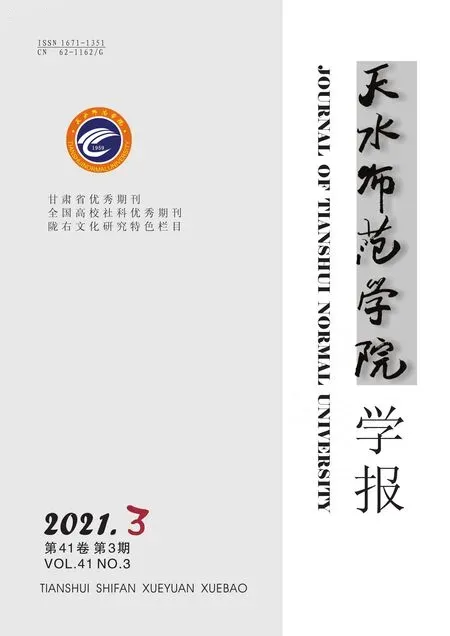苏轼的三位妻侍及身世述论
蒋 凡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一、问题的提出
苏轼研究一直是学界热点,然而鲜有人关注其身边休戚与共的三位妻侍——原配夫人王弗、续妻王润之、侍妾王朝云,她们与苏轼同生死共命运,深度参与其生命历程,并刻画下深深的印迹。王弗是苏轼的少年结发夫妻,不幸早夭,死时年仅二十七岁;继室王润之,系王弗堂妹,她与苏轼共同生活了二十五年,死时四十六岁。在两位王夫人先后去世之后,苏轼未再娶,侍妾王朝云却自愿随侍先生南贬岭南惠州,历尽苦难,始终相伴,以温情与理解给予苏轼精神上的慰藉。苏轼与她感情很深,为她创作了许多诗词文章,其感激之情是难以言表的。如果依封建婚制言,前二位王夫人是正式妻子,王朝云则是侍妾。妻妾之位,主仆之别,地位悬殊,妾终之后,难入宗庙祠堂,这是历史的现实。换一视角而言,如从现代人性看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在实际生活中,苏轼早就视朝云为知己,是其人生的另一半。
苏轼的三位妻侍都热爱自己的丈夫,在家庭生活中各尽其职,相濡以沫。她们都与东坡有共同语言,有感情交流,思想品格都值得称赞,对苏轼的生活和创作也都有各自的贡献。
二、结发之妻王弗
人类世界由男人与女人共组社会。男人的活动与贡献,又岂能没有身边女人的影响与功劳呢?苏轼研究是古今热议话题,一般只论苏轼的天才贡献与社会关系,沉潜于男人世界,而很少注意到其另一半的身影及贡献。苏轼固然是天才,但是如果他身边的另一半不给他的生活和工作创造良好的环境,甚或整天吵闹而家无宁日,他又将如何安心工作而吟诗作赋呢?如果文学家的内在心理因家庭生活偏于阴暗,又怎能挥洒出阳光灿烂的天才之作呢?
王弗(公元1039-1065年),蜀之眉州青神县人。据宋人施宿《东坡先生年谱》于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载曰:“是岁娶通义郡君眉人王氏讳弗,乡贡进士方之女。”[1]结婚时苏轼十九岁,而王弗十六岁。通义郡君,是王弗死后朝廷封赠的名位。颜中其编写《苏东坡年表》于至和元年(甲午)下载:“苏轼与青神县乡贡进士王方之女王弗结婚。王弗年十六。其始,未尝自言知书,见苏轼读书,则终日不去。其后苏轼有所忘,王弗辄能记之。问其他书,则皆略知之。”[2]由此可见,王弗出身书香门庭,少随父学,知书识礼,在妇女中,亦可称为略识得诗书的文化人。东坡读书,她陪伴在旁,“终日不去”,见其兴趣所在。苏轼是博闻强记之人,他偶有所忘,王弗却能记忆而启省之,其读书记忆力可谓惊人。
依据中国古代传统礼制,男女地位不平等,夫妻之间地位悬殊。以此,儒者强调妇德妇言,就有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之言。但年轻的王弗在家中就拥有一定的发言权。随时关注年轻丈夫的行动举止,如果发现问题,一定忠言而谏以纠夫之失。苏轼在《记先夫人不发宿藏》文中,记载母亲程夫人不许家人擅发他人宿藏之物以自利。作为儿媳,王弗谨记先夫人教训。“其后吾官于岐下,所居古柳下,雪,方尺不积雪,晴,地坟起数寸。吾疑是古人藏丹药处,欲发之。亡妻崇德君曰:‘使先姑在,必不发也。’吾愧而止。”[3]卷121,3413①崇德君,指王弗。按:苏轼文及施宿《东坡先生年谱》皆称王弗卒,朝廷赠通义郡君封号。见利不忘义,王弗纠夫之失,才是真正的关爱丈夫。而苏轼也没有耍男子汉脾性,而是欣然纳谏,从善如流,知愧而止。于此可见这对年轻伉俪的感情交流非常和谐快乐。以此,王弗死后,苏轼痛心疾首,写了《亡妻王氏墓志铭》:
治平二年(1065)五月丁亥(28日),赵郡苏轼之妻王氏,卒于京师。六月甲午,殡于京城之西。其明年六月壬午,葬于眉之东北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先君先夫人墓之西北八步。轼铭其墓曰:
君讳弗,眉之青神人,乡贡进士方之女。生十有六年,而归于轼。有子迈。君之未嫁,事父母;既嫁,事吾先君、先夫人,皆以谨肃闻。其始,未尝自言其知书也。见轼读书,则终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后轼有所忘,君辄能记之。问其他书,则皆略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静也。从轼官于凤翔,轼有所为于外,君未尝不问知其详。曰:“子去亲远,不可以不慎。”日以先君之所以戒轼者相语也。轼与客言于外,君立屏间听之,退必反覆其言曰:“某人也,言辄持两端,惟子意之所向,子何用与是人言。”有来求与轼亲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与人锐,其去人必速。”已而果然。将死之岁,其言多可听,类有识者。其死也,盖年二十有七而已。始死,先君命轼曰:“妇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他日汝必葬诸其姑之侧。”未期年而先君没,轼谨以遗令葬之。铭曰:
君得从先夫人于九原,余不能。呜呼哀哉!余永无所依怙。君虽没,其有与为妇何伤乎。呜呼哀哉![3]卷62,1645
以上材料,可读到许多信息:
第一,王弗事公婆以“谨肃”闻,颇获公婆欢心。苏洵长年游学在外,轼母程夫人操持全家生计,兢兢业业,并主动负起了教育子女的任务。《宋史·苏轼传》载,轼“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4]卷338可见程夫人知书识礼、通于经史而以节慨大义教育子女。王弗随侍身旁,耳濡目染,多受教诲,同样以节慨仁义辅助夫君。所以,苏轼对于王弗的批评,不以为忤,而是欣然接受。于此可推见,少年夫妻之间,感情甚好,有商量,有争论,有交流,家庭生活和谐愉快。所以苏洵明白交代儿子,王弗与你是“艰难”与共的夫妻,故有“不可忘也”的遗训。
第二,王弗随时关注丈夫,曾多次批评苏轼交友过于随便,容易上当受骗。对阿顺取容之友,她从其“言辄持两端”,见其为人之不忠;对唯求亲厚者,看出了是利益所驱动,一旦形势有变,就会迅速叛去而化友为敌,岂可不防?王弗之言,后来不幸一一命中。在慎交友和谨言辞等方面,王弗所戒,正中丈夫“政治幼稚病”的软肋。可惜苏轼知其是而难于行。苏轼为人,豪爽慷慨而率情任性,公忠体国,正直而行,政治上只问是非而不顾党争,即使妻子一再劝诫也难以实行。在杭州任上,他就因过分相信朋友沈括而被新党告密迫害。人生路上,大多跌跌撞撞而悔之莫及之时才回想到妻言的正确。王弗陪伴苏轼读书,“则终日不去”,感情日进,知识日增,思维也日渐活跃,逐渐形成了东坡式的独立精神。以此,她并不一味温柔敦厚地驯服于男人,而是自由思考,以便能对丈夫事业有所助益。苏轼在墓志铭中就称颂夫人“其言多可听,类有识者”。所谓“有识者”,即指妻子具有自己的独立人格而不以阿世媚俗为容,是真正的贤妻。
第三,苏轼与王弗,良辰美眷,似水流年而伉俪情深,但却好景不长,为什么?除了身体有病的自然因素外,是否另有原因?苏轼是公认的天才,王弗与其相伴,应是幸福犹如春常在。但实际不然。从宋仁宗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结婚,到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五月,王弗二十七岁去世,她与苏轼共同生活了十一年。但实际上,夫妻离聚参半,王弗经历了许多艰辛的生活。结婚一年多,苏轼即被父携出游学,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正月游成都,三月离川赴汴京求取功名。家中一切交由程夫人及长媳王弗打理。苏洵《嘉祐集》曰:“洵离家时,无壮子弟守舍,归来屋庐倒坏,篱落破漏,如逃亡人家。”[2]354公公和丈夫长期在外,门庭破败,生计日艰,王弗这位长媳,上要侍奉年迈婆母,下要维持全家生活,身上重担,难以喘息,只能全力以赴,天长日久,积劳成疾,实属自然。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苏轼中进士,不久因母丧返蜀守丧,这才在悲伤中夫妻重会。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启程返京,买舟经长江三峡抵荆州,然后登岸陆行,于嘉祐五年抵汴京,一路携王弗随行,长子迈生于旅途,风尘仆仆,舟车劳顿,加以缺医少药,对于身体素质较弱的王弗来说就是折腾与考验。苏轼《出峡》诗曰:“入峡喜巉岩,出峡爱平旷”,“峡山富奇伟,得一知几丧”,“今朝脱重险,楚水渺平荡”。[3]卷1,23舟行出峡,惊心动魄。陆行车马,也是艰苦备尝。这对身怀六甲即将生子的王弗来说,于健康并非无碍。
家庭生活较稳定的时期,乃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苏轼应制科试后,朝廷授其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王弗随侍凤翔三年任满返京,苏轼仕途还算顺利,但在丈夫的上升时期,妻子隐约地感到了风险。苏轼初试高第,名动京师,其恩师欧阳修有“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之言,见《宋史》轼本传。当时苏轼年轻气盛,以为取青紫如拾芥耳。以此树大招风,多有忌而攻之者,其中包括王安石,曾几次在皇帝面前加以非议和批评。但苏轼仍然是诗酒高会,毫不在意。在凤翔签判任上,府主陈希亮曾加以裁抑,苏轼曾曰:“轼任凤翔签判日,为中元节假不过知府厅,罚铜八斤。”[2]283因不守规定而被府主判罚示戒。这是对少不更事、自由散漫行径的示戒。还朝后,又受抑于宰相韩琦,不让直升冒进。当时苏轼年轻躁动,交友轻信,政治就可能载觔斗。以此引发了年轻妻子的担忧,因而才有她批评丈夫的“类有识者”之言。小夫妻的和乐生活,甜尚未尝够,苦辣之味已来。这在王弗心理上,开始蒙上了一层阴影。王弗之所以早夭,除身体欠佳外,或有这方面的原因。
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王弗去世后十年,时苏轼知密州,写下了深切悼念亡妻的名词《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十年生死两茫茫”,词一开篇,即是呼天抢地、声嘶力竭的悲痛呐喊,真情喷发,犹如火山。词虽记梦,但上半阕纯是白描抒情,直抒胸臆。夫妻生死十年之别,并非短暂,但词人是一刻也不能忘怀。表面无言,却难掩内心的沸腾。“不思量,自难忘”,正说明是潜意识深处的激动和怀念,凄凉心潮中自有一股无法控制的真挚之情。词人假设,如果王弗还活着,这时相逢见面,还认得出昔日的丈夫吗?言外之意,自己在官场焦头烂额,已非昔日旧模样。当时苏轼只有四十岁,却已“尘满面,鬓如霜”。词人在这里假设王弗的“不识”,反思之深,心痛之巨,令人震撼。
下半阕记梦点题。王弗之坟,遵父嘱葬于故乡“眉之东北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距母坟西北八步,婆媳永远相依相伴。作词时东坡在密州,所以称“千里孤坟”。但时空距离,隔不断真情的思念,艺术想象的翅膀弥补了缺憾。“小轩窗,正梳妆”,多么温馨美好的回忆。但梦醒之后,却是阴阳两隔,徒唤奈何!“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不是无话可说,而是千言万语,齐涌心头,不知从何说起。因而只能以泪洗面,无限心事都在“无言”中,这是苏轼心底对王弗的深切思念。这首《江城子》,从情绪意境言,应属词家中的婉约一路;但词人在婉约深情之中,又独具嚎啕悲怆之巨痛,犹如大钟鸣鼓,捶击心胸,令人心灵震颤。若论其笔力风格,正是由深情婉约向豪放慷慨一派过渡的征兆。王水照、朱刚说:“熙宁八年冬天的一次打猎活动,使他有了第一首豪放词名作(按:指密州出猎的《江城子》)。”[5]69前一首“十年生死两茫茫”,正是很好的铺垫。
三、续弦夫人王润之
王润之(公元1048-1093年),蜀之眉州青神县人,字季章。王介幼女,系王弗堂妹。结婚时,苏轼三十三岁,始入中年,而王润之年方二十一,青春年华。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苏洵卒于京师,轼、辙兄弟扶父柩还蜀守丧。三年服除,苏轼因亲戚关系续娶王润之为妻,并于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还朝,携王润之同行。此次离蜀乃陆路,由成都至阆中,经凤翔、长安而抵汴京。舟行经三峡有风险,陆行同样是艰辛备至。苏轼曾回忆昔日旅途困况,作《和子由渑池怀旧》诗:“往日崎岖君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自注云:“往岁马死于二陵,骑驴至渑池。”二陵,当指崤山南北二陵,形势极为险要。王润之当时心怀对于京师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对于丈夫的才华充满信心和希望。遗憾的是,随着苏轼京师新生活大幕的拉开,带给王润之更多是忧虑与惊恐。
神宗熙宁、元丰年间,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在皇帝支持下,力推变法改革,而以司马光等为首的“反对派”则坚决反对变法,人称旧党。新旧党争,愈演愈烈,直至北宋灭亡而始休。苏轼也被卷进了这一狂潮。在京城,王润之很快就发现了丈夫在强烈的政治漩涡中浮沉挣扎。中年后,苏轼混合儒道释的思想理论,逐渐形成了睿智旷达的品格,来应对严酷的现实。苏轼即使主动请求离开京师而外放地方,仍然被新党政敌一路跟踪,其迫害之离奇残酷,无以复加,直至掀起了北宋最大的文字狱——乌台诗案。苏轼任通判杭州时,挚友文同送行诗有“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之句。[6]417又以“胡学士”指代表弟苏轼,作《寄题杭州通判胡学士官居诗》四首,其中第三首《方庵》诗又劝导:“众人庵尽圆,君庵独云方。君虽乐其中,无乃太异常?劝君刓其角,使称著月床。自然制度稳,名号亦可详。东西南北不足辨,左右前后谁能防?愿君见听便如此,鼠蝎四面人恐伤。”[7]5370的确如此。在新旧党争中,王安石本人固然清廉,但政治上却缺乏容人之雅量,急于变法成功,就以火箭速度迅速提拔了一大批官员来推行新法,组织上并不健全,一时当政队伍中混进了很多政治野心家,如吕惠卿、王珪、李定、舒亶之流都急于置苏轼于死地。可以说乌台诗案文字狱的发生是必然的,危机早已潜伏在苏轼身边。文同是旁观者清,他竭尽全力来挽救苏轼的政治生命,但无济于事,只能眼睁睁看着挚友被套进了罗网而难脱困厄。文同是士大夫中的智者,尚难援以手;王润之这个弱女子,自不待言。东坡后来贬谪再三,愈贬愈远。后来苏轼自嘲:“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8]142苏轼是哲人,能够超越自我苦难,他逐渐读懂了现实生活这本书,苦中作乐,不改其志,进一步把贬谪苦难转化为光辉的文学名篇,传之不朽。虽然王润之生活在他身边,却缺乏超脱智慧,文字狱带来的惊恐长期积压,因而先丈夫八年而亡。
苏轼在政治漩涡中跌打滚爬,尝尽滋味,于是借诗自嘲:“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3]卷6,112但王润之并非仅是“姓名粗记”而已。她不仅通诗书文墨,而且聪慧有智。据苏轼于黄州《与章子厚》信中说:“仆居东坡,作陂种稻,有田五十亩,身耕妻蚕,聊以卒岁。昨日一牛病几死,牛医不识其状,而老妻识之,曰:‘此牛发豆斑疮也,疗当以青蒿粥啖之。’用其言而效。勿谓仆谪居之后,一向便作村舍翁。老妻犹解接黑牡丹也。言此,发公千里一笑。”[3]卷101,2655据今中医药物研究,青蒿草含有青蒿素,具有抗菌消炎、排热解毒的功效。王夫人虽非兽医,却能疗牛之疾,保障了五十亩稻田的牛耕之劳。又据赵令畤(德麟)《侯鲭录》记载:“元祐六年,汝阴久雪。一日,天未明,东坡来召议事,曰:‘某一夕不寐,念颍人之饥,欲出百余石造饼救之。老妻谓某曰:‘子昨过陈,见傅钦之,言签判在陈赈济有功,何不问其赈济之法?某遂相召。’余笑谢曰:‘已备之矣。今细民之困,不过食与火耳。义仓之积达数千石,可以支散,以救下民;作院有炭数万秤,酒务有余柴数十万秤,依元(原)价卖之,二事可以济下民。’坡曰:‘吾事济矣。’遂草放积谷赈济奏。”[9]赈灾救民,人人有责。可见,王润之不因自己是女性而坐视不管,她是位关心百姓生活的知识妇女。她与苏轼的家庭生活可谓是相辅相成,其乐融融。她不仅在治家理政上有自己的见识,而且也有一定的文学解悟的修养。据《侯鲭录》卷四记载:“元祐七年正月,东坡先生在汝阴州。堂前梅花大开,月(按:原作“明”,讹)色鲜霁。先生王夫人曰:‘春月色胜如秋月色,秋月色令人凄惨,春月色令人和悦,何如召德麟辈饮此花下?’先生大喜曰:‘吾不知子亦能诗耶?此真诗家语耳!’遂相召与二人饮。用是语作《减字木兰花》词云。”(同上)东坡词《减字木兰花》(二月十五日夜,与赵德麟小酌聚星堂)曰:
春庭月午,摇荡香醪光欲舞。步转回廊,半落梅花婉婉香。 轻云薄雾,总是少年行乐处。不是秋光,只与离人照断肠。
《侯鲭录》作者赵德麟是当事人之一,所言真实性不容怀疑。此事广为流传,皆知王夫人润之颇有文学雅兴。于此可见,苏轼与王润之本是佳偶天成的一对,琴瑟和鸣。遗憾的是,在新旧党争漩涡中,苏轼迅即被卷入深渊而难以挣脱。《东坡志林》讲了苏轼在知湖州任被虎狼御史逮赴诏狱的故事:
真宗东封还,访天下隐者,得杞人杨朴,能为诗。召对,自言不能。上问:“临行有人作诗送卿否?”朴曰:“无有。惟臣妻一绝云:‘且休落托贪杯酒,更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上大笑,放还山,命其子一官就养。余在湖州,坐作诗追赴诏狱,妻子送余出门,皆哭。无以语之,顾语妻曰:“子独不能如杨处士妻,作一诗送我乎?”妻子不觉失笑。予乃出。[2]291
又苏轼《黄州上文潞公书》也描绘了自己被逮时的恐怖情景,给妻子和家人的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书曰:
轼始得罪,仓皇出狱,死生未分,六亲不相保……轼始就逮诏狱,有一子稍长,徒步相随。其余守舍,皆妇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书。州郡望风,遣吏发卒,围船搜取,老幼几怖死。既去,妇女恚骂曰:“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烧之。比事定,重复寻理,十亡其七八矣。[3]卷94,2439
在长期的贬谪苦难生涯中,苏轼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调和儒道释三教思想,吟诗著文,实现了智者的超越,而王润之却大受惊吓。因此,当苏轼回忆昔日夫妻恩爱时,一直内疚而觉得愧对妻子。其《予以事系狱……以遗子由》二诗中有“身后牛衣愧老妻”之句。[3]卷19,485《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诗更有“饮中真味志更浓,醉里狂言醒可怕。闭门谢客对妻子,倒冠落佩从嘲骂”之言。[3]卷20,497自己因文字狱而连累家人,受到妻子埋怨,事出自然。王润之的“嘲骂”,乃是希望丈夫能够认真地吸取教训,更好地活下去。可惜,王润之已然经不起折腾,不久便卒于京师。为了悲悼妻子,苏轼泪尽泣血,写下了《祭同安郡君文》:
维元祐八年,岁次癸酉,八月丙午朔,初二日丁未,具位苏轼,谨以家馔酒果,致奠于亡妻同安郡君王氏二十七娘之灵。呜呼!昔通义君,没不待年。嗣为兄弟,莫如君贤。妇职既修,母仪甚敦。三子如一,爱出于天。从我于南,菽水欣然。汤沐两郡,喜不见颜。我曰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须,弃我而先。孰迎我门,孰馈我田?已矣奈何,泪尽目干。旅殡国门,我实少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呜呼哀哉![3]卷111.2991
祭文中通义君指前妻王弗,生了大儿子苏迈,不久而亡。作为继室,王润之又生了二儿迨、小儿过。她心胸开阔,三个儿子一样疼爱。在古代,后母苦毒前妻所生子女的故事很多。但王润之反之,“三子如一,爱出于天”,充满了母爱精神,乃天性使然。这就为丈夫排除了后顾之忧。“从我于南,菽水欣然”,南贬黄州的五六年间,与丈夫同甘共苦。如果妻子天天埋怨缺柴少米,整天哭啼吵骂,东坡还能保持其“回也不改其乐”的人生之境吗?他还有机会和朋辈相聚,醉酒狂欢,挥洒诗词歌赋文章吗?有时苏轼一高兴,深更半夜带朋友回家,向妻子呼酒索食。王润之就把平日所藏美酒家酿,献出招待,尽欢而散。明瞿佑《归田诗话》卷中有《与李之仪简》条,载东坡诗云:“‘小儿不识愁,起坐牵我衣。我欲嗔小儿,老妻劝儿痴。儿痴君更甚,不乐复何为?还坐愧此言,洗盏当我前。大胜刘伶妇,区区为酒钱。’其旷达如此。又《与李之仪小简》云:‘伏惟起居佳胜,眷聚各安庆。无他祝,惟保爱之外,酌酒与妇饮。’”[10]1254刘伶是晋时记载于《世说新语》中的嗜酒任诞之士,妻子要他戒酒。可是王润之待东坡正相反,出酒洗盏,助他与客饮酒为乐。旷达的东坡,如果没有贤妻支撑,能旷达得了吗?因此,苏轼很骄傲地对人宣示“妻却差贤胜敬通”。敬通,即东汉时冯衍,妻妒。所以东坡有《题和王巩六诗后》释曰:“仆文章虽不逮冯衍,而慷慨大节乃不愧此翁。衍逢世祖(按:指刘秀)英睿好士,而独不遇,流离摈逐,与仆相似。而衍妻悍妒甚,仆少此一事,故有‘胜敬通’之句。”[3]卷116,3157冯衍妇妒,“后院”失火,故有顾此失彼之恨。东坡则胜之多多,贤妻在家,为自己排忧解难,何其幸哉!妻贤子孝,给苏轼细心的照顾和极大的精神慰藉,从而成为文坛的一代天骄,其中三位妻侍是有一定的功劳和贡献的,包括侍妾王朝云。王润之卒于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第二年苏轼即贬惠州,东坡独携王朝云及幼子过赴岭南贬所生活。
四、侍妾王朝云
王朝云(公元1063-1096年),字子霞,钱塘(今杭州)人。熙宁元年(1074年)苏轼任杭州通判,买了四个侍婢教习歌舞,王朝云在其中。许多笔记小说,都说此年苏轼纳朝云为妾。此说实误,因为当时朝云是年仅十二岁的孩童。纳妾当在她十六七岁长成少女以后才有可能,具体时间待考。又《燕石斋补》称朝云是当时的“钱塘名妓”,这是小说家言,尤不足信。四个侍婢中,朝云聪慧秀美,能歌善舞,颇得苏轼欢心。东坡喜茶,常以茶待客,若是贵客,则出上等密云龙茶招待。如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人称“苏门四学士”,得意门生上门,苏轼必出密云龙茶。据明袁中道《次苏子瞻先后事》记载:“茶有密云龙者,最甘馨。四人每来,必令侍儿朝云取密云龙。家人以此知之。”[2]243雅士美茶,书房中畅饮高论,朝云侍坐服务,何等风雅之事。这说明了四侍儿中,朝云最善解人意,逐渐超越侪辈。她对东坡尽心尽责,细致观察身边的一切,有所思考,见识日增甚或有所建言。这既是环境使然,更与朝云的用心与努力上进有关。苏轼曾戏称朝云为“老云”。[2]337南宋陆游《注东坡先生诗序》,曾感叹苏诗内容丰富厚重,一时难以尽解。所以当时范至能劝他注苏诗时,“游谢不能”,不敢承命。序中举例曰:“‘白首沉下吏,绿衣有公言’,乃以侍妾朝云尝叹黄师是仕不进,故此句之意,戏言其上憯,则非得于故老,殆不可知。必皆如此,然后无叹。”[1]428黄师是,名寔。他是苏辙的儿女亲家,东坡亲戚。曾相继提点梓州路和两浙刑狱。他因得罪权贵,林希沮之,难于升迁。据施注:“先生侍儿尝问:‘朝之诸公,迁擢不淹时。独黄师是,昔为提刑,今又提刑,何也?’先生大笑,方作诗送之,故云‘绿衣有公言’。”[3]卷36,916绿衣之典,出自《诗经·邶风·绿衣》篇,指侍妾,用以称朝云。于此可见,朝云在先生身边可以自由发言,颇有见识。所谓“公言”,即指朝云分析,一语中的,堪称公论。元祐朝,苏轼较顺遂之时,朝云明白东坡不会为安享富贵而箝口不言。东坡忧国忧民,忠亮正直,不可能做明哲保身的乡愿。忠谏直言,勇于担当,方是苏轼本色。宋人费衮曰:“东坡一日退朝,食罢扪腹徐行,顾谓侍儿曰:‘汝辈目道是中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为然。又一人曰:‘满腹都是机械。’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乃曰:‘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坡捧腹大笑。”[11]第一个侍儿称他满腹诗书文章,第二个会儿称他满肚子智慧机巧,东坡都不以为然。只有朝云知面更知心,一语道出了先生的秘密,直揭其精神本质。这才是画龙点睛之言,所以东坡“捧腹大笑”,欣然接受。
元祐三年苏轼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时高太后召见宣谕之曰:“内翰直须尽心官家事,以报先帝知遇。”命撤御前莲烛送苏轼归院。[1]459东坡为人公忠体国,法只问是非,而不论其新旧。他虽反对王安石推行新法,但实事求是,并不全然否定新法某些正确的地方。如王安石的免役法,当司马光想全部推翻而恢复旧的差役法时,东坡就成为神宗皇帝和王安石推行新法的辩护人,与司马光廷争面红耳赤,直呼司马牛而不少让。因此,不仅新党之人打击他,旧党之人对他也多加排斥。政治上,左右不讨好,正可见其为国为民的初心。如果苏轼善于察言观色,阿谀奉承,以人主权相之言为是非,那么以他的才华自然仕途飙升,宰辅三公之位可待。但这就不是今天人们所熟知的苏轼了,岂能传之千秋万世而不朽。他甘愿外放远贬,也不放弃忠谏直言。他的坎坷人生,正是祸从口出,这是因为其本性所决定的。朝云谑称其“一肚子不合时宜”,虽为戏言,却读懂东坡之心。
朝云之言,既是提醒,又是示警,正体现了她准备与自己心仪偶像共赴险难的决心。四个侍儿,三个先后离去,唯朝云不离不弃,随侍在侧。苏轼有《朝云诗》(并引),引曰:“世谓乐
天有鬻骆马放杨柳枝词,嘉其老病,不忍去也。然梦得有诗云:‘春尽絮飞留不住,随风好去落谁家?’乐天亦云:‘病与乐天相伴住,春随樊子一时归。’则樊素竟去也。予家有数妾,四五年相继离去,独朝云者,随予南迁。因读乐天集,戏作此诗。朝云姓王氏,钱塘人,尝有子曰干儿,未期而夭云。”诗曰:“不似杨枝别乐天,恰如通德伴伶玄。阿奴络秀不同老,天女维摩总解禅。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衫歌扇旧因缘。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阳云雨仙。”[3]卷38,965如诗所述,朝云随先生南贬,侍奉汤药、同诵佛经是她的“新活计”,尽量给苏轼以生活照顾和感情温暖。“不作巫阳云雨仙”,用宋玉赋典,说明朝云具仙风道骨,在精神上给予先生慰藉。“逐我三山去”,可见并不视朝云为普通侍妾,而是生死与共的贴心人。秋去冬来,风雨与共,东坡是真心爱护朝云,其炽然之情,并不减于前面两位夫人。在黄州贬所,朝云生儿苏遯,小名干儿,活泼可爱,可惜早夭,朝云痛不欲生,东坡也为之伤心落泪。东坡作诗二首哭悼干儿,诗前小序:“去岁九月二十七日,在黄州,生子遯,小名干儿,颀然颖异。至今年七月二十八日,病亡于金陵,作二诗哭之。”诗曰:
其一
吾年四十九,羁旅失幼子。幼子真吾儿,眉角生已似。未期观所好,蹁跹逐书史。摇头却梨栗,似识非分耻。吾老常鲜欢,赖此一笑喜。忽然遭夺去,恶业我累尔。衣薪那免俗,变灭须臾耳。归来怀抱空,老泪如泻水。
其二
我泪犹可拭,日远当日忘。母哭不可闻,欲与汝俱亡。故衣尚悬架,涨乳已流床。感此欲忘生,一卧终日僵。中年忝闻道,梦幻讲已详。储药如丘山,临病更求方。仍将恩爱刃,割此衰老肠。知迷欲自反,一恸送余伤。[3]卷23,592
东坡晚丧幼子,夫妻同悲,哭念亡儿,实是偏怜其母,情真意切,感动天地。朝云丧子之后,“一卧终日僵”,郁郁寡欢,健康日亏,身体大不如以前。自元祐八年王润之夫人去世后,苏轼家中折了擎天一柱,于是朝云自觉挑起“另一半”的重担。绍圣元年六月,苏轼谪惠州,朝云不顾自己身体状况,毅然随其南行。古时岭南乃烟瘴蛮荒之地,韩愈曾有“好收吾骨瘴江边”之叹。朝云自愿远投蛮荒,需要怎样的决心和勇气。于此可见为了东坡,朝云做好了付出一生的准备。丈夫那“一肚皮的不合时宜”,生还中原的希望渺茫,朝云内心隐隐作痛,这才有在惠州唱东坡乐府《蝶恋花》(花褪残红)的故事发生。词曰: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12]
龙榆生《东坡乐府笺》附录引《林下词谈》曰:“子瞻在惠州,与朝云闲坐。时青女初至,落木萧萧,凄然有悲秋之意。命朝云把大白,唱‘花褪残红’。朝云歌喉将啭,泪满衣襟。子瞻诘问其故,答曰:‘奴所不能歌,是“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也。’子瞻幡然大笑,曰:‘是吾正悲秋,而汝又伤春矣。’遂罢。朝云不久抱疾而亡,子瞻终身不复听此词。”[3]卷23,404
朝云初到苏家是不识字的女童。侍东坡日久,见其读书,日渐浸染,不仅粗通文字,而且写楷法有模有样,对诗词情境也有一定的领悟。“枝上柳绵吹又少”,正是一种春去也、无计留春住的伤春之感。人生如驶,功业付之东流,又将奈何!“天涯何处无芳草”,东坡那“一肚皮的不合时宜”,恰如离恨春草,渐行渐远还生,哪里才是尽头呢?朝云唱到此句,不禁悲从中来,哽噎难当。这就引发了苏轼的“悲秋”“伤春”之言。以此,朝云卒后,东坡一生不唱“花褪残红”的《蝶恋花》,正可见二人的感情共鸣。
可见,东坡与朝云早已突破了主仆之分,成了相互照顾的终身伴侣。在东坡眼里,朝云不仅外貌姿容美,其内在心灵更美。苏轼一生写了许多纪念朝云的文学作品,正是彼此真情的结晶。据龙榆生称引《艺苑雌黄》曰:“东坡尝令朝云乞词于少游,少游作《南歌子》赠之云:‘霭霭迷春态,溶溶媚晓光。不应容易下巫阳,只恐翰林前世是襄王。暂为清歌住,还因春雨忙,瞥然归去断人肠,空使兰台公子赋高唐。’”[3]卷23,313秦观以巫山神女会襄王,比喻苏轼与朝云,其赞美之情溢于言外。但与苏轼之作相比,尚是隔了一层。东坡词《殢人娇》曰:
白发苍颜,正是维摩境界。空方丈,散花何碍。朱唇筯点,更髻鬟生采。这些个,千生万生只在。
好事心肠,著人情态。闲窗下、敛云凝黛。明朝端午,待学纫兰为佩。寻一首好诗,要书裙带。[3]卷23,312
据王文诰《苏文忠诗编注集成总案》卷39,此乃《绍圣二年乙亥五月四日赠朝云〈殢人娇〉词》。诰案曰:“公与张耒书云:‘某清净独居一年有半尔。已验之方,思以奉传。’读此词,知其无诳语也。”[13]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苏轼已是花甲之翁,多独宿养生,所以他与朝云重在夫妻的感情交流。“敛云凝黛”“维摩境界”,正见朝云的端庄肃穆,以此生出了仙女侍坐而“散花何碍”之句,佛典用得非常贴切。“朱唇筯点,更髻鬟生采”,可见典型美人风采,惊为天仙。“千生万生只在”,朝云之美,永留脑海。但重要的不仅是外貌之美,更是内在精神之美。他与朝云终日闲坐相对,心心相印。他希望朝云学屈原,“纫兰为佩”,芳香高洁,永留人间。“寻一首好诗,要书裙带”,朝云之美,值得向世人一展风采。在《殢人娇》词,先生柔情,朝云心醉。
绍圣三年春天某日,朝云诞辰,苏轼为作《王氏生日致语口号》:“人中五日,知织女之暂来;海上三年,喜花枝之未老。事协紫衔之梦,欢倾白发之儿。好人相逢,一杯径醉。伏以某人女郎,苍梧仙裔,南海贡余。怜谢端之早孤,潜炊相助;叹张镐之没兴,遇酒辄欢。采杨梅而朝飞,擘青莲而暮返。长新玉女之年貌,未厌金膏之扫除。万里乘桴,已慕仲尼而航海;五丝绣凤,将从老子以俱仙。东坡居士,罇俎千峰,笙簧万籁。聊设三山之汤饼,共倾九醞之仙醪。寻香而来,苒天风之引步;此兴不浅,炯江月之升楼。”诗云:“罗浮山下已三春,松笋穿阶昼掩门。太白犹逃水仙洞,紫箫来问玉华君。天容水色聊同夜,发泽肤光自鉴人。万户春风为子寿,坐看沧海起扬尘。”[3]卷46,1146王文诚案曰:“绍圣三年春中为王子霞作。时唯子霞从公南迁,居惠三载。此因子霞生日而作。子霞是年三十四,至七月而病没,并未生子。观口号不及生子,而以为寿作结,信为生日之词矣。各注皆作生子口号,本集亦作生子致语口号,并误。今改定。”按王文诰之说是。“海上三年”,正合朝云随东坡贬惠三年的生活。朝云生子是在黄州时,未期而夭。诗中“万户春风为子寿”者,岭南有万家春酒,故用为祝寿吉语。但朝云在当年七月病亡,破碎了东坡的祝寿心愿。东坡为之痛哭落泪,时加悼念,曾作《西江月》词:
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么凤。 素面翻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3]卷23,314
王文诰案:“丙子十月梅开作。”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称引《冷斋夜话》曰:“东坡在惠州,作梅词,时朝云侍儿新亡,其寓意为朝云作也。”[3]卷23,314-315考绍圣三年七月五日,朝云死,十月,东坡作此《西江月》(梅),运用传统香草美人比兴艺术,以梅喻人,人梅合一,不仅写姿容,更见其冰肌玉骨之高洁风神。这是东坡对朝云的心灵评价,朝云是他心中最为圣洁的美好思念。古代岭南,烟瘴弥漫,是贬谪士人的九死一生之地。王润之于元祐八年去世,东坡终不再娶,日与朝云为伴。朝云也不离不弃,随先生万里投荒,忠心一片。这怎能不让多情的东坡感动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朝云虽逝,但却永远活在东坡心中,具有了永久的生命,并随《东坡乐府》传之不朽。
朝云去世后,东坡又作《丙子重九》诗二首,其一:“三年瘴海上,越峤真我家。登山作重九,蛮菊犹未花……亦复强取醉,欢谣杂悲嗟。今年吁恶岁,僵仆如乱麻。此会我虽健,狂风卷朝霞。使我如霜月,孤光挂天涯。西湖不欲往,墓树号寒鸦。”[3]卷40,1020查注曰:“朝霞,借以言朝云也。”施注曰:“朝云葬栖霞寺,墓在西湖上。”青灯直对,黯尽孤眠滋味。痛失朝云,心中滴血,哀乎惨哉。又作《朝云墓志铭》:“东坡先生侍妾朝云,字子霞,姓王氏。钱塘人。敏而好义,事先生二十有三年,忠敬若一。绍圣三年七月壬辰,卒于惠州,年三十四。八月庚申,葬之丰湖之上栖禅山寺之东南。生子遯,未期而
夭。盖常从比丘尼义冲学佛法,亦粗识大意。且死,诵《金刚经》四句偈以绝。铭曰:浮屠是瞻,伽蓝是依。如汝宿心,惟佛之归。”[3]卷62,1647盖棺论定,取信鬼神苍天,纯出于一片真心。依照古代封建礼制,东坡是主,朝云仆妾,地位悬隔。但东坡却视朝云为自己晚年生活的另一半,平等对待,相亲相爱。在两位王夫人去世后,日与朝云相依为命。墓志之作,严肃之言,岂偶然哉?“敏而好义”“忠敬如一”,是极高的人格评价。如果不是心心相印,说不出这样的话来。不久,又作《悼朝云》(并引),其引曰:“绍圣元年十一月,戏作《朝云诗》。三年七月五日,朝云病亡于惠州,葬之于栖禅寺松林中东南,直大圣塔。予既铭其墓,且和前诗以自解。朝云始不识字,晚忽学书,粗有楷法。盖尝从泗上比丘尼义冲学佛,亦略闻大义。且死诵《金刚经》四句偈而绝。”诗曰:“苗而不秀岂其天,不使童乌与我玄。驻景恨无千岁药,赠行唯有小乘禅。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归卧竹根无远近,夜灯勤礼塔中仙。”[3]卷40,1019惠州谪地,条件极差,加以内在心理备受压抑,心爱之人一病不起,岂偶然哉?“驻景恨无千岁药,赠行唯有小乘禅”,世上岂有千年不死灵药救生!家贫如洗,送行只能用《金刚经》陪葬,给予精神解脱之安慰。斯人云逝,人何以堪,情种正是天才之苏轼。从这方面言,朝云何其幸哉!
五、结语
苏轼一生的三位妻侍,正式名号是二妻一妾,从今天的平等观念、人性视之,皆是他生活中的另一半。三位女性,同样都热爱着苏轼,家庭生活可谓琴瑟和鸣,其乐融融。结发伉俪王弗,少年夫妻,与丈夫离聚参半,代丈夫持家侍奉公婆,毫无怨言;续弦王润之,在丈夫外任职密、徐二州时,正遇特大天灾,府无存粮,只能采杞菊野菜充饥裹腹。随贬黄州,如苏轼《致章子厚》信中言,是“身耕女蚕”,同甘共苦,不改其志。至于侍妾朝云,随先生宦海沉浮,家中仆侍,先后离去,但朝云却立志甚坚,不离不弃,终生相伴,给先生精神慰藉与生活的悉心照顾。东坡自嘲,一生功业在“黄州、惠州、儋州”,巨大的政治风波,宦海沉浮,贬谪流放,艰辛备尝。三位妻侍都与东坡有共同语言,有感情交流,思想品格都值得称赞,对苏轼的生活和创作也都有各自的贡献。
苏轼天赋异禀,然而宦海沉浮,也将忧患带给其妻侍。当他在知湖州任上被逮诏狱时,一家老小受尽惊吓,妻子王润之尤甚。现实残酷,但一时还压不垮爽朗旷达的苏东坡,他以圣贤睿智,苦中作乐,笔耕不辍;但作为他生活的另一半,王润之除了承受生活重担之外,则是饱受煎熬。颜中其《苏东坡年表》于元符三年记载:“苏轼窜流岭海,前后七年,契阔死生,丧亡九口。”面对此情此景,谁能无动于衷?苏轼曾写《超然台记》,但面对丧亡相继的滴血人生,即是圣者贤者,亦难以超然待之。后来,苏轼虽然遇赦渡海北归,但很快逝于常州城中。疾病当然是主要原因,此外苏轼身边命运攸关、荣辱与共的三位妻侍之死以及生活的重压也是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