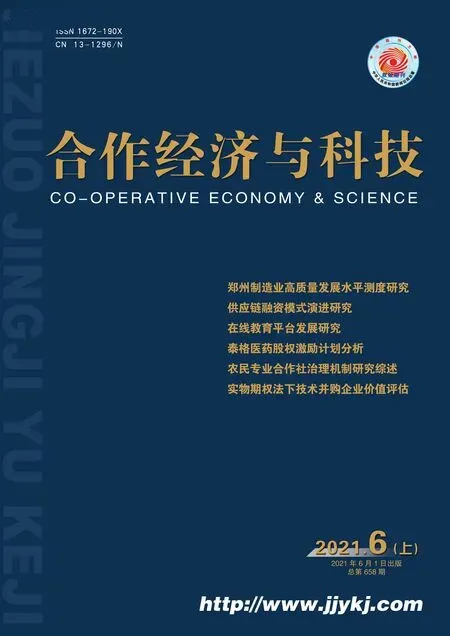零工劳动市场评价制度研究
□文/马瑞婷
(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成都)
[提要]21世纪以来,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互联网技术的应用造就新型用工模式零工经济的发展,“劳动”这一生产要素的内涵也在技术推动下不断丰富。多样选择、灵活高效的零工用工模式取代长期合同聘用制,为劳动者提供弹性就业的新方式,满足劳动者的主体需要;对雇佣企业来说,零工劳动帮助节约人力资源成本,增加企业的经济效应。从表面上看,零工劳动实现双赢,但实际上零工劳动者仍然面临诸多问题。为此,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保障零工劳动的市场评价和按贡献分配的机制建设,就必须从零工劳动的全过程出发,从事前、事中、事后三个方面保证零工劳动者的公平,促进零工经济的发展。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深化改革,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即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同时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贯彻落实这一制度安排,关键是要回到马克思的理论传统,“从现实的生产活动中理解劳动这个生产要素”,历史地、具体地把握劳动的样态和市场的形式。21世纪以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入发展,引起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一是基于大数据技术的互联网平台组织大量出现,成为“数字经济循环的中介”;二是随着零工经济的快速发展,长期合同聘用制劳动逐渐被零工劳动所替代;三是市场结构从传统的“卖方市场”、“买方市场”的单边市场,日益发展为双边市场。这些变化深远影响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生产要素报酬的形成机制,是完善这一制度安排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一、基于数字平台的零工经济的形成
(一)零工经济的由来。零工经济最早起源于美国,“通常指已有特定技能并独立自主的普遍的自由职业者作为劳动力市场参与主体,注重工作结果,以项目付酬的经济工作模式”。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美国经济陷入“滞胀”阶段:企业倒闭,工人面临失业威胁;美元贬值,在职工人工资水平不断下降,大量企业开始雇佣临时工进行生产。“临时兼职工作者”成为零工经济的最早雏形。在这此后的30年,尽管传统就业模式仍占主流,但零工经济的规模也在随着时间不断扩大。
(二)基于数字平台的零工经济的形成。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涌现,催生了“以收集、处理并传输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信息活动的一般性数字化基础设施即数字平台。数字平台以双边市场作为支撑。双边市场的外部性即平台的交易量与加入平台的双方呈现正相关并且“其中一方的收入取决于加入平台的另一方的数量”将大量用户都纳入了数字平台。以亚马逊为例,亚马逊为消费者和生产者提供了交换平台,生产者数量增加会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物美价廉的商品,消费者数量增加会带来更多的潜在客户。数字经济下,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即双边市场的主体通过用工数字平台进行信息的实时高效交换,造就了以数字平台为中心的零工经济的蓬勃发展。根据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未来三年间零工经济的年均复合增速将保持10%~15%。
二、零工劳动按市场评价贡献的不足之处
零工经济为零工劳动者和企业带来了双重经济效应。从劳动者主体看,零工经济为劳动主体提供了弹性就业的新方式,劳动者可以根据自身偏好自主选择工作地点、工作方式、工作内容,不受传统工作的界限束缚。从劳动力需求方来说,零工经济满足了企业的短期用工需求,企业可以根据用工需要调整就业和工资水平,降低生产成本。但值得关注的是,零工经济是“基于互联网数字平台对于供求的大规模匹配”。数字平台在零工经济中充当着中介作用。当用户数量和资金总量达到了一定规模时,数字平台便依靠自身的技术优势和信息垄断,以排他性的竞争方式获得了垄断地位,攫取了垄断利润。数字平台的天然垄断性迫使零工劳动者在交换中处于不平等地位。
(一)零工劳动者的生存状况。作为零工经济的主体,零工劳动者通常根据平台企业发布的信息,以任务为导向按需工作,看似“灵活高效”、“独立自由”,实际上,零工劳动者的生存境况却差强人意。
第一,收入低,具有不稳定性。除个别劳动者以外,大多数零工劳动者的收入低于同学历的合同制劳动者。以某网约车平台为例,调查显示“网约车司机每月平均总收入11,446元(已扣除平台抽成),每小时净收入平均为27.4元”。从表面上看,网约车司机的收入高于最低工资标准,实际上,网约车司机需要承担汽油费以及其他所有耗费。和一般用工模式不同,零工经济的生产资料归零工劳动者所有,要进行再生产活动,就必须对生产资料的耗费进行补偿。零工劳动者在扣除必要劳动资料的价值后,实际收入远低于正常工资标准。
第二,工作时间过长。从事零工的劳动者大体上可划分为两类:一是高技能劳动者;二是低技能劳动者、全职零工者。高技能劳动者凭借自身拥有的丰厚知识、独特技能可取得较高的工资收入。但低技能劳动者、全职零工者却只能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增强劳动强度等方式增加收入。根据对某网约车平台调查,“25%的全职司机平均每天工作12.3小时,每周工作6.6天;58.9%的兼职司机平均每天工作11.4小时,每周6.3天”。与“996”模式相比,零工劳动者的平均工作时间更长、工作强度更大。在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模式下,零工劳动者的收入却令人唏嘘。“25%的全职司机对收入满意度最低;56.1%的司机对收入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58.9%的兼职对收入的满意度较低”。
第三,社会福利机制缺乏。根据《劳动法》,雇佣企业须为劳动者购买社会保险以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零工经济下,零工劳动者的“独立承包商”角色,帮助企业规避了传统的用工职责,企业无需为零工劳动者购买任何法律规定的社会保险。同时,零工劳动者以“个人”生产者身份参与零工活动的,分散性的群体特点也使工会保护无法触及。
第四,立法层面空白。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劳动关系一经认定,用工单位就必须承担相应的用工责任。“因为现有劳动法基本上采取了全有或全无的劳动关系认定框架,并以此来施加或者豁免劳动关系中的所有责任”。零工经济下,零工劳动者和企业签订的是临时用工合同,这些合同对用工关系的模糊界定,使零工劳动者无法得到应有用工保障。
(二)零工劳动者按市场评价贡献不足的原因。市场经济中,资源的配置与利用必须以市场价值作为重要评价基础。“市场价值是决定市场分配的根本行为准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交换要以市场贡献率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零工劳动者创造了物质财富,但在交换中他们却处于不利地位。归其原因,关键在于“劳动”这一生产要素,并没有按照其创造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价,即没有按照零工经济需求方的评价决定零工劳动者的贡献。究其原因,关键在于数字平台组织。平台组织是导致交换不平等的根本因素。平台组织依靠自身的信息垄断隐晦实现了对零工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占有。在平台创立初期,通常采用“双补贴”机制,在“虹吸效应”下,平台的人数和交易额迅速增长。随着市场份额的逐步扩大,平台组织开始占据垄断地位并采取“双收费”策略。以网约平台为例,该平台中介服务费高达18%。在平台组织下,以需求为主的收入变为了以平台为依附的收入,等价交换的原则遭到了破坏。除此以外,大部分平台组织的资本组成以私人资本为主,他们对利润的迫切追逐也使零工劳动者更加处于不平等境地。
三、完善零工劳动的市场评价和按贡献分配的制度研究
零工经济下“劳动不再被视为体现专业技能的工作,而是随机和仆役的差事”。完善零工劳动的市场评价和按贡献分配的制度,关键在于扭转零工劳动的不公平交换。这就需要从事前、事中、事后三个方面即“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分配公平”三个角度来保障零工劳动者的平等地位,促进零工经济的良性发展。
(一)确保零工劳动者权利公平。“美国法律提出要在制度层面建立‘共同雇主’的责任模式,保护零工劳动者可以向所有雇主追究责任”。“在英国,国会正在准备立法规定零工经济劳动者的最低时薪”。在我国,关于零工立法层面仍处于空白。要保护零工劳动者,立法机构要根据新形势需要研究这种新型的劳动关系,为零工劳动者制定统一的法律标准。法律层面完整,让零工劳动者有了保护自身权益的武器,也让处理零工纠纷时有了严格的衡量标准,真正可以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保证零工劳动者的权利。
(二)确保零工劳动者机会公平。零工经济下“平台积极地制定规则,利用平台的直接数据,对零工劳动者进行严格的挑选和监督”。平台组织作为零工经济的主要参与者,有义务保护零工权益。数字平台组织要积极建立商业保险。“根据零工工作特点和需求,以更灵活的保险方式来保障用工过程的安全”。同时,政府作为监管主体,要对平台组织进行全面量化考核,对违反市场准则的行为要采取“罚款、整顿、休业”等措施。
(三)确保零工劳动者分配公平。零工经济下,零工劳动者成为了平台组织的后备军,激烈的行业竞争让零工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不断下降。要保证零工经济的收入公平,就必须坚持以市场分配为根本,将市场贡献作为分配的根本标准。初次分配中,要以市场贡献为准则提高零工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增加零工劳动者的奖金收入,推动建立零工工资保障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保护零工劳动者的合法收入。同时,要为零工劳动者购买社会保险,保障零工劳动者享有基本的社会福利。要注重分配的效率与公平,完善相关政策手段;要加大再分配过程中的资金投入力度,要积极将零工劳动者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提高零工劳动者在医疗保险等社会公共政策中的比重,促进零工经济的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