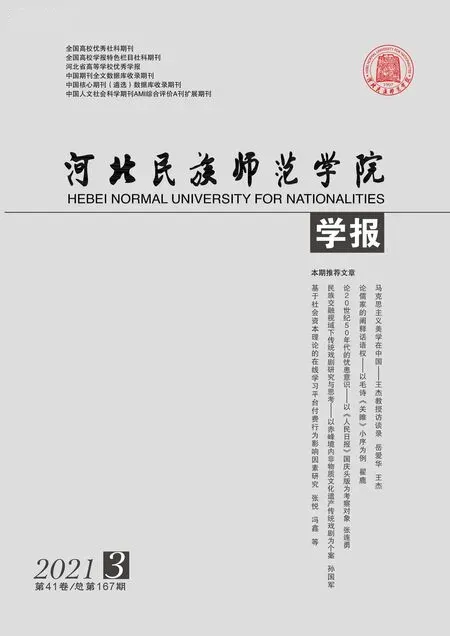传媒时代语-图时空范式变化研究
王 妍
(合肥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语言艺术和图像艺术的区别,曾被莱辛在《拉奥孔》中明确而详细地论述过,其关于诗画界限的论述,核心就是,诗(语言艺术)是时间先后承续的艺术,而画(图像艺术)是空间整体并列的艺术。随着当代传媒社会图像技术的飞速发展,图像艺术在现代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传媒时代,“是指传媒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渐突出,尤其是数字媒介和电子媒介给人类带来巨大变化的时代。”[1]1传媒时代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由于电子屏幕的增加,人们越来越多地依赖视觉和图像接收信息,“在艺术和文化领域的‘视觉的’和‘图像的’转向问题是哲学和社会理论中展开的众多讨论和出版物的主题。”[2]2加之被许多后现代理论所揭示出的,当代社会的“超空间”趋势,使得莱辛所在的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下的传统时空范式和诗画观已无法解释当下新变化的语言艺术与图像艺术。传媒时代,信息交流广泛而频繁,语言和图像艺术相互影响借鉴,传统的时空观受到动摇,以时间为主导的语言文本中,时空关系已不如从前那般呈现出内在的同质性和稳定性,时空联系更加变幻不定、复杂莫测。
莱辛关于语-图时空范式的观点,彰显着德国18世纪进步的现实主义文学的繁荣,有其时代的逻辑和烙印,因此,要想深入思考当代语-图时空范式较之传统观点的变化,需要首先分析莱辛诗画观背后所包含的历史逻辑。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至今日的传媒时代,其中历史逻辑本身的嬗变,则是语-图时空范式变化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
一、时空的二元分化
莱辛的“诗画界限”观为艺术创作与鉴赏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作为18世纪的德国启蒙主义者,他所提倡与批判的观点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一些现实目的。正如朱光潜所说,莱辛的“一切论点都在说明诗的优越性”,[3]232而且,他“毕生大部分精力都花在建立市民剧方面”。[3]237莱辛的理论和实践打上了德国启蒙运动的时代烙印,其诗画界限说需要为其宣扬启蒙人生观的市民戏剧服务。“这里的区别骨子里就是静观的人生观和实践行动的人生观之间的区别。”[3]232莱辛的人生观是运动的、发展的,体现在《拉奥孔》中,便是对行动性和情节性的追求。
诸多关于艺术的理论性思考,深层次都与历史文化背景紧密联系,不论是诗与画的界限问题,或者是语言、图像艺术区分问题。米歇尔也说:“空间和时间范式从来就不是清白的,它们始终携带着意识形态的分量,而这最突出地表现在这个问题的源出文本,莱辛的《拉奥孔》。”[4]123莱辛认为,诗只能模仿时间承续的行为,图像艺术则模仿空间静止的对象,诗再现静止空间以及绘画再现行为都是极为困难的。然而,即使是在莱辛所在的18世纪欧洲,语言艺术爱好描写,“堕落”为文字式的绘画,或者绘画侵入文字的领域,显示出叙事的功能,这些现象都是极为常见的,这也是莱辛所反感并转而强调“诗画界限”的出发点。但换个角度来看就是,诗与画的时空界限,并不是诗很难再现空间、画很难再现时间,反而是这种现象太容易发生了。莱辛不惜将空间范式留给图像艺术,把“静穆”这一温克尔曼所提倡的艺术理想限定在造型艺术的领域中,而让诗专注于表现时间范式,并以此来突显诗的优越性。绘画与空间,在与时间及诗的比较中无形地被降低了地位。莱辛明白,绘画具有鲜明的优点,它直观、生动、给人在场的幻觉。从古至今,许多时代对绘画给予限制,希腊人制定出抵制“讽刺漫画的法律”,“命令艺术摹仿事物要比原来的更美”。[5]12莱辛并不排斥这些做法,他像柏拉图将荷马驱逐出理想国一样,认为绘画,“特别是造型艺术,除掉它们能对民族性格发生不可避免的影响之外,还可以产生一种效果,是必须由法律严格监视的。”[5]13莱辛意识到,造型艺术能激发起非理性的,无意识的力量,使人陷入某种“物恋”的情结中,因而他说:“我们近代人认为母亲的温柔的想象力仿佛只能表现为牛鬼蛇神”,[5]14感性的、女性化的、非理性的想象思维往往表现为图像和造型画面。由此,在米歇尔看来,表面上看起来属于艺术方法论层面的“诗画界限”观,实则包含了美与崇高、沉默与雄辩、眼与耳、身体与精神、外部与内部,乃至女性与男性、理性与非理性的二元区分。“与女人一样,理想的绘画是沉默的,是为满足眼的快感而设计的美的造物,男性诗歌艺术的崇高的雄辩相对立。绘画局限于身体外部展示及其装饰空间的狭小领域,而诗歌则自由安排一个具有无限潜能的行为和表现的领域,即时间、话语和历史的领域。”[4]139语言与图像艺术在时空范式中并非天然具有明显的区分,二者的交叉是极易发生的现象,正因如此,莱辛“出于理性探讨了对形象的恐惧,这种恐惧可见于从培根到康德到维特根斯坦的每一位重要哲学家,不仅仅是对异教‘偶像’的恐惧,或对庸俗市场的恐惧,而且有对渗透到语言和思想之中的偶像的恐惧”。[4]143时空范式被人为地分化开来,并被分别纳入语言艺术与图像艺术中,潜在地进行带有意识形态的二元比较。然而,随着20世纪新思想新技术的发展,时空二元对立的传统历史逻辑不断受到挑战与冲击。
巴赫金在《长篇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中,将爱因斯坦相对论中的术语“时空体”借用于文学理论之中,表示“文学中已经艺术地把握了的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相互间的重要联系”,[6]269以此对“诗画界限说”加以补充。然而,巴赫金实际上只是将这个科学术语平移至文学理论中做了一个“比喻”式的利用,除了“空间和时间的不可分割(时间是空间的第四维)”这一点之外,巴赫金的小说“时空体”与爱因斯坦相对论几乎大相径庭。巴赫金声称其“小说时空体”是时间与空间的统一体,“在文学中的艺术时空体里,空间和时间标志融合在一个被认识了的具体的整体中……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6]269-270在这里,时间元素与空间元素具有明晰的相关性,流畅而又稳定地统一于小说之中,“时空体在时间和空间的结合展示出世界的整体图式”,[7]8时间随空间变化而变化,空间随时间推移而转移,时空元素呈现出一个内在统一连贯的均匀结构,并以这种统一性来勾画整个连贯且均匀发展的世界图景。然而,这种统一性却被现代物理学时空观所质疑。“现代科学成果(物质的不连贯结构、原子裂变……),它用一种建立在对世界的小块的、有缺口的认识之上的不连续的哲学,取代了直到一战时期都占上风的连贯的哲学。”[8]121在现代物理学中,时间与空间不再呈现出稳定的正相关性,而表现出多变和不稳定性,这与经典物理学中相互孤立的时空观极为不同。在经典物理学视域下,时空与物质的关系被认为是外在的,二者是两个独立的范式,如同两个框架一样先于物质而存在,并将物质置于其中。根据牛顿的时空观点,“时间的流逝在宇宙的任何地方都是相同的,而空间(不论是微观世界还是整个宇宙)永远具有由欧几里德几何所表示的均一性。”[9]587时空被抽象化为两个先验的概念,拥有各自独立的,与物质无关的地位,世界处于稳定而抽象的二元时空中。然而现代物理学中的时空并非是二元分化的,而是在物质世界中紧密相关、互相交融,并且因为物质世界的复杂多变性,导致时空呈现出非连续、不稳定以及偶然性。例如,按照欧几里德几何定律,即使是不同的观察者,测量同时发生的两个事件的距离是相同的,两事件之间的空间关系应该满足欧几里德几何定律,应该是稳定统一的。但在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看来,“无论事件之间的时间间隔还是空间间隔,都依赖于测量它们的观察者,两个作相对运动的观察者测量这些量会得到不同的答案。”[9]723时间与空间并非是稳定不变的量,在运动中,量杆的长度会有所变化,只要它具有速度;粒子的大小也会随着速度的变化而变化,即使它再小也不能忽略其体积。随着人类认识的深度与广度的发展,物质界实际上被证明是复杂而异质的,无法用经典物理学中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抽象概念来衡量。爱因斯坦的“引力场”理论认为:“引力场中某一点空间上的时间状况就由那一点的引力势所决定,而引力场中每一点的曲率都是不同的,所以时间和空间的特性在每一点上也彼此不同”。[10]由于物质世界本身的不均匀和复杂,与物质紧密相关的时空也被证明是不均匀而复杂的。时空不能被简单地抽象出来,作为概念化的量被二元并置在一起,“在自然界中,规则的、简单的秩序只是大量混沌、复杂、不确定事物和过程的特例”,[11]时空的联系并非是表面上的正相关或稳定均匀,其联系是不连贯不统一的。
20世纪,科学思想的新发展带动了一系列上层文化逻辑的转变,这种转变也鲜明地投射在文学中。战后以颠覆著称的法国新小说派,“颠覆了编年学的顺序”或“动摇了拓扑学的规则”,这些颠覆使巴赫金建立起的“传统的小说时间场所(chronotope)碎裂开来,失去了其同质性、稳定性和内在的布局。”[8]120同质统一且具有流畅性的时空联系受到震撼,让位于断裂、虚空、破碎、混沌等等这些可以同时运用于二战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词汇。
巴赫金的小说“时空体”,虽借用了现代物理学的概念,声称小说是时间与空间的统一体,实际上他依然将小说的重心放在了时间上。巴赫金直白地称:“在文学中,时空体里的主导因素是时间”。[6]275虽然他将空间范式包含在“小说时空体”中,但是对空间范式的论述却极其简单,小说中,时间范式依然占据着主导,空间范式则是时间范式的附属。因此,这种外表看来格外明晰稳定的“统一性”,呈现的是时间范式与空间范式之间较为表面化的联系,其内在仍然是时间与空间这两个独立的范式嫁接在一起,并且在这种拼接的“统一”中,空间范式附属且服务于时间范式。因此,巴赫金虽引用的是现代物理学概念,但得出的结论仍带有浓浓的莱辛色彩,二者有着隐含的二元同构性。然而在当下传媒时代,由于时空思想的新变化,以及图像艺术的兴盛,空间不再被认为是与时间互相独立,或潜在地附属于时间的范式,表现在文学艺术中则是,当代语-图时空范式越来越多地对这种以时间为主导的二元时空观提出了质疑。
二、语言艺术时间的空间化
在莱辛的“诗画界限”理论中,文学应是时间性的艺术。然而,现代主义小说改变了传统的按照外在时间安排情节的描写方式,将时间内在化,内在的时间流动表现在外在却是相对静止的空间,扩展了一个时间段面中的广度和深度,复苏了人心理的内时间维度。这就是为什么《追忆逝水年华》被称为一部关于时间和记忆的作品,普鲁斯特通过对内在生命和时间的反复追溯,强调时间这一主题,也被本雅明称为“现代人的神话”——普鲁斯特“用记忆的持久性功能来协调它在现代社会处于回忆控制下的普遍破碎化。他以艺术来在破碎的现实生活中怀念那个已逝去的、和谐的、感应的真实存在。”[12]519以记忆模式出现的内省时间的完整性,是人能否在当下社会保持一个完整的活的自我的关键。“一战之前时间经验的经典原型是并且仍然是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13]246自现代之后,又很少再有如《追忆逝水年华》这样倾力于描写时间的作品,时间在后现代小说中多是碎片式、混乱、前后颠倒的。诸多后现代理论家看到,在复制时代,空间意识对时间意识进行了压制和排挤。詹姆逊指出:“后现代主义现象的最终的、最一般的特征,那就是,仿佛把一切都彻底空间化了,把思维、存在的经验和文化的产品都空间化了。”[14]293现代化城市、商品化消费消解了历史感,什么都可以复制,什么都可以用货币进行交换,淡化了沉重感,反而让人觉得有些缥缈而无所适从。个体体验伴随着社会空间都被同质化和碎片化,主体难以获得对空间的总体性把握,在后现代主义空间之中,主体往往处于一种无方位感,以及身体与环境的断裂感之中,个体在空间中逐渐迷失。城市中,人们成为波德莱尔式的“都市漫游者”,“透过自己的主体凝视,构筑都市的生活。但他随即为都市的诸般形式所困。都市的建筑格局与终有一朽性决定了他的生活,规定着他的生活”。[15]133日日生活于其中的城市也变成了空间化的符号,成为人们规范自已行动的框架,生活中到处都充满了这种具有形式感的空间框架,不论是身体还是意识,人真正地“漫游”在这个城市“空间”中。
在这个空间膨胀而被詹姆逊称为“超空间”的时代里,文学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实质性的转变,“符号生产中,割裂、压缩时间,将时间空间化, 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文化表现方式。”[16]语言艺术由关注时间范式向关注空间范式的转变,一方面受到图像艺术的启发,另一方面,当代环境下人们线性时间观的断裂以及空间意识的增强直接影响了这一转变。语言艺术要想真切深入地记录人类的精神与环境的状态,则必须紧跟这一发展趋势,忠实于人类置身于当代生活空间中的努力、挣扎、孤独、迷惘等等各种情绪以及内在的心理根基。杰姆逊说:“我用时间的空间化把这两组特征(表面与断裂)联系起来。时间成了永远的现时,因此是空间性的。我们与过去的关系也变成空间性了……在后现代的这种新空间里,我们丧失了给自己定位的能力,丧失了从认识上描绘这个空间的能力,对此我做的最后诊断是后现代新空间中的存在困惑。”[17]133语言并非被图像从时间逼到了空间角落,而是在这个时间加速、距离缩短、空间爆炸的当代社会中,主动选择了忠实记录空间这个范式。古老的二元时空统一体被打破,传统线性时间秩序崩裂,空间被重新发现,文学则敏锐地从这种时间秩序的崩裂中挖掘出了生存的荒诞性。人这个原本具有线性时间意识的主体如今却被限定在静止的时间中,被浓缩为一个可以无限缩小的质点,并被抛置入世界这个无限大的且可无限分割的空间之中,因而只能永远在某个有限的角落原地踏步。就如同《城堡》中人与城堡之间的空间间隔是固定的,而主角所做的一切时间性的行动则是徒劳杂乱而无意义的,时间的混乱衬托空间的庞大和压抑。测量员永远达不到城堡的位置,他只拥有测量空间的能力,没有与时间相关的线性效率,在与城堡之间的这段距离轴上,他被无限缩小化为一个质点,小人物的“小”被量化、可视化了,而空间距离却是可以无限分割扩大的。时空的不均质,是对世界不可测量的无限性以及人类缺乏行动能力的表现主义式的揭示,小测量员只是空间范式的一个极小质点,是永远无法在时间范式上到达城堡的。
法国新小说是关于颠覆小说时间范式,专注于空间化写作的典型。罗伯-格里耶在小说创作中推崇“物化主义”,按照人对世界和物质的绝对主观感受写作,在这种绝对的主观小说中,世界不是按照时间线性地、有条不紊地呈现,而是同时以面的形式,像一幅画、一张网,一下子包裹在主体周围,因此,“有些新小说家主张把绘画的原则应用到小说创作中去,要把小说由‘时间艺术’变为‘空间艺术’。表现在小说叙述上,作者常常无视所叙之事在时间上的承续性,不断把线性的叙述‘切断’,也就是让故事中的‘时间’停下来,注目于某一个细节上,然后做‘横’的、空间的铺展,然后再回到主要的剧情主线上,再后又被‘切断’……”[18]766-767在现象学的影响下,新小说强调对写作的“还原”,即悬置人对周围物质的认识,反对将物质作为人类的创造者或者附属品,专注于对物的直观感受上,结束了现实主义小说中文字与世界,外在与内在,现象与本质的二元模式,“自此以后,我们……再也不相信那种‘深度’了……事物的表面对我们来说就不再是事物的‘心脏’的外罩了,而就是事物本质之所在。”[19]119在罗伯-格里耶的大部分小说中,前后两个场景的描写随意转变衔接,阻止读者形成时间连贯的传统阅读习惯,拒绝任何统一完整的观念,“意义间的联系仅仅是由关于词组的空间式的同时性感知来实现的,因此,如果是时间式的线性阅读,就无法理解意义间的相互关联”,这种审美形式“建立于一种空间逻辑之上,要求彻底地重新定向读者对语言的看法。”[20]229在这类文本中,叙述不断遭受袭击,传统文本中那种朝向一种因果明确的、具有目的性的组织方式和价值追求,让位给了一种割裂的、不知所措的认知和混乱行为,这些认知与行为往往以失败、虚无告终。灾难,溃败、幻灭充斥于文本之中,新小说的空间化写作带给读者的正是这种对自身价值的思考。
三、图像艺术空间的时间化
图像满足人直接而生动地把握世界表象的需求,使人的认知能力更有效率地得到发挥。图像的效率性还体现在大量符号的运用,符号与其背后内容的联系,让观者在最短的时间内接收到其所包含的信息,借助于画面的直接表现,图像艺术相较于语言艺术,拥有更加丰富多彩的意象,能够迅速地把握整体形象。20世纪,摄影复制技术的革新,以及报纸、杂技印刷品的商品化,使图像在人们认识掌握世界的过程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E·H贡布里希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视觉时代,我们从早到晚都受到图片的侵袭。”[21]106关于“视觉文化”,也有学者认为,广义的视觉文化,并非仅仅存在于图像传媒兴盛的现代,而是存在于印刷文化出现之前,只是当今新媒体的发明,使人们重新“恢复对视觉文化的注意”。[22]25在此之前,正如莱辛在《拉奥孔》中所说,图像艺术在许多时代受到限制,要求其应该具有“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严守在静止的空间范式内,不越雷池一步,那些尝试表现叙事的历史画或连环画则会受到苛责。然而,自20世纪以来,诸如立体主义、未来主义以及抽象派等具有革命先锋性的图像造型艺术,带来了反传统的新美学。以毕加索,布拉克为首的立体派,常常把物体分解为各个角度的几何切面,并进行组合拼接。“立体主义废弃了文艺复兴时期以来建立在观众的静止上的透视法,而创建出基于动态变形的复合视点法则”,[19]212将物体的几个不同角度切面组合在同一平面上,让四维空间全方位并且同时性地表现出来。紧接着立体派后出现的未来主义则致力于用艺术符号表现现代都市生活日益加快的节奏,兴盛的工业,并擅长彰显激烈的运动和力度。新兴艺术形式的出现,“在绘画领域,最典型的就是焦点透视法逐渐走向终结,取而代之的是散点透视。”[19]209艺术手法改变的背后,是对文化史上理性传统的质疑和颠覆。当代社会爆炸性的节奏冲击了艺术家的神经,“艺术家莫霍利-纳吉(L.Moholy-Nagy)就认为,飞机、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的出现,将速度引入静止的视觉之中,造成形象的瞬间变化、叠加,”[19]211立体主义、未来主义、波普艺术等等,都力图捕捉现代人的现代感受,用图像和造型来表现这个运动的时代,以及人类面对这个时代的直观情感。画面与人类情感之间的沟通是“一种不是通过观照而是通过行动达到的一致性……由此导致了审美的时间形式对‘确定空间’的破除”,[19]211并以此揭示现代人内心非理性的意识之流,反叛绘画造型艺术传统的静态美学观。
在20世纪初始阶段,语言文字依旧是主要的表现形式,图像只是起到辅助文字,使表达生动化的作用,直到在活动照相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电影电视技术的普及,才真正改变了图像与语言长期的主从关系。“电影作为造型艺术的落脚点和归宿点是体现在电影空间上,它是借助于影像画面的运动空间将影像的三度空间活化成了四度空间。”[23]电影首先是一种视觉艺术,它以图像媒介为基础,效率原则使观者愿意接受图像,获得观感的轻松愉悦,以电影为代表的多媒体图像艺术则将这一愉悦提升到新的高度。自此之后,文字对于观众的吸引力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比起一本文学作品,人们更喜欢欣赏影视作品。电影的原理基础是图像技术,是属于空间范式的,电影利用图像画面快速转换,给人造成视象暂留的错觉,“蒙太奇组接可以大大改变时间的计数,从而仿佛在影片结构中构成一个新的时间层次。”[24]用图像表现运动进而构建故事的效果。虽然莱辛强调,讲故事属于时间范式,图画是空间性的,然而电影却属于用图画说故事的艺术,“电影是在时间的推移中再现空间,又在空间的流逝变化中展示时间。”[23]电影的出现,真正将时间范式赋予了图像艺术。不论对电影做出怎样的学院式解释和先锋的创新,我们不能否定,它首先是当代大众化的新兴艺术,电影的流传之所以有超越文学之势,并非因为图像超越了语言,而是因为电影似乎比文学更会说故事,更能让人观摩、见证、享受时间性的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尾。从这个角度来看,电影反而体现了大众的阅读和欣赏惯性,而突破传统线性时间描写的现代、后现代语言艺术在大众眼中则成了先锋性的新事物,变得越发晦涩。
四、结语
当今时代,语言艺术与图像艺术越来越难以仅仅通过时间/空间范式来进行划分:艺术创作方法和艺术观念的改变,加之新兴的多媒体技术让图像艺术运动起来,能够更逼真地模仿世界,甚至比作为时间艺术的小说更会说故事;空间化的语言艺术则使得文学能更深入表现当代社会中人们的生活现状,表现人类线性时间意识的缺失和空间迷失感。后现代小说喜欢选择游戏性的符号和直觉性的空间描写,用零碎的、感觉式的叙述表现深度感的削平。叙述对深度感的削平并不代表艺术本身的无深度,这些直觉式的无深度的符号起到了类似于图像艺术的作用,让人在阅读过程中容易产生整体空间感,仿佛突然置身于文字构筑的空间之中,从而集中再现人身处于现代社会空间中的失落感。后现代语言艺术破碎化、符号化、空间化的形式,不同于以往现实主义小说对世界镜像式的仿真模拟,而是从更符合当代人心理体验的视角表现物质空间,深度还原人们现实生活中的迷失感,以此追求一种无须模仿现实,其自身即具有意义,能够自恰的艺术形式,因而,“现实主义小说幻想时间的崩溃,可与透视画中幻想空间的崩溃相对应,两者提供了一个类似的功用:要求艺术作品的合法性在于它自身,而不是对别的事物的模仿。”[25]433无论是语言艺术的空间化或图像艺术的时间化,都致力于揭示人类在当代社会的本质性感悟。传媒时代,人们感受到的是不再均质、稳定,而是充满了偶然性与动荡性的时空观念,“那些选择栖居于后现代性境况中的人,也同时生活在现代人和前现代人当中。这是因为,后现代性的根基本身就在于认为,世界是由多重异质性空间和时间构成的。”[15]30人们体验到的是膨胀性的空间感和爆炸性的时间感,艺术家、学者们正努力突破过去人为形成的时空二元结构,尝试时间范式与空间范式之间新的对话与融合,来表现当下人们的具有“多重异质性”且复杂丰富的时空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