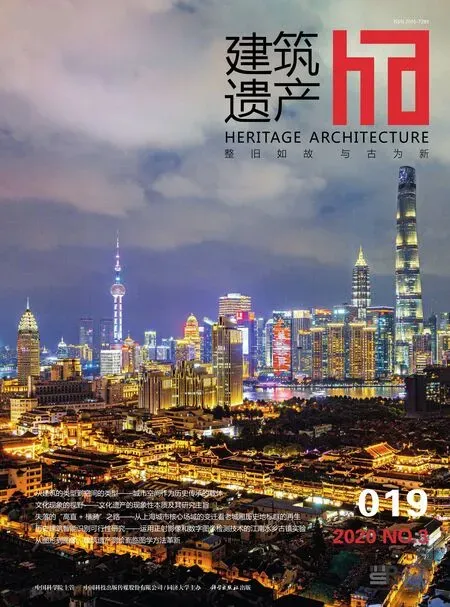长乐长宁
——肥东县南部明初移民村落的空间规划体系研究
张靖华 Zhang Jinghua
巢湖,地处江淮之间。其北部岸线弯曲形如半岛,面积约150 km2。半岛中部为郯庐地震带形成的山岭,从北向南斜向纵贯整个半岛。山岭两侧被湖水包围,明清两代为庐州府合肥、巢县二县,今为合肥市肥东县和巢湖市分治。位于肥东县南部的半岛区域呈倒三角形,明清时分布着两个重要市镇,一为长宁镇,一为长乐集(图1)。长宁镇,今为长临河镇政府所在地,距巢湖仅200 m 左右;长乐集在长宁镇北,距长宁镇直线距离约6.5 km,今为撮镇长乐社区驻地。明清以来,这两个市镇均有较大规模的人口集聚,商业活动较为繁盛。从空间关系上看,它们都处于店埠镇(今肥东县县城所在地)向南进入巢湖北岸半岛南端的道路沿线,同时又分别为长宁河和沙河(又称长乐河)流经区域。西侧濒临南淝河和店埠河,是庐州南部重要的水陆交通节点。其命名显然是基于当时的历史文化环境,由于江淮之间较多战乱,“长乐”和“长宁”带有强烈的祈福意义①另外一种说法认为,长宁镇的得名与它濒临的长宁河有关。。今两镇之东有长乐寺和长宁寺两座古刹,据嘉庆《合肥县志》记载分别为唐代和元代建造,但在当地人的传说中,长乐和长宁二寺都与吴魏战争时孙权来此祈福的故事有关。
今所见长乐和长宁古镇,应该主要形成于元明交替阶段的战乱之后。长乐镇流传着“先有古寺,后有长乐集”的说法,同时还流传着一个“三姓建镇”的传说。传说明永乐九年(1411),河南祥符人王谷兴携三子南下到此,为躲避兵役,将三子改为张、王、李三姓,开始世代建祠祭祀②2005 年重修《谷兴公宗谱》卷一《三姓同宗原序》。。这一时期,也是整个巢湖流域移民集中迁移,并从单一家庭逐步形成村落的历史阶段[1]。据《中国移民史》的研究,洪武三年(1370)开始,明政府向凤阳等地迁入了大量人口。与此同时,巢湖流域也迁入了来自江西、徽州等地的移民约25.6 万人[2]。这一规模庞大的人群散落在遭到战争破坏的土地之上,留下了强烈的时代烙印,最为明显的印记就是长乐、长宁二镇的许多原始移民村落仍保留着以祖先姓名作为村名的传统,如胡道二村③据1938 年编修的长临河镇胡道二村《胡氏宗谱》卷一《淝东胡氏合修宗谱序》记载:“胡氏之远祖,道二、回二、允二三公,由江西瓦砾坝来肥,爱青阳山南麓山水灵秀,遂卜宅于此而居焉。”、徐万二村④据1799 年编修的长临河徐万二村《徐氏宗谱》卷一《徐氏重修宗谱序》记载:“明太祖中原定鼎,万、关二公避难图存,由婺源迁淝,卜吉于朝霞之东,聚族而居。”。这一风俗与洪武初期实行以户贴制度的特殊历史密切相关。
由于本地区聚落的产生具有明显的开发性背景,因此建筑空间往往具有强烈的规划特点。从空间形态上看,无论是长宁镇还是长乐集,其空间结构都十分规整,具有明显的营寨特点。长宁镇的平面为圆形,中部两条道路十字交叉(图2),周围有壕沟环绕;长乐集的街区呈矩形分布,形态规则(图3),历史上也有壕沟。两镇的形态均与明代北方官式城堡十分相似,而和巢湖流域其他市镇的自然形态大相径庭。虽然不排除它们有更久远的创建时间,但目前的建筑空间制式与风格都暗示它们更有可能是元明之际建造发展的结果。在其周围分布的移民村落,原始的空间形态也同样具有这一时代鲜明的特色。
1 明初移民村落的分布特点
长乐、长宁地区的明初期移民村落,主要分布在以下三个区域:
第一区域是河口和圩田,其中的移民村落有刘寿大、章宗三、贺铁关、牛关堡、王福一、张隆一、李六、范四六、王会堡等。这些村落多数由明初的皖南移民所建,如张隆一村①据2004 年编修的长临河张隆一村《张氏宗谱》卷一《张氏族谱序》:“元至正间,中原鼎沸,我始祖隆一公以避乱故,道经合肥之巢湖,爱北涯水绕山环,遂定宅焉。”、牛关堡(原名牛关保)村②据1904 年编修的长临河牛官堡村《牛氏宗谱》卷一《五修宗谱序》:“我始祖官保公与关保、召保,奉母戈氏孺人,避乱于合邑之东乡。”,它们多数分布在古巢湖北岸的圩田东侧,呈圆弧型分布,村落间距比较均衡,历史上保持着密切的经营合作(图4)。
第二区域位于长宁镇与长乐集之间,包括今长临河镇境内的柳家岗(原名柳仲二)、丁家桥、丁陈二(原名丁成二)、丁成三、张保二、罗胜四、万受益、倪伏三、张胜五、许家榨(原名许贵二)和长乐集附近的部分村落。这些村落,一部分相对密集地集中在长宁镇周边并呈环状包围态势,另一些则在长宁镇北部与长乐集之间呈网状分布态势。如刘伏二、马正二、张胜吾、倪伏三与长乐集地区的贺胜堡、荚堡、长乐集古镇连成一条东偏南约60°的聚落分布线,这条分布线大约长5 km 左右,两端分别穿过长宁寺和长乐寺。两寺之间是一条古道,与该聚落线大致重合,当地人称“十里长亭”。“十里长亭”上,有几条移民聚落形成的分布线与之明显垂直:一条是南部的LN1,由王端二、王赤堡、吴赤堡、倪伏三、奚家岗(原名不详)、柳仲二等村组成;一条是北部的LN2,由李贵二、王宗二、贺胜堡、牛关堡、贺铁关组成。这两条线上的聚落,彼此间距十分均衡(图5)。

图1 长乐集和长临河镇的位置(图片来源:张靖华据国民政府参谋本部陆地测绘总局编、中华民国十八年五月印制的《烔炀河》历史地图改绘)

图2 长临河镇空间形态(图片来源:Google Earth 遥感照片)

图3 长乐集空间形态(图片来源:同图2 )
第三区域位于今长宁镇的东南部,巢湖北岸半岛内部,是移民村落集中分布的区域。山地与丘陵纵横,中部保留有大片耕地。相对平原地区而言,这一区域虽然地形崎岖,但原始移民聚落数量不仅并未减少,且十分集中。经调查,其中元末明初的移民村落有:孔永五、山毛、张德山、张永久、盛宗三、罗荣八、吴兴益(原名吴兴一)、胡道二、凌福寺、大宣(原名宣道七)、黎兴三、杨元三、朱龙七、大徐村(原名徐太六)、王信一、王道三、刘寿三、徐万二、大蔡村、靠山杨、山口凌等,从北向南大致来源如下:
山毛村,始祖徐盛公,江西人。
大宣村,始祖为宣道七,推测为皖南人。
孔永五村,始祖孔永五,字敬夫,句容人。
张永久村,始祖张永久,推测为江西人。
杨元三村,始祖杨元三,推测为江西人。
盛宗三村,始祖盛宗三,族谱记载来源地为“徽州瓦洗坝”。
黎兴三村,始祖黎兴三,江西人。
吴兴益村,始祖吴兴一,宣城人。
罗荣八村,始祖罗荣八,村民口传为江西人。
朱龙七村,始祖朱龙七,推测为皖南人。
胡道二村,始祖胡道二,江西人。
山口凌村,始祖凌载一,歙县人。
凌福寺村,始祖为凌载一之子凌福士,歙县人。
大徐村,始祖徐太六,皖南人。
刘寿三村,始祖刘寿三,江西梓溪人。
徐万二村,始祖徐万二,徽州婺源人。
大蔡村,始祖宽公,宁国人。
王信一村,始祖王信一,疑为江西人。
王道三村,始祖王道三,疑为江西人。
靠山杨村,始祖诚公,宣城人。
沙二岗村,始祖吴兴五,宣城人。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村落,如记载于六家畈《吴氏宗谱》的吴泼养村,今虽不存,但也可以推测其始祖为明初移民。
这些移民村落和第二区域一样呈明显的网状分布。从长宁镇向东偏南30°划一直线会发现,它们十分均衡地分布在这条直线以及它的几条平行线上,从北向南依次为:
LS1:张永久→盛宗三→罗荣八→吴兴益→胡道二→凌福寺
LS2:宣道七→黎兴三→杨元三→朱龙七
LS3:徐太六→吴泼养→梅寿二→刘寿三→徐万二
LS4:王信一→王道三→吴兴五
这四条线间距离相对均等,皆为0.5 km左右。其中LS1 和LS2 更近一些,聚落线保存的样本也较多。LS3 和LS4 上的聚落存在后期移动现象,如原在茶壶山下的吴氏,后北迁至玉带河口;王道三与王信一两村,黎兴三和杨元三二村,都存在彼此靠近后连片发展的态势(图6)。
2 插草为标——村落空间体系分析
这种非常明显地按照一定几何图示进行空间分布的村落群体,无论在巢湖当地还是中国其他地区都不太常见。虽然在许多平原地区,受经济和交通环境影响,村庄的数量和间距会伴随人类的活动,自然形成一定的规律,但在不受人为干预的情况下,像第三区域那样崎岖不平的山区,仍出现方格网状分布的村落群,就基本可以排除自然发展的可能。与长宁镇和长乐集传统建筑空间严整性特征形成的原因一样,这两个古镇域内的村落,在600 年以前也一定经历了一个同样十分宏大的统一规划与建设阶段,才能形成这样的空间形态。对于这段历史,长临河当地的老人一般以“插草为标”来形容。“插草为标”是一句常见的民间俗语,在很多地方都能听到,一般都和元明时期的移民垦殖联系在一起。插和标,是树立“标识”,这一行为在湖南等地同一时期的族谱里也有记录①湖南衡阳《厚雅田王氏谱》卷一称:“至者,各插标以记,谓之安插户。”转引自杨总铮著《湖南客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22 页。湖南《云阳涂氏族谱》卷十《家传》亦记有“占垦者,则各就所欲地结其草为标,广袤一周为此疆彼界之划”。,隐含着对土地进行规模测量和确定边界的行为。在长乐、长宁地区,恐怕实际还会包含更多复杂的系统工作。这些工作虽然缺乏文献记录,但能根据蛛丝马迹进行推测和复原。
首先,通过对上述三个区域移民点及其水系道路进行分析后我们发现,移民村落的空间规划方式与水系、道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无论是第二区域还是第三区域,方格网的中心地带基本都有河流穿过。如第二区域,南部线路LN1 与长宁河流域基本重合,而其与“十里长亭”之间的交汇点——倪伏三村附近恰有一座古老的水库,通过在长宁河上筑坝形成,当地称之为乌金陂。当地从乌金陂中导出的河水,灌溉下游农田。关于乌金陂,当地人传说是一位叫“王老先生”的人从京城归来,在此扔下了一条金锁链,后人在集体寻找的过程中不断挖掘而成;另外一个说法是称乌金陂里隐藏着神秘的力量,人们轻易不敢靠近。第三区域的中心地带是整个区域最重要的水系——玉带河主要流经地区。玉带河从白马山向西南而下,之后折向西流入巢湖,其转折点所在的笏山臧村一带,几乎就是该区域的几何中心点。这两大区域中心和水系之间的巧妙关系,以及当地的神秘传说,赋予了这两个空间中心点某种历史性和文化性的象征意义。
水系之外,道路系统对空间格局形成的影响也很大。第二区域“十里长亭”两端的寺庙,无论从文献记载,还是从两座寺庙及周边的相关遗迹来看,都可以确认它们建造的年代在明代以前。那么这条更为古老的“十里长亭”是否也是移民村落建设时依据的一条历史空间轴线,移民村落以此轴线为中心向周围拓展,形成了与之垂直的几条分布路线?除此之外,在第三区域也能发现一些历史上存在的平行道路,呈东偏北60°分布,彼此距离均等,与LS1 等村落分布线的走向垂直(R1 -R4,见图7)。
由此可见,道路和水系显然与聚落分布线的形成有着十分切的叠合联系。这些村落形成之初,极有可能确实存在一个依据水系先确定区域性的作业中心,再依据传统道路或地形条件划分地块,之后按照一定的距离树立标杆,逐个确定居民点位置的“插草为标”的历史过程。
其二,对所在区域和长乐、长宁二镇的空间关系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两个市镇恰好分别处于其所在区域网络的正方形顶点之上。如果前文对两个村落分布区域判断是正确的话,那么长乐、长宁二镇和周边移民村落似乎还存在着一种特别的依存关系。或者说,600 多年前,长乐、长宁地区的市镇和乡村有可能存在过一个更为系统性的形成过程。之所以这样判断,是因为明初移民所到达的江淮地区人烟稀少,个体移民者缺乏独立生存的能力,客观上需要有统一的集聚地来完成开发的准备,如果在一个待开发区域没有可供使用的聚落空间,那么就需要由政府进行建设,之后再对人口进行统一的管理和调度。路伟东在对清代敦煌移民和农坊制度的研究中,发现了流行于当地的“中心集散地与乡村群落”的建设模式:雍正年间敦煌农坊“2 405 户移民分别来自50 多个不同州、县、卫、所,每地移民人数多不过六七十户,少者仅三四十户,不足一保或一里”。它们一开始采取的是群居在小城之中、生产时向周边散处的方式:“移民初至,全部聚居城关,五方杂处,稽查匪易,而所种田地又散处四乡,每年春耕伊始,挈眷赴田,夏耘秋收,妇子散处原野,结茅而居,待至浇毕冬水,又搬回城内居住。”[3]但这种候鸟式的居住和劳作模式显然对管理者和劳动者来说,都很不方便,因此后期这些小城中的居民开始慢慢迁移到被指定的劳动地点,建立起独立的村落。从某种程度上说,长乐、长宁地区的情况和敦煌应该是类似的:移民开发的集散需要决定临近城镇必然成为原始的聚居地,伴随着生产的推进,后期又慢慢引发人口向指定耕作地点扩散开去,并形成固定的聚落。从“方格网”上很多村庄的始祖墓建在村边,如徐万二村(图8)、刘寿三村、黎兴三村,可以推测,在洪武年间,这个扩散和固定化的过程已经接近完成。在人口从聚集到扩散的过程中,作为聚居地的小城,如果它们确实是为了移民集散和管理而新建的,就难免伴随着“逆城镇化”的过程而出现明显的空间衰退。比如长宁镇,虽经600多年的发展,其护城河内的面积至今仍有将近一半左右为农田,而其十字交叉型的街道,经历了数百年的商业发展,也仅南北方向有店面开设,东西方向街道有一半早已衰退为镇中小路。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个小镇拥有过一批曾经居住但现在无法统计的城镇人口。清代以来的小镇聚居人群与其说是明代以来逐步发展的结果,还不如说是明初短暂集散和繁华之后,人口大规模迁出之后的遗留。这种人口流动造成的“空镇”现象,在长乐集也有蛛丝马迹可循。现有的三条南北向街道,中部商业街形制规整,缺乏一般商业市镇所有的自然形态,两侧街道与之平行,其肌理具有形成于同一时期的明显特征。其居住者基本为王谷兴的后代,但王谷兴家族在明初只有五口人,早期的长乐集似乎有着更为丰富的居住者。联系到这一区域的整体情况,这些问题就不难解释。或许,正与敦煌地区的小城和村落关系类似,长宁镇和长乐集,无论明代以前是否存在,在明初的短暂时间内它们都曾作为移民者短暂聚居的场所,而这一场所由于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内建造或命名,留下了共同的空间特点,及名称上的呼应关系①与此类似,巢湖北岸半岛的东部,和长乐、长宁二镇对应的位置还有烔炀镇、桐荫镇(今黄麓镇),二镇的名称疑似从“同阳”“同阴”改来,反映出一种近似的年代烙印和管理痕迹。。

图4 圩田地区移民村落分布情况(图片来源:张靖华根据Google Earth 遥感照片改绘)

图5 第二区域移民聚落空间分布分析图(图片来源:同图4 )

图6 第三区域移民聚落空间分布分析图(图片来源:同图4 )

图7 第三区域的平行道路(图片来源:同图4 )
3 规划动因与社会控制
这样一种包含了对城镇、村落的综合考量,又融合了水利工程建设和道路系统的乡村空间格局,无疑是中国古代国家主导下的乡村规划的珍贵样本。这一建筑遗产,除了和今天较为类似的资源性的建设动机之外,元末明初的社会环境才是这一规划实施的主要动因。严格来说,作为一种社会资源控制手法,古代社会的乡村规划行为不可避免地和政府对农业社会的管理行为直接挂钩,并与政府对社会资源的调度能力密切相关。这一调度能力所转化成的空间建造思想——从春秋战国时期就慢慢开始强化的城乡规划的意识与实践,在城市建设领域从汉代至唐代走向顶峰,在唐宋之际趋向于衰退。最终伴随里坊制的崩溃,城市街巷空间也相应地走向自由形态。这一从控制走向非控制的发展过程在乡村聚落群体之中,应该是大体同样存在的。只是到了元明鼎革时期,无论是城市空间还是建筑空间,其控制性色彩似乎都出现了明显的加强。梁思成注意到了这一时期的大木建筑风格从宋元以来的灵活优雅过渡到僵化呆板的现象,虽然未解释其成因,但形容“这种转变来的很突然,仿佛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突然改变了匠师们的头脑”[4]。近年来,历史学界也开始注意到这种“不可抗拒的力量”的真实存在,意识到传统的历史叙事之外,明政府的本质,是朱元璋在吸收元代兴亡经验基础上,对强大的社会控制与资源管理体系的再建构。就这一点而言,明初的大移民本身也很能说明问题。在苏中和苏北地区流行将“移民”称为“洪武赶散”,透露出大移民是通过“赶”的行为将原有社会组织强制“散开”的真实意图。在长乐、长宁地区,更多的社会记忆透露出迁移过程中,原有社会组织被刻意分隔、打散的历史事实。典型的例子如长宁镇丁家桥村,祖先名丁华六,原有兄弟五人,居住在无为之开城桥,因不愿被分离,折梅祈祷,得名五果丁:“因矢志同居,恐其弗信,乃折梅五枝,插地以誓曰:一有异心,梅必枯死。已而五枝皆生,且成实焉。兄弟感泣②长临河镇丁家桥村《丁氏宗谱》卷一《五果丁氏传》,1920 年编修。。”长宁镇山口凌村,始祖名凌载一,来自皖南。据说原有兄弟三人,迁移中被强制拆离。三人临行前将一块刻有鳌鱼的木板一劈为三,各持一块,以为日后相认凭证。长宁镇的刘氏家族,始祖迁出时有兄弟三人,名刘寿一、刘寿二、刘寿三,现村址虽然都在巢湖北岸,却分处黄麓、长临河两镇,三村呈三角形分布。这种刻意拆散亲族,使个体移民被“原子化”,从而使其被完全控制的社会控制行为,作为长乐、长宁地区乡村规划的前置条件,构成了本地区移民村落分布中十分有趣的“监控”与“穿插”现象:在对LS1和LS2 上的聚落进行文献调查之后我们发现,区域三聚落线上的移民村落,其始祖的起源和相邻两个村落存在相区别的现象,即如果一个村落的始祖来自江西,那么它相邻的两个村落始祖就来自皖南;如果始祖来自皖南,那么其相邻村落就来自江西。换言之,区域三的移民村落,是按照“皖南-江西-皖南-江西”的模式彼此穿插分布的(表1,表2)。

图8 徐万二村外始祖墓(图片来源:张靖华摄影)

表1 LS1 线明代移民聚居点序列分析

表2 LS3 线明代移民聚居点序列分析
这样一种特殊的村落分布方式,带有明显的监控意图,印证了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对历史的评价。他从一个封建帝王的角度,认为明初的最高统治者实际一直存在着对社会的防备意识:“朕读洪武宝训,见明太祖时时以防民防边为念。盖明太祖本以元末奸民起事,恐人袭其故智,故汲汲以防民奸;其威德不足以抚有蒙古之众,故兢兢以防边患[5]。”“穿插”手法的存在,一方面有力地证明了长乐、长宁地区移民村落的空间体系确实是人为规划设计而成,另一方面也更证明了乡村“规划”作为社会管控与空间建设手段,在我国确实有着更为久远的发展历史。无论如何,国家意志控制下的规划是一把双刃剑,在缺乏现代意义的权力与智力博弈的情况下,历史上大规模的乡村规划建设基本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某种程度上说,“规划”既创造了宏大的建筑遗产,又限定了社会的自由发展。
在长宁镇南部,很多村庄或因深受这种“乡村规划”影响,留下了一些有趣的传说。比如现龙陈村,村民传说历史上地下曾经有一条龙,这条龙原本富于活力,但心存妒忌的皇帝故意用两个钉子——实际是村庄临近的两个丁姓村落,一南一北将龙钉住,使龙最终丧失了活力;分布在LS3 上的梅寿二村,前后土地狭窄,发展空间局促,当地人传说是地下有个螺蛳精,慢慢吸干了村庄的力量。这种“钉死”和“吸干”的传说暗示,本区域的移民村落在建立过程中,人与土地的关系存在着强烈的不自由状态。而有些村庄位置较好,则发展快速。乾隆年间,对比相邻的吴兴五村,梅寿二村的后代梅昆曾困惑地疑问:“迄今五百余年,予族寥寥,而吴姓繁衍不啻数十倍,何盛衰若此?”①详见2011 年编修的长临河镇沙二岗村《吴氏宗谱》卷一《吴氏续修宗谱序》。这些传说或疑问,暗示了这一规划体系本身在推进乡村发展的同时,或也存在因其带有强制性的安置布局和监控意图,影响到了部分村庄的正常发展,同时也加深了资源分配的不均。近年来的调查发现,一些先天条件不足的乡村发展滞后、空心化现象更为严重,地处岗地的罗荣八、朱龙七等村,地下水质还出现明显的盐卤化问题。
4 村落体系的衰退和保护策略
以上分析可见,长乐、长宁地区的明初移民村落及其空间规划,是一个创建于元明之交的特定年代,带有强烈控制性目的,且发挥作用比较复杂的系统。它在推进区域整体性开发的同时,伴随时间的推移,也不可避免地对村庄空间的正常发展产生影响,或者刺激了人口的外迁,或者引发聚落位置与空间的变动。实际上,可能是为了摆脱某种发展桎梏,从移民的第三代起,即有村庄开始迁出不适合耕作的原位置,前往更适合发展的区域;或者从较为孤立的移民点向另外一个移民点靠拢,从而形成生活和生产上的联合体。前一种情况较典型的如六家畈村,该村原居茶壶山下,其位置正在LS3 线上,至第三代时吴氏六子均向旧村以北的玉带河流域迁徙,并逐渐繁衍成为当地巨族;后一种情况,如连片发展的王信一和王道三、杨元三和黎兴三村,以及由三姓联合形成的刘、罗、蔡村,都形成了连片的、融合式的发展。
在空间发生移动的同时,社会观念也在发生悄然的变迁。这种变迁在祖先起源的问题上表现最为明显。相比其他移民区域,长宁镇南部的移民家族对于自身的身份认同显得十分复杂。六家畈村的吴氏在族谱中一直称始祖是来自宋末的皖南移民,但同时又在对第一世祖的介绍中提到“户名吴泼养”,让人十分疑惑②长临河镇六家畈《吴氏宗谱》中的《东乡吴氏宗谱世系图》提到其一世祖吴七三公:“公妣俱葬四顶山东北谭树棵,户名吴泼养。”从长临河地区族谱的一般记录习惯来看,如果祖陵更为靠近其他村庄,这些异姓村落一般记作“某宅”,除非吴氏定居之处即名吴泼养,否则一般不会刻意强调明初的户名,故怀疑吴泼养极有可能是六家畈最初的名称。加之以宗谱记载来看,六家畈吴氏迄今仅传20 余代,其一世祖不可能上溯至宋代,而吴泼养既为户名,其人又不见于族谱,恐是后世修撰族谱时被替换为家族对其的日常称谓。。无独有偶,还有很多明显的明初移民村庄,如吴兴五、梅寿二、刘寿三等,或者形成了祖先为宋代而非明代移民的历史讲述③如吴兴五村(今沙二岗)于乾隆二十五年编修的宗谱称“我始祖兴五公于宋宝庆间由宣城渡江,卜居于二大沙岗”,又说“其时南北分争,江淮之间无宁岁。元末天下兵端又多起,两淮遗民仅有存者”。梅寿二村族谱称:“第一世始祖寿二公于宋末自宛陵迁肥下,居茶壶山下。”,或者出现了反复多次将祖先来源从江西移民改为皖南移民、又从皖南移民改回江西移民的现象④1921 年编修的刘寿三村《刘氏族谱》卷一,对于祖先世系存在“寿三公由梓溪渡江而北”“寿三公由宁国渡江而北”“世居宛陵,自寿三公渡江而北”“始祖寿三公,其先宛陵人,于宋恭帝时渡江而北”等几种说法。。这些复杂的历史观念及其背后的逻辑,很多并未取得社会的认同,相反在它著于文字的上百年时间里,时常遭受着同时期迁来的移民家族的异议,如长临河北部罗胜四村在族谱中,刻意地强调六家畈之始祖是其祖先罗胜四的老表,同从江西而来,并记录了迁移的时序、更换土地等一些细节信息⑤“同里吴氏始祖为(胜四公)中表之戚,公来较早,先卜宅于六家畈……吴来略迟,屡次乞让……此数百年来两姓子孙递述之词,证之今日,尤为可信。”详见1948 年编修的长临河镇罗胜四村《东乡罗氏宗谱》卷一《世系》。。还有一些移民家族对历史的记述引发了公开的讨论。吴兴五村的吴静江等人,曾以编户名称和世系特点为依据,认为文献中祖先迁自宋代的历史绝不可靠⑥吴静江认为,从世系特征来看,本村完全不具备宋代村落的特征:“先生谓自宋宝庆迄国朝嘉庆间,应不止一十六世。”吴静江的朋友也赞成这一观点,且敏锐地发现了村庄的原名“吴兴五”和明代户名的关系:“兴五为编里户名”。详见2011 年编修的长临河镇沙二岗村《吴氏宗谱》卷一《吴氏续修宗谱序》。,并因此与家族中另一些人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这些关于历史的争议和事实上存在的更为频繁的迁移行为,似乎暗示着长宁镇南部山区的移民村落群相对北部平原地区,可能存在着对原有规划控制系统更为灵活的态度和更为隐秘的处置。而这种或明显或隐蔽的对“规划”的反馈,一定程度上又成为地域社会形成中的某些动力,进而雕塑着整个区域的社会文化。明清之际,伴随明王朝的衰亡,明初形成的乡村规划空间也逐步经历着瓦解的过程。此后,伴随太平天国的战火燃及江淮,早已人满为患的长乐、长宁地区子弟,在同乡李鸿章的号召下,大量参加淮军,使得村庄的历史逐步融入近代化的洪流。建国以后,长乐和长宁地区成为名人辈出的“侨乡”,明初移民的历史被新的荣光所取代,逐步退出人们的记忆。
今天长宁和长乐地区的传统村落,因为环巢湖大道的兴建,面临着发展的巨大机遇,也承受着风貌衰退的重重压力。这种压力体现在许多方面,多年来人口外迁导致的村庄普遍的空心化,新的发展机遇引发的村民拆毁传统民居、新建住房的热潮,以及新的城乡道路和产业系统对旧的空间体系的侵蚀,都严重地影响着这一区域传统村落建筑遗产的保护。如何协调产业与发展、现代与历史的关系,在经济状况并不发达的长乐、长宁地区,尚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作为体系性的移民村落群,是否存在整体性保护的可能?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几乎是尴尬的,因为这一区域本身为环巢湖大道所经之处,就在政策研究部门制定相关保护规划之时,一些省级道路的规划路线已经穿越移民村落分布的区域,导致部分村庄被拆毁。移民村落体系完整性的受损,使整体的遗产保护在很大程度上似乎只能停留于纸面的设想。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即便没有上述的破坏,这片一直处于无法避免的衰退中的、体现劳动人民伟大智慧,然而更多是体现历史长河复杂面孔的建筑遗产,是否仍有足够的吸引力去勉强今人克制发展的意愿,将其作为一个庞大笨拙的历史文物来加以存留和展示,仍然是一个问题。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处理,很大程度上拷问着我们对于文化遗产终极价值的理解,也考验着今人处理现实与历史冲突的智慧和技巧。2015 年,笔者曾借鉴浙江宁海体育健身步道的做法,对重点的南部第三区域进行了空间梳理。通过对传统交通道路的适当改造,引入市民休闲运动,将区域内传统村落和其他自然人文资源进行连接,促进村庄的改造和活化(图9),目前已取得一定的成效。自步道体系建立以来,沿线靠山杨、吴大海、大蔡等村陆续被市民“发现”。但与此同时,部分生态敏感区域以及值得保护的古建筑,也被积极参与乡村建设的市民或村民自行改造,风貌遭到破坏。
5 小结
综上所述,作为形成于特殊历史社会环境下的文化遗产,巢湖北岸肥东南部的移民村落群体系宏大,数量众多,不仅具有建筑学领域的研究价值,更是特殊历史时期规划与社会发展关系的生动样本。这些分布于庞大而精巧的方格网上的移民村落群,可能是中国现存最早也最庞大的乡村规划和建设的真实遗存,反映着元明鼎革时期,强大国家力量对社会个体的支配与控制,启示着我们进一步认识传统规划在权力与社会之间的定位。

图9 长临河南部地区步道空间体系示意图(图片来源:张靖华根据Google Earth 遥感照片改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