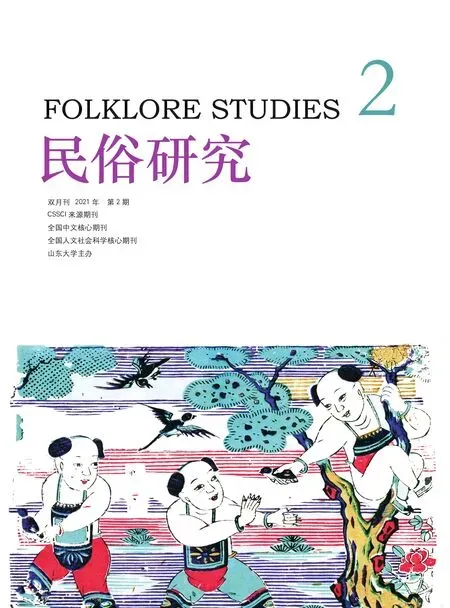如愿归去紫姑还:中古荆楚地母信仰与域外文化交融
海力波
西亚文化与华夏文化的交流成为近年来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除传统的历史文献与考古学研究外,民俗与民间文学研究也是探讨这一问题的重要视角。中古时期,以萨珊波斯、粟特为代表的西亚文化对华夏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求如愿”与“迎紫姑”习俗最早见于六朝时期的文献记载,一向被认为是各自独立的华夏传统民俗活动,但从六朝荆楚新年祭仪这一特定情境考察,却可发现两者在六朝时期共同构成荆楚地方文化中地母女神的死亡-复活仪式,在形成过程中还受到以植物之神“塔穆兹”信仰为核心的西亚农业祭仪的影响。宋代以后,求如愿故事的“反抗-逃亡”主题因与儒家礼教不符而被逐渐淡忘;迎紫姑故事“怨而不哀”的主题符合儒家的女德要求而得以流传至今。“如愿”已逝、“紫姑”尚存,这成为中原文化、荆楚文化与西亚文化交融互动的历史见证。
一、如愿与紫姑:地母女神的化身
求如愿故事最早见于东晋干宝《搜神记》“青洪君婢”篇:
庐陵欧明,从贾客,道经彭泽湖。每以舟中所有,多少投湖中,云:“以为礼。”积数年。后复过,忽见湖中有大道,上多风尘。有数吏,乘车马来候明,云:“是青洪君使要。”须臾达,见有府舍,门下吏卒。明甚怖,吏曰:“无可怖。青洪君感君前后有礼,故要君。必有重遗君者。君勿取,独求如愿耳。”明既见青洪君,乃求如愿,使逐明去。如愿者,青洪君婢也。明将归,所愿辄得,数年,大富。(1)干宝原著,黄涤明译注:《搜神记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7-118页。
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对求如愿故事及相关习俗的记载最为完整:
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谓之端月……鸡鸣而起……又以钱贯系杖脚,回以投粪扫上,云“令如愿”。
按《录异传》云:“有商人欧明者,过彭泽湖。有车马出,自称青洪君,要明过家,厚礼之,问何所需。有人教明,但乞如愿,及问,以此言答。青洪君甚惜如愿,不得已,许之,乃是一少婢也。青洪君语明曰:‘君领取至家,如要物,但就如愿,所须皆得。’自耳商人若有所求,如愿并为即得。数年遂大富。后至正旦,如愿起晚,商人以杖打之,如愿以头钻入粪中,渐没失所,后商人家渐渐贫。”今北人正旦夜立于粪扫边,令人执杖打粪堆,以答假痛。又以细绳系偶人投粪扫中,云“令如愿”,意者亦为如愿故事耳。(2)宗懔撰,宋金龙校注:《荆楚岁时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3页。
北宋高承《事物纪原》“捶粪”条记:
今人元日鸡鸣时,辄往积壤间捶之,云使人富,盖起自欧明也。今京东之俗犹然。(3)高承撰,李果订等点校:《事物纪原》卷八《岁时风俗部四十二》“捶粪”条,中华书局,1989年,第427-428页。
京东即京东路,包括豫东南、皖北、苏北、鲁南等地。(4)弓守奇:《北宋京东路经略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19-21页。可知北宋时求如愿习俗还流行于江淮之间,也即《荆楚岁时记》中“北人”所处之地。南宋时求如愿习俗仅见于江南,范成大《腊月村田乐府》中有《打灰堆词》记江南求如愿习俗:
除夜将晓,鸡且鸣,婢获持杖击粪壤致词,以祈利市,谓之打灰堆;此本彭蠡清洪君庙中如愿故事,唯吴下至今不废云。(5)范成大:《范石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409-410页。
南宋以后,求如愿习俗消逝于民间,各地方志中罕见此俗。(6)陈金文:《越南财神信仰与中国民俗文化》,《社会科学家》2014年第1期。但在六朝荆楚新年习俗中,还有另一习俗即迎紫姑习俗与求如愿之俗极为相似。以往研究多将迎紫姑与求如愿视为相互独立的习俗,但若对两者的故事、信仰与仪式加以比较,就可发现两者存在诸多联系。迎紫姑习俗亦见于《荆楚岁时记》:
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祀门户……今州里风俗,是日祀门户,其法先以杨柳枝插于左右门上,随杨枝所指,乃以酒脯饮食及豆粥、膏糜插箸而祭之……其夕,迎紫姑,以卜将来蚕桑,并占众事。(7)宗懔撰,宋金龙校注:《荆楚岁时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3-25页。
又,南朝宋刘敬叔《异苑》记紫姑故事:
世有紫姑神,古来相传云是人家妾,为大妇所嫉,每以秽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于厕间或猪栏边迎之,祝曰:“子胥不在”,是其婿名也。“曹姑亦归”,曹即其大妇也。“小姑可出戏。”捉者觉重,便是神来。奠设酒果,亦觉貌辉辉有色,即跳躞不住。能占众事,卜未来蚕桑。又善射钩,好则大舞,恶便仰眠。平昌孟氏恒不信,躬试往捉,便自跃茅屋而去。永失所在也。(8)刘敬叔:《异苑》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编:《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638页。
唐宋以后,迎紫姑习俗从荆楚江淮流传至全国各地,地方志中多有记录,明代刘侗《帝京景物略》卷二“春场”条记北方迎紫姑习俗:
望前后夜,妇女束草人,纸粉面,首帕衫裙,号称“姑娘”,两童女掖之,祀以马粪,打鼓,歌“马粪芗”歌,三祝,则神跃跃拜不已者,休;倒不起,乃咎也。男子冲而扑。(9)刘侗、于弈正著,栾保群注:《帝京景物略》卷二“春场”条,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67页。
再以清光绪八年(1882)刻本湖北《孝感县志》为例:
妇女先于“小除日”取粪箕之架埋厕侧,是夜洗净覆以女衫,仍画人面于上,焚香拜祝,两女持之,神来则自动扣地,谓之“拜问”者,但以拜之数为例。相传戚夫人死于厕为神,故曰戚姑。(10)丁世良、赵放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中国图书馆出版社,1991年,第329页。
诚如前文所引《异苑》记孟氏妇人将紫姑迎到家中后“平昌孟氏恒不信,躬试往捉,便自跃茅屋而去。永失所在也”的这则故事,实为孟氏男子违犯了迎紫姑仪式只能由女性操办的禁忌,试图接近、捉弄之,紫姑从屋中跃出逃逸,最后导致“永失所在”,其逃逸的情节与如愿的逃离极为相似。又如《显异录》“紫姑……正月十五日夜,阴杀于厕间”(12)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十三《紫姑神》,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417页。的相关记载,可知紫姑之结局亦与如愿相同,皆逃亡不遂而死于粪壤中。
如愿与紫姑同为身份卑微的女性,同见害于粪壤中,且因此成为财富与丰产女神。这是理解两者共同性的关键。魏晋六朝之时,“粪”多为垃圾、腐土之意。(13)杨荫冲:《“粪”字词义考释及其在古文献中的应用》,《湖北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东晋张华《博物志》称:
地以名山为之辅佐,石为之骨,川为之脉,草木为之毛,土为之肉。三尺以上为粪,三尺以下为地。(14)张华:《博物志》卷一“地”条,上海古籍出版社编:《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86页。
地表三尺之土为“粪”,也即如愿与紫姑投身之处。地表三尺土这一概念在汉魏六朝时还有着宗教上的神圣意义。东汉张鲁在《太平经》中称:
凡动土入地,不过三尺,提其上,何止以三尺为法?然一尺者,阳所照,气属天;二尺者,物所生,气属中和;三尺者,属及地身,气为阴。过此而下者,伤地形,皆为凶。(15)王明编:《太平经合校》卷四十五“起土出书诀第六十一”,中华书局,2014年,第226页。
可知地表三尺之土被认为乃天地阴阳中和万物生长之地,人类与万物的生命皆来自其中:
夫天地中和三气,内共相与为一家,共养万物。天者主生,称父;地者主养,称母;人者为治,称子。子者,受命于父,恩养于母……今人以地为母,得衣食焉。(16)王明编:《太平经合校》卷四十五“起土出书诀第六十一”,中华书局,2014年,第118-119页。
因此,教育需要“引”而非“领”,很显然,这种教育方式更优。正如黄侃所赞成的观念:术由师受,学自己成。“引导”这种教育方式能够使被教育者摆脱依赖的心理,从而产生极大的自主权。
“地,人之真母”或“地者,万物之母也”,大地被想象为具有生命与鲜活肉体的女性形象。(17)参见杜正乾:《论史前时期“地母”观念的形成及其信仰》,《农业考古》2006年第4期;叶舒宪:《中国上古地母神话发掘——兼论华夏“神”概念的发生》,《民族艺术》1997年第3期。地母是土地之神,《淮南子·说山训》引高诱注言“江淮谓母为社”(18)刘安撰,许慎注:《淮南鸿烈解》卷十六《说山训》,四部丛刊景钞北宋本。,又《史记·高祖本纪》集解引《礼乐志》云楚地称“地神曰媪”(19)司马迁:《史记》卷八《高祖本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342页。,它们皆可作为荆楚地母信仰存在的证据。地母被视为人与万物的起源,因此兼具人类始祖神的身份。如女娲不仅是华夏先民信仰的始祖神,也是地母神、创世神。(20)李祥林:《傩母·地母·人母——民间神灵信仰中的女娲形象》,《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李祥林:《女娲神话传说与中国傩戏神灵崇拜》,《民间文化论坛》2019年第2期。女娲原型即为大地,女娲抟土造人神话就是人由地中所生观念的表现。(21)陈建宪:《女人与土地——女娲泥土造人神话新解》,《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东汉应劭《风俗通义》云:

有趣的是,在女娲造人神话中,女娲引绳将泥土变化为人,而在如愿故事中,则是祭祀者用绳系住象征着女性的偶人投入土中,寓意人重新投入大地的怀抱,化为泥土;后者在结构上成为前者的镜像式反映,都在人与泥土间建立起相互转换的联系。无论是如愿投粪,或紫姑被埋于厕壤中,皆为古代“瘗埋”之礼即对地神祭礼的折射。以人祭祀地母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23)杜正乾:《论史前时期“地母”观念的形成及其信仰》,《农业考古》2006年第4期;[英]詹·弗雷泽:《〈金枝〉精要——巫术与宗教之研究》,刘魁立编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393-403页。荆楚地区的人祭之风由来久远。在距今8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湖南沅水高庙遗址中就发现了中国境内最早的人祭坑遗址。(24)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洪江市高庙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06年第1期。经分析,人祭的目的是为了祈求农业的丰产,说明当时已有地母信仰。(25)刘俊男、易桂花:《从地下文物看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宗教祭祀文化——兼论该地宗教与其他文明要素的关系》,《农业考古》2011年第1期。江苏铜山丘湾的商代社祀遗址显示当时江淮一带居民以立石为地母像,在遗址中发现作为人牲的人骨架22具,多有手脚被捆绑的痕迹,且为多次分层掩埋,说明以人祭地母是当地古俗。(26)俞伟超:《铜山丘湾商代社祀遗迹的推定》,《考古》1973年第5期。北宋时“巴峡之俗,杀人为牺牲以祀鬼,以钱募人求之,谓之‘采牲’”(27)马鸿波点校:《宋会要辑稿·刑法二》“禁约一”条,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4页。。南宋高宗绍兴年间有记:“至于杀人以祭巫鬼,笃信不疑,湖、广、夔、峡,自昔为甚,近岁此风又寝行于他路,往往阴遣其徒,越境千里,营致生人,以贩奴婢为名,每至岁闰,屠害益繁。”(28)马端临著,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文献通考》卷九十《郊社考》“杂祠淫祠”条,中华书局,2011年,第2773页。南宋洪迈在《夷坚志》中称“杀人祭祀之奸,湖北最甚”(29)洪迈著,何卓点校:《夷坚志》三志壬卷第四“湖北稜睁鬼”条,中华书局,2006年,第1497页。。除湖北外,宋代湖南仍有人祭之俗:“湖南风俗,淫祀尤炽,多用人祭鬼,或村民裒钱买人以祭,或捉行路人以祭。”(30)陈淳著,熊国祯、高流水点校:《北溪字义》卷下“鬼神”条,中华书局,1983年,第65页。《夷坚志》“建德妖鬼”条记安徽池州建德县有劫略行人祭神之陋习。(31)洪迈著,何卓点校:《夷坚志》甲志卷第十四“建德妖鬼”条,中华书局,2006年,第126页。“护界五郎”条记南宋江州即今江西九江有名为“护界五郎”的“妖鬼”之庙,恶少年劫掠行人杀之祭祀,以至庙中“堆积白骨无数”。(32)洪迈著,何卓点校:《夷坚志》三补“护界五郎”条,中华书局,2006年,第1803-1804页。江西抚州为古临川郡,与求如愿传说的发源地庐陵郡相毗邻。可知直至宋代,荆楚江淮之地仍存在人祭之风。以赣江-鄱阳湖为中心的庐陵郡,早在三千年前就已出现以新干大洋洲遗址为代表的青铜文明(33)周兆望:《六朝隋唐时期鄱阳湖——赣江流域的经济开发与持续发展》,《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打灰堆仪式中所用之钱杖为荆楚上古青铜文化元素。近年来,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考古发掘出一定数量的青铜权杖,研究者认为这些青铜权杖不同于中原地区的“鸠杖”,整体而言可视为一株简化的太阳树,是对古籍中“扶桑”“若木”“桃都”等承载日月的宇宙神树的模仿。(34)朗剑锋:《吴越地区青铜时代的太阳崇拜—— 一种青铜杖饰的文化解析》,《东南文化》2015年第4期。在这些青铜权杖的杖首、杖镦部位都有纵向分布的层叠的凸棱,棱上有云纹与锯齿纹,与三星堆考古文化中青铜神树上的玉璧型器一致,这些凸棱为玉璧的象征物,是铜制的玉璧模仿物。(35)俞伟超:《三星堆蜀文化与三苗文化的关系及其崇拜内容》,《文物》1997年第5期。打灰堆仪式中所用的“以钱贯系”之杖,在造型上与此类古青铜权杖极为相似,都是以金属币(璧)型贯穿于杖上,时间上前后相承,寓意上亦极相近,前者当是对后者的继承与模仿。
在荆楚古文化中存在的地母崇拜、神树崇拜是如愿故事、紫姑故事得以产生的历史背景与社会基础。地母的祭品自然以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少女为最佳。在献祭仪式中,牺牲往往也兼具神祇的身份。如愿与紫姑既是献祭给地母的祭品,同时也是地母的化身,因此具有女神的身份,虽然生前身份卑微,死后却可以具有带来财富与丰裕的神力。
二、荆楚新年祭的植物神话原型
年的初意就是谷物的生长,一年四季与谷物的生、长、收、藏相对应,谷物的生命周期也就是年度周期。五谷皆由地生,地母也是谷神。(36)[英]詹·弗雷泽:《〈金枝〉精要——巫术与宗教之研究》,刘魁立编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388-403页。谷物冬藏春生,地母亦复如是,每年秋冬谷物成熟、植物枯萎之时就是地母衰弱、死亡之际。冬去春来,植物复苏、谷物播种之时也就是地母复活、回返人间之时。地母在祭仪中周期性死亡与复活正是对植(谷)物冬藏春生的具象化表述,也是地母崇拜的重要元素。(37)[英]詹·弗雷泽:《〈金枝〉精要——巫术与宗教之研究》,刘魁立编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65-280页。人们对地母的祭祀仪式也包括送走衰弱的地母、迎来复活的地母两个部分,死亡仪式通常在谷物收割或年终之时举行,而复活仪式则通常在庄稼播种前夕或新年来临之际举行。(38)[英]詹·弗雷泽:《〈金枝〉精要——巫术与宗教之研究》,刘魁立编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91-323页。
如愿与紫姑两者皆为地母的化身,同神而异名,其故事亦各有侧重。如愿故事讲述的是女神与人发生冲突而逃离的主题,前文所引“如愿以头钻入粪中,渐没失所”的故事以人间失去地母的化身如愿而结束。紫姑故事则渲染地母复活重返人世的过程,祭祀的女性用稻草、桃枝或竹条制成紫姑的身体,为其穿衣打扮、描眉画目,赋予其人性化的形貌,就是在象征层面上令地母女神复活。前文所引“妇女先于‘小除日’取粪箕之架埋厕侧,是夜(正月十五日夜)洗净覆以衣衫,仍画人面于上”的记叙,尤可证迎紫姑实为复活仪式的看法。被埋入粪土中的粪箕之架多为竹制,其形与人的骸骨也有几分相似,正是紫姑骸骨的象征,因此妇女们才会将其洗净后“覆以衣衫,仍画人面于上”,象征着洗净死者的骸骨,为其增添血肉。此后“捉者觉重,便是神来”,则说明神灵已经附体于人偶之上,也即地母复活、再临人间。“小除日”即除夕前一日,恰好与正旦凌晨、如愿被瘗埋入土之时相符,如愿血肉化为春泥,唯余骸骨,紫姑之骸骨实亦为如愿之骸骨,而紫姑之复活其实也是如愿之复活。在叙事逻辑上,紫姑故事堪为如愿故事的后续,而在仪式过程上,求如愿表现的是女神的离去与死亡,迎紫姑表现的是女神的回归与复活,两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仪式过程:在新年正旦曙光之时,送走地母女神;在正月十五暮色之时,迎接地母女神的复活。
正月是冬春两个季节交替的中间时段,也是地母死亡与复活之期,因此兼具神圣与危险双重属性。人们更进一步联想到时间秩序本身的死亡与新生,即年岁的更迭也意味着时间的生死:
换言之,时间被分为独立的单位“年”时,我们见到的不仅是某一时段的停止以及另一时段的新始,也见到过去一年与过去时间的泯除……每一“新年”都是时间之源的再开始,也是宇宙开辟之重返……在一年结束,以及对于“新年”的期待中,混沌化为宇宙的神话时刻重现了。(39)[美]M·耶律亚德(Mircea Eliade):《宇宙与历史:永恒回归的神话》,杨儒宾译,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6年,第50页。
新年为死生契机,故需要举行仪式以确保植(谷)物、地母乃至整个宇宙时空的平安复活。原初的春节正是“时间生死观”指引下的祭祀仪式(40)薛红艳:《中、日、韩岁时更迭祭祀的“时间生死观”》,《民族艺术》2001年第3期。,也是神圣与世俗的二度转换(41)张士闪:《春节:中华民族神圣传统的生活叙事》,《河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春节作为岁时通过仪式,是旧岁与新岁相交接的阈限阶段,而除夕夜与新年正旦的交接时段更是阈限中的阈限,因此也具有更大的神圣性与神秘性。(42)[美]M·耶律亚德(Mircea Eliade):《宇宙与历史:永恒回归的神话》,杨儒宾译,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6年,第60-64页。
前引《荆楚岁时记》中将新年第一日称之为正旦,即“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元,始也”。所谓三元,指岁之元、时之元、月之元,即时间的开始。正旦为新年之始,正旦前夜正是新旧交替的宇宙混沌之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危险性,因此古人才将“年”视为凶恶的怪兽。求如愿仪式却必须在正旦“夜将晓、鸡且鸣”之时,也就是旧年即将过去、但新年还未真正来临、正处于阈限中的阈限之时举行,说明如愿的离去不仅象征地母的消逝,也寓意旧年的结束。如愿之所以晚起被责,就在于象征旧年的如愿不在正旦来临之前离去,岂不占据了本该属于新年的位置!
六朝荆楚新年在正月望日即十五日结束。“望日祭门,先以杨柳枝插门,随杨枝所指,仍以酒脯饮食及豆粥插箸而祭之。其夕,迎紫姑神以卜。”(43)宗懔撰,宋金龙校注:《荆楚岁时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3-25页。祭门与迎紫姑于同一日举行,两者亦有关联。清代俞樾曾引《嘉定县志》来记述江南民间迎紫姑神的仪式,“群女以笊篱偷门神糊于上,画成人面,以柳枝为身,以衣覆之,神来即能拜”(44)俞樾撰,贞凡等点校:《茶香室丛钞》四钞卷一“上元日箕帚诸卜”条,中华书局,1995年,第1479页。,可知民间亦有将紫姑视为门神、以柳枝为紫姑化身的观念。杨柳枝头春意闹,意味着万物复苏,民间还将杨柳视为女性生育力与繁殖的象征。因此望日白天的祭门仪式也是为地母复活做准备,杨柳盈门是地母新生、重返人世的征兆,枝条所指乃地母降临的方向,其夕为迎接地母重返人间而举行的神秘仪式。在西亚和欧洲很多民族中,人们认为地母女神或谷神在经历了一年的劳作之后,已经精疲力竭,不再具备保佑丰产的能力,故要在新年来临之前举行仪式,将用作物根茎做成的、代表着“五谷妈妈”的人偶驱逐出村庄。人偶在仪式中被人们辱骂、驱逐与杖打,最后被埋葬在粪堆之下,随后人们又从森林中找来绿枝条绑扎为人偶,将其迎回村落中,这被认为有利于生命和增殖。(45)[英]詹·弗雷泽:《〈金枝〉精要——巫术与宗教之研究》,刘魁立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65-280页。不难看出求如愿、迎紫姑习俗与此所具有的相似之处。
求如愿与迎紫姑仪式在新年祭仪的开始与结束之时举行,恰与时间秩序的死亡与新生同步,其神迹与诸多仪式细节皆与土地崇拜、丰产祈求和死亡-复活的植物神话有联系,更可证其为地母死亡-复活祭祀仪式的表现。
三、“塔穆兹”信仰:荆楚文化中的西亚文化元素
求如愿与迎紫姑之信仰皆源自荆楚文化中古老的地母崇拜,但地母崇拜与新年祭仪、死亡-复活仪式元素的结合非源自荆楚本土。细究其背景,可发现其受到西亚“塔穆兹”祭仪的影响。
新年中神祇的仪式性死亡与复活,少见于中原地区民俗活动,但在古代中亚花拉子模布哈拉地区,却有相近风俗。当地新年时要将泥塑的神像毁坏,再当着国王的面,重新塑造新的神像。(46)龚方震、晏可佳:《祆教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166页。据唐代杜佑《通典》所记,此俗名为“哭神儿”:
康国人并善贾……其人好音声,以六月一日为岁首……俗事天神,崇敬甚重,云神儿七月死,失骸骨,事神之人每至其月,俱著黑叠衣,徒跣抚胸号哭,涕泪交流。丈夫妇女三五百人散在草野,求天儿骸骨,七日便止。(47)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一百九十三《边防》,中华书局,1992年,第5256页。
康国为中古粟特“昭武九姓”之一,地处今中亚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以撒马尔罕为中心,该国居民以印欧人为主,语言上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东伊朗语支。以康国为代表的中亚粟特地区,中古时有新年期间哀悼年少之神(神儿、天儿)死亡、庆祝其复活之俗,所谓神灵骸骨当为塑像碎片,将神像碎片散弃于草野中,意味着神灵的死亡,哀悼七日后,再塑新像即代表着神灵的复活。“哭神儿”习俗源自西亚,为西亚“塔穆兹”崇拜的变种。粟特文化受波斯影响极大。康国人信仰的波斯祆教即琐罗亚斯特教、拜火教,塔穆兹为祆教中谷物与春天之神,也是死亡与复活之神。塔穆兹因其美貌被地狱女神艾里斯基伽尔所垂涎,将其扣留于地狱中,化为僵尸,从此大地丧失生机与活力。其恋人爱神伊斯塔尔求助天神埃阿,天神命令地狱女神将生命之水交给伊斯塔尔,后者用神水洗净塔穆兹身体,为其涂上香膏,穿上红袍,吹响玉笛,让他复活重返人间,大地也因此恢复活力。但根据地狱女神与天神的协定,塔穆兹每年要下到地狱陪伴艾里斯基伽尔六个月,只有其余六个月方能在人间与恋人相厮守。为了确保万物复苏,古巴比伦与波斯每年都会举行塔穆兹祭仪,重演其从地狱复活的故事。塔穆兹死亡之日,女人们会在夜里高举火把号啕大哭,将塔穆兹的雕像埋葬。待到塔穆兹回返人间之日,人们会用清水洗净其雕像,涂上香膏,裹以红袍,对着雕像颂唱挽歌,以刺激其苏醒。(48)[英]詹·弗雷泽:《〈金枝〉精要——巫术与宗教之研究》,刘魁立编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93-294页。
波斯与粟特地区的夏至前后为谷物收获之时,也为新年之始,祆教教历规定每年六月一日为新年,要举行被称为诺鲁孜节的新年庆典;又以仲夏之月为塔穆兹月,在该月举行为期七日的塔穆兹死亡-复活祭仪,该月被称为“大诺鲁孜”,也被视为新年的一部分。祆教徒认为在此期间,不仅谷物与各种植物复苏,整个宇宙亦被重新创造,国王宣布:“这是一个新年新月新天,一切过去的时间于兹更新!”(49)[美]米尔恰·伊利亚德:《神圣的存在:比较宗教的范型》,晏可佳、姚蓓琴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77-378页。古代中东、地中海世界中的死亡-复活观念被认为起源于古巴比伦塔穆兹崇拜,发扬光大后传播至地中海世界各地,在埃及被称为奥锡利斯,古希腊称为阿多尼斯,罗马称为阿蒂斯,都被视为谷物之神的化身,也都以死亡-复活祭仪为信仰的表现。(50)伍玉西:《古代中东、地中海世界的死人复活信仰》,《世界宗教文化》2009年第1期。
塔穆兹祭仪经中亚粟特文化为中介传入中国,融入中国传统节日“七夕”中,令唐宋时期的七夕节增添鲜明的域外文化色彩。(51)刘宗迪:《摩睺罗与宋代七夕风俗的西域渊源》,《民俗研究》2012年第1期。但本文认为,塔穆兹祭仪影响所及应该不限于七夕,求如愿、迎紫姑之俗也受到塔穆兹祭仪的影响。粟特文化在南朝时对长江中下游荆楚地区影响也颇为深远。南朝时期,粟特人信仰的祆教在江南流行较广,粟特胡商或泛海至岭南,辗转至长江流域,或从西域至蜀地,或从关中南下襄阳,再进入江陵地区,荆襄为南北交通枢纽,也因此成为长江流域粟特人聚居之地。(52)荣新江:《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流域南方的粟特人》,韩昇主编:《古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多元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38-152页。此外,东晋江州安城郡也是长江中下游粟特人聚居之地,当地有来自昭武九姓中安国(今布哈拉)的祆教巫师,奉祆教密特拉神,行火幻术,影响颇大。(53)姚潇鸫:《东晋时期流寓南方的粟特人补说》,《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东晋江州包括“扬州之豫章、鄱阳、庐陵、临川、南康、建安、晋安,荆州之武昌、桂阳、安城,合十郡”(54)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十五《地理下》,中华书局,1974年,第462-463页。,安城郡地处今江西中部偏西,与湖湘相邻,有庐水与鄱阳湖相通。荆襄江州之地为荆楚文化核心地区,六朝时当地有大量粟特移民居住,如襄阳地区有来自昭武九姓中康国的康绚一族,经陇右、山西蓝田“举乡族三千余家入襄阳之岘南,宋为之置华山郡蓝田县,寄居于襄阳……并为流人所推,相继为华山太守”(55)姚思廉:《梁书》卷十八“康绚”条,中华书局,1983年,第290页。。可知南朝宋时仅襄阳岘南一地就有粟特移民三千余家之众,至今在襄阳岘山脚下还有康湾村、石湾村、曹湾村等以粟特姓氏为名的村落,村民身材、面目酷似中亚人种,极可能为粟特移民的后裔。(56)李梅田:《长沙窑的“胡风”与中古长江中游社会变迁》,《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5期。众多粟特胡人于荆楚之地生息繁衍,自然会对当地文化产生影响,学界熟知陈寅恪指出《柳毅传》中“火道士”为火祆教祭司、饶宗熙指出巴蜀“穆护歌”为祆教祭神颂歌。此外,荆楚新年礼俗中也有粟特祆教成分,与本文主旨关系甚密。
《荆楚岁时记》中记腊日“村人并击细腰鼓,戴明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大疫”(57)宗懔撰,宋金龙校注:《荆楚岁时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2页。。腊日驱疫虽为中国传统习俗,但驱疫之神已由先秦时之方相变为印度佛教中的金刚力士,还要戴面“如胡人状,做勇力之势”。胡公乃老年胡人的称谓,所跳的驱疫舞被称为“文康舞”,初始于荆襄,流传于江淮间,其源头是来自中亚粟特的康国歌舞(58)李梅田:《西曲歌与文康舞:邓县南朝画像砖墓乐舞图新释》,《故宫博物院院刊》2016年第4期。,属于南朝流行的“西曲”之一。西曲是南朝时流行于荆、郢、樊、邓地区的民间歌舞,刚健清新,颇显异域风情,与宫廷雅乐和建康吴歌风格都不相同,为荆襄一带“蛮夷”所创。所谓荆襄“蛮夷”,除世居当地山区“不服王化”的土著族群外,也包括大量原来从西域迁入中原、又徙居荆襄的粟特部民,南朝荆襄民间歌舞与民间信仰也因此渲染粟特胡风。(59)李梅田:《西曲歌与文康舞:邓县南朝画像砖墓乐舞图新释》,《故宫博物院院刊》2016年第4期。除腊日驱疫外,荆楚新年礼俗中还有别具特色的“人日”信仰:
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剪彩为人,或镂金箔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
按董勋《问礼俗》曰:“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羊,四日为猪,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以阴晴占丰耗。”……北人此日食煎饼,于庭中作之,云“薰天”,未知所出也。(60)宗懔撰,宋金龙校注:《荆楚岁时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16页。
正月一日为鸡、至七日为人被认为是天地初开时之事,已有学者指出当与创世神话相关。(61)叶舒宪:《人日之谜:中国上古创世神话发掘》,《中国文化》1989年第1期。更有学者指出这一神话与祆教经典《阿维斯塔》中所记祆教主神六次创世,创造出天空、江河、大地、植物、动物与人类并于第七日举行诺鲁孜庆典的神话极为相近。(62)赵洪娟:《中古人日节与波斯诺鲁孜节渊源考——基于比鲁尼〈古代民族编年史〉的探讨》,《民族文学研究》2019年第2期。在诺鲁孜庆典中,祆教徒要在庭院中设置火坛,祭祀天神,即所谓熏天之俗的由来。塔穆兹祭仪中,妇女们在填满泥土的花盆瓦罐里种上小麦、大麦、莴笋、茴香等作物,并照管八日,作物受太阳热能培育而快速成长,又因无根而很快枯萎,妇女们以八日内作物的长势来预测一年内此种作物的丰歉。第八日则将瓦罐及其中的作物砸碎后弃于水中或野外,以此作为塔穆兹年度性死亡的象征。(63)[英]詹·弗雷泽:《〈金枝〉精要——巫术与宗教之研究》,刘魁立编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310-319页。粟特地区的塔穆兹祭仪中也有此内容。(64)刘宗迪:《摩睺罗与宋代七夕风俗的西域渊源》,《民俗研究》2012年第1期。以粟特为中介,这一环节传入荆楚地区,演变为新年中“以七种菜为羹”“以阴晴占丰耗”之俗。(65)赵洪娟:《中古人日节与波斯诺鲁孜节渊源考——基于比鲁尼〈古代民族编年史〉的探讨》,《民族文学研究》2019年第2期。在此过程中,原为男性神灵的塔穆兹也为适应荆楚文化中原有的地母信仰而变为女神形象,恰如观世音菩萨传入中国后由男性而变为女神。
与波斯诺鲁孜庆典相似,荆楚新年也是创世神话的年度性展演。(66)吕微:《神话何为——神圣叙事的传承与阐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59-190页;田兆元:《节日神话:概念及其结构——以〈荆楚岁时记〉为中心的讨论》,《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将新年开端的求如愿与结束时的迎紫姑视为一个完整的仪式。与塔穆兹祭仪相比较,可发现更多的相似之处:
塔穆兹祭仪为新年时举行的土地之神(植物之神)的死亡-复活仪式,也象征着宇宙的重新创造;求如愿、迎紫姑仪式也是地母的死亡-复活祭祀仪式,具有宇宙论的意义,在新年开始与结束时举行。
塔穆兹因非自愿的婚姻关系而死,待摆脱恶劣的婚姻关系后方得以复活;如愿、紫姑被迫为侍妾婢女并因此惨死,与塔穆兹相类似,如愿逃归方才成神,紫姑不与子胥、曹姑相遇,方会降临人间。
塔穆兹祭仪以神灵的死亡-复活为核心,将仪式分为时间上相分离的两部分,历时七日方完成;塔穆兹死亡时人偶被毁坏埋葬,复活时人偶被装饰一新。如愿与紫姑故事分别以死亡与复活为主题,两故事在叙事逻辑上相衔接,人偶如愿被埋入粪壤中,十五日后,紫姑复活,被重新制成人偶。无论七或十五,在各自文化中都是神圣数字,具有宗教含义。
塔穆兹祭仪由女性在深夜时于屋顶、园圃等隐蔽处举行,祭仪颇为神秘,有占卜农桑之效,尤不可令男性参与,犯禁者甚至可能被处死,在此基础上形成被称为希腊秘仪的宗教形式。(67)王来法:《古希腊及罗马的Μνστηριον(神秘仪式)》,《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1期。求如愿、迎紫姑仪式也有对男性的禁忌,从举行的时间、地点与目的看,也颇有几分秘仪的味旨。唐《显异录》记“紫姑,莱阳人。姓何,名媚,字丽卿。寿阳李景妾也。大妇曹氏,于正月十五夜,阴杀之厕间”(68)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十三《紫姑神》,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417页。。何、曹虽为中土姓氏,但粟特昭武九姓有康、安、曹、史、米、何、史、穆、毕等国,入华者多以国号为姓。(69)许序雅:《粟特、粟特人与九姓胡考辨》,《西域研究》2007年第2期。曹姓、何姓为入华粟特人中常见的姓,紫姑得名也极可能与粟特文化有关。西域胡姬擅歌舞、喜音乐,据《荆楚岁时记》杜公瞻注称紫姑一说为“帝喾女,将死,云‘生平好乐,至正月可以见迎’”,(70)宗懔撰,宋金龙校注:《荆楚岁时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5页。可知紫姑生前美丽妩媚,又喜好歌舞音乐,颇近于六朝时人对胡姬的印象。
吕微指出如愿故事与印度《梨俱吠陀》所记“摩奴与伊达”洪水创世神话相似。神话中,人类始祖摩奴救助了神鱼,神鱼为报恩嘱咐其常年向水中献祭,得到水中所生的女性伊达,世界大洪水过后,摩奴与伊达共同苦修,繁衍生育出众多子嗣,也令世界重新萌生万物。三国时,居于吴国的康居人康僧会把摩奴与伊达故事收入其编译的《六度经集》中传入中土。(71)吕微:《神话何为——神圣叙事的传承与阐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37-319页。不难发现,摩奴与伊达故事与《搜神记》所记如愿故事的原型“青洪君婢”相近,都以“向水中献祭-受秘嘱-得水中女性-致富”为故事的母题链。可知如愿故事也受到南亚、西亚文化的影响而产生。
粟特人以绿洲灌溉农业见长,粟特胡人入华,虽多以经商、从军为业,从事农业生产者,实亦不少,古代山西的葡萄种植业就因粟特移民而兴盛。建康城外有茄子浦,为胡人所居,以多种茄子而得名。茄子源自印度,后传入粟特地区,粟特人入华后,先于成都平原栽种,后传播于长江中下游,再传至北方。(72)姚潇鸫:《东晋时期流域南方的粟特人补说》,《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从事定居农业的粟特人与荆楚土著居民互动更为密切,繁衍生息、丰产富足是双方共同的心愿,西亚的植物神死亡-复活信仰与荆楚本土的地母崇拜在观念上本就相近,为东西方农业文明所共有,塔穆兹祭仪与荆楚地母崇拜相结合,演化为求如愿、迎紫姑习俗。地母崇拜虽为荆楚本土元素,但传统的祭仪本当遵循春祈秋报的时间规范,每年立春、立秋后第五个戊日为春社、秋社之时。《荆楚岁时记》中也有“社日,四邻并结宗会社,宰牲牢,为屋于树下。先祭神,然后享其胙”(73)宗懔撰、宋金龙校注:《荆楚岁时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3页。的记载。这也说明荆楚之地另有祭祀土地之神的原生仪式,求如愿、迎紫姑中体现的地母女神死亡-复活仪式并非本土元素,更可确认其西亚文化渊源。
四、三元和合:荆楚、中原与域外文化的交融
自新石器时代至先秦时期,荆楚文化自成一脉,可与中原文化相拮抗。(74)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导言”第1页。《汉书·地理志下》称楚地“信巫鬼、重淫祠”(75)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中华书局,2005年,第1327页。,《晋书·地理志》称“荆,强也,言其气躁强。亦曰警也,言南蛮数为寇逆,其人有道后服,无道先强,常警备也”(76)房玄龄等:《晋书》卷十五《地理下》,中华书局,2010年,第453页。,可知在中原视角中,荆楚之地在六朝初期仍然是华夏化极低、充满“蛮夷”的他者之地。但随着六朝时对江南各地的开发,长江中下游渐成乐土。《隋书·地理志》称长江下游鄱阳、庐陵一带“自平陈之后,其俗颇变,尚纯质,好简约,丧纪婚姻,率渐于礼……然此数郡,往往蓄蛊”,至于荆州之襄阳、九江、江夏诸郡,则“其风俗物产,颇同扬州……诸郡多杂蛮左……颇与巴、渝同俗……自晋氏南迁之后,南郡、襄阳,皆为重镇,四方凑会,故益多衣冠之绪,稍尚礼义经籍焉。九江襟带所在,江夏、竞陵、安陆,各置名州,为藩镇重寄,人物乃与诸郡不同。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77)魏征、令狐德棻:《隋书》卷三十《地理中》,中华书局,1997年,第887-897页。经六朝生息繁衍,荆楚扬州虽然“多杂蛮左”,仍有“蓄蛊敬鬼”等陋俗,但整体上已经成为华夏体系中的重要一部分。唐代中叶至南宋时,长江流域已经反超中原地区,成为中国乃至东亚经济文化最发达的核心地区。(78)牟发松:《汉唐历史变迁中的南方与北方》,《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1期。
荆楚土著居民在此历史大进程中渐渐被中原儒家礼教所涵化,其风俗信仰也发生重大改变。自两汉后,民间出现“社公”之称,地母崇拜变为对男性社公的信仰。(79)龚维英:《古神话和仙话中地祇的变性探研》,《池州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至宋代杀人祭神之俗被严厉禁绝。如宋太宗淳化元年(990)下诏“禁川陕、岭南、湖南杀人祀鬼”(80)脱脱等:《宋史》卷五《大宗本纪二》,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后宋仁宗又于天圣六年(1028)诏云对荆湖地方“四路采生之人,并行收捉,邻甲照已排立保伍,互相举觉,赏钱三千贯,仍许诸色人陈告,如有违犯,不分首从,并行凌迟处斩,家属断配,家业抄籍充赏”(81)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下),中华书局,1987年,第546页。。至宋高宗十九年(1149)又下诏“禁湖北溪峒用人祭鬼及造蛊毒,犯者保甲同坐”(82)参见李燕:《宋代对民间巫术犯罪的法律规制》,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23页。。此后荆楚一带杀人祭祀之俗也被历朝所禁绝。地母崇拜与人祭习俗至宋代已淡出人们视野,求如愿、迎紫姑习俗的社会文化土壤消失,人祭仪式蜕变为偶人木杖的游戏,两习俗与地母崇拜的关系及地母崇拜本身也被人们淡忘,仅仅在故事中留下对古老的地母崇拜与人祭仪式的曲折追忆。
安史之乱后,胡风稍息,来华胡人逐渐汉化。(83)周伟洲:《一个入华西域胡人家族的汉化轨迹——唐〈戎进墓志〉〈戎谅墓志〉续解》,《西域研究》2019年第2期。粟特人在新年祭礼中所举行的戏乐名为“苏摩遮”,又名“泼胡乞寒戏”,对于唐代戏剧、音乐、舞蹈、宗教信仰都有极大影响,也被视为中国古代仪式剧的开端,但在唐玄宗开元年间仍然因其“滥觞胡俗”“深玷华风”而被官方禁断。(84)柏红秀、李昌集:《泼寒胡戏之入华与流变》,《文学遗产》2004年第3期。至唐末时,粟特人的新年“苏摩遮”祭祀仪式已被禁绝,某些粟特移民在野外秘密举行该仪式,甚至被偶尔窥见的樵夫乡民视为妖孽魔怪而大为惊骇。(85)海力波:《从〈庐江民〉看唐代志怪中的祆教仪式》,《文化遗产》2018年第1期。粟特文化在民间影响力渐渐式微,求如愿、迎紫姑与西亚塔穆兹祭仪的关系也因此被淡化,两仪式相隔十五日,被视为相互独立的礼俗,其内在关联性也被人们遗忘。
宋以后,求如愿习俗消失,如愿故事与印度传入龙女故事相结合,明代以后部分龙女故事中,龙女甚至直接以如愿为名,两者合二为一,成为中国龙女故事的一大特色(86)龚浩群、熊和平:《娶得龙女 事事如愿——“龙女”故事解析》,《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也是印度龙女故事中国化的重要标志。(87)刘守华:《中印龙女报恩故事之比较》,《中国比较文学》1999年第3期。但在相关的龙女故事中,反抗-逃离的母题消失了,如愿变身为对丈夫忠贞且为其带来财富与好运的妻子,与六朝时的如愿已经判若两人。如愿故事之所以被冷落、被改造,其原因大概在于,如愿作为婢女反抗主人的命令甚至勇敢逃离的行为在儒家正统观念看来无疑是不能容忍的,是对尊卑等级秩序的冒犯,也是荆楚地区“未开化的”“蛮夷”之风的标志。在开发荆楚的过程中,奴婢的主要来源就是荆楚的土著居民,六朝地方官员常常以抓捕蛮夷的数量为政绩。(88)王玲:《魏晋六朝荆襄地方官吏与经济开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1期。如南朝宋时,沈庆之“自江汉以北,庐江以南,搜山荡谷,穷兵罄武,系颈囚俘,盖以数百万计”(89)沈约:《宋书》卷九十七《夷蛮传》,中华书局,2006年,第2399页。,“庆之前后所获蛮,并移京邑,以为营户”(90)沈约:《宋书》卷七十七《沈庆之传》,中华书局,2006年,第1998页。。在此过程中,奴婢的反抗与逃亡亦不胜枚举。前引《隋书·地理志》称荆州“诸郡多杂蛮左,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多不别……其相呼以蛮,则为深忌”(91)魏征、令狐德棻:《隋书》卷三十《地理中》,中华书局,1997年,第897页。。为避免“污名化”的身份,这些被迫移居城邑、成为荆襄下层民众的蛮夷及其华夏化的后代,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在集体记忆层面回避乃至淡忘其反抗-逃亡的历史及被认为沾染蛮风的习俗。在宋代律法宣布人祭为非法之后,长江下游的打灰堆习俗中,也就不再出现将人偶投于粪堆中的环节,这一有趣的细节可作为佐证,即底层民众在某种自我审查之下,也在精英与下层民众的合谋之下,如愿及其反抗-逃亡的母题被回避、被淡忘,最终消失于人们的记忆中。
与如愿故事不同,迎紫姑习俗在宋代以后并未消失,反而流传更广,几乎遍及中原各地。唐代及唐代以前,迎紫姑之俗主要流行于乡间,宋代开始,文人雅士亦热衷迎紫姑(92)赵卫邦:《扶箕之起源及发展》,岳永逸、程德兴译,王雅宏校,《民间文化论坛》2019年第1期。,并将仪式改造为高雅的游戏(93)黄景春:《紫姑信仰的起源、衍生及特征》,《民间文学论坛》1996年第2期。,如北宋沈括《梦溪笔谈》所记:
旧俗正月望夜迎厕神,谓之“紫姑”。亦不必正月,常时皆可招……其家亦时见其形,但自腰以上见之乃好女子,其下常为云气所拥……近岁迎紫姑者极多,大率多能文章歌诗,有极工者,余屡见之,多自称蓬莱谪仙,医、卜无所不能,棋与国手为敌。(94)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一《异事》,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180-181页。
宋代以后的紫姑已经变形为可与文人唱和酬答的女仙或女史形象,其被文人所推崇的原因在苏轼《子姑神记》中表述甚详:
余观何氏之生,见掠于酷吏,而遇害于悍妻,其怨深矣。而终不指言刺史之姓名,似有礼者。客至逆知其平生,而终不言人之阴私与休咎,可谓智矣。又知好文字而耻无闻于世,皆可贤者。(95)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十二卷《子姑神记》,中华书局,1990年,第406-407页。
正因为紫姑虽然被主人杀害于厕,却始终不肯道出主人的名字,怨而不哀,谨守主奴的尊卑名分,至死不敢忤逆,于礼法而言最为恭顺,才得到苏轼等文人的赞赏和喜爱。文人们还给紫姑附会上不言人之阴私的君子之风以及耻于文章不达的文人习气,实际上是借紫姑之名来咏叹际遇、寄托情怀(96)林继富:《紫姑信仰流变研究》,《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刘勤:《试论苏轼对紫姑神的矛盾态度》,《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但同时也令紫姑的形象与迎紫姑习俗得以雅化并具有更顽强的生命力,流传甚广。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北方的胡化与江南的华夏化进程同时进行。汉魏西晋王朝所褒扬的华夏文化自永嘉南渡后,与荆楚地方文化相结合,变得更为丰富辉煌,成为当时中华文化的主流和代表,令华夏文脉在江南保持了强劲的生命力,也间接推动了北方胡族王朝的华夏化进程。近年来,长江中下游地区六朝时期的华夏化过程得到史学界的关注,但论者多关注华夏化进程的政治层面,即当地的土著居民如何在制度与政治上被纳入华夏统治秩序中(97)胡鸿:《六朝时期的华夏网络与山地族群——以长江中游地区为中心》,《历史研究》2016年第5期。,而对于文化维度上的华夏化进程,则由于资料上的缺乏,少有论及。从地母崇拜的演变,可看出荆楚之民在其地方性知识传统的基础上,借鉴域外文化的元素,创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地方文化传统。在华夏化进程中,荆楚地方文化并非被动地接受中原文化的涵化过程,为了避免受到“污名化”打击,放弃了可能被视为“蛮夷之风”的部分文化元素,在《荆楚岁时记》中有意识呈现出“腊鼓鸣,春草生”的南方意向。自居华夏文化核心的文人精英阶层也与底层民众一道将地方性的、民间的文化元素打造为华夏文化的有机部分。华夏与华夏文化本来就不是僵化之物,地方文化、域外文化及其承载者在华夏化过程中不断地被吸收入华夏文化与华夏群体中,也令华夏这一概念常在常新,如同亘古不变的大地般具有伟大的活力、包容力与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