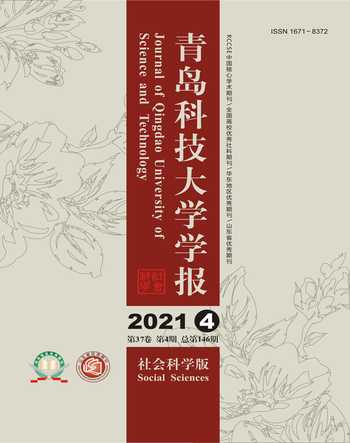中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制度缺陷及改革思路
王金堂 赵许正
[摘 要]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作为一项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非常态制度在国内外得到了立法支持。我国虽然构建了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框架,但至今仍处于“零实施”状态,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标准的缺失与立法缺陷是造成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未能付诸实践的重要因素。中国药品专利许可制度需要在利益衡量原則的指导下,充分利用TRIPS协议赋予的自主决定权,改革僵化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启动机制,在切实保障专利权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完善相关立法。
[关键词]药品专利;专利强制许可;药品可及性;TRIPS
[中图分类号]D923.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21)04-0063-07
The system defects and reform ideas of compulsory licensing of pharmaceutical patents in China
WANG Jin-tang,ZHAO Xu-zheng
(Law School,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Qingdao 266061,China)
Abstract:As an abnormal system to deal with sudden public health crisis,compulsory licensing of pharmaceutical patents has been supported by legisl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Although China has built the framework of compulsory licensing of pharmaceutical patents,it is still in the state of“zero implementation”. The lack of compulsory licensing of pharmaceutical patent standards and legislative defects are the important factors that cause the system to fail to be put into practice.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principle of balance of interests,we need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independent decision power granted by TRIPS to reform the rigid starting mechanism of compulsory licensing,and improve relevant legislation on the basis of effectively protecting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patentees.
Key words:pharmaceutical patents; compulsory licensing of patents; drug accessibility; TRIPS
药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部分药品或药品的制造方法被授予专利后,市场上会形成高昂的价格与作为社会必需品的药品的可负担性和可及性要求之间的尖锐矛盾。有学者研究,一支治疗乳腺癌的“赫赛汀”售价为24500元[1],完成治疗周期一般需要使用12支,这意味着患者一个周期的治疗费用就高达294000元,以我国2020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000元[2]计算,我国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仅够支付一支原研药物的费用。导致药品价格昂贵的因素是多重的,其中专利因素是最主要的。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披露的数据显示,2002年“格列卫”进入中国市场时,价格为每盒23500元,患者一年的治疗费用超过28万元,而2013年国内制药企业生产的与“格列卫”功能相同的仿制药甲磺酸伊马替尼(昕维)上市并于2018年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每盒价格不到专利药的1/9,大大降低了病患的医疗负担[3]。同样,罗氏公司生产的原研药头孢曲松钠每克价格高达80多元,而国产药为4~5元,仅就价格而言,两者相差近20倍[4]。原研药与仿制药价格的主要区别正在于后者不含专利成本,由此可见药品专利费用在部分药品价格中所占权重之高。
通常而言,专利药的研发周期长、费用高、风险大,为弥补研发成本,专利费用高昂是药品专利持有者采取的市场行为和经营策略,也是国内外药品研发厂商的通常做法。如何降低专利费用进而降低专利药品价格不仅是缓和专利权与公众健康要求之间矛盾的重要手段,还是完善药品专利制度的客观需求。
一、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立法及实践现状分析
(一)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立法沿革
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指的是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根据申请,不经专利权人许可向第三方授权实施专利并由被许可方支付一定专利使用费的法律制度。我国的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与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以下简称《专利法》)同时诞生,1984年《专利法》专设第6章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而第6章专利强制许可第25条同时明确规定对药品和用化学方法获得的物质不授予专利,药品专利的强制许可也就无从谈起。这样的规定是为了推动国内医药行业的发展,同时减轻国家在公共卫生安全方面的负担。20世纪90年代受中美贸易争端影响,我国在1992年对《专利法》进行修改,修改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便是将药品纳入专利保护范围,同时规定在特定情形下可以给予专利强制许可,这些内容构成了我国早期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框架。2008年《专利法》的第三次修订侧重于从立法层面平衡药品专利权人和社会公众健康之间的利益冲突,明确规定为了公共健康目的可以给予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并将药品出口至特定的国家和地区,此规定顺应了国际社会越发重视公共健康的大趋势。2020年《专利法》引入开放许可制度,这一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许可双方谈判的难度和交易费用,促进专利的市场供求对接和充分利用。
国务院于2001年颁布的《专利法实施细则》规定,给予专利强制许可的决定应限定于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这一举措并不是我国对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主动调整,而是为了与TRIPS协议保持一致。2003年,国内外共同面临危及人类健康的SARS危机,国家知识产权局随即颁布《专利实施强制許可办法》(简称《办法》),细化了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运作方式,但《办法》也存在“合理期限”界定模糊、被许可人举证负担较重等不足。2005年印发的《涉及公共健康问题的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简称《公共健康办法》)解释了“药品”“传染病”以及“国家紧急状态”“公共利益”的含义,彰显了我国在立法上对公共健康问题的重视。2012年出台了新修订的《办法》,宣布废止2003年《办法》和2005年《公共健康办法》,同时将上述两个文件中的专利强制许可审查决定、专利使用费裁决以及专利强制许可终止等进行统一,使得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程序性和可操作性较之以前更强。
总体来看,我国对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规定主要是为了落实《TRIPS协定与公共健康多哈宣言》《关于执行<TRIPS协定与公共健康多哈宣言>第六段的总理事会决议》等国际条约和满足参与国际贸易的需求,对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规定远超TRIPS协定所设置的标准,欠缺对国内公共利益特别是突发卫生安全危机的考量,导致我国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一直未能走向实践。
(二)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实践现状及其反思
经过一系列的立法调整,我国已经构建起形式上比较完备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框架,内容上也更加贴近现实。遗憾的是,自1992年设立专利强制许可制度至今我国未作出一例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决定。反观同样是发展中国家的印度,不论是在立法上还是现实中都对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实行了宽松的政策,有效满足了本国的医药需求。
作为仅次于中国的人口大国,印度人口密集、医药创新研制能力相对薄弱且气候类型是传染病多发的热带气候,其公共卫生状况并不理想,因此印度对赋予药品专利权保护一直持谨慎态度。1970年印度专利法并未给予药品专利保护,仅对药品生产过程授予专利。加入WTO后,印度必须根据TRIPS协定设置的国际义务修改专利法,最终在2005年才将药品纳入专利保护范围,却也仅限于1995年之后的新药或大幅度提升疗效的药品。同时,印度专利法规定:自专利授予之日起满三年后的任何时间,任何利害关系人都可以基于以下理由申请授予专利强制许可,即(a)未满足公众对专利发明的合理要求,或(b)专利发明无法以合理的、可负担的价格向公众提供,或(c)专利发明在印度境内未实施。这一规定在激励药品生产企业提出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和增强药品可及性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典型的例证即印度Natco公司申请“多吉美”专利强制许可案。德国拜耳(Bayer)公司生产的“多吉美”药物作为治疗晚期肾癌和肝癌的首选方案之一,其治疗效果被绝大部分患者所认可,但每月28万卢比的费用使普通民众根本无法承受,且拜耳公司提供的“多吉美”数量仅满足印度公众对此药品需求量的2%。因此,印度Natco公司认为“多吉美”无法让民众以合理的价格承受,且此药品虽在2008年即被授予专利权,但并没有在印度境内实施。在向拜耳公司请求提供自愿许可遭拒后,Natco公司随即申请针对“多吉美”的专利强制许可,最终获得生产许可并以远低于原研药的价格销售此药。从维护公共健康利益角度来看,Natco公司以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为矛,以政府权力为盾,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取得了生产销售“多吉美”的权利,提高了药品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在普通民众受益的同时帮助本国医药企业积累了大量的技术经验和资本。
二、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缺陷
虽然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至今处于“零实施”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没有出现《专利法》第54条、第55条所规定的情形,制度层面的缺陷是影响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实施的重要因素。造成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窘境的制度症结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作出标准存在缺陷
虽然专利意味着一定范围的市场垄断,但这是一种“必要的罪恶”[5]。药品研发投入巨大,如果没有专利制度的激励,医药企业就无法通过行使药品专利权收回前期研发成本并为后期新药研制提供资金。2014年,塔夫茨药物开发研究中心调查了10家跨国制药公司提供的106种新药,调查结果显示,一种获得市场认可的新药研发成本约为25.58亿美元;2020年《美国医学会杂志》的一项研究根据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2009—2018年批准产品的公开信息,估算出平均每种新药的研发成本在13.36亿美元左右[6]。药品专利不仅关乎专利权人的知识产权,而且往往涉及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贸然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易引发国际纠纷和技术贸易摩擦等重大负面效应。因而,即使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效果迅速而强大,但在技术创新方面具有政策优先性的国家会根据本国政治、经济、医疗技术以及公共卫生情况谨慎对待药品专利强制许可,这也是包括我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虽然在法律层面确立了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却极少付诸实践的主要原因。
新发展理念背景下,我国在维护公共健康与依靠专利驱动创新方面均存在需求,既需要控制专利药的高昂价格以实现药品可及、可负担,又必须为药品专利营造安全稳定的法律环境以吸引投资、激励创新。当面临严峻的公共卫生安全危机而公众用药需求又十分依赖某一专利药时,药品专利过分保护所带来的垄断和高价将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利益。我国已经对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申请、审查等程序进行明确,用列举的方式明确了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申请事由,但与印度、英美等国相比仍存在核心概念模糊、审查标准不明确等弊端。更重要的是,我国当前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缺少是否给予专利强制许可决定的指引标准,对公共健康需求的敏感度不足,导致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能否顺利推进依然存在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引发了相应的负面效果,申请人担心审查不通过使得前期准备功亏一篑,专利权人则忧虑自己投入巨额资金研发的专利能否收回研发成本。专利强制许可作出标准的缺失,一方面让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面临被随意侵害的危险,另一方面则削弱了相关主体申请专利强制许可的积极性,使得已经具备实施条件的单位和个人望而却步。在此种情形下,即便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出裁决,药品专利强制许可裁决的最终结果是否合理、是否存在多重评判标准,不免令人疑惑。
(二)专利强制许可事由缺乏灵活性,核心概念模糊
根据《专利法》的规定,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给予专利强制许可的事由限于专利权人未实施或者未充分实施专利、垄断行为、出现紧急状态或者非常情况或基于公共利益目的、基于公共健康目且对特定市场出口的、从属专利等。
一方面,我国对专利强制许可事由采用的是列举式规定,缺乏能够灵活应对突发状况的“符合专利强制许可条件的其他事由”。按照WTO成员方的普遍共识,TRIPS协定并未要求成员方必须使用协议规定的专利强制许可事由,只要成员方善意地执行TRIPS协定,就可以根据本国实际情况自由规定申请事由。《TRIPS协定与公共健康多哈宣言》也规定,各成员均有权自由决定批准专利强制许可的理由。对申请事由的过多限制不利于保障药品可及性,应当进行修正以减少其带来的负面效果。另一方面,条文所列举的“紧急状态”“非常情况”“公共利益”“公共健康”等概念界定不明晰,申请主体难以准确把握,无形中削减了医药企业申请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可能性。
(三)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内容设置不尽合理
1.内容分散,体系性较差。除了上述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标准以及申请条件严苛外,强制许可的内容安排不合理也是影响作出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决定的重要因素。对比TRIPS协定可以发现,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对出口条件的规定过于分散,直接导致这一制度的体系性不强、可操作性较差。《专利法》第55条规定,符合“公共健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有关国际条约规定”两个条件即可将药物出口至进口国。然而要获得制造出口的专利强制许可,还必须同时满足《办法》第13条的规定,即申请主体应当提供进口方给予专利强制许可的有关信息。易言之,医药企业如果申请制造取得专利权的药品并将其出口国外,需同时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在国内取得专利强制许可;二是在进口国也应取得专利强制许可。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出口条件的内容并未放置在同一法律条文中,而是分散于《专利法》第55条和《办法》第13条,破坏了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完整性,极易造成法律理解与实际操作上的困境。
2.专利强制许可的效力范围相对狭窄。加拿大、菲律宾和欧共体有关落实《关于<TRIPS协定>修正案议定书》的立法选择均把出口方的范围扩大至非WTO成员,TRIPS协定理事会对此并未提出异议[7],印度2005年《专利法》也将合格的进口方规定为没有药品生产能力或相关药品生产能力不足的任何国家。依照我国《专利法》第55条及《办法》第7条的规定,合格进口方的范围仍限定在最不发达国家或者地区以及WTO的发达或者发展中成员,如此设置非但不利于我国承担大国责任以帮助他国及时有效地应对公共健康危机,还束缚了本国医药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减少了本国医药企业通过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提高制造技术和效率的機会。在这方面,加拿大给世界各国作出了有益示范。加拿大于2004年颁布的《药品获取法(Bill C—9)》规定,非WTO成员方和非政府间组织可以作为合格的进口方,随后加拿大根据此法案顺利将获得专利强制许可的药物出口至卢旺达,帮助其解决了公共健康问题,同时也为TRIPS协定第31条之二的实践树立了正面典型①。
三、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关联问题分析
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基于特定专利权人与社会公众健康之间的矛盾而设立,目的在于协调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提高药品供应保障能力,在保障专利权人取得合理市场利益的同时降低公众健康负担。厘清药品专利与公共利益、专利强制许可与医药创新和药品可负担性等的关系,有助于更好地完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
(一)药品专利与公共利益
现有专利制度的法哲学基础仍旧是传统的亚当·斯密式自由竞争哲学[8],保护专利权与满足社会公众对药品的合理需求是专利法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对药品专利的保护必须围绕“私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进行。专利保护并非专利法的最终目的而仅仅是手段,专利法的最终目标是为了人类整体的福祉,这一终极目标的实现建立在一定的利益协调基础之上[9]。具体到药品专利领域,就是通过制度设计实现私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的协调。专利得以获得保护的基础是为激励创造创新而让渡了部分公共利益,因此专利权人在行使权利时必须对社会公众的利益有所权衡。专利由人创造,药品专利所享有的“独占和排他”由法律所赋予,社会公共利益则为专利权的行使划定了界限。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充当着维护公共健康利益和促进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性角色。显然,目前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协调作用并未被真正发挥出来。
(二)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与医药创新
一方面,药品研发投入巨大,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一个危险是可能影响某一特定市场所维持的药价水平。尤其是对于跨国医药专利而言,发展中国家实施专利强制许可会将资助医药创新的负担集中在发达国家的消费者身上,从而削弱医药企业针对实施专利强制许可国家的流行疾病开发新药物的积极性,最终降低病患在未来获得创新药物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专利强制许可对新药研发的负面作用不应被片面夸大。首先,在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后,医药企业承受着继续创新以保持领先竞争对手的压力,这将促使其创新能力得以加强而不是下降[10]。其次,认为专利强制许可将降低整个社会新药品研发创新积极性的观点值得商榷。研究表明,除专利权回报外,还有许多激励社会实体研发新药物的因素,例如政府提供资金资助新药研发等。统计显示,发达国家的公共部门和非营利部门对新药研发的投资接近新药研发投资总量的40%,而在发展中国家,政府为治疗某些特定病症所投入的研发资金会占到本国相应领域全部研发资金的60%[11]。
(三)药品专利与药品可负担性“囚徒困境”的破解
如前文分析,提供专利保护的重要目的在于给予专利权人一定时间的市场垄断利益以补偿研发成本并获取一定的利益,从而实现激励药品研发的目的。但在自然状态下,药品专利权人通常倾向于制定高专利使用费策略,以期早日收回成本,由此易产生天价专利药品现象。天价专利药严重违反了药品可负担性要求,过高的价格往往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从而难以达到收回成本的目的,并且造成天价药困扰病患的社会问题。从理论上讲,若将专利实施费用适当降低从而降低药价,可以增加有效需求的数量,从而扩大专利药市场规模,专利权人获得的市场利益可以保持不变甚至增加,这是一种“帕累托”式制度改进。但专利权人基于市场的不确定性往往不愿意主动降低专利实施费用,而宁可维持药品的“天价”,潜在的专利许可实施者和药品消费者又因没有制度支持而对此无能为力,由此形成“囚徒困境”。优化后的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应该可以为“囚徒困境”的解除提供助力。可以设想的方案是,只要任何主体能够提供必要的评估报告,证明降低专利费用后的市场规模可以扩大到给专利权人带来的市场利益不低于降价前水平,就可以向国家专利行政部门提出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申请并获得许可。
四、完善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思路
专利强制许可决定的作出,是权力介入专利制度以促成协议从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过程,是国家、社会和权利人共同参与的过程[12]。因此,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不能被粗暴地解释为权力对权利的侵犯,完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不是对私人权利的任意破坏,而是对公共利益维护的理性回归。为了实现专利权人与公共健康利益的最优化配置,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应当以利益衡量原则为指导,吸收比较法上的立法与实践经验,结合我国专利管理制度的优势进行设计。
(一)确立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指导原则:利益衡量原则
药品专利是医药技术与权利结合的产物,专利制度理应为其提供稳定而不受任意侵害的法律环境,但这并不代表排斥一切合理使用,只是要求使用须经过充分论证,不得违背公平正义且存在合理限度。当药品专利与药品可及性、可负担性产生冲突而现行法律又不能及时作出有效判断时,就需要借助一些评价不同利益的重要性和提供调整利益冲突的方法来指导制度的运用。从法律经济学角度出发,引入并贯彻市场利益衡量原则符合对公平的要求,亦与公共健康的合理主张相契合。
利益衡量是指在双方利益存在冲突且各自具备实质价值时,裁判者对双方争议的法律关系背后所代表的实质利益进行衡量评价后作出整合、选择和分配的活动,其过程包括调查、分析和权衡三个阶段。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实施过程是一个市场利益衡量的过程,若申请主体的药品市场调查专业报告足以证明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后既能满足患者对低价高质药品的强烈需求,又不会对专利权人的合理利益期待造成根本性不利影响,就可以认定达到作出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决定的标准,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就应该批准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为了保障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不减损,可以同时规定:若在合理期限内(如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之日起5年内)专利权人所获收益无法达到专利强制许可前的市场水平,则申请人须对其进行经济补偿。这一权衡看似是对专利权的强制干预,实际上并不存在绝对的利益牺牲,因为专利权人完全可以通过收取专利使用费的形式获得稳定的市场收益,甚至获得比高价药策略更加广阔的医药市场。阿根廷经济学家Pablo Challu研究认为,在完全垄断和相对竞争任一专利制度下,医药企业的研发成本与政府的机会成本是稳定的,“消费者购买药品的支出”和“因为药品价格上升使得社会实质性需求下降给医药企业造成的损失”将因专利强制许可的设立而相应降低[13]。換言之,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实施不仅不会给医药企业的经济利益带来绝对的消极影响,还会给社会公众带来福利,依法韦仑(Efavirenz)专利强制许可案件就是最好的佐证①。以建立市场利益衡量原则指引下的具有透明度、可预测性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标准为肇始,构建符合国情的针对个案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不仅符合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还顺应了市场供求机制,可以极大地缓和专利权与公众健康权之间的紧张关系。
(二)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立法完善
1.对《专利法》第53条第(一)项作扩张解释以增加专利强制许可的法定事由。不可否认的是,现行专利法中关于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规定存在硬性照搬TRIPS协定的缺陷,放弃了TRIPS协定赋予的自主立法空间和解释权。为了提高我国应对重大疾病的药品供应保障能力,我国应增设更加灵活的专利强制许可申请事由,提高条文的可操作性。在这方面,印度2002年《专利法》修正案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模式,此修正案对专利强制许可事由做了直观且操作性较强的规定,包括“公众与专利发明有关的合理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和“专利发明没有以合理可承担的价格提供给公众”。考虑我国的现实情况及面对的国际社会压力,完全照搬印度模式不可取,但可以适当借鉴印度在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增加兼具弹性和可行性的申请理由,以实现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维护公共健康利益的功能,如补充“公众对专利产品的紧迫需要没有以合理的条件得到满足”“符合专利强制许可条件的其他事由”等。另外,对“非常情况”“公共利益”“合理条件”等概念在不违反TRIPS协定的前提下作出符合我国实际的善意界定,使相关部门在应对公共健康危机时能够掌握主动权。
未来适时启动《专利法》修改程序无疑是破解药品专利强制许可难题的最终路径,目前而言对《专利法》第53条第(一)项作扩张解释可以成为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法律依据。《专利法》第53条第(一)项规定自专利权被授予之日起满三年,且自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满四年,无正当理由未实施或未充分实施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根据申请可以给予专利强制许可。这里的“实施”可以被理解为《专利法》第11条规定的以生产经营目的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相关专利产品,只要医药企业没有以上述任一方式行使药品专利权,即构成“未实施”。但“未实施”的情况在实践中比较少见,更为常见的情形是专利“未充分实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73条第1款规定,未充分实施专利是指专利权人及其被许可人实施专利的方式或规模不能满足国内对该产品的需求。实践中,医药企业通常会利用未充分实施专利制造特效专利药并以远高于成本的垄断价格对外销售,从而无法以民众可接受的价格满足相关市场对此药品的合理需求。因此,即便医药企业实施了药品专利,如果药品的生产销售规模或者价格不能满足国内民众的合理需求,同样可以认定构成未充分实施专利,进而对此药品专利作出专利强制许可决定。
2.整合出口条件,放宽出口范围。在出口条件方面,建议将《办法》第7条及第13条有关专利强制许可出口申请条件的规定整合后纳入《专利法》,增强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完整性和可操作性,提升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适用的可能性。同时,借鉴印度、加拿大等国的立法选择,将出口范围扩大到“制药行业没有足够能力或不具备相应药品生产能力来解决公共卫生问题的任何国家和地区”。在此基础上,WTO成员仍依照有关国际条约通知世界贸易组织表明希望作为进口方,非WTO成员则可通过外交途径书面通知我国外交部表明其进口意向[14]。
(三)司法上探索尝试新路径
在我国,专利强制许可决定是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如果作出决定的程序不合法或者内容不合理,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就有成为被告的可能性,其中的利益博弈甚至引发更为严重的国际争议和贸易摩擦。因此,充分和灵活运用司法实践的经验和做法,在司法上探索开辟新途径或许是一条值得尝试的路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是对现有专利制度的丰富与完善,其中第26条规定的涉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之专利侵权不适用禁令规则与专利法上的专利强制许可制度虽然在启动程序、申请主体、法律依据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②,但就效果而言,二者都实现了维护公共健康利益的目标,可以说是授权法院以判决的方式作出了“司法专利强制许可”。并且,法院作为解决矛盾纠纷的国家机关,在审判活动中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经验和专业知识,对公共利益、公共健康的认定有着相对丰富的经验,因此其所作出的不禁止专利侵权行为判决更容易被当事人所接受。尝试在部分药品专利侵权案件中适用不停止侵权判决可以达到平抑药价和维护公共健康利益的目的,可以说是一种扩充专利强制许可范围的新路径。
(四)善用可替代性方案
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伴随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深入推进,贸然作出专利强制许可决定,势必会动摇国际社会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信心,有悖于我国创新性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还可能会因此承受来自美国、欧洲等国家施加的政治压力(包括贸易制裁等)[15]。例如依法韦仑事件虽然对医药企业的投资策略不会产生根本性影响,泰国却因颁发专利强制许可被美国列入优先观察名单。所以,需要谨慎对待专利强制许可对创新活动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平衡药品價格的短期利益和国家国际地位的长期利益。
在处理公共健康危机时,必须站在国家整体利益的高度,实现多个部门、多重方案共同推进,在完善制度的同时,积极寻求合适的替代性方案。以美国为例,在炭疽病毒事件中,德国拜耳公司所有的专利药“西普罗”是当时治疗炭疽病毒的首选药物,美国将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作为谈判的筹码,迫使拜耳公司将其价格从每片5~7美元降至1美元以下。再如,巴西政府在2001年通过谈判使瑞士罗氏制药公司生产的抗艾滋药价格降低了40%,大大减轻了巴西政府在卫生安全方面的负担[16]。美国、巴西的实践为解决类似问题带来了启示,即灵活运用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威慑作用,将其与我国庞大的医药市场相结合,一并作为与专利权人协商谈判的筹码。这种策略不必触碰国际社会和部分国家对专利保护的“红线”,同时谈判协商的方式自由度较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专利权人实施自愿许可或将药价降低到公众可接受的合理水平,从而有效保障公众用药。
[参考文献]
陈永正,黄滢.我国专利药独家药价格谈判机制的战略问题[J].现代经济探讨,2017(6):16-23.
政府工作报告[EB/OL].(2020-05-23)[2021-06-08].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zhuanti/2020lhzfgzbg/index.htm.
了解人类对抗癌症的“武器”:抗癌药[EB/OL].(2019-12-13)[2021-06-08].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https://www.nmpa.gov.cn/xxgk/kpzhsh/kpzhshyp/20191213163101824.html.
原研药与仿制药的区别在哪里[EB/OL].(2017-10-24)[2021-06-08].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https://www.nmpa.gov.cn/xxgk/kpzhsh/kpzhshyp/20171024171601804.html.
ABBAS M Z.Pros and cons of compulsory licensing:an analysis of argument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y,2013(3):254-258.
WOUTERS O J,MCKEE M,LUYTEN J. Estimat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vestment needed to bring a new medicine to market,2009-2018[J].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2020(9):844-853.
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关于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完善[J].电子知识产权,2010(4):36-40.
邹彩霞.中国知识产权发展的困境与出路[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58.
冯晓青,周贺微.知识产权的公共利益价值取向研究[J].学海,2019(1):188-195.
唐广良.知识产权反观、妄议与臆测[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154.
Small group of rich nations have bought up more than half the future supply of leading COVID-19 vaccine contenders[EB/OL].(2020-09-17)[2021-05-08].https://www.oxfam.org/en/press-releases/small-group-rich-nations-have-bought-more-half-future-supply-leading-covid-19.
康添雄.专利强制许可的公共政策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3(6):103-107.
CHALLU P.The consequences of pharmaceutical product patenting[J].World Competition,1991(2):65-126.
KAMPF R. Special compulsory licences for export of medicines:key features of WTO members' implementing legislation[J].WTO Staff Working Paper,2015(7):31.
JAIN DIPIKA,DARROW J. An exploration of compulsory licensing as an effective policy tool for antiretroviral drugs in India[J].Health Matrix(Cleveland,Ohio:1991),2013(2):425-57.
周平.《公共健康宣言》及外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实践对中国的启示[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8(1):101-104.
[责任编辑 王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