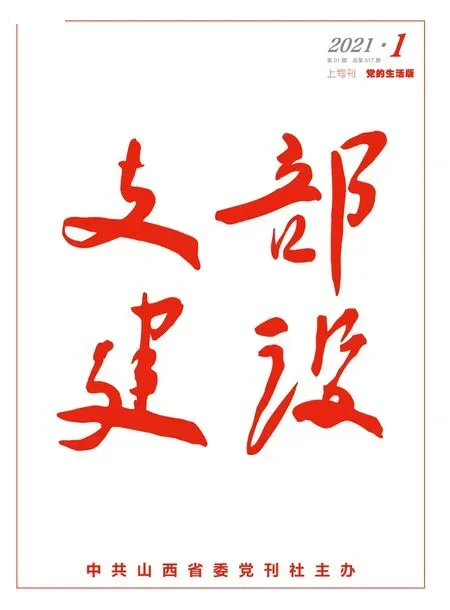红飘带上一巾帼
王哲士
她从长征走来
如果安庆英健在,应该是105 岁的老人。回溯她的人生年轮,2001 年去世,86 岁;1947 年落户隰县上均庄村,30 岁;1935 年参加长征,18 岁;193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7 岁;1933 年参加红军,16 岁。16 岁,正是人生的碧玉年华,她毅然告别家园,投笔从戎,走上亘古未有的长征路。
笔者至今依然记得多年前采访安庆英时的情景:高喉咙大嗓门,浓重的川音,爽快的谈吐,一下子把你吸引到她那种豪爽的气场里。一旦触及往事,或眼里冒光,或声音哽咽,自豪中有激动,激动里有自豪。面对这位个头中等、面色白里透红、穿着朴素的女性,如果不是事先知道她的身份,还以为是随早年南下开辟新区工作的丈夫,回到黄土旮旯里的川妹子。
她说,她能三过草地两过雪山走到延安,是红军带给她的幸运。长征中2500 多名女红军,仅有350 人走到延安。我把她比作凤毛麟角,她说不妥,只能说是屈指可数。她并非穷困潦倒到生活无着才参加红军,而是凭着一腔抗日救国的爱国热情,在生死未卜的漫漫长路上跋涉寻求。她说,既然认定了这条路,就要义无反顾地朝前走。我们不难想象,她要忍受多少常人难以忍受的身心创伤。
战火中虽然没有立过功,受过奖,但是她是那场壮举的践行者、见证者。细数她的功绩,不在一两枚奖章上,而在万水千山的双脚丈量中,在拳拳不变的一颗红心中。我们回顾她那段难以忘怀的往事,会有一种平凡而不平庸的敬仰,会有人生价值和使命的追寻,会想到从万里长征走过来的人,一定会慨然向新的万里长征走去。
少小离家老大回
一个人走得再远,也不会忘记出发的地方。说安庆英,不妨从她离家35 年后探访故园说起。
1968 年春天,因长征时身负重伤久病在身的爱人何占青与世长辞,夫妻“双红”成了“单红”,一时间少了依托,安庆英陷入片云孤木的境地。人在孤寂的时候越发容易忆旧:这里是她的家,但不是老家;这里的亲人走了,老家的亲人又怎样了?多少年联系,多少次无果,倒不如暂时撂下这头的牵挂回一趟心里牵挂着的老家,或许是一种精神慰藉。那年9 月,安庆英在儿子陪同下,穿吕梁,过黄河,翻秦岭,终于来到大巴山下朝思暮想的那个老家——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龙山镇——一个山清水秀,“鸡鸣三府,货通九州”的码头之地。
下了车,一头扑进曲曲弯弯的街道,她的心提到嗓子眼。近乡情更怯,果真不假。她盼回乡,试图找回昔日的温馨;也怕回乡,一走几十年,音讯全无的这个家会是个什么样子,亲人们能不能经受得住岁月的磨砺?为什么一次次去信一次次退回?难道……她不敢往下想。她找她的老宅,但忘了在哪道街哪道巷;她打听亲人们的下落,可惜现在人不知当年事。寻来寻去,终于在一堆聊天的老人那里打听到比较靠实的信息,原来有个改了名字的弟弟依旧守着故居,怪不得久不通信呢。脚步急,心里跳,一抬头,梦中的那个青瓦覆顶、青砖铺地、前店后院的老家在眼前闪现,久违的故园气息便扑鼻而来。安庆英抑制不住如潮似浪就要沸腾的归心,进院就喊“月德”,闻声出来的安月德愣在那里。安庆英大着嗓门道:“我是你姐庆英呀,我回来了!”
“啊?”大梦初醒的安月德这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这位从天而降的女人,难道就是离家几十年的庆英姐?不容分说,姐弟俩扑向对方,抱头痛哭起来。
安月德拍着安庆英的肩膀问:“姐,这么多年你都去了哪里?我们还以为你早不在……”
安庆英答非所问:“这么多年我时时惦记着这个家,为什么老写信老不应答呢?”
“姐,你可曾知道,你这一走,爸爸像疯了似的走上寻女路,就再也没有回家,连个骨殖也没留下。一家人老的老,小的小,不知是该找你还是找爸爸,找来找去,谁也没有找到,倒把妈妈给气得病故了,好端端的一个家一下就散了摊子。姐呀姐,你走了你省了心,可知我们是怎样熬过来的?”
“对不起弟弟,全是姐姐惹的事。那时姐姐年纪小,怎么能想到走了我一个,祸及全家人呢!”
“姐,我不过就那么一说,不怨你,不怨你。如今时过境迁,悲极喜来,咱们家出了你这位红军姐,咱们家光荣啊!”
这真是:十六从军行,五十始得归。亲人无一字,天涯思断肠。
一身肝胆长征路
亲人的遭遇一言难尽,安庆英的境况说来话长。
1933 年,苍溪县走来红军。红军一到,满街通红,“红军是武装起来的工农”“打倒帝国主义,建设苏维埃政权”“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标语随处都是。正在镇上学校读书的安庆英,眼里闪动着的是红军,心里激荡着的是红军。她和小姐妹们天天跟到红军后边观操练,看演出,听演讲,小心眼里就活动开来——参加红军去!父亲开着杂货铺,虽然不是大富,但也不穷,见女儿对红军着了迷,既叮咛,又照看,生怕年幼的女娃子跟上红军走了。谁知,十六岁的安庆英还是不声不响地离开生她养她的这个家,一去再无音讯。
安庆英参加的是红四方面军,她被分配到妇女独立团。
1935 年3 月,红四方面军从苍溪县塔山湾强渡嘉陵江,从这里走上长征路。这支队伍里,就有返回故乡的红小鬼安庆英。当她即将离开故土时,不由回眸对岸熟悉的山山水水和亲人。她擦了把泪,心里黙念着:“爸,妈,恕女儿不孝,你们可知道参加红军,解救天下受苦受难的父老乡亲是更大的孝道吗?爸,妈,你们千万要挺住,一定等女儿回来!”

图为双红军安庆英和何占青夫妻合影
踏上长征路才知道,这是一条险叵难测没有尽头的路。为了躲避敌人的追剿和围堵,红军走的是人烟稀少的羊肠道,跨的是汹涌奔腾的大江河,翻的是鸟兽绝迹的茫茫雪山,过的是无边的泥淖草地……安庆英记得,红军乘黑夜沿岷江急行军,脚下一打滑,就有人掉进深谷,被江水吞没,刚才还生龙活虎的战友,一眨眼就没有了踪影。她知道,悲伤过后要坚强,走好自己的路,才能替姐妹兄弟们继续长征。爬雪山,她穿着单衣,拄着木棍,脸和手冻得黑紫,高山缺氧,走不了几步就得喘息。有的战友经不住天寒地冻的侵袭,永远长眠在这里。草地方圆几百里,草丛叉河,曲流交错,不时有雨雪冰雹袭来,死亡陷阱横在红军战士面前。饥肠辘辘却没有吃的,便吃树皮吃野草吃牛皮,人困马乏没睡的地方,天当铺盖草当床。好不容易走出草地,谁知道喘息未定,上边又传下命令,原路返回,原路返回意味着重过草地。当时并不知道这是张国焘企图南下另立中央搞分裂。安庆英随队伍再过草地,重走雪山。一路上不时看到第一次过草地时牺牲的红军战士的遗体。“他们有的手挽着手,胳膊挽着胳膊,一起倒在地上;有的趴在地上,背上则背着另一个战友;有的牺牲之前仍保持着向前爬行的姿势,两手攥着泥土和青草,身旁有用手指挖出的长长沟痕;有的女战士抬着伤员一起牺牲,担架还压在她们的肩上……悲壮景象触目惊心。”这一路不仅走得身体疲惫,且走得心情沉重。安庆英咬紧牙关暗暗嘱咐自己:你一定要争气,一定要活着,只有活着才能走完长征路,只有活着才能见着父母亲。不久,张国焘南下失败,在中央电令下不得不再度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这时已经是连长的安庆英因为极度羸弱,几天昏迷不醒。而红军既不能带她,又不能等她,只好把她安置在老乡家里,开拔走了。等她苏醒过来,不见了部队,急得出了一身汗,就要起身去追。老乡劝安庆英留下,说要回家,这里还不算太远。安庆英说:“我哪里还有家,红军就是我的家。跟上红军走,走到天尽头!”于是找了根木棍,踉踉跄跄地追赶红军。肚子饿了,不是乞讨,便是到庙里吃献品,实在没吃的,就吃观音土和青草充飢。白天还好说,一到夜晚,狼嗥狐叫,寒气逼人,无处藏身。有一天好不容易看见红军的影子,她拼命追呀,追呀,在一座大山下终于追上了红军,但身子一软便瘫倒在地上。首长叹口气,说好一个铁了心的女红军娃。想带她,带上凶多吉少,就好言劝她留下,兴许能落个活命。安庆英心想,与其留下来死去,还不如跟上红军去“光荣”。二话没说拽住马尾巴,站了起来,一步一踮,两步一摇,硬是跟着红军上了山。两过雪山,安庆英没有掉队;三过草地,安庆英没有倒下。最终,她挺了过来,红军挺了过来,但是却付出了本不应该付出的巨大代价。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导致红四方面军八万人减员一半还多,安庆英所在的妇女独立团,也由原来的2500 人减到1300 人左右。这种减员大多是因冻、因饿、因病、因灾、因失散等等原因所致的自然减员,并非倒在刀枪拼杀的血泊中。安庆英所以能跟着红军转战南北,凭的是信念,凭的是毅力,凭的是有一个能够支撑生理极限的强壮体魄。
本以为走出草地,人生的坎坷可以就此迎来转折,谁知安庆英又随红军西路军西征,陷入数倍于红军的国民党军堵截,两万多人的红军队伍,除被中央红军营救出来的几千人,大部分血洒疆场。安庆英和战友们在弹尽粮绝命悬一线的危急时刻,幸遇前来解救的红军,这才一路走向她梦寐以求的延安。
这场发生在1930 年代的红军长征,被誉为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前所未闻的故事、地球上一条永恒的红飘带。而长征中的女红军尤其引人注目,她们出入枪林弹雨,跋涉雪山草地,与生命的极限顽强抗争,承受着比男红军更多的艰难困苦。安庆英和她的战友们,历经血与火的洗礼,为这条红飘带绣上一道光彩熠熠的风景。
骨肉绝命黄河悲
走过长征路,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做过长征人,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到延安后,安庆英被分配到被服厂工作。安庆英年轻漂亮又有文化,自然是年轻人注目的对象。经人介绍,安庆英与一位团职干部相识相恋相携走进婚姻殿堂。沉浸在新婚喜悦的安庆英,怎么也不会想到,婚后三天丈夫即奉命率队远行,这一去便没有了音讯。她四处察问,登报寻人,她的这个三天的丈夫,就像断线的风筝,再也没有回到身旁,成为心头永远抹不去的牵挂(这件事,直到临终时才说给家人)。1937 年,又与同是长征过来的同乡何占青相识并成婚。这一次,她的丈夫再也没有离开她一步,但因长征负伤带来的病痛折磨,也只陪伴她到53 岁便撒手人寰。这是后话。1947 年3 月,国民党胡宗南部25 万人向延安大举进攻。毛主席党中央决定撤出延安,“要用一个延安换回全中国”。安庆英夫妇随后方机关一路朝山西撤退。当走到黄河渡口时,遭遇国民党军飞机轮番轰炸,安庆英雇的毛驴受惊,挣脱缰绳,收不住狂奔的脚蹄,竟一头朝黄河栽了下去,坐在驴驮里的两个女儿和全部家当一同葬身于浑浊的波涛里,霎时没有了踪影。安庆英撕心裂肺,何占青捶胸顿足,一个要跳河,一个要跟随,都被战友们死死拉住。不曾想,长征路上的一次次生离死别的悲剧在这里再度上演。这是转瞬间的悲剧,是来不及告别的悲剧,是完全意想不到的悲剧。孩子没了,行李没了,为了未竟的事业,夫妻俩只得泪眼婆娑地望呀,望呀,送别一双女儿,直到黄河远上白云间……
这是从她身上掉下的血肉啊,她既不能够忘怀,又从不愿意说起。此次回到老家,还是忍不住给亲人们说了。安庆英哭了,安月德哭了,所有在场的人都哭了。谁能不为之动容!离家,安庆英抛弃了母女情,过黄河,安庆英又割断了母女情,上有愧于走失的父亲、多病的母亲,下有愧于一双年幼的女儿。安庆英这一生,不曾有愧于革命,却欠下亲人们一个个难以弥补的痛楚。
安庆英来到母亲坟头,烧香化纸,连连叩头,哭得呼天抢地,几乎昏厥。她有一肚子话要给母亲倾诉,要给不知下落的父亲赔罪。但是都为时太晚,纵然把三十年的话全倾诉出来,也不足以报答父母养育恩,骨肉情。“坟里的妈妈,女儿对不起你;天边的爸爸,恕女儿不孝,走上革命路,忠孝难两全呀!”
战士解甲不下鞍
事情还得从渡河说起。丢了女儿,丢不了志气。安庆英何占青夫妇擦干泪水,冒着敌人飞机的狂轰滥炸强渡黄河,还没有靠岸,船就中弹漏水,只得水里淌,泥里爬上了岸。队伍被打散了,夫妻俩相互搀扶着,硬是过了对岸的山西。一路上,心尖滴血的安庆英,还得搀扶悲怆和病痛交加的何占青。设想一下当时情景,最让人动心的是天地间的患难夫妻,革命道路上的并肩战友。安庆英给我描述过当时的窘况:春寒料峭,山路崎岖,因为丢了行李,上衣成了半袖衫,下衣成了半腿裤,两个肩膀抬着一张嘴。冻也得走,饥也得行,病还得跑,因为他俩没有忘了自己是红军,没有忘了前边的新长征在召唤。好不容易来到临县,找到设在碛口的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报了到,要求分配工作。鉴于她俩的身心创伤不宜再随军行动,上级给发了证件和给养,随南下工作队来到新解放区隰县就地休养,在隰县一个叫上均庄的小山村落了户。从此,安庆英何占青夫妇解甲归田,在这个全然陌生的黄土地上度过后半生。在农村,安庆英仍像长征时一样,风风火火,吃苦耐劳,掏茅粪,吆牛车,搬石头,开荒地,一点不输男人们。村里的麻烦事、难缠事从不回避,有她在场矛盾就会化解。人家叫她老红军,她说她是老农民——有红军的肝胆,无摆架子的资格。几十年来,模范党员、模范妇女队长、劳动模范、优秀老红军、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等等荣誉接踵而来。几十年来,从没有向组织张过嘴,伸过手,要过待遇,连她逝世后的灵柩仍然停放在土改时分的两孔旧窑院。无怨无悔,无求无索,安庆英就是这样一个人。
半生战士,半生农民,一生红军。履历简明,风采夺人。安庆英说,走过长征路,永远是红军。是呀,初心在,本色在,浩气在,她永远是地球红飘带上令人忆念的铿锵巾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