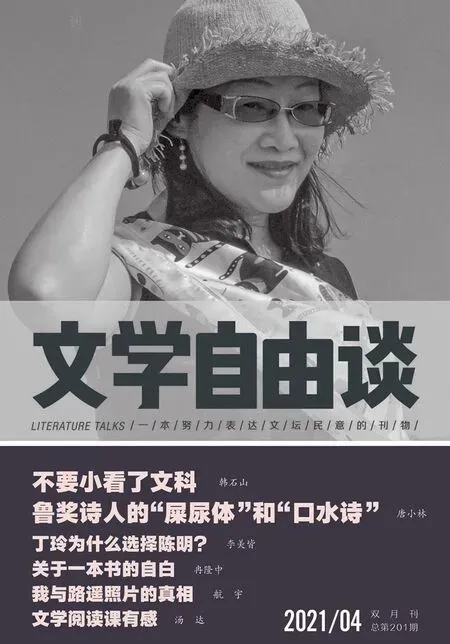谢冕诗学工程的两大考验和五重矛盾
□古远清
2010年,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成立时,就把有关新诗创作和史料的整理研究当成首要任务。从2015年开始,经过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中国新诗总论》终于呈现在大家面前。这套书入选“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收录了中国新诗百余年间重要诗论家、诗人的评论文章,是中国新诗理论批评文献的总汇。和早先的《中国新诗总系》一样,《总论》是中国新诗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极深的诗学挑战,同时也是对中国传统诗学质疑最为深切和系统的一项编辑工程。它弥补了中国新诗理论研究和出版的空白,亦可视为一贯低调、从未打旗称派的 “北大新诗学派”纪念碑式作品。
“北大新诗学派”的诗学著作,还包含谢冕个人以史家的严谨、学者的慧眼、诗人的情怀写成的《中国新诗史略》。有了这接连问世的三本著作,尤其是本子薄、分量重的《史略》,谢冕晚年的诗学建设工程完成了龙门一跃,他由此成为“北大新诗学派”名副其实的领军人物。
通过这两“总”一“史”,我越来越感到,“北大新诗学派”无论是从学术背景、诗学观念,还是诗学贡献、诗学影响来说,都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但我常感到“北大新诗学派”面临两大考验:
一是批评。这批评有来自外部,也有来自内部,比如说到底有无“北大新诗学派”。当事人孙玉石前几年在《中国新诗总系》研讨会上,当着谢冕和笔者的面激动地说:“根本不存在什么派,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他把“派”理解为“拉帮结派”,系一种误读。洪子诚则说得比较温和,他在2012年11月16日给笔者的信中说:“你说的‘北大新诗学派’,好像并不存在。……但对这个事情,我们当事人其实不必多嘴,由评论家和文学史家评述就可以。”刘登翰也给笔者写了一封信《“北大新诗学派”的几点存疑》。更有一位学者断言:“中国近五六十年以来,创作没有流派,学术界没有学派。”在北大诸君子中,大概只有孙绍振支持我的意见。其实,作为研究者,大可不必征求当事人(也就是研究对象)的同意。新诗史上就出现过文学史家说谁谁谁是“七月派”或“九叶派”,但个别成员根本不买账。有人提醒我:“‘北大新诗学派’主要成员个个还健在,你未‘盖棺’先‘定论’,是一种‘危险’行为。”其实也不一定“危险”,我有充分的学术自信。评论者与被评者意见不一致,本是正常现象,像我非常崇敬的学者孙玉石对《野草》的诠释有理有据,可鲁迅如果健在,也不一定都认可吧。
二是批判。现在很少有人写批判或大批判文章了,但当我们“重返八十年代”,就会发现纲上意识形态、火药味甚浓的文章不少。批评和批判这两者本是一体两面。当批评升格时,就会演变为批判。郑伯农式的付于无情锋刃的炮击式文章,今后是不太可能出现了,甚至善意的批评也很少有人会写,但总有像我这样被人讥为“学术警察”的喜欢挑刺的人在做。《中国新诗总系》岀版时,我就曾在《文学报》写过《对〈中国新诗总系〉的三点质疑》的文章。
作为谢冕的诤友,我觉得编纂《中国新诗总论》和编纂《中国新诗总系》一样,工程十分浩大,要完成困难肯定不少。依愚之见,编这套书至少要解决五重矛盾:
一,学院派与“草莽派”文章的矛盾。所谓“草莽派”,是台湾诗人兼评论家痖弦对非学院派的一种调侃。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港,都有不少“草莽派”也就是“诗人批评家”。这些并非科班出身的评论家,写的文章同样有系统性和严密的逻辑性,理论深度也不一定输于学院派,像未入选《总论》的流沙河发表在《香港文学》上的《诗人余光中的香港时期》等。不可否认,“草莽派”的文章,多半是吉光片羽,像王光明主编的第四卷所选的《青春诗论》,姜涛主编的第一卷所选的戴望舒、吴兴华的文章,就属此类。至于“北大新诗学派”的先驱废名的《新诗问答》,也不符合学院派的体例。该文既无注解,又写得随意,但谁能否定其中有不少真知灼见?相对来说,选八十年代以后的诗论,则过分着重学院派轻车熟路的“学报体”文章。夸张一点或说得难听一点,这有点像钱锺书说的:“重视废话一吨,轻视微言一克。”
二,现代派与写实派理论的矛盾。现代派的理论很受各卷主编们的青睐,他们虽然没有对写实派的文章不屑一顾,但至少遗漏了“北大新诗学派”的对立面丁力、闻山、宋垒这些编辑型的写实派评论家。介于“崛起派”与传统派之间的孙光萱《论近年来新诗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发展趋势》、吕进《新时期诗歌的逆向展开》、朱先树《实事求是地评价青年诗人的创作》等均榜上无名,也欠妥。不错,现代与写实两派的诗歌评论在各卷中都可以看到,但比例严重失调。如果让发明“北大派”(即“北大新诗学派”)一词的臧克家来主编,肯定会有另一番风景(当然,臧氏以创作著称,他不一定能肩负起这种重任)。《中国新诗总论》个别编者未能超越远近亲疏的局限,独沽一味地选了一些自己偏爱的文章,这会给“选家”的“史识”打折扣。不可否认,这套书的编者,均是学富五车的学者,这回他们换了一种“选家”的身份登场。做“选家”的确不易,不仅要有“史识”,还要有“史笔”。这“史识”和“史笔”,充分表现在各卷主编认真所写的高屋建瓴的序言中。
三,论战文章与“建设”文章的矛盾。比如台湾,诗人们为“巩固国防”,写了大量的论战文章。余光中说过,不论是诗人还是论评家,都不能靠论战或“混战”成名。但不可否认的是,不少论战文章“破”中有“立”,在与对手激辩时,展示了自己崭新的诗学观念。和1958年谢冕、孙玉石、孙绍振、洪子诚、刘登翰、殷晋培在《诗刊》发表的《新诗发展概况》一样,可视为“北大新诗学派”“史前史”的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也属此类。不能说这类文章因为短小,且没有详细的注解,就认为其学术价值不高。相反,这种“时评”(如徐迟抗战时期写的《抒情的放逐》),比学院派写的所谓“建设型”的长篇大论,学术含金量还要大。
四,老一辈与青年一代之间的理论矛盾。一般说来,老一辈诗论家守旧,而年轻一代的诗论家观念前卫。其实,两者并没有截然的界限。“北大新诗学派”的领军人物虽然年长,但他们永远站在诗歌的前沿,其论文及时回答了新诗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当然,也有个别老一辈的诗人写的评论文章观念僵化,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如第四卷所选艾青把朦胧诗打成“逆流”的《迷幻药》——顺便说一句,既然选了《迷幻药》,也可选对当年(潜在的)“北大新诗学派”作总批判的郑伯农所写的《在崛起的声浪面前——对一种文艺思潮的剖析》。
以上四种矛盾绝大部分属隐性,而第五种——大陆与境外诗歌谁的成就高的比较,则较为显性。
“东海西海,此心此理。”这是王国维在《叔本华像赞》中所说的,意思是学问不分中西,只要是精华,均可“拿来”。以中国新诗而论,按文学地理学划分出来的大陆、台湾、香港、澳门新诗,其实都是中国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中国新诗的宝贵财富和资源,虽然成就不同,但并无优劣之分。只有在平等互补前提下,才有可能整合两岸四地诗学理论。超越意识形态局限,就是祛除人为设置的禁区,以博大的胸怀消解大陆与台湾、内地与港澳二元对立的文化幻象,这是编纂《中国新诗总论》的重要宗旨之一。
必须指出,《中国新诗总论》总主编及各卷主编,均以研究大陆新诗著称,对境外尤其是台湾和大陆诗歌谁的成就高的比较声音,可能较少听到。其实,这种声音一直不绝于耳。如钟鼎文在《诗刊与理想与使命》中,就认为“中国诗的传统,只好由台湾的新诗接续”,大陆诗人们“都不再写诗”,只有台湾地区的文学运动,才是中国文学的“正统”。如果说,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还说得过去的话,那到了八九十年代,还这样认为就不准确了,可台湾不少作家仍持这一观点,如由大陆到台湾定居的小说家无名氏,就一直称“台湾的诗凌驾于大陆之上”,并认为在台湾的中国诗人“才是中国诗的希望”。 有人还大言不惭地认为,大陆的新诗至少比台湾落后二十年;评论方面的成就在这里虽然没有说,但显然包括在里面。2011年,曾是诗评家的陈芳明在其著作《台湾新文学史》的封底上,更是吹嘘“最好的汉语文学,产生在台湾”,这“汉语文学”,当然包括汉语诗歌创作和评论。对这种观点,“北大新诗学派”诸君子肯定不以为然。他们编诗选、诗论选,均不自觉地贯穿着自己的“论敌”臧克家所说的“文学,大陆是树干,台湾是枝条” 的看法。这种观点很多人都拥护,笔者也基本认同。就新诗这种文体来说,其源头在北大,大陆诗人之多、佳作之丰、读者之众、市场之广,任何一个地区都难于比肩,这就难怪许多以“新诗三百首”命名乃至像《中国新诗总论》这样权威的选本,无不“泼墨如云”地推出大陆新诗和诗论,而对境外诗歌和诗论,则可用“惜墨如金”来形容。可“树干”与“枝条”之说不能无限膨胀,它受时空制约,如大陆在闭关锁国的年代尤其是十年浩劫时期,就不可能是“主干”。在与世界华文诗歌交流方面,境外的诗歌及诗论无疑起到了先锋作用。以 “翻译卷”为例,由于历史原因,1949年以后大陆诗歌与国外交流甚少,与台港澳诗歌的交流也是空白,而境外诗歌创作和翻译活动在这一时期则层出不穷。读了赵振江主编的第六卷后,人们也许会改变“文学,大陆是树干,台湾是枝条”或“大陆新诗是树干,台港新诗是枝条”的笼统看法。
为处理好这五重矛盾,“北大新诗学派”制定了《中国当代新诗总论》的编辑方针,我将其概括为“以大陆诗论为主干,学院派为主导,现代派为主流”。大陆学者对境外新诗创作及其评论所做的文化薪传工作持高度肯定态度。而且随着与境外诗人或诗评家的频繁交流,选家们打破大陆诗学与境外诗学的隔阂,并超越了地域的界限。如吴思敬主编的第三卷,所选的台港诗论最多,其中台湾的余光中三篇、叶维廉两篇,香港的林以亮也是两篇,且还不忘记以写“爆破型”闻名的左翼评论家关杰明、唐文标以“大扫除”的方式批判现代诗的文章,这均体现了编者的慧眼。王光明主编的第四卷,也选了台湾叶维廉、杜国清、杨牧和郑树森、张汉良、向阳,及香港黄维梁、梁秉钧、陈少红等人的诗论。张桃洲主编的第五卷所选的台湾林燿德、简政珍以及香港黄灿然的文章,同样说明作为“枝条”的台港诗论,不可小视。
《中国新诗总论》的选家们将境外与大陆诗论融为一体,不将台港诗论单独设卷,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但将不同文化背景产生的诗论“一锅煮”,给人油飘在水面而非水乳交融的感受。笔者还是赞成像吴思敬主编的《百年新诗学案》那样,将台港澳部分单独设卷。如不单独处理,境外诗论必然无法改变叨陪末座的境地。比如《中国新诗总论》从第三卷开始才出现台湾诗论,这是否意味着台湾“光复”前就没有诗论或不存在优秀的诗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如日据时期《风车》诗刊上的《土人的嘴唇》,首次使用“现代诗”一词,并比洛夫更早揭起超现实主义的旗帜。当时倡导超现实主义,是为了躲避殖民者的检查和压迫,可谓用心良苦。许多人认为,台湾“现代派”的火种系纪弦从大陆带来,其实台湾本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劲吹过现代主义之风。这篇文章还说明台湾新诗不仅受过大陆新诗的影响,而且还从日本西胁顺三郎、北园克卫、泷口羞造的诗学论著中吸取过养料。这篇相当于“风车诗社”宣言的《土人的嘴唇》,是中国新诗史上一篇重要文献,其意义决不亚于某些诗刊的创刊词。《中国新诗总论》总主编曾告诫各卷负责人“选文力求赅备,以不遗漏任何一篇有价值的文献为目的”,可这篇如此重要的文章居然未能在大陆重新“出土”,真令人扼腕长叹。当然,任何著作都难免有遗珠之憾,像台湾的颜元叔、高准,还有“本土派”的林亨泰、陈千武,以及香港的温健骝、黄国彬,就有佳构可入选。澳门在这套“总论”中,则“白茫茫大地真干净”。须知,在这座小城中,仍有陶里、郑炜明、黄晓峰、李观鼎这样出色的诗论家。
编纂新诗理论总系,是一项十分严肃的工作。选什么文章就包括了主编者的评判标准。选者不可能没有自己的主观偏好,可又不能完全违背一定的客观标准。《中国新诗总论》所奉行的客观标准,我揣摩应该是“代表性”乃至“经典性”。像第一卷所选鲁迅的《诗歌之敌》、腾固的《论散文诗》、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均带有经典性,而选的八九十年代后的文章,则“代表性”远大于“经典性”。这也难怪,因为距离越近越难选,重要的是时间老人对此还未做出筛选和评价。即使这样,这套书的学术价值仍必须充分肯定。正如“北大新诗学派”的坚强后盾黄怒波所言:“《中国新诗总论》虽然只是近400万字的一套书,但它却含有说不完、道不尽的民族精神气质。如果说,这套书是编者和出版者们为民族的历史做总结、写见证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其实就是在记录和表现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史。”让《诗探索》与“北大新诗学派”合流、同时称得上是“北大新诗学派”掌门人的吴思敬也说:《中国新诗总论》编选工作不仅是为历史存照,更着眼于当下与未来的中国新诗理论建设,因此所选文章对今天与未来的诗人、诗歌理论家均有重要的启示。换句话说,《中国新诗总论》不仅为新诗读者提供了一个亮丽悦目的櫉窗,同时也为后来者继吴思敬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出版后写出同类著作,做了奠基性的工作。
谢冕在《中国新诗总论》的新书发布会上高喊“我的百年工程终于竣工了”,但真的“竣工”了吗?还留下什么遗憾没有?这很值得谢冕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