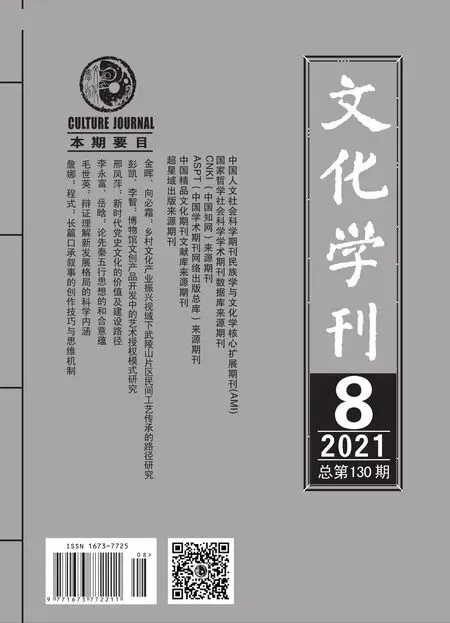《活着》英译中的“中国英语”探究
孟 洁 徐玉凤
通信作者徐玉凤(1979—),女,山东莱州人,青岛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文学理论、翻译研究。
引 言
余华的《活着》是中国文坛上的一部成功之作。小说讲述了从民国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福贵一家的生活变迁,在语言表达和运用上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小说以主人公的第一视角阐述特定时代背景下中国的乡村生活,语言质朴,真切地展现了一位中国老农的独特形象。文章选择以美国翻译家白睿文(Michael Berry,1974—)的《活着》英译本[1]为例分析英译文中的“中国英语”,体现在习语、谚语、农业场景的翻译和中国特有风俗的翻译中。
“中国英语”是英语的一种本土化变体,它以规范英语为核心,表达中国社会文化诸领域特有事务[2]。“中国英语”凭借富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可以帮助外国读者更加准确透彻地理解中国文化。译者白睿文是一个文化相对主义者[3],他一直保持着对翻译工作的热爱,秉承尊重原作、尊重中国特有文化的理念,这些都体现在《活着》的英译文中,因此他的译作对原文的把握也非常透彻,其翻译的准确性影响着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宣传效果。在译文中,白睿文成功地再现了原文的语言形式,完整地保留了原文的情节,在整体风格和叙事技巧上都与原文保持了基本一致。在文化层面,白睿文使用了大量的“中国英语”以准确传达出原著中的表意。
一、“中国英语”
1980年,“中国英语”的概念由复旦大学教授葛传槼提出,“各国有各国的情况。就我国而论,不论在旧中国或新中国,讲或写英语时都有些我国所特有的东西需要表达”,如我们将“四书五经”“人民公社”翻译为“Four books and Five Classics”“People's Commune”。在分析例证的基础上,葛传槼的结论是:“所有这些英译文都不是Chinese English或Chinglish,而是China English[4]。”
在之后的研究中,“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和“中式英语(Chinglish)”常被比较研究。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的许多学者更加细化了翻译原则并纠正了“中式英语”20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中国学者主要研究如何界定“中国英语”和“中式英语”,以及如何区分两者之间的差异。如李文中的《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中阐述了“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的界定以及两者的区别与联系[2]。但文中并没有说明“中国英语”与“中式英语”是如何构成的。2005年,万鹏杰的论文《中国英语与中式英语之比较》[5]完善了“中国英语”的界定,并论述了“中国英语”和“中式英语”是如何构成的以及“中式英语”的形成原因和几点表现。
“中国英语”与文化负载词有相似之处但并不相同。“中国英语”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句式和语篇,而文化负载词只是停留在中国文化的词汇翻译层面。汪榕培提出:“中国英语是一种以标准英语为基础,有中国特色的英语变体[6]。”当下,“中国英语”的概念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全面的研究体系。
二、农业场景翻译中的“中国英语”
中国是个文明古国,也是个农业古国,中国典籍中有很多关于农耕文明的经典作品[7]。《活着》这部小说见证了中国历史的变迁,“中国英语”对其中的很多场景都有很强的适用性。白睿文以其出色的中英文水平对原文进行了深刻地解读,凭借对“中国英语”的准确理解巧妙表达了原作的文化内涵,并充分考虑到译文读者的感受。
《活着》[8]一书中有许多关于中国农业场景的独特表达,如地理位置、土地术语和耕作技术等。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运用“中国英语”力图更准确地传达原作内容。以下以“田埂”“下地”“自留地”的翻译为例论述。译者将“田埂”译为“atop the ridge”“ridge”有“山脊,隆起”的意思,“田埂”就是乡下田间稍高于地面的狭窄小路,是田间的土地高于田块凸起的一部分。“田埂”的翻译生动形象地还原出乡下田野里小路的真实面貌,更有利于外国读者了解中国农业耕作场景。
《活着》的译本中,译者在充分了解“中国英语”内涵的基础上对很多农业场景进行了恰当地翻译,展现出“中国英语”的特色,尤其体现在“下地”的翻译上。“下地”是中国农村的特有叫法,通常指到外面的农田去干活。如果译者用直译法把它翻译成“go to the floor”,这个词的准确意思就不能在译文中表达,也不能反映农民的耕作习惯。因此,白睿文将“下地”翻译为“out in the field”。运用意译的方式,将“下地”的内涵意义阐述出来,避免了由于文化差异给读者带来的困惑。
译者将“自留地”翻译为“a small plot of land”不是非常恰当。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地全部归国家所有,只有一小部分留给农民自己,这部分土地被称为“自留地”,但白睿文的翻译并没有体现“留下”这一特点,应改译为“a small plot of remaining land”。将中华文化鲜明直接地展示在读者面前,让读者感受到强劲有力的中国魅力。
以上几点都体现了“中国英语”在《活着》中的应用,译者凭借自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透彻了解,同时具备“全球视野”与中国“本土意识”,在译文中尽量还原出原文所描写的真实场景与表达的感情,让读者在读作品的同时更能感受到其中所传达出的文化底蕴。
三、中国特有风俗中的“中国英语”
中国特有风俗在这部小说中随处可见,小到人名称呼,寒暄用语,大到风土人情、社会现象、时代背景,方方面面都有所体现。对于这类“中国英语”的研究是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民族文化、文学风格等区别于其他时期、其他民族以及文学作品的一种有效手段。
“私塾”这个词语在这部小说中多次出现。“私塾”是中国古代在家庭、宗族或村落中设立的一种民间幼儿教育机构。如果译者只是把它翻译成“school”,就不能反映出整部小说所要表达的时代感,也体现不出“私塾”的特点。因此,译者运用“中国英语”的思想将其翻译为“an old-style private school”。这样,就将其与普通的“school”和大众习惯认知中的“private school”区别开来,保留了“私塾”的传统文化特色。
“小脚”也是在这部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个词语。在当时,“小脚”一词并不同于我们今天用来形容一个人的脚很小的意思,而是代表中国女性中一个常见的现象。在古代,中国人以女性脚小为美,所以女性在四五岁的时候就要缠足。也就是说,女人的脚要用布料和丝绸包裹起来,长期的压迫变形使双足逐渐成为又小又尖的形状,长约三寸,俗称“三寸金莲”。这是中国长期沿袭的陋习。女孩的脚由于长期的束缚而变形难看,甚至走路也极其困难。白睿文没有直接把它翻译成“little feet”,而是“twisted little bound feet”。通过对缠足这一外在形象的描写,加深外国读者对中国缠足文化的理解,并影射出女性经历的苦难。
自古以来,中国人便有烧香祭祖的习俗,因此“香火”一词也代表“子孙后代”的意思。“香火旺”意味着一个家庭人丁兴旺,“断香火”意味着一个家庭没有子嗣。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的很多地区,尤其是欠发达的农村地区一直有着重男轻女的思想,因此“香火”一词通常指家庭中的男丁。因此译者将“香火”直译为“flame”是欠妥当的,并没有传达出“香火”的隐含意义。
四、习语中的“中国英语”
汉语中每个习语背后都凝结着丰富的中华文化内涵和典故,大多反映了中国劳动人民的实际生活经历,包括成语、谚语、格言、歇后语等。英语是一门综合性语言,句子由代词、从句和其他语言形式连接起来。由于英汉语言的这种差异,翻译表达的完整性往往受到阻碍。然而,“中国英语”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
在汉语中,一些颜色如“青”“紫”经常被用来表示受伤的程度,但在英语中,大多数颜色只是概括为“black”。英语中没有各种各样的关于伤痛程度的颜色表达。所以色彩的内涵意义也是一种典型的中国文化。白睿文将“鼻青脸肿”译为“a bloody nose and a swollen face”。如果鼻子被打“青”了,那么便很容易流血。因此,作者用“bloody”一词来表示“青”的严重程度,这种代表颜色内含义的“中国英语”就被很好地表达了出来。读者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伤害的力量,使译文符合语言维度和交际维度的要求。
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农业耕作中“牛”不可或缺,“牛”已成为与中国文化密切相关的家畜之一。原作中有许多关于牛的表达。“Oxen plough the fields, dogs watch over the house, monks beg for alms, chickens call at the break of day and women do the weaving. Have you ever heard of an ox that didn't plough the land?” 这是原作中中国民间谚语“做牛耕田,做狗看家,做和尚化缘,做鸡报晓,做女人织布,哪头牛不耕田?”的译文。译者采用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方法,在翻译过程中使用与原文相同的修辞手法,完美地展现了“中国英语”的特点,使读者易于阅读。译者并没有直接将“哪头牛不耕田?”翻译为“Which cow doesn't farm?”而是采用拟人的修辞方式,将福贵和牛商量、劝说的语气展现得淋漓尽致,更符合原作所传达的思想。
译者将“男人都是馋嘴的猫”翻译为“Men are nothing but a bunch of gluttonous cats”,用双重否定来加强语气,意指福贵母亲劝家珍不要离开福贵时担心和急切的心情。同时,“nothing”一词一语双关,同样表达了福贵母亲对父亲的愤怒,认为男人无一都会在外面放纵自己。译者用“中国英语”很好地表达了原作情感。因为这两个习语在翻译中运用“中国英语”就能很容易被目标读者理解,这也体现了“中国英语”对于目标语的重要性,不仅表达了原文的意思,而且符合英语的表达方式。白睿文能恰当地理解中国习语的意思,借助“中国英语”,实现了语言维度、文化维度和交际维度的转换。
综上,白睿文在翻译时更倾向采用意译的翻译方式。译者在翻译原作时,虽然有一些方面并没有非常恰当准确地运用“中国英语”,但译文已经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中国文化特点,并且很少出现偏僻难懂的词汇,尽量忠于原文。“中国英语”在汉文学英译中的应用研究还没有广泛普及,相关的研究领域应拓宽,英译中“中国英语”应当得到更多的关注,以更好地服务中国文化的外宣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