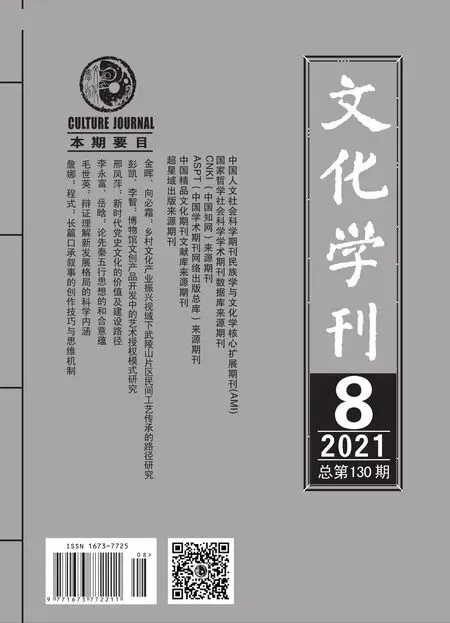从接受理论看《歌德谈话录》的重译
王丹若
早在20世纪30年代,《歌德谈话录》就已译介到中国,至今已有多个中译本,其中不乏具有较高名望与深厚翻译功底的译家之作。细读译本,可以看到不同译者在翻译主题与内容的选择、译文风格等方面的不同之处,这既有不同译者对于原作理解和阐释的差异原因,也有时代发展带来的读者语言习惯与社会文化的变化原因。《歌德谈话录》重译现象所体现出的译者、译文读者期待视野变化及其对文学翻译的影响令人深思。
一、接受理论
接受理论提出之前的历代作家和文学评论家普遍认为,作者和作品是文学创作的中心。而姚斯1967年提出的接受理论摒弃了以往学者们陈旧的看法,首次把作品和读者的关系放在文学研究的重要位置,肯定了读者对于作品意义和审美价值的创造性作用,认为作品的意义既有作者赋予的,也有读者赋予的,是二者的结合体,而这其中读者的赋予则更加重要[1]。是读者的阅读让文学创作的价值得以体现,而不同的读者在原文规定下的不同理解与阐释给予了文本不同的意义。
期待视野是接受理论的重要概念之一,是指读者因具有区别于他人的个人经历、文化背景、独特的思维方式与既有的知识结构等,在接触文本内容之前就对作品有所期待与预估。读者的阅读并非被动地接受[2]。这一理论的提出让文学创作开始重视读者作为接受者的审美。读者的期待视野包括对文本的形式和内容的期待,如文学形式、语言特色、表达方式、作品主题、人物情感等[3]。
二、期待视野与文学翻译
在我国,重译已是近年来翻译出版界较为常见的现象。许多德语经典文学作品,比如黑塞的《荒原狼》、歌德名篇《少年维特之烦恼》均已有多个中译本。在文学作品重译的过程中,译者重译的直接动机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是从深层次上分析,都可以用接受理论的期待视野影响来解释。
在文学作品的翻译过程和译文读者的阅读过程中,译者也是原作的读者之一,承担着为非原写作语言读者进行文本初步解读的任务。译者因不同的生活和教育经历所形成的个人期待视野会对文本有独到的理解与阐释,在翻译时会于作品的内容、形式和价值上找到不同的侧重点,选择其认为适当的翻译策略。因此,同一部作品的译作便会表现出差异性与多样性。
译文读者的个人期待视野与审美要求虽然千差万别,但在某一特定的时期,读者因其相似的时代文化背景会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公共期待视野。译者在考虑译文读者的审美时,会主要关照占主导地位的公共期待视野,从而调整自己的翻译策略,以适应读者的期待视野而被更好地接受。而读者的期待视野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着语言文化、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变化而发展。因此,同一部作品在不同的时代,由于译者或读者公共期待视野的变化都会有不同的解读与阐释。
“在译者、译文与读者这三者中,译者和读者都不是被动的存在,都是能动的角色。”“读者的期待视野影响和决定了译者对译文的处理;反过来,译者通过译文也保持或改变了读者的期待视野[4]。”因此,一部优秀的作品在不同时期由不同译者尝试重译,也就有其必要的原因。是译者与译文读者的期待视野的变化促使文学翻译推陈出新。
三、《歌德谈话录》的重译
歌德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并不再陌生。,由歌德私人秘书艾克曼辑录的《歌德谈话录》是人们了解、研究歌德的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之一。原书四十余万字,采用对话语录体,以日记的形式,用平实、轻快的笔调记录了歌德晚年在文艺创作、哲学思想、自然科学、宗教政治等领域的言论和活动。该书在出版后的近两百年里传遍了世界各国,西方各国几乎都有译本,且不止一种,堪称文学类、传记类著作中的经典,不论对普通读者还是人文学科学者来说都具有跨越时代的学习、研究和借鉴意义。
《歌德谈话录》的中译本已颇具规模。1935年,曾觉之先生的译本《高特谈话》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发行,该译本因年代久远而难再觅得[5]。1937年,周学普先生根据1912年柏林一家书店的《书友丛书》中梅列安氏(Gerhard Merian)的选编本[6]翻译的选译本于商务印书馆出版,由于当时战争迭起,该书的流传受到了影响,除了少数藏书者,几乎不为人所知。2000年3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和上海教育出版社又重新出版了周学普先生翻译的《歌德对话录》。
周学普先生对歌德的文学创作有着十分深入的了解,曾译有《铁手骑士葛兹》《浮士德》《少年维特的烦恼》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完全是因为“兴味上的关联”才翻译这本《歌德谈话录》,作为向“莎士比亚般多方面的活动的伟人”的致敬。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总会出于自己审美与兴趣的期待对文本的不同部分与内容给予关注。译者的期待视野甚至影响了译者对原作内容与形式的取舍,也左右了译者阅读与翻译的重点。周译本极大地保存了谈话录原有的风格,让人们在阅读中仿佛感到它给予人们的不只是理论,而是可以亲见的歌德的精神面貌。周译本的译文不仅传神,文学性也较强,比其他译本尤显从容优雅,实属最值得一读的《歌德谈话录》中译本之一。
《歌德谈话录》能被中国大众广泛接受和关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78年出版的朱光潜先生翻译的选译本功不可没。该书印行十余次,流传最广,目前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列为中学生课外读物。朱光潜先生选译的内容完全依据他自己的标准,用他自己的话说,凡属于应酬游览和个人恋爱之类家常琐事皆不取,而涉及哲学、美学、文艺理论、创作实践这方面的议论则包罗无遗。而有些主题,译者虽博学多才,却也不甚了解,比如颜色学、植物变形、地址和气象之类的自然科学内容只能暂放一旁,没有译出[7]。
朱光潜先生作为将西方美学介绍到中国的奠基人,在翻译黑格尔的《美学》时经常遇到提及歌德文艺创作实践和理论的内容,他也由此认识到歌德对于近代文艺发展历史的重要影响。因此,译者把《歌德谈话录》的翻译工作当作自己对歌德文艺理论思想的一种学习和研究,将选译内容的重心放在了文艺理论和美学方面。该译本在译文风格上,理论性和思想性较强,却让本来亲切、随意又具趣味性的对话录变成了一部正襟危坐的“谈话录”,或者说更像一个文学伟人的语录,读罢使人对这位欧洲伟大人物心生敬仰,不愧为名家之作。
以上两个译本均为选译本,译者所选话题与文本的不同,是由译者不同的生活经历、审美观念与艺术追求所决定的,皆可归因于译者差异性的期待视野。译者作为原作的读者,在阅读、理解和阐释原文的过程中,总会格外关注符合其自身审美与研究兴趣的内容部分;而作为译者,只能在自己的理解与能力范围内用目标语言为读者重现原文的内容与意境,这也让不同的译本体现出各不相同的译文语言风格与表达方式。
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读者更希望读到内容积极向上、理论性和思想性较强的读物,而不是有异国风味的作品。不断满足读者变化着的审美期待是译者的天职。译者虽有自己的期待视野,但也是身处在某个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社会的人,总会从自己所生活了解的文化出发,来解读异国的语言文化、社会与历史。当译者看到从前的译作不再能适应和满足当时读者的公共期待视野时,重译将成必然。这或许也是朱光潜先生重译《歌德谈话录》的理由与意义。
从21世纪开始,《歌德谈话录》的汉译经历了一段热潮。2001年,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吴象婴先生等人翻译的“全译本”。2002年,由南京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洪天富先生翻译的《歌德谈话录》“全译本”由南京译林出版社出版。此外,2000年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王君梅先生主译的另一译本。到2004年,先后有顾士渊先生等译者合译并由漓江出版社出版、王颖波先生翻译并由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两个译本问世。由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杨武能先生翻译的《歌德谈话录》先由浙江文艺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而后又相继于2006年和2008年,分别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和四川文艺出版社陆续出版。据此,《歌德谈话录》的译本达到了三十余种之多[8]。
除了朱光潜先生的选译本,杨武能先生的“全译本”当属目前极受关注的热门读本,再版次数也较多。杨先生曾于四川外国语学院的前身西南俄文专科学校学习俄文,那时班级盛行读前苏联和法国的翻译作品,他也深深地被《贵族之家》《猎人笔记》等作品吸引。通过大量的阅读,杨先生感悟到了译文优劣的重要性:一部外国作品是否能得到广泛的传播,文学翻译家的职责与贡献不可忽视——“名著随名译诞生而诞生”。自此,杨先生立志成为文学翻译家,随后转而学习德语,并师从冯志先生从事歌德研究。此后杨先生的德语文学研究与翻译实践几十年如一日,也为他带来了中德两国的多个重要奖项与学术声望。
早在1978年朱光潜先生的选译本刚问世时,杨武能先生就曾将其反复研读,也多次有过翻译“全译本”的设想。朱光潜先生曾谦逊地讲明,自己在翻译《歌德谈话录》的过程中遇到难于理解的方言口语等语言上的问题,便参考了英译本与法译本,转译成中文。然而,由于不同的语言与文化等方面存在着差异,艺术性较强的文学作品有许多弦外之意难以做到完全对等传达。经过两种语言的转换,原语信息的丢失、误读或者误译在所难免。从这一角度来看,朱译本虽是经典译本,但杨先生以其多年的德语文学研究为基础,重译《歌德谈话录》也有其明显的优势与意义。
《歌德谈话录》的第一篇谈话中,即1823年6月10日篇,有一段对歌德住宅内部装饰的描写:
朱译本:“仆人打开一间房子的门,我就跨过上面嵌着‘敬礼’字样的门槛,这是我会受到欢迎的预兆。”朱先生将拉丁原文译为中文“敬礼”,并将二字由加注标明“原文为拉丁文。”
杨译本:“他拉开一扇房门,但见门槛前嵌着‘SALVE’这个预示着客人会受到亲切接待的拉丁字。”其中的“SALVE”由杨先生保留了拉丁原文,加注标明了其中文语义:“拉丁文常用的问候语:您好。”
在同一篇谈话中歌德与爱克曼谈到了一位知名的编辑,朱译本:“我很快就把它交出去,今天就写信赶邮班寄给柯达。”其中“柯达”由朱先生加注,写明此人为“耶拿的出版商,歌德和席勒的著作都现先由他出版。”
杨译本:“我今天就给柯塔写一封专递快信,明天再通过驿车寄去装文稿的包裹[9]。”其中“柯塔”由杨先生加注,写明此人为“耶拿的出版商,以系统出版歌德、席勒的作品享誉文坛,留名史册。”杨译本对人物柯塔的更进一步介绍,是有意地在向读者介绍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
从以上两段译者对外来文化信息的处理可以看出,朱先生有意让译文更具中国特色。然而随着社会、历史语境的变迁,国人素养的改变,国际视野的开阔,70年末代的译本也许不再能吸引那么多的读者。我国读者对文本的语言特征与表达方式的期待也逐渐倾向于了解更多的异国文化,愿意领略到外文原文的独特风情;而对读本主题内容的期待已经超越了70年代末的爱情主题、政治斗争、阶级斗争、反封建等主题,更乐于读到能反映西方社会与文化的读物。由此可见,杨武能先生的“全译本”符合当时读者的公共期待视野,满足了读者的阅读需求与期待。
可以说,某一特定时期历史文化背景下的译本只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很难经受住时代更迭的考验。随着时代的变迁、文化背景的变化等种种因素必定会造成接受者(包括译者、读者)即使对同一话题也有不同的期待。时代的变化带来了不同的公共期待视野,能动的译者与读者让作品的时代意义也发生了变化。
四、结语
杨武能先生在接受中华读书报采访时曾表示,如果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他首先会选择耐读又富有哲理的《歌德谈话录》它不仅是一部雅俗共赏的文艺理论著作,也是一部极富情趣风韵的歌德晚年生活和言论的优美散文。周学普、朱光潜、杨武能三位的译本皆为经典,而三个译本的特色与不同也反映并证实了《歌德谈话录》重译的重要价值。
在文学翻译的过程中,不仅译者自身的期待视野会影响到译本,译者也会自觉不自觉地考虑译文读者的期待视野而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在当今通讯技术与传媒方式快速变化的时代,互联网发展和全球化进程让读者有了更高效的阅读体验,阅读范围更为广泛,中西文化差异也早已不再是阅读的壁垒。读者的鉴赏能力在快速地提升,对文学翻译势必会有更高的期待,这也就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得文学经典的重译成为必然——而这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译者所面临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