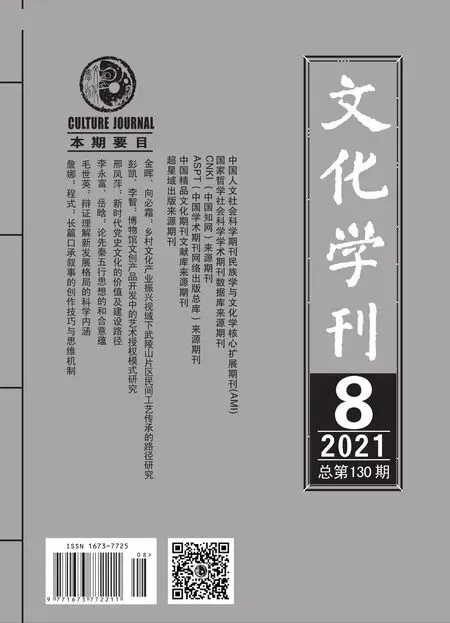浅析《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前四条
赵思帆
一、实践——超越唯物与唯心之争的纲领
(一)对旧唯物主义观点的批判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对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进行了批判与改造,认为这些观点强调世界的物质性以及人的受动性,在其中受动性被片面地发展了。他首先对包括旧唯物主义进行了批判,认为它们未能真正理解实践,没有从主观出发来看待物质世界,“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只从直观的形式来看待、理解整个世界,势必会使主体对人与现存世界的联系形成片面的认识,其原因在于旧唯物主义离开人的活动本身、离开人来考察整个世界。“实践”“感性的人的活动”,其实是某种可以被人们所具有的感觉所感知到的活动,即可以被感知、观察、意识到的活动,是实际存在的活动,它具有某种实在性、直接现实性,而不是所谓的纯粹的理论活动,不是假想出来的活动。我们通常所说的主体的人进行的认识活动以及理论活动,这些都是在思维的领域内进行的活动,不具备直接现实性的特点,不能使现存事物发生某种实际的改变,只有通过实践这种感性的人的活动,我们才能够有能力去超越思维领域内所进行的认识活动和理论活动,进而达到对现存的事物的某种改变,逐渐打破现存条件的束缚,这是马克思在对旧唯物主义的改造之后所形成的新的唯物主义思想,通过对费尔巴哈思想的扬弃,马克思阐明了自己与旧哲学的根本区别。
(二)对唯心主义的批判
马克思也对唯心主义进行批判与改造,认同其强调人的主体性以及能动性的方面,它把人的精神、意志等因素置于主导性的地位,对否认世界的物质性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人的受动性等进行了批判,即能动的方面被抽象地发展了。马克思认为唯心主义相对于旧唯物主义来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意识到了“能动的”方面,但是对这方面发展也是有局限性的,它其实只看到人的精神和意志等作用,并提出:“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1]这里所提到的“能动的方面”,是构成实践的重要因素。他认为唯心主义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把实践看作是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没有看到人在现实世界的现实的活动,这一切都只是在抽象的、思辨的领域中进行的。这种唯心主义只是从思维的范围内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认为从理论上可以解决现存世界的现实性问题,而没有看到实践活动在生产活动中的作用。
(三)超越唯物与唯心之争
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可以说是扬弃了二者。在他看来,唯物主义所抽象发展的能动性、唯物主义所抽象的发展的受动性,二者都是实践活动不可或缺的因素。正是鉴于能动与受动两大特性,才随之形成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阵营。他结合了唯物主义所强调人的受动性的特点以及唯心主义所强调人的能动性的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也就是超越了两者。
他超越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在于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批判唯物主义所认为受动的特性而强调实践活动的能动性。他将过去属于唯心主义的“能动性”的原则运用于实践活动,也就是说吸收了唯心主义中的合理的、正确的因素,肯定了人的能动的特性和主体性的特点。另一方面,他又在一定程度上批判唯心主义的能动性,指出要看到实践活动中的物质性的特点。他首先对“物质性”进行了肯定,认为进行实践活动的主体、客体,以及运用的手段都是物质的,都具有物质性的特点,这体现了这种能动性的物质性,也可称为“受动性”。强调受动性是唯心主义的基本特点,要想真正克服唯心主义,就要看到实践活动的物质性,看到物质性的力量。脱离了物质性的制约来讨论、看待人在实践活动中的能动性,是抽象的、片面的,只是纯粹的理论活动,只是不切实际的妄想。
在对旧唯物主义观点的批判以及对唯心主义的批判基础上,马克思对二者进行了继承与改造,进而建立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观。“马克思是唯物主义者,肯定唯心主义和思维的能动性之后,接下来必须在唯物主义的框架中对这种能动性作出解释。”[2]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实践中才是检验自己的思维是否具有真理特性的标尺,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真正使自己对象化的思维上升为真理,离开了实践,这种思维就是不现实的,它就仍是“彼岸性”的,还与现实存在巨大的鸿沟。实践是检验思维是否具有真理性的一把“标尺”,人们的思维是否具有真理性,仅仅在理论上、仅仅在思维的领域内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正是由于实践自身具备联系主体和客体的中介的特点,才使得实践具有检验思维真理性的作用,同时它能够在生产活动中不断对思维活动加以改造,使思维活动更加符合真理性,这种观点批判了旧唯物主义者把感性直观当作真理的标准,从而坚持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真正的真理标准。
二、实践——重构人、环境、教育的关系
(一)旧唯物主义中三者之间的关系
《提纲》中第三条提到的“唯物主义学说”,指的是出现于18世纪法国的机械唯物主义,其主要代表人物为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人,提出了诸如“环境决定论”“教育万能论”等等观点。主要特点是过度夸大教育与环境对人的影响,认为环境与教育决定着人的发展,也决定着社会的发展,同时认为教育是万能的。“这种学说必然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1]这些学说把教育与环境的关系建立在一种单向的基础上,没有看到人对教育与环境的作用,没有在人、环境与教育之间建立一种双向的关联性。它们只看到了教育与环境对人所形成的影响,却片面地认为人不能够对教育与环境加以改变。他们还指出,人之所以能够进行生产生活,进而改变环境和教育他人,是由于在社会中有少数的天才人物可以突破环境对他们的制约,而这些天才人物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总的来说,这种学说没有看到人在教育与环境中发挥的作用。
(二)马克思重构人、教育与环境的关系
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中三者的关系进行了批判性改造,重构了三者的关系。在《提纲》中,马克思关于人与环境、教育关系的阐述有力地批判了旧唯物主义对教育与环境的“决定论”,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崭新的世界观。“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1]马克思看到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人、环境与教育不仅是基于实践的,同时也是统一于实践的,他认为实践将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环境联系起来,在实践活动中,作为客体而出现的环境以及作为主体而出现的人,都需要依赖于实践这一中介,通过实践才能将它们二者真正的联系起来。每一个人在生产生活中都可以自发的、自主地与环境进行或多或少的互动与关联,不是被动地去适应所属的客观环境。他看到了人的主体性地位,看到了以往“唯物主义学说”所忽视的人对环境所进行的反作用,看到了人具有能动与受动的特点,看到了环境具备能动与被动的特点。从一方面来看,环境影响着人。作为主体的人在物质世界中进行生产生活,在实践活动中必定会受到整个大环境,即物质世界某种程度的制约;另一方面,人也影响环境。每个独立的主体在社会所给予的各种条件中,根据自身的情况从而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最终达到对环境的改造。人的实践与环境相互作用,而教育作为实践中的重要形式之一也属于实践,因此,人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必不可少地受到教育的影响,在谈到人与环境的关系时,必须把教育因素考虑进来,三者不是孤立的。
针对旧唯物主义所提到的教育与环境决定论等观点,马克思也对其进行了改造。马克思打破了旧唯物主义所认为的人与环境、教育的单向的关系,建立了三者的关联性。人的实践活动将环境与教育结合起来,教育与环境统一于主体所进行的实践中。“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所谓的“革命的实践”,是指人进行的实践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人改变了环境。人是环境的产物,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人不断改变环境时,其实也在改变着自身,即人的改变在某种程度上说其实是“自我”的改变,促使主体不断发生改变的原因恰恰在于人自身。之前的唯物主义只看到了环境对于人所起到的决定作用,而唯心主义抽象的发展人的能动性,可以说它们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马克思基于实践的观点,将人改变环境与环境改变人结合起来,看到了在实践中人和环境的相互作用,同时将教育包含在实践中,从这个角度看,他重构了人、教育与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
三、实践——揭露消灭宗教的途径
(一)对费尔巴哈的肯定
《提纲》中马克思也对宗教问题有所涉及,他首先对费尔巴哈所做的工作进行肯定。他在其中提到,费尔巴哈对于宗教问题的研究不仅仅是将宗教局限在自身中进行考虑,而是打破了宗教的界限,着眼于世俗世界中去对宗教问题加以研究和深入,他将世界分为宗教世界与世俗世界,为宗教的研究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最终他将宗教世界归结于它自身的世俗基础。费尔巴哈认为:“人的依赖感是宗教的基础”[3]。宗教的产生是由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有无法突破的限制,在现有条件下难以满足自身的欲望,于是人们转而诉诸于某种神灵,由之形成依赖性,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宗教,而随着这种依赖的增强,人们对其信仰程度也就越来越高,宗教的发展就变得更加稳固。在宗教中,与神灵有关的概念其实都与人的活动密切相关。在此,马克思肯定了费尔巴哈所做的工作,即从世俗世界切入,从而为揭露消灭宗教的途径指明正确的方向。
(二)揭露消灭宗教的途径
1.阐明宗教产生的根源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进行肯定,同时也指出他的局限性,认为他没有对世俗基础本身进行深入地批判与深层次的探究。马克思从世俗世界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出发,阐明了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他认为,在人类社会早期,宗教源于与自然界的矛盾,人们处于生产力及其低下的环境中,面对无法解释的现象从而诉诸于某种神灵,逐渐对其产生依赖,由之产生了宗教。在进入阶级社会后,人们处于不同的阶级,各种阶级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需要对其他阶级进行思想上的控制与奴役,不可避免地将宗教与政治统治普遍联系在一起,宗教日益成为统治阶级实现其权力的掩盖物,成为掩盖在阶级斗争中获得胜利一方的权益的“武器”。马克思立足于实践,从费尔巴哈所引出的路径,即世俗世界自身的矛盾出发,通过分析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找到了宗教产生的根源。
2.揭露消灭宗教的途径
马克思在找到宗教的源头之后,对宗教进行了更加深入与彻底地批判,进而揭露了消灭宗教的途径。他认为宗教产生于世俗社会中的自我矛盾,既然产生于世俗社会,那么消灭宗教就不能只在宗教自身的范围内进行,必须从它的产生根源中来消灭。宗教作为社会发展的产物,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的,宗教必然具备一定的客观原因以及现实基础。因此,如果不在实践中找到宗教存在的客观原因,废除宗教赖以生存的现实基础,那么通过其他手段所进行的废除宗教的活动,不会达到对宗教的真正废除。马克思认为,废除宗教的途径必须在世俗基础本身所存在的矛盾中去寻找,只有在实践的过程对世俗基础所存在的矛盾进行“革命的”改造,进而推翻宗教赖以生存的现实基础,才能真正地废除宗教。宗教的产生与发展,归根结底都是来自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各种矛盾,来自人们在现实中的某种缺失。只有当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表现为合理的状态时,即达到物质资料极大丰富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的状态时,也就是说,人们不再需要也没有必要从某种神灵的期许中去获得满足感,实现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时,只有达到了这样的状态,宗教才能够真正地走向灭亡、才能真正被废除。
总之,马克思首先肯定了费尔巴哈对宗教研究的正确导向性,即费尔巴哈将宗教的产生归于世俗基础,然后他从世俗社会的矛盾中进一步对宗教加以分析、批判,进而找到消灭宗教的真正途径。马克思将费尔巴哈对宗教所做的工作进一步深入,对宗教赖以生存的世俗基础进行更加深入地研究,阐明了崭新的观点,揭露在实践中消灭宗教的途径。
在《提纲》第一条,马克思通过对包括在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以及唯心主义的批判阐明了自己鲜明的观点,首先表明了实践是二者的结合;第二条中,表明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证明自己思维是否符合真理性,第三条中,提出实践活动使得人与教育、环境相互作用,重构了三者之间的关系;第四条中,他进一步分析世俗社会的矛盾,揭示了消灭宗教的路径。在这四条中,马克思突出表达了实践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