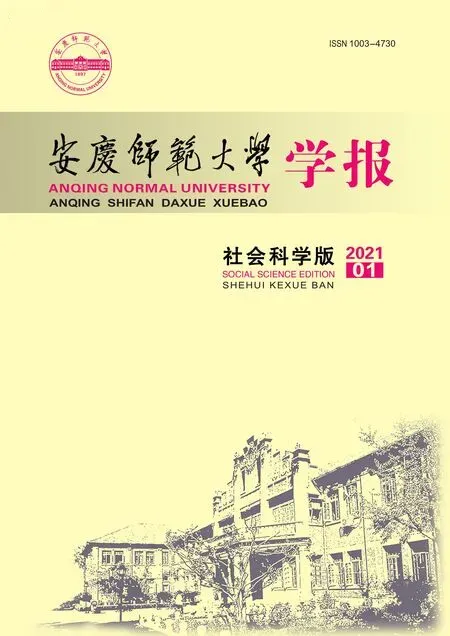运用传统学术方法 创作与研究老舍传记
——以徐德明著述老舍传记为例
谢昭新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芜湖241003)
在老舍研究领域,老舍传记迄今已有近20种。徐德明著述老舍传记,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此之前已有多部老舍传记问世,可他编著的《老舍自传》一登场,即以崭新的面貌,打破了老舍自身未写过完整的自传以及学术界也未曾有过的《老舍自传》的格局。《老舍自传》于1995年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2006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再版,更名为《老舍自述》;2018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老舍自传》未标明徐德明编著。徐德明在《老舍自传》出版之后,又推出两部创新之作,一是《图本老舍传》(长春出版社2012年版),二是《老舍自述:注疏本》(现代出版社2018年版)。本文首先引论老舍对三十年代“自传热”的反应,以凸显《老舍自传》的突破意义;其次分别论述三部老舍传记的特色,并作版本比较,以显示其内在的联系及创新发展;再次论述三部老舍传记所运用的传统学术方法,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启示。
一、引言:老舍对三十年代“自传热”的反应
20世纪30年代初中期,文坛曾兴起自传写作“热”。胡适1930年开始写自传《四十自述》,他自己写自传,还动员老朋友们写自传,比如他曾劝林长民、梁启超、蔡元培、张元济、陈独秀、熊希龄、高梦旦等写自传。在他倡导带动下,形成了20世纪30年代“自传热”。上海第一出版社推出“自传丛书”,先后有1933年出版的《从文自传》,1934年出版的《巴金自传》《钦文自传》《庐隐自传》《资平自传》,1936年出版的中文版《林语堂自传》等。20世纪30年代的自传有两大类,一类是偏重于传记的历史属性的自传,像胡适、郭沫若的自传;一类是偏重于传记文学属性的自传,像郁达夫、沈从文的自传。老舍没有在20世纪30年代“自传热”中写自传,他在1934年1月《大众画报》第3期发表了《自传难写》一文,可以视为他对20世纪30年代“自传热”的回应:他不愿写自传,不愿以自传而“留名千古”;他说写自传要有“好材料”,可到哪里去找“好材料”呢?他还对自传流行的写法加以奚落,头一章要叙述家庭谱系,可他家既非名门,家族里又无“英雄”;第二章要写如何降生且富有传奇色彩,“怎么产房闹妖精,怎么天上落星星,怎么生下来啼声如豹”,可他生下来,母亲无奶,“常吃糕干”,无法写;第三章幼年入学光景,即使写出,“又不体面”;第四章写青春时期“更难下笔”。思来想去,自传难写,他写不成[1]。到了1938年他才在《宇宙风》上发表《小型的复活——自传之一章》[2],其写法不像胡适、郭沫若自传那样从家族、出生、童年写起,而是写他青春期,如何克服不良“嗜好”度过“二十三,罗成关”的,从类型上看它不以史实记述为主,用的是小说的笔法带着感情写那时的“苦闷”,是属于文学属性的自传,在具体地记述中有描写有故事有细节,生动有趣!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小型的复活》还算不上自传,说它是回忆散文更贴切些。由于老舍生前没有写过完整的自传,这就为撰写《老舍自传》设置了莫大的难度,再加上学界迄今只有老舍的他传、评传、传略等,而未有一部《老舍自传》,更显示出徐著《老舍自传》的突破价值了。
二、《老舍自传》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自传写作现象,从表面看,《老舍自传》是基础,为后面的《图本老舍传》和《老舍自述:注疏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从内质上看,它们各有特色各有创新,每部著作都有说不尽的精彩。自传一般成为老人对自己青壮年往事的重新阐释甚至塑造,这就难免带上主观色彩,自己写自己,哪有那么冷静客观的。徐德明把《老舍自传》视为“准自传”,是他从老舍自述的所有文本中,包括生平自述、回忆散文、创作谈、自叙小说去搜罗自传材料,按照时间顺序加以编著,这样就避免了自传中的主观色彩与失误,有着“准自传”的客观真实与生动。作者在《后记》中记述了编写原则:“我将老舍的自传材料作了适当的调度、合并、删节、组合。但我的准则是:尽可能保持作品原貌。除删节、组合外,我仅仅加了极有限的几个贯通语气的字,用括号标出,想必能获读者理解。”[3]307全书以老舍的《昔年》与《今日》两首诗作为“序诗”,呈现其“童年习冻饿”“壮岁饱酸辛”“晚年逢盛世”“滚滚横流水”“茫茫末世人”的一生情景。用诗引领读者进入老舍人生的主要时段,按照时间顺序设置了八章:第一章:童年习冻饿(从出生、童年到入学读书,1899—1918);第二章:糊口四方(1918—1924年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到社会上做教育事业,再到英伦讲学1924年9月—1930年2月);第三章:壮岁饱酸辛(1930年3月—1937年11月,济南、青岛期间的教书、创作);第四章:八方风雨(抗战时期在武汉、重庆的生活与创作1937年11月—1946年3月);第五章:旅美译介(1946年3月—1949年12月);第六章:晚年逢盛世(1949年12月—1966年4月);第七章滚滚横流水与第八章:茫茫末世人(从1966年5月开始到同年8月24日离世)。以上各章括号内的文字为笔者所加,由此可以看到此书按时间顺序选取老舍自述文本,体现自传的史实性、真实性,更加之选取的老舍自述文章所具有的文学性、艺术性、审美性,比如第一章写童年时期老舍的出生,选取了《正红旗下》的一段文字,有记述,有描写,尤其是“洗三”的风俗:从“添盆”开始,把“我”放到盆里,白姥姥边洗边说些吉祥话儿;洗完后“我”发出了啼哭声,这叫作“响盆”;“响盆”后白姥姥又用大葱打了我三下,口中念念有词:“一打聪明,二打伶俐”,后来应验了“我”和“大葱一样聪明”[3]3。整个情节生动有趣,使自传的头一节就紧紧地抓住了读者。这一章的最后一节写老舍的初恋,选取的是老舍的一篇散文《无题〈因为没有故事〉》,其实是小说的写法,有对初恋者眼神的描写,有内心情感富有层次的波动,呈现了一个初恋者的“甜美的梦”[3]24。还有像第六章第四节找到自己位置,编者在此加了必要的注释:“是他对自己一生思想、对中国革命认识的总结。”[3]286这样的选文与注释,在文学性、审美性中又具有可贵的学术价值了。因此,这本《老舍自传》熔文学性、艺术性、审美性、学术性于一炉,不仅为普通读者提供认识老舍的生动史料,而且为研究者提供必要的参考资料,具有独特的实用价值。
三、《图本老舍传》
在《老舍自传》问世后,徐德明又推出《图本老舍传》,在此书出版之前,虽然已有几部或以画集以显老舍简传或在《老舍评传》中配以若干幅图的著述,而真正标明“图传”的是关纪新著、舒济供图的《老舍图传》(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段煜在评价此书时认为:“此书的文字部分是关纪新《老舍评传》的缩编,图片部分则取材于《老舍》画册,可以看作是对两部著作的精选。但是,这种加工过于粗浅,由关著在写作时是纯文字的,因此,无论是用现成的文字去找图片还是根据图片来截取与之相关的文字,都会存在契合度较低的问题。这种直接摘编的写法使得本书的图文之间缺乏有机联系,难以充分发挥图文配合的优点。”[4]徐德明的《图本老舍传》又是对老舍图传写作与研究的突破。在我看来,徐著的突破意义不仅在于图文并茂、图文的有机联系所凸显的文学张力和审美情趣,更让我欣赏的是它的学术价值,它颇似一本老舍评传和老舍传论,它凝聚了作者数年来研究老舍的成果,比如对老舍创作的研究,对老舍小说中西诗学的实践的研究,对《离婚》及老舍小说叙事艺术的研究,对《骆驼祥子》和现实主义批评的研究等,还有对老舍着装研究,老舍与书画的研究等等,那么多的研究成果都融入画传中去了。
从《老舍自传》到《图本老舍传》,又可以看到徐德明的老舍传记写作与研究对自身的发展与突破。如果说《老舍自传》系“准自传”,那么《图本老舍传》属他传,自传与他传的写法,当然不一样。从两本书章节的标题看,不尽相同,图本的章节标题不仅文学审美色彩浓郁些,而且扣紧与图的联系,但在以时间为序的时段上大抵相近。由于是一个作者既写“准自传”又写“图本传”,再加上作者是老舍研究著名专家,对老舍全部著作稔熟于心,因而使得《图本老舍传》与《老舍自传》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比如在章节中,文字部分除了有作者的评论外,还用了一些《老舍自传》中的老舍自述文章,比如第一章选用了《〈神拳〉后记》《我的母亲》等文,第三章《英伦记略》选取了《东方学院》《写与读》等文,可这里用老舍自述文章与《老舍自传》又有不同,在《老舍自传》里是将选取的自述文章列出后加以简略的注释,而《图本老舍传》是在记述、评论中自然融入所选取的老舍自述文章。比如在记述老舍的“入学”经历时,最让老舍感恩的是宗月大师(刘寿绵),于是此节配有宗月大师的图像,在评述文字中,则融入了老舍纪念宗月大师的文章《宗月大师》,老舍感激宗月大师对他的引导,“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与意义”[5]。
四、《老舍自述:注疏本》
《老舍自述:注疏本》是《老舍自传》的升华,它们在章节的设置上基本相同,章节标题的文字相同,每章每节选取的老舍自述文也基本相同,只是《注疏本》将《自传》的第六章也即新中国成立后的老舍篇,分成二章,形成第六章《晚年逢盛世》和第七章《文章太平》,这比《自传》更科学些,更贴近老舍解放后的思想、创作的发展历程。尤其是第八章的《滚滚横流水》变化较大,选取了老舍自述文《下乡简记》,由此取消了《自传》的《滚滚横流水》。最后一章《茫茫末世人》,两书都用“再见”二字结束全书,但《自传》附录舒乙的《再谈老舍之死》,而到了《注疏本》再用这一附录那就不合时宜了。但《注疏本》的“再见”配有老舍与孙女舒悦的照片。由最后一章的文与图的有机结合,再看看前面几章,也有自述文与图的结合(正文配图15幅,扉页13幅),可见《注疏本》与《图本老舍传》的有机联系。更让人称赞的是作者将《图本》中的老舍研究的精华成果用于《注疏本》,增添了《注疏本》“注疏”的更多亮色。
是的,《老舍自述:注疏本》的突出特色即在它的“注疏”上。其“注疏”特色主要表现:
一是难度大。在《老舍自传》中,作者已经作了对老舍自传材料的选择、调度、合并、删节、组合的难度很大的工作,但这本书中的注释较少且较简略。即是说《老舍自传》只为《老舍自述:注疏本》提供了必要的老舍自述材料,而没有为“注释”“注疏”提供什么帮助,奠定什么基础,所以《注疏本》完全是在“0”的起跑线上的开拓创新。更为艰难的是“注疏”的对象是多才多艺的并在创作文体上无所不包的著名作家老舍,是老舍的一生各个历史时期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史料涉及面广,注疏难度大。正像舒济先生在本书的《序》中所言:“这些需要注释的词汇涵盖老舍先生一生各个历史时期和生活的各个方面。词汇名目繁多,涉及大量历史、地理、习俗和人名,有些注释的资料是很难搜集到的。”[6]2比如老舍著作中涉及的古今中外人名太多,仅现代人名就有475人,当然,书中的老舍自传材料没有涉及这么多现代人名,但在抗战时期的老舍,作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总负责人,他交往的现代作家、文化人特别多,有的可以在《老舍文学词典》或《简明老舍词典》中找到参考资料,但找到了也要作剪裁、组合,有的人名不见于“严格”的史书,只得去搜集整理,作“古籍整理”工作了。因此,老舍的“历史化”和其生活、创作时空的广阔性,为作自传的“注疏”增添了莫大的难度。
二是具有严格的史实性、科学性。对人名、地名、文学期刊、出版社、社团流派、作品发表出版的时间等等,均做到了博考文献,言必有据,注释科学、准确无误,为研究者提供了必要的参考资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以人名的“注释”为例,比如对艾支顿的“注释”即突出其是英文版《金瓶梅》译者,并疏证直到此译本诞生54年后才有另一译本的出现,还引用了艾支顿感谢老舍对他译此书的“慷慨的帮助”[6]66。不仅让读者了解了艾支顿其人,而且也照见了老舍与艾支顿之间的亲切关系以及老舍对英文版《金瓶梅》所作的贡献。对人名的注释突出重点兼顾一般,比如第四章第四节,抗战时期的老舍自述中涉及的人名,像冯玉祥、郭沫若、茅盾、吴组缃、胡风等注释文字较翔实,大抵在400~500字,而注一般作家或政府官员则用墨较少,比如注方治只用了87个字。还有对地名的注释,也都经得起实地考证,像老舍旅英期间的伦敦住所,不仅注明其具体方位:“在伦敦西部的荷兰公园区圣詹姆花园街31号”,而且对“注”作“疏”:由于老舍在中国文学艺术方面的杰出贡献,经英国文化部评定,老舍居所已列为名人故居[6]66。
三是以评论代注疏,凸显独到的学术价值。作者将自己多年来研究老舍的成果带进“注疏”中,以评代注,疏出新意。对老舍最早于1923年写的短篇小说《小铃儿》,除注明小说发表的时间、刊物,点评小说背景、主要情节,引用老舍《儿童主日学和儿童礼拜设施的商榷》的话,得出小说的主旨是关注“教育”[6]66问题。对《断魂枪》的注疏,将其视为“反武侠类小说”[6]69。将这一条注疏与《图本老舍传》“另类武侠”一节连起来读,更觉得作者对《断魂枪》从情节、想象、人物性格和动作描写等方面所作的评论格外精彩。对《骆驼祥子》的注疏,不仅从接受美学角度去阐释《骆驼祥子》的读者定位,而且将其视为“一个现代人类生存的寓言”,并突出小说的情感主调“仍然是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6]69。全面审视本书,有诸多注疏均似独到的评论,属作者多年学术成果的结晶,它们具有文学性、学术性。
四是以自述注自述,显示注疏的审美性。在选取老舍自述《我怎样写〈赵子曰〉》一文,其中有这一句话“《赵子曰》便是这点高兴的结果”。对此选取了老舍《写与读》作注[6]70-71,共有1 000多字,以证实老舍系统阅读了欧洲文学作品,促进了其创作的发展。在选取老舍自述《我怎样写〈离婚〉》一文中,有“故都景象”一词,注疏全录老舍的《想北平》以呼应“故都景象”,也说明北京对于老舍创作的重要性,显得这样的注疏非常机智巧妙。第四章“八方风雨”篇,抗战全面爆发后,老舍自述离开济南时的内心复杂情感,注疏则用老舍致陶亢德的信呼应老舍当时的复杂心情。像这样以自述注自述,正文篇“自述”是美文,注疏中的“自述”也是美文,让人感到真实亲切,享受美文的审美魅力!
五是以谐趣取胜,增强注疏的可读性。老舍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因治肠胃病,医生严嘱他戒酒,第四章“八方风雨”第七节选取老舍自述文《戒酒》,注疏则节选了台静农《我与老舍与酒》一文,此文妙趣横生,写出了老舍以酒待人与朋友相处的真挚情感,再加上老舍在《抬头见喜》一文中非常风趣幽默地谈了自己三次戒酒的情景,呈现出一位真性情的幽默作家老舍形象。也是在这一节的老舍谈“衣”的文章中,作者在注疏中特别将老舍的着装中装、西装、中山装的变化与社会政治的互动联系起来,以阐明“身份”意识。这里的注疏融入作者的论文《老舍着装的历史内涵与精神表征》,我记得关于老舍的着装,徐德明好像在第六届老舍国际学术会上作过演讲。在第六章第四节的家居生活,“儿女们”体现了“家”的温馨,父母儿女们的亲情;“花草”体现老舍的生活情趣、生活的艺术;“看画”凸显老舍看画、懂画、评画精湛的艺术修养;“怀人”则选有老舍自述文章《白石夫子千古》,注释“齐白石”的文字与前面扉页配画:黄永玉的套色版画《齐白石像》,这幅画像上有老舍“一代风流老画家”的题词,正文与注释与画图连起来读,美趣无限,读兴无穷。
六是以阐释问题见长,显示注疏的“小学”特征。所谓“注疏”是注解与解释注解的文字合称,作者在《后记》中言此书“注疏”“虽不谈小学训诂,也要言必有据”[6]115,其实在“言必有据”中已显示出“小学训诂”特征了。书中不少“注疏”不仅注明“是什么”,还疏证“为什么”,这就使得“注疏”似带着问题在作“考证”。比如老舍在旅美期间,为《离婚》译事的版权问题,注明老舍被迫集中精力与伊文·金理论,由此还将老舍此间的复杂心情展示出来,从而得出结论:老舍为维护著作权益而不得,由此造成心里“苦闷”,这“苦闷”促成他“不能一直待在这样的国家里”[6]134。又比如新中国成立后,在第六章第二节由老舍致劳埃得的十封信,注明老舍进入新社会生活,很少写个人生活的文章,并疏证老舍不愿写个人生活的三个原因。又比如第三章第五节的老舍自述《我怎样写〈二马〉》中有“报章文学”一词,何为“报章文学”,作者博考文献,首先注释了复旦大学新闻系首任主任谢六逸的“报章文学”观,他从新闻与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及文学对新闻的影响出发,“通过辨析两者各自的含义、性质,认为从广义上讲报纸上所有的文章都可以当成文学形态来看,文学涵括新闻,从而充分阐述了‘报章文学’的思想”;其次阐释了朱光潜关于“报章文学”观是“一种纯文艺的界定”;最后疏证老舍多有认同朱光潜之义,“表达的是一种纯文艺的界定”[6]73。这又是一篇阐释问题的“考证”。
五、徐著老舍传记的方法论的启示
徐著三部老舍传记主要运用了中国传统学术方法:文献研究方法,考据方法,义理阐释方法,直觉体悟方法。这些传统学术方法是在文本的章节设置、内容阐释、注疏条目中自然显露出来,而不是先以某种传统方法去套用文本中的某些内容。文献研究方法主要体现在作者对老舍自述文本的搜集、鉴别、整理上,它要从《老舍全集》(共19卷)中选取老舍自述文本,包括生平自述、回忆散文、创作谈、自叙小说等,对其进行适当的调度、合并、删节、组合,形成老舍自传材料,并通过对这些自传材料的研究形成对老舍其人的科学认识。考据方法主要体现在注疏对人名、地名、传说、历史典故的考证上。比如老舍自述文中说他在全北京的人“都在欢送灶王爷上天的时刻降生的”,注释便注明了灶王爷是玉皇大帝的“东厨司命灶王府君”,保护和监察一家。每年到了腊月二十三(中国北方腊月二十三,南方腊月二十四)灶王爷升天,向玉皇大帝汇报这家人的言行善恶,并把这家来年吉凶命运带回。因此,人们通过祭灶的方式希望他能“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6]9。这就把灶王爷的传说注释得清清楚楚。又如对儒家经典的注释,老舍自述文中出现“鲁卫之政”,对此加以注释:语出《论语·子路》:“鲁卫之政,兄弟也”。鲁是周朝周公的封国,卫是周公之弟康叔的封国,两国的政治情况也像兄弟一样差不多[6]72。再如对道家典故的注释,老舍自述文中有“阴骘文”,注云:《文昌帝君阴骘文》简称《阴骘文》,道家重要典籍。作者不祥。劝善之书。义理阐释方法主要针对老舍自述文本中的关键词句、重要作品进行阐释、评论,比如老舍自述他是如何度过“二十三,罗成关”的。注云:旧时民谚,大抵是受《说唐演义全传》和据此而编的戏曲《罗成叫关》的影响,并阐述了罗成战死的故事情节。罗成战死时年二十三岁,故民间青年男子忌讳二十三岁(虚岁),认为它是人生第一个关口[6]43。直觉体悟方法主要体现在作者将自己对老舍人生及其作品的细读、体悟融入注疏,往往以注出新意见长。比如说《骆驼祥子》的主旨是“一个现代人类生存的寓言”;《断魂枪》属“反武侠”类小说;《茶馆》是老舍“反思一生经验的现代语境的结晶”[6]385。这些传统学术方法的科学运用,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启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