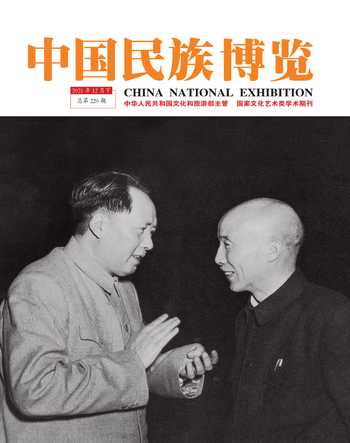蒙哥马利《绿山墙的安妮》对女性成长小说的继承和突破
【摘要】尽管屡被批评缺乏深度,露西·莫德·蒙哥马利(Lucy Maud Montgomery)《绿山墙的安妮》依然对传统女性成长小说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发展。与多数女性成长小说相同,《绿山墙的安妮》具有自传色彩,并通过对日常生活的细致描绘勾勒了主人公的成长历程,与此同时,小说打破了女性成长小说以爱情和婚姻为主的成长模式,表现了主人公成长过程中女性意识的真正觉醒,实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女性成长小说的突破。
【关键词】《绿山墙的安妮》;成长小说;自传性;日常生活;女性意识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24-189-04
【本文著录格式】卢星宇.蒙哥马利《绿山墙的安妮》对女性成长小说的继承和突破[J].中国民族博览,2021,12(24):189-192.
写作《绿山墙的安妮》(以下简称“《安妮》”)之前,露西·莫德·蒙哥马利(Lucy Maud Montgomery,1874—1942)已经发表了数篇短篇小说或诗歌,但《安妮》的出版令其获得了国际声誉,马克·吐温曾盛赞《安妮》是“继不朽的爱丽丝之后,最令人感动和喜爱的儿童形象”,但因《安妮》描绘了一个“冬天短暂得似乎从未留下痕迹,不存在生存问题,也缺少山川、灌木、海盗和铁路”[1]的世外桃源,很长一段时间,评论家都将蒙哥马利看作是毫无深度的作家。蒙哥马利的写作风格也与以“生存”为主题的加拿大文学格格不入,因此研究者甚至一度将她从加拿大文学史除名。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安妮》作为女性主义文学作品才重新走进了研究者的视野,近年来,國内外对《安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接受状况,以及小说所体现的宗教思想或宗教原型等,但作为一部经典的女性成长小说,鲜有研究者从成长小说的角度去解读这部作品。
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常英译为Initiation Story)起源于德国,它“不像是英国的和法国的小说那样,描绘出一幅广大的社会图像,或是纯粹的故事的叙述,而多半是表达一个人在内心的发展与外界的遭遇中间所演化出来的历史”[2]。成长小说的主人公大都是年龄在10—20岁之间的青少年,学者莫迪凯·马科斯认为,主人公通常在历经挫折或磨难之后,“或改变了原有的世界观,或改变了自己的性格,或两者兼有;这种改变使他摆脱了了童年的天真,最终把他引向了一个真实而复杂的成人世界”[3]。自1795年歌德《威廉·迈斯特的学徒时代》出版,标志着这一小说体裁的正式确立,成长小说在欧美各国兴起并不断发展,伴随着本国文学的独特气质,19世纪英国成长小说的主人公大都出生贫寒,但通过自身不断奋斗,最终取得成功,并获得成长;在19世纪的美国,“美国梦”是成长小说贯穿始终的主题;20世纪以来,英国成长小说偏重主人公的“顿悟”瞬间,如乔伊斯的《阿拉比》;美国则走上了“迷惘”与“垮掉”的反成长道路;起源于航海与拓荒日记的加拿大文学在《安妮》出版前则缺少优秀成长小说作品。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以来欧美国家涌现了大批优秀的描写女性主人公成长历程的成长小说作品,如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美国路易莎·梅·奥尔科特《小妇人》等,女性成长小说的内容通常包含爱情与婚姻的挫折、对男权的反抗以及对性别平等的追求,且常常颠覆男性成长小说的结构与情节模式,相比较之下,安妮的成长似乎过于平淡而顺遂,但蒙哥马利也对传统成长小说包括传统女性成长小说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了突破与改写。
一、改编童年:成长的自传书写
成长小说大多具有自传性。学者莫甘(Maugham)认为,成长小说虽不是自传,但具有自传性,真实与虚构事件互相交织;作者在写作成长小说时投入了真实的情感,但并不是所有情节都取材自作者的亲身经历。此外,成长小说一般是作家的早期作品[4],读者可以在一部成长小说中窥见作者自身,比如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主人公的经历就是作者在寄宿学校的悲惨童年与成年后去布鲁塞尔求学经历的改写,其英文副标题也是An Autobiography。
《安妮》是蒙哥马利第一部长篇小说作品,也具有浓厚的自传色彩。蒙哥马利于1874年出生于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的卡文迪许村,幼年丧母的她由外祖父母抚养长大,她自幼喜爱写作,曾于1895—1896年在达尔豪斯大学研习文学,大学毕业后教书并供职于一家报社,1902年因外祖母重病不得不辞职,返回卡文迪许村照顾外祖母,在此期间她完成了《安妮》的创作。可以看出,小说主人公的成长轨迹与蒙哥马利总体一致:安妮·雪莉从小父母双亡,11岁时因误会被本想领养男孩的马修、马丽拉兄妹收养,开始了绿山墙农庄的生活。被收养之前,安妮常常用丰富的想象力填补童年生活的不幸,她将这个习惯带到了绿山墙,带到了阿冯利村,安妮的敢于幻想使她与村民格格不入,她也因莽撞、冒失的性格吃尽了苦头,给自己和周围的人都带来了不大不小的麻烦,但与此同时,安妮学习刻苦,为人善良,待人真诚,这为她赢得了村民的好感与友谊。小说结尾,安妮已经成为一个精神独立、品学兼优的年轻女性,她凭借优异的成绩获得了艾弗里奖学金,本打算进入大学深造,家庭却横遭变故:艾比银行破产,马修和玛丽拉一辈子的积蓄付之东流,马修因此突发心脏病去世,玛丽拉不得已准备出售绿山墙农庄。于是安妮放弃了深造的机会,选择了阿冯利小学的教职,留在绿山墙农庄照顾年老多病的马丽拉。
除了主人公的成长历程,蒙哥马利对阿冯利村的描写,也带有自己从小生活的卡文迪许村,乃至整个爱德华王子岛的强烈印记。阿冯利的村民们大都善良淳朴、热情好客,他们虽然难以理解安妮的丰富想象力,但并没有排斥这个孤女,相反,他们欣赏安妮的真诚与聪慧,和她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每个阅读蒙哥马利的读者,都会了解到爱德华王子岛的邻里关系是多么亲密”[5],可以说,是爱德华王子岛的淳朴民风赋予了阿冯利村世外桃源般的气质。尽管安妮的成长历程不全是蒙哥马利的亲身经历,她在写作过程中却注入了最真诚的感情,正因如此安妮与马修、马丽拉兄妹的亲情,与戴安娜与吉尔伯特的友情才如此真挚动人。
因此,有学者直接指出,《安妮》写的就是蒙哥马利自己的童年故事[5],蒙哥马利将亲身经历融入小说情节,令小说具有自传色彩,也更显真实。蒙哥马利对安妮的成长描写是从安妮的日常生活中渗透出来的,这不同于18—19世纪传统男性成长小说的发展模式,但与19世纪后期美国女性成长小说不谋而合。
二、美国模式:日常生活的成长描绘
很多学者认为,成长小说遵循程式化的结构模式,即“幼稚→受挫→释怀→长大成人”,这是因为成长主人公大多处于青春期,在生理、心理或行为方式上具有类型化倾向,而且成长受挫是成长的必由之路[3]。早在20世纪70年代,杰罗姆·巴克利(Jerome Hamilton Buckley)就在专著《青春的季节:从狄更斯到戈尔丁的成长小说》提出了成长小说的经典模式:“一个敏感的孩子在乡村或小镇中长大,他发现家乡限制了自己自由发展的可能。他的家庭,尤其是父亲反对他的创造能力,压制他的野心……因而他在可能年龄还很小的时候,逃离家庭的压抑氛围,独自前往城市,在城里他真正接受了‘教育’,这种‘教育’不只关乎未来的职业发展,也涉及他的直接城市生活经验……经过痛苦的探索,他告别了青少年时代,走向成熟,这时他可能会返回家乡,宣布他的选择是正确的。”[4]
然而,这种模式更多见于以男性为主人公的成长小说中。由于与自然和宗教的关系严重受损,被疏远的社会弃儿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这是许多小说女性主人公的共同特征。诚然,成长小说的创始者们对表现问题、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以及主体性问题都很感兴趣,他们从审美和社会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因此女性成长小说常常改写甚至颠覆男性成长小说的经典模式[6]。“出走”是男性成长小说的关键词,也是男性主人公成长的必经之路,却成为许多成长中的女性角色渴望卻犹豫不决的事情。“一方面,她们渴望离开家庭,开始一种独立自主、自由自在的生活;另一方面,她们也深切眷恋甜蜜的女性友谊,渴望与舒适的女性关系圈融为一体”[7],通常,女性主人公们会选择家庭,放弃出走的想法。19世纪下半叶,美国出现了别具特色的书写日常生活的成长小说,成长主人公始终生活在平静、安详的日常生活中,这种平淡、安详的日常生活不动声色地让成长者感受到了成长的真谛,主人公在风平浪静中完成了成长,这样的成长书写看似平常,实乃更切近大多数成长主人公的成长状貌[3]。女作家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小妇人》、薇拉·凯瑟的《我的安东尼娅》都是其中的代表。
蒙哥马利也注重日常生活的成长书写。纵观安妮的成长过程,可以发现安妮从未有过于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也未曾起过出走的念头,她只是白天忙于学业,晚上回家后帮助玛丽拉做家务,或偶尔在周末和朋友们出门散步,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见到的最普通的女孩并无区别。安妮也与许多女孩一样,似乎永远都不能阻止自己犯错:做蛋糕不小心错把止痛药当成了香草精;赌气与同学打赌走房梁,结果从房梁上摔了下去;厌恶自己与生俱来的红发,渴望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却把头发误染成了绿色;错把葡萄酒当饮料,导致朋友戴安娜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幻想绿山墙外的森林闹鬼,结果走夜路穿过森林时胆战心惊,被想象中的鬼怪吓得魂飞魄散;与朋友贪图浪漫扮演丁尼森诗歌中的“百合少女”,躺在木船中顺水漂流,船却漏水了,安妮险些溺水,狼狈不堪……但安妮的教育和成长也是在这些啼笑皆非的错误中完成的,她不断吸取教训,克服了自己的种种缺点,最终成为令人喜爱的年轻女性。安妮自己的话也证明了这一点,险些溺水被救后,安妮对玛丽拉说:
“……since I came to Green Gables I’ve been making mistakes,and each mistake has helped to cure me of some great shortcoming……The Haunted Wood mistake cured me of letting my imagination run away with me. The liniment cake mistake cured me of carelessness in cooking. Dyeing my hair cured me of vanity. I never think about my hair and nose now—at least,very seldom. And today’s mistake is going to cure me of being too romantic……I feel quite sure that you will soon see a great improvement in me in this respect,Marilla.”[8]
(“自打我住进绿山墙,我就一直在犯错,但每个错误都帮助我改掉了一个大的缺点……“闹鬼的森林”治好了我沉溺幻想的毛病;止痛药蛋糕让我改掉了做饭时心不在焉的习惯;染发事件令我不再虚荣,我现在再也不在乎我的头发和鼻子了——至少,很少在乎;而经过今天这事,我不会再贪图浪漫了……我相信,你很快就会发现,我变得现实多了,玛丽拉。”)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曾经的英属殖民地,18—19世纪的加拿大文学缺少成长小说这一体裁。《安妮》在加拿大本土曾屡遭退稿,最后才被美国一家出版公司接受,这证明安妮的成长历程符合美国女性成长小说传统,可以说,《安妮》在内容和叙事结构上都对美国女性成长小说进行了一定继承,同时也是对传统离家出走、冒险漫游式的成长小说的发展。
三、忽视婚恋:背离传统的成长精神
女性很长一段时间一直男性的附属。歌德曾说:“妇女必须从小了解,她们生来就是为了服务的。”当妇女掌握了“写作”这一发声工具,她们开始将对性别平等的诉求诉诸笔端。女性成长小说常常包含女性主人公争取独立自由、反抗男权压迫的内容或主题:“她们是如何被迫学习看轻自己与同性,如何被男权社会否认个体身份,如何被迫接受男性强加的从属地位并且安于现状。”[6]然而,纵观欧美国家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女性成长小说,主人公的成长通常围绕爱情与婚姻进行[9]:女主人公的成长之路从寻找合适的伴侣开始,以婚姻结束。
19世纪的英国女性成长小说塑造了一批自强不息、独立自主的女性形象,但这些女性的自强与独立通常体现在她们对爱情和婚姻的追寻中,她们认为自己与男性——哪怕这名男性经济和社会地位都远远高于自己——是平等的,男主人公也为她们不卑不亢的姿态而倾心,最终两人是否喜结连理成为女性成长完成与否的标志。因此曾有学者用“灰姑娘模式”描述这一时期的英国女性成长小说,这些小说对灰姑娘的故事模仿的同时又有一定颠覆,“在这种既模仿又颠覆的过程中,作家赋予小说以新的内涵和意蕴,似乎昭示人们女性仅有婚姻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独立的人格和自尊、婚姻和自足才能构成幸福人生”[10]。夏洛蒂·勃朗特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提及了她对奥斯汀作品的不认同,认为奥斯汀格局较小,将“绅士淑女们”禁锢在一个高墙之中,然而她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作品实际上也是高墙中的绅士淑女的变奏,只是表面上,主人公摆脱了淑女的身份,走了一条全新的成长道路。美国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出现了以描写日常生活为特色的女性成长小说,这些小说大都也未走出恋爱和婚姻的成长路径。以薇拉·凯瑟《我的安东尼娅》为例,小说主要讲述了女主人公安东尼娅在农场上的奋斗故事,安东尼娅勇于挑战传统与权威,但她的自我价值与成长也是通过与理想伴侣组建家庭实现及完成的,被情人抛弃时,她也一度丢失了自我。
也许因为加拿大成长小说传统的缺失,《安妮》反而真正做到了另辟蹊径。小说围绕安妮的日常生活展开,着重描绘了安妮的学校生活与亲情、友情,对爱情与婚姻的追寻并未涉笔,这其中可能有主人公年龄相对较小的原因,但从安妮的朋友戴安娜初中毕业后被父母禁止去女王专修学校求学的事件便可知,当时的加拿大社会对待女性的态度依然是“房中的天使”,戴安娜的父母认为,女孩子不需要受到太好的教育,阻止了戴安娜继续发展的可能,戴安娜的成长道路从此被局限在了寻求理想伴侣与美满婚姻中,她的成长只能依靠争取成为“好房子中的天使”来完成了。
安妮则在女王专修学校继续求学,并通过不懈努力获得了艾弗里奖学金,取得了去雷德蒙德大学深造的资格,如果此时意外没有发生——艾比银行没有倒闭,马修与玛丽拉身体健康,绿山墙没有被卖的危险,安妮很可能成为阿冯利村第一位女大学生,她的女校长职业生涯将提前两年来临(蒙哥马利在共写了八部“安妮”系列小说,从系列第四本《风吹白杨的安妮》可知,安妮大学毕业后去了夏缘镇中学担任校长一职)。尽管安妮于家庭变故后选择了承担家庭责任,她依然没有走上以往女性主人公争取成为“好房子中的天使”的成长道路,而是接受了阿冯利小学的教职,乡村女教师,对阿冯利村民来说,是他们想象中一名女性的发展极限——邻居林德太太在得知安妮放弃深造机会后向她表示祝贺:“听到这个消息我真是太高兴了,你作为女人,受到的教育已经够多了。我才不相信一个姑娘与小伙子们一块上大学,脑子塞满拉丁文和希腊文之类的废话能有什么好处。”[8]需要指出的是,安妮并没有排斥恋爱和婚姻,相反,她写作爱情故事,也与朋友们分享过自己的理想型,所以安妮对婚恋的态度其实是顺其自然的:不排斥,也不刻意追寻。以往女性成长小说主人公大都将婚姻爱情看作成长的主旋律;而在安妮这里,婚姻爱情只是個人事业与发展的装饰音。可以说,安妮的成长过程体现了女性意识的真正觉醒,安妮已经具备了一些现代女性的特征。这是蒙哥马利对传统女性成长小说模式的一大突破。
四、结语
《绿山墙的安妮》是蒙哥马利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主人公安妮·雪莉的成长轨迹与蒙哥马利十分相似,小说自然而然地染上了自传色彩。日常书写是小说的另一特色,尽管平淡,蒙哥马利对安妮与阿冯利村的笔调饱含深情,这其中包含对童年的追忆、对家乡的热爱,以及对未来的期盼,安妮的成长也在日常生活中不露声色地完成了,这种模式与19世纪下半叶以《小妇人》为首的美国女性成长小说异曲同工。然而,蒙哥马利并没有局限于美国模式,而是抛弃了女性成长小说对爱情与婚姻的追寻的经典模式,使婚恋从女性成长的主旋律中退出,并用学习和工作取而代之。这是女性意识的真正觉醒,也是《安妮》对传统女性成长小说的模式的一大突破。因此,虽然安妮的成长过程较为顺遂且理想化,但安妮身上体现的现代女性特征令这部小说在众多女性成长小说中脱颖而出,在成长小说缺失的加拿大国土上开出了绚丽夺目的花朵。作为一部经典而独特的成长小说与女性主义小说,《安妮》不应该被轻视与遗忘,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的“安妮热”与近年来研究者对这部小说的关注更是证明了这一点。
参考文献:
[1]hmansson,Gabriella:A Life and Its Mirrors: A Feminist Reading of L. M. Montgomery’s Fiction Uppsala[J].Acta Universatis Upsaliensis,1991.
[2]韩加明.欧美文学论丛第十辑:成长小说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3]张国龙.成长小说概论[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
[4]Hamilton,B. J .:Season of Youth: The Bildungsroman from Dickens to Golden[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5]Heilbron,Alexandra:Remembering Lucy Maud Montgomery,The Dundurn Group Toronto,2001.
[6]Lazzaro-Weis,Carol:From Margins to Mainstream: Feminism and Fictional Modes in Italian Women’s Writing,1968-1990[M].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93.
[7]李贺青.《秀拉》:一场独特的人生实验——莫里森对女性成长小说的继承和发展[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59-67.
[8]Montgomery,L. M. :Anne of Green Gables,ICON Group International,Inc,2005.
[9]Abel,Elizabeth; Hirsch,Marianne; Langland,Elizabeth:The Voyage In: Fictions of Female Development[M].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1983.
[10]孙胜忠.一部独特的女性成长小说——论《简·爱》对童话的模仿与颠覆[J].外国文学评论,2009(2):49-59.
作者简介:卢星宇(1997-),女,安徽合肥,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加拿大文学。
3775501908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