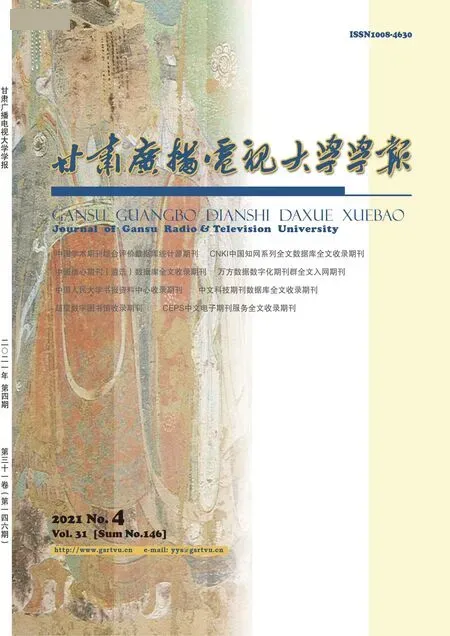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分配
——以第三人介入情形为视角
李 静,马雯雯
(甘肃政法大学 民商经济法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一、问题的提出
自《侵权责任法》第37条第2款规定了第三人介入情形下存有过错的安保义务人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以来,学界对于补充责任的性质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论证。而我国侵权法上规定的安保义务人对受害人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的前提是实施了直接侵权行为的第三人不明确或者第三人就受害人的损害因经济能力不足不能进行全面赔偿。但是如果作为第一顺位的第三人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承担受害人全部的损害责任份额时,侵权法却未赋予第三人就安保义务人过错范围内的责任份额享有追偿的权利。虽然法律的主要目的在于惩罚故意侵权的行为,但却造成侵权法上关于有损害结果时的过错赔偿和自己责任原则的弱化,也在法律层面削弱了安保义务人恪尽职守和积极履行义务的内在动机。同时,由于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所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存有《合同法》上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义务和《侵权责任法》上的法定义务的双重属性,导致补充责任和违约责任在法律适用效果上的断层。因此,本文主要从安全保障义务的性质和第三人与安保义务人责任分配的法效果困境方面进行分析,以期望为第三人与安保义务人在责任分配中提供可能途径。
二、侵权补充责任的性质认定
目前,关于安保义务人的补充责任无法纳入任何一种多数人侵权之债的传统形态[1]。学界对于补充责任的性质因认识角度的不同,并未就该责任的性质为何达成统一共识。张新宝认为,安保义务人承担的补充责任是在顺位和责任范围上负有法律限制的一种独立的责任形态[2]。杨立新和张民安则认为安保义务人的补充责任性质应归属于不真正连带责任[3]。关于安保义务补充责任的性质探析,本文主要是对补充责任与按份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进行对比分析进而得出对于安保义务补充责任的性质认定。
相较于传统责任形态的按份责任与不真正连带责任而言,《侵权责任法》规定的安保义务人的相应的补充责任有以下三方面的不同之处:一是安保义务人在责任承担范围上是一种与过错相对应的有限责任;二是安保义务人在责任承担顺位上是第二位的,受害人必须首先向直接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主张全部责任份额的赔偿权利,在第三人无法查明或者第三人就受害人所受损害无法进行全额赔偿时,受害人才得以向安保义务人主张相应的责任份额对自身损害进行弥补;三是安保义务人承担责任后是否享有对第三人的追偿权问题。《侵权责任法》关于安保义务人的追偿权未在法律条文中予以明确肯定。程啸在《侵权责任法》一书中认为安保义务人不应享有追偿权。理由在于:安保义务人既然负有保护服务领域内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法律义务,那么进入该领域的自然人也有合理理由期待安保义务人积极履行义务保护他们的权利不受外界侵犯。而安保义务人不履行义务的行为也是导致受害人损害结果产生的原因,就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4]。再者,既然安保义务人承担第二顺位的补充责任是在第三人不明确或者无足够经济能力对受害人进行全额赔偿的情况下,那么即使法律赋予安保义务人承担责任后向第三人追偿的权利,安保义务人对该部分责任份额向第三人追偿也无任何实现的可能。但《民法典(草案)》第1198条又明文规定了安保义务人在第三人不能承担的剩余责任范围内向受害人承担与其过错范围相应的赔偿责任,且对自己承担的该部分有向第三人追偿的权利即对受害人的损害赔偿由第三人作为最终责任人承担。因此,本文对于安保义务人补充责任的性质认定主要是从侵权人在承担责任上的顺位、责任范围和彼此之间的追偿权三个方面与按份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进行对比分析,以体现立法者在侵权法上设置补充责任的初衷即侵权人和受害人之间的价值衡平和权益保护。与补充责任相比,按份责任在侵权人角度是数个侵权人按照自身责任份额的大小向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且数个侵权人之间不享有追偿权。在受害人角度,受害人只能向各侵权人求偿与其责任大小相应的份额且受害人的求偿顺位不受任何限制。相比较而言,补充责任有顺位限制且作为第一顺位的第三人负有承担全部赔偿的义务。因此,不能将补充责任归入按份责任形态。与不真正连带责任相比,不真正连带责任在外部关系上,受害人可自由选择其中任何一位与其存有相应法律关系的责任人求偿自己所受损害的全部责任份额,任何一负有责任的人都有向受害人赔偿全部损害份额的义务。在内部关系上,因多个责任人与受害人之间产生责任的法律关系不同,受害人进行首次求偿的责任人不一定是最终责任人。因此,对受害人的损害结果未施加侵权行为的责任人承担责任后,可向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直接侵权人进行追偿,由直接侵权人承担终局责任。可见,不真正连带责任在求偿顺位和责任范围上与补充责任大不相同。本文认为对于补充责任的责任形态归属问题,应承认补充责任在《侵权责任法》上是有别于按份责任与不真正连带责任的独立责任形态。同时,应把握补充责任与按份责任在责任承担范围上的相似之处,为第三人与安保义务人之间在责任的分配上提供可能途径。
三、第三人与安保义务人责任分配的法效果困境
第三人介入安保义务人管控的风险范围实施侵权行为,而安保义务人未在安保义务范围内进行防范第三人侵权行为发生的侵权责任如何在第三人与安保义务人之间进行合理分配,一直是一个理论两难问题[5]。虽然《侵权责任法》第37条第2款对存有过错的安保义务人在责任承担上创造性地规定了补充责任的形态。但对于第三人和安保义务人的行为形态和主观过错并未进行明确区分。学界通说认为,只有在第三人故意实施作为的侵权行为与安保义务人的过失不作为行为结合导致受害人损害结果发生时,安保义务人的补充责任才有适用的余地。
(一)侵权补充责任的法效果困境
关于第三人与安保义务人的数人侵权补充责任分配形态,是我国侵权法领域责任承担形态的一大创新。补充责任在外部关系上,受害人就其所受损害必须首先向直接侵权的第三人主张全部的赔偿份额,在第三人无法确定或者在第三人经济能力有限的情形下无法就受害人的损害承担第一顺位的全部责任时,安保义务人在过错范围内向受害人承担自己责任即“相应的”补充责任。而在内部关系上,即第三人与安保义务人承担责任后的追偿权有无问题上是引发本文探讨侵权补充责任在适用上的法效果困境的关键。
按照《侵权责任法》的立法意志,可以将第三人与安保义务人之间的责任承担分为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受害人所受损害由作为第一顺位的第三人全额承担赔偿责任且即使在安保义务人有过错的情形下也不能就安保义务人应承担的责任份额向其追偿。此时,存有过失的安保义务人即安保义务人消极不作为的侵权行为对损害存有一定大小的作用力却不承担任何责任,是否造成侵权领域的二律背反值得深思[6]。另一方面,在第三人不明确或者无经济能力对受害人的损害进行全额赔偿的情况下,安保义务人只承担与其过错和作用力大小相应的责任份额。根据侵权法规定,安保义务人承担赔偿后对该部分份额不享有追偿的权利,导致直接侵权的第三人在安保义务人的赔偿份额范围内享有相应的消极利益。将意味着法律鼓励第三人尽可能地以各种手段隐匿、转移财产,迫使受害人向安保义务人进行求偿以逃避自身责任。此种情形下,安保义务人承担的补充责任更像是一种后顺位的按份责任,与《侵权责任法》惩罚故意侵权的立法理念背道而驰。然而,按照《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的立法意志,在第三人不能确定或者第三人无法就受害人的损害进行全额赔偿的情形下,安保义务人承担了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后,对该相应的赔偿份额有向第三人追偿的权利,也就意味着第三人对受害人的损害承担结果上的终局责任。有学者认为,承担补充责任的安保义务人只是对受害人损害的发生提供了一种消极的不作为行为,而第三人的故意侵权行为具有导致损害发生的全部原因力,让第三人承担全部份额的最终责任符合法律惩罚故意的立法理念[7]。因此,此情形下的补充责任更接近于一种受害人在求偿顺位和责任份额方面负有限制的不真正连带责任。综上可以看出,不论是在立法论角度还是解释论角度,安保义务人承担的补充责任在法律适用效果上均处于两难的困境[8]。
(二)侵权补充责任与合同违约责任的法效果冲突
安保义务人违反义务的责任承担问题同时规定在《侵权责任法》和《合同法》中,而《侵权责任法》中补充责任的存在使得《合同法》上关于安保义务人承担“无过错的违约责任”趋于缓和,也正是补充责任的存在使得安保义务人的责任承担在侵权领域和合同领域产生巨大的冲突[9]。《合同法》第60条还将合同当事人之间的附随义务法定化,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安保义务人在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承担上的竞合。在第三人的侵权行为造成安保义务人对受害人违约时,《合同法》第121条进一步加剧了安保义务人在《侵权责任法》和《合同法》上责任承担的法效果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安保义务人存有过错的补充责任和无过错的违约责任之间的冲突;二是安保义务人与过错对应的有限补充责任和无过错下的全部赔偿的违约责任之间的冲突;三是安保义务人承担第三人不明确或者第三人无力承担的剩余份额情形下的第二顺位责任,而在合同领域安保义务人是第一顺位的直接责任人。可见,假如法律赋予受害人在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之间进行自由选择的权利,受害人自然选择获取赔偿方式最简单、成本最小、对自己保障最有益的违约责任,从而截断了安保义务人通过对过错的有无或者原因力比例进行抗辩的机会,无形中强化了安保义务人责任的绝对化,使得补充责任在法律适用上的效果无从体现,势必也导致安保义务人补充责任的虚设。加之,《合同法》的私法性质不能就人身遭受损害的精神损害赔偿进行自由约定,《侵权责任法》也不能就对受害人的纯粹经济利益损失加以弥补,使得侵权补充责任与合同违约责任的法效果冲突愈加明显。
四、解决第三人与安保义务人责任分配的可能路径
受害人在公共场所遭受第三人侵权,如果在第三人实施直接侵权行为时安保义务人没有采取合理范围内的措施避免损害后果的发生或者扩大,第三人与安保义务人就受害人所受损害应如何在彼此之间分配,本文在坚持《侵权责任法》第37条第2款规定的基础上结合《合同法》相关规定,为第三人与安保义务人之间的责任分配提供以下两种可能的解决路径。
(一)无共同过错下数个侵权行为间接结合的按份责任
在第三人介入情形下的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事件中,在第三人与安保义务人责任承担的外部关系上,我国《侵权责任法》应坚持对安保义务人补充责任的规定,由直接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第一顺位的全部赔偿责任,就受害人在第三人处无法受偿的全部或者部分,安保义务人仅在自己责任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在内部关系上,《侵权责任法》应规定对于第三人承担完全部赔偿责任后,就超出其责任份额的部分有向安保义务人追偿的权利。理由如下:在行为形态方面,受害人的损害是由直接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导致的或者与安保义务人所管领域的公共场所固有风险相结合导致的,而安保义务人对此种固有风险负有侵权法上的防范义务[10]。在因果关系方面,受害人损害结果的发生是由第三人的侵权行为直接引发的,而安保义务人如果在其合理限度范围内进行一定作为的防范行为便可以防止全部损害的发生或者部分损害的扩大,但因其未履行该防范行为而未能防止或者阻断第三人的行为与受害人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使得损害结果最终得以发生。因此,受害人的损害是由第三人的直接作为行为和安保义务人的不作为的防范行为共同导致的。在主观过错方面,第三人与安保义务人在侵权事件发展进程中的任何阶段都不曾存有意思联络的行为,只是因各自侵权行为的偶然结合导致了同一损害结果的发生[11]。因此,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3条第2款之规定,直接侵权的第三人与安保义务人因各自行为间接结合造成同一损害后果,双方应在过错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范围内向受害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二)侵权补充责任与合同违约责任的体系化衔接
由于安保义务人的安全保障义务即可以来源于法律规定,也可以由安保合同的双方当事人进行约定,使得安保义务人的侵权补充责任和合同违约责任在法律适用效果上产生了冲突。因此,该部分在坚持第一路径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建议,以期望侵权补充责任与合同违约责任在法律适用上达到体系化的衔接。根据《侵权责任法》第37条第2款之规定,可将安保义务人在侵权补充责任与合同违约责任承担上的法律适用分为以下两种情形三个层次进行分析。第一种情形第一层次,直接侵权的第三人在第一顺位时就受害人的损害承担了全部的赔偿份额。此时,第三人有权就超过自己责任的份额向安保义务人追偿。这种情况下,由于第三人承担了全部的责任份额,受害人在侵权事件中所受的损害得到了全面赔偿,此时,安保义务人在责任承担上便不存在违约责任与补充责任适用上的竞合。第二种情形是作为第一顺位的第三人不明确或者第三人无法就受害人的损害进行全额赔偿时,则受害人只能向存有过错的、第二顺位的安保义务人进行求偿。此时,便出现安保义务人责任承担上的违约责任与补充责任适用上的竞合。在这种情形下可分为两个层次即总体上的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在第二层次中,安保义务人与受害人约定的违约责任份额高于法定的相应的补充责任份额时,则适用违约责任的规定。安保义务人承担违约责任后就超过其应承担的相应的补充责任份额的部分享有向第三人追偿的权利。第三层次是约定的违约责任份额与法定的补充责任份额相当的情况下,则适用法定的补充责任的规定且安保义务人承担责任后对该部分没有向第三人追偿的权利,从而体现出立法者在侵权法第37条第2款特殊的价值决断。针对现行《合同法》上规定的违约责任承担内容中不包括对人身造成损害时的精神损害赔偿和《侵权责任法》中侵权损害赔偿内容中不包括纯粹经济利益损失的规定,目前理论界对该问题已有相关研究,此后,完全有可能在各自的体系中进行相关规定,已达到法律适用的体系化衔接。
总之,无论是从侵权法角度出发增加第三人对安保义务人的追偿权,还是从侵权补充责任与合同违约责任的体系衔接来看,都是在尽量贯彻侵权过错赔偿和自己责任原则,以平衡第三人与安保义务人之间的责任分配,从而防止每个自然人的权利不受他人侵犯以及使已受侵犯的受害人的权利尽可能恢复到侵权行为发生前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