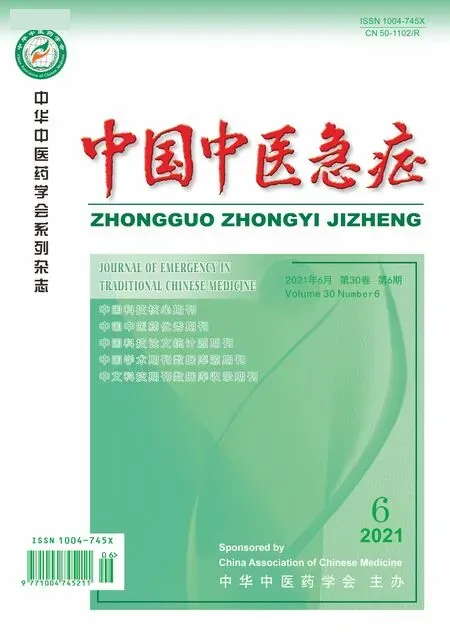王行宽教授“肝心同治”在心系疾病治疗中的应用∗
喻远霞 余桂枝 王宇红 张 稳 范建民△
(1.湖南中医药大学,湖南 长沙 410007;2.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湖南 长沙 410007)
王行宽教授为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级名中医,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第2、3、4、5、6批指导老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指导老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王老临证五十余载,学术渊博,医术精湛,尤其在治疗心系疾病方面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学术体系,名噪潇湘。王老推崇《名医杂著》“凡心脏得病,必先调其肝肾二脏,肾者心之鬼也,肝气通则心气和,肝气滞则心气乏,此心病先求于肝,清其源也”之说,倡导“肝心同治”心系疾病,效果甚验。笔者有幸跟师学习,受益匪浅,现将其经验介绍如下。
1 理论基础——肝气通则心气和,肝气滞则心气乏
肝木、心火二者为母子脏腑,息息相关,相辅相成。在经络循行上,足厥阴肝(少阳胆)经与手少阴心(厥阴心包)经及其络脉、经别、经筋在诸多部位有交互贯通,使得心与肝的关系愈加密切[1]。王师认为,对防治心系疾病来说,肝心同治法的理论基石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1.1 心、肝共主血脉 王师认为,心、肝共主血脉,两者协调则肝有所藏,心血充盈。《素问·痿论》载“心主身之血脉”,心气推动和调节血液循行于脉中,流注全身以濡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素问·调经论》云“肝藏血”,王师指出其意有二,一则如《读医随笔》所谓“肝藏血,非肝之体能藏血也,以其性敛故也”,肝木柔韧酸敛之性有藏血之功;一则如《素问·六节脏象论》载“肝者,罢极之本,以生血气”,肝禀春木升发之气有生血之能。故肝主藏血亦能生血。诚如王冰注《素问·五脏生成》云“肝藏血,心行之,人动则血运于诸经,人静则血归于肝藏。何者?肝主血海故也”。血藏于肝,布行于心肺,经血脉运行全身。故心赖肝血之滋养,若肝不生血,肝无所藏,则心无所主。“火非木不生,必循木以继之”(清·王孟英《归砚录》)即寓意于此。
此外,王师提出,肝木疏泄助心行血,两者互用则气血冲和,生化有序。《读医随笔》云“肝者,贯阴阳,统气血,居贞元之间,握升降之枢者也”。肝体阴而用阳,以血为本,以气为用,为气机升降之枢纽。《格致余论·阳有余阴不足论》亦云“司疏泄者肝也”。肝主疏泄有度,气机调畅,气行则血行,血行畅达,心脉通利,气血冲和,即《血证论·脏腑病机论》云“以肝属木,木气冲和条达,不致遏郁,则血脉通畅”;若肝主疏泄失司,气机郁滞,一则气不行血,血行瘀滞,加重心行血的负荷,可导致心气亏虚无力推动血液运行而形成气虚血滞,瘀血日久,津化成痰,痰瘀互结,痹阻心络,脉络不通,气血不荣,发为胸痹心痛、心悸;一则气郁化火,肝火上扰,心神失宁,发为心悸、不寐。《读医随笔》所谓“肝气舒,心气畅,血流通,筋条达,而正气不结,邪无所客矣”是其意也。
1.2 神、魂共主七情 王师认为,心、肝各司神魂,共主七情,以行情志。《素问·天元纪大论》中说,“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七情由五脏所化生,其中最主要的是与心、肝两脏密切相关。“心藏脉,脉舍神”(《灵枢·本神》),心为君主之官,主神志,主司精神、意识、思维和情志等心理活动,如《类经》云“心为五脏六腑之主,而总统魂魄,并赅意志。故忧动于心则肺应,思动于心则脾应,怒动于心则肝应,恐动于心则肾应,此所以五志唯心使也”“肝藏血,血舍魂”(《灵枢·本神》),肝为将军之官,主疏泄,性喜条达而恶抑郁,如“气血安和,万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七情之病,必由肝起”(《柳州医话》)。王师认为,肝藏之血与心主之血是神志活动的物质基础,由于心、肝两脏共主血脉,因此在神志方面,心藏之“神”和肝藏之“魂”也息息相通,相互依存,共同主宰情志活动。随着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重大转变,对心身疾病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精神心理因素在疾病的发生、发展、预后及转归方面有着特殊的作用。而大部分心系疾病包括胸痹心痛、心悸、不寐等系集躯体疾病、心理、社会因素“三维”一体的典型的心身疾病。肝通过司疏泄调畅气机,协助心调节情志活动,七情内伤多通过肝伤及于心。故王老提出诊治心系疾病,毋忘疏肝解郁更具现实临床意义。
2 临证经验——补益气营、疏肝解郁为基本大法
王行宽教授熟谙“肝气通则心气和,肝气滞则心气乏”之医训,同时遵从“损其心者,调其营卫”之说,提倡“肝心同治”心系疾病,确定了补益气营、疏肝解郁的基本治疗大法,并针对不同疾病的病机特点,分别佐以豁痰化瘀、清热化痰、安神定悸等法治之,方药可鉴。
2.1 胸痹心痛治法——补益气营,疏肝解郁,豁痰化瘀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心绞痛,中医称为“胸痹”“心痛”。传统中医认为其病因多为风寒湿等外邪内侵、饮食失调、情志失节、劳倦内伤和年迈体虚,治疗多从痰、瘀、热、虚等方面着手[2]。王师总结多年临证经验,提出本病基本病机为肝失疏泄,心气亏乏,肝心失调,血行瘀阻,痰瘀互结,心络痹阻[3]。王师临床发现胸痹心痛之疾多见于性情急躁之人,认为长期的情志不畅,尤其是郁怒失节,即肝失疏泄、条达失司在本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郁怒伤肝,肝气郁闭,疏泄失司,令肝气不得疏泄于心,引起心气亏乏,无力推动血液运行而致血脉不畅;再者肝气郁结,疏泄失司,气郁而血行不畅,日久瘀血乃成,津液外渗,化生痰浊,痰瘀互结,心络痹阻,不通则痛。临床症见胸中闷痛、胁肋胀满、善太息、郁郁寡欢或急躁易怒、脉弦等,且其病情每随情绪波动而变化。综上,王师认为,本病病位在心络,与肝密切相关。肝失疏泄、肝心失调是胸痹心痛发病及病情转机的关键。
《石室秘录·双治法》云“双治者,一经有疾,单治一经不足,而双治两经,始能奏效,故曰双治,如人病心痛,不可只治心痛,必须兼治肝……病心致痛,理宜治心,而今不治心者,何也?盖心气之伤,由于肝木之不足,补其肝而心君安其位矣”。基于以上医论及来源于实践中的认识,王师认为,心痛治心,乃辨证之常,心痛治肝,乃治法之变,即言心痛不唯独治心,必须兼以治肝[4]。
据此,王师自创心痛灵系列(Ⅰ、Ⅱ、Ⅲ号方)肝心同治,以补益气营,疏肝解郁,豁痰化瘀为法用治胸痹心痛。心痛灵Ⅲ号方以Ⅱ号原方合小陷胸汤而成,药物组成包括白参、柴胡、郁金、川芎、丹参、白芥子、九香虫、川连、瓜蒌皮、法半夏。方中郁金、柴胡疏肝行气解郁,使肝气通则心气和;丹参活血通心络,配伍柴胡疏解肝木,一以治肝,一以治心;一疏透和解,一入营理血,相辅相成,而能协理肝心失调之机。新添之小陷胸汤乃仲景经方,寒温并用,苦降辛通,既起清热豁痰之功,又具疏肝解郁之效。全方通补兼施,标本兼顾,在临床与实验研究中均已被证实有较好的疗效[5]。此外,王师临证发现胸痹心痛之疾常伴颈项不适,指出此多由督脉病变所致,与肝心失调密切相关[6]。《灵枢·经脉》载督脉与肝脉“会于巅”,得肝气以为用;《素问·骨空论》又言其脉“上贯心入喉”,与心气相通。若肝气偾郁,疏泄失度和(或)心络瘀阻,脉气亏乏,必致督脉经气不利,故循“实则泻其子”之旨,立疏通督脉之法,每用葛根除项颈胀痛,兼佐治肝心。
2.2 心悸治法——补益气营,疏肝利胆,佐以安神定悸 王师认为,心悸病位在心,责之于肝胆。肝胆同司疏泄,有助于心行血正常。肝为心之母,怒气伤肝,肝失疏泄,一则导致心血运行不畅,心神失养;一则气郁化火,上扰心神;胆气内通于心,惊气入胆,胆气不宁,心气为之不足,故心无所主,神明不安而怔忡惊悸之证发生。诚如虞抟所谓“夫惊悸怔忡之候,或因怒气伤肝,或因惊气入胆,母能令子虚,因而心血为之不足,又或遇事烦冗,思想无穷,则心君亦为之不安。故神明不安,而怔忡惊悸之证作矣”。心之气营亏虚,肝胆失疏,胆气虚怯为心悸发生的重要病机。这类患者发病往往由情志因素引起,西医检查多无器质性病变,以围绝经期妇女多见,临床可见心悸不安,善惊易恐,夜寐多梦易惊醒等。
据此,王师创制宁心定悸汤以补益气营,疏肝利胆,宁心定悸。方由生脉散和柴芩温胆汤化裁而成,药物组成包括白参、麦冬、五味子、柴胡、黄芩、枳实、竹茹、茯苓、法半夏、瓜蒌、丹参、郁金、炙远志、紫石英、炙甘草。王老遵循《难经·十四难》“损其心者,调其营卫”之训并结合自身多年临证经验,在治疗心系疾病气营不足证时多用生脉散,取其大补心气,兼滋心营之效。和柴芩温胆汤既可化痰清胆和胃,又可疏肝宁心,有肝胆并治,一举两得之功。其中妙在一味瓜蒌,诚如《重庆堂随笔》曰“瓜蒌实,润燥开结,荡热涤痰,夫人知之;而不知其疏肝郁,润肝燥,平肝逆,缓肝急之功有独擅也”。王老视瓜蒌为肝心同治的首选药物,祛痰之外更含从肝治心之意[7]。临证按此加减,肝气郁结甚者,加强疏肝解郁以行气血,治之以刚;心肝阴虚甚者,柔肝养心以养阴血,治之以柔。以此从肝治心,从胆治悸,至肝获疏泄,胆得通降,刚柔相济,气血调和,方能心气渐复,心神渐守,心悸得止。此外,王师在诊治过程中亦重视对患者精神情志的调适,积极与患者进行沟通,尊重患者的主观感受,倾听患者的苦闷,开导患者以放松心情。如此身心同调,才能更快地帮助患者改善症状,趋向健康。
2.3 失眠治法——安神,静魂,定魄 王师认为,人之睡眠由神、魂、魄之三维体系所筑。魂为肝之所藏,肝所藏之血是保证肝魂内藏的物质基础。不寐的发生虽为神之主,亦与肝所藏之魂和肺所藏之魄密切相关。周声溢曰“肝主睡,主眠”。因肝为魂之所,居血之藏,主知觉,主升,能除秽。昼则脑神统魂,以行知觉之功;夜卧则血归于肝。“人之魂,藏于夜”,知觉功能内收,故肝主睡眠。入寐艰难,寐不深沉且伴噩梦纷纭,辗转易醒,此为肝魂浮游在外之变也。诚如《血证论》云“肝病不寐者,肝藏魂,人寤则魂游于目,寐则魂返于肝,若阳浮于外,魂不入肝,则不寐”。临床症见夜寐艰难,辗转反侧,心烦易躁,坐卧不宁,口干口苦等。
因此,王师认为不寐本肝、心、肺三脏之病,神、魂、魄三维失调,提出应多脏调燮,综合治理本病,着重从心、肝、肺三脏入手,一以安神,一以静魂,一以定魄,以百合安神汤主之[8]。百合安神汤乃王老治疗不寐之验方,方由百合地黄汤、柴芩温胆汤、酸枣仁汤增减而成,以益气阴,养心肺,疏肝胆,清痰热,安定神魂。王老用药讲究药物配伍,柴芩温胆汤中柴胡、黄芩相配,疏清同用,其中柴胡味苦性寒,轻清升散,疏肝解郁,解表和里且善升举阳气;黄芩善清肝胆气分之热,又可燥湿泻火解毒。两药同用,一升清阳,一降浊阴;一疏透和解,一清解而降,从而升不助热,降不郁遏,相辅相成,而能调肝胆之枢机,理肝胆之阴阳。肝为乙木,内寄阳魂,肝木得疏,法中肯綮,阳魂潜降,得以安眠。
3 验案举隅
患某,女性,63岁,2019年8月8日初诊。阵发性心前区憋闷2年,加重半年余。心前区憋闷不定时发作,劳累时症状明显加重,动则气短。头晕昏沉,目眩,无耳鸣,颈胀痛,夜寐尚谧,纳食一般,口干稍苦,大便日解1次,成形,小便可。舌淡暗红,苔薄黄,脉弦细。冠脉造影(2018年5月24日,外院):冠状动脉多处严重狭窄。BP 162/90 mmHg(1 mmHg≈0.133 kPa);心电图:T波多导联地平、倒置。西医诊断:1)冠心病;2)原发性高血压病。中医诊断:胸痹,风眩;肝胆失疏,肝阳上亢,肝心失调,心气营不足,心络不畅,痰瘀胶着。治以平肝利胆、益气养营、豁痰化瘀、肝心并治。处方:心痛灵Ⅲ号加减。具体药物:白参10 g,麦冬15 g,五味子5 g,柴胡10 g,法半夏10 g,川黄连5 g,瓜蒌皮10 g,丹参10 g,天麻10 g,钩藤5 g,蒺藜10 g,石决明 20 g,姜黄10 g,葛根20 g,炙甘草3 g。14剂,水煎服,每日1剂,早晚分2次温服。嘱调畅情志,作息规律,适度运动。二诊(2019年8月22日)。诉前方药后症状均获改善。舌淡暗红,苔薄黄,脉弦细。BP 142/86 mmHg。心络获通畅之势,肝阳已获平潜,原法既中肯綮,不必更弦易辙,守方加减肝心同治。处方:白参10 g,麦冬15 g,五味子5 g,当归10 g,白芍10 g,柴胡10 g,法半夏10 g,川黄连5 g,瓜蒌皮10 g,丹参10 g,天麻10 g,郁金10 g,葛根20 g。14剂,水煎服,日1剂,早晚分两次温服。药后胸闷气短均明显改善。
按语:患者为老年妇女,阵发性心前区憋闷2年,加重半年余。冠脉造影示冠状动脉多处严重狭窄。西医明确诊断为冠心病,归属中医学“胸痹”范畴。心主行血有赖于肝的正常疏泄,肝失疏泄,气机郁滞,致使血瘀、津停、痰浊内生;肝气横逆犯脾,致使脾失健运,可聚湿生痰;肝气郁滞化火,煎熬津液,亦可灼津成痰。心气亏虚,肝失疏泄,心络瘀阻发为本病;肝肾阴亏,肝阳上亢故见风眩之证。针对病机,处以心痛灵Ⅲ号加减补益气营,疏肝解郁,豁痰化瘀,加减滋生青阳汤滋阴平肝潜阳。二诊时,肝阳已获潜降,故去钩藤、石决明等。依此治疗后患者胸闷大减,生活质量明显改善。
——琐忆王富仁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