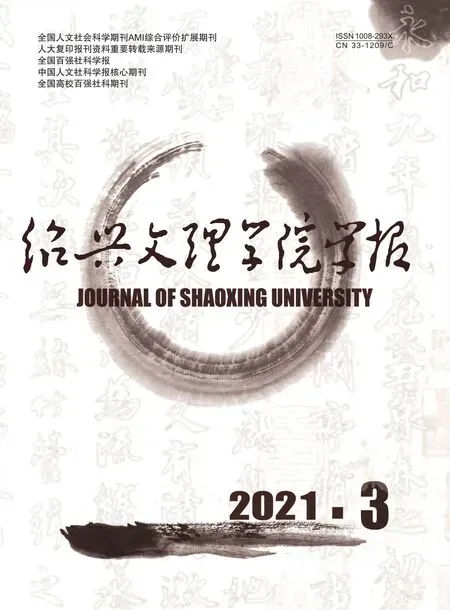影像的时间纵深
——德勒兹时间—影像理论与电影创作之关联
沈钰扉
(清华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 100084)
麦基在《故事》的序言中写道:“我对你们的希望已经超越了能力和技巧。我渴望看到伟大的影片。”[1]序言在他看来,故事的核心是内容与形式的融合,卓越的作者之所以出类拔萃,正是因为“他们选择了别人没有选择的内容,设计了别人没有设计的形式,并将二者融合为一种他所独有的风格”[1]序言,《故事》一书的写作宗旨更是“为了加强你(即创作者)对这门手艺的掌握,解开你的束缚,让你能够表达对生活的原创看法,提高你的才能以超越陈规俗套,创造出具有独特材质、结构和风格的电影”[1]序言。
“手艺能将天才推向极致”[1]序言,在麦基看来,这种能力来自“天才”。然而,克服了创作的技术问题,并不能确保一部作品达到艺术的高度。技艺精巧而其质平平的影片不在少数,因此另有一种力量决定着电影的优秀抑或平庸。排除一切外在因素,手艺决定着影片的下限,而真正伟大的作品并不取决于精巧的叙事结构或是花哨的画面表现,其从混沌现实中凝练真实,并让真实以震撼人视听的形式喷薄而出的能力才是关键。
“天才”“灵感”之类的概念本就带有一定超验的神秘色彩,我们只能设法在技艺上追赶而无法在“灵韵”上企及。伟大的作品往往会给予观众扣人心弦的震撼力,它们是如何做到的?为此类问题寻求“终极答案”或许并不现实,但不妨发掘一个便于理解的“切入点”:时间。人们在追逐技艺、仰望天赋时,往往忽视了作品的时间维度。这并非我们惯常理解的可被计算的时间(如一小时、九点五十分,在文学中还会体现为叙事时间、故事时间等),而是一种我们存在其中却时常忽视、突破人们惯常理解的纯粹时间。关于这一点,柏格森与德勒兹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部分的答案。
一、影像中的真假时间
感知,只涉及当下的知觉,只要我们睁开眼,便可看清周围的环境;伸出手,则能感知物体的质地。我们何以感受时间之流?答案是运动。太阳东升西落、钟摆匀速摆动、人自出生至老去,我们能在事物的运动中把握到时间的流逝。但这种说法仍不准确,因为我们对运动的理解大多并不连贯(1)人们对运动的感知是连贯的,一如人们对时间的感知。而一旦涉及对二者的描述,就像用符号描述现象一般,其连贯性便被打破了。,位置变化替代了实际的运动(如日出、日中、日落),这样一来,我们用运动感受时间,又用空间变化认识运动——极端地说,我们在利用“当下瞬间”把握时间。
假设一个场景。角色A出尔反尔,角色B对他说:“你过去做出的承诺,现在却没有兑现,将来我不会再信任你了。”如果按经典叙事逻辑粗略用三个电影镜头表现,则呈现为“A做出了承诺”“A不信守承诺”“B不信任A”。不难发现,尽管三个镜头间可能具有相当长的时间跨度,但每个镜头都仅包含着一个“当下”的动作(这个当下可以发生在过去、现在或是将来)。正如之前形容的生老病死,我们也习惯于用一个个具有代表性的瞬间(婴儿期、青年期、中年期、老年期)表达时光的飞逝。
在电影中,连续性剪辑、蒙太奇效果(2)在此笔者并未采用“蒙太奇技术”的说法,而泛指使画面产生运动、变化、冲突的效果,而非简单的镜头组接。在很大程度上承担起制造“运动”、构建时间的职责。镜头间时空转换过程遭到省略而我们能通过事物变化感知其连续性——更多是时间的连续。由于抓取的是一个个不连贯的时间点,因而我们只能在运动中发现时间(想象中的连贯时间),也就是说,在视觉化呈现的事物的差异对比中,我们感受到了时间的流淌——时间是运动的派生物。但在德勒兹看来,“我们不能感知整个事物或者全部画面,我们的感知总是不全面的,我们只能根据我们的经济利益、意识形态信仰和心理需求感知与我们有关的或者引起我们兴趣的部分。因此,我们通常只能感知底片”[2]31。我们感受到的并非真正的时间。人类在运动中把握时间,运动便依据需求而被分割、筛选、重组。在一个个相对“静止”瞬间的组接中,人们把时间体会为一种线性的、倏忽而逝的流动体,就像大多数影片中的镜头,飞速闪过,用之即弃。
然而依柏格森与德勒兹的说法,运动是一种无法分割的经过性行为,这是因为运动本身包含了运动物体经过的空间以及经过空间的动作,我们分割前者以构建匀质而线性的时间,却忽视了无法分割的后者——于真正时间中生成的连续的动作。在《时间与自由意志》中柏格森提到:“倘若我们把时间解释为一种媒介并在其中区别东西和计算东西,则时间不是旁的而只是空间而已。”[3]柏格森揭示出,“真正的时间”(或曰“纯粹时间”)是“绵延”——一种非时序性的异质时间,运动、影像乃至世界万物都于绵延中生成。绵延,顾名思义,作为一个动态、不可分割的过程,时刻融合着过去与现在。德勒兹将柏格森的时间理论概述为“过去与它曾是的现在并存;过去作为一般过去被保存下来;时间在每一刻被分为现在与过去,即过去的现在和保存的过去”[2]129。真正的时间是异质性的、非时序的时间,现在不断成为过去,被保存的过去又如同绵延的山脉、流水,共存而不可分割,不断与现在交流,循环往复、不舍昼夜。为此,柏格森在《材料与记忆》中建立了著名的有关记忆的“倒锥”模型,我们也可把它理解为有关时间的模型(如图1)(3)在这个模型中,SAB锥体代表我们的全部回忆,S点表示现实现在,也是最大程度缩小的过去,由S展开的平面是我们当下接触的世界,平面AB、A’B’则代表着不同的时面。随着时间的推进,S点会无休止地向下移动,锥体的体积也随之越来越大。在对过去进行回忆的时候,我们会从S点跳回到这些截面,现实与潜在得以交融,AB则会下降到一个新的S’点,即一个新的现在。见昂利·柏格森《材料与记忆》,肖聿译,华夏出版社,1998年,144页。。德勒兹解释说,它揭示了非时序时间的特征,即“一般过去的先在性,所有过去时面的并存性,最大程度缩小点的存在”[2]155。简言之,真正的时间不会“流逝”,过去会继续与当下并存,当下也就包含着过去。

图1 柏格森记忆倒锥模型
根据柏格森有关时间的锥体模型,我们发现真正的时间应在一种现实与过去的循环中得以显现(由现实现在跳回过去,再由过去跳至一个新的现实现在,无限往复)。这种过去作为现实现在的潜在面,代表着我们的纯粹回忆,它记录着我们生活中的全部事件(自然包括不可回忆的东西),储存在无意识里、绵延中,一旦受到意识的召唤,就会从混沌中现身,下降至接近S点,形成一个新的现实。
二、时间—影像的界定
从柏格森绵延时间的观点来看,电影内容同样生成于真实时间而非惯常理解的空间化的时间。然而,我们在多数电影中看到的,仍是依需求而分割的运动、人为建构的时间,那么真正的时间又在哪里?
为发掘影像中的异质性时间,德勒兹提出了“时间—影像”的概念。时间—影像,一言蔽之,就是展现异质性时间真相的影像。进一步阐释,就要求我们对其“时间”与“影像”作一定的了解。
如上文所说,异质性时间,即是一种当下与过去、现实与潜在的循环——要注意这里的过去、潜在不是我们回想或感知到的东西,能够回想到的只是过去、潜在的现实化产物,而这种由回忆等机制产生的现实影像已然与现实现在产生了联系。真正的过去与潜在无法被现实化,它们更像是回忆的邀请者。
影像,在柏格森与德勒兹构建的语境下已不再仅仅指涉影片中的活动图像,它不是客体的附庸(现实的幻觉)抑或主体创造的表意之物,而是具有本体地位的、一切能够为我们感知并储存于记忆中的影像——就电影而言,光线是影像、场景是影像、声音是影像,人物同样是影像。虽然柏格森对于“电影式思维”所体现的时间概念不无悲观(4)柏格森在《创造进化论》(2013年)中认为,电影将真正的运动变为了一种简单化的抽象运动(正像人们根据经济原则感知事物一样),而时间在这种运动中只呈现为一个瞬间,并非绵延的时间之流。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又无法解决,电影展现的只是一个虚假的世界。,但德勒兹拓展了视野,将影像视作世界的“活动切片”。世界就是一部无限宏大的“元电影”,由胶片放映带来的帧间等时运动(任意瞬间)恰恰就是世界绵延的最佳模型。
这种对于时间与影像的独特观点与我们的惯常理解大相径庭,毕竟我们在大多主流电影之中并不能直接感知这种影像的存在。黑泽明执导的电影《罗生门》(罗生门,1950)中,武士金泽武弘的被杀将一群证人聚集了起来,各人心怀鬼胎,在一系列主观闪回镜头中回忆着事件的经过,竭力维护着自己,致使证词各不相同,产生了相异甚远的一系列“真相”。当然,《罗生门》中的真相始终无法现身,就连作为事件旁观者的樵夫也因其欲望为“真相”笼罩上一团疑云。如果跳脱出具体的闪回镜头,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回忆并非推进动作的手段,甚至可以说,《罗生门》整部影片就是建构在一系列的回忆之上。这些回忆是同一事件、同一情境的变体与重复,人物一遍遍地跳回到过去,最终又不约而同地汇聚到当下——对武士之死真相的追询。在德勒兹看来,单纯由回忆—影像(5)回忆—影像可被粗浅地理解为将记忆现时化、现实化的影像——显然这种产物并不与纯粹的记忆等同。德勒兹将时间—影像按时间循环的大小划分成回忆—影像、梦幻—影像、世界—影像与晶体—影像,但这并非本文探讨的重点,笔者在此也不作赘述。构成的心理记忆不能成为电影,“电影或者是产生于现实现在之中和回忆—影像形成之前的回想尝试,或者是对这些回忆—影像最终出现的过去时面的探索”[2]171,《罗生门》影片本身得以成立,并能给予观众以情感的冲击,不在于对回忆—影像的安排,而在于将他们汇聚于一个被压缩的现实现在,在于他们的并存揭示出真正时间的侧影。我们难以从镜头或情境中发觉异质性时间的存在(因为《罗生门》中展现的大多仍是分切的运动、空间化的时间),因而不如放宽视角,纵览全片,《罗生门》所揭露的,正是纯粹过去的不可呈现。证人的众口异词,无论是谎言还是他们业已相信的事实,都不过是那个纯粹过去的变体,在当下——武士之死——的询唤下扭曲、变形。德勒兹说道:“逝去的回忆仍能在某一影像中复现,但这个影像不再具有可用性,因为产生回想的现在已失去了影像的原始延伸。一个回忆根本不能复现在影像中,尽管它存在于过去的时区中,现实现在已不能再遇到它。”[2]174尽管“过去”在《罗生门》中被一遍遍地复现出来,但那终究是现实化的回忆,我们相信每个人的口中都有一部分的真相,但失去参照点的观众已难辨真假。对观众来说,每一段回忆都是现实与潜在的融合,我们看似已经接近纯粹的过去,但又被下一段回忆中断——它永远不可能被触及。《罗生门》的剪辑手段大多虽属传统剪辑,但放眼其整体架构,它已不是在分切运动基础上产生的时间的间接影像,“而是在直接时间—影像中组合并存性的秩序或无时序的关系”[2]175。
因而欲发掘时间—影像,就必须摆脱将影像视为活动图像的惯式思维。但这种影像究竟有何特殊之处,以致要将其从影像的整体中分划出来?它对于一部电影的意义为何?这是我们将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三、时间—影像的表现作用
回顾一下那些能够带给我们情感震颤的影片就会发现,震撼我们的往往不是对故事的交代、对事物情境的再现(在主流电影中,这通常是影片的主体,却还不是决定其优劣的关键),而如果一部影片完全建基于这些,那它基本与我们心目中的艺术佳作无缘。就拿动作片的高潮部分举例,这本是命运降临的时刻,若影片单纯将它处理为打斗—胜出,哪怕场面再过宏大壮观,观众也只会认为这是个不错的画面、庸俗动作片中的“高个儿”。再看战争场面,让观众热血沸腾、使影像富于张力的,是将帅鼓舞士气的战前动员、是两军冲锋时的义无反顾、是士兵纯粹的情感、是对死亡的恐惧或征服,而一旦厮杀起来,这种感觉就消失了(例如影片会在交战前使用音乐,短兵相接的时候换用环境音)。优秀的战争场面会着力于表现,而非叙述,像《指环王》(TheLordoftheRings,2001—2003)中放慢的冲锋镜头、《天国王朝》(KingdomofHeaven,2005)中如飞蝗般的箭矢、《血战钢锯岭》(HacksawRidge,2016)中道斯的勇敢,这显然无法仅凭逻辑性的叙述概括。一部优秀作品的优秀之处绝非逻辑的自洽,而是其“表现”的能量。
如果创作者们一味地依赖分切的运动去构建空间化时间,那么他们很难摆脱“再现”(representation)的桎梏。倘若就以“某人的一生”为题去拍摄一部故事片,而作者将其处理为每隔一段时间对主角生活的记录(这就类似于用婴儿期、青年期、中年期、老年期来描述人的一生),那整部电影就彻底沦为对“某人的一生”的再现。“再现就是假定了在艺术行为之前已经有一个存在着的既定的东西,艺术只是摹仿=拷贝这个东西,而且永远是一种不完全的拷贝”[4],若一部影片仅存“再现”,那它无非就是对现实的临摹,哪怕赋予其逻辑性的建构,仍无法掩盖意义与情感的缺失。尽管此例实属极端,但在多数平庸的作品中,对再现的狂热崇拜压倒了一切,因而造成影像可思性、感染力的匮乏。影片需要“表现”(expression)——正如让·米特里于《电影美学与心理学》中说“一切艺术都是创造和阐释”,单纯的摹仿难以使电影成为艺术。“表现是一种彻底的一元论的思想,一种野生的、原初的力量,其所衍生的林林总总乃是它的形态、它的样式”[5],表现赋予影像以生命力,使其脱胎于现实而为真实,影片也只有在表现中,在给予观众以情感的震颤时,方能及至艺术的高度。
在德勒兹眼中,时间—影像就是表现,这种表现来源于影像时间的纵深。再现是对一个确定事物作确定性的描述,表现则不然,当我们用时间—影像的概念去解读电影,往往不会得到一个最终结论——相反,我们只能以问题收场。这是因为时间无法传授“信仰”,而只表现出“可能”。我们在时间—影像中看到的就是分解的时间(现实现在与纯粹过去)。拥有自主性的事物在时间分解的循环中不断生成、变化,形成一个新的整体,每一处细微的改变都有可能导致结局的天壤之别。时间—影像的特性——真实与潜在、现在与过往的无限循环——表明了它是一种可思的影像,它旨在表现,而不是为表现下定论。当一切皆有可能,一切就会激发起观众的思维,这就大大弥补了再现的影像中思想的匮乏。可以说,时间—影像之优势不在于呈现出真正的时间,而在于展现现实的混沌,在于将现实的决定权交还给时间,它重在表现“可能性”迸发的思想会丰满其血肉,直接展现出时间生成的权力。简言之,“再现”关注的是事物的现实一面,并试图描述“世界是什么”;而“表现”则展示出现实与潜在的交流与循环,呈现出“世界可能是什么”。
四、时间—影像的运用
事实上,当我们试图将时间—影像带入创作时,就已经违背了德勒兹划分影像的意图。德勒兹从未将电影视为一种创造、排列影像的艺术(即影像不是人造的表意之物),他将影像视作世界中自在的存在,世界作为影像的集合就是电影,电影就是世界的呈现。因此,“德勒兹并不是真正在讲电影艺术,他的关于影像的两卷本著作是某种自然哲学,把电影式影像当成是发光物质的事件和装配”[6]6。德勒兹将自主的影像与电影结合,本就构成了虚构与现实的悖论,对物质意识二元论分立的弥合终究无法抹平主观意图与现实世界的裂隙。在当下电影中,往往存在多种影像的结合、抽象与真实时间的混杂,无论过度迷信哪种看法都有以偏概全之嫌。因而我们可以在德勒兹影像本体论与影像幻觉论之间取折中的观点,在虚构之上赋予影像本体地位,不仅能看清当下影片的建构方式,还能为今后的影片创作提供一部分理论化的方法。
我们可以在德勒兹对时间—影像的阐释中体会出一种电影美学的理念——对蒙太奇建构的中心的破除、对现实的邀约。但此中心对于采纳经典叙事影片的重要性已无须赘言——此类影片更是当下电影中的主流,其重要地位不可忽视。因而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指明另一条道路:在幻觉层面(再现)上对表现加以应用,从而在不打破影片叙事逻辑的前提下赋予影片一种情感与思维的深度。
“对时间—影像的运用”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创作者并非要将这种影像安插至电影之中,时间—影像本身即是影片得以实现的前提。电影创作首先涉及虚构,但创作中的取景、拍摄、剪辑并非作者最初的目标,需要他们优先考虑的,是以虚构为基础的时间呈现,即时间—影像的构建。如此说来,几乎任何影片都无法摆脱时间—影像(只是对时间—影像的呈现有显隐之别),也难怪朗西埃说:“我们宁愿得出这样的结论:运动—影像与时间—影像,并不意味着对应于两个电影时代的两种对立的影像类别,而是关于影像的两种不同看法。”[6]8
使影像展现出异质性的时间真相需要一个前提,即事物本身的“历史性”——时间纵深。这种“历史性”同样介于虚构与现实之间,就像历史小说中的人物或许可以虚构,但背景真实存在;科幻、魔幻影片即使背景完全架空,其中也会留有为大众认可的行为准则。此外,“历史”不是我们惯常理解的过去发生过的事件,而是与现实影像共存的潜在。人会经历婴儿期、少年期、中年期、老年期,但这些时期不会成为流逝的过去,它们共同构成了现实中的人。
在创作中,“历史性”的设定首先体现在影像的构建之中,这种构建又直接显现为影像的时间填充,其中包含独一无二的情境、物品、人物等要素,是赋予影像时间循环可能的关键性步骤,处理不当就极易导致几者间的离散。人物难以融入情境、情境又脱离事件……如果影像各自为政,处于相互平行的平面之上,哪怕它们拥有逻辑上的联系,也难免让观众费解,成为拼凑时长的工具(在一部律政剧中加入恋爱情节并不违背逻辑,但如果因此导致题材的混乱,影像历史关系的模糊就使得人物、情境脱离了律政的框架)。作者在构思创意之初便要给予影像足够的“历史”,各影像的历史间则是千丝万缕的联系。以《绿皮书》(GreenBook,2018)中的人物为例,托尼身为白人却处于社会的底层、唐优雅体面但因其黑人身份备受歧视,他们背景的互补为其相遇、携手奠定了基础,身份、性格的设定缺一不可。这即是他们成为时间—影像的潜质:托尼与唐可以在对方身上发掘自己的潜在,这种潜在不需要来自对方,一人只是另一人潜在的邀请者。在虚构中更进一步的还有经典动画《猫和老鼠》,难道还有比“瘦小而机智的老鼠与强悍却愚笨的猫”更为精妙的设定吗?他们并非正邪对立的双方,物种的相克即决定了其永无止境的博弈宿命;他们又不可失去彼此,只有在斗智斗勇中他们才能相互成全、实现自己的意义。有关情境的创意同理,在故事中没有无根据的场景,更没有无起因的结果(公路片也不例外),每个情境乃至事件都有其历史的景深,不用将其完全展示于画面之上,因为潜在永远伴随现实左右。
可以将影像的时间构建视为创意的过程,这涉及笔者对于创作灵感的一种解释,一种有关真正时间的思考(与弗洛伊德潜意识理论相似,但更关注时间而非心理):创作者的灵感常常来自日常生活中一个不起眼的情境,这种看似寻常的感知一瞬间唤醒了作者的回忆(潜意识、与当下共存的纯粹过去、锥体的AB面),现实与过去联通了起来,一个平庸之物就在一瞬间获得其全部循环。任何人的回忆都不尽相同,一个灵感正源自作者当下的感知与其独一无二的过去的联合。这种基于灵感的创意将直接体现在影像之中,而赋予影像一种时间的纵深。这就是作者设置影像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因其“历史”专利(显然所有人的过去各不相同)而成为他人不可逾越的壁垒;它又符合时间的生成,诞生于对现实的感知之中,与其过去并存。事实上在作者构思影像之初,现实化的影像就已经开始对潜在发起邀请,进而显现为时间—影像,作者能否把握住这种潜在,能否将其投入到现实化的努力当中(再举律政剧的例子,把握潜在即作者不可放弃律政的背景及人物的身份,现实化努力则可以是人物职业对其生活的影响、潜在人物性格对其行动的干扰等),才是构建时间—影像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
然而异质性的时间并不会时时呈现于影片之中——尽管它无处不在——因而影像大多也不会以一种时间—影像的姿态贯穿影片始终。从经验上看,主流电影中的时间—影像往往现身于行动的断裂处、情感与思维的迸发处——以一种比较传统的段落划分法来看,出现在高潮部分。虽然影像会在影片中显现出分解的时间,但不要忘记影像仍要服从于机械或是人为的选择。经典的电影叙事往往会抑制历史影像的时间呈现,因为拥有丰富过去的人物不能永远困于过去,他们要在叙事的逻辑中继续行动,延宕其潜在(过去)的现身,这就说明时间—影像的设置还未结束,将时间填充进影像只是赋予惰性影像重新显示时间的权利。现代主义影片往往会将此权利悉数返还给影像:人物就是这样的人物、情境自始都是这样的情境。他们全部的过去糅合在一起,表现压倒了叙事(如费里尼的《八部半》);主流影片则会以“按揭”的形式逐步归还影像其潜在:有些可以现实化,有些还需耐心等待。《罗生门》会不断让下一位叙述者的回忆驳斥前者的谎言,在颠覆中显示纯粹过去的真相;《寄生虫》试图将别墅潜在(别墅的暗室)的浮现不断滞后,让观众在惊奇中感知其隐喻的社会现实。时间—影像的设置还在继续,主流影片内另有一种力量——“运动—影像”的规定性作用——在压制着它,同时指引着它现身的方式。这股力量拧成一条中枢神经,使异质性时间中的影像在抽象时间里得以表现,既满足着观众对于幻觉的渴望,同时迸发出令人惊颤的情感与思想。但这已不是本文所探析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