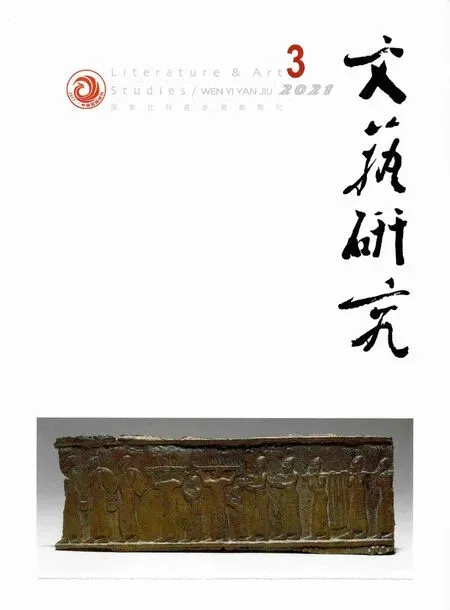目连入戏图像生成路径探赜
喻忠杰
在中国佛教戏剧发展史上, 神鬼剧最具类型化之特征。 以佛陀弟子目连为人物基型演变而成的目连戏, 又是神鬼剧的代表, 在东亚、 东南亚汉文化圈内的影响极其深远。 目连戏以行孝为内核, 其演出文本经过几十代艺人的不断创新与完善, 业已形成各具地方特色的剧目, 并成为传唱不绝的佛教戏剧经典。 这种以佛教思想引领戏剧故事主题并主导戏剧内容的做法, 扩大了中国传统戏剧的题材, 提升了传统戏剧的表演伎艺。 对于目连戏的研究, 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日本学者仓石武四郎的 《关于〈目连救母行孝戏文〉》①。 随后百年间, 对目连戏的剧本整理、 演出形态、 声腔演变、宗教仪式、 民俗文化、 田野考察及传播接受等, 中外学界已有充分讨论, 成果斐然②。但一直以来, 关于目连戏剧形象的图像生成问题却没得到应有的关注, 仅有少数论著在探讨其他问题时附带涉及③。 事实上, 对目连故事图像化的原始起点、 目连图像样态生成的内在机理以及目连形象如何融入戏剧等问题的深入探究, 一方面有助于理清目连形象进入图像叙事的路径, 另一方面有助于全面认识目连戏在生成早期所受不同文化的影响。 本文拟作一尝试, 请方家不吝赐教。
一、 看图讲诵: 文化互动中的目连呈现和观看之道
目连 (Màudgalyāyana) 是古印度佛教创立时代一位真实存在的人物, 其行迹在《增一阿含经》 《佛本行集经》 及 《妙法莲华经》 等佛教典籍中均有载述④, 由古印度输入中国的有关目连其人其事的佛典数量繁夥。 目连救母故事最早的出处, 是西晋译经家竺法护所译 《佛说盂兰盆经》⑤。 此经全文八百余字, 讲述目连救母的部分虽仅一百余字、 情节简单, 却为后世目连故事和目连戏的演化奠定了基础。 其中的报恩思想、异常题材和盂兰盆会等要素, 成为后世诸多佛教经典引申和加工目连救母故事的叙述内核与原始起点⑥。 《佛说盂兰盆经》 译介不久, 中国民间就比照经中载述开始举行盂兰盆会。 最晚自6世纪起, 目连救母故事即得到广泛传播。 每年的七月十五日被定为父母斋日, 人们于当日抄写本经, 并在寺院举行追荐献纳的法会供养仪式。 盂兰盆仪式自此渗透到普通民众的宗教生活中, 逐渐演化为历久弥新的风俗。 有唐一代, 盂兰盆会在皇室和民间都极为流行, 甚至作为国家礼仪在寺院举行⑦。 史料对盂兰盆会的仪式过程鲜有载述, 但透过根据 《佛说盂兰盆经》 创作的目连图文画卷, 可寻绎出目连形象生成的大致轮廓。

图1 《 佛说目连救母经》( 卷首)宋元 木刻版画33.3×596.3cm 日本京都市金光寺藏

图2 《 佛说目连救母经》( 卷尾)宋元 木刻版画33.3×596.3cm 日本京都市金光寺藏
敦煌目连变文及其画卷和日本藏《佛说目连救母经》 (下文简称 《救母经》, 图1、2)⑧, 均属典型的看图讲诵形式, 它们在外观构成和图文内容方面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和亲缘性。 类似的看图讲故事形式早在中国先秦、 两汉时期就已存在。 诸如商、 周时期绘于庙堂、 用于警示后人的人物故事画⑨, 屈原创作 《天问》 时面对的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中的壁画⑩, 山东武梁祠画像石上的历史故事画等⑪, 多以纪事为目的, 有着明确的叙事功能。 最早的看图讲诵故事,大致与古代管理祠庙的巫祝有关。 巫祝多会借助故事阐释图像, 赞颂有关人物之功烈。 在已有故事画像基础上,就图像而讲史的看图讲诵逐步萌发并形成。 两汉之际, 佛教传入中国后,为传扬教义、 广纳信众, 佛教徒便顺势利用看图讲故事的方法诱导听众,从而促使这种伎艺走向成熟和繁荣⑫。在佛教起源地印度原本也有着悠久的看图讲诵传统, 只不过在佛教未涉中土之前, 这种讲诵形式在华、 梵两种话语体系中独立并行、 尚无交集而已。早至公元前五六世纪, 印度就已出现看图讲诵者, 他们带着湿婆神或其他神的画像游历各地, 按图讲述, 并以此为生⑬。 与中国早期讲诵者情况相反, 他们大多社会、 经济地位很低,且通常是文盲。 至孔雀王朝时期(前325—前184), 看图讲故事已经发展为一种大众娱乐形式⑭。 桑奇大塔门楼下的浮雕, 巴尔胡特佛塔石围栏上的浮雕及阿旃陀石窟壁画中的睒子故事画, 都是以连续构图的形式把多个情节发展阶段置于同一画面中, 这些图像可视作印度看图讲诵的早期蓝本⑮。 在图画形成之初, 为了让观图者对较长情节的了解也能达到与书面表述大体相当的效果, 绘制者会重新改造书面文本的叙述样式。 他们把故事情节分割成多个阶段, 力求在图画里逐一还原, 使观图者能够在连续的场景中跟上情节的发展。 这种以连续单帧图画表现事件的方式成形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 在古代东方很早以来就已流行⑯。 可以说, 在亚洲很多国家和地区 (甚至欧洲), 早期的看图讲诵既是当地民众在探索世界时发现的一种宣教方式, 也是不同文明在其进化序列中显现出的一种文化共生现象。 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 这种伎艺便成为互动双方自主选择和共同认可的一种有效传播方式。 敦煌变文讲唱中看图讲诵伎艺的最终形成, 实际上是跨区域文化交流与互融的结果, 而日本藏 《救母经》 则是出自敦煌变文的一条支流,其渊源在中、 印看图讲诵伎艺的交汇之处。
公元5—7世纪, 随着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持续扩大,中亚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 各种文化要素在诸色往来者的转输下, 经此通道一路向东, 譬如深受佛教影响的粟特人在传扬佛教时, 便带来了印度特色的看图讲诵⑰。 这一时期, 佛教在中土得以全面发展, 作为外来佛教文化和本土文化融合产物的变相和变文二体逐步成形。 为使世俗民众乐于且易于接受佛教经义, 在同一佛教主题的介入下, 偏重艺术性的变相和富有文学性的变文互相配合、 共同发展, 催生了一种图文并茂的通俗化宣教方式。 在目连变文中, 一系列被用来表现主人公品质和行为的事件, 大多融摄、 提炼了佛经中与目连直接相关的记载。 比如, 目连赴地狱访母一节敷演各色人物堕入饿鬼道受苦之情形, 所依正是《撰集百缘经》 卷五《饿鬼品》⑱。其他同类题材对《目连变》 故事熏染较为显著者, 尚有《目连弟布施望即报经》 《贤愚经》 等佛典中的片断⑲。 在这些源自佛典的原型材料的铺垫下, 目连逐步从一个佛教弟子演化为变文主人公, 并进入变相的图像视野。 值得注意的是, 无论是有图无文的目连变相, 还是图像缺佚的变文画卷, 它们都采用了连环画式的表现形式。 一方面, 二者在各自的功能领域存在较大差异: 作为石窟有机组成部分的变相壁画, 很可能只是用于宗教奉献, 并不是口头说唱的视觉辅助; 作为说唱伎艺表演底本的变文, 直接目的则在于化俗娱乐, 看图讲诵也只是表演者采用的辅助方式。 另一方面, 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 目连变相模仿经文的叙事结构, 并根据自身逻辑将文字转化为空间性的图像; 新的目连主题图像一旦出现, 便会影响到目连变文的创作, 而变文一经形成, 又会成为变文表演者所使用的画卷以及石窟内变相壁画的素材来源⑳。 易言之, 佛经借助变文被演绎成通俗文学作品, 而变相则以图像形式将佛经内容形象化,看图讲诵作为联结变文和变相的最佳方式, 在变文和变相的加持中日益丰富繁杂。《救母经》 将图文汇于一体, 以水平长卷的形式将叙述连续、 彼此相关的场景一一铺陈出来。 随着讲述者展开画卷, 故事的讲诵和展演便同步开启。 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源自佛典的目连形象持续递变、 反复凝练, 并最终定格在图像世界里。
看图讲诵作为一种民间口头伎艺, 为众多地区的不同群体喜闻乐见。 从传播层面看, 看图讲诵是在 “说—听” 模式的长期循环往复中逐步形成并流播的; 从接受层面看, 无论是故事的讲述还是图像的传播, 看图讲诵的魅力首在 “观看”, 次在 “听讲”。限于卷幅容量和表现手段, 图画不可能把文本内容完全对应呈现, 因此变文画卷在描绘时, 就着力把故事发展中相对重要的环节连续表现出来, 使观众通过观看获得身临其境的效果。 此外, 看图讲诵还采用多种载体形式, 通过挂轴、 水平画卷、 书册型插图等与讲述内容匹配, 满足不同观众的观看需求㉑。 这也说明看图讲诵的创制者在画卷生成之初, 就已注意到了 “观看” 先于 “听说” 的特点以及 “观看” 主、 客体之间的内在联系。 画工绘画时会营造出属于画卷的独立空间, 强化观众的视觉意识。 在画工因势利导下, 加之个人知识和信仰对观看事物方式的影响, 在目连画卷讲诵展演的过程中, 观众便会对画卷产生与预设同向的理解, 给予观演更高热情的投入和更大程度的认可。
二、 画融新声: 目连变文中的图文生成及声画同步
佛教自印度东传之后, 经汉魏六朝数百年传扬、 融汇与发展, 中土僧俗两界对其理解与领悟日臻成熟。 至隋唐两朝会通儒、 道后, 佛教初步完成了自身的本土化。 佛教传播的主要媒介有二: 一为经文, 代表诸佛言说; 一为图像, 呈现诸佛形象。 二者互为表里, 密不可分。 对于借图文以弘法, 无论是西行求法者, 还是本土传法者, 都高度重视㉒。 可见, 在佛教传统中, 用图文阐释佛法的作法由来已久, 目的是使佛教经典通俗化、 形象化, 以便信众学习、 参悟。 图文结合的形式在中国古代早期就已出现,如秦汉简牍中的占卜数术书、 帛书中的养生保健图㉓。 唐张彦远在 《历代名画记》 卷一《叙画之源流》 中云: “留乎形容, 式昭盛德之事; 具其成败, 以传既往之踪。 记传所以叙其事, 不能载其容; 赞颂有以咏其美, 不能备其象; 图画之制, 所以兼之也。”㉔特别强调图画的叙事作用, 认为图画兼具记传叙事、 辅助讲诵和载录形象的功能, 已有图文与声画互动的观念。 及至宋代, 郑樵在 《通志》 中又对图文的形意互补、 传播功能和视觉布局进行了概述:
图,经也;书,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图,植物也;书,动物也。一动一植,相须而成变化。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图,至约也;书,至博也。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㉕
《通志》 成书于南宋, 所述内容迄于隋代, 在礼、 乐、 刑、 政诸方面又时涉唐代。 所以无论是张彦远还是郑樵, 论述图文结合及其重要性时, 所凭物质文本不会仅限于自身所处时代, 还包括唐宋及之前的史料。 唐五代敦煌文献中所存此类图文共存的写本,对于讨论这一时期图文叙事的生成、 发展和声画同步等问题颇有助益。
敦煌所见目连系列变文的同题异构现象为同类抄本之最, 以目连救母为主题的变文计有14件, 大抵可分为4个系统㉖。 其中, S.2614 (图3) 和北京盈字76号 (BD876号, 图4) 两个写卷, 在物质外观和文本内容方面表现出清晰的图文互涉特征。 S.2614写卷题目原有的 “并图” 二字, 在抄手书写完成之后即被抹除, 现存此卷有文无图。不过, 该写卷最早底稿应是图文并行, 只是抄手在实际传抄时出于某种原因仅抄写了文字, 而未绘录图像, 画卷内容因此缺失, 然而借助写卷文本自身的程式套语又可补充说明问题。 变文在从散文说白向韵文唱词过渡时, 通常会使用诸如“且看某处, 若为陈说” 等套语, 这些套语是用来提醒观众在听取讲唱内容的同时注意画卷对应情节的。 经统计, S.2614 写卷中此类套语共有17处, 利用这些套语大致可推断出画卷的情节内容, 两相对应, 该写卷“并图” 部分至少有17 幅与文本情节互涉的画面㉗。 再将榆林窟第19窟前室甬道北壁所绘“目连变相” 图卷(图5) 与此对照即可发现,就双方共有情节而言, 变相中部分画面可对应到S.2614 变文的相关情节, 且二者主题一致。 内容比对如下:

图3 S.2614 (卷 首) 唐 五代 卷轴 26.5×613cm 英国国家图书馆藏

图4 北京盈字76号 (卷尾)唐五代 卷轴 31.5×407cm国家图书馆藏

图5 目连变相 五代 壁画 榆林窟第19窟前室甬道北壁

文本顺序变文情节(S.2614) ㉘目连变相(榆19窟)1 目连父母双亡, 守孝 无 存2 目连投佛出家 无 缺3 目连深山坐禅 看目连深山坐禅之处, 若为…… 缺4 目连天宫寻父 无 存5 目连冥间寻母, 首遇野鬼 目连向前问其事由之处 缺变文套语(S.2614)6 目连过阎罗王殿 门官引入见大王, (王)问目连事由之处 存7 目连至奈河上 行经数步, 即至奈河之上……目连问其事由之处存8 目连至五道将军处 至五道将坐所, 问阿娘消息处 存9 目连遍寻地狱 便向诸地狱寻觅阿娘之处 存
虽然二者在表现形式方面存在差异, 且经考证, 此变相与S.2614所佚目连图卷亦非同图, 但该变相中与目连故事相关联的主要情节并无缺环, 且画面过渡衔接比较紧凑㉙, 客观上与变文存在互文性, 这使不同文本之间的连通成为可能。 目连变相与变文均以佛经为起点, 前者以线条色彩生成图像, 进而达到描绘事件的目的, 后者则以浅近通俗的语言、 韵散交错的方式铺叙情节。 在同一主题下, 图像以语言为根本, 语言以图像为延伸, 二者合力促成目连图文叙事的结合, 从而将抽象的佛典语言具象化, 严肃的语境和生动的画境彼此融合, 在图文交映的同时又发挥出各自的叙述功能。 在整个图文叙事生成的过程中, 以往单纯、 分体的口头言语、 文字书写和画面表述得以结合, 通过语言、 文字、 图像的综合互融, 促使展演效果倍增, 叙事的渗透力与感染力也得到进一步强化㉚。 图文生成之初的变文在说唱展演伊始, 即显现出视听互补与声画同步的传播优势。 作为观演者, 以往单一的听觉或视觉接受方式也因此逐步转化。

10 目连过刀山剑树地狱、 铜柱铁床地狱 今日交( 教) 伊手攀剑树, 支支节节皆零落处存11 目连往阿鼻地狱, 逢守道罗刹被挡回 即逢守道罗刹问处 缺12 目连返至娑罗林所咨白世尊, 承佛赐锡杖须臾之间, 即至娑罗林所……白言世尊处 缺13 至阿鼻地狱 吸着和尚化为灰尘处 缺14 在阿鼻地狱 饶君铁石为心, 亦得亡魂胆战处 缺15 母子相见 驱出门外, 母子相见处 缺16 母子地狱挥泪话别 言“ 好住来, 罪深一寸肠娇子” 处 缺17 目连无力救母, 再白世尊 腾空往至世尊之处 缺18 世尊拯救地狱之苦, 地狱化为天堂,目连母转生饿鬼如来领八部龙天……救地狱( 之) 苦( 处)存19 目连救母, 至王舍城中长者门前非时乞饭 长者见目连非时乞食, 盘问逗留之处 缺20 目连与母饭、 水, 成脓河猛火 且看( 与) 母饭处 缺21 目连三白世尊, 受教造盂兰盆 无 缺22 目连母托生黑狗, 目连乞食寻母, 读大乘经典, 母转为人身 无 缺23 目连劝母修福, 母亲罪灭, 往生西天 无 缺
北京盈字76号 (BD876号) 反映出与S.2614写本互文的图文信息。 该卷卷背所抄《大目犍连变文》 的格式很有特点: 每段文字之间留有很大空白, 且这些空白尺寸不一;文字记载部分均设乌丝栏, 无文字记载部分则没有, 颇似量好长短、 预估图像大小后,特地预留了所需空间㉛。 该卷卷尾题记云: “太平兴国二年 (977——引者注) 岁在丁丑润 (闰) 六月五日, 显德寺学仕郎杨愿受一人思微, 发愿作福。 写画此 《目连变》一卷, 后同释迦牟尼佛尝会弥勒生作佛为定。 后有众生, 同发信心, 写画 《目连变》者, 同池(持) 愿力, 莫堕三途。”㉜其中 “写” “画” 并提, 说明该卷原本亦附有图像。 虽然两个写本在传抄过程中都被删略了图像, 文字部分亦有差异, 但可以肯定的是, 二者在写本生成过程中采用了相同的创制方式, 即图文互涉。 在加工文本时, 变文写本创作者大体依循印度佛典在形成与传播时的 “说—听” 模式, 以通俗化手段对源自佛典的诸佛、 菩萨神变故事进行多次创作或改写, 形成 “说—听—看” 的新模式,从而在写本内部或者写本之间生成图文互涉的互文关系, 其中敦煌写卷P.4524 (图6、7) 即为典型代表。 该卷正面为“降魔变” 画卷, 背面对应的则是从《降魔变文》 中摘录的韵文部分, 散文说白部分因非唱词而被删略。 在说唱展演时, 至少有两人协同表演: 一人作为“说者” 在前, 面对观众以散文形式讲述故事; 另一人作为“唱者”, 手执画卷立于卷背后, 吟唱韵文唱词并展示画卷。 在画卷展开过程中, 每个场景中靠近结尾部分, 总有画面人物将头转向下一个场景。 这种兼具“观—演” 功能的画卷设计,一方面可以提示表演者在吟唱韵文时, 无须看画就能明确画卷展开对应部位的画面内容, 另一方面可以引导观众对即将展开的部分产生心理期待㉝。 据此可知, 用于说唱展演的目连变文, 在生成之初具有类似P.4524的写卷形制, 其大致样态或为: 以写卷中的目连故事 (S.2614) 为讲述基础, 利用左图右文 (北京盈字76号) 或者正图背文(P.4524) 的外观形式, 由说唱艺人合作展演。 在演出时, 随着画卷的展开, 表演者以语图互动的方式对情节进行陈述: 语言描摹故事轮廓、 点明人事意义, 图像则呈现故事的特定瞬时场景。 在此过程中, 虽然语言和图像分别运用各自的叙事符号讲述故事、表情达意, 但写卷内部互文关系的存在, 最终使得二者的功能在本质上渐次趋同。 与此同时, 表演者会借助表情和身姿来表达对故事的理解, 进而展现出更加丰富的内容和复杂的场面。 画卷的 “画” 通过模仿故事中的形和物, 说唱的 “声” 通过模仿生活中的音和调, 最终以视、 听的形式达到叙事的传播和接受的目的。 因此可以说, 在变文说唱的图文生成初期, 声画的发展也是与之同步的。

图6 P.4524 (正面局部) 唐五代 卷轴 27.5×571.3cm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图7 P.4524 (背面局部) 唐五代 卷轴 27.5×571.3cm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三、 图文合体: 说经伎艺中的目连展演与戏剧雏形
20世纪60年代, 日本藏 《救母经》 被作为佛教美术研究资料在日本刊物 《美术研究》 上发表㉞。 之后, 中国学者常丹琦和张鸿勋各自从俗文学研究的不同方向进行探考, 客观论述了此经卷的文本属性, 并明确认定其为宋代 “说话” 伎艺中的 “说经”一体㉟。 事实上, 《救母经》 的“说经” 文体渊源有自, 敦煌写本中同样存在一个以目连救母为主题且以“经” 称名的残卷S.4564。 此卷虽称《目连经》, 但从体式和内容来看, 并非与目连相关的佛经, 却更接近变文一体。 从现存变文体式看, 生成期和发展期的变文大多是用于讲唱展演的底本。 随着变文样态和展演伎艺的不断演变、 成熟直至式微, 目连变文在经过众手传抄改易、 增删修正之后, 原来图文并茂的变文画卷一分两路: 一类被简化为有文无图的 《目连经》 样式, 最终走向案头化; 一类继续保持着图文并茂的原初形式, 在深度发展中赓续、 嬗递和转型。 从目连变文画卷到 《救母经》 再到元末明初的目连宝卷, 它们之间的代际演化, 一方面说明以目连救母为主题的文本在流播过程中一直经历着持续改写, 另一方面也显现出在图文合体过程中目连形象逐步融入戏剧的轨迹。
《救母经》 画卷首页为全幅佛说法图, 其余各页上图下文, 上附榜题, 整个经卷近似后世全相平话版式。 此卷绘画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 作为佛教题材的绘画艺术, 其画风朴实通俗, 释迦牟尼佛形象简约, 地狱描绘直白真实, 目连行止富有戏剧色彩和生活气息。 画卷明显带有宋代宗教绘画的世俗化倾向, 同时还有宋代人物故事画的生动气韵和世俗情调。 此外, 版画画面厚重, 镌刻时大量运用粗黑宽线, 较多使用大块黑色, 景物刻画细碎。 人物线条虽然流畅, 却不工细, 线纹转折处略显生硬, 衣褶发板, 无悬垂感。 与之后元代同类作品相较, 其技艺稚拙古朴, 更近于宋版印刷作品㊱。杭州雷峰塔出土的吴越国王钱俶所造《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 用字与敦煌写本用字基本一致, 而 《救母经》 无论是书体还是所用俗字都与此经高度相似。 据敦煌俗字与国内其他地区俗字的时代共性大于地域个性这一特征㊲, 亦可补证《救母经》 源出敦煌变文, 而其生成时间最晚可断于宋代。 而在宋代, 以纸张的普及和印刷术的发明为标志的“后写本时代” 正式开启, 文本与图像的关系也因此发生新变。由于文学文本与图像艺术的长期共存、 互相熏染和彼此需要, 文与图在同一个文本界面上相互映衬, 进而缩小了文本与图像的空间距离, 并使二者的联系更加密切, 直至融为一体㊳。 与变文画卷相比, 《救母经》 中的图像和文本之间表现出更加紧密的相互牵引与弥合, 图文之间不再是彼此简单的辅助说明或二度解释, 而是呈现出互文性阐发的关系。 虽然文本叙事的节奏跨度远非图像所能及, 二者亦非同质艺术媒介, 图文互仿本不可能做到一一映射, 只能是 “异质同构” 式的趋同, 但是, 当图文所要描述对象的内在意象得到沟通和连接并表现出较大自由度时, 图文合体的文本形态便自然生成㊴。 比如在描绘阿鼻地狱之恐怖时, 《救母经》 便使用了较长篇幅的文字, 为达到图文平衡, 画卷篇幅亦随之增加, 经文朴素绵长, 图像周到细致, 图文之间借助互文在主题、 动态、 时空等方面逐步趋同并保持一致。
将 《救母经》 与变文、 变相进行比照, 更能看出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 前者明显沿袭了唐五代变文与变相依循佛教故事 “摹画叙事” 的传统, 既重视故事的转述和情节的描写, 又强调图文的互动和形式的功能。 具体而言, 一方面, 《救母经》 继承了《佛说盂兰盆经》 和变文的核心部分。 故事内容的前半部分从 《目连缘起》 发展而来,后半部分则与 《目连救母变文》 相似, 并在转述基础上产生新的内容、 事项以及不同的情节顺序, 新生内容在后世得以延续和改进。 比如变文中目连呈现为 “神通第一”的形象, 在 《救母经》 中, 目连成为释迦弟子之后, 每逢其救母陷入困境之时, 皆会依仗释迦力量, 佛的威力被极大提高。 这种转述和情节的强化, 在之后出现的目连戏文中被长期因袭下来㊵。 另一方面, 《救母经》 在画面构图设计上又与变文画卷和变相一脉相承。 P.4524 “降魔变” 画卷即注意到了内部格局的分割, 整个画面由若干单元格组成, 画工使用风景要素划分单元, 画面以树或山作为区分独立叙事场景的标志。《救母经》 在经卷创制之初便袭用了同样的手法, 以云、 树、 山、 墙作为内部界限来分割超长画面。 图画上对应题写的说明性文字, 明确指出故事发生的场所, 且对图画内容进行简要概括, 如 “青提夫人与罗卜分财处” “造盂兰盆会处” 等, 其指向功能与变文中 “且看某处” 的作用并无二致。 不过, 同样是指故事在叙述过程中的 “某处”或 “某点”, “处” 在这里向时间意义的转变甚为明显㊶。 这也再次证明在由目连变文向 《救母经》 演化的较长一段时间里, 这个以目连救母为主题的文本, 无论是在内部细节还是外部形式上, 一直都经历着改写。 另外, 《救母经》 在描述目连遍游地狱时,出现八次“目连次复前行”, 与之对应的画卷内容则是目连所见地狱的不同情形。 叙述路向在空间层面的整齐线性排列, 使文本与图像在叙事过程中形成平行呼应。 在整个图文生成过程中, 文字的作用不仅仅限于讲述故事、 解说图像, 还可以组织画面并控制观看, 从而最大限度地将时间性和空间性结合起来㊷。 由是, 文本意象引发情节想象, 画卷图像催生人物形象。 在 《救母经》 实际展演时, 图文合力塑造的目连形象自然就被同时期的其他演艺形式所借鉴, 并逐步融入表演实践, 走向舞台。
大致来说, 公元5—11世纪是中国文化传播史上的写本时代, 而7—14世纪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的成熟时期。 二者交集的重合期, 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中国写本文化向四周辐射的一个重要时段。 紧邻中国的日本、 朝鲜, 甚至远在西亚的部分地区,都在某些领域受到这一辐射。 日本藏 《救母经》 中广为流传的目连故事, 正是通过古代丝绸之路上的 “印度—于阗” 一线, 途经高昌、 敦煌、 凉州而至长安, 由佛典而入变文。 经过长期本土化和世俗化的改造, 变文逐渐化身“说话”, 并由民间艺人和世俗供养人合力传至江南地区, 后又由浙东传播至浙南、 闽北和粤东㊸。 闽北一路的流传版本为之后形成于金元时期的 《目连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 所继承, 后者在版式和内容上直接受到前者的深刻影响。 创作者以 《救母经》 为故事蓝本, 充分借鉴其叙述情节和细节, 在自主增饰和发展的基础上, 择取现成文词, 创制出兼具独立性和文学性的宝卷作品。 由于要面向以女性为主的崇佛民众, 《目连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 将《救母经》 发展为更详细的长篇歌谣。 随着宗教科仪的发展, 最终产生出更具观演性的目连戏㊹。 粤东一路的流传版本则由日本僧人在广州购得, 经水路而携卷东渡, 刻版刊印后入藏名刹。 《救母经》 的最终定型, 客观再现了中古时期历代叠加型图文叙事文本的生成过程, 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目连形象由平面展现走向立体表演的演变路径。
余 论
有文献可考的最早目连戏演出是北宋末年在汴梁搬演的 《目连救母》 杂剧。 成书于南宋初期的《东京梦华录》 “中元节” 条对此有如下记述:
七月十五日,中元节。先数日市井卖冥器:靴鞋、幞头、帽子、金犀假带、五彩衣服,以纸糊架子盘游出卖。潘楼并州东西瓦子,亦如七夕。要闹处亦卖果食、种生、花果之类,及印卖尊胜目连经。又以竹竿斫成三脚,高三五尺,上织灯窝之状,谓之“盂兰盆”。挂搭衣服、冥钱,在上焚之。构肆乐人自过七夕,便般目连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观者增倍。㊺
在以佛教仪式为主导的盂兰盆会上, 连演七日的 “目连救母杂剧” 实质是以诵经和说经为中心的佛教仪式活动。 活动期间, 杂剧搬演只是其中的一个辅助部分, 而此处所谓 “杂剧”, 大致相当于变文说唱, 并杂以诸般伎艺㊻。 在唐五代时期的寺院中, 时有“百戏” 演出, 目连变文讲唱作为其中一环, 是寺院借助庙会形式将 《盂兰盆经》 通俗化的一种有效途径。 到了宋代, 这种情形得以延续, 只不过外在表现形式发生了新变。以目连救母为主题的“杂剧” 和“说经” 开始兴起, 并继续发挥着对世俗的教化作用,其原有的宗教意味渐趋淡化。 宋代中元节勾栏瓦肆所搬演的目连杂剧, 可以认为是目连救母故事之讲唱表演进一步戏剧化的结果。 在编剧方面, 变文非常接近戏剧脚本,尽管变文的曲白多是叙事体, 但在描述人物对话时又都使用第一人称代言体。 变文中还出现了关于角色上下场的舞台提示语, 加之丰富多变的音乐形式、 初具规模的舞台美术和表演环境, 在戏剧生成的雏形阶段, 变文自然成为难得的可用文本。 当所有条件具备后, 演出历时一天的 《目连救母》 杂剧便成为现实。 为了符合盂兰盆会宗教仪式要求, 演出活动会持续七日。 在目连形象定型并在杂剧中呈现的同时, 市面上亦有印卖尊胜目连经者, 所售经文内容当与目连救母相关, 而该经文很有可能就是图文合体版的 “说经” 底本。 这种现在看似粗简的演出虽由其法会的特殊性决定, 却经历了漫长的“法事(盂兰盆会) —变文—法事戏—戏剧” 的演变过程㊼。 而与此演变过程相对应的目连形象展演和入戏路径亦了了可见: 法事 (佛陀弟子目连) —变文 (图文展演中的目连) —法事戏(图文入戏后的目连) —戏剧(舞台表演中的目连)。
目连戏从宋代杂剧起便广泛传唱, 在漫长的演出过程中, 它不断地吸收新养分、融汇新内容、 创造新样式, 并长期保持着动态化的自我改造和立体化的实践演出。 正是由于这种强大的内在创造性和延展性, 至宋元时期, 南戏目连开始深入民间, 而到元明时期, 杂剧便产生了成熟的目连剧本, 明清以降目连戏更是蔚为大观。
① 盐谷温等: 《中国文学研究译丛》, 汪馥泉译, 北新书局1930年版, 第225—248页。
② 参见王馗: 《20世纪目连戏研究简评》, 《戏曲研究》 第64辑, 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年版; 谌曾灵: 《近三十年目连戏研究述评》,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 2019年第2期。
③ 如巫鸿: 《什么是变相——兼谈敦煌叙事画与敦煌叙事文学之关系》, 敦煌研究院编: 《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 梅维恒: 《绘画与表演——中国绘画叙事及其起源研究》, 王邦维、 荣新江、 钱文忠译, 中西书局2011年版; 梅维恒: 《唐代变文——佛教对中国白话小说及戏曲产生的贡献之研究》, 杨继东、 陈引驰译, 徐文堪校, 中西书局2011年版; 马丽娜: 《论敦煌本 〈佛说十王经〉 图卷与目连变文、 目连图卷之间的互文性》, 《浙江学刊》 2018年第5期。
④《增一阿含经》, 瞿昙僧伽提婆译, 《大正新修大藏经》 第2册, (台湾) 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 第594—595、 603—604页; 《佛本行集经》, 阇那崛多译, 《大正新修大藏经》 第3册, 第655—656页;《妙法莲华经》, 鸠摩罗什译, 《大正新修大藏经》 第9册, 第21—22页。
⑤《佛说盂兰盆经》, 竺法护译, 《大正新修大藏经》 第16册, 第779页。
⑥ 刘祯: 《中国民间目连文化》,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版, 第4—5页。
⑦ 池田温等: 《敦煌文薮》, (台湾) 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版, 第137—142页。
⑧《佛说目连救母经》 原刻印于 “伊势神宫关系之梦想记” 纸背, 由13单页装裱成卷。 卷长596.3厘米、 宽33.3厘米。 上图下文, 图高10.3厘米, 文高12.7厘米。 该经卷载述目连前往地狱寻母一事。 据卷末牌记所署, 此经为元代刊印本同样式的翻印本。 现藏日本京都市六条河原町金光寺。
⑨ 伏俊琏: 《先秦文献与文学考论》,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第139页。
⑩《孙作云文集》 第1卷, 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第548—554页。
⑪ 巫鸿: 《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 第271—332页。
⑫ 伏俊琏: 《敦煌文学总论》,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 第376页。
⑬㉑ 梅维恒: 《绘画与表演——中国绘画叙事及其起源研究》, 第23—52页, 第85、 184、 187页。
⑭ F. W. Thomas, “Political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Maurya Empire”, in E. J. Rapson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Vol. I,Ancient India,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2, pp. 474-494.
⑮ Stella Kramrisch,Unknown India: Ritual Art in Tribe and Village,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 1968,p. 70.
⑯ 迪特·施林洛甫: 《叙事和图画——欧洲和印度艺术中的情节展现》, 刘震、 孟瑜译, 兰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第29页。
⑰ Guitty Azarpay,Sogdian Painting: The Pictorial Epic in Oriental Art,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p.102.
⑱《撰集百缘经》, 支谦译, 《大正新修大藏经》 第4册, 第222—223页。
⑲ 陈允吉: 《〈目连变〉 故事基型的素材结构与生成时代之推考——以小名 “罗卜” 问题为中心》, 荣新江主编: 《唐研究》 第2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⑳㉝《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 郑岩等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 第389页, 第378—381页。
㉒ 李小荣: 《图像与文本——汉唐佛经叙事文学之传播研究》, 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第9—10页。
㉓ 徐小蛮、 王福康: 《中国古代插图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第5—11页。
㉔ 张彦远著, 秦仲文、 黄苗子点校: 《历代名画记》, 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 第3页。
㉕ 郑樵: 《通志》, 中华书局1987年版, 第837页。
㉖ 系统一为北京成字96号 (BD2496号) 及北京水字8号 (BD4108号3), 二者原本无题, 后被分别拟为 “目连变文” 和 “目连救母变文”。 系统二为P.2193, 写卷首题 “目连缘起”, 卷背题 “大目连缘起”。 系统三为S.2614, 写卷首题 “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 尾题 “大目犍连变文一卷”, 上有题记,附图已佚。 另有相同内容者八卷: P.2319、 P.3485、 P.3107、 P.4988、 北京盈字76号 (BD876号)、 北京丽字85号 (BD4085号)、 北京霜字89号 (BD3789号)、 S.3704, 参见王重民、 王庆菽等编: 《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第714—755页; 潘重规编著: 《敦煌变文集新书》, (台湾) 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4年版, 第685—734页; 黄征、 张涌泉校注: 《敦煌变文校注》, 中华书局1997年版, 第1024—1070页。 此外, P.4044当亦属此系统, 但以上三书均未提及, 颜廷亮 《〈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 的一个未见著录的节抄卷》 (《社科纵横》 1994年第4期) 有详细论述。 系统四为S.4564, 首尾俱缺, 尾题 “目连经”, 参见黄永武主编: 《敦煌宝藏》 第36册, (台湾) 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版, 第576页。
㉗ 参见樊锦诗、 梅林: 《榆林窟第19窟目连变相考释》, 《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 第51页。 该文原统计共有16处, 本文认为尚需增补言 “好住来, 罪深一寸肠娇子” 一处。
㉘ 本表内 “变文情节” 及 “变文套语”, 均据S.2614 “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 黄征、 张涌泉校注: 《敦煌变文校注》, 第1024—1038页。
㉙ 樊锦诗、 梅林: 《榆林窟第19窟目连变相考释》, 第46—55页。
㉚《朱凤玉敦煌俗文学与俗文化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第126—151页。
㉛ 荒见泰史: 《敦煌讲唱文学写本研究》, 中华书局2010年版, 第67页。
㉜ 中国国家图书馆编, 任继愈主编: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 第12册,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 第326页。
㉞ 宫次男 『目連救母説話とその絵画——目連救母経絵の出現に因んで』, 『美術研究』 (1967年) 第225號, 155—177頁。
㉟ 关于 《佛说目连救母经》 的体式, 学界存在争议。 最早进行讨论的吉川良和认为, 它不是一般的佛经,也不属于话本, 参见吉川良和: 《关于在日本发现的元刊 〈佛说目连救母经〉》, 《戏曲研究》 第37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 嗣后, 常丹琦发文指出该经 “是被南宋造经人误为佛经而刊印的 ‘说经’ 底本, 是杰出的宋代 ‘说经’ 艺术”, 参见常丹琦: 《宋代说话艺术 〈佛说目连救母经〉 探讨》, 《戏曲研究》 第41辑, 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版。 此后, 刘祯提出相反意见, 认为此经既非宋元时代的 “说经”伎艺, 亦非佛经, 而是与 《慈悲道场目连报本忏法》 关系最为接近的一种, 属于同源。 他说: “《救母经》 刊印于元中叶, 《报本忏法》 的最早出现流行亦当在此期, 或更早。” 参见刘祯: 《宋元时期非戏剧形态目连救母故事与宝卷的形成》, 《民间文学论坛》 1994年第1期。 张鸿勋综合诸说, 论称 《救母经》“极有可能就是直接承袭唐代俗讲转变演化产生的一部宋代说话中 ‘说经’ 的底本”, 参见 《张鸿勋跨文化视野下的敦煌俗文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第97—114页。 本文认为, 常、 张二说可从。 另外,《救母经》 在叙事内容和图文构制方面与敦煌目连系列写本存在明显的继承性, 而经卷的物质外观则清晰呈现出宋元时期的文化传播载体由写本向刻本过渡的样态, 其文本形成期最晚当在宋代早期。 中国忏法虽发源于南朝萧梁时, 但 《慈悲道场目连报本忏法》 却是元代之作, 晚于 《救母经》。
㊱ 常丹琦: 《宋代说话艺术 〈佛说目连救母经〉 探讨》。
㊲ 黄征: 《敦煌俗字典》 “前言”, 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 第16—19页。
㊳ 赵宪章: 《文学和图像关系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江海学刊》 2010年第1期。
㊴ 李彦锋: 《中国美术史中的语图关系研究》, 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第62—63、 104—110页。
㊵ 吉川良和: 《关于在日本发现的元刊 〈佛说目连救母经〉》。
㊶ 梅维恒: 《唐代变文——佛教对中国白话小说及戏曲产生的贡献之研究》, 第90—124页。
㊷ 巫鸿: 《全球景观中的中国古代艺术》,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 第143—195页。
㊸《佛说目连救母经》 卷末牌记提供了关于经卷来源、 供养人、 刊印时间等的信息, 其中所载造经供养地为浙东道庆元路鄞县。
㊹ 田仲一成: 《元代佛典 〈佛说目连救母经〉 向 〈目连宝卷〉 与闽北目连戏的文学性演变》, 张宏生主编:《宋元文学与宗教》,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第118—149页。
㊺孟元老著, 伊永文笺注: 《东京梦华录》, 中华书局2006年版, 第794—795页。
㊻ 康保成: 《中国古代戏剧形态与佛教》, 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版, 第246页。
㊼ 朱恒夫: 《目连戏研究》,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第30—43页。
——弋阳腔艺术保护中心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