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体与救赎
文敏
好几位朋友向我推荐《下沉年代》(The Unwinding),豆瓣读书评论对它一片赞扬,有人认为此书相当于美国当代史的《万历十五年》。我的看法是,乔治·帕克(George Packer)的叙事能力确实不错,但作为一种美国断代叙事,它还是缺少早先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那种灵动风采,论到对观察对象的平视白描以及纤秾合度的叙述表达,我觉得彼得·海斯勒似乎更胜一筹。为什么大家评价如此之高?粗略看了下留言,大体认为此书在展示各路人物及其生活轨迹的同时,“诚实地谱写了一曲美国挽歌”……大致是这个意思吧。所以,中文书名将“unwinding”(解开、松开)译作“下沉”(这样翻译真的好吗?)。
经济学家菲利普·朗曼认为,一九五○年后出生的美国人是历史上第一代经历了终身向下流动趋势的美国人。《下沉年代》的书写对象正是这一代美国人的生活:他们出生于战后经济增长的黄金年代,摸爬滚打半生后,却遭遇传统社会结构的分崩离析。全书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写起,纵越美国三十余年历史,其中包括经济滞胀、石油危机、互联网泡沫、伊拉克战争、次贷危机、产生第一位黑人总统、占领华尔街等重大事件。作者以多年积累的人物追踪访谈,将个体命运置于美国当代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中,梳理出一幅与发展相悖谬的图景:产业创新、全球化、后城市化……美国人终于被分割成不同区块。他们为自由而戰也被自由拖累,他们共处一片土地却难以怀抱同样的热忱,不再理会“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的呼唤。这个国家曾有人口占比最大的单纯而稳健的中产阶层,现在他们不得不各自为战。
读完全书后,自然感到帕克的文字至少是真诚的。苦涩又艰难的经历被诚实地记录下来了,一切才算没有白白发生。

《下沉年代》[ 美] 乔治·帕克著刘 冉译文汇出版社2020 年版
乔治·帕克,自二○○三年起连续十五年担任《纽约客》专职作者,现为《大西洋月刊》专职作者。作为社会观察者和一线写作者,帕克长期深入社会各个阶层,记录从华盛顿、华尔街到“锈带”工厂的美国众生,《下沉年代》就是这样一部沉潜之作。二○一三年,本书因“撕开美国的破碎裂痕”获美国国家图书奖。二○一九年,他又获得希钦斯奖,该奖旨在表彰“为自由表达和追求真理而不顾个人或职业后果”的作家。
我不知道他的“职业后果”是什么,但他笔下人物触动我的地方在于:他写他们身不由己地倒下去,也写他们靠自己双腿站起来。那些“失败者”,其实指枷锁之下努力抗争过的人们。
流水线噪声中苦涩的笑话
我个人的阅读体验可能跟许多读者不太一样,帕克这书能让我一口气读下来,是因为我对他描述的底层人物命运产生很深的共情。他让我想起自己早年的工厂生涯,想起数控机床和流水线引进之前技术工人的职业地位。当然,也想到一个假设:如果不是在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时进入大学,而是一直在工厂做下去—这一闪而过的念头,让我不禁打了个寒颤。

乔治·帕克(George Packer)
在我操作机床的年代,工人(尤其技术工人)很有社会地位且有自我成就感。其时制造业尚以传统的“车钳刨铣”为主要工艺流程,技术或曰手艺,是一份职业骄傲,那时蓝色工装背带裤与后来大学生胸前的校徽一样招人艳慕。后来,我曾就职的那家阀门厂转型为一家中美合资公司,厂子境况还不错,可是工人的命运却大不相同。当年与我同在技术攻关小组的几个伙伴各有去向,其中一位钳工成了新公司的副总经理,另一位操作曲线磨床的技工却武功全废,被提前下岗。那磨床工是我最好的朋友,技术精湛,人很聪明,从前我们一起在工厂排球队打主力。恢复高考时她听从家人意见,怕毕业后被分配去外地,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可是谁曾料想,厂里引进的美国生产流水线让她精湛的技术变得毫无用处,她不甘成为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钉,只能黯然出局。她把自己的才智用在麻将桌上,有她的牌局别人没赢钱的份儿,落下个外号叫“收割机”。这不是个例,技术和生产模式进步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产值利润遮蔽了个体的悲催。当然,在“收割机”离厂的同时,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入了工业流水线。中国的改革无疑在总体上大大提升了社会富裕程度,传统技术工人离岗不至于造成美国那样根本性社会问题,只是被描述为一种“阵痛”。

美国锈带的废弃工厂
帕克这本书告诉我们,流水线和产业结构转型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也让我意识到:此岸的下岗潮,正是因为彼岸蝴蝶扇动翅膀,而美国作为传统制造业大国遭遇的风暴远甚于我们这边。不同的是,他们是产业外移而形成大量工业废墟,我们则是引入流水线挤出了技术工人。
美国人同样遭遇买断工龄自谋出路的危机,他们也打着买房养房的主意,与通货膨胀赛跑,结果却一脚踏空……帕克笔下的历史并不是抽象的政治经济学,他尽量不让自己跳出来做判断,只是让故事和人物说话,在命运踪迹中显示经济规律的叙事逻辑。书中几乎没有对诸多社会问题(去工业化、阉割工会、经济衰退、网络泡沫、金融危机等)影响下的大局做分析,而是通过几个身份不同的角色来完成他的叙事。这些人物有来自烟草种植家族的创业者,有在锈带长大的黑人瘾君子之女,有乔·拜登先前的竞选幕僚,还有聪明绝顶的PayPal创始人。书中还重点描述了佛罗里达州的坦帕市,因为这里是美国炒房热的重灾区。
帕克追踪的一个人物名叫塔米·托马斯,俄亥俄州的黑人姑娘,在青春期亲眼见证了五大湖区的重工业疾速衰落。她拼尽全力挣脱原生家庭的不良习气,进入了通用汽车公司,本以为这就使自己一生有了保障,却眼睁睁看着昔日的“民主军火库”变成无人问津的锈带。一九九九年,通用汽车将包括帕卡德在内的分厂整合成一家名为德尔福的独立公司。当时塔米每小时工资是二十五美元,每年包括加班费在内的税前收入是五万五千美元。塔米工龄已有十年,距离退休还有十三年,她业余时间在扬斯敦州立大学攻读社会学课程,预计退休时能够获得学位,她打算借以养老金去某个第三世界国家生活。可是变化来得太快了,二○○六年,德尔福宣布即将关闭,出售其二十九个美国工厂中的二十一个,削减两万个小时的工作职位。于是,工人被鼓励一次性买断工龄(公司通过幻灯片向工人们传达了复杂的细则)。塔米买断工龄时获得十四万美元,她最后悔的是交完税付了生活费之后,没有将剩下的钱搁到银行做定期储蓄,而是交给一个亲戚去投资房地产(对方承诺有10%的年回报率)。这个故事的走向,我们绝不陌生。一开始每个月会收到些许利息,那些楼盘也都取了英国古典庄园式的好名字:阿什顿橡树园、国王路吊床园……然后,到了二○○八年,房地产泡沫破裂,亲戚跑路,她的养命钱就没有下文了。
坦帕的“大门律师”(指那种什么案子都接的律师)代理那些因投资房屋破产的各色人等,根本就忙不過来,因为“低技能工人在结构上无法再参与劳动,并且蠢得不明白他们昔日的旧工作已不可能回来。公司则不受任何国家利益概念的束缚,财产法体系分崩离析”。在俄克拉荷马州的扬斯敦,四成的房子是空置的。差不多四分之一的业主是在加州,或是远在奥地利甚至是在中国。他们通过“一分钱买房”网站买下房子,至今也没搞清房屋状况。黑人市长拼命拆除那些鬼屋样的废旧房子,但废弃的房子太多了,拆都拆不过来。
塔米·托马斯式的惨剧不光见诸制造业,全球化的产业链已经拴住了各行各业。出身烟农的迪恩·普莱斯,走自主创业道路,沿220号公路做加油连锁店,到头来也被壳牌、BP那些跨国集团搞垮了。他气得发疯,在心底呐喊:他们应该是美国人,而不是“没国人”(Americaints)。
作者在本书“序幕”一章中发出沉痛的告解:“没人能说清解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曾经有一束线圈将美国人安全地绑在一起,有时甚至紧得令人窒息,可不知从何时开始松开了”,“在解体的过程中,一切都在改变,没人能够幸免,不变的只有解体之声……解体之声,是在装配流水线的噪声中被说出的笑话,是拉上隔离世界的百叶窗后发出的抱怨……是卡车在黑暗中驶过时,人们在前廊上做着的响亮的梦”。作为中国读者,我感受到一种天地不仁的诅咒。
一开始我不太明白,帕克追踪的那几个背景完全不同的人物,有何共通之处?后来才看懂,他们看似不同的命运都为“解体”做了注脚,无论贫富,亦无关种族,人们都陷入经济动荡和社会变革的持续风暴中。周围的一切都在沉浮变化,很难再找到恒久可靠的坐标以确定自己的人生方向。它又并不局限于美国,而是展示了全球化进程中的连锁反应—科技发展、政治走向、行业兴衰,如何结结实实地落在每一个人头上。没有一片雪花能造成雪崩,但所有的雪花累积起来,形成一个又一个雪球,无数雪球从高空无情袭来时,普通人靠什么来扛?
拉上隔离世界的百叶窗后的抱怨
解体带给美国人更多的自由选项:改变人生或是接受现实,坚持到底或是逃离废墟,重新创业或是彻底认栽……书中写道:“输家经历了漫长的坠落才跌至谷底,有的甚至永远不会触地。”赢家则青云直上,“像充满气的飞艇飘上云端”。帕克让大家看清楚一个现实:美国建制派已经无法为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提供上升通道。精英人士认为每个人都应成为计算机程序员或金融工程师,在时薪八美元与年薪六位数收入中间没有其他工作,答案只在0与1之间。政府曾致力于推进全民编程,但编程能够救美国吗?
书中借用在大银行工作的凯文·摩尔的话说,金融是胡扯,他从不认为它有任何价值。但事实上,健康良好的金融体系对整个社会都有利。没有华尔街的支持,硅谷的新兴产业不可能发展得如此迅速。作者虽然对华尔街精英殊无好感,但一方面狠扒他们的外衣,一方面倒也不忘提示不同的声音。在描述占领华尔街的场景时,他特别注意到队伍里有两名中年男子拦住一个抗议者,他们带着浓重的俄罗斯口音发出奚落,劝抗议者转投委内瑞拉那样的国家。可见,有人既不喜欢华尔街,也不喜欢那些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者。
彼得·蒂尔,硅谷明星,脸书(Face-book)最初的天使投资者。十几岁时成为一名自由意志主义者,作为硅谷的人生赢家,他也看到了贫富差距的迅速拉大,对前景并不乐观,甚至感到惴惴不安。作为聪明人,他看到了“创新产业”的本质。他认为:“我们基本上已将一切与物质世界有关的事情都禁止了,你唯一获准去做的事情只能在数字世界完成。”确实,在过去四十年里,只有这两个领域出现了大规模的创新。
彼得二十岁时读过安·兰德的《源泉》和《阿特拉斯耸耸肩》。在一九五七年出版的《阿特拉斯耸耸肩》里边,兰德已预知未来不会美好—书中两个主角去度假,到了中西部地区发现这里每个人都满腔愤怒却无心工作,发动机公司废弃的厂房里堆满了新型发动机的残骸,那家公司的继承者最终破产。要知道,当时通用公司在全世界所有公司中拥有最大市值,底特律的平均收入高于纽约40%……彼得真是越来越佩服兰德的“远见”。在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毕业之前,他为《斯坦福评论》写了最后一篇社论,其中说道:“政治正确为贪婪找到的替代方案并不是个人的满足或幸福,而是对他人的愤怒和嫉妒,而那些人正在做更有价值的事情。”他说他宁愿生活在一个人们不肯分享的社会中,也不愿生活在一个人人都想拿走属于他人东西的社会。
作为PayPal的创始人,彼得有足够聪明的头脑和学习的能力。有一本名为《主权个体》(The Sovereign Individual)的书深深吸引了他。这本书描述了一个即将到来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计算机革命将侵蚀民族国家的权威,瓦解公民的忠诚以及传统职业等级。并且,通过全球化的网络商务赋予超个人权力,通过电子货币将金融搬上网络,借此将金融去中心化,并埋葬福利国家的民主政体,同时,它也会加速财富的不平等分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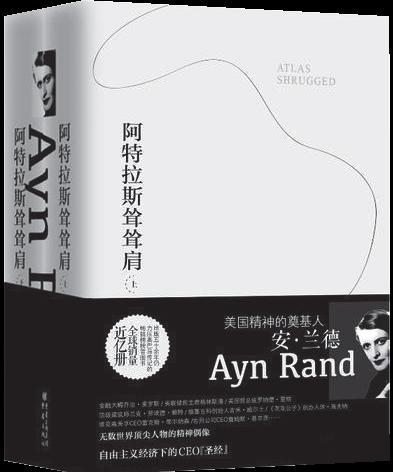
《阿特拉斯耸耸肩》(全二册)[ 美] 安·兰德著杨 恪译重庆出版社2013 年版
这里提到了一种危机意识:社交媒体建立的网络,强调的是种族、宗教、政治乃至性取向等身份或观念认同,将这些集合提升到高于国家层面的地步,结果是削弱了国家认同,使美国四分五裂。正是基于这种圈内共识,促使强大的跨国经济抛开了美国而走向世界。这种看法认为,欧美各国的企业领袖和政治精英,现在成了一群全球化的合伙人,他们更关心彼此的意见,而并不在意各自国内普通人的生存和痛痒。
二○○二年,eBay以十五亿美元价格收购PayPal。彼得于同一天辞职,带着当初二十四万美元投资所得的五千五百万美元离开,也带走了一帮技术精英。后来,那些被称为“PayPal帮”的人陆续创立了YouTube、领英(LinkedIn)、特斯拉、SpaceX、Yelp……然而,这些在信息时代赚得盆满钵满的人,却并不满意这样的时代。蒂尔认为互联网公司创业者或多或少都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简称AS,指某种社会交往障碍),所以这类企业的产品本质上都有古怪的反社会倾向。问题归结到这里:发明了现代装配流水线、摩天大楼、计算机和集成电路的美国人不再相信未来。彼得·蒂尔和另外两个朋友一起创立了一家名为“创始人基金”的风险投资公司。它发布的关于未来的在线宣言,头一句话就带着一股怨气:“我们想要飞行汽车,结果却得到了一百四十个字符。”
深夜里徘徊前廊的梦游
有人说《下沉年代》这部作品像是没有终结篇的超长美剧。但是,所有的美剧都是在寻找一个拯救大众的英雄,而这部作品中的人物,他们是自己的英雄,除了自我拯救之外,他们能够有所牺牲去坚持正直与良善。
杰夫·康诺顿的故事无疑是更有深度的《纸牌屋》,这个来自阿拉巴马的政治狂热者,目睹华盛顿褪去了最后的伪装,不再假惺惺地声称“政治并不全是为了钱”。随后,他也投身其中,成为一个握有权力的说客。他自认是个成熟的投资者,但美国的股市已不再是他读商学院时的模样。曾经,穿着蓝色外套的交易员挥动订单大声嚷嚷好让人听到,一次只能进行几笔交易。如今,它成为一个计算机化的赌场,由高频交易员主导—每秒钟进行几千笔交易。连他这样的人都不太明白交易订单背后的逻辑。
二○一○年五月六日下午,杰夫目睹了美国股市在八分钟内暴跌七百点,片刻之间,近一万亿美元灰飞烟灭……不该死的死了,该死的却毫发无损地离场。杰夫终于选择将自己的前半生一切归零,抛弃在华盛顿和华尔街赚取的一切,直接飞去了哥斯达黎加,在徒步八小时后回到酒店,“打开淋浴,没有脱衣服就走进去。站在水流下,让它浸润身体,直到他觉得自己干净了”。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一边照顾自己收养的流浪狗,一边写回忆华盛顿生涯的书,书名是《收益:为何华尔街总是赢》。
当然,更为触动人心的故事,发生在那些默默无闻却始终怀抱希望的普通人身上。那些内陆深处的居住者们,在过去的三十年间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变迁,却一直隔绝于主流叙事之外,只有发生极端事件时才能进入公众视野。那里流淌着沉默的诗歌,真正有心者才能听见。他们有的为被毒品和暴力摧毁的街区而奔走,有的终生为绿色经济的创业梦而奋斗,有的为改变政治秩序而孤掷一注。

電视剧《纸牌屋》海报
有人认为书中唯一的英雄是伊丽莎白·沃伦,那位哈佛法学院的破产法专家戳穿了信用卡公司和银行反复碾压消费者的游戏套路,被称之“大草原平民主义者”。不过我觉得,更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另外一些人物。如,丹尼和罗纳尔,他们出身的家庭和社区都很糟糕,但这对年轻人努力摆脱周围亲友酗酒吸毒的影响,通过辛勤的劳作去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他们摆脱不了天然的劣势:严重缺乏教育,更缺乏资金和来自家人的支持,两人虽然年轻但健康很差,小女儿还患有骨癌。几乎美国穷人常见的疾病他们全有:肥胖、龋齿、肌肉劳损、糖尿病……但他们的良好品质在同阶层中显得十分令人瞩目:他们不喝酒也不吸毒,孩子们举止有礼,夫妇相亲相爱。由于知识局限,他们没有更多的选择,做出抉择也往往短视而冲动,好几次差点陷入无家可归无路可走的绝境。但是他们一家还是相濡以沫地走过来了。慈善机构为这对夫妇修复牙齿,为他们的小女儿支付了治疗骨癌及康复的费用,使他们能够正常生活。丹尼曾经工作过的沃尔玛的主管帮他找到了一份时薪八美元的卸货和补充库存的工作,使他能租住每月七百四十五美元的公寓。他们在坦帕开始将生活的乱麻理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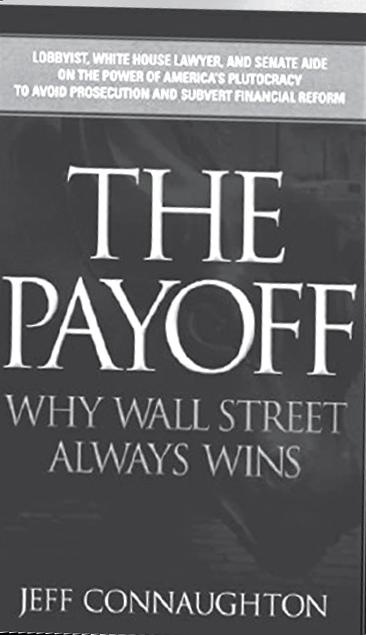
杰夫·康诺顿《收益:为何华尔街总是赢》(The Payoff: Why Wall Street Always Wins)
也难说产业转型和全球化给穷人带来的全是糟心事儿。它起码使产品质量和产量都稳步上升,穷人也受惠于廉价手机、食品和服装。丹尼和罗纳尔不再自己做意大利面了,因为沃尔玛的冷冻食品更便宜,比萨和牛排都比自己家里做要便宜还好吃。可是与此同时,作为蓝领的丹尼,他的工作却越来越难找了。他怀恋之前的电焊工职位,觉得那才是踏实又有成就感的工作,他的梦想是获得贷款开办一家自己的焊接公司(那样他会觉得自己就是个国王)。但现在,传统的蓝领职位基本消失,虽然沃尔玛让他有了经济来源,但他还是不喜欢这种企业,他认为是沃尔玛和石油巨头控制了世界,每当家人去超市购物时,丹尼就留在车里。
通用公司改组时,被迫二选一的塔米·托马斯在二○○六年的最后一天买断了工龄。她想起了那句老话:“上帝关上了一扇门,必定会打开一扇窗。”社区已全面凋败,犯罪问题尤其严重。但就是在扬斯顿这样一座城市里,塔米出人意料成长为一名精力充沛、卓有成效的社区组织者。她自己活了下来,还养大了三个子女,儿子没有加入帮派,女儿没有早早怀孕,三个孩子都进了大学,这才是了不起的成就。
在“解体”的风声雨声中,普通人开始醒悟。退休军官的女儿凯伦·贾洛赫是坦帕中产阶层的一员,丈夫是她的大学同学,两人都是受过培训的工程师,生育了四个孩子,拥有一幢价值二十五万的房子。他们夫妇一向量入为出,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安排生活消费。可是她认识的一对夫妇,收入相对较低,名下却有价值七十五万美元的房子,这让她非常震惊。由于政府放松对银行的监管,次级贷款造成了大量畸形物业。二○○八年次贷危机爆发后,凯伦从联邦政府那里拿到了六百美元经济刺激支票,对此她并不感觉欣慰而是十分不安。她觉得自己这样勤恳老实地做人做事,却要去帮助那些随心所欲花钱的人,是不公平也不可持续的。从政府这种举动来看,他们是不再相信美国人的理想,即辛勤工作才能带来回报,以及量入为出的生活准则。她想起了古埃及的法老,法老王想为自己的荣耀建造金字塔,向人民征税。罗马也是同樣。现在,美国也正在发生同样的事—国家的凝聚力不在于拥有相似的价值观,而是方便捞好处。
持有同样态度的是坦帕的失业建筑工人马特·班德,《圣彼得堡时报》记者凡·西克勒采访了他。马特对能够获得的工作机会来者不拒,但他拒绝申请失业救济。他说:“我会走自己的路,我们追求的是幸福而不是保障。”凯伦们和马特们,他们满怀热情,富于开拓精神又迷茫无助,不甘被抛弃又十分无奈。
不管怎么说,美国这样的国家具有相当务实的底色。社会大众总能在各种对立的观念之中找到平衡点—这或许就是美国人自己所说的美国精神。
不幸的是,现在,将美国人凝聚在一起的那束线圈松开了。地基塌陷了,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遭殃。为什么会这样?结果会怎样?作者没有答案。关于这个解体与救赎的方程,也许每个孤独的个体会有自己的答案。
丹尼说:“我对所有事物的看法就是—如果想改变这个国家。你就得选一个从来没有从过政的人进办公室。选一个像我这样普普通通的老家伙,一个经历过生活的人,一个除了经历生活什么也没有做过的人。”他代表了许多人的一种期待:在建制派以外或许有另一种可能?但这显然不是作者帕克的看法。他告诉我们,那个八月的倒数第二天,共和党人在十五分钟车程之外举办一场耗费一亿二千三百万美元的大会,而哈兹尔一家在付清所有的账单之后,要靠仅剩下的五美元撑到九月一日。硅谷富豪彼得·蒂尔似乎是最明显的人生赢家,但他在意识到互联网革命的内核实则空洞无物后,一头扎进了克服死亡的计划;如果无法实现永生,他将在公海上建立属于自由意志论者的漂流殖民地,将乌合之众甩在身后。
成为百分之九十九的“我们”,在0和1的数字世界,虽然是毫无重量的存在,但如果富有智慧而诚实地将它置于历史记录,是否会让世界不一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