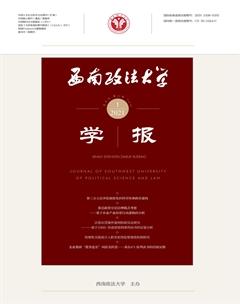财产犯罪中存款归属的认定
苏青
摘 要:随着数字货币时代的来临,存款的流通性逐渐增强。若将存款等同于存款现金,会使案件的判断陷入“两难”,所以应当将存款区分为存款债权与存款现金,但是有关存款债权的占有,以及存款现金所有的归属一直存在理论争议。为解决以上问题,应当明确刑法与民法虽然统一于法律体系,但是因为调整对象、手段与目的的不同,相较于民法,刑法具有相对独立性。基于此前提,刑法的占有是规范占有,不是民法的事实占有,刑法占有的对象可以包括财产性利益。“占有即所有”原则适用于民法,而不绝对适用于刑法;根据以上结论,可以推导出存款人占有存款债权。存款未被取出时,存款现金归属于银行,若存款被非法取出,存款现金的所有权人是存款人,而非取款人。
关键词:存款债权;存款现金;占有;财产性利益;占有即所有
中图分类号:DF625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8-4355.2021.01.11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2020年8月29日,中国建设银行试行了央行数字货币钱包。毋庸置疑,中国即将迎来数字货币时代。数字货币钱包更是显著加快了货币数字化时代的进程。不过,这样的便利也会引起我们的担忧,未来他人只要掌握银行卡账号、密码等个人信息,就有可能非法获取账户内的存款。现实的发展已经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曾经饱受争议的问题,即存款的含义与归属如何认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会直接影响到案件的评价结论。例如,偷换二维码案,①如果存款仅是存款现金且归属于银行,行为人的行为则难以被认定为盗窃罪。因为银行的现金并没有减少,我们无法主张行为人非法转移了“存款”的占有。转而我们只能考虑行为人是否构成诈骗罪,但是,“换二维码”的行为很难被评价为诈骗行为,顾客的付款行为也不是由于认识错误所做出的,因此,诈骗罪的因果链条其实难以成立,这就会导致案件定性陷入两难的困境。所以为顺应时代的发展,我们必须对“存款”的相关问题进行思考。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已生效,“存款疑难”还涉及“刑法与民法发生交叉之时,如何对案件事实进行评价”的问题,
“存款”涉及债权关系、货币所有权、占有等民法问题。所以我们还需要思考刑法与民法的关系。为了走出理论困境,本文从有关存款归属的争议入手,寻找争论的核心问题,并追溯问题的产生原因,为问题寻找解决的思路与方法。
一、有关存款归属的争议与困境梳理
“存款”是一个看似简单,但又极为复杂的概念。它既指存款人
本文所写的“存款人”为银行债权凭证的真实、有效且合法的所有人。与银行之间的债权关系,也与对应数额的现金具有紧密的聯系。刑法学界对于存款的定性与归属都存在较大的争议,导致存款归属主体的明确陷入困境。为寻找解决思路,笔者认为有必要梳理现有的学术观点与争议焦点。
(一)存款是否要区分为存款债权与存款现金
国内学者对存款的含义存在争论。主流观点认为存款同时包含存款债权与存款现金两个概念,例如,有学者认为若存款只能等同于存款现金,会造成处罚的漏洞,从而不利于财产性利益的保护,所以赞同存款包括两层含义。
参见钱叶六:《存款占有的归属与财产犯罪的界限》,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2期,第226页。
有少数学者主张存款仅指存款现金,但是,理由不尽相同。其中有部分学者承认存款人与银行之间存在债权关系,但是,未提及“存款债权”这个概念,而直接将存款等同于存款现金。
参见王世柱:《论刑法上的占有》,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第117页;张红昌:《财产罪中的占有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2页。有部分学者则直接否认存款包括存款债权,并且否认存款债权的占有。他们的主要理由有:第一,德日刑法理论中并不存在类似的概念,而且国内有关存款债权占有的观念尚不成熟;第二,占有的对象是有体物,而存款债权不是有体物,所以存款债权无法成为占有的对象;第三,肯定存款债权的占有可能会造成占有对象的不合理扩展;
参见徐凌波:《存款占有的解构与重建:以传统侵犯财产犯罪的解释为中心》,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第549-550页。第四,在民法上债权难以成为占有的对象,刑法与民法的概念应当保持一致,所以刑法上存款债权也不能被占有。
参见张燕龙:《刑法上存款占有的归属》,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第92页。
笔者更加赞同主流观点,认为应当将存款区分为存款现金与存款债权。因为随着数字货币钱包、支付宝、微信钱包等支付媒介的发展,我们较少采取先支取存款现金,再消费的交易方式,而是直接以存款债权购买生活所需,应该说存款债权作为一项财产性利益,已经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同时,犯罪人侵犯财产的方式也从非法获取现金变化为侵入他人与数字钱包或者第三支付平台绑定的银行账户。所以当前我们不仅无法忽视“存款债权”的存在,还必须对社会现实做出回应,发展与存款债权相关的理论。
(二)存款债权占有与存款现金所有的主体如何确定
在认定“存款”含义二分说的基础之上,又会产生三个新问题:第一,如何认定存款人占有存款债权?第二,能否因为存款人占有存款债权,而同时肯定他所有存款现金?第三,如果否定存款人享有存款现金的所有权,那么存款现金的所有主体又如何确定?
学界对此也存在多种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承认存款人对存款债权的占有,但是认为银行是现金的管理者,由此存款现金应由银行占有与所有;
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下)》,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947页;[日]山口厚,《从新判例看刑法》(第3版),付立庆、刘隽、陈少青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78页。第二种观点主张存款人占有存款债权,并基于存款债权合法支配等额的现金,因此肯定存款现金在法律上由存款人占有;
参见李强:《财产性利益犯罪的基本问题》,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179页。第三种观点强调存款人占有存款债权,但是存款现金由银行与存款人共同占有,至于现金的所有权应当采实质判断,即否定占有即所有原则,主张存款人为现金的真正所有人;
参见陈洪兵:《中国语境下存款占有及错误汇款的刑法分析》,载《当代法学》2013年第5期,第76页。第四种观点则认为存款现金的所有主体应当根据“占有即所有”的原则判断,所以银行占有并所有现金。
参见杨路生:《刑事法理中存款占有问题的教义学逻辑建构——基于刑民一体化的进路》,载《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第111页。
笔者认为,学者们之所以对存款债权是否为占有对象,以及对存款归属如何确定等问题的回答大相径庭,是因为他们对财产犯罪的两个基本理论存在不同理解。其一,占有的本质是事实占有,还是规范占有。因为债权与有体物不同,其不具物理性,所以主张事实占有的学者,则会否定存款债权的占有。但如果认为占有的本质是规范占有,存款债权的占有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其二,“占有即所有”原理在刑法中是否可以当然的适用。主张刑民一体化的学者会认为应当适用,即依据现金的占有状态判断存款现金的归属,但是有学者反对此原则的当然适用,而主张对存款现金的归属进行实质的判断。
二、走出存款归属困境的前提性问题
有关存款归属的纷争其实透露出,学者们对财产犯罪的基本概念与理论存在争议,包括占有的本质、货币所有权的判断准则等等。而这些争议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人们对于刑法与民法的关系依旧存疑,尤其是在面对民法与刑法的共有概念之时,刑法是否要从属于民法?这个疑问是解决存款归属如何确定的前提问题。
(一)刑法与民法的统一
首先,我们可以明确虽然民法与刑法的法律性质并不相同,但是它们同属于一个法律体系。所以在法秩序统一的语境下,刑法与民法统一于法律体系。
其次,我们必须回答“法秩序的统一”意味着什么。目前,学界对于“法秩序的统一”基本形成两点共识:第一,是各部门法的根本目的统一,不是概念、规范、违法判断的统一;
参见简爱:《从“分野”到“融合”:刑事违法判断的相对独立性》,载《中外法学》2019年第2期,第447页;陈少青:《法秩序的统一性与违法判断的相对性》,载《法学家》2016年第3期,第18页。第二,是合法的统一,为维护其他部门法的宗旨,其他部门法中的合法行为,在刑法中不能认定为违法。
参见王昭武:《法秩序统一性视野下违法判断的相对性》,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1期,第179頁;陈兴良:《刑民交叉案件的刑法适用》,载《法律科学》2019年第2期,第166页。从民法与刑法的关系出发,这种“统一”意味着,刑法不能规制一个在民法上被允许的行为,只有被民法评价为不当的行为才可能适用刑法。具体而言,非法获取他人存款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具有民法上的“不当性”。如果行为还符合犯罪构成,就需要进入刑法的评价范围。但是民法允许的行为,比如紧急救助行为,《民法典》明文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责任,那么刑法不可能将此类紧急救助行为评价为危害行为或者犯罪行为。
最后,我们还要探究刑法与民法的关系是不是只有“统一”,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刑法的判断是不是都要从属于民法?如果回答还是肯定的,刑法在解释违法行为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要件时,是不是还须优先进行民法上的判断?如果需要,那么从司法适用层面而言,这显然不符合刑法适用的逻辑,还可能导致刑法惩罚与预防犯罪的目的无法实现。此外,从立法层面而言,当前刑法所规定的许多罪名,已经超出了民法所能涵盖的内容,比如《刑法修正案(九)》规定的一系列预防性罪名,在民法上并不能找到对应的内容。笔者认为,这些现象已经说明刑法与民法的关系不只有“统一”的一面,二者也不是简单的从属关系,刑法具有自身的独立性。更关键的问题是独立性的来源是什么,以及刑法如何独立?
(二)刑法的相对独立性
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刑法具有独立性,其中部分学者主张犯罪认定的过程体现了独立性。例如,有学者强调刑法不是对违反民法、行政法的行为进行处罚,而是依据犯罪构成判断行为是否应受刑法处罚;
参见简爱:《从“分野”到“融合”:刑事违法判断的相对独立性》,载《中外法学》2019年第2期,第453页。还有学者提出民法强调对法律关系的分析,而刑法注重从行为入手,判断行为是否符合构成要件。
参见陈兴良:《刑民交叉案件的刑法适用》,载《法律科学》2019年第2期,第168页。
还有部分学者主张独立性来源于刑法的规范目的。有学者认为,刑法在一些重要问题的判断上之所以与其他部门法不同是因为刑事违法性判断的独立性,以及其自身独特的规范保护目的。
参见吴镝飞:《法秩序统一视域下的刑事违法性判断》,载《法学评论》2019年第3期,第49页。还有学者主张决定因素是法律的功能不同,如合同法的功能是保护交易安全,侵权法的功能是为了让侵权行为人承担责任,而不是惩罚他,而刑法的主要功能是惩罚与预防犯罪。
参见李兆阳:《犯罪对于私法“二次违法性”之批判》,载《中国刑警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第51页。
其实,学者们的观点并不存在冲突,只是从不同侧面说明刑法对事实的认定不能从属于民法,而是要依据自身的目的与功能做出判断。笔者也赞同各学者的观点,但想强调的是,刑法的独立性是在法律部门相统一的前提之下阐述的,因此这种独立性是相对的,即刑法相对于民法的独立性。
至于刑法相对于民法的独立性的来源,综合各学者的观点与笔者的认识,可以总结为刑法的调整对象、调整手段与目的。其一,民法的调整对象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而刑法调整的是犯罪与刑罚关系。
学界对于“刑法的调整对象”存在较大争议,包括广泛社会关系说、重要社会关系说、罪刑关系说等。笔者认为,这些结论并不冲突,只是思考的层面有所不同。所以本文不对各观点进行比较,而是从最能体现刑法与其他法律不同的调整对象出发,采罪刑关系说。所以在评价具体案例的时候,民法关注的是法律关系与法律行为,刑法则是聚焦于定罪量刑,主要解决如何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指导下,落实“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其二,刑法的调整手段具有权利剥夺性与强制性,是对行为的否定,而民法以“意思自治”为基石,以肯定法律行为的效力为导向,违约人和侵权人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自由地选择承担责任的形式,其承担责任的方式也不具有剥夺性与强制性。其三,民法的目的是为民事主体提供安全、公平、便捷的交易环境,促进商品的流通。然而刑法以“实体正义”为追求,其目的是惩罚犯罪,维护秩序。
有关刑法如何独立于民法的问题,可以从“法秩序如何统一”中寻求解答,即只要保证两部法律对行为合法与否的判断不出现矛盾,对于共用的概念与原理,二者可以根据独立性的来源做出不同的解释,而且判断违法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也应当以行为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以及《刑法》第13条为标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应当以辩证的眼光看待两者的关系,刑法与民法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之中是统一的,因为它们不仅是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部分,以保护人民权利,促进社会发展为目标。但是两者各自的调整对象、调整手段与目的又决定了它们需要从不同层面对社会进行治理,理所当然,两者对同一事实或者共有概念的规范判断就有可能出现差别。
需要注意的是民法的合法行为不可能被刑法评价为违法。
三、应基于刑法相对独立性认定存款的归属
在确定刑法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前提之下,可以对导致存款归属产生争议的根本问题,如占有的本质、占有即所有原则等,进行刑法的解释,从而推理出存款归属的认定方法。
(一)存款债权占有的推理验证与主体明确
要破解存款债权是否可以被占有,以及被何人占有的难题,首先应当回答“占有”的本质是事实占有还是规范占有、财产性利益能否成为占有对象等重要问题。
1.占有的本质是规范性占有
在大多数时间里,“占有”主要作为一个民法概念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大部分民法学者,比如张双根老师,强调从事实的层面观察占有人对标的物的控制与支配,从而判断占有的有无,以及占有的主体,而不考虑背后的权利来源。
参见张双根:《物权法释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45页。传统刑法理论也认为占有指对财物的事实上的支配状态,而刑法的任务是保护此种状态。
参见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09页。所以曾经在大多数情形中刑法与民法相同,采取事实占有说,以主体对物是否具物理性支配为判断标准。
不过传统理论也承认刑法与民法存在差异,刑法不承认死者的占有、间接占有与占有改定。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新型犯罪的增加,在刑法理论界规范的占有、观念上的占有等概念被逐渐提出。正如有学者所描绘的那样,在财物流转速度不断加快、交付手段愈加便捷的今天,以实物或者货币为支付手段的交易逐渐被有价证券、刷卡付款、电子支付等方式所取代,占有有无的判断不再依赖于对实物的控制,而在于对社会性因素的考虑。
参见孙运梁:《选言式而非选连言式:财产犯中占有概念的界定路径》,载《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1期,第36页。有学者更是犀利地指出,随着新型财产犯罪案件的出现,事实性的占有概念愈发表现得独木难支。因为新型侵财行为的犯罪对象大多为不具实体的财物,执意坚持从事实控制的角度判断占有,根本不利于司法机关对新型案件的定罪与量刑,亦有碍于刑法对财产的保护。
参见马寅翔:《占有概念的规范本质及其展开》,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3期,第74页。
随着占有的观念化,刑法学界对占有的性质产生了争议,事实占有与规范占有究竟哪一个才是判断占有的实质要素?笔者将在下文详细叙述。
第一种学说认为规范的占有为判断占有存在与否的关键,即可以通过规范的占有独立地判断主体是否占有某财物。
规范或者观念的占有是指刑法上的占有不再限定为物理上的自然支配,而涉及社会观念的判断,即根据日常生活判断支配可能性是否存在。
参见陈兴良主编:《判例刑法教程(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05页。占有的观念化使得占有是否存在的判断变得复杂,时而扩大了占有的情形,时而又缩小了占有的现象。在某些情形中,虽然主体在事实上未支配财物,但是根据社会一般观念,财物其实已经被他占有,或者在某些情况下,盡管已经存在事实上的控制,但是规范占有却不成立。例如财物被甲以物理手段实际的支配,但是从观念占有的角度,可以推断出乙控制着财物之时,财物应当被乙所占有。
参见黎宏:《论财产犯中的占有》,载《中国法学》2009年第1期,第112页。有学者清楚地揭示了占有的本质即是主体对物的规范性支配,物理性的支配仅是一种表象,规范的占有可以通过与财物的特别事实关系来体现,占有本就是一个规范概念。
参见黄小飞:《财产罪占有的法理——对“占有规范化”批判论之否定》,载《河北法学》2019年第1期,第176页。
第二种学说认为判断占有是否存在的必要要素依然是事实的占有,规范的占有仅是一种补充要素,不能作为独立地判断标准。不过,仅以物理性的支配来判断占有有无的观点已几乎不再出现。
在占有观念化的趋势中,部分学者开始提倡事实占有作为判断材料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有学者主张占有的存在判断必须以客观事实为基础,而这种客观事实是一种排他性的“壁垒”,可能表现为财物具有排他性状态或者财物处于排他性的场所之中。
参见白洁:《刑法中占有的认定》,载《政治与法律》2013年第12期,第32页。还有学者主张占有的本质具有二重性,包括事实与规范两种要素。但是事实控制是占有存在的必要条件,而规范要只起到增强主体在事实层面对财物的支配和控制的作用,或者作为消极判断因素,阻碍占有的成立,而承认存款债权的占有会将占有概念推向纯粹规范化的歧途。
参见车浩:《占有概念的二重性:事实与规范》,载《中外法学》2014年第5期,第1193页。有学者对占有二重性的观点表示赞同,即事实性支配为判断占有有无的必要要素,而规范占有仅为补强与补充要素,不过却同意存款债权的准占有,与上述观点有些矛盾。
参见梁云宝:《财产罪占有之立场:缓和的事实性占有概念》,载《中国法学》2016年第3期,第181-183页。
第三种观点类似于折中说,同时承认事实占有与规范占有。有学者认为事实与规范都不是必备要素,应当根据哪一种占有更具说服力来判断占有。
参见孙运梁:《选言式而非连言式:财产犯中占有概念的界定路径》,载《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1期,第39页。
经过不同观点的对比,笔者认为,占有的本质是规范性的支配,事实性占有只是规范性支配的表象,正如康德所说若要探究“占有的本质”,我们需要撇开所有经验占有中的时间和空间条件。真正的占有并不是物理上的“拿住”或“持有”,而是“我占有它,虽然它已经不在我手上。”
参见[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56-60页。康德的这番话已经直指占有的性质,占有的判断应当是规范的、理性的,而非仅仅依靠时间与空间等表面现象。笔者不赞同“占有本质具有二重属性”,因为这种观点很容易造成事实占有(表象)和规范占有(本质)的混淆。
有关占有的本质,刑法的结论之所以不同于民法,是因为刑法与民法具有不同的目的与调整对象。民法主要调整的是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中所形成的法律关系,面对的案件情景主要是日常交易。而人们在日常交易的过程中,需要通过“事实”来快速地判断对方是否占有标的物,从而相信对方具有处分权,而不是大费周章地调查对方是否支配标的物。但是刑法以规制财物被非法转移的行为为对象,以保护公民的财产为目的。如果只把事实占有纳入财产犯罪所保护的对象,明显会造成刑法对财产保护不充分。因为随着数字货币时代的来临,公民无法再通过事实占有表明自己对财产的支配。坚持事实占有的观点会导致我们不能承认公民对财产的合法支配,也无法对行为人非法转移财产的行为进行较为合理的评价,陷入认定的困境,所以我们应当承认刑法的占有是规范占有,事实占有只是一种表象。
2.占有的对象包括财产性利益
在占有本质为规范占有的前提下,我们应当按图索骥,思考行为人是否可以占有财产性利益。财产性利益为权利人能请求他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进而享受相关利益,
王骏:《刑法中的财物价值和财产性利益》,载《清华法学》2016年第3期,第50页。包括以债权或者物权为来源利益。
根据财产犯罪种类的不同,日本刑法典将侵财罪的犯罪对象区分为财物与财产性利益,并直接在刑法条文中规定财产性利益不能被他人所盗窃,仅强盗罪、诈骗罪与敲诈勒索罪的犯罪对象包含财产性利益。德国刑法亦对财产犯罪的行为对象作了区分,划分为财产与物。与具备物理性的物不同,财产是指被害人的具有经济价值的利益。
Vgl. Wolfgang Mitsch, Strafrecht Besonderer Teil 2,SpringerVerlag, 2003,§6 Rn. 49,转引自李强:《财产犯罪法律规定的比较分析——以日本、德国、中国刑法为对象》,载《法律评论》2019年第6期,第73页。传统学说认为,盗窃罪与侵占罪的对象则仅包含“物”,而诈骗、背信以及敲诈勒索类犯罪的犯罪对象确定可以包含财产。
参见Vgl.RGSt 22,2(3);RGSt 39,239(243).转引自王钢:《德国判例刑法分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65页。我国刑法未对二者加以区分,因此,“财物”一词的涵摄范围一直存在争议。有学者主张,我国刑法在侵犯财产犯罪一章中仅使用“财物”来指代侵财行为的对象,对财产性利益未做任何规定。但是,财产性利益的经济价值愈加突显,它可以直接与现金或者其他财物“挂钩”,应当对其进行保护。
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下)》,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932页。因此,在不修改法律的前提下,“财物”的涵摄范围应当包括财产性利益。不过,还有学者反对此种扩张解释,认为其实质为类推解释,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参见姚万勤、陈鹤:《盗窃财产性利益之否定》,载《法学》2015年第1期,第52页。
笔者认为,“财物”一词可以囊括财产性利益,此解释结论未超出国民的预测可能性,不是类推解释。首先,《刑法》第92條已规定公民私人所有财产包括储蓄(即对银行所享有的存款债权)、股票、股份等财产性利益。其次,应当对《刑法》侵犯财产犯罪章中所使用的“财物”一词进行客观解释。传统的观点主张财物一般指有体物,因为刑法上的占有以事实占有为本质,所以财物需要具备物理性。但是,随着现代私人财产承载载体的发展,从货币到账户存款,再到当下的支付宝、微信钱包、数字货币钱包,物理性已经不再是财物的必备特征。因此,我们也应当对财物进行扩张解释,将财物解释为“具有财产性质的利益”。因为某些财产性利益与财物具有相同的必要特征,它可以被有效管理、亦可被转移至不同的账户,损失它将给被害人造成相当程度的损失。相对于“财物”这一概念而言,财产性利益的“加入”仅是扩大其外延,并没有改变概念的内涵。因此,将财产性利益解释为财物并没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其实,德国已经有司法判例主张某些物品承载的经济价值亦可以成为非法所有的对象,比如存折所承载的债权,表明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盗窃罪与侵占罪的对象。德国刑法曾确立物的价值说,将物与物的价值相分离,主张犯罪主体可以非法占有财物所蕴含着的价值,而非财物本身。
参见Sauer,Der Zueignungsbegriff,GA 63,284ff;Kindhaeuse in :Kindhuser/Neu mann/Paeffgen(Hrsg.), Nomoskommentar zum StGB,3. Auflage.2013,§242,Rn.76,m.w.N. 转引自王莹:《论财产利益可否成为盗窃罪行为对象——“介入行为标准说”之提倡》,载《政法论坛》第4期,第156页。不过,我国有学者则主张因为财产性利益,比如债权、用益物权等,都是无实体状态的法律权利,不可能被转移,所以占有的对象不可能包括财产性利益。有学者则认为,将财产性利益归为占有的对象还会导致盗窃罪处罚范围的扩张。
参见刘明祥:《论窃取财产性利益》,载《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8期,第71页。有学者却反对此种观点,认为财产性利益是占有的对象,也可以被转移占有,即利益的取得与丧失,而且即使占有规范化,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结论还会受到其他构成要件的限制,不会导致盗窃罪处罚范围的扩张。
参见王骏:《刑法中的财物价值和财产性利益》,载《清华法学》2016年第3期,第54页。
笔者认为,占有的对象可以包括财产性利益。大多数学者不愿改变占有的传统的对象,主要是担忧某些不构成犯罪的盗用、侵害财产性利益的行为亦会被评价为犯罪。这样的忧虑其实是多余的。一方面,占有对象的扩张并不会改变占有本身的含义,行为人如果要占有财产性利益,其依然要对财物形成社会观念上的支配与控制。如果要达到非法转移占有的目的,行为人依然要排除他人占有并建立新的占有关系。比如,行为人盗窃债权人的欠条,向债务人主张债权的行为(谎称自己受债权人之托,帮忙收取钱款),即使支持财产性利益可以被占有,也不意味着行为人的行为将被评价为盗窃他人的债权(仅有针对债权人的还款构成诈骗罪的可能)。因为行为人虽然盗窃了他人的欠条,但并没有达到社会观念上对债权的支配,债权人依然对债务人享有请求权,其实质利益并未受到侵害。另一方面,行为具体构成何种犯罪还要受到其他构成要件的限制,对象的扩张并不会导致犯罪圈的无限扩大。例如,盗用行为,行为人似乎造成了被害人利益的丧失,但是盗窃罪必须以非法所有为目的,行为人“用”的行为表明其仅具有利用意思而无排除意思,并不会构成盗窃罪。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物品的利用价值是否也可以被评价为财产性利益?上文提到财产性利益是可以通过请求权的行使而获得利益,而物品的使用价值与数字货币、支付宝里显示的余额、有价证券所象征的等财产性利益具有本质的区别。例如,我们似乎可以将他人盗用自行车的行为抽象为对财产性利益的非法转移,然而,客观上行为人转移他人自行车使用权的行为就是使用自行车本身的行为,不能独立于自行车被非法转移,所以物的使用价值无法独立于物品本身被转移或者管理,并属于财产性利益。
诚然,从主张对“财物”进行扩张解释,到主张占有的对象可以包括财产性利益,再到承认财产性利益可以被转移,每一步都是对传统理论的新建构,以及对当下新型财产犯罪的回应。笔者认为,与其不断修改分则,不如完善刑法基础理论,使得概念体系化与科学化。不过,笔者亦赞同为了防止犯罪圈的不断扩张,我们需要对财产性利益自身做一些限制,追问财产性利益的刑法保护边界应当在何处?有学者提出“介入行为说”,认为行为人若形成了对财产性利益的占有,行为人在实现财产性利益的过程中则没有再实施介入行为的需要。例如,欺诈、虚构他人身份证件等行为。
参见王莹:《论财产性利益可否成为盗窃行为的对象——“介入行为标准”说之提倡》,载《政法论坛》第4期,第158页。我们也可以根据实现财产性利益是否需要介入行为(欺骗行为)来判断某项财产性利益是否被控制和支配,是否形成了需要刑法保护的占有。因为“介入行为说”不以事实占有为必要条件,不僅与占有的规范本质相契合,还明确提出了如何判断他人是否占有财产性利益的标准。除此之外,还有学者提出,可以成为占有对象的财产性利益必须具有以下三点特征:可转移性、确定性、即存性,并且被害人灭失此种利益会导致其财产遭受损失。
参见王骏:《刑法中的财物价值和财产性利益》,载《清华法学》2016年第3期,第55-56页。笔者认为这三个特点实质上就是我国刑法“财物”的特点。如果基于社会发展需要,我国将财产性利益解释为财物的一种,那么可以成为占有对象的财产性利益应当具有上述三个特征,此为当然的解释结论,笔者认为“介入行为说”才更能体现财产性利益占有的特殊之处。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财产观念的转变以及交易方式的进步,我们应当不断对刑法的基本理论进思考,并且主动地对基本概念进行客观解释。为了应对新型的财产犯罪,更为了保护公民的财产性利益,应当认清占有的本质是规范占有,所以占有成立与归属的认定应以社会一般观念为准,判断主体对对象是否形成控制与支配。占有的对象也不再局限于有体物,还可以包括财产性利益。不过刑法所保护的财产性利益应当符合财物的基本特征,并且还要利用“介入行为说”判断主体是否占有财产性利益。
3.存款人占有存款债权
经过对占有本质与对象的理论梳理,我们将在承认占有的本质是规范占有,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被占有对象的前提下,对存款债权的占有进行讨论。
存款债权是典型的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占有的对象。第一,它符合财物的必要特征,存款债权可以进行转移,具有管理可能性,还具有明显的价值性,丧失存款债权会对他人造成损失。第二,以“介入行为说”进行验证,存款债权亦可以成为能够被占有的财产性利益。因为存款人持有本人的且真实有效的借记卡或者存折,其不用实施欺骗行为即可行使对存款的请求权,所以存款人可以对存款债权形成占有。不过,有学者并不赞同这种观点,认为存款人在取款之时需要输入密码,而银行对密码的审核为一种实质性的审查,因此,储户对存款并没有实质的控制力,承认存款债权的占有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参见车浩:《占有概念的二重性:事實与规范》,载《中外法学》2014年第5期,第1219页笔者反对此观点,银行给存折或者储蓄卡设置密码的目的是确保使用存款凭证的主体是存款账户本人,是出于对账户安全的考虑,这与判断存款人是否控制存款的关系不大。只要存款人使用的是本人真实有效的银行卡或者存折,就可以形成对存款债权的占有。存款人输入密码提取存款的行为便类似于一般人拿钥匙从柜子中拿取现金的行为,我们并不会因为一般人需要打开柜子锁才可以拿到现金,而否定一般人对自寄柜子中财物的占有。虽然不得不承认储蓄银行与柜子具有较大的区别,但是就保管这一功能来说,两者本质上是相同的。
第三,以社会一般观念为判断标准,存款人对存款债权的占有虽然无法以物理性的支配表现出来,但是随着网络及科技的发展,存款人可以通过ATM机、支付宝、数字货币钱包等媒介实现对财产性利益排他性地支配,而且存款人对存款债权凭证(银行储蓄卡或者存折)的占有,其实亦体现了他对存款债权的控制力与支配力。不过,笔者认为,若是第三人占有他人的存款债权凭证,即使其知道他人的账户与密码,也无法形成对他人存款债权的占有,因为他需要输入正确的账户密码(介入行为),让银行误以为他是存款账户的真正所有人,所以存款债权无法成为他占有的对象。
(二)存款现金所有的原则批判与归属确定
基于民法上“占有即所有”原则,部分学者认为现金的占有人即现金的所有人。例如,有学者认为按照民法基本原则,货币属于特殊的种类物,就应当认定为银行占有并所有了货币。
参见张燕龙:《刑法上存款占有的归属》,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第85页。针对特殊种类物的“占有即所有”原则似乎成为一条普遍适用的公理,它使一切问题简单化、公式化,但是,我们必须对这样的“便利”保持警惕,对其进行不断地发问与思考,探究“占有即所有”的真实含义,并且追问刑法是否与民法一样适用此原则。为明确存款现金的归属,我们首先要区分存款现金的状态。在生活中,存款现金的状态基本可以被划分为未取出与被取出状态。在未取出状态,存款现金由银行保管,在被取出状态,存款现金则由收款人取得。其次,还要思考在两种状态中,是否当然地适用“占有即所有”原则,以认定存款现金的所有人。最后,根据以上结论确认存款现金的所有权归属。
1.对“占有即所有”原则的反思
“占有即所有”原则最早由德国学者提出,目的是简化货币的交易过程,以实现货币作为高度等价物的功能。但德国学者明确表示此原则并非绝对的,在某些领域(比如盗窃)不能适用。
参见Vgl. Kaser, Das Geld im Sacherecht, AcP 143 (1937) 1 ff,转引自朱晓喆:《存款货币的权利归属与返还请求权——反思民法上货币“占有即所有”法则的司法运用》,载《法学研究》2018年第21期,第119页。在民法上,占有之所以具有推定权利的机能,旨在避免占有人为了证明占有的权利源泉是否存在或者正当而花费大量的精力,浪费社会资源与时间,具有节约成本的效果。同时,第三人也无须调查占有主体是否为有权占有,即可基于对占有外观的信赖与占有人进行交易,此为占有的公信力。
参见谢在全:《民法物权论》,新学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486页。因此,主体若是占有货币,便推定主体对货币享有所有权。
不过“占有即所有”并不是一项确权的原则,而是一项证据原则,具有的是推定效力而非确认效力。这项原则却被绝对化,还被用于解决存款现金的归属认定问题,使得被侵害的存款现金无法受刑法的保护。例如,在错误汇款案中,有的学者认为根据货币“占有即所有”的原理,该笔现金的所有权归属于收款人,故难以成立侵占罪。
参见杨路生:《刑事法理中存款占有问题的教义学逻辑建构——基于刑民一体化的进路》,载《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第114页。
笔者不赞同以“占有即所有”原则认定存款现金的归属。因为这样的认定思路不仅忽略了存款现金的特殊性,还使得存款现金不能受到与一般财物相同的刑法保护。第一,与不特定的货币不同,存款人对账户内的存款可以根据债权凭证的交易记录将存款特定化,即根据存款来源区分特定的存款现金。第二,存款不能受到与普通动产相同程度的法律保护,着实令人疑惑,一般的动产若被错误地放置在他人之处,原占有人享有基于所有权的原物返还所有权。当他人以非法所有为目的,将一般动产占为己有之时,原占有人还可以侵占罪起诉他人。然而根据“占有即所有”原则,非法所有他人存款现金的行为却不能被认定为犯罪。
在刑法中“占有即所有”原则并不与民法保持完全一致。刑法有时更加注重保护合同的宗旨,比如,当金钱委托给他人保管之时,金钱所有权应当属于委托人,受托人随意使用可能构成侵占罪。此时寄托的现金与寄托的物品受到同等的保护。
参见[日]佐伯仁志、道垣内弘人:《刑法与民法的对话》,于改之、张小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15页。究其原因,在于民法与刑法调整对象与目的的差异。在调整对象方面,民法所调整的范围是正常交易,强调货币的流通功能,而刑法关注的是非正常的交易,注重双方之间的侵害与被侵害问题。就刑法与民法的目的而言,民法为保证交易的信赖基础,并为了给第三人提供安全的交易环境,需要关注存款现金的归属判断可能对第三人产生的效力。然而,刑法并不关注行为人与被害人以外的第三方,因此,占有的推定效力、公信力在刑法中并不重要。
2.未取出的存款现金归银行所有
在存款未取出的状态下,存款现金由银行所保管。依据社会的一般观念,银行占有存款现金,而存款现金的所有权归属则存在争议。学界通常认为,存款现金亦为银行所有,不过有部分学者持不同的观点,例如,有学者主张存款人对存款仍然享有所有权。
参见孟勤国:《物权法的现代意义》,载《湖北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第2页。有学者甚至区分了存款现金与存款所有权,存款是以数字为载体的、具有与货币相同支付功能的无体物,由此主张银行对存款现金拥有所有权,而存款人对存款享有所有权。
参见夏尊文:《存款貨币财产所有权研究》,载《北方法学》2011年第5期,第51页。
相较于通说观点,其他观点都存在着些许不足。首先,若是主张存款人所有现金,此结论与现状不符,也不利于银行业的发展。银行确实享有对存款现金的所有权,其可以通过放贷以获取利益。若是将存款现金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不利于现代社会现金的流转,况且贷款人想借入的不可能仅是存款现金的使用权。
其次,公民将现金存入银行也是为了享有利息,而利息的来源就是银行的放贷行为,所以大多数公民都能够认清自己将存款存入银行所要带来的收益和风险,也明白“存入”意味着存款现金变为银行所有。
再者,将存款列为所有权的对象会使得所有权与债权发生纠缠,因为上述学者所提到的“存款”一般为活期存款,本质是存款人可以任意时间支取的“强大”债权,而将债权列为所有权的客体违背大陆民法的基本理论,也不符合我国《民法典》的规定。
最后,笔者认为存款之所以会被学者提倡成为所有权的客体,一是因为存款人与银行之间的特殊关系。根据银行与存款人之间的储蓄合同,银行可以利用存款进行放贷等活动,而存款人无需银行的同意,可以随时请求银行支付其活期存款,或者直接将存款作为一种支付方式。正如有学者所说:“存款已经替代纸质货币成为新的等价物,是属于存款人的即存的支配性利益。”
参见陈承堂:《存款所有权归属的债法重述》,载《法学》2016年第6期,第101页。与一般债权的实现不同,存款人可以对于标的物单独实现自己的意思,无须依靠他人的意思协作,
参见金可可:《论支配权概念—以德国民法学为背景》,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2期,第77页。反而具有行使物权的特点。二是因为存款人对存款债权享有支配利益,体现了“债权物权化”的趋势。债权所表现出的支配性与控制力使其成为目的本身,而不是取得权利的手段。如今经济价值并不仅由“物”来体现,而是在于一个债权向另一个债权不断地移动。
参见[日]我妻荣:《债权在近代法中的优越地位》,王书江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存款债权并不仅是手段,而是我们许多经济交往的目的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存款债权的支配性利益可以看作是对存款人的一种“补偿”,存款人放弃了对存款现金的所有权,却获得了具有支配性质的债权。银行享有存款现金的所有权,却要受到存款人取款自由的约束。
3.存款被取出时现金所有的判断
根据取出主体的不同,存款被取出状态可以被区分为以下两种情况:第一,存款被真实的存款人合法取出。第二,存款现金被虚假或者错误的取款人(以下简称为取款人)非法支取,并且他拒绝向存款人返还现金。在第一种情况中仅存在一对法律关系,法律事实只在银行与存款人之间发生。银行将存款现金交付给存款人,存款现金的所有权亦一并转移,存款现金的归属并无争议;在第二种情况中,有学者认为,根据货币“占有即所有”的原理,该笔现金的所有权归属于取款人。
参见杨路生:《刑事法理中存款占有问题的教义学逻辑建构——基于刑民一体化的进路》,载《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第114页。笔者不赞同此种观点,认为取款人并不能根据简单的效力推定原则而所有现金,并且由此否定他的违法行为有构成犯罪的可能。
占有外观具有的是推定效力、证据效力、公信力,而非确权效力。在存款被取出的状态下占有能够赋予取款人对于存款现金的权利外观,但是,不能用于确定存款现金的实质归属。我们应当具体分析存款现金与存款债权的流转过程,思考存款现金的归属应当如何确定。
取款人将存款现金取出,为了保护第三人的交易安全,当货币置于流通领域之时,“占有即所有”原则有效,第三人有理由基于占有的权利外观,认为存款现金为取款人所有,并与之进行交易,此亦为占有公信力的体现。但是,笔者认为此种推定效力、公信效力并不当然地作用于存款人与取款人之间。因为存款人与取款人的法律关系具有相对性,在相对法律关系之间两者的权属关系是明确的,并无利用占有推定的必要。在存款人与取款人的双方法律关系之中,我们需要对存款现金的所有权进行实质地判断。由于存款现金是被取款人非法领得,所以存款现金的所有权并未转移给取款人,而是归属于存款人。正如有学者指出,在存款人非自愿或者未按照其真实意愿转账,或者存款人的现金被非法取出的情形之下,取款人不具有对存款的最终实质性权利,其无权对所占有的存款进行如所有者般地处分,存款人才对存款具有最终实质性的权利。
参见陈洪兵:《中国语境下存款占有及错误汇款的刑法分析》,载《现代法学》2013年第5期,第77页。
因此,在民法领域,我们应当适用“占有即所有”原则,以维护动态的交易安全,鼓励交易的进行。而在刑法体系之中,“占有即所有”原则不再是万能的公式,我们应当明确存款现金的实质归属,以保护静态的财产安全。
四、财产犯罪中存款归属的认定思路
在数字货币时代,存款债权作为一种财产性利益,它所蕴含的价值不言而喻,2020年“双十一”购物节,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成交额突破4982亿元,这意味着成千上万的消费者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将存款债权直接用于消费,总价值已经高达千亿元。如果我们将非法获取他人账户内存款的事实,仅作为民事案件处理,显然不利于对人民财产安全的保护,不符合我国新时代的法治精神,也不符合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目的。因此,刑法作为法律体系中惩罚与预防犯罪的法律,应当对这类侵犯公民财产的行为进行规制。不过,若运用传统财产犯罪的基本理论或者民法理论,解决存款归属的问题,会导致刑法的规制陷入困境,所以基于刑法的相对独立性,以及前文的论证结论,笔者提出以下解决思路。
(一)基于规范占有确定存款债权的占有主体
存款债权是公民重要的个人权利,他人非法侵害存款债权的行为会给公民带来较大的损害。为依法评价侵害存款债权的行为,我们必须对存款债权的状态进行分析,判断存款债权是否可以成为占有对象,然后在肯定存款债权能够被占有的基础之上,确定存款债权的占有主体。
以演绎推理的三段论模式为逻辑依据,笔者提出基于规范占有认定存款债权占有主体的解决思路。首先,占有的本质是规范占有,不属于有体物的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占有的对象。因为刑法以罪刑关系为调整对象,以惩罚犯罪、保护被侵害的权利为目的,而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以保护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为宗旨。将占有本质理解为事实占有,在民法上确实有利于维护市场交易的稳定,但是,在刑法上可能会造成被侵害的财产性利益无法得到充分保护,或者导致侵害财产性利益行为的定性出现疑难。所以在刑法体系中,占有的本质是规范占有,不以物理性的支配为必要条件。只要公民控制或者支配财产性利益,就可以认定公民占有财产性利益,他人非法转移财产性利益的行为可以构成盗窃罪、抢劫罪等转移占有型财产犯罪。其次,存款债权是财产性利益,由于数字钱包、支付宝与微信钱包等支付工具的出现,公民可以利用支付工具随时转移、管理存款债权。事实表明存款债权的流通性逐渐增强,是具可转移性、即定性与确定性的支配性利益,属于刑法上典型的财产性利益。再次,基于前两个结论,我们可以推导出存款债权可以成为占有的对象。最后,可以借助“介入行为”理论,判断哪一主体对存款债权形成了支配力与控制力。对于合法、真实的存款人而言,因为他不需要介入任何欺骗行为,便可以通过支付宝、数字货币钱包等媒介实现对财产性利益排他性的支配,所以存款人占有存款债权。
(二)在相对法律关系中明确存款现金的归属
民法为维护市场交易的正常运转,需要考虑市场的交易成本与交易安全,所以民法上的占有具有推定效力与公示效力。民事主体可以依据他人占有的权利外观,相信他人的占有是合法占有与有权占有,从而与对方进行交易。对于现金而言,两种效力就被归结为“占有即所有”原则。发展到今天,“占有即所有”原则有时候甚至被作为确权原则,以认定存款现金的占有人即所有人。
然而,刑法的调整对象是罪刑关系,涉及的主体是犯罪人与被害人,并不涉及第三人,不需要考虑存款现金归属的判断结论对市场交易的其他民事主体产生了何种影响。因此,在财产犯罪中存款现金归属的认定不应以民法的“占有即所有”原则为依据,而应在侵害与被侵害关系之间,也就是存款人与取款人之间,确定存款现金的所有人。
由于存款现金是否被取出,会决定我们是在银行与存款人,还是在存款人与取款人的相对法律关系中判断存款现金的归属,从而影响最终的认定结论,所以笔者将存款现金区分为未被取出状态与被非法取出状态,再分别认定处于不同相对法律关系中的存款现金的所有人。一是存款现金未被取出之时,存款现金由银行所有。因为一旦存款人将现金存入银行,银行便占有存款现金,可以使用现金进行放贷等经营业务,所以银行已经成为存款现金的所有人。二是存款现金被非法取出时,在存款人与取款人的相对法律关系中,存款人才是现金的所有人。因为取款人以欺骗或者其他违法手段侵害了存款人的利益,使存款人遭受了财产损失。为惩罚非法转移他人财产的行为,保护受到利益损害的存款人,我们不能依照民法中的“占有即所有”原则,仅以占有的公示效力与推定效力,主张取款人因占有取得对存款现金的所有权。而是应当坚持刑法的相对独立性,认定在存款人与取款人的关系中,存款现金归属于存款人,然后对取款人的行为进行刑法上的定性。
The Identification of Deposit Ownership in Property Crime
SU Qing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digital currency era, the liquidity of deposits is gradually enhanced. If the deposit is still equal to the deposit cash, the judgment of the case will fall into a “dilemma”. Therefore, the deposit should be divided into deposit creditors right and deposit cash. However, there are theoretical disputes about the possession of deposit creditors right and the ownership of deposit cash. In order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we should make it clear that although criminal law and civil law are unified in the legal system, compared with civil law, criminal law is relatively independent because of different adjustment objects, means and purposes. Based on this premise, the possession of criminal law is normative possession, not factual possession of civil law, and the object of criminal law possession can include property interests. The principle of “possession is ownership” is applicable to civil law, but not to criminal law. When the deposit has not been withdrawn, the deposit cash belongs to the bank. If the deposit is withdrawn illegally, the owner of the deposit cash is the depositor, not the payee.
Key Words: deposit creditors rights; deposit cash; possession; property interests; possession means ownership
本文責任编辑:李晓锋
青年学术编辑:张永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