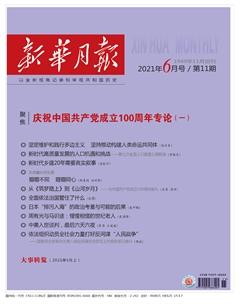中国人都应该学习一点经济学
朱绍文教授在85岁高龄时,出版了《经典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一书,概括总结了几十年研究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历史的部分成果,对我们所有经济学者来说,这是一份极为可贵、值得认真一读的传世之作。
在此书的封面上,印有朱先生最为推崇的三位经典经济学大师的头像,他们是英国的亚当·斯密,德国的弗·李斯特和卡尔·马克思。为了与经济学中通常所说的“古典经济学”相区别(那个词特指斯密、李嘉图、穆勒等经济学家的理论),朱先生用了“经典经济学”的概念,来特指在经济学发展的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但又有别于现代经济学的种种理论学说,其中包括了李斯特、马克思等人的学说。所谓“经典”,自然意味着“不可不读”,同时也有“永恒价值”的意思——一切经典的理论,都因其包含着真理(在当时是新的理念)而具有永恒的价值,也因其反映了产生那种理论的时代所特有的烙印而永远给后人以历史和思维的启迪。在朱先生所着重分析的经典理论的现实意义中,以下两点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第一,经典理论的反封建性;第二,经济学研究的“本国立场”。
朱先生特别批评了把“现代化”(严格地说应是“近代化”)等同于“工业化”的错误概念,指出现代化指的不仅是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增长,更重要的是经济社会关系的改变,是使过去在封建桎梏中受压抑的、受制约的、存在于民众当中的生产力解放出来。在这方面,斯密可以說是早期反封建的经济学理论的杰出代表,他的代表作《国富论》的宗旨就是提倡“自由贸易”,要求打破中世纪封建势力对生产活动和交易活动所设的各种障碍和限制,打破各种“控制”和“审批”,解放生产力,使人们能够通过自愿和自由的分工与交易,提高效率、增进社会的福利。在斯密的著作中,“自由贸易”一词还不像现在往往特指的是国际之间的交易,而是指一般意义上的“交易的自由”,指市场经济的发展,指市场活动所体现的新的经济社会关系。
朱先生这些年一直在各种场合指出我们现在事实上还在进行的是许多“反封建”的工作,其意义就在于此,就在于要打破计划经济的种种“遗产”,打破中国两千年封建专制制度的种种“遗产”,使市场经济的原则和精神,最终在中国建立起来。
改革开放,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比起这个任务所要求的内容与范围,也就是比起那种种的“遗产”,我们已经打破了的还太少,还有大量的封建遗产在那里顽固不化,有的甚至还在不断地死灰复燃,它们不仅存在于我们的一些体制、规章、政策当中,很多情况下是深藏于我们许多真的热衷于改革、真的希望发展市场经济、真的想反封建的同志的头脑当中,不时地冒出来“干扰我们自己”。由此可见反封建的任务之艰巨、之复杂、之长期,可见朱先生其书的“现实意义”,恐怕还会持续很久,学习经典经济学的现实意义,还会持续很久。打开斯密的著作,每每你都会想对自己和周围的人说,“那正是在说阁下的事情”。我们现在写的许多文字、做的许多努力、进行的许多工作,许多自己当做很“新的”观点,其实都是当年人们已经写过的、做过的、争论过的、“玩剩下的”。这或许也是经典经济学的魅力所在:即使在一些关系到历史发展进程的问题上,它的理论仍然可以有长久的适用性。
朱先生一生极为推崇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不是简单地照搬和学习当时先进的国家——英国的经济学理论与经济政策,而是从当时德国作为一个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出发,“建立了从本国立场出发的‘国民经济学,特别强调本国创造财富的生产力……的重要性”。为德国的现代化进程、为德国追赶上英国等发达国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著作成为影响当时属于发展中国家的美国和日本走向现代化的重要著作。
朱先生所推崇的这种经济学研究的“本国立场”,对于我们所有的研究人员来说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所谓“本国立场”,不是要另起炉灶,置人类几百年以来已经发展起来的知识和科学体系于不顾,井底之蛙,搞什么“中国经济学”,而是要充分利用现代经济学,充分利用哪怕是昨天别人已经发展起来的知识与成果;只不过,作为致力于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中国经济学者,必须针对中国的特殊问题、特殊发展阶段,由此出发,来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才能真正使经济科学为我所用,而不是人云亦云,跟着“别人的问题”走,不能对本国的发展起促进作用,相反却可能起负面的作用。西方经济学家当前所研究的问题和提出的政策,多数都是针对他们作为先进国家当前所面临的一些前沿课题,而我们作为各方面还都很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同时还是“转型经济”),则有我们的特殊问题,如果不认真地分析这种差别,就可能提出错误的政策主张。比如当前非常热门的“新经济、旧经济”问题。“新经济”的概念,本来是根据某些发达国家的新经济现象提出的,与我们的现状相差甚远。即使是用“新经济”“旧经济”的概念特指一些新兴部门和传统产业,也会有很大的差别——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是“旧经济”的一些部门,对我们来说还是刚刚开始发展的新兴产业,如汽车、住房、家电等等;而对一些发达国家来说日益丧失国际竞争力的一些“夕阳产业”,对我们来说则可能正是当前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如劳动密集型产业)。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到中国来大谈特谈“新经济”,是因为那正是他们的“兴奋点”,他们正在为其在全球“开拓新疆场”。而如果我们盲目地跟着起哄,也要把中国的“经济结构”现在就提升到发达国家那样水平,忘记了现在我们“能卖得出去”的东西主要是什么,能“赚钱”的东西主要是什么,也就是“竞争力”所在是什么,忘记了我们还有9亿农民等着就业,等着进城,我们的经济就一定会在国际竞争中被挤垮,自己内部的矛盾也会激化。不能现实主义地冷静客观地分析本国的现实情况,在此基础上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是发展中国家经常会犯的一个毛病。而这正是缺乏“本国立场”的一个表现。
其次,一个经济学家,从“本国立场”出发,不仅能为本国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也恰恰因此能为经济理论的发展做出自己独到的贡献。比如,如果中国经济学家能为解决一个至今人均GDP只有800美元(注:此为2000年的数据)的国家能够一步一步改革开放,持续增长,最终实现现代化、追赶上发达国家这样一个难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方案,他们也就能对经济学、特别是发展经济学(即关于落后国家如何发展的理论)做出重要贡献。经济学的一般性原理都是在对各种特殊问题的分析中逐步形成的。落后国家如何发展这个特殊问题,同样能为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增加新的内容。这也是李斯特为什么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德国经济学家,也是一位在整个经济学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国际级经济学家的原因。
只要翻开书本,就能对老一辈学者的严谨学风和大师风范肃然起敬。但我想它对我们大家最重要的警示和启迪还在于它的“反封建精神”和它的“本国立场”。
(摘自《经济十八讲》,樊纲著,东方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