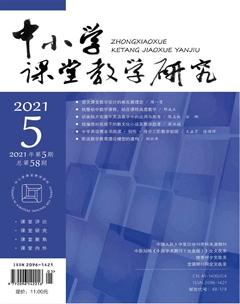形象分析:聚焦篇性的审美建构
【摘 要】蒋兴超老师在长三角语文教育论坛“语言运用与思维提升”主题研讨会上执教的《台阶》,以散文入,从小说出,以求诗意融合。他将人物形象塑造与叙事张力的营构、抒情气质的凸显、哲理品格的生成、文化意蕴的接续关联起来,对散文化小说进行审视、剖析,磨砺学生的高阶思维,实现学生“篇性”的审美建构。
【关键词】《台阶》教学;形象分析;高阶思维;审美建构
【作者简介】汲安庆,文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阅读与文学教育。
小说创作以人物形象塑造为鹄的,因此,小说教学自然也应以人物形象的审美建构为核心。如何分析与建构?学界目前形成的共识是:由“这一类”走向“这一篇”,即在类性辨识的基础上,聚焦篇性进而达成审美建构。
对于发现并揭秘篇性的路径,我们通常围绕小说三要素展开,即先情节概括——整体把握小说内容,继而形象分析——突出人物形象的丰富内涵,再是环境分析——上升到人物形象的时代性。然而,在这一路径的探索中,人物形象与情节、环境的独特关联是什么?如何从某一视角切入,将三者关联的秘妙有机联动?如何避免因只抓知识点或关键点,脱离文本整体观照而无法达成人物形象分析模型的建构?如何在教学中将人物形象分析与文化意蕴,作家言语表现的情趣、抱负、人格勾连?
蒋兴超老师对《台阶》一课的教学设计,将人物形象塑造与叙事张力的营构、抒情气质的凸显、哲理品格的生成、文化意蕴的接续关联起来审视、剖析,显然是对上述教学窘境的自觉突围。
一、形象与叙事:对比中的个性变化
在情节的处理上,蒋兴超老师避开了简单的事件梳理,摒弃按“起因、发展、高潮、结局”的情节四要素理论,转而关注小说的情节叙事与父亲形象塑造的关系。如,父亲为什么要建高台阶的房子?用了多长时间?怎么建造?建好前后,父亲有什么表现?为什么有这种变化?《台阶》中的父亲,是作者李森祥的父亲吗?在上述问题的架构中,教师完成了对学生赏析父亲形象的引导,切中了作家小说创作中对文章学起承转合写法吸纳的精神。但是,蒋兴超老师在将父亲形象的“转变”作为一个教学主问题单独拿出来探讨时,对之又有所打破——文本有起、承、转,但是没有合,而是在高潮处戛然而止,呈现开放的结构,这就是文本的篇性。顺着篇性之势而教,所探讨的问题自然出新出彩。
更为重要的是,蒋兴超老师还引导学生审视文章中事件之间的逻辑——父亲有地位吗?种田、砍柴、过年、编草鞋等和建高台阶的房子有关系吗?父亲辛劳了一辈子,得偿所愿,可为什么浑身不自在?这样的逻辑引导可以磨砺学生的思辨能力。同时,蒋兴超老师虽未在父亲与自我矛盾的基础上进一步审视父亲与母亲、父亲与“我”的潜在矛盾——“我”与母亲并不嫌弃旧台阶低,以充分揭示情节的表现张力,但他避开单纯的外部事件概括,转而关注情节中人物性格变化的内在逻辑,值得借鉴。
二、形象与抒情:激情与失落的点染
如果说从分析情节的内在逻辑、要素感知父亲形象属于遵类而教的话,那么关注小说文本的抒情气质,则属于对作家跨类创作的高度敏感与重视。引“史传”“诗骚”入小说的倾向古已有之,这“对中国人审美趣味的塑造以及对中国叙事文学发展的制约”显而易见[1]。引诗词入小说是作者惯用的技巧,而童话小说、散文化小说、诗化小说更是充满了浓郁的抒情气质。
李森祥的《台阶》也有抒情气质,集中表现在激情与失落的点染上。不过,小说的抒情不是直接抒情,而是间接、隐蔽的抒情:情融于事——如文中对“我”幼时趴在青石板上啃一嘴泥沫子,稍大些津津有味地跳台阶等描写,就是抒发“我”对台阶的喜爱之情,与父亲嫌台阶低的情感构成了潜在的对比;情融于象——如对新旧台阶模样的特写镜头,很能体现父子内心的情感;情融于貌——“那极短的发,似刚收割过的庄稼茬,高低不齐,灰白而失去了生机”,这句话正是在抒发父亲的失落、迷惘之情,也是在抒发“我”的钦敬、不安、同情之情。甚至连小说的标题叫《台阶》而非《父亲》,也有一定的抒情意味。
对于《台阶》一文的抒情气质,蒋兴超老师在引导学生时也有所关注,集中表现在对父亲激情与失落的审美上。关于激情的审美,蒋兴超老师采用的是精读法:精读父亲用大半辈子建高台阶房子的部分,用笔圈点勾画感触比较深的地方,写一写阅读感受。通过精读,学生关注了捡砖瓦、种田、砍柴、过年、编草鞋等事件,以及“柳树枝老是摇来摇去,却摇不散父亲那专注的目光”等细节。关于失落的审美,蒋兴超老师采用的是浏览法:快速浏览课文,看看高台阶的房子建好之后,父亲有什么表现?由此,学生感受到了父亲的尴尬与失落。
在执教过程中,蒋兴超老师通过引导学生品咂词语,体悟作者和父亲的情感。巧妙的是,蒋兴超老师并未在引导过程中点破文本抒情的含蓄性、复合性以及真实而概括的特性,加上文中大量农村生活的细节描写,又因为父亲形象的象征性极强,自具抒情性,这些让学生恍然而生写实之感,从而误以为作者是在写审美散文。这就让学生领悟到作家跨类写作中的语言魅力。
三、形象与说理:我们每个人的父亲
优秀的小说皆有哲理品格,但哲理不是镶嵌在文本中,而是像盐溶于水一般渗透在字里行间,正如美国艺术史家伯纳德·贝瑞孙在给海明威的信中写的那样:“任何一部真正的艺术品都散发着象征和寓言的意味。”[2]渗透、散发的艺术,正是文本的篇性。
《台阶》也有哲理品格,蒋兴超老师在教学中也捕捉到了。在引导学生感受父亲抽烟、挑水、打招呼、挺胸等方面表现出来的不自在之后,他追问:父亲辛劳了一辈子,得偿所愿,可为什么浑身不自在?学生的回答大体如下。
学生1:可能是因为伟大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感觉像在做梦一样,不适应。
学生2:因为父亲老实厚道,低眉顺眼,累了一辈子,不适应高高在上的感覺。
学生3:父亲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闪了腰,没法下地干活,闲着没事不习惯。
学生4:青石板已经伴他很多年,就像挚友一样,新台阶全是用水泥抹的面,不再是老友的感觉。
学生5:父亲为了建新房子操劳了大半辈子,新屋建成了,他也老了,身体也垮了,感觉到头来也挺没意思的。
不管是愿望实现后的不适应,还是社会地位在形式上的变化带来的不适应,或者是从忙到闲生活习惯的改变带来的不适应,又或者是面对新生事物的不适应,都是蕴含着一定的哲理,即人生中这样或那样的改变,常会带来精神的不适应,如阵痛、迷惘、失落等。蒋兴超老师抓住作品的哲理品格,让学生贴紧文本,实现思维的深度、广度发散。
不过,如果蒋兴超老师能再做进一步的引导,应该还会有更深刻的发现。比如,辛劳付出、得偿所愿,本应该高兴才是,为什么反而跌入深深的迷惘、失落,甚至苦痛之中?你们如何看待这种反常的变化?学生5的言下之意是:操劳了大半辈子,用衰老和垮塌的身体,换来这么一座新房子不值得。对于这样的观点,你们是否认同?以此激发思维,学生就不难发现文本中隐含的对希望命题的思考——有希望的支撑,人生可以迸发无穷的毅力与动力;没有希望的伴随,人的精神生命则会很快走向衰朽。换言之,拥有奋斗的希望,就会永葆年轻;丧失奋斗的希望,则会迅速走向衰老。
事实上,这种哲学思考在很多作家的作品都出现过。比如鲁迅的《故乡》:“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比如但丁《神曲》中地狱之门上的铭文:“你们走进这里来的,把一切希望都捐弃了吧!”
四、形象与文化:在铢积寸累中圆梦
文化的理解与传承是语文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遗憾的是,在现代文中涉及文言文教学时,有些教师常常不知不觉将之过滤掉,仿佛现代文中就不存在传统文化。还有一种现象:人们谈论文化时往往对典章制度、天文地理、民俗风情、造字文化等方面情有独钟,却对文本中蕴含的自古及今、赓续不绝的精神道统、学统、文统,特别是作家的言语抱负、言语创造匠心上显示的文化特色视而不见。
在上述背景下,蒋兴超老师于现代文教学中将人物形象分析与传统文化的血脉接通,则显得尤为珍贵。他的做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开头的导入部分,将“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思想,与父亲的行动、精神关联;二是在结尾的升华部分,探讨“父亲是谁的父亲?”。由朴实农民的代表,到城市里的父亲,到天下所有人的父亲,再到李森祥自己的创作主旨的表达——在中国乡村,一个父亲的使命也就那么多,或造一间屋,或为子女成家立业,然后他就迅速衰老,并且再也不被人关注,我只是为他们的最终命运而惋惜,这几乎是乡村农民最为真实的一个结尾。但是,即使富裕起来的农民,他们最终的命运会不会有所改变呢……这其实悄然渗透了中国的乡土文化,是对锲而不舍、奋斗不止的儒家文化精神的呼应。只不过,蒋兴超老师没有点明罢了。或许是囿于时间,也没有就如何看待这种独特的乡土文化引导学生展开充分的讨论。
至于说写作文化的渗透,蒋兴超老师在教学中也有体现。如对父亲在新屋造成前后的行为与精神上背反的感知,对细节与形象的多维度分析,对事件间逻辑关系的审视,对“究竟是谁的父亲”的探讨等,这些实际上都已经触及了矛盾营构中的叙事张力,人物形象塑造的丰富性,情节与形象发展的同构,叙事中的象征品格等言语表现知识或智慧。
参考文献:
[1]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余秋雨.艺术创造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責任编辑:蒋素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