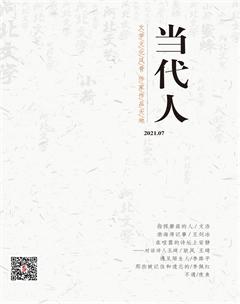远亲
程溪
“表伯死了?”
我不咸不淡地贩了母亲一句,听清了还问一句,是我的习惯。这个消息并没使我感到震惊,或悲哀,像听到旁人说着闲事。
母亲声音沙哑,眼神无光,面容比父亲去世时还显憔悴。淌下的汗水没有洗去她脸上的晦暗,母亲的形概使我凛了一下。
“你赶三十几里路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个?要我怎样?”
我的话很冷,比空调里吹出的冷气还冷。
“帮表伯写篇祭文吧,也该回去送送他,唉!他苦了一世。”
母亲听出了我的语气冷淡。她的泪潽出了眼眶。
“你只狗不认骨的东西,你这校长是怎么当的。要不是你表——”
母亲说半句留半句。
打锣听声打鼓听音,跟聪明人说话只需点破便可。乡下人叫打惊窠,说破了岂不彼此都尴尬。
一百多人的屋场,几十年就出了我一个大学生,还是中学校长,实属凤毛麟角。乡人都说我是芥菜地里扯出的大萝卜。乡人说话一向刻薄,也一向贴切。说实话我是认可的,毕竟母亲身高不到四尺。
母亲的肩膀刚齐我的办公桌,她那双失神的眼睛,在桌面上滚来滚去。最后巴巴地滚在我脸上。这双眼睛使我想起了第一次去表伯家,那年她也是这样,呆滞地杵在表伯面前,巴巴地望着他。
那年臘月的雪真大,呜呜的风也大,雪被风吹得凌乱不堪,母亲像匹枯叶似的被雪风卷进了屋,手上那块冻僵的猪肉裹着一层厚雪,肥腻腻的似要流油。她把肉挂在门边,迅速关上门,跺了跺脚,双手交替着拍拍胳膊上的雪。
“还好,总算没白去一趟,世芬听说我要做人情,忍忍诺诺的还是让了两斤给我。”母亲高兴地说,似挣了个天大的面子。
“嗯,嗯。”
躺在摇椅上的父亲在黑暗里算是应了。
屋面上几匹亮瓦被雪压着,像父亲一样没起作用,关上门黑得如同钻进了老鼠洞。父亲挣扎着想坐起来,架几次势还是未能如愿。母亲循声蹿上前,吃力地把他扶了起来,拿起摇椅上的毛巾帮他揩拭着嘴角。她知道,父亲只要一开声就会流口水。
“唉!我是头世该了你这家人的债。”
母亲轻叹一声。摸起火塘边的火钳,把烧散了的柴头重新拢起,屏声的火终没忍住,冒出几缕青烟后,哔哔叭叭地又着了。
“水根,水根,你只打短命的又跑到哪去了!”
母亲大声呱气地喊着我。每次都这样,一开腔便夹带着骂,骂起人来不骂见骨头不罢休。骂父亲,说是头世该了他的债。骂我骂得最多,起床晏了骂我摊尸,没听她的话,骂我死伢崽、打短命,去河里戏水骂我漂尸。妹妹病了也骂,骂她是只讨债鬼,喂妹妹喝药又骂她是喝血。也骂自己,骂自己头世做多了过事,打多了牛,得多了别人的冤枉钱。但从不在外面骂,更不敢骂别人。
“妈,我在房里写字哩。”
“画灵牌吧,叫你招呼你爸又跑去写字。”
“嗯,嗯,嗯。”
父亲龇着牙翻着白眼,直朝母亲嗯着,似在抗议母亲骂我。他只能发出这种声音。这声音单调,只需从喉咙里往外挤出点气就成,不要动嘴,甚至不需张口。
母亲不吱声了,默默地从炉罐里舀碗菜粥,拿出羹匙从盐罐里挑几粒盐进去搅了搅。舀起一羹匙送到自己唇边试试,再送进父亲嘴里。
“他爸呀,你说他表伯会帮我们啵?我估计会,俗话不是说,播了春风就有夏雨么。这几年不管多艰不都每年给他送了汤,拜了年,每次去他家从没空过手哩。”
明知父亲不可能回答她,也只得自家打珓自家捡,这是母亲的习惯,五年来的习惯。每每碰到大事拿不准主意时,她都要这样跟父亲说,之前她一直都在父亲这棵大树下躲着荫,从没操心过。
“你说一个八岁的伢崽,骨头还没长硬哩,不读几年书做得了什么呀!”
“妈,我饿了。”
我像皮球样从房里弹出来。着件坏了拉链的劣质羽绒服,前胸袒露开来像条剖开的鱼。这件衣服是母亲从世芬婶那讨来的。
“忍忍吧,留着肚子随我去你表伯家做客,他家有肉吃哩。”
父亲闻言,闭口不吃了。还剩小半碗。
“端去吃吧,你爸不要了。”
雪还在下,落了一日一夜仍不觉疲倦。一世界的白,白得无边无际,白得地比天大。天大能看见边,看见天边那溜令人神往的灰色边缘,那是幕阜山。今日看不见了,只有单纯的白,无穷尽地延伸着。一直往天上伸去,似要把天撑破。
母亲与我在雪地上溜来滑去,耘禾般。母亲的右手搭在我肩上,我便成了她拄着的拐杖。地上的雪硬了,踩在上面不太像雪,没有那种心颤颤的软,咯吱咯吱的,地皮像被踩痛了,一味地发出尖锐的叫声。
表伯是团转有名的木匠,家底厚实,哪家手头短缺都去找他翻门槛,都把他家当成了银行。他也很乐意借出去,把钱当表伯娘样,养着生崽哩。
表伯娘的确会生崽,给他生了三个磉礅样的儿子,个个捻得牛死,却老说他有四个。说从老大到老三都不孝顺,只有老四最乖,要他怎样就怎样。
“哪个是老四?”
别人不明白。
“钱呀!钱就是我家老四。”
表伯向来大话喧天,这次却拐着弯来显摆。都晓得他的钱是下崽的,比他三个儿子都看得金贵,来他家还账的人,哪个也不好短他半分三厘。尽管利息收得规矩,别人还是敬他,毕竟哪个也不晓得何时还要求到他头上。
表伯离我家不算太远,也不很近,在对面山脚下一个叫野兽洞的地方。隔着两条河,一条是沙河,另一条也是沙河。其实原先是一条,日子久了,河中积成了个大沙洲,成了两条河。沙洲上的雪白得格外伤眼,踩在上面绵绵的,留下我和母亲两串足迹,像极了拖拉机的车辙。
“水根,快喊表伯。”
母亲扽了一下我的袖子。
第一次到表伯家,他的生相着实吓着了我。额头上的皱褶,像平静的水面投进一块石头,一道一道的有形有状。嘴巴藏在黑黝黝的胡子里,似隐蔽在茅丛里的野兽洞。他正把最后一口硬撒撒的饭扒进嘴里,又搛一大箸青菜塞进去,腮帮便鼓了,鼓得像溜进只大老鼠,我的心颤了一下。
“嗬,赶到饭背去了,你们两娘崽也是,就没个早晏。饭也赶不上。”表伯打了两个嗝。
“不晏,才大半昼哩。”
母亲不晓得落雨下雪天,表伯家是吃两餐的,还以为掐好了时间。表伯个子长大,嗓门却不大。带着磁性的男中音,很悦耳,责备中掺杂着关心的话意。
“表兄,给你送碗汤来。”
母亲像我一样,也怕看表伯的面颜。
“哎呀,快拿走,死猪肉我家没一个人敢吃,莫把我家的猪惹病了。”
表伯娘像看见了瘟神。她大概晓得我家那头过年的猪死了。
“表嫂,你放心,送人须好物哩,我家那头讨债的才四十斤,死猪肉怎好做人情,一两都没卖,全被我腌来过年了,这是从下屋世芬家让来的。”
母亲有点语无伦次,生怕表伯娘委屈了她的心意。
母亲没个正经亲戚,父亲六岁也成了孤儿,父母没哪亲处。想到了这个远房表兄,便攀上了这门亲。每年解年猪时都要送上两斤肉给表伯,谓之送汤,是乡人的谦逊之语。正月去拜年也从未断过,表伯没上过我家,更没给我家送过汤。正合上“穷人攀富亲,富人懒动身”那句话,有点巴结的味道。
“挂到壁上吧。”
表伯坐着未动,两眼却随着母亲在动。蹲在饭桌下的那只母狗,支著两条前腿,咧着嘴,紧盯着母亲手上那块肉也在动。都放着绿光。此时,我觉得表伯不像表伯,倒像那条蹲坐的母狗。
母亲身穿世芬婶女儿的学生装,小巧得如同一个小学生。她皮肤白皙。鼻翼两边各有几颗不太显眼的油麻痣,大概气血不佳,嘴唇白得没一丝血色,有种病殃殃的感觉。两条又粗又黑的辫子拖至腰际,额头的刘海儿往内弯卷,缝隙里,隐隐透出她前额细腻得如同橘子皮的皱纹。
“把饭菜暖暖让他们娘崽吃了饭去。”
表伯吩咐表伯娘,摆着一副特权威的派头,眼睛又盯着母亲的屁股,舌尖润了润嘴唇,咂巴几下,像尝着了肉味。母狗盯着墙壁上那块白肉,猩红的舌头在嘴筒上搅一圈,似把挂在壁上的肉吃下了。
“哪还有,只半碗了,猫还没吃哩。”
不知表伯娘生哪个的气,把碗洗得哗啦啦的响。
“不麻烦了,我们早饭吃得晏,还饱的哩。”
母亲挂好肉回头望了望我,眼里有种辜负了我的神情。很不自然地拍了拍衣裳,像身上沾了不少灰尘。
“那你们就早点回去吧,天不好,这雪还不晓得落到何时哩。”
表伯再没叫表伯娘暖饭菜,炉罐没洗哩,大概是要留作晚饭。表伯娘的吝啬使我很恼怒。我的肚子呱呱地叫了几声,怀里像藏了几只蛤蟆。我下意识地把敞开的前襟叠起来,紧紧捂住,似怕蹦出来。抬头望着墙上那块白肉,蛤蟆又叫了几声。我很想冲上前取下那块肉拎回家。真想不通,好好的一块肉,不知母亲为何要送给他们。
“表兄啊,你表弟自那年修水库,把头砸坏后,家里就没熄过药味,前年水莲又病得重,还了她两年债还是没留住她。水根呢,还是只幼虫,也做不了什么正经事,不读几年书,就是长大了不也是只懵懂虫。这不,开年就要起学了,报名费还不晓得在哪家箱角里蹴着哩,你表弟让我来你这翻个门槛,不晓得表兄是不是——方便?”
表伯还是端坐着未动,母亲像根木头样杵在他面前,眼巴巴地望着他。他那张被胡须覆盖着皮肉的脸,根本看不出喜怒哀乐。
“三秀呀,你就莫心子大了,轻快饭不是你想吃就吃得了的。你们屋场下也有三几十户人家,又有几个伢崽读了书?说句你莫着气的话,他们就是随便扯出一户人来,也比你家条件好。俗话说有样没样但看世上,你又何必要充这个尖呢。依我看呀,水根就根本不是块读书的料,莫麻雀没系着反去了根线,做那些赔工丧种的事,就太不值了。”
表伯还没开腔,表伯娘就应上了。好像生怕母亲上了天大的当,又似一眼就看穿了我的皮毛骨。
一床被窝不盖两样人。表伯娘像表伯,也身长个子大,但她嗓门粗犷。骨骼奇粗,一点都不像女人。刚一说完就拿起笤帚粗脚大手地围着母亲扫起地来,好似母亲站的地方格外脏。母亲轻轻巧巧地避让着,她在等表伯发话,毕竟表伯才是这个家的主脑。
“你表嫂说得在理,我一日书没读,这团转几十里,又有几个木匠的手艺有我精,人有没有发旺不是靠读书的,你上屋的大状书还读得不多?高中哩,他爸叫他去滤薯粉,他只大蠢崽却把包袱里的薯浆渣拎到圳沟里去洗,你说这是不是读书读呆了?这样吧,再过个几年让水根来跟我学木匠,手艺三分香,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表伯适时发了话,但并没说借钱给母亲,也没说不借。可这分明就是跟母亲作了主,像是他家的事。表伯的话无疑断了母亲的路,她脸上的肌肉在断断续续地拉扯着。几颗痣被拉扯得蹦蹦跳跳,险些落了下来。那张小巧秀气的脸,显得格外的丑陋。
“表兄,不方便就算了,大有大难小有小难,至于让伢崽跟你学木匠的事以后再说吧。还要好几年哩。我再到其他地方看看,水根若有书份的话,定会碰上贵人相助的。就看他有没有瞎眼鸡婆天照应的命了,让他信命去撞吧。”
母亲脸上的痣不跳了,恢复了往日的俊秀,还有点儿潮红。
“我也没说不借呀,只是觉得读书纯粹是烧钱,还不如学门手艺合算哩。”
表伯的话母亲没接应,像溜平静的风拂过耳边,她转身又拄着我走了。我感到她搁在我肩上的手,均均匀匀地抖动着。
“嚄唶!来求人家火气还这样大,有本事就莫上人家的门呀……”
声音粗犷得比雪风还硬,母亲缩了缩脖子。
“你是打斜屄屁,什么事都要插上一句,人穷能穷得了一世?”
磁性的声音被雪风淹没了,听不出悦耳的味道。
“哼!没三垛牛屎巴高,还心高气傲。破窑能出得了好货?菩萨跌跤鬼都不信哩。”
母亲从后面用两只小巧的手,紧紧捂着我的双耳。那双冰冷得僵硬的小手掌捂得我生痛,她是怕雪风割破我的耳朵?还是怕——
搞不懂。
雪天的夜来得早,母亲给我点上灯,亮了我那方读书的小桌。没写两页,灯火跳动几下,熄了。满屋弥漫着一股布条烧焦的臭味,连灯芯上結下的两朵桔红的小火花,也渐渐淡了。
“水根,还不上床摊尸。”
母亲嚎着我上床。真是个怪人,明明是她规定每夜要我做作业,却又骂我没尽早上床睡觉。好在我适应了,如同聋哑父母的子女,早已适应了父母的指手画脚。尽管屋里黑得如同十八层地狱,但窗户门的缝隙里还是透出几缕淡淡的光,是雪光。在那个漆黑的夜里,我心中仿佛也看到了几缕淡淡的光。
大概在半夜,几粒字一句,几粒字一句,断断续续地叠进我耳里。
“想……送吧……伸手拿见骨头……也跑了……家……他命……可能……注定……没……书份……有我……你怕……上昼你……没法……懒跟她……莫……这样……不行……依我……送他……对不起……就……废人……也……”
声音越来越低沉,字数越来越少。用木板隔成的房间拦不住声音,我听到了低微的啜泣声,是母亲在哭。随即递来了床铺吱吱嘎嘎的响声,匀匀称称,不像翻身时引起的响动。我被一种燥热压抑着,不敢继续听下去。母亲与谁在唧唧哝哝?是父亲?不。父亲除了能挤出几个嗯字来,再也说不出半个其他的字。母亲又究竟是为何而哭?我不敢探究。只一个劲儿地钻进被窝里,薄弱的被子被我捂出一身大汗,润润的像放在屋外受了一夜露水。
正月初几里,表伯正儿八经地来了我家一趟,坐在火塘边与母亲嘀咕半昼。父亲咧着嘴也嗯了半昼,很高兴的样子。坐在父亲身边的母亲,不停地给他擦拭着嘴角的口水,手势轻盈而利落,看得出,母亲的心情像我过年时一样。从那次起,表伯来的次数就越来越频繁。每个月要来好几次,不是提油就是扛米,逢年过节还会扯上几块布料。有母亲的,也有我的。反正每次都要带些东西,从没空手过。他的胡子也刮得精光,每次都一样,好像不喜欢蓄胡子了。没有浓密的胡须遮盖,笑就显在脸上,越堆越厚了。相貌比我第一次见到时,更像表伯些。
母亲挖到了窖银子,是她悄悄告诉我的。说以后再不愁学费了,叫我只管用心读书就是。果真,以后每次开学我再也不是最后一个报名的。但看不出她有多喜悦,心事很重的样子。在路上碰到人,不管男女老少,总是早不早仄着身子站到路边让着。即使有人跟她说事,也说不上两句便匆匆离去,好像家里有做不完的事。也不串门,更不往人多的地方扎,似很怕人。
母亲是怕人,表伯娘来过一次,还带着她三个捻得牛死的儿子。人一多母亲就怕,全身颤栗着像见到了活鬼。
“水根……去外面……玩吧,表伯娘……几个表兄……屋里坐不下。”
母亲的话支离破碎。
“小观音啊!你只贱屄也不屙泡尿照照你的生相,细丁丁的还没三垛牛屎巴高,就敢架个这么大的势,就不怕我家那只剁颈的撬死你……”
刚出门,表伯娘的大嗓门就咆哮起来,她不再喊母亲三秀了。团转几十里没一个像母亲这样矮。但像母亲容貌这样出奇的美,在团转几十里也找不出第二个。不知哪个喜欢绰名绰字的人,觉得母亲的脸蛋漂亮,像极了观音菩萨,又根据母亲的身材小巧,便给母亲取了“小观音”这个雅号。
我吓得飞快地跑了。表伯娘比表伯矮不了几寸,她手指的骨节突兀得像算盘珠子。虽然担心母亲,但我更怕她那双攥起来像八磅锤似的拳头。
不消说得母亲要吃苦了,不消说得母亲要遭殃了。我没有娘亲爷戚,又有哪个愿为了母亲而跟表伯家翻脸呢?果然,暴风骤雨过后并未出现彩虹,而是出现了一地的破锅烂碗,还有凌乱不堪的头发。是被表伯娘剪下的。母亲黑亮的秀发没有了,鼻青了,脸也肿了。那次母亲没有哭,没骂我,也没骂父亲,脾气出奇的温柔。她不停地往地下吐着唾液,红红的溅在地上,像一朵朵绽放的梅花。雪白的牙齿也红了,看着令人作呕,像我家那只猫吃老鼠时的形概一模样。
倏地,我有点儿希望母亲是我家那只猫。我家那只猫太有福气了,母亲捧了它几年,疼它比疼我还要多几分。母亲喜欢骂家里所有人,包括她自己,但从不骂它。那次它吃了只毒死的老鼠,踉踉跄跄地歪在母亲脚下。母亲赶忙把它搂在怀里,楼上楼下到处找老鼠屎喂它。她从老班辈那儿得知,鸡发瘟喂几粒老鼠屎就能好。老班辈的话不能全信,那只猫还是没救活。母亲哭熟了,哭得很伤心,起码比妹妹走时伤心。她老说妹妹没带根来,是来讨债的。而那只猫是来还债的,年年可护住她谷桶里那几箩谷。母亲为它花了大价钱,满满一担谷哩,或许是心痛那担谷也未可知。
母亲怪是真怪,幕阜山一带有个祖辈传下来的乡俗。猫死了是不能埋的,更不能吃。只能用根绳索系着死猫的脖子,挂到树桠上,俗称挂桠。一向遵循乡俗的母亲,那次没遵奉这一乡俗。剥皮炒给我和妹妹吃了,母亲一坨没尝,只一个劲儿地呕,眼泪和着胆汁一起呕,呕了半昼还止不住。
我不懂母亲,真的不懂。她对我家那只猫那么亲,却能残忍地剥它的皮,炒它的肉。对她养的猪也疼,把猪看得比她的家人还重。每次解年猪,临宰前一餐的潲食,比我们的吃食还高级。屠夫进门时她就眼泪含含的,猪将咽气时她燃着表心纸,一边烧还一边嘀咕着。
“去吧,轻轻快快地去吧,你是给我还了债的啊!下辈子投到一户好人家吧,跟着我你是可怜啊!没吃过一餐好潲食哟!”
念往生咒般。
父亲去世了,是表伯娘来我家的第三日。表伯娘完全不念及母亲年年给她送汤,给她拜年的情分。在她那双骨骼奇粗的手爪下,母亲如小鸡遇上了老鹰。表伯娘骂起人来很在行,句句像刀,还专往心口上扎。母亲那天一句都没还嘴。父亲坐在摇椅上翻着白眼,不断地嗯嗯嗯,他是想以此来援助母亲,那是他唯一的方式。表伯娘那天大概骂顺了嘴,骂了母亲又骂父亲,她指着父亲的鼻子骂。
父亲挨骂并不是第一次,有次表伯从母亲房里出来,对躺在摇椅上的父亲说,老是充好汉充好汉,集体的事就你积极,这下好了吧,老婆伢崽跟着你受罪了吧。表伯的话恰巧被我放学回来听见了。
在大门边他还摸了摸我的头。
“水根,好好读书,你妈全指望你了,靠你爸是吃茅都没人给她割。”
表伯双手叠在屁股兜上,昂着头挺起胸,像个村干部似的,摇摇晃晃地跨出门走了。那神态,那步调,又像极了我家那只老公鸡。我家那只老公鸡,每次从鸡婆背上下来正是这个样貌。
母亲跪在父亲摇椅边。当看到我时便戛然而止,爬起来用胳膊拭了一下眼睛。自那次后母亲对父亲照顾得特别好。
父亲的眼睛到死都没眯上,母亲不停地宽慰他。
“他爸呀,你就眯上眼吧!眼不见心不烦哩,你是好命啊!两手一撒,就是天蹋下来也不关你的事了,安安心心去吧,下世投胎做猪做狗就是做猫,也莫投胎做人了。做人难啊!要活几十年哩,太长了。”
母亲没眼泪,没哽咽,像往日跟父亲聊天一样,自说自解。
“水根呐,你爸走了。也好,他的罪总算受满了。来跟你爸拂拂眼皮,眼还没眯哩,或许是等你来让他看看。”
母亲看到我才哽咽起来,眼里也有了泪。那天我刚放学,一点征兆都没有。
渐渐地,见到表伯的日子越来越少,有很多年再也没与他打过照面。在我读大学放假回来期间,有次险些狭路相逢。那是最后一次,却被我灵巧地避开了。
也不能说我有多灵巧,那时他的背驼了,驼得只能瞧见自己的脚趾头,似在寻找丢失的什么东西。他的胡子又重新蓄了起来,比第一次看见他要厚很多,且白,白得像当年那场雪。他勾着头走得很稳健,那时我还不知他的岁数,就是现在我也还是不知他的岁数。
(戴成标,江西武宁县人,木匠。2017年开始文学创作,有长篇小说一部,中短篇小说十余篇。长篇小说《免赦源》即将出版。)
编辑:耿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