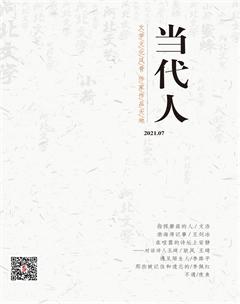大地细软
苜蓿
梦见在一片开满苜蓿花的田野里奔跑,大汗淋漓,跑到一半,像中弹一样,背朝大地倒下去,在苜蓿地里睡一觉。醒来以后,像是真的嗅见了苜蓿的清香,可那味道明明离我很遥远。于是,借这个梦想起苜蓿。
我出生的甘渭河流域,苜蓿分紫花苜蓿和黄花苜蓿,前者家生,花为紫色;后者多为野生,花为黄色。两种苜蓿其他诸如分枝、花萼、荚果之类的详细分法,我就不大能说得上来了,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两种苜蓿从气质上来说,一个是小家碧玉,一个就有些粗犷不羁。
小家碧玉的紫花苜蓿,出自农人之手,他们挑一块不远不近的地,撒几把苜蓿种子,从此这块地就不用再操心了。对于苜蓿的种植时间,东汉人崔寔在《四民月令》中就已经明确:“七月、八月,可种苜蓿。”苜蓿的种子撒到大地上之后,来年三月定会发芽。
人吃第一茬苜蓿嫩芽,在五月的时候,牲畜们再吃一茬青草,到了九月,还可以再割一茬,晒干、储存,以备漫长的冬季。而到了冬天,这苜蓿还有一层地衣可以薅,用特制的筢子搂一遍,干枯的苜蓿,就可以拉回家做填炕的材料。我有时候想,这取之不尽的苜蓿,就像我那些生下来养大就能帮父母干活儿,嫁出去再远也会帮衬娘家的姐姐们,一生任劳任怨。
粗犷不羁的黄花苜蓿,则大多长在山坳里、水洼边,它们有些不务正业,孤独的一两株,迎风摇曳着,似乎在等诗人把它们写进诗歌里。
我专门查过写苜蓿的古诗词,古人们但凡写到它,总与吃分不开。《齐民要术》卷三《种苜蓿》说,“春初既中生啖,为羹甚香。”甘渭河两岸的人们一直延续着古书里的传统,每个出生于斯的人,童年里也都有挎着篮子掐苜蓿芽的经历,这段记忆的重要性,相当于城市里的孩子周末去公园坐摩天轮或者旋转木马。宋代的陆游,诗文中多处提到食苜蓿之事,如其《对食作》云:“饭余扪腹吾真足,苜蓿何妨日满盘。”可见,吃苜蓿这件事,上到文豪,下到平头百姓,爱得没有区别和界限。
而对于苜蓿的吃法,明朝的朱橚在《救荒本草》说得清楚:紫花苜蓿可食,但必须用沸水焯过,去其毒性。乡下人不知道《救荒本草》,但知道要用清水洗去苜蓿身上的尘土,才把它们放在锅里煮,出水再过凉水,加盐、加油,搅拌均匀就可以食用。
祖父应该是甘渭河边吃苜蓿最讲究的那个人,他只吃刚冒出头的嫩芽,长到两三寸长以后,就不会动筷子了,问原因,说是年少缺吃,就到地里等苜蓿长出来,一冒尖就掐掉,扔嘴里就嚼,那一口比肉都香。如果没说错的话,这应该是饥饿留下来的后遗症。而古人里,吃苜蓿最讲究的,应该是性格豪放不羁的王翰,这个《全唐诗》里仅收14首诗的唐朝大诗人,在《食苜蓿》中这样写道:“东皋雨过土膏润,采撷登厨露未晞。生处碧条侪苋藋,糁时白粲埒珠玑。”从诗句中看,他采摘苜蓿的时间,也是春雨过后,那时候唐朝的土地也湿润肥沃,而苜蓿抽出嫩芽,不管是古人还是现代人,看一眼就走不动路。王翰眼里,在马齿苋和蕨菜的围绕中,苜蓿的茎干显得优雅,而搭配着米饭就是人世间的美味。不过,我更喜欢就着刚出锅的馒头吃苜蓿,觉得这才是北方人对待苜蓿的正确方式,一口馒头,瓷实,一口苜蓿,舒心。
王翰还在《食苜蓿》里说到了苜蓿的身价,“阑干敢效诗人讽,顑颔多惭战马肥。还胜红蓝遍中国,冶容争不济年饥。”苜蓿这似草非草,似菜非菜的物种,虽然人畜共食,可身份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在唐朝,王翰就看中了它野蛮生长的习性,他说,饥肠辘辘的人们,应该明白这些更适合成为战马的饲料,但比起那些妖艳的红蓝花儿,苜蓿有更强的生命力,摇曳在中国的土地,能够在饥荒的年代,帮助困难的人民。
王翰的诗,传递了一个信号,在唐朝苜蓿就是救荒的最佳食材,也因此,就能理解祖父一代人對于苜蓿的报恩之情。土地再紧缺,也都要留一块地种苜蓿,这样春天可以当蔬菜,秋冬牲畜不挨饿,如此算计,患得患失的小农意识一目了然。据祖父说,苜蓿是庄稼里唯一需要照看的,饥荒年代,每个村都有几个苜蓿看管员,他们守着一村牲畜吃的苜蓿,比守着自家清贫的日子还用心。
不管是出于饥饿,还是受了美味的诱惑,对于苜蓿总是无法抵挡,人知道吃太多苜蓿胃会受不了,可牛不知道。清晨,一头挣脱了束缚的牛犊,被大片的绿所吸引,一头扎进露水未干的苜蓿地,舌头卷个不停。它顾不上闹清楚这是谁家的苜蓿地,也不知道追它的人离自己有多远,一个劲地卷着苜蓿,唇边流出绿色的汁液,肚皮也慢慢胀大,可它就是停不下来,吃了一个冬天干草的牛犊,想一次吃够这绿色的嫩芽。贪婪的代价是,牛被牵回家就胀气而死。苜蓿芽好吃,带露水的苜蓿芽却似毒。前程大好的牛犊,突然死了,牛主人咽不下这口气,就去找那块苜蓿地的主人要说法,两个人为了你家的苜蓿吃死我家的牛和你家的牛吃了我家的苜蓿还没找你算账这两个问题纠缠不休,双方骂累了,问题也没理出个头绪,倒是那头牛犊,已经被扒了皮。肉煮出来的时候,死了牛犊的人家,端了一碗牛肉,送到苜蓿主人家,苜蓿主人拿出来女婿春节时送来的酒,两个人划着拳,吃着牛肉,喝下一坛子。苜蓿花开了还会再来,日子过完今天明天还要继续,一场因为苜蓿引发的恩怨,就此化解。
我一直以为,紫花苜蓿只生长在中国的大地上,后来再翻资料,才发现这紫色的尤物,是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在汉代来到中国的,张骞将它带到陕西西安,故而《救荒本草》记苜蓿,说的是紫花苜蓿,也说:“苜蓿出陕西,今处处有之。”而多年以后,读美国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歌《草原》,竟然也看到了苜蓿:要造就一片草原 / 只需一株苜蓿一只蜂 / 一株苜蓿,一只蜂 / 再加上白日梦 / 要是蜜蜂少/光靠梦也行。也才发现,这苜蓿到了大洋彼岸,不光能成草原,还可以成为梦。
又是梦,它和我一开始做的那个梦一样吗?我不得而知,只知道,梦转瞬即逝,诗意不可靠,而苜蓿之于大地,是衷心的,可信的。一直留着挖掘苜蓿的记忆,一镢头下去,是比苜蓿秆粗几十倍的根,难怪苜蓿只能割,而拔不得,它是把自己长进了大地深处的,它才是以大地为家的植物,它开出一地的紫花时,就等于大地扔出来了无数的碎银子。
可惜,吃着苜蓿长大的人,没有学会苜蓿的忠心。一茬一茬的人,吃着苜蓿长大,然后陆续离开乡下,去寻找比苜蓿更加诱人的东西,他们收起苜蓿喂养过的脾气,收拾苜蓿滋润过的表情,努力地把根扎进被重新当作家园的地方。他们明知道那里的土地厚实,根没那么容易扎进去,但是他们还在努力,哪怕是扎在花盆大小的区域,也算作成功。
想起他们,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那么多背井离乡的人,到底有几个人会像我一样,在春天的时候,在失眠的时候,在某个很突然的时刻,想起一地的紫花苜蓿,如果想起过,他们想到什么?他们有没有像我一样,想起苜蓿就想起自己离开乡下的目的和意义呢。
这一切不得而知,紫花苜蓿在乡下的春天里绽放,它们或许知道答案,但诗人们说,答案就在风中,不知道乡下那么远的风,何时才能把答案送到我们身边?
地软
村庄里还点着灯盏的时候,一豆昏黄之下,一切都显得模糊,暗夜的屋子里和屋子外没什么区别,出门和进屋也没什么两样。等通了电,一米长的灯管电棒和一滴水变胖了一样的电灯泡,一下子就把夜隔在了屋子外面。白天被无限拉长,不过很快就发现了问题,关掉灯之后,再到暗夜里走路,竟然眼前一片模糊,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墙,好几次都是碰得鼻青脸肿,狼狈不堪。
我怀疑自己得了严重的眼疾,就去问做赤脚医生的三爷爷,我怕是要瞎了吧,这毛病还有没有办法医治。三爷爷翻了翻我的眼皮,又摸了摸脉,说这不是病,不过要像病一样治。
三爷爷开出的药方子里,都是村庄里所没有的物件:枸杞、菊花、苍术……我说三爷爷,咱们四条腿的蛤蟆好找,枸杞、苍术这些东西不好找啊。他说了句碎怂,把你的懒不说,你等我再看看。于是就从八仙桌下的匣子里拿出一本没有封皮的书来翻,没翻几页,就猛地抬起头来,像是突然想起来一样东西似的。三爷爷调整了下眼镜,转过头看着我说,地软到处都是,你去捡些吧,吃了它你这症状准好。
用我三爷爷的话说,地软常年匍匐于地,所以带着大地的脾气和温度,性凉、味甘,入肝经,能清热明目,收敛益气。我根本就听不懂这些术语,看我一脸懵懂,他就拿出做了一辈子赤脚医生的架势说,你看书上写得清楚哩,地软主治目赤红肿、夜盲、烫火伤、脱肛。我才知道,我得的病叫夜盲,这名字还挺贴切,夜里跟盲人一样。
都说眼不见为净,我这人却偏偏喜欢热闹,凡是眼睛能看见的,耳朵能听见的,一定要凑到跟前去闹个一清二楚,所以这眼睛和耳朵就不能有问题,所以对治好眼疾就有了一种超过一切的迫切心理。拿到三爷爷的药方子,我就像找命一样,到山上沟壕平川里去找地软。
夏天的时候,我拨开冰草,看到绿油油的草颈之下,蜗牛在缓慢搬运阳光,螞蚁三五成群转移一只死去的蚂蚱,就是看不到地软。秋天的大地上,万物萧瑟,金黄抵抗着时光,我俯下身子,拨开草丛,就只看见大地皴裂,这病了的皮肤上,树叶像牛皮癣一样藏在草木的根部,还是看不见地软。
大人们说,只有冬天才能捡到地软,它们是雪的孩子。我等不到冬天了,在秋天的时候就盼着斗大的雪花赶紧落下来,落在苍茫的大地上,这样,每一寸土地上就能生出地软,这样我的视网膜就能被地软的营养覆盖,每一根视觉神经就能像水管一样,畅通无阻,我再也不用害怕黑暗了。
你还别说,雪一落下来,地软就从土里冒了出来。我们常常说大地开花,大地之上开着的花儿,都有自己的名字,有自己的根系、香味和花语。所有能叫上名字或者叫不上名字的花儿,都为自己开。只有地软,这无根无叶无蕊无香的片状植物,虽然在专业的分类学中隶属蓝藻门,但却常常被忽视。不过在我眼里,它也是一朵花儿,属大地科,它只为大地开放,或者说它就是大地之花,无根但是吸收大地精华,无叶但每片雪花每寸阳光都是它的叶子,无香但在厨房里经过淘洗烹制就能尝出人间冷暖。不过它们并不像那些真的花朵一样,急着让人欣赏让人靠近,它们悄悄隐在草颈之下,等着人们拨开草拨开雪去寻找,它一定喜欢捉迷藏,不过很明显,小家伙们笨拙得挤在一起,只要发现一片,其他的地软就会束手就擒。也有聪明的地软,躲在你找不到的地方。等雪化得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去捡地软,布鞋踩在软塌塌的积雪上,发出沙沙的声音,地软听到声音就躲起来,你怎么找也找不到。
苦苦寻找的除了地软本身之外,还有它的身世。我们好奇的是,大地上的植物,都有自己的来处,要么靠根系繁衍,要么通过种子生长,而地软这匍匐于地又不扎根大地的植物,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最初我们怀疑它是羊粪变的,你看大冬天的,一群羊被赶到洼地里,这一片枯黄的洼地突然就生动了,羊一股风一样过去,地上到处是羊粪,雪落下来,羊粪不见了,地软冒出来,不是羊粪变的难道还有别的?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我们拿地软和羊粪做过比较,虽然都黑乎乎的,但是一个无味,一个臭烘烘,明显不是谁变谁的问题。也有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说得跟天上掉下来个林妹妹一样悬乎,可是谁也没见过从天上掉下来过黑乎乎的东西,这个说法不攻自破。还有一种朴素的说法是灵魂长出了大地,就像星星一样,地上死个人天上就多一颗星星,同理,这世上死个人,地上就长出一些地软来。到底怎样谁也说不清,我们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捡了地软回去吃,我的眼疾竟真的慢慢改善了,能在旷野一眼看到地软,也可以在黑夜里穿过村庄的任意一条巷道。
多年以后,我走出村庄,开始在城市的街巷里行走,眼疾已经完全不用担心,因为每座城市都有很多条不夜的街道,也就是说,我再也不会走夜路碰得鼻青脸肿,每一条路都有光的指引。
说到指引,我突然就想起地软的来历来,那么多年我找寻的问题,似乎有了一个不太科学但是一定富有诗意的答案,你看,抛开地软的专业术语和生物属性不说,单从“地软”两个字的字面来看,地软,不就是大地的细软吗?这些大地的细软,医治好了我的夜盲症,还让我成了一个携带细软走天涯的人。
走得再远,还是要回来。每年腊月,我都会趁着夜色回到故乡,回到这片怀揣着细软的大地。可以不用走亲访友,但是一定会带着女儿去我捡拾过地软的地方,拨开枯草,寻找大地散落在此的细软。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和我一样的人不在少数,年少时曾经佝偻着腰身捡地软的孩子们,已经到了带着自己的孩子捡地软的时候,而这些高不过任何草木,也没有鲜艳的外观,藏在大地的犄角旮旯的细软,不仅用藻类的特性疗治我的眼疾,还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体里装满细软,让我们在离开村庄以后,乡愁丰满,目光有神。
(田鑫,80后,出版有散文集《大地知道谁来过》。)
特约编辑:刘亚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