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不和谐的“复调”演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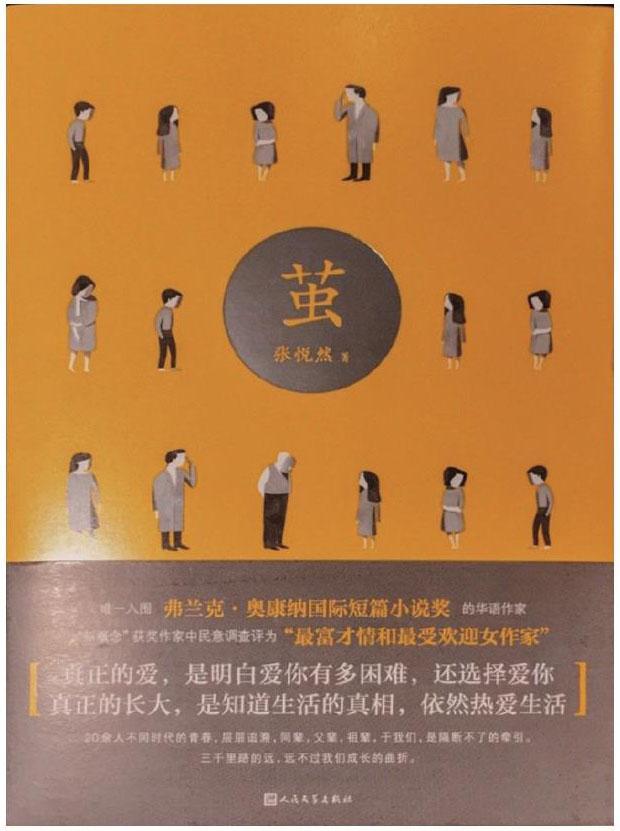
摘 要:从整体上看,张悦然的新作《茧》可以用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解读。小说以男女主人公的对话为结构,叙事在人物的“声音”中推进,符合巴赫金提出的“大型对话”概念。然而《茧》同时又是一部“非典型”的“复调小说”,主要表现在男女主人公的“声音”并不对等,女性“声音”在小说中处于领先地位。这正是作者的目的:在刻意强调的女性“声音”背后,是张悦然对女性命运的独特思考。这种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双重努力,也显示出曾经作为“青春写作”代言人的张悦然向“主流写作”转型的努力。
关键词:茧;“复调小说”;女性“声音”;创作转型
作为“80后作家”代表人之一,张悦然于2016年一推出新作《繭》就受到文坛关注。一方面,有论者借助对张悦然以往作品阅读的经验,直接把目光聚焦在张悦然的创作转型上:“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张悦然选择‘茧作为新作的标题似乎是颇有深意的,除与文本内容的贴合外,它既表达了一种自我期许,也显示出一定程度上的自信。而诸多不吝溢美之词的评论也仿佛宣告着张悦然向‘青春写作的告别已臻完成。”[1]83另一方面,小说中指向历史的叙事也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2]92,因为历史叙事在“青春写作”中可以说是凤毛麟角的存在,张悦然的此番尝试也就自然受到重视。然而,在这一过程中,《茧》在形式上的努力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忽视。实际上,《茧》的对话结构虽然算不上独此一家,但也是当代小说中较为新颖的存在。究其来源,小说中的对话结构非常符合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形式上的刻意创新无疑是张悦然创作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
一、《茧》的“复调性”
“复调”最早是一个音乐术语,指的是某段音乐没有主旋律和伴声之分,而是两段或两段以上的各自独立却又相关的旋律,通过艺术加工与处理之后和谐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良好的整体。巴赫金在总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特征时,巧妙地借用了这一跨学科概念,将这一音乐术语引入文学:“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这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基本特点。”[3]29与此同时,巴赫金认为:“复调的实质恰恰在于:不同声音在这里仍保持着各自的独立,作为独立的声音结合在一个统一体中,这已是比单声结构高出一层的统一体。”[3]50由此可以得出巴赫金关于“复调小说”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在复调小说中,声音应当是互相独立的,应当是“众声喧哗”的,但这种声音上的独立并不代表小说的松散,而是使小说紧密结合成一种更高层次的统一体,即“复调”中声音独立的形式对于小说整体的完整度是有益的。
《茧》在大体上符合巴赫金对于“复调小说”的定义。小说中李佳栖和程恭的“声音”是相互独立而且互不相融的,二人分别在自己的“声音”中完成了对自身命运的叙述。但从整体上看,《茧》的结构并没有因为对话而变得松散,李、程二人越是对话,“声音”中回响的命运就越是统一。此外,把《茧》视为“复调小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小说符合巴赫金“大型对话”概念。钱中文①如此阐释巴赫金的“大型对话”:“‘大型对话涉及小说结构、人物关系结构……一种情况是有意运用不同的调子来结构小说……另一种情况是复调表现为结构上的平行性。”[3]12-13以此来观照《茧》:一方面,小说中张悦然明显地运用了“不同的调子”来处理对话结构,在完成对李佳栖和程恭的阅读之后,读者由此产生的阅读感受也是完全不同的;另一方面,李、程二人各自的“声音”分别完成了对历史的重构,而这种重构是平行开展的,这也就是所谓“结构上的平行性”。由此观之,《茧》的对话结构的确对应着巴赫金提出的“复调性”。
值得强调的是,虽然并没有直接材料表明《茧》在形式上的创新来源于巴赫金的理论,但这种对话结构确实产生了“复调小说”的效果。与之结构类似的还有莫言的小说《檀香刑》。《檀香刑》分为凤头、猪肚和豹尾三部,其中凤头部和豹尾部由第一人称限制视角的眉娘、赵甲、小甲、钱丁、孙丙等五人的“声音”构成。猪肚部虽然是第三人称视角,但也有着明显的、按照人物划分的叙事界限。从结构上看,《檀香刑》同样符合“大型对话”概念,但莫言曾经明确表示《檀香刑》的构思来源于民间艺术,尤其是说唱艺术:“民间说唱艺术,曾经是小说的基础……在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压倒了民间文学的继承的今天,《檀香刑》大概是一本不合时尚的书。”[4]换言之,尽管民间艺术与复调小说植根于不同的土壤,但效果可能相同。因此,即使张悦然并没有刻意按照巴赫金的理论创作,但《茧》能够产生“复调性”也是合情合理的。
总地来说,对话结构和“复调性”是作者在小说形式上的一次创新,也是张悦然向“主流写作”转型努力的一个侧面。“青春文学”曾经受过太多“结构单薄、叙事幼稚”的批评,因此为了摆脱“青春作家”的名号,在小说形式上下一番工夫也就成了张悦然的必然选择。
二、《茧》的女性“声音”
作为一部“复调小说”,《茧》中李佳栖与程恭的“声音”是各自独立、互不相融的,但是二者却并不对等。读者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作为女性主人公的李佳栖,在小说中“声音”的分量是要重于男性主人公程恭的。从叙事内容上看,对李佳栖的叙事中除了祖辈经历的“文革”,还有父辈经历的“下海”热潮等,空间跨度也是从小城到北京甚至远及莫斯科。相比之下,程恭的叙事内容就显得单薄很多。叙事内容的对比显得李佳栖“见多识广”,读者对李佳栖的“声音”也就自然而然地投入了更多注意。另外,李佳栖在情感上也是处于优势地位的。李、程二人的情感经历过波折,产生过竞争,但这种竞争最后将变成程恭对李佳栖“无可救药的爱”[5]123。因此,在两种“声音”叙述的情感中,李佳栖的角色是支配者。这或许是命运带给李佳栖的不得已的苦衷,而这苦衷却也恰恰符合女性主义中“自恋的女人”的提法。波伏瓦认为:“环境更加促使女人而不是男人转向自身,把爱给予自己。”[6]李佳栖的确如此,命运使她更多地关注自己,因此在爱情的层面上,她始终保持清醒,成为理性且占据优势的那一方。
文中最能够体现女性“声音”高于“男性”声音的,则是李、程二人的性经历。在小说中,作为女性的李佳栖的性行为被赋予了一系列意义,其中最主要的意义是寻找父亲失落的历史。程恭作为男性,其性经历则乏善可陈。要么是正常交往中的性行为,比如与女朋友小可做爱;要么干脆是欺负弱者,比如与智力有些低下的陈莎莎之间的隐秘关系,并且这段关系开始于程恭对陈莎莎的强暴。在性经历上,李佳栖多且神圣,与平凡且罪恶的程恭相比,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借助性经历的对比,张悦然使女性的“声音”得到了强化。
值得一提的是,借助性来强调女性是大部分女性文学的常用主题。正如女作家张抗抗所言:“‘女性文学有一个重要的内涵,就是不能忽略或无视女性的性心理;如果女性文学不敢正视或涉及这一点,就说明社会尚未具备‘女性文学产生的条件,女作家未认识到女性性心理在美学和人文意义上的价值。假如女作家不能彻底抛弃封建伦理观念残留于意识中的‘性=丑说,我们便永远无法走出女人在高喊解放的同时又紧闭闺门、追求爱情却否认性爱的怪圈。”[7]《茧》中大量关于李佳栖性经历的描写,无疑是对女性文学这一脉的继承。尽管李佳栖对待性的目的并不单纯,但她在事实上准确认识并且成功运用自己的身体,这一点可以说是非常“女性”的。
《茧》对女性“声音”的强化,除了性描写这一在女性文学中普遍存在的方式之外,还有一种个人化的方式,即对女性反抗意识的书写。反抗意识是新时期以来文学作品常常触及的话题,但是女性文学中对反抗意识的强调却并不多见。很多女性文本停留在对女性身体和性心理的迷恋,甚至滑向“身体写作”的范畴;也有女性作家深刻反思女性命运,却往往与社会意识夹缠不清,也就是所谓的从“私人空间”转换到“公共空间”[8]。值得欣慰的是,张悦然对女性命运的思考并没有直接扩大到整个社会层面,而是将其浓缩成一种具有女性特点的反抗意识——“消极反抗”。李佳栖自然是这种“消极反抗”的代言人。比如小说开头,面对着对自己命运造成无数影响的爷爷李冀生,李佳棲所做的是“现在我只想要他死,把他的死占为己有”[5]8。即使对爷爷有诸多不满,她所做的也是静待死亡对他的审判。最能体现反抗的“消极性”的是李佳栖的恋父情结。恋父是贯穿李佳栖生命的元素,甚至可以说是李佳栖成长的动力。无论是年少时独自前往北京寻找父亲,还是后来与许亚琛等人的性关系,恋父情结都在其中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为了反抗家族和反抗世俗,李佳栖把作为叛徒形象出现的父亲李牧原视作偶像,似乎接近父亲就是接近反抗:“为了逃避,为了掩饰你面对现实生活的怯懦和无能。你找不到自己的存在价值,就躲进你爸爸的时代。”[5]385这种逃避实际上就是李佳栖的反抗,把逃避当作反抗,本身就是苍白无力的,更何况这种逃避本身也并不坚固:“我对爸爸的感情不一样,它非常敏感和脆弱,总是不断受伤。”[5]54以逃避的方式反抗,然而可逃避的地方本身也是脆弱的,因此这种反抗无疑是十分消极的。
总而言之,张悦然借助李佳栖这个人物,通过女性文本中较常见的性爱描写和较少见的反抗书写,双管齐下实现了对小说中女性“声音”的放大,而在这放大的“声音”背后,则是张悦然对女性命运的独特思考。当作品注入了更多思考的元素,尤其是这种思考是关于自身、关于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时,“青春作家”的名号自然也就离张悦然越来越远。
三、向“主流写作”转型的得与失
从小说产生的效果来看,张悦然无疑做出了摆脱“青春写作”、转向“主流写作”的努力:《茧》由国内地位最高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张悦然也因此跻身第十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之一。相比其他“80后作家”,张悦然受到了主流文学界更多的肯定与欢迎:在韩寒和郭敬明依靠电影消费粉丝时,张悦然已经拾起人大教鞭,走上了一名主流文学作家应当走的道路。的确,这种努力是值得肯定的。《茧》无论是在形式上力求创新、实现“复调”,还是在内容上指向历史叙事、思考女性命运,都是对“青春写作”业已僵化的题材的突破:“对张悦然而言,这是对其写作困境的一次有效突围,显示了她作为一个写作者的自觉。”甚至可以说,张悦然代表了整个“80后作家”群体面对十字路口的转型努力:“而作为80后写作的代表之一,张悦然在写作上的转向对更新公众对80后写作的固有印象具有重要意义。”[2]94
但不得不说,张悦然的转型还有诸多不够完美的地方。一方面,在个人话语与历史话语的交锋中,二者始终没能有一个明显的界限。张悦然试图把人物命运完全地楔入历史潮流之中,反而造成了一种不真实感。比如李佳栖的父亲李牧原,他短短的生命却几乎经历了上个世纪所有的重大事件,从上山下乡、恢复高考再到政治风波、经商热潮,这难免使人感觉人物的命运是为了迎合历史事件而可以捏造的。更遑论一些无关紧要的对历史的议论,比如对20世纪80年代的看法:“那个时候的人心还没有埋得太深,还是可以把它谈出来的。”[5]76这些都使人觉得作者为了加强作品的厚重感而刻意为之。另一方面,“青春写作”的影子在《茧》这部小说中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比如小说中依然存在着明显的成长小说的痕迹:“如果说向历史纵深处的开掘是《茧》所取得的突破之一,那么对成长小说模式的套用则表现出其对早期写作‘遗产的承袭。”[1]85此外,叙事节奏的拖沓和主人公的性格特质也仍然有着“青春小说”的痕迹。但这种残留也是在所难免的,对于一个转型期的青年作家来说,这种转型本身便是一件值得瞩目的事情。正如张悦然在后记中所说:“文学的意义是使我们抵达更深的生命层次,获得一种从未有过的体验。”[5]424这种对文学的追求,无疑值得被肯定。
注释:
①钱中文是国内较早进行“复调小说”理论研究的学者。1983年,钱中文在“中美双边比较文学讨会”上宣读的论文《“复调小说”及其理论问题——巴赫金的叙述理论之一》对于国内“复调小说”理论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1]杨有楠.“破茧”的艰难——从长篇新作《茧》看张悦然的创作转型[J].当代文坛,2017(1):83-87.
[2]蔡郁婉.追溯与断裂——论《茧》中的历史叙事与个人话语[J].艺术评论, 2017(1):88-94.
[3]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白春仁,顾亚铃,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4]莫言.檀香刑[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414.
[5]张悦然.茧[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6]波伏瓦.第二性·Ⅱ[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475.
[7]张抗抗,刘慧英.关于“女性文学”的对话[J].文艺评论,1990(5):69-71.
[8]张浩.从私人空间到公共空间——论王安忆创作中的女性空间建构[J].中国文化研究,2001(4):159-164.
作者简介:许亚云,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
编辑:高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