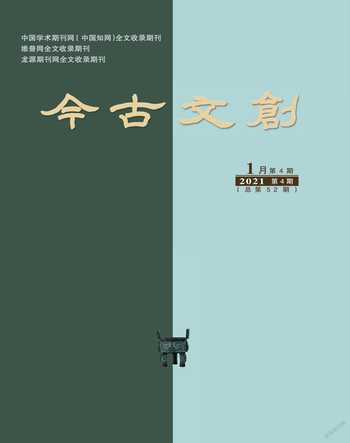印度尼西亚元哲学有无之问
郭露 何冠岐
【摘要】 印度尼西亚是否有自己本土哲学这个问题一直都困扰着印尼学界,虽然现在的印尼不乏学者研究西方的分析哲学、现象学、政治哲学和伦理学,哲学科目,甚至有精通希腊古典哲学的专家,但是对于印尼自己本身的哲学却一直处在迷惘之中,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因为印尼独特的历史进程使然,寻找印尼原则学的答案在于印尼传统文化的作品之中。
【关键词】 印度尼西亚哲学;元哲学;构建元哲学来源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04-0047-04
印度尼西亚(下称印尼)是否有自己本土哲学这个问题一直都困扰着印尼学界,虽然现在的印尼不乏学者研究西方的分析哲学、现象学、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等哲学科目,甚至有精通希腊古典哲学的专家,但是对于印尼自己本身的哲学却一直处在迷惘之中,换句话说,印尼学者一直在探索的问题是印尼存不存在元哲学?
所谓元哲学就是元哲学是对“哲学为何物”这个问题进行理想化和抽象的刻画。(Double;1996:22)印尼学者们关于“印尼的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即找不到传承也找不到方向。
更具体地说,如果按照道布尔划分元哲学的四种类型即对人生活贡献艺术性的对话、改变自身和世界的实践性理论、作为社会和思想观念的精神支撑以及作为一种能够精确刻画外部世界实在的世界观去从印尼本土著作中寻找元哲学颗粒依旧难以找到成体系的文本。
印尼学者艾尔·马金(Al Makin)如是说:“印度尼西亚人的作品中可能没有明确提及哲学一词。印尼本土是否有哲学著作或能否产生哲学家是我们经常提及的一个令人生畏的问题。(Al Makin;2016:2)”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困惑,其原因跟印尼本身哲学历史的进程有密切的关系。
本文把印尼哲学史发展划分成启蒙时代、建构时代、重构时代和迷惘时代四个时期,通过梳理印尼哲学的发展史归纳印尼困于本土是否有哲学或哲学家这个问题的原因并试图提出一些能够构建印尼元哲学的研究路径和方案。
一、印尼哲学的启蒙时代(15世纪— 1945)
在15世纪之前,印尼这片土地上诞生国一些不同信仰的王朝,例如信奉佛教的三佛齐王国和同时信奉爪哇传统信仰、印度教、佛教、泛灵论的满者伯夷国。不可否认这些王朝确实留下了一些关于印尼元哲学的文化遗产,至少宗教信仰的存在就是一种社会和思想观念的精神支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印尼进入了哲学史的时代,首先这些王朝没有完成印尼群岛的大一统事业,作为精神支撑的宗教哲学具有地域性,难以普及和传承;其次这种在封建王朝下出现的宗教多为封建统治者的政治工具,不具备构建为哲学的条件。
所以印尼哲学的启蒙时代是从15世纪开始的。因为荷兰殖民者统治印度尼西亚期间很多印尼地接受了西方教育,由此西方的哲学思想开始渗透入印尼人的思维方式中,印尼人真正成体系化地了解哲学也是从这个时代开始的(Al Makin;2016:3)。但是因为这个时期了解了哲学的印尼人对于哲学的需求是有时代背景特点的,所以他们学习和运用哲学的方式带着明显的目的性。尤其是在殖民时代的后期,越来越多的印尼人民希望摆脱殖民者的统治获得独立自主的权利,故而大多数以民族主义精神为民族独立运动的印尼领导人都引用了西方带有民主意识的哲学家作品,例如卡尔·马克思,黑格尔和其他西方文学作品。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印度尼西亚第一任总统苏加诺、马拉卡(T·Malaka)、 塔杰特罗米诺托(Tjokroaminoto) 三人作品。他们的作品中经常表达西方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在支持那些民族独立而奋斗的哲学思想,比如他们的作品中时常提到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共产主义这类思想(Al Makin;2016:5)。
尽管在这个时期印尼人民对于哲学的理解是来自于西方,但是西方的哲学作品同样教会了印尼学者关于提供价值、规范、智慧、知识、推理以及其他哲学思考过程,没有哲学思考的过程哲学体系的形成也会成为可能,故而在殖民时代到印尼独立之前的这段时间是印尼哲学史的启蒙时代。
二、印尼哲学的构建时代(1945-1967)
之所以把这个时间段称为印尼哲学的构建时代是因为印尼摆脱殖民者即将独立的时候,是因为受启蒙时代西方哲学的进入以及印尼民主运动领袖受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将西方哲学与印尼融合在一起并寻求印尼元哲学身份的创新方法很普遍。这也是印尼有识之士从对西方哲学单纯的“拿来主义”加入自身文化因素的第一次尝试。
在独立前夕,印尼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处于鼎盛时期,很多学者将欧洲的批判性思维方式与印度尼西亚的传统文化的背景相结合,产生独特的反思方式。
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印尼民族主义运动早期领导人穆罕默德·亚明(Muhammad Yamin),他在解释民族主义意识对群岛人民的重要性的过程中,借鉴了欧洲历史上对民族主义的定义的同时还回顾了殖民时期之前的印尼历史。他描绘了满者伯夷国国王加贾·玛达(GajahMada) 的英雄形象,并提出了加贾·玛达统治期间满者伯夷国的多宗教文化传统,继而把西方哲学的民族主义和满者伯夷国的文化传统相结合,以此创造印尼元哲学的研究路径(Al Makin;2016:7)。
这种构建元哲学的方式在独立前后的印尼广受关注,包括总统苏加诺在内的印尼领袖都乐于以这样的方式去找寻印尼的元哲学,而这种构建方式也取得了一个相对令人满意的成果,那就开国领袖苏加诺称之为印尼“基础哲学”的潘查希拉。
潘查希拉是从印尼語Pancasila音译而来,也是印尼的建国五项基本原则,即“信仰神道”“国际主义”“民族主义”“民主协商”和“社会正义”(苏加诺;1956:7)。从这五项建国原则就可以看出当时的印尼哲学深受西方哲学的影响,除了信仰神道之外,“国际主义” “民族主义”“民主协商”和“社会正义”这四个理念都来之于西方,而信仰神道则是满者伯夷国的特色,故而在这个时期,印尼事实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他们的元哲学,尽管其上有着西方哲学的烙印。
三、印尼哲学的重构时代(1968-1998)
继苏加诺之后成为总统的苏哈托采取了很多和其前总统不同的治国理念,在这个过程中,印尼的哲学体系也受到了深远的影响。尽管苏哈托还是把潘查希拉作为印尼的建国五项基本原则,但是对于原则本身的解读却已经和苏加诺时代大有不同。其基本的特点是引导印尼的年轻人否认前总统苏加诺的功绩以及他结合了西方哲学因素构建的印尼哲学,并且以否认先辈的功绩来借新秩序之名巩固苏哈托自身的政治霸权。在这之前,印尼的哲学构建在西方哲学和殖民时期的印尼历史之上,随着苏哈托对于苏加诺的全盘否定,找寻新的印尼哲学构建路径就成为了苏哈托的重要工作。
在构建时代期间,苏加诺为了激起印尼民众的民族主义爱国情绪,使用了批判“敌人”来定义新的民族身份的方式。在独立之前,印尼人民的敌人是荷兰殖民政府,因为他们剥夺了国家的财富并剥削了人民。
在独立之后,印尼人民的敌人是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阵营。苏加诺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指出了西方国家是一个资本主义阵营,狡猾地利用了发展中国家的财富。因通过这样的方式苏加诺确实得到了人民的拥戴,但是在重构时代期间,苏哈托把苏加诺的理念完全推翻,更把印尼在 1965 年因为政权更迭的(事实上是他自己造成的)动荡原因归咎于共产主义。因此在苏哈托的总统任期时,在教育、思想和国家政策上得到推广的所有政治言论以及哲学作品都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内容。
苏哈托在关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门同时也摒弃了把西方哲学和印尼历史相结合的元哲学构建方式,而是以教育推广、法律限制、媒体宣传等方式重构了一种个人哲学 ,这种个人哲学针对每一个印度尼西亚人民,强调这种自我约束和自我控制,实际就是在灌输教育和法律控制 ,因此在印尼哲学的重构时代,印尼哲学被苏哈托作为一种强化政权的政治工具利用了。
四、印尼哲学的迷惘时代(1998至今)
1998年,苏哈托的统治结束,印尼的哲学和他们的政治一样迎来了新时代,但是因为苏加诺和苏哈托两届领导人对于哲学构建方式差异导致了印尼的哲学陷入了迷惘期。尽管在构建时代和重构时代时,印尼都确立了潘查希拉的国家哲学,但是对于这个国家哲学的解读却大不一样,随着苏哈托统治的结束,他试图重构印尼哲学体系也开始崩塌,显然没有人原因去构建一个为了强化某个人政治权利的国家哲学,但是另一方面苏加诺构建的西方哲学和印尼殖民前历史结合的哲学随着苏哈托的统治时期停滞了整整三十年,加上苏哈托三十年统治给予印尼哲学的影响,印尼哲学的未来何去何从又陷入了争论中。
虽然对于构建印尼哲学体系的争论很多,但是所有哲学工作者都达成了一个初步的共识,即印尼的哲学需要建立在结合西方哲学和东方哲学的基础上。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和自苏哈托统治结束之后,印尼越发的渴望融入国际社会的情况有着必然的联系,印尼人希望通过哲学构建找寻本身的身份认同,即要印尼国民认同自身的身份也想国际社会对他们认同,而这种身份就是用一种包容地多元化哲学体系来实现,印尼学者认为只要印尼对的哲学体系是多元化的,那么就可以跟不同语言、政治体系的国家找到共同点。
这既和构建时代时西方哲学结合印尼历史的哲学构建方式不同,也和苏哈托那种政治灌输式的哲学构建方式不一样。除了一如既往地注重西方的哲学思想之外,中国和日本的哲学文化被印尼学者纳入了视野中,印尼的潘查希拉五個主导思想之一的信仰神道从构建时代的泛灵论过度到了苏哈托时代的六种合法宗教,而在六种合法宗教中,来自中国的儒家思想也成了一种合法宗教,即孔教。
在印尼人的视角里,儒家思想中的忠孝仁义都是孔教的思想,这也是东方文化进入印尼哲学构建的代表方式。同样,另外五种合法宗教的思想也以这种方式进入了印尼哲学的构建中,这样的情况下,要构建印尼的哲学就绕不开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如何把宗教和西方哲学那种思辨精神结合起来。
事实上对于印尼哲学的构建是回归到宗教虔诚或西方理性思维本身就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对于渴望参与到全球化进程的印尼来说,这两样因素都是他们构建哲学体系必不可少的,因为无论两者都是外来文化,首先六种合法宗教伊斯兰教,天主教,新教,印度教,佛教和儒教都来自外国,而西方的理性思维则是毋庸置疑的舶来品。
结合六种宗教传统和西方思辨精神意味着印尼哲学体系的多元性和世界性,同时又承认印度尼西亚传统由外国元素的不同部分组成。但是要把六种宗教和西方思辨哲学结合起来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纵观哲学史。还没有任何一个哲学家能够把几种宗教和西方的思辨哲学相结合而成一种独特的哲学体系,何况印尼的六种宗教文化本身就有南辕北辙的世界观和思想,更遑论把这六种宗教和思辨哲学将结合了。
五、构建印尼哲学的四可能来源
构建印尼自己的哲学史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课题,没有人能够给出最终的答案。艾尔·马金认为构建印尼自己的哲学体系需要重新阅读印尼历史上思想家们的手稿和文本,甚至包括那些并没有明确地全部涉及哲学或任何思想体系文本。这种作品可以是各种形式的,例如诗歌、日记、甚至是教义或者只是在寺庙的石头那些只言片语的记录。
印尼学界已经承认了印尼的文本没有明确提及哲学一词。但是,这正是赋予印尼哲学界的一个新任务,即在其中重新发现哲学的某些要素或基础,并将其按照如亚里士多德或者柏拉图思想体系进行系统化。换句话说,艾尔·马金认为通过印尼学者们的努力,通过重新诠释的方法把文本中的哲学元素提炼出来,是可以构建印尼自己的哲学体系的(Al Makin;2016:13)。
根据印尼哲学界现今的探讨,关于构建印尼哲学体系的文本来源具体来源可以总结为四种,即流传到印尼的印度佛教精神、印尼本地的文化传统、在印尼落地的伊斯兰文化和现代思想基础。
其中找寻流传印尼的印度教佛教精神的文本不仅仅限于书籍,而且还涵盖了物质文化,例如寺庙或古代建筑作品。以及像 Syang 、Hyang、 Kamahayanikan 这样的旧著作仍然可以使用。
但总的来说,印尼从这一古老传统中继承的著作太少了。但是,在日惹、东爪哇、中爪哇、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发现的以庙宇形式出现的材料依旧被发现了一部分,可以用新的解释来解读。总的来说,留存在印尼从印度佛教的文本不多。
但是,在日惹、东爪哇、中爪哇、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诸多地区发现的以庙宇形式出现的文本来源依旧相对丰富,可以让学者们进行新的解读。至于解读的方式,印尼学者们倾向于把印度佛教精神的哲学智慧带入印尼20世纪初的思想家努桑塔拉的新语境进行解读。因为努桑塔拉的新语境解读发更适用于外国的思想。
同样,印尼学者们主张重新解释如今仍在印尼各地口头传播的地方传统和智慧,他们认为这些已成为许多地方宗教习俗中保留的活体哲学。就像建筑作品中保存的物质文化一样,这些文本需要重新阅读。把这些文化以哲学的角度切入实当下印尼哲学重构印尼哲学的重要任务。
关于从印尼的伊斯兰文化找寻哲学文本来源相对前两者来说更为简单一些。印尼作为一个90%左右的國民都是伊斯兰信徒的国家,伊斯兰教的文化涵盖了印尼广泛的书面文学领域,这形成了独特的印尼伊斯兰文化。
印度尼西亚的宗教史证明印尼苏门答腊岛是印尼伊斯兰教的发源地和故乡,印尼的伊斯兰教融合了当地文化以及诸如波兰、印度和阿拉伯等外来文化衍生而成宗教信仰。而印尼的另一个岛屿苏拉威西岛至今还是一个秉承着融合主义的地方,各种新传统常常在这个岛上诞生。同样地,如印尼的小巽他群岛也孕育了一种独特的融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与当地传统文化融合的宗教。因此印尼的伊斯兰教除了具备了系统的宗教精神之外还融合了一些外来文化和当地传统,显示除了一定的包容性,从这里面找寻哲学文本来源相对前面两者资源更为丰富一些。
从荷兰殖民时期印尼实现独立,如马拉卡、塔杰特罗米诺托、苏加诺等人著作毫无疑问地对印尼人民族主义精神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受西方哲学的影响,这些作品包含着最为明显的哲学智慧,要重构印尼的哲学就应该对这些作品进行梳理和解释,把里面的哲学精神框架化跟合理化。就算做不到,从这些著作中至少可以发掘出印尼哲学认识论的基础,因为这个年代的著作更跟潘查希拉的形成有极大的关系,只要印尼没有抛弃潘查希拉,重构印尼哲学就无法绕过这个时期的相关著作。
六、结论
显然,印尼的元哲学就在重新诠该国各种类型的作品中,这是找回印尼元哲学最为重要的藏宝图。问题在于印尼的学者们是否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有信心。毕竟印尼历史作品从没有明确哲学思维。要从这些作品中发掘出哲学思维显然是一个琐碎而长远的工作。换句话来说,发觉印尼哲学的任务能否实现取决于印尼哲学以及有志于研究印尼哲学学者的态度。印尼学者们自己的传统文化的信念是否坚定?研究印尼哲学的哲学是否相信能够在印尼的作品中重构印尼元哲学的内核?这两个问题是找寻印尼元哲学的关键。
值得一提的是,印尼学者的自卑感是找寻印尼元哲学的主要障碍,因为印尼学界认为印度尼西亚的文学作品和文化遗产不会产生任何思想体系,更不用说哲学了。原因在于印尼作品中的世界观显然不能和中国、希腊、拉丁、 阿拉伯的古典文化或现代欧洲的分析哲学相提并论。印尼在感知这一现实时提供了自己的“哲学”方式。鉴于此,印尼是否确实有元哲学的哲学作品并不取决于自封的哲学家或哲学作品的可用性, 而是取决于能够欣赏和批判性理印尼作品的读者。
实际上,在印度教佛、伊斯兰教和西方殖民主义时期,印尼人民与生活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其他人一样,从未停止思考关于他们本身、他们的社会,他们所处的环境,他们的信仰他们与世界的联系。所以找寻印尼元哲学的关键就在于找寻印尼作品中没有被充分理解的哲学元素,然后重新阅读、理解和阐发。
参考文献:
[1]Double R. Metaphilosophy and free will[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n Demand, 1996.P22.
[2]Metametaphysics: New essays on the foundations of ontology[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P1.
[3]Makin Al. Are there any Indonesian philosophers? Dealing with a common question and possible answers[J]. Ulumuna, Journal of Islamic Studies, 2016,P1-28.
[4]苏加诺.苏加诺演讲集[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7.
[5]王子昌.国家哲学还是个人哲学?——对印度尼西亚建国五基的文本解读[J].东南亚纵横,2003,(12):50-55.
作者简介:
郭露,女,广西柳州人,广西机电技师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文学。
何冠岐,男,广西南宁人,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