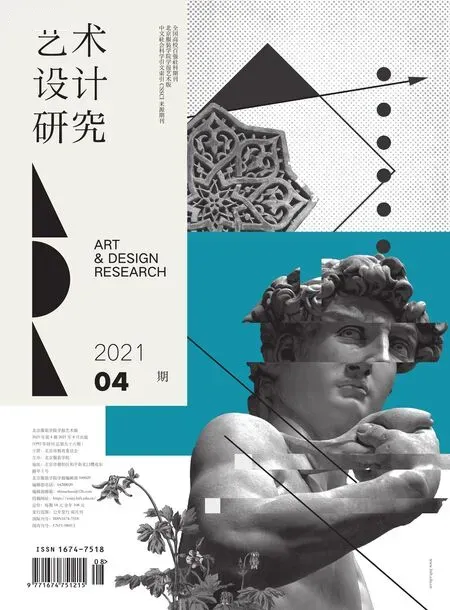东亚佛足迹的样式、图像结构与风格问题
祁姿妤
一、引子:玄奘、王玄策与东亚中古时期佛足迹的关系
佛陀生前并未离开过中印度,如何在中印度以外的时空制造与佛陀相关的图像与故事,是佛教不断发展壮大的历程中不可避免要面对的难题。早期中印度地区使用佛足迹石暗示佛陀。①随后贵霜时期在西北印度运用与佛足迹石相关的佛陀圣迹神话故事来营造佛陀到过西北印度的佛教文化背景;与此同时,东南印度延续了早期中印度图像传统,形成了复杂图案的佛足迹图像。佛足迹的“复杂图像”与“神话故事”历经融合、东传,形成了东亚佛足迹的图像与文本,并以佛足迹石、石碑、纸本等多种媒材为载体进行传播。
这些不同载体上的图像与文本有共性,也有差异。其中最为关键的分歧在于:在日本佛足迹铭文或题记提到佛足迹是由王玄策带回中国,继而传到日本的;而中国、韩国的材料提到佛足迹是由玄奘带回中国的。中日学者分别基于本国的材料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经历近半个世纪的对立与融合,依然存在种种无法调和的图像矛盾。
1、佛足迹图像东传的问题
(1)一方面,自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兴起了对奈良六大寺院的研究并出版相关图册,其中也展开了对奈良药师寺佛足迹石的研究。②日本学界普遍认为“佛足迹是由历史人物王玄策带回中国,继而传播到日本的,在日本奈良药师寺保存着东亚最早的佛足迹石(752)”③(图1)。这类观点可被视为 “根据铭文中的王玄策来区别佛足迹的样式”(图2)。孙修身注意到了日本药师寺的佛足迹石的重要性,他援引王玄策相关传记,推论佛足迹石是由王玄策在第二次遣使印度(648年)带回到中国的。④

图1:日本奈良药师寺佛足迹石线图

图2:日本奈良药师寺局部铭文线图
(2)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考古学家基本持“玄奘说”,譬如韩伟、李静杰、霍巍等前辈学者。⑤韩伟先生援引《大唐西域记》和中国陕西宜君玉华寺出土的佛足迹碑铭,认为碑文中记载的“玄奘图写佛足迹回中国”一事是史实,而且玉华寺佛足迹石碑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佛足迹图像实物(高宗显庆四年658~永徽元年664)(图3、图4)。⑥这样一来,中国学者认为玉华寺佛足迹石要早于日本药师寺佛足迹石(752),成为了东亚最早的佛足迹石。可将这类观点归类为“根据铭文中的玄奘来区别佛足迹的样式”。

图3:陕西宜君玉华宫佛足迹石残片复制品照片

图4:陕西宜君玉华宫佛足迹石拓片
(3)后来,李静杰综合了日本学者丹羽基二的观点并进行了实地考察,提出玄奘和王玄策都有可能带回佛足迹图像。玄奘带回一种图案复杂的和一种图案简单的图像,王玄策带回的是图案复杂的图像。玄奘带回来的佛足迹粉本脚掌有通身纹、足跟有须弥山型三宝标,代表案例是陕西宜君玉华寺;王玄策带回来的佛足迹粉本脚掌无通身纹、足跟有海螺型三宝标。他曾对比中国玉华宫与日本京都观智院的版本,提出以有无“通身纹”来区分玄奘与王玄策所带回来的佛足迹石。⑦这种人名(决定)图像样式的观点开始增加了更多细节:
王玄策—佛足迹样式1(内有海螺型三宝标)
玄奘—佛足迹样式2(内有须弥山型三宝标、通身纹、多种图案)
(4)另外,斋藤理惠子还提出了“玄奘从摩揭陀带回佛足迹粉本、王玄策从鹿野苑带回佛足迹粉本”的观点。⑧继而,霍巍在此基础上还对比了陕西玉华宫与奈良药师寺的版本,把佛足迹周身有无放射光线,作为区别玄奘、王玄策两人名下的佛足迹图像的标志。⑨这些观点都是延续了用碑文中的人物来区别图像的思路,并且将图像不同的原因归因于印度不同地区存在着风格差异。我将这类思路归类为“人名(决定)地名(决定)图像样式”的模式。即:
玄奘—摩揭陀国—1有放射光线的佛足迹样式
王玄策—鹿野苑—2不发光的佛足迹样式
这种图像与文本关系的观点看上去调和了图像、人名与地名之间的关系,由于人名而所选取的判定图像样式的特征并不统一,是否能通用于所有材料还有待论证。在印度本土尚未发现集中于摩揭陀国或鹿野苑的佛足迹石实物。大部分有复杂图案、与东亚佛足迹图像相似的佛足迹石集中出土在2~4世纪的东南印度,而非中印度的鹿野苑或摩揭陀国。
以上便是佛足迹图像近半个世纪以来呈现出的学术问题分野。究其根本在于佛足迹图像产生较为早且图文分离发展,并不能直接使用“二重证据法”解释它的图像发展问题。佛足迹图像的分类标准值得被重新探讨。而探讨人名、图像样式、图像风格之间的关系,需要一个动态的对比过程。总结方法论得失、与探讨对比过程本身,很可能比“东亚佛足迹图像是由玄奘还是王玄策带回中国的”这一问题,更为重要。因此本文将采用传统绘画史、艺术史以来的风格分析方法,拆解“人名(决定)佛足迹样式”的分析模式,以时代风格的方法重新讨论图像自身变化的原理。⑩
2、传统绘画史中的人名与样式
从碑文中的人名来判断图像样式的做法,之所以被沿用了半个世纪,主要是由于中古时期的佛足迹石都是发掘出土物。足迹石中的碑文被视为一种真实的历史记载。纸上文献与碑刻中的文字相照应的二重证据法,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种科学的考据方法。但佛足迹石原本是被放在地面上供世人观看,后来这类图像逐渐出现在纸本绘画、版画、石碑中,仍具有一定被观看的公共性意义。对佛足迹这类实物、题记的理解方法,应更类似于理解传世绘画作品。
中古时期,绘画史中也出现大量“人名加样式”的叙事结构。有一些将时代风格相似的作品附属在知名画家名下籍以流传的情况。比如,在中古时期中国绘画史上有“四家样”,分别对应的是张僧繇、曹仲达、吴道子、周昉的四种风格。虽然这些画家名下的作品早已散佚,但他们名下的作品风格一直在传承,至今可以参照一些同时代出土的作品进行对照研究。张僧繇画“凹凸花”被认为是一种天竺画法、曹仲达画佛像“曹衣出水”,被认为与笈多时期的湿衣佛像表现一致等等。其实这些新时代的风格或来自域外的新风格一旦与中国本土画家结合在一起,便形成了一种个人风格,便可在本土长久流传下去。
来自印度的佛足迹图像是如何与中国的访印人士产生关联的呢?是否也与中古绘画史保持着一直的书写思路?玄奘、王玄策这两个人分别与佛足迹图像的关系,通身纹、放光的放射线能否作为图像的分类依据,是需要再度验证的。
20世纪以来,美术史形成了对于作品的风格分析的方法体系,具体可以从时代风格、区域风格、个人风格等维度,来探讨作品是怎样被绘画和雕刻出来的。以下将通过对佛足迹本体的图像内容和雕刻风格进行分析,从而加深目前对该图案性质、风格来源的认识。
二、东亚佛足迹的图像内容研究
1、图像内容:三组符号组合
以往研究往往将佛足迹实物视作单个个体分析其图像特征。在中国唐至明清时期佛足迹图像在数目和图像内容上变化不大。五代僧人义楚在《释氏六帖》中最先描述了他所见到的陕西宜君玉华宫佛足迹石是何模样。
“西域记云,佛在摩揭陀国波吒釐城石上印留迹记。奘法师亲礼圣迹,自印将来。今在坊州玉华山镌碑记之。赞云:‘代金轮我佛尊,遗留圣迹化乾坤,慈悲因地修行力,感果亲招千幅轮。’其佛足下,五足指端有卐字文相,次各有如眼,又指间各有网鞔,中心上下有通身文。大指下有宝剑,又第二指下有双鱼王文,次指下有宝花瓶文,次傍有螺王文。脚心下有千幅轮文,下有象牙文,上有月王文。跟有梵王顶相文。”⑪
据韩伟先生在报告中所述出土情况,玉华宫佛足迹石碑是具有复杂图案的佛足迹。⑫陕西宜君玉华宫出土佛足迹石的实物藏地不明,目前在玉华宫展出的是佛足迹石的复制品。⑬从拓片图像中可以看清足跟有梵王顶相文,对应海螺型三宝标、脚掌有四图案(双鱼能明确看得清)、单线通身纹、月王纹和象牙纹;脚掌轮廓都比较方正。
由于图3、图4清晰度有限,可参照图5明代山西五台山塔院寺佛足灵相之碑的局部线图,来理解东亚富有多种小符号的佛足迹内部的基本布局。综合印度佛足迹石在西北印度、东南印度的分区分期特征,⑭可将东亚佛足迹的基本结构再细分为三组符号:主体图案三种、副图案四种、肌理装饰图案和轮廓线。不同的组别能够体现出不同的图像性质与历史。

图5:山西五台山塔院寺佛足灵相之碑局部线图
(1)佛足迹主体图案为三种图像,即“脚趾有卍字纹(有的大脚趾为棕榈纹图案)、足心有法轮、足跟有三宝标。对应义楚描述中的“五足指端有卐字文相、千辐轮相、跟有梵王顶相文”。这三种图像的图像组合可追溯至2~4世纪贵霜时期西北印度马图拉出土的坐佛足底、犍陀罗周边出土的独立佛足迹石,于3~4世纪传到东南印度。“卐字纹、法轮、三宝标”图像传入东亚后,一直是佛足迹图像的主体,只是在画法上略有差异。
(2)脚掌有四种图案。在唐代至清代的中国、和清代的韩国佛足迹脚掌中,皆为绕帛的宝剑、双鱼、水瓶、海螺,顺序从大脚趾向小脚趾依次排列。参考印度和斯里兰卡的佛足迹石,绕帛的宝剑在南亚原来可能是旗帜的图形,后来传入中国传摹变形为绕帛的宝剑。目前所见中古时期的中国佛足迹图像部分为绕帛的宝剑只有玉华寺一例且残损。宋代以后,由于采取版刻和石碑拓印的方式,图像保留非常完好。因为日本并没有使用严格的刻版或拓印的方式传承,17~19世纪绕帛的宝剑在日本又发展出金刚杵图案。
(3)肌理图案有通身纹、象牙纹、月王纹、轮廓线。一般来说,佛足迹两脚内侧由上自下刻画月王纹、象牙纹,笔直的通身纹从足心车轮通向二、三脚趾。目前尚未在印度发现“月王纹、象牙纹,通身纹”这类图案。虽然公元1~3世纪的贵霜马图拉坐佛足底就已经出现了佛足迹图像,但当时只具有“万字纹、法轮和三宝标”三种主题图案,且足部较为平坦。因此,原本应该是出现在平面图像中,用来再现雕像足底的立体起伏,是一种足底肌肤褶皱肌理的程式化表现。这类图案在中国、日本的平面线刻图像中都出现过,如中国陕西宜君玉华宫佛足迹石与日本奈良药师寺佛足迹石。
2、通身纹图像性质的讨论
与脚掌四图案、法轮、三宝标等图案相比,通身纹是一种足底肌理性质的图像,能够作为区别与玄奘和王玄策有关的佛足迹图像吗?
中国玉华宫佛足迹石碑、日本奈良药师寺佛足迹石分别被归属于玄奘和王玄策名下,但均有单线通身纹。有题记表明日本奈良药师寺佛足迹石、日本京都观智院纸本佛足迹属于王玄策名下,但前者有通身纹,后者并无通身纹。可见,中古时期,有无通身纹、单线通身纹或双线通身纹等多种情况都频频出现,与佛足迹所属国家和人名归属均无关。
中、日同时存在单线、双线通身纹的佛足迹石。玉华宫佛足迹石年代被判定为唐代显庆四年至麟德元年(658~664),下线最迟也不会晚于义楚访碑的时期,药师寺佛足迹石的年代在752年。以上2例均为单线,而双线通身纹出现的时代很可能晚于单线通身纹。10世纪奈良药师寺金堂主尊足底也出现了复杂型佛足迹图像,其中包含双线通身纹(图6)。在药师寺佛像起伏的足底原本没有必要雕刻三种肌理图案,但这里的肌理图案应该已经与其他图案完全组合起来,被描绘成起伏的足底了。可见,通身纹作为肌理图案又被刻画在佛像足底和平面雕刻中都出现过,而且双线通身纹出现得较晚。

图6:日本奈良药师寺金堂佛像足底
因此,东亚复杂图案的佛足迹图像中的通身纹的性质,属于描绘足部肌理、起伏效果的装饰图像。无论是双线的还是单线的,都源于平面绘画对造像上肌理的模仿。而且据目前的实例统计,通身纹尚不能成为作为判定佛足迹属于玄奘还是王玄策的依据。另外,奈良药师寺佛足迹石周围的放射线是对碑文中“光明炳照”描述的图像再现,且处于佛足迹轮廓以外,也不具有能作为区别诸多实例的图像标准而普遍应用在各项案例之中。
三、三种风格的论证
五代僧人义楚记载的小符号与现存中国佛足迹实物图案在布局上基本能够一一对应、图案数目一个不少。但画了什么和怎样画是两个问题。文字描述无法反映轮廓和三宝标的形状变化,因此有关风格方面的规律一直没有被总结出来。
不同时代、地域的画法会形成相对稳定的绘画、雕刻风格。如果将佛足迹图像所依附的载体视作一类作品群体来看,佛足迹的风格会伴随着载体的不同,而分别呈现出三类风格。佛足迹在印度本是石块形态,唐代传到中国后形成了上图下文的纸本、碑刻形态,三种载体形式图案大体一致,也都传入了日本。南宋时期,为了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清晰,曾经以雕版重绘佛足迹图像,便派生出第二种风格,继而影响朝鲜半岛。唐代传入日本的佛足迹在日本也发展出了本地多种次生图像。这三类不同风格之间的区别也体现在足迹肌理图案中的轮廓、主要图案中的三宝标和脚掌图案之中。
1、第一种风格与玄奘、王玄策的关系
第一种风格,处于唐至五代(8~10世纪)的中国和日本。中古时期,佛足迹石、佛足迹纸本形式在日本被保留下来。
这类图像的主要判断依据有:佛足迹单线轮廓较为接近矩形,大脚趾第一跖骨并不突出。足跟三宝标两侧有海螺图案,三宝标的法轮下方是连续弧线。其对应文本显示出:在日本的佛足迹石与王玄策有关,在中国的佛足迹石与玄奘有关。⑮
中国与日本的诸多例子包括日本药师寺佛足迹石、药师寺金堂坐佛足底、京都东寺观智院纸本(图7)、玉华宫佛足迹石碑等。
(1)风格分析
这一时期的中日佛足迹,不论在铭文中被划归给谁,它们的符号、轮廓、风格都是相对一致的。
轮廓方面,中国玉华宫与日本药师寺佛足迹石,所绘图像也比较一致(玉华宫看不清右足和左足右一图案),两者的轮廓形状与线条都比较一致,属于同一类时代风格。这种风格承袭早期中印度、东南印度、斯里兰卡佛足迹石的接近矩形的轮廓特征,并不强调人足曲线的特点。在中国内部,这应该是从唐代流行到五代、北宋的一种时代风格。而在日本这种风格流行更久,甚至持续到现当代。
从描绘足内符号来看,中国玉华宫佛足迹石碑和日本京都观智院的佛足迹图像都属于同一种类型(图7)。这种图像在日本奈良药师寺金堂造像的足部也得到验证。

图7:日本京都东寺观智院旧藏纸本佛足迹图像
海螺型三宝标,这类图案可追溯至贵霜时期犍陀罗出土的佛足迹实例。⑯而这一部分早期在印度有被描绘成小叶子、有被描绘成双鱼。中古时期,东亚三宝标两侧突起图案被描绘成海螺,例如玉华宫、日本药师寺佛足迹石等中古时期东亚佛足迹中三宝标两侧都是海螺形状的,这反映出了接近唐代佛足迹图案的类型。
这种三宝标图像稳定地在日本发展到当今。京畿地区的诸多佛足迹都流行着这类三宝标。
(2)分类模式的扭转
唐至五代(664~954)这一时期,中国、日本两地的复杂图案佛足迹在图像上、风格上并无实质性区别。中古时期佛足迹图像流行的时间跨越诸多王朝,并非取决于王朝的更新换代。无论从图案还是轮廓风格,现存玉华宫佛足迹图案其实也属于药师寺型,也能说明与玄奘有关的佛足迹和与王玄策有关的佛足迹图像基本一致。
从长时段的视野来看,中古时期虽然有佛足迹石和石碑两种媒材,佛足迹绘制图像的风格依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中国玉华宫的石碑物质形态并非是最初的方形佛足迹石,而是上图下文的石碑形态,也有过一些中国化的改变,但图像、轮廓风格依然能反映出唐代风格。
复杂图案的佛足迹中有双鱼、宝瓶这两种图案。有关这两种图像的文字记载并非出现在初唐玄奘所著的《大唐西域记》中,而是出现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688)中。而且,目前的文献也没有直接描写详细的图案与过程。
因此存在一种可能,中古时期的佛足迹图像并非都是玄奘、王玄策所在的初唐时期传入中国的,而是有一个逐渐托名给王玄策和玄奘的图文发展过程。中古时期,东亚佛足迹碑文、题记中的玄奘或王玄策应当是作为与印度相关的历史人物,被分别写到中、日佛足迹对应的文本中,便于图像流传。二人是否亲自带回佛足迹也已不再重要,二人之盛名与佛足迹绑定在一起之后,意义重在传承佛足迹。而在中古时期的中国、日本、韩国传承图像的主体是供养佛足迹的信众,这是由于供养佛足迹与灭罪功能有关。
2、第二种风格与玄奘的关系
第二种风格,稳定地流传于南宋至清(11~19世纪)的中国和韩国。
明清时期,版画上的佛足迹图像在中国本土又形成了佛足灵相之碑,以呼应中国传统的山志、谶纬祥瑞之说,使图像、石碑、寺院土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目前韩国发现了多例19世纪的佛足迹雕版与拓片。其中多例佛足迹图像的祖本可追溯到南宋时期的宁波延庆寺。南宋以来流行以雕版印刷佛经,佛足迹图像也在这种浪潮中因而被延续下来。画面采取上图下文,文本题刻与玄奘有关,与王玄策无关。
(1)风格分析
南宋使用雕版重绘佛足迹,使中国佛足迹的轮廓、脚掌四图案、足跟海螺型三宝标等方面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南宋之前,中国佛足迹内侧轮廓边缘均较为竖直,接近印度佛足迹的最初形态。南宋之后,中国、韩国的佛足迹版画经过重绘,双足内侧轮廓分别凸起,这正是大拇脚趾的第一跖骨的位置,更接近真实人足的形态。脚趾四图案的排布由平行改为斜向排列,这是由于翻刻后佛足迹雕版的尺寸也比佛足迹石明显增大,所以空间排布上也出现了偏差。例如,中国宜君玉华宫、日本奈良药师寺佛足迹石、日本京都东寺观智院佛足迹纸本的脚掌四图案,均为并排排列;以南宋延庆寺为祖本的韩国诸多佛足迹版刻、拓片,以及中国明清佛足迹石碑中的脚掌四图案的排列呈斜方向,例如韩国安国寺拓印的佛足迹版画(图8)。

图8:韩国安国寺拓印的佛足迹版画,现藏于华藏寺
南宋以来足跟三宝标被描绘成上有三座山下有法轮的须弥山型,足跟三宝标都具有多个小三角形堆积成小山形。这种风格一直持续地从宋代影响到清代,遍及中国和韩国。
(2)三宝标与重塑玄奘求法僧形象
表1唐宋时期东亚佛足迹图像类型简表中,举出了四例有代表性的佛足迹足跟三宝标与对应人名的信息,能够说明图像风格的变化也不取决于玄奘,而取决于南宋时期以雕版传播佛足迹的背景。
表1中体现出两种风格,第一种风格的时代在前,第二种风格的时代在后。例1、2为第一种风格:三宝标为海螺型,三宝标中的法轮下方的连续弧线是单线,W形的两端弧线中央只有一条曲线。表1例3、4为第二种风格:法轮下方的连续弧线是双线,W形的两端弧线中央有多条曲线,可以明确地看出后者的线条被重新绘制过。⑰
从表1中,佛足迹的形态以及载体形式来看,产生了对应人物的序列关系。历史中的玄奘早于王玄策,例1通过实物能够说明752年王玄策与日本药师寺建立了联系;例2中,945年义楚在《释氏六帖》中又再次强化了“玄奘”与玉华寺佛足迹石碑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例2玉华宫、例3韩国佛足迹、例4中国明清佛足迹中,铭文或题记都是玄奘。他应是五代以后被重新塑造出来,传承佛足迹图像的文本人物,与历史中的玄奘不同。

表1:东亚佛足迹图像类型简表
在中国,佛足迹图像在唐代灭法、战乱等背景下,应当是失传了一段时间。由于晚唐至五代时期一度掀起了神话玄奘西行求法僧形象的热潮,使得南宋时期佛足迹图像及文本通过雕版拓印的方式广布流传。虽然中国没有现存宋代延庆寺版刻的实例,但韩国保留下来的诸多佛足迹刻版、拓片也能反映出中国南宋时期稳定的图像与文本结构。而且这种复兴佛足迹传统的行为,可以上溯至从五代时期义楚所感怀的佛足迹石碑那一时刻。
之后,在明代佛足灵相之碑的形式,承袭了雕版拓印佛足迹的传统。影响波及中国现当代寺院中的佛足迹石碑,例如河南大相国寺和西安大慈恩寺。⑱
3、第三种风格与王玄策的关系
第三种风格,17~19世纪日本佛足迹再度兴起,在奈良药师寺类型的基础上,后续形成了三种次生风格类型。中国南宋—明清版本的第二种风格的佛足迹,于20世纪也传播到日本东京周边的寺院。
有些材质经历过一次重绘之后,变得更容易维持图像,譬如版刻、石碑;有些在传摹过程中,更容易随着地域的流转而变形,譬如日本17~19世纪的佛足迹石。由于图案较为多样,准确地说并不能统称为一种时代风格或地域风格。但日本不同佛足迹图像的变动与区域分布联系紧密。可以从这些图案的变动中看出区域风格在百年间的小范围演变。
(1)与王玄策相关的日本佛足迹
东亚佛足迹脚掌的四种副图案是:旗子(在中国为绕帛的宝剑、日本为叉子、金刚杵)、双鱼、水瓶、海螺。这部分图像原本在斯里兰卡、印度是旗帜的图形,在中国、韩国由于版刻和石碑的形式而发展得较为稳定,只有旗子发展为绕帛的宝剑。
日本的佛足迹图像延续着印度礼拜佛足迹石的方位,大多以平放在地面上人们对佛足迹石顶礼膜拜,这些传统都应当是从唐朝传入的。日本佛足迹石不论哪种形态、有无铭文、什么时期,都和王玄策有关,基本与玄奘无关。
日本中古时期复杂图案的佛足迹图像也被称为药师寺型,其中以奈良药师寺佛足迹石、东寺观智院纸本、药师寺金堂佛像足底为代表。另外在《大正藏》图像部中,还有一版年代不确定的佛足迹图像,基本符合中古时期图案布局,但绘制笔法草率,也无法确定其年代,基本属于药师寺型。
(2)复兴的佛足迹衍生风格与分布关系
17~19世纪佛足迹在日本一度复兴。在江户时期也由于传摹产生了多种变化,变化尤其表现在脚掌四图案与足跟图案。
除了药师寺的类型还在京畿地区延续发展,据丹羽基二的调查,还出现了酉阿型、贞极型、良定型等次生类型。⑲它们分布的区域从奈良周围逐渐东移,后来广布日本沿海地区。到了20世纪,中国第二类与玄奘有关的佛足迹图像也传入日本,零星围绕在大城市附近的内陆地区。
①酉阿型集中在毗邻奈良的贺滋县、三重县,双鱼被重绘得异常大,足跟三宝标变为金刚杵;
②贞极型集中在名古屋县周边,脚掌双鱼变为单鱼,足跟三宝标变为金刚杵;
③良定型集中在沿海各县,大脚趾下为绕帛的金刚杵,足跟三宝标车轮明显变小,海螺变为双叶、足跟最下方还增加了富士山;
④20世纪,又传入印度、东南亚的佛足迹类型以及中国的玄奘型佛足迹石碑。它们的分布更为广泛,主要集中于规模较大的城市圈。可以看出日本的佛足迹石17世纪之后逐渐从京畿地区拓展到整个本州岛。参考药师寺的碑文,这些没有碑文的佛足迹石有可能依然延续着灭罪功能。
四、结论
中古时期复杂图案的佛足迹图像的判定依据,与玄奘还是王玄策无关,与通身纹无关,与放射性光线无关,而与时代风格、地域风格有关。佛足迹自身的演变可具体分为三类风格:
第一类风格流行于中古时期,图像轮廓接近矩形,足跟三宝标两侧有海螺形图案。媒材有佛足迹石、佛足迹石碑、佛足迹纸本绘画等。目前被认为是玄奘或王玄策传入中国的佛足迹图像皆属于同一种风格。
南宋时期改用雕版重绘佛足迹,产生了新的第二类风格,流行于中国、韩国。复杂型佛足迹图像流行于中国(明清时期)、韩国(相当于从南宋到明清)的寺院中。在图像上,佛足迹具有双轮廓线,内轮廓跖骨突出,足跟三宝标被绘制成复杂的须弥山。在文本上,记载佛足迹是由玄奘带回中国的。这一文本与图像的关联应始于五代时期义楚参访玉华宫,五代至南宋时期在神化玄奘的背景下,僧人把 “玄奘”作为传播佛足迹的传播者记录在碑文中。玄奘本人与东亚佛足迹图像之间的关系是后人逐渐构建起来的,而非玉华宫石碑所述,摩揭陀国、玄奘、佛足迹间的关系是相对松散的历史信息碎片,不应当直接理解为是玄奘本人带回的佛足迹图像。
中古时期以来日本的佛足迹图案与文本相对分离发展。17~19世纪复兴佛足迹石高潮形成了第三类风格,无论有无铭文,都被认为是王玄策从印度带回的粉本,继而传到了日本。佛足迹轮廓与足跟三宝标都保存有中古时期的特征,轮廓接近矩形,内轮廓跖骨不突出。在药师寺的基础上产生了三个次生类型,流行于中、韩的第二种类型也传播到了日本大城市周围。
由此可见,玄奘和王玄策与佛足迹图像之间的关系是后人逐步构建出来的、易于流传的图文组合,佛足迹图像有其自身的变化规律和传承方式。
注释:
① (日)宫治昭著,王云译:《印度佛教美术系列讲座—第一讲印度早期佛教美术》,《艺术设计研究》,2011年第4期,第85-97页。
② 奈良六大寺大观刊行会:《奈良六大寺大观药师寺》,岩波书店,1970年,图版103。
③ 1968年,以日本《古美术》第24号为平台,形成第一次集中讨论药师寺佛足迹石的高潮,讨论的议题主要是奈良药师寺佛足迹石本身的铭文。著名的学者有松久保秀胤、龟田孜然、三宅米吉、福山敏男、保坂三郎、桔健二、浅田芳朗、加藤谆、足立康、田中重久、吉村怜等人。
④ 孙修身:《王玄策事迹钩沉》,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5页。
⑤ 霍巍:《王玄策与唐代佛教美术中的“佛足迹图”》,《世界宗教研究》,2020年第2期,第9-17页。
⑥ 韩伟:《陕西的佛足造像》,《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第70-80页。
⑦ 李静杰:《佛足迹图像的传播与信仰(下):以印度和中国为中心》,《故宫博物院院刊》,2011年第5期,第58-80页。
⑧ (日)斋藤理惠子:《佛足石》,(日)大桥一章、松原智美编著:《藥師寺千三百年的精華—美術史研究のあゆみ》,裏文出版社,2000年,第270-271页。
⑨ 霍巍:《王玄策与唐代佛教美术中的“佛足迹图”》,《世界宗教研究》,2020年第2期,第9-17、193页。
⑩ 由于东亚佛足迹石块、石碑都属于地面遗迹,传世文物,其碑文与考古出土物的性质不同。佛足迹的碑文以《大唐西域记》中的圣迹故事为核心,其中涉及到多重引用、混合了与玄奘和王玄策相关的两种文献。玄奘、王玄策两人与图像演化的体系并无直接关系;与中国化佛足迹文本、日本化佛足迹文本关系更大。而本文针对图像问题的研究方法展开讨论,另外有关王玄策与佛足迹图像间的关系的论证参见本人其他近期待刊论文《移地造迹:奈良药师寺佛足迹石新解》。
⑪ [五代]释义楚:《释氏六帖》卷一中《法王利见部》,第一“像化灵异”,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6-17页。据义楚《进释氏六帖表》,《义楚六帖》编纂起自后晋开运二年(945),终于后周显得元年(954)。
⑫ 韩伟:《陕西的佛足造像》,《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第70-80页。
⑬ 玉华宫佛足迹石则最初发现于 1960 年,出土于玉华宫肃诚院石窟内。在此刻石的左下方原刻有发愿文,但仅保存有“近(匠)李天诏”四字,发愿文仅见“供”字,余皆残损,图文漫漶不清。1999年,在玉华宫肃诚院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又出土了刻有文字的残石数块,经拼合粘接,发现石块上方刻有带有纹饰的足印残部,下方刻有楷书铭文,内容为:“佛迹记/摩揭陀/国波吒/离城释/迦如来/蹈石留/迹奘亲/观礼图……”考古报考告参见卢建国:《陕西铜川唐玉华宫遗址调查》,《考古》,1978 年第 6期,第 380-387、435-436页。拓片参见:仵禄林、王民:《玉华宫遗址的发现与研究》,《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5期,第99-101、105页。
⑭ 西北印度佛足迹石图像的分期,参见李静杰:《佛足迹图像的传播与信仰(上):以印度和中国为中心》,《故宫博物院院刊》,2011年第4期,第6-35页。西北印度佛足迹中的三宝标对东南印度佛足迹石的影响,参见拙文《礼拜看不见的佛陀—2至4世纪东南印度佛足迹石的朝向问题分析》,《创意设计源》,2021年第2期,第25-31页。
⑮ 日本奈良药师寺型与中古时期中国佛足迹较为一致,17~19世纪日本国内不同地区新出现三种次生的佛足迹图像,足内图案略有不同,足迹轮廓还保存着中古时期的矩形宽脚掌形态。
⑯ 佛足迹图案中的三宝标在东亚主要有三种形态:钩状三宝标、海螺型三宝标、须弥山型三宝标。钩状三宝标,来源于犍陀罗三图案的佛足迹图案,例如龙门擂鼓台佛足迹石;“万字纹、车轮、三宝标”三图案作为佛足迹主图案,从2世纪在西北印度产生以来,就一直较为稳定,不论在3~4世纪东南印度还是斯里兰卡的佛足迹石、东亚佛足迹石中,极少改变位置和形态。
⑰ 表1唐宋时期东亚佛足迹图像类型简表中,图片或线图从上至下依次来自四川眉山法宝寺佛足局部、日本京都东寺智院纸本佛足迹局部、陕西宜君玉华宫佛足迹石碑拓片、山西五台山塔院寺佛足灵相之碑局部。
⑱ 长安卧龙寺、山东兖州兴隆塔地宫、河南登封少林寺、巩义慈云寺、北京华藏弥陀寺、石景山区八大处灵光寺、山西五台山塔院寺、宁波阿育王寺等。
⑲(日)丹羽基二:《图说世界的佛足迹石—从佛足迹石看佛教》,名著出版社,1992年,第179-2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