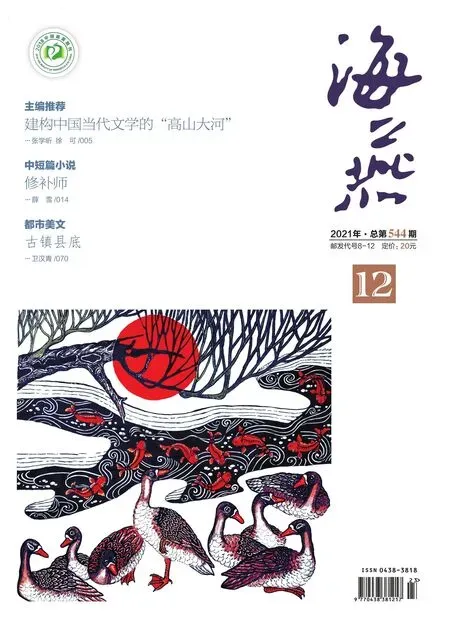稻子熟了
周玉潭
十月,家乡的稻子熟了。
国庆放假,我回老家小住几天,陪陪父母,也让自己呼吸几天清甜的空气。
走进老屋庭院时,已是傍晚,夕阳在长满梨树的小院里洒下斑驳的疏影。父亲站在院子的中心,清瘦,头发花白,正拿着一条抹布使劲地拍打打稻机的灰尘。看见我,笑了,说你回来正好,明天一起去割稻。我问不雇人帮忙吗?父亲说不雇人了,自己慢慢割吧,总共也就一担秧,年轻时我几筒烟的工夫就割完了。我心中就涌上一丝感慨,我的老爸哟,那是“年轻时”呀,现在不仅你老了,连儿子我也快要退休了。但我不想反驳父亲,嘴里说,好。
稻子是父亲种的,父亲今年84岁。
父亲一辈子都在地里忙活,7岁开始放牛,10岁开始跟爷爷下田干农活,一直到80岁还在田里种作。这几年,村里种作的人越来越少了,青年大多外出务工,老年体弱多病的也不再上山,田地大片大片的荒芜,父亲却没有停歇的意思,播种、除草、打虫、收成,一年一年乐此不疲。远离村庄的田地不能种了,山上到处是野兽,野猪、山兔、豪猪,成群结对,个个是糟蹋农作物的能手,因而村人种作的范围就收缩到村庄的周围。父亲靠近村庄的田地不多,就去种别人空置的土地。我劝父亲不要种了,父亲总是说,再种一年,现在还有力气,过两年想种也种不动了。
80岁那年,父亲挑着一担肥料去种稻,经过一条田埂,田埂窄,泥松软,脚一滑,身体失去平衡,人像木头一样硬梆梆地翻到田里,幸好肥料已甩出去了,没压着人,老半天才从田里爬出来,从头到脚粘满烂泥,人没什么大碍,却把母亲吓得不轻。我接到母亲电话赶回家时,父亲正坐在走廊的竹椅上,悠悠地吸着烟。我说,怎么了?这次怎么就摔倒了呢?父亲感慨起来,说老了,腿脚不便了,过去担这么几斤东西,就像吃大蒜放个屁一样。现在真的不中用了。我说老了就不要种了吧。父亲看看我,叹了一口气。
之后父亲就将水田送给远房的侄子,真的不再下田种作了。但空闲下来的父亲显然有点无所适从,东转转,西摸摸,不知道自已干什么好,有时莫名其妙扛着锄头到山上转悠一圈,谁也不知他去干什么。话语也少了,有时大半天不说话,坐在走廊慢慢地抽烟。
今年春节刚过,父亲对我说,今年还是种点水稻吧,要不家里的鸡都没东西吃了。我知道鸡没东西吃是假,真的是父亲种田瘾又上来了,再劝也没用,就说好,少种点。父亲笑了,说当然,就种一丘秧地,多了我也种不动了。
清明节前几天我回老家,父亲上山了。我问母亲,父亲干什么去了?母亲说,这两天你父亲都在山上翻地呢。我赶到山上,父亲正在翻一块旱地。这块地不大,本来是水田,三年前父亲排干水用来种菜。现在父亲又引进水,改作水田重新种稻。我到田边时,父亲已筑好田埂,开始平整田里的泥土,他高高卷着裤脚,挥动钉耙将高处的泥土耙到低处,再用双脚踩平。身上脸上都溅满泥巴,背部的衣服早已湿透。见我去了,放下钉耙,冲着我笑,说你怎么来了,路不好走呢。我说,不是说就种一丘田的吗?父亲说,反正是种,这丘田也近,就附带把它种上好了。我说80多岁的人了,这样翻地太吃力了。父亲说还行,马上就好了。我望着父亲,也只好摇摇头。
以后的日子里,我们父子电话就多起来,内容大都与稻谷有关。什么时候雇人犁好田了,什么时候插秧了,什么时候耕田了,什么时候除虫了,我劝父亲多雇人,但父亲总是说不用,这么一块地,除了家里没牛不能犁田外,其余的自己都能做。我也只好听之任之。现在农村种田也越来越图方便了,田不犁了,秧就插在老稻头的中间,田草也不拨了,就用田圈推几下。我也劝父亲简便点,父亲却不同意,说那是种什么田呢?那是糟弄土地啊!前几天父亲打电话来很兴奋,说今年年时好,稻谷出奇得好,过几天就可收割了。
第二天,阳光很好,天高气爽。父亲又叫来姐夫帮忙,但三个人也顶不了一个正经劳力了。父亲老了,姐夫也是60多岁的老人,我还算壮年,但长期没劳作,半个劳力也算不上。站在田埂上,我发现自己处在美景的中心了,整个山弯满是黄灿灿的稻谷,高低起伏,一直延伸到目光的尽头,天地间一片静谧,远处几个人正在一起一伏地收割,一群小鸟在田园中飞过,它们也在分享着丰收的喜悦。
父亲催我下田了。姐夫在那边田头,我与父亲在这边田头。我干过的农活不多,但稻却割过很多次,因而一下田就嗖嗖嗖割起来。不想刚开个头就被父亲嫌弃了。农家自有农家的美学,插田讲究又快又直,秧行竖看横看都要成一条线;种番薯,窟要打得整齐均匀,时大时小也就被人笑话。割稻呢?也有很多讲究,稻茬要割得平整,割把要用稻叶绕得结实,四个稻把放在一起,要放得整齐有序。父亲是农家美学的忠实守护者,我在他眼里满是缺点,镰刀握得不对,稻茬时长时短,稻把松散不齐。面对固执的父亲,我只好一一改正。
父亲动作虽然规范,但速度却明显慢了一拍。在水田割稻,要将稻把放在田埂上,里面人离田埂远,送来送去耗费时间,就需要两人配合。两人并排,里面的将稻把递给外面的人,外面人两把合成一把放在田埂上,这样就要求外面的人割稻比里面的快,这样才不会浪费时间。小时候,我站在里面割,父亲站在外面接把,常常催我,快点,快点。现在我站在外面,等我割好一把站起身时,父亲还弯着腰在割后半把。父亲头埋得低,一手拿镰刀,一手握住稻杆,“嗖”得割一棵,再“嗖”得割一棵,再没有年轻时行云流水的感觉了。割好一把,用稻叶紧紧绕实,慢慢伸起腰,长吁一口气,才将稻把递给我。我说爸你先休息,让我姐夫两人割吧。父亲却说,不要紧,慢慢来,总共才这么一个田。说着又弯下腰割起来。
花了大半天,我与姐夫终于胜利会合,望着田埂上一溜儿的稻子,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心想一项重大工程已基本完成了,接下来三人打完稻就大功告成。
想不到打稻才是艰难开始。父亲在田头的上面找到一块平地,三个人铺开油布,摆好打稻机。姐夫负责打稻,我与父亲背稻。父亲显然还没缓过气来,背了两趟,就差一点坐到田埂上。我说,你去帮姐夫打稻,余下的我来背。这一次,父亲同意了,站着给姐夫打下手,我明白,这次父亲轻易同意我的建议,一是体力实在吃不消了,二是对姐夫有点不放心,姐夫做事大大咧咧,谷粒没打干净就将稻把丢了,因而父亲说是帮忙,其实还有点监督的意味。
背了几趟,我才发现,背稻并不轻松。稻绳放在地上,将稻把搬到绳子上,然后弯下腰将肩膀抵在稻杆上,双手抓住稻绳,用力往上提,嘿地一下,将稻子翻到背上,这真是一项花力气又讲技巧的活儿。稻子在背上,稻叶割得头颈横一条竖一条的,又痒又痛。田埂滑,我只好从田里走,深一脚浅一脚,踏得泥浆四溅,背得眼冒金星。幸好稻把越背越少,我咬咬牙,终于背完最后一堆稻把。
最后一个任务就是担谷了。一堆谷,500
多斤的样子,分成四担,姐夫腰部有伤,不能担重担,担一担轻的,父亲挑了一担重的,剩下两担由我来挑。我送回一担回来,父亲与姐夫已打完稻谷收拾完毕,父亲挑起稻谷,我说,能行吗?父亲说,行,我年轻时都能挑300多斤呢,百来斤东西,没问题。但说归说,住下走时,脚下已飘浮不定,我说,不行,田埂你肯定过不去,还是我来吧。父亲也意识到自已不再年轻了,只好将担传到我的肩上,这一担比前一担重多了,压得肩膀生疼,我咬紧牙,拼命往前,晃晃悠悠地迈过田埂。脚刚踏到路上,就一屁股坐到地上。幸好朋友听说我在山上割稻,跑来帮忙,要不真说不好,那一天我是否能将几担稻谷搬回家。
第二天,我全身酸痛,起床时,父亲已将稻谷晒在阳台上,黄灿灿的稻谷在阳光下散发着光彩。父亲拿着谷耙来回翻弄着稻谷,脸上写满得意与满足,再也没有半点劳累的影子。我望着父亲,心想,种作虽然辛苦,但丰收的确是一件幸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