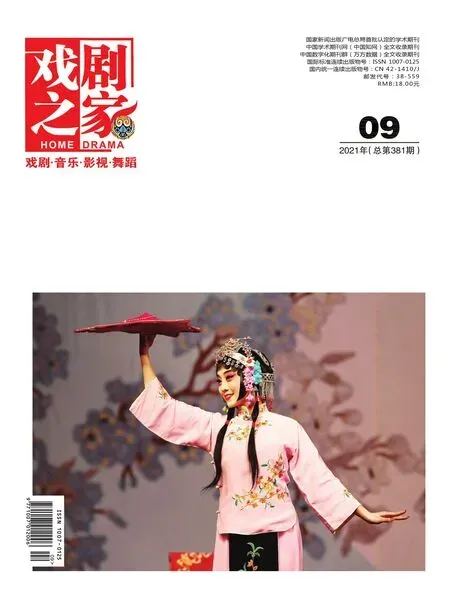从“标出性”浅谈话剧《北京法源寺》的人物形象塑造
(重庆大学 美视电影学院,重庆 400000)
2015 年12 月5 日,话剧《北京法源寺》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首演。该剧讲述的是戊戌变法的最后十天里,表面上平静的北京城实则暗流涌动。慈禧太后干涉变法,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袁世凯却出卖了光绪皇帝以及戊戌六君子,导致变法失败。然而与我们以往所认知的史实不同,《北京法源寺》对于这些人物提出了另一个角度的解读:深爱大清,却又不得不推翻它的袁世凯;有着母子柔情,却又不得不杀伐果断的慈禧。每个人身上都贴着一个一直以来固有的标签,整部戏则可以看作是撕掉这个标签的过程。
历史人物的功与过并不在艺术学的研究范畴之内,从艺术的角度出发分析历史,得出的观点投射在历史学的专业领域终究显得太过于浅显。但我们可以试着从符号学的角度重新解读《北京法源寺》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并且找到其背后的理论依据。
一、“标出性”的历史翻转
(一)慈禧:从一个被妖魔化的掌权者到一个伤心欲绝的“母亲”
在男权统治的封建社会里,慈禧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存在。在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中,权力本就应该是由男性掌握的,权力的顶峰——皇权,更是不可能被女性染指的。在封建社会中,掌权的女性是社会中的异项——即“标出项”。男权社会中,为了维护男性的统治地位,男性往往动用“男性社会权力,使男性为占据中项的‘正常’性别”,于是“牝鸡司晨”这样的词语应运而生。“牝鸡司晨”最早出现于《尚书·牧誓》。毫无疑问,《尚书》的编纂修订者是男性,因此在创造词汇时,便将女性掌权这一事件作为了标出项,将其强调为与社会道德伦理所不相符的存在。而男性掌权则作为非标出项,被我们的传统文化视为一种“正常”,获得了为大多数中项代言的资格。
所以,在《北京法源寺》中,慈禧作为这个帝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甫一出场,在场的所有人便对她都不友善。在过去的影视作品中,慈禧往往作为一个十恶不赦的民族罪人的形象出现,这种看法已经成为了文化中的非标出项。而随着近代女性的觉醒,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女性也可以掌控权力,于是《北京法源寺》在塑造人物形象时,选择了这种想法,成为了文化中的标出项。
回归到剧中的慈禧的形象,我们也会发现这个人物的两面性:一方面,她是这个文明中的标出项,而另一方面她自己也要求将女性标出。慈禧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昏庸无能的统治者,她认为自己可以驾驭,“统治大清朝47 年”、“两度垂帘听政”必然有其自身能力作为依托。而另一方面,她的内心深处也并不认为皇权应该由女人来控制。正如慈禧所说,作为大清朝的媳妇,我深知我不能称帝。当面对执意变法的光绪帝时,她摘下了大清朝“皇太后”的光环,认为自己只是一个伤心欲绝的“母亲”,在这一刻,她还是回归了传统礼教赋予的女人本应该成为的角色。
(二)袁世凯:功臣与罪人的争辩
作为一个颠覆性的人物角色,戏中的袁世凯有着多段内心独白,每一段内心独白都起着揭示人物内心、展现人物动机的重要作用。透过这些独白,“人物潜在的思想斗争过程鲜明地展示出来,使观众听其声而知其心”。
袁世凯最令人难忘的一句台词是:我像个女人一样深深地爱着大清。这个在某种意义上毁灭了大清朝的罪人,对着观众大声疾呼着他对于这个国家深深的爱意,使得观众不禁思考:袁世凯真的是个恶人吗?
判断袁世凯的善恶,取决于我们对于善与恶的定义。赵毅衡先生曾经提到过:善与恶的定义变动不居。在那个时代里,袁世凯是个恶人无疑。在传统观念中,卖主求荣、不忠皇权的大臣令人不齿。正项必须想尽办法让中项认同善,并且以恶为耻,只有这样,才能够保持一个国家的道德水准不会出现滑坡。对于袁世凯的批判和谩骂,有利于维护统治。维护君主统治,保持国家长盛不衰这一思想一直作为非标出项而存在,这是几千年来中国士大夫默认的道德准则。但剧中的袁世凯打破了这种准则,谭嗣同要救大清,袁世凯则选择了更为简单利落的办法:灭亡大清。这与瑞士剧作家迪伦马特笔下的《罗慕路斯大帝》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罗慕路斯大帝通过自己的毫不作为使得罗马灭亡,但其实他是一位洞悉历史的智者,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的:“如果历史无意于罗马,励精图治反而是一种反动。”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袁世凯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但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袁世凯依然不被今天的观众所喜呢?原因依然在于标出项与非标出项。当我们脱离传统的忠君爱国的思想去看待袁世凯时,我们会认为他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是,“信义”也是我们的文化中非常重要的非标出项,是每一个人默认的道德准则,如果你违反了这样的准则,就将被划为“恶”,受到批判。在观众看来,你对世界作出的贡献应该以一种善的、正确的方式达成,袁世凯的行动显然并不符合这一要求。
因此,从“标出性”的历史翻转这一角度来看,袁世凯能够以这样的形象站在舞台上,本身就说明“标出性”会随着文化发展的变化而变化。但袁世凯依然很难获得观众的认同,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部分非标出项古往今来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比如人们对于道义的追求。
二、谭嗣同:从正项走向异项的英雄
随着文明的发展,许多历史人物都从昔日的异项变成了正项。但那与他们本人关系并不大,更多的是因为文明的演变使得文化的“标出性”发生了变动。而谭嗣同不同,他是那个时代里主动从正项走向异项的英雄。谭嗣同第一次登场时便说,保全自己是大多数人的选择,而我却选择一条极少有人走的道路——殉。这是一条他主动选择的路,其他人或多或少都是被命运推上了这样的轨迹,而谭嗣同却在明知道结局的情况下,选择了成为社会中的那少部分人。
符号学理论中强调:“标出性会导致很强烈的自我感觉。”谭嗣同内心深处很清楚自己与这个社会上大多数人是不同的,世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同时谭嗣同也很清楚这种清醒的后果是什么。谭嗣同之悲,不在于悲惨,而在于悲壮,在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在于他主动选择了这样的道路,而不是按照命运铺设的轨迹,被命运裹挟着前行。在任何一个文明中,从正项走向异项,成为社会中被标出的部分,都需要莫大的勇气,谭嗣同做到了,当我们透过他的行动,分析背后的人物动机时,便会明白他所有的行动都指向了一件事——他像个女人一样深深地爱着大清。
这句台词,袁世凯也曾说过。当我们细究这句台词时,其实就会发现这句台词本身就可以说明一些问题。“我像个女人一样深深地爱着大清”,谭嗣同将对于国家的爱,比成了夫妻之爱。这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并不少见,就像《北京法源寺》中多次出现的配乐《清平调》,《清平调》是唐代诗人李白所作,“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表面上写的是男欢女爱,实则比喻的是君臣之情,李白借赵飞燕抒发自己希望得到明君赏识的期盼之情。后世也有许多诗作以夫妻喻君臣。但为什么是像一个女人一样?联系符号学理论,我们便不难理解。在过去的文化中,女人是标出项,情爱更容易与女人挂钩。“三纲五常”讲究君为臣纲,夫为妻纲。如果将君臣比作夫妻,那么臣子一定是妻子的位置,因为她在社会中并没有自己独立的地位,而是要依附于丈夫。而男性作为非标出项,则可以拥有更高的权力与地位,被他人依附、爱戴。
回到谭嗣同角色本身。谭嗣同本可以不必过这样的人生。在那样一个沉疴百年的大清帝国里,他可以选择和当时大多数的人一样麻木地活着。但谭嗣同选择了从正项走向异项,用自己的生命做一个石子,投向已经沉睡了百年的中国,投向腐朽不堪的大清。
三、中项问题:那些叫好声重现着三百年前的人间
《北京法源寺》这部戏中,并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围观群众。原书中众人围观谭嗣同被砍头的画面,在改编为舞台剧的过程之中被隐去,仅仅只是通过谭嗣同的一句台词“我隐隐约约听见人群之中有几声叫好声”来体现。但这些围观群众却是体现这部剧的主题的重要媒介。
《北京法源寺》舞台剧对原书做了颠覆性的改编,但二者都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人——袁崇焕。当年皇太极使用反间计,让崇祯皇帝误以为袁崇焕通敌叛国,将袁崇焕凌迟处死。史书记载,袁崇焕被杀之日,京城百姓无不拍手叫好,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谭嗣同和袁崇焕有着相同的命运: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他们身后的百姓和国家是他们抛却性命想要维护的,但他们却被百姓和国家所抛弃。在那样的文化时代里,袁崇焕与谭嗣同无疑是社会的异项,而那些在阴谋家的世界中涉血前行的人则是社会的正项。然而无论是正项还是异项,都只是一小部分群体,构成文化的主要部分还是中项,符号学理论认为所有文化中可见的二元对立格局都是三元,中间都有一个非此非彼的中项,投射在那样一个风云诡谲的时代里,则体现为无知麻木的普通百姓。“中项无法自我表达,它只能够被这两种对立的思想裹挟携带,只有当它倾向于正项时,它才能够获得它的文化意义。而文化的非标出性本质上很不稳定,因为其意义不能自我维持,需要依靠中项的支持”。也就是说,统治者努力地让这些普通百姓提高对于自己的认同感,拉拢中项,而那些破坏他们稳固统治的人,都会被中项看作是异项,继而加以消灭。因此,约三百年前围观袁崇焕凌迟的那群人,和三百年后为戊戌六君子殉难而拍手叫好的人群,本质上并无任何区别,都只是社会文化中的中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