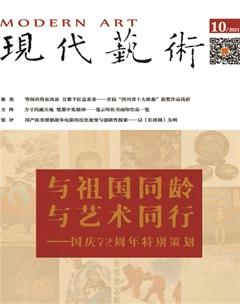包德宾:从石匠到编剧的逐“梦”之路
荀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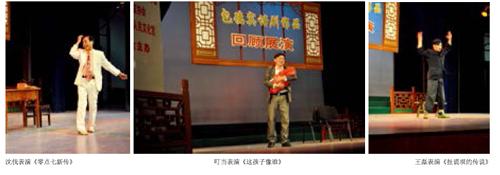
四川省曲艺研究院一级编剧,四川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
其谐剧作品《这孩子像誰》曾获文化部“全国曲艺优秀节目观摩演出(南方片区)”创作一等奖;《王熙凤招商》获第四届中国曲艺牡丹奖(文学奖);《零点七》《兰贵龙接妻》分别参演1986、1988年央视春晚。扬琴作品《亲家》、清音作品《成都的传说》分别获1981年“四川省巴蜀文艺评选”创作一等奖、1995年“四川省第二届巴蜀文艺大赛”创作一等奖。199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创作有曲艺作品一百余篇,获省级以上创作奖三十余个,著有作品集《包德宾作品精选》。
四川南溪,有位大书法家叫包弼臣(1831-1917),晚清三大碑派书家(张裕钊、赵之谦、包弼臣)之一。他自创了一种将北碑与南帖熔为一炉独树一帜的“包体字”,自成一格,被称“字妖”。至今,“包体”书法仍是人们寻求、收藏、研究、借鉴的对象。包弼臣曾任盐源训导、邛州学政、资州学政长达20多年,培养出大批人才,清代蜀中唯一的状元骆成骧即出其门下。
1949年,包弼臣逝世32年之后,他的曾孙包德宾出生。不同于曾祖包弼臣,包德宾见长于剧本创作,是国家一级编剧,享受国务院政府专家津贴。著有谐剧、清音、扬琴、相声、小品、唱词、戏曲等艺术形式作品200余篇(部),获各级创作奖30多次。
包德宾的父亲毕业于北京大学,母亲毕业于北师大,哥哥姐姐也都是高材生。但文化世家出生的包德宾,却只读到了初中二年级。“我父亲1961年去世,母亲虽然是教师,但因为身体不好,停薪留职几年,到了1965年完全没有生活来源了。”没有条件继续读书的包德宾,16岁就参加工作,当起了石匠,一干就是13年。生活虽然艰苦,但包德宾始终有个“作家梦”。
因为有梦想,少年包德宾一有时间就“拼命阅读”。但家境困难,买不起书,包德宾读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姐姐抄下来的笔记,如普希金的《青铜骑士》 《欧根·奥涅金》《波尔达瓦》等。除了这些,包德宾还接触了大量的古诗词。“我外公是晚清最后一批秀才,所以母亲从小就读私塾,四书五经张口就来。我哥哥记忆力特别好,《红楼梦》《三国演义》《警世通言》这些,过目成诵,甚至有段时间他想去说评书,因为他所有看过的书,几乎都可以背下来。”受家人影响,包德宾的古典文学量积累深厚。此外,包德宾还喜欢到图书馆读书,“我读小学时就喜欢读剧本,那时候能借出来的剧本,我几乎读完了。”包德宾阅读能力很强,小学三年级就读完了《水浒传》。喜欢阅读的他,还会从自己的生活费里省出一部分去看书,“4分钱去租书,可以读一天。”
1966年,17岁的包德宾进入业余文艺宣传队,成了一名业余文艺演员。“我利用休息时间上台说相声,还拜了一个相声老艺人。”说了几年传统相声、新编相声之后,包德宾便开始自编自演。1972年,23岁的包德宾创作出了自己人生第一部独幕话剧《前进路上》。
回忆起这部话剧的创作初衷,包德宾笑得有些无奈。“那时候我每天上工都要背个洋瓷碗,洋瓷碗很贵,买一个很不容易,还要凭票。那天我赶公交,碗被车门压扁了,非常气,就跟售票员吵起来了。下车以后,我就想,一定要写一个服务态度非常好,素质非常高的售票员。于是,就有了独幕话剧《前进路上》。”剧本完成之后,“自娱自乐”的包德宾把作品“丢”到一旁。直到1973年,包德宾的同学来家里玩。“他看到我的剧本,说他的姐夫在成都市文化馆工作,把剧本带给他看一下。”同学的这一举动,为包德宾打开了编剧创作的大门。
“写了这个剧本(《前进路上》)之后,我还写了一个相声。因为我们业余宣传队演话剧演不出来,但我们有一批痴迷曲艺的业余演员。所以我就自己学着写相声,写清音,写扬琴、荷叶、金钱板。写完之后,我就把作品拿给大家看,看要不要得。他们说‘可以,唱得走,我就写,边写边走。”
尽管是在业余文艺宣传队,但因为写“本子”比较有名气,包德宾成了当时“成都业余创作组”曲艺组和话剧组互相争抢的人才。“后来曲艺组争赢了。”从事石匠工作的包德宾,虽然已经搞起了创作,但面对生活,他不能放弃“石匠”这一维持生计的重要手段。所以,白天经过高强度的劳动之后,晚上还要坚持写作。“我当时写通夜,脚冻得冰凉,半天都暖不过来,但我就是有这个梦想。”
1977年之后,包德宾的剧本创作迎来“大爆发”,并在省文化局群众文化工作室写书、创作。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办不到调任手续,他仍是个石匠。好在,有不少人被包德宾的作品吸引,关注、关心着他的生活。“《四川日报》文艺部的老师对我特别关爱,接连发了我很多作品,给我的创作提一些很好的建议,还经常从《四川日报》图书馆借书给我看,我需要什么书,都帮我借来。那几年我看了很多国外的戏剧作品,包括莎士比亚、亨利克·易卜生的话剧。”
1978年8月,包德宾正式调到四川省曲艺团,从事专业曲艺创作。当年,成都市话剧团将包德宾创作的独幕话剧《前进路上》搬上舞台;他创作的四川扬琴《山村鸡叫》在《四川日报》发表,随后改编成独幕话剧被四川人民艺术剧院搬上舞台,并获得了1978年四川省文艺调演一等奖。
此后,领导又给了包德宾一个新任务——写谐剧。谐剧是四川独有的艺术曲种。1939年冬天,谐剧创始人王永梭先生在合江县庆祝新年的晚会上,自编自演了一段11分钟的小节目《卖膏药》,作品表现出的对小人物的深切同情和对当时社会的抨击,引发了观众强烈共鸣。之后,他将这“一人独演,独演一人”的新形式定名为“谐剧”。
上个世纪80年代初,王永梭先生应邀到中央戏剧学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北京人艺讲课和表演,引起文艺界对谐剧的极大关注,专家学者好评如潮。很快谐剧就成为四川曲艺“以说为主”的代表曲种,影响全国,波及海外。王永梭先生还在川、渝、黔、滇等地开门办学,培养弟子学生数百人,为谐剧打出了一片明朗的天空。包德宾是王永梭先生的学生,也就是这个时候,他开始了自己的谐剧创作。
1980年,因着儿子出生,包德宾带儿子回家,周围邻居纷纷上前,围着他讨论孩子像谁,这个场景让包德宾灵感迸发。一个月之后,他就写出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谐剧作品《这孩子像谁》。“当时全社会正在大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有的人说‘领导是标准,我就写了《这孩子像谁》,讽刺那些人云亦云没有主见的人。”
“这个节目一出来,得到的评价就比较高。”1981年元旦,著名谐剧表演艺术家沈伐,将《这孩子像谁》搬上了四川电视台的元旦晚会,“我在公交车上都能听到大家议论这个节目。”后来,包德宾又带着《这孩子像谁》赴京参加创作座谈会,引起极大的反响。“这个创作班12月结业,第二年2月《曲艺》杂志(1981年第2期)就发表了我的作品,还特别请重庆曲艺团的老作家写了篇评论文章。然后,上海广播说唱团还把这个节目改编成上海说唱,搬上舞台。”
1981年,文化部、中国曲协来四川选调演节目。“我这个节目在北京已经火起来了,看都不看就要调上去,参加全国优秀曲艺观摩演出。”这次全国优秀曲艺观摩演出可以说是1978年以来全国第一次大型演出,《这孩子像谁》一登台,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当时,还有调演组专家提出该剧是“新时期曲艺创作的里程碑式作品。”
因为《这孩子像谁》,包德宾彻底“火了”。“全国十几个省市来学习这个节目,加拿大、美国等国外曲艺爱好者、学者也来了,他们也感兴趣,想来学谐剧、演谐剧。电视台、广播台、报纸都来采访我,但我太年轻了,紧张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因为《这孩子像谁》,包德宾收到了很多赞誉,但也有人断言他再也写不出有这种影响力的作品了。为创作出超越《这孩子像谁》的谐剧作品,包德宾开始“踮起脚尖走路”。“我这一生的创作,总结起来,就是在不断挑战自己,不断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虽然我很累,很苦,但我的眼界开阔了,我人就显得更高大了。‘踮起脚尖走路成了我的座右铭,我的宿命,我创作的动力。”
1986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著名谐剧表演艺术家沈伐用四川话表演的《零点七》,引得现场观众捧腹大笑,台词“全心全意为人民币服务”等迅即成为流行语。《零点七》原名《演出之前》,包德宾创作于1983年。
《零点七》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一次全省艺术市场调研。包德宾感慨,“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关口,艺术家对艺术还是要真诚,不能一切向钱看,特别是艺术活动、艺术创造。艺术家的艺德、艺品、舞台演出,如果都向钱看就不好了。对艺术创造,还是要充满敬畏充满真诚。艺术是一种高级的审美活动,不能让铜臭玷污。”这也是《零点七》想要表达的观点。
1988年,包德宾创作的三个谐剧《梁山一百零九将》《公关小姐》《零点八》参加四川省曲艺创作比赛。一等奖作品五个,包德宾一个人就占了仨。“评委老师打分,《梁山一百零九将》居然是满分。”
因为表演包德宾的剧本,沈伐火了,其他演员也火了。“我的表演天赋不是第一流,沈伐才是。他演技好,而且非常聪明。我们俩很有默契。像《兰贵龙接妻》1981年就写出来了,跟沈伐讨论,他贡献了很多意见。”其他演出单位也请包德宾写过不少作品,但很多都没有搬上舞台,“我在省曲艺团,跟沈伐一‘咬耳朵,喝点茶就解决了。”
1988年,四川四家单位联合主办了“谐剧作家包德宾作品展览演出”,效果轰动。“最开始是在新声剧场演出两场,门口黄牛、串串儿很多。领导又临时加了两场。后来有一个会议包了两场,非常火爆。最终一共演了11场。”之后的包德宾谐剧作品研讨会,更是名家云集。
包德宾专注创作,哪怕是别人请吃饭,他都不去。“我为了让自己高大,已经是‘踮起脚尖走路了,就是一门心思搞谐剧。” 每年,包德宾会构思数百个作品,真正落笔的只有三四个,最终能够产生影响的,更是少之又少。“现在我的写作已经成熟了,写出来基本上没有废稿。”
包德宾的作品,总是与时代紧密结合。他将自己对时代的思考,通过《这孩子像谁》《兰贵龙接妻》《零点七》《梁山一百零九将》等作品展现出来。“除了当时的政策,也会将对人、对人性、人的品德、价值观,人的行为模式,都写进去。”除了理性的思考,包德宾创作还需要亲身接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他鼓励创作者应该去体验生活。“那个时候我到处跑,全省有名的乡镇都去过,集中精力观察生活、观察人。”
除了笔耕不辍,包德宾还经常受邀讲课,為四川曲艺创作培养新人。他自己也有两个弟子,徐崧和秦渊。包德宾对两位弟子喜爱有加,经常为他们的创作出谋划策,“徐崧曾获得第三届巴蜀笑星,秦渊创作的四川清音《莲花开》、四川扬琴《守望》分别斩获第九、十届中国曲艺牡丹奖文学奖和节目奖。”
相比过去曲艺的兴旺,现在从事曲艺表演、创作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已越来越少,观众也越来越少。包德宾也忧心曲艺未来,“曲艺主要是为大众服务的通俗化的艺术,如果观众少了,说明我们为大众服务的不好,特别是作者有责任。当今曲艺工作者创作的数量和质量,都满足不了演出的需求。量少了,质也少了。”他呼吁,要加强对青年创作者的扶持,扩大曲艺作者群体,动员各行业的青年知识分子都来参加曲艺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