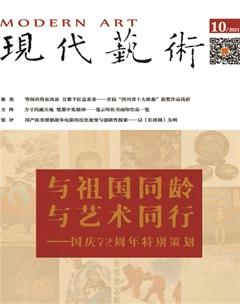故乡,流水的记忆切片
姜文彬
故乡,就像那一根被剪断又没有踪影的脐带,无时无刻不在汩汩流动的血脉,拉近了我们与母体的关系。
一
一个夏日的傍晚,夕阳从城市高楼的缝隙照临成荫的绿树。我刚下班跨入小区,手机上的来电便跳出奉来禹的名字,一阵寒暄之后,他告诉我,他的散文作品即将结集出版。在我对他的祝贺声中,他向我提出为该书作序的请求。我当时想,我一不是名家,二在散文创作方面涉猎较少,觉得写序不妥,但他从我们工作在一个系统,又是文学爱好者知音的角度循循以劝,让我不好再推辞。
写序使得我对奉来禹的作品先睹为快。“最忆苍溪县”,奉来禹告诉我这是陆游的诗句。“最忆”二字在我心中泛起阵阵涟漪,就像一池如绸的绿波,在大脑的皱褶中和大海的浪谷里闪出粼粼金光;犹如鲜活的鲤鱼跳出流水带起晶莹的水滴。我想起白居易的《忆江南》,其一“江南好,風景旧曾谙”;其二“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其三“江南忆,其次忆吴宫”。三首词,分别描绘江南的景色美,风物美和女性美。奉来禹,你的《最忆苍溪》,是描绘苍溪的什么美呢?
翻看着奉来禹的作品,全书分为六辑:乡土、老家、吃相、成长、大院、风物。在这个炎热的夏季,读着这些作品,犹如温润轻柔的微风,让躁动不安的心平静下来。
从在他老家那里名气颇大的《白鹤观》开始,读到最后一篇《姗姗来迟的文化惊艳》,他历经三十余年才一睹寻乐书岩的芳容。奉来禹出生在川北山区苍溪县一个远离县城的运山镇的小山村,长大后外出读书,再回到家乡苍溪县城,再到广元市。作者从农耕文明的乡村出发,进入到渐进繁荣的城市,又以对故土的留恋,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行走,在这个过程中,故土始终是他的根和魂,是他生命的血脉,是他心灵的皈依。作者于在场的记忆与不在场的审视中,描绘的是苍溪的山美、水美、人美、风物美,是作者饱含深情对家乡的赞美,也记录了其在家乡经历的苦难、悲痛、伤感、无奈、辛酸,是作者心灵创伤的凄美表达,还展示了家乡人的勤劳、智慧、果敢、纯朴、隐忍、善良、乐观、上进,是作者怀揣正能量的美学价值追求。
从奉来禹的作品中,我们能感受到作者强烈地亲近苍溪的地域本位意识,他的记人叙事写景状物体现了作者强烈的属地性抉择。作者以苍溪的时空场域为依托,随着自身经历的流转和审美经验的延展,以生命的体悟触及故乡的深层底蕴,从苍溪的地理家园到自己的心灵家园,对读者来说有一种不可抵抗的牵引,若你抵达作者描述的现实世界的场景,就能抵达作者精神世界的腹地,勾起读者对自己家乡绵绵不绝的思绪,升华起来自心底对家乡的热爱乃至热爱祖国的情结。
二
“乡下的秋夜是真正的秋夜。”
奉来禹坐在“乡下的秋夜”(《回乡杂记》)老家的院坝里,凝神远眺家乡镇上那一条灯火的带子,或是“院坝边梨树那儿,窸窸窣窣,传来稍大的声音,忙打开手电,原来是小青蛙在枯叶间跳动。”冬日回到乡下老家,叩问《月华星光何处》,“突见那窗却是一口浅亮。于是披衣起床去窗口探视,院坝及周边更亮呢,原来今夜有月亮。”“一口浅亮”用词精妙,与“院坝及周边更亮”对比起来,作者对月色的观察细致入微。读到这里,遂会想起苏东坡“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的句子。一个是解衣欲睡未睡,一个是狗吠惊醒无眠;一个是与怀民月下庭院散步,一个是独自在院坝静赏月华,都是因月而起,为月生情,不禁会让人发出古人、今人,寺庙、农舍、月色笼罩的美妙感叹。
不断地读着文中的句子。《那些年的柴火》中“我中午放学后的任务就是去菜园子各处拾柴棍,就像鸦鹊衔柴棍做窝那般,往灶屋里一小把接一小把给母亲送去。”就仿佛看到作者小时候抱着柴棍奔跑在田埂上的身影,或者可以想象母亲接过柴棍之后几句关切的话语。岁月流逝,人到中年在乡下为老母亲“储备烧柴”时,作者执拗地“搭梯上树,窜至树冠之中,从上至下,将柏树枝樵掉。”作者的孝心与母亲的担心流淌在字里行间,母子亲情不禁让人眼睛和心口发热。母子亲情,更多的读者或许有切肤之感,文学作品能够打动更多人的心灵,对于作者来说是欣慰的。这些看似日常生活的景物描写,作者用淘洗的功夫,接受时间流水的冲刷和空间幽光的穿越,那些感人的细节犹如粒粒的沙金沉淀下来,捧献在读者面前,光彩夺目。
“那山太高了……一拨人从山脚下几户人家的茅坑里将粪水挑到堰沟那里,另一拨人从堰沟处接着挑到山上地里。交替时,就需要换肩,下面人将满满当当的粪水挑子替给上面下来的人,并换下上面人替给的空挑子,交替换肩时,需背靠背,肩对肩进行,粪水挑子与空挑子直接相互替换,不得落地,更需要平衡稳当,利索灵巧。”(《肩挑那些事儿》)高山沟谷和沿途的场景,你追我赶的场面,人物的动作情态,就像摇摄的电影镜头,呈现在读者面前。而作者小时候与小朋友们结伴捡桐子的画面也相当诱人:“小朋友们便在手指粗细的木杆或斑竹竿端头钉上一颗铁钉这样的辅助工具去打捞,那些桐子在水里,外壳早就绵软,只要握紧细棍(竿),将钉有铁钉的棍(竿)头朝那桐果一啄,桐果就再也逃不掉了。”(《桐忆》)这些灵动的画面,传达着童年深切的喜悦,仿佛有碰触的波光,映衬在挥动的棍(竿)子上和同伴们的笑声里。镜头画面感如此强烈的类似描述在作品中还有很多,读者可以从中体悟。作者描绘的是身边熟悉的人和事,他一笔一画勾勒出饱含情感的画面,画面中的鲜活情节感染着读者,体现着作者驾驭语言文字的功力。文学就像一枚硬币,能够表达自我认知是一个方面,而能将这一成果体验传达分享给别人并能引起情感共鸣是绝佳的另一个方面,就看作者能否将这一枚硬币运用自如。
三
作者这把年纪(自语),或多或少有亲人老友离开人世。在这本集子中,有一些篇什涉及到死亡的主题。如《送姑父归山》《斯人已去》《老陶》,与世纪伟人邓小平同年生同年辞世、家族里常称她世纪老人的婆婆,还有爷爷、大爹、父亲。面对死亡,正视死亡,并把死亡之后祭奠亡灵在自己心灵的印记中呈现出来。“灵魂窥见了坟墓后面的光辉。”(波德莱尔)在这些文章中,奉来禹让我们看到了死亡的深刻。“如果我们只热爱生命而不热爱死亡,那是因为我们并不真正热爱生命。”(路易-樊尚·托马)作者的亲人,大都是高寿,面对死亡,在记叙这些亲人的英容笑貌和平静地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时,作者没有带给读者焦虑和恐惧、绝望和阴郁的文学感受,而是从容地直面死亡,把那些人间最美好的亲情,呈现在读者的眼前,打动着读者的心灵。如《爷爷去世的时候》,“那个时节,谷子(水稻)扬过花,才刚刚开始灌那白白的米浆。爷爷的病更重了,他想吃新米。于是,一家人便使出近乎千里眼顺风耳的功夫到处打听,终于打听到有一处有……父亲跑去,说了老人的愿望之后,人家同意卖给一点。父亲下到田里,把那包裹着新米的黄黄的谷穗割下来。父亲把湿漉漉的谷穗背回来,一家人忙用手将谷穗上的谷粒往下剔,接着弄去热热的锅里加速炒干,而后拿到碓窝里去舂出新米来。这新米,大约四五斤,爷爷没有吃完那些新米就去世了。”这一段文字中,动词的连续使用,使情节和情绪跌宕起伏,让读者为之动情动容。而作者涉及的长辈题材,虽是对自身孝道的书写,却可成为川北地域孝文化、家庭伦理道德、社会伦理道德的个体样本性思考,是对孟子所言“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的一个生动注释。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告诉我们:“艺术家从出生至死,心中都刻着苦难和死亡的印象。”作者在作品中也写到了苦难,在《吃相》《成长》这两辑中多有表述,如《馋果》中偷吃桃子不成,老三挨了痛打;《春荒》中立马就要断顿的节奏;《红苕杂记》中整整一冬,红苕几乎天天见,甚至顿顿见;在《跑通学那条路上的故事》一文的《卖猪》中写到的欠学校生活费,在《为小媳妇们换吃的》中写到的偷出些米来换馒头、包子。这不仅是作者个人的苦难,而是他的家庭过去的苦难,他的乡村曾经的苦难,是那一个时代苦难历史的缩影。作者在叙述中没有将之写成纯粹对苦难的控诉,而是进行客观地描写,以作者当时少年的身份或视角,写出与大人不一样的忧伤,有的篇什还带着少年的天真和乐趣,在苦涩之中有些意外的喜悦,就像婆婆或外婆不经意从什么地方给他拿出一把花生或几粒糖果或一个鲜梨。在这些作品里,作者给读者提供了检视作者自身和所处时代地域的艰苦蓝本,并从艰苦中抬起头来。人生愈艰苦,或许我们愈能为之感动。我们从悲伤中不仅能感受到悲情和悲悯,更能感受到文学和心灵的美丽。
四
院落讲述着生活,大院渗透于血液。无论是《住在木楼房》,还是《住在堂屋》;无论是《住在牛圈屋》 《住在草房和瓦房》,还是《记忆里的大院子》……在现实中都再也见不到了,这些建筑物承载作者的生活状态和精神意象,成为建筑在他心灵上的聚落,而这些聚落随着时间的推移,又被拆得支离破碎,成为他记忆深处幸福美好和苦难疼痛的刻痕,就像黄连沾着蜜糖,他感觉到的是自己舌尖上的味道。而与老屋和大院有关的那些熟悉或陌生的脸孔,如今已渐行渐远,留下的只是跨过门槛的背影,好在读者能从文章的字里行间看到其真实的表情和隔空的镜像。
另一座“意义非凡”的大院,仍坐落在时间的掌心。那就是作者心中的苍溪县委大院。从青砖砌墙,白灰勾缝,红漆门窗,青瓦结顶的“苏式办公楼”外观,到“撮箕口”“一条枪”“尺子拐”的川北民居造型,再到樟树、桂花树、桉树、洋槐撑起的幽静环境,这些建筑物与场景在作者个体生命里已赋予外形、色彩、空间、办公、读书、居住、景观以及人际关系的体验价值,乃至具有升华而来的文化价值和文物价值。作者从乡下老家的大院走到县委大院,到回眸两座大院的变迁,作者走过或停留的每一间屋子的影像都叠印着人生的印象。乡下的大院消亡了,而县城的大院因决策者、有识之士和苍溪人民的智慧,在城市的进程中作为标志性建筑物得以保存,在带给作者和读者失落和欣慰的同时又带给大家无尽的深思。文化的传承、文化的渗透,文化的消亡,文化的记忆,或许可在灰色的屋檐和重叠的青瓦缝中长出几缕春天的青葱和冬日残败的岁月经络。
阿多尼斯说:“爱,是持续瞬间的永恒”。奉来禹就是将这些人生中闪亮的瞬间串成珠串,把高山、大河、梨花、虫鱼、稼禾、耕牛、老屋、蛮洞、水田、堰塘之类的景物,以及人和事融合在对故乡的大爱里,定格在记忆的永恒间。
五
对故乡最好的尊敬就是不要忘记。对平凡人生中难以磨灭真实价值的致敬就是找到自己的表达。
近年来,写故乡,写乡土,写乡愁的作品不少。奉来禹却能顺着几十年的脉络,在纷繁的人情世故和众多的乡土风物中,用他那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洞若观火的沉思去挖掘那些震撼心灵的细微。他的手犹如有一把精美的小锄头,就像他小时候在麦茬地里挖麻芋子(半夏),挖出了生活的酸甜苦辣麻。其实,作者在一次又一次的身体回乡之中,用视线和血脉,在内心串连起城市与乡村的关系,这是其一种精神源头的寻根和人文积淀后一次又一次思索的情感书写。作者居住的城市离故乡不远,他有更多的机会去亲近乡村,去体味亲情,乡村的变化就像作者老家那一株株猕猴桃在自然而然地挤占苍溪雪梨的领地,它慢慢地长高长大,慢慢地铺天盖地……奉来禹的乡村,没有那种城市与乡村的拦腰折断,没有那种城市与乡村的残暴撕裂,没有那样伤筋动骨的疼痛断裂,没有那种找不到来处的精神割裂,他最多就是在曾经住过又消失的大院的土地上顺其自然地伤心叹息,或在“老母亲弯腰锁门,那一刹那,我心头一酸,双眼湿润了——我们这个家移动了。”之后的无奈,以及老母亲离家不到两个月,那棵年年挂满甜脆鲜亮苹果的老苹果树还是死了的忧愁和伤心。作者更多的是以一种理性的思维在对待乡村和城市的变迁。在汩汩流淌的时光里,读者仿佛能够看到那些镀上光影的故事,那些“可见性”的形象被作者赋予了来自心灵深处的思想。就像贾斯培·琼斯以铜铸造了两只啤酒罐那样,可以让我们“以更宽容也更警醒的目光看待周围的世界。”
故乡,是奉来禹生命中的泉水、粮食、空气。《最忆苍溪》是一部作者关于自己生活、生存和生命的难忘历史, 是作者亲人朋友部分生活的真实写照,是作者对苍溪的山水风物、乡土人情的深切观照。作者在与自己对话,与生活对话,与生命对话,在与养育他的苍溪大地对话,他仰望的是故乡深邃而又宁静并闪烁着耀眼星光的天空。作者心净透亮,心境相依。
六
从生活中来,到灵魂中去。《最忆苍溪》,也可以说是奉来禹的“与苍溪书”和“与生命书”,也是作者报答苍溪养育之恩的本意。无论是身处苍溪还是苍溪以外的各色人等,如你有机会邂逅《最忆苍溪》或奉来禹,或许就能牵挂起你“梨花一枝春带雨”和苍溪雪梨的味道。
就这样,苍溪也牵出了我生命中的记忆:小时候听父亲讲,他1957年从南充师范学校毕业就填报了到当时南充地区最偏远的苍溪去当教师的志愿,但没能如愿以偿,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苍溪的名字。有一年,大舅在苍溪流动行医,用一个大纸箱给我家带来了雪梨,我第一次吃到了又脆又甜、白白胖胖、流着汁水、让人口舌生津的苍溪雪梨。还有一年,我到苍溪参加全省农村经纪人经验交流会,车过嘉陵江大桥,到了苍溪县城,去过龙山镇,沿街摆放的销售沙参的长蛇阵,一根一根沙参像参差不齐的矛的坚硬仍让我记忆犹新。还有一年,拍摄助力新农村发展电视专题片,在夕阳西下的傍晚,农妇用敞口背篼背起刚刚采摘下新鲜硕大的雪梨低头弯腰走出梨园走进我们的镜头。还有一年,我到嘉陵江畔塔山湾古渡口——苍溪红军渡,瞻仰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战役遗址。
夜深了,我关上电脑,蓦然又想起那一次与奉来禹在成都城西的一处茶坊饮茶,交谈毕,夜色与灯火之中我们亲热地握手告辞,他那略为孤独又爱好沉思的背影消失在枝繁叶茂的银杏树下,而沉淀在我记忆的深处,那晚天空中透过淡淡云层的月华,对他谦逊的美德静静地表达着深深的敬意。
這一部散文集,是奉来禹在日积月累的散文历练中积累的心血结晶,呈现出奉来禹散文朴实、真实、真诚、温和中还略带川北方言幽默面貌,平常的藏而不露,也就以这种方式向我们展现和传达着他的性格和品质。韩愈那句“文从字顺各识职”或许就是对他的真实写照。当然,作品集中也有少量篇什因作者离开家乡之后对一些乡情体味渐淡,略显单薄,个别文字略嫌冗长,如删繁就简,则更加精当。总之,奉来禹从故乡出发,又回到故乡,他在故乡收藏自我,收获自我,展示自我,升华自我。作者把那些像东河的流水一样容易逝去的事实信息和感觉信息,用记忆的切片保留了下来。作者攫取了事物与情感的本质,用心灵切割和打磨,留下了对苍溪恩重如山的纪念品。读者可以从他的作品深入到他的内心世界,而这些作品,不仅属于他自己,也属于他的故乡苍溪,属于巴山蜀水,属于更广阔的天地。
贴近,是苍溪的情。
走远,是故乡的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