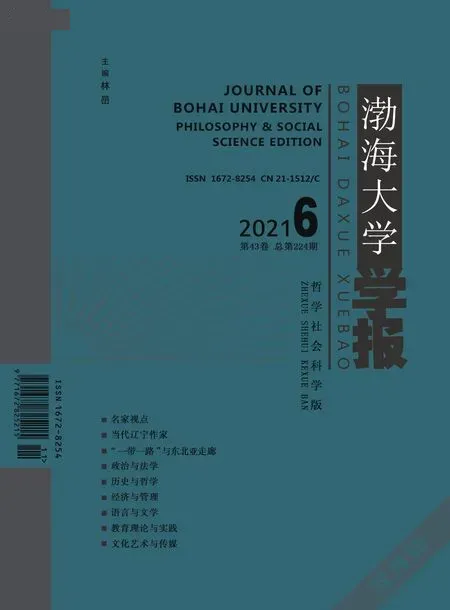塞利纳小说中的“时间”与“空间”
段慧敏(苏州大学外语学院,江苏苏州215006)
20世纪法国作家路易-费尔迪南·塞利纳(1894-1961)被誉为“平民普鲁斯特”[1],更有研究者将塞利纳与普鲁斯特并称为“法国20世纪最伟大的两位小说家”[2]。塞利纳的写作内容涵盖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历史的众多方面,其八部小说揭示了法国乃至整个欧洲战前、战时、战后社会诸多不可回避的问题,以俚俗却雄辩的语言、夸张的手法、史诗般的笔触描绘了一个异化的、罪恶的世界,在20世纪法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与普鲁斯特一样构建了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学巨厦。贯穿塞利纳八部小说作品始终的一个核心问题即“人”的问题: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内,人是以何种状态生存、以何种姿态抗争?时间与空间所构成的外部世界是塞利纳小说人物生存境遇的重要影响因素。塞利纳小说的叙事者总是在不断地逃亡之中观察着这个世界,他的视角总是逐渐消失的,全景式的或俯瞰式的[3]。逃亡之中的时间是模糊的,空间是混乱的,致使塞利纳小说的时空背景表面上看似乎都具有随意性,呈现出零散、无规则的样态。实际上塞利纳小说中的时空主题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它并不是简单的背景确立,塞利纳不但通过独特的时空交替方式组织叙事结构,而且通过时间与空间主题的叙事将生存与死亡主题引入其中,展现了塞利纳的生死时空观,构建出塞利纳小说统一的时空下的整体世界。
一、“封闭”与“开放”:流浪者的空间
塞利纳小说中的空间是流浪者的空间。主人公对远方既充满向往,又充满各种惶恐不定。“大海”是塞利纳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空间之一。塞利纳赋予航船与水域以开放的意义,它们代表了模糊未知的远方。“大海”在小说叙事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情节推动作用。在《茫茫黑夜漫游》中,主人公巴尔达缪为了逃避战争而踏上开往非洲的航船,在非洲碰壁后又辗转乘船到达美国,每一次情节转折都与大海相关。《分期死亡》中的父母也是在小主人公学徒生涯屡屡失败后,将他送往了一水之隔的英国。大海与航船是推动主人公命运转折的标记,是将主人公命运引向开放的标记。与大海相关的一切,在其核心要素“水”的重复之中,展现了其文本深层的意义,即空间的“开放性”。大海或水元素,在塞利纳的小说中代表了开放与自由,但是只有当人们航行于其上之时,这种自由才会显现出来,一旦人落入水中,水便具有了其致命的危险性[4]。《分期死亡》中所描绘的在迪耶普的海水浴便是末日般的场景:
“就在这时,一团可怕的卵石突然向我的胸部齐射过来……我变成了靶子……我被水淹没……真可怕……我被一场滔天的洪水淹没……然后我又被抛了回来,被抛射,被横陈在我母亲的脚边……她想把我抓住,把我从水里拽出来……可我又被卷走……她发出一声恐怖的尖叫。整个海滩上的人都涌了过来……但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游泳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焦躁不安……怒涛把我吸到海底后,又让我弹回水面,发出死人般嘶哑的喘气声……”[5]
落入水中的人面临着被水淹没的危险。此时的水便不再具有开放性,而是相反地具有封闭性,直接将人物引向窒息与死亡。我们在塞利纳的作品中随处可以看到水的元素。但是使人乐观的、开放性的水的形象却往往暗藏着杀机;使人窒息的封闭的水的形象以多种面目呈现,将人拉入死亡之地。水在塞利纳的作品中永远都不是新鲜清洁的水,水不但是不纯净的,而且还经常会与其他物质混合起来。水是士兵们在弗兰德平原上与之斗争的烂泥浆,也是不幸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每天必经的烂泥塘之路:“村子从未完全摆脱工地与垃圾堆之间的这些烂泥。”①[6]污水和泥浆因此成了塞利纳笔下空间景物的特征,也成了其人物的一个恒久的威胁。处于充满污水与泥浆的空间里,人物总是面临着陷入封闭与窒息的危险。塞利纳笔下以水元素为核心的空间意义可以通过以下图示呈现出来:
大海(船)——水——开放性(拯救)
大海(雨、污水、泥浆)——水——封闭性(威胁)
“大海”或与水元素相关的空间是带有两面性的。其开放性的一面推动了小说情节的发展,将主人公的命运引向自由的新的未知,而其封闭性的一面则会给主人公带来封闭甚至死亡的威胁。
“坟墓”同样是塞利纳小说具有典型意义的空间。这其中包括真正的坟墓,也包括被塞利纳描绘成坟墓的城市、地窖、地铁、地下厕所等。真正意义上坟墓在塞利纳的作品中并没有太多的描述,只有《分期死亡》中祖母的坟墓和《茫茫黑夜漫游》中约瑟夫·比奥迪莱的陵墓。坟墓将尸体封在里面,显然是一个腐烂之地,是一个聚集了腐肉、粪便与死亡的地方,是一个完全消极的空间。比奥迪莱的坟墓位于约瑟夫·比奥迪莱学院的正中心,把这幢建筑物的意义集中体现了出来——这幢建筑物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坟墓,动物的遗体在研究它们的科学家们漠然的目光下慢慢腐烂:“出于成本节约,某些腐烂经受着不同程度的降解和延长。实验室里某些训练有素的小伙子们确实曾经在这个活棺材里做饭,腐烂及其怪味都没能对他们产生任何影响。”[6](280)“坟墓”这个词不仅限于其表面意义,在塞利纳的作品中,更为广阔的空间都可以成为坟墓:地窖、房屋,甚至是城堡[4](97)。《茫茫黑夜漫游》中图卢兹的地下墓室和《木偶戏班》中放置克拉本尸体的地窖,因为死亡出现,都成了塞利纳眼中的坟墓。《从一座城堡到另一座城堡》中,西格马林根城堡的地窖里也发现了死尸,“被人们遗忘了十四个世纪”,“被杀死的对手,被吊死,被勒得僵硬(……)还有被劫持的骨架。”[7]这些令人窒息的密闭空间,同样具有“坟墓”的特色。
《茫茫黑夜漫游》中,作为城市的巴黎,被塞利纳通过反复出现的“克里希广场”②描绘成“坟墓”。图卢兹的“坟墓之地”是木乃伊地下墓室,昂鲁伊老太太请巴尔达缪参观了这个地下墓室,这个地下墓室也同时成了被罗班松谋杀的昂鲁伊老太太的坟墓③。《北方》中,在哈拉斯看来,图卢兹是“无菌世界末日”期间唯一一处仍存在着谵妄现象的地方[8]。显然对于塞利纳来说图卢兹是与死亡密切相关的一座城市。同样,在《北方》中,柏林也被描绘成一个“尸体城市”,但是和图卢兹的木乃伊一样,那里的“尸体房屋”也被整理得有条有理:
“房子已经完全死去,就像一个火山口一样,所有的肠子管子都喷射在外面,还有心脏,骨头,皮肤;但是所有的内脏都整齐排列在屋顶,就像是屠案上的动物,只需一棍就可以打出它的内脏,但是它突然间又奔跑起来!”[8](517)
《木偶戏班》中的伦敦也同样是死亡之城。在这些城市里,“我们大口呼吸着死亡的气息,此生都难以忘记。”[6](286)城市被描述成坟墓,与作为坟墓的地下空间具有了同样的功能:封闭的死亡容纳地。坟墓之地的核心要素是地下空间,而在此它代表了一种封闭性,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图示理解“坟墓之地”的空间意义:
“坟墓”——地下空间——封闭性
与“坟墓”的封闭空间相对应的“公墓”,在塞利纳看来则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尸体变成了幽灵[4](99)。公墓具有一种自然与文明相结合的特征,它既是人造的场所,又往往与自然景物紧密连接,这使得公墓具有了自然性与虚幻性。尸体变成了幽灵在公墓的自然的开放空间中游荡,飘向远方。在塞利纳的作品中极少提到的下葬的场景也证实了塞利纳的这一观点。在《北方》中,警察局长西米耶和冯·列登的葬礼上,出现了两个幽灵:卫兵加尔马尔和他的囚徒牧师。两个人曾经在很久以前便消失了,此时似乎是从另一个世界回来,“非常安静,一个人敲着鼓点,另一个人唱着圣歌,跟在棺材后面……看上去像是外地来的人。”[8](563)而后他们又神秘地消失在了“北方”,很显然,塞利纳的“北方”正是“彼岸”与“幻境”的方向。这里的音乐声使人物如同飞在空中,此时死者并没有被封闭起来,而是变成幽灵飞升起来。塞利纳通过死亡的方式使人得到最终的轻灵的解脱,“死亡”成为使“坟墓”这个地下空间走向开放的唯一途径。塞利纳的小说中,地下空间是一个具有威胁性的场所。无论是纽约的厕所(“粪便洞穴”)、图卢兹的地下墓室或是缪济娜带巴尔达缪去躲避轰炸的防空洞,地下空间都充斥着粪便、木乃伊或腐烂的尸体。这些封闭的空间中充斥了死亡的意象,其作用完全是消极的、面向死亡的。公墓的开放性则具有一个积极作用,即人们要经过以地下空间为象征的死亡,才能获得拯救,这是塞利纳空间主题中所特有的“向死而生”的观点。“公墓”这一空间形象在塞利纳小说中的独特意义,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图示来进行表示:
公墓——地下空间+自然——开放性
塞利纳笔下的空间丰富多变,错乱的表象下呈现出封闭与开放两个序列,构成了统一的主题。小说的情节在封闭性与开放性之间不断交错进展,空间封闭,人物面临威胁;空间开放,人物的命运被推向新的未知。塞利纳笔下的人物,不停地、被动地游走在封闭与开放之间,挣扎于生存与死亡之间。他们总是在不断重复自己的旅程,逃脱的希望几乎变成了不可能。在塞利纳式的噩梦里,只有死亡才能将人们唤醒[9]。空间主题与生存和死亡主题由此紧密相连,构成了人物命运的图景。
二、历史的时间与小说的时间
塞利纳小说的时间是复杂的、模糊的、非线性的。他不断地通过回忆的方式呈现时间,打破了时间的线性流淌,又将时间与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相结合,构建一种“编年史”的时间,并强加了遗忘、断裂等使时间淡化的因素,使时间呈现出表面分散零散的状态。在文本的内在层面,塞利纳则通过“过去”与“现在”明确地交替与循环,使小说的时间主题呈现出统一的内在关联性。塞利纳小说以战争为写作背景,其中的社会群体从历史角度来看都是处于危机之中的。面对这种危机,塞利纳早期的作品中首先是通过回忆来对抗“当下”的时间,暂时逃避战争中时刻存在的死亡威胁。对一战前的曙光的怀恋是这种回忆的重要体现。自1900年起,法国就不停地经历着一种疯狂却不可见的衰落。对于塞利纳来说,“美好年代”成为战前时光最值得追忆的时期。《分期死亡》中,对“美好年代”时期的巴黎的描述非常全面。随处可见的公共马车、玛莱区及工匠们、王宫的拱廊下的妓女们、万博会的低俗品味、巴黎的时尚,还有塞利纳亲眼所见的巴黎的工商劳务界以及巴黎的郊区……塞利纳使用了大量的老生常谈的代表形象来描绘这个时代,就像是给1900年前后的时光不断地贴上各种标签[10]。同时,塞利纳还通过复原各种典型人物来重建那个时期的现实,在《分期死亡》中,塞利纳通过这些人物构建了一个小小世界:暴躁的父亲、懦弱的母亲、坚强开明的外婆、发明家库尔西亚、高尔罗热一家、诺拉、流浪儿、痴儿荣金德……而最具代表性的“美好年代”的人物则是《茫茫黑夜漫游》中的昂鲁伊老太太。昂鲁伊老太太是“美好年代”的遗属和见证,她经历了战前的美好时光,年老后则自闭在花园的矮屋里,儿子、儿媳妇时刻算计着她的退休金。为了摆脱对她的照顾,儿子和儿媳妇甚至雇凶杀人。而长期隐居在“墓室一样的陋室中”的昂鲁伊老太太却表现出惊人矍铄的神采:
她怒喊的时候,声音沙哑;她像常人一般说话时,声音爽朗,吐字清晰,口齿伶俐,华丽的辞藻和格言警句生动活泼,跳跃奔腾,令人发笑。这种借助声音叙事的本领使人想起古时候的人,那时要是不会又说又唱,不会把说唱巧妙结合起来,就会被视为愚蠢、耻辱和怪癖。(……)岁月给昂鲁伊老太太披上活泼的轻装,有如老树逢春,清癯抖擞。二十年来她家徒四壁,身无分文,却没有给她的心灵造成创伤[6](254-255)。
昂鲁伊老太太是从“墓室”里走出的“美好年代”的人物,她的行为与话语表现出她对时间的抵抗,她的语言并不是对垂死的现实的反射,而是一种生机的源泉,这种语言反射出了一个幸福的时代。对于塞利纳来说,昂鲁伊老太太诠释了他对1900年前的黄金时代的怀念。在那个时代,所有的女性都会以昂鲁伊老太太的方式来讲话和歌唱。《分期死亡》中有关外婆的描述也印证了这一点。但是最终昂鲁伊老太太与外婆的去世,都暗示了那个时代的一去不复返。塞利纳描述美好年代的人物及其语言,不仅是单纯的回忆,而是通过模仿这种语言,使其魅力获得重生。塞利纳曾说,“昂鲁伊老太太就是我”[11]。塞利纳通过引入回忆的“复古”方式,使其人物逃出小说的叙事时间,在“现中”与“过去”的转换中暂时逃脱死亡的威胁。塞利纳通过“回忆”的方式,在怀念与追忆的表象之下,呈现了时间维度中的“过去”。具有怀念性质的“过去”的反复呈现,使人物跳出“当下”,暂时逃脱死亡的威胁的同时,给小说人物带来了一种与历史的关联性。
在塞利纳看来,历史是用来背叛的,也是用来遗忘的。这里有一种对官方历史的反抗,因为官方的历史建立在一种记忆缺失的选择的基础之上、建立在遗忘了生活的复杂性的选择的基础之上,这种选择将某些记忆排除在外[12]。“一切被战胜的都是垃圾!……我非常清楚!……”[8](21)只有最后的胜利者才是有道理的,“是胜利者们写就了历史”[7](311)。塞利纳认为,已经消失或已经逝去的一切都留有痕迹,在写作中他着力重现那些被官方记忆所排除的特殊线索。塞利纳站在“弱者”的一边,致力于写出“被战胜者”反抗“战胜者”的历史[13]。他所关注的时间,是历史长河中短暂的零散时间,也就是那些重大转变或关键时刻中并不重要的痕迹。例如《从一座城堡到另一座城堡》中,当轰炸的威胁不断临近的时候,叙述者却只想送一个焦躁不安的小女孩回家:“……我在这时候,并不关心什么大战略,而是关心让希尔达回到她父亲那里……”[7](229)塞利纳通过对重要时刻中微小事件的描述,使历史变得具体,将自身经历融入历史。战争的历史中,各种事件带来的恐惧因此更容易被感知:“不断听到炸弹的爆炸声,我们最终感知到了自己的重要性,(……)实际上,对我们来说,(在左恩霍夫期间),重要的是金色烟叶和食品柜……”[8](326)这种对于零散而短暂的时间的关注,通过主人公对“当下”的具体感受,将“现在”折射到了写作之中。塞利纳所关注的,并不是集体的时间,或大写的历史,而是个体的时间,即主人公的经历。大写的历史在小说中被遗忘,并被个体的经历所取代,因此塞利纳小说的主人公,与其说是历史的见证者,不如说是历史的参与者,他以自己的经历重新构建了战争时期的非官方编年史。在塞利纳看来,历史会通过“净化”而将自身歪曲,失去其一致性:“人们几乎从来不知道,那时候我们上演的是另外一出戏。这样的人太多了!”[7](177)塞利纳的小说即是官方历史之外的“另一出戏”,小说时间解构了官方的历史时间,集体记忆和个体记忆都变得不可靠,“记忆是明确的,忠实的……然后突然之间便不复存在,不复存在!……”[7](129)没有记忆能够与官方的历史时间重合,历史的时间与历史的可能性,似乎都顷刻之间归于乌有。
塞利纳小说中最多的描述是关于逃亡与流亡。在战争情况下,这是一种匆忙的经历,也是具有威胁性的死亡的经历。逃亡与流亡造成了时间的混乱,必须要透过一些距离、一些遗忘,结合当下的实际才能对逃亡与流亡进行关注与回顾。逃亡与流亡期间,人们所经历的是另一种时间性,在痛苦中度过的时期可以使人们与现实分离,逃离了惯常的节奏,时间开始变得不真实[12](217)。这种感受只是让人更加疯狂地感知到自己的末日。塞利纳通过个体经历将官方历史变得模糊错乱,使历史的时间变成了被遗忘的时间。他致力于呈现出一种毫无负担、毫无掩饰的时间,因此他努力在“现在”中摆脱“历史”的束缚,通过自己的叙事和想象重新建立了时间。他认为自己是有关“消失”的历史学家,是一个编年史家:“历史过去了,您还在这里,我讲给您听……”[8](20)“我把您重新带回那些已经消失了的人的小事实、小动作或惊恐之中……”[8](494)。塞利纳以“战争时代的语言”[14]重现了战争,在塞利纳的碎片式的时间中,折射出了现代的历史。
塞利纳以回忆时间与个体时间打破了官方历史的时间,建立起小说的虚构时间。在这个破与立的过程中,“模糊”与“遗忘”是塞利纳解构历史时间、建立小说时间的两种重要方式。塞利纳以个人具体经历将重要的历史时刻模糊化,使人遗忘官方的历史记忆,将短暂的零散时间中的微小事件不断重复扩大,使时间跳出现实,体现出一种不真实性。在“零散时间”的表象之下,是一种被现在模糊化的过去,是站在“现在”的角度对官方历史的遗忘,它代表了一种新的确立,是塞利纳小说时间的最终呈现。塞利纳的历史观也是在这种逐渐演变的过程中形成。塞利纳突出了个人的经历与具体的微小事件,使战争中的恐怖被言说得淋漓尽致,给历史蒙上了一种更为悲壮的色彩,最终达到了塞利纳“为遗忘撰写历史”的目的。在塞利纳的最后一部作品中,历史的内在化意义以“黎戈登舞步”的形式展现出来:“(……)……历史的真正意义……以及我们所处的历史阶段……跳到这里!……噢!又跳到那里!……黎戈登舞步!到处都是舞会!(……)……见鬼的看热闹的人们……愿一切重新开始!……”[15]历史的真相如狂欢舞步般杂乱而难以把握,而塞利纳小说中时间主题的意义则在于采取一种“重新开始”的方式,构建了自己的时间,即融入大写的历史的个体时间。
三、幻境与“摆渡时空”
“幻境”一词在塞利纳作品中指与现实相对立的一切,塞利纳将彼岸世界定义为幻境,成为现实世界的对立面。现实世界对于塞利纳来说是活人的世界,即充满恨意的世界[16]。幻境是脱离了现实的时间与空间,即塞利纳所谓的“彼岸世界”。幻境不是一个确定的地点,而是某一个目的地,一个非现实的时空,塞利纳在小说中不断地设置“通道”使人物抵达幻境。这个通道,即从现实时空到虚幻时空的中转地,是塞利纳小说中独有的空间类型——“摆渡空间”。“通道”的典型代表是《轻快舞》中的弗朗斯堡车站地下通道。这个车站是德国和丹麦之间的边境检查站,当时的德国是世界末日之地,而丹麦则有如一个拯救一切的彼岸世界。经过德国逃亡丹麦的旅客们都必须下到这个地下室,从“真相—死亡”走向一个彼岸幻境,通向复活之路。塞利纳所描述的灯光也呈现出了一种幽灵的氛围:
“上面是一盏巨大的吊灯,透出青幽的光线……不太好区分那些人是不是都已经死了……或是他们只是睡去……然后呢?然后我们也像其他人一样,也躺了下来……为了旅行,那是一次旅行!无论是活着还是死了,我们都有权利去旅行,而且没人会阻止我们……”[15](261)。
通过“青幽的灯光”而表现出的氛围中,旅客们就像是幽灵,等待着彼岸之门打开,北方的丹麦即是一个可以自由呼吸的彼岸世界。去往丹麦之前,首先要在这个通道中经历虚幻的死亡。塞利纳的作品中,大多数人会关注战争及其杀戮造成的死亡,对虚幻的死亡则关注较少。幻境中的死亡是通往彼岸世界的一个出口,塞利纳将之称为“世界的另一端”。“死亡幻境”的意象在塞利纳的作品中随处可见:《木偶戏班》中图伊—图伊俱乐部被称为“地心”;《北方》中勒维冈在左恩霍夫的房间被描述成一座坟墓,并且由名叫伊阿戈的狗来把守,塞利纳认为,这条狗就像是看守地狱之门的三头犬塞伯拉斯一样,会允许或阻止那些想进入死亡世界的人们。塞利纳笔下的主人公也会幻想自己死后进入“幻境”的生活。在《别有奇景》中,他幻想自己在圣马洛,住在大广场上特别为他而建的坟墓中。他在城市的中心落脚,骑着特制的自行车飞过大街小巷,那辆名为“安彭代尔”的自行车完全没有重量,“我的自行车是你们完全想象不到的东西,我的安彭代尔!!……活着还是死去?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我会从这里出去,幻境会把我带走!……”[17]“这里”在此处指的是叙述者所处的监狱,即残酷的死亡之地,而幻境将它引向的地方则是一个幸福的死地,生灵最终交付出肉身的重量,化为幽灵飞起在圣马洛的上空。“轻”与音乐或舞蹈一样,是塞利纳幻境世界的符号之一[16](185)。塞利纳笔下的人物,通过轻灵的上升抵达“幻境”,进入虚幻状态的时间与空间。塞利纳的“幻境”是作家想象中人死后所处的时空,是一种遥远的、上升的空间与美好的、不再有痛苦的时间。塞利纳将许多幻境归属于“北方”。法国的北方、北欧的丹麦等地是童话的发源地,“幻境”这种遥远的、不再痛苦的时空,在无形之中与童话结合了起来。
塞利纳的写作是一场永恒的流亡,这场奥德修之旅的引导者是不断出现和消失的小说人物们。消失了的人物以幽灵的身份在彼岸世界重现,引导主人公脱离死亡痛苦,轻灵地飞向自由。《从一座城堡到另一座城堡》中,在勒维冈牧棒下登船的幽灵们,就连勒维冈本人也不知他们是从何处回归到“民众号”的甲板上。在这个著名的情节里,主人公看到已经成为幽灵的“活死人”们登船进行他们最后的旅行;在《分期死亡》中,主人公开始谵妄的情节里也看到了装满死者的船:“所有的死人我都认出来了……我甚至还认识那个手拿大棒的人。”[5](45)同样还有《茫茫黑夜漫游》中的“幽灵群游”,叙述者和女伴塔尼娅一起来到蒙马特高地的制高点,在那里他们除了天空无处可去。“我们来到了世界的尽头,此后就只有死者。”而后这个队伍消失了,跳出了时间,飞过英国,逃往北方的幻境。英国是由一位高大妇人掌管的岛屿,彼时她正在船上为自己泡茶。“那是世界上最美的船……她用巨大的船桨支配着一切。”[6](366)“船桨”这个意象在幽灵的旅行中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元素。塞利纳将船桨这一意象与希腊神话中冥王的船夫卡戎联系到一起,卡戎划着桨,带死人渡过冥河。“卡戎”这一形象最初出现在《从一座城堡到另一座城堡》中。卡戎在《从一座城堡到另一座城堡》被描述成一个可怕的存在,幽灵们上船时遭到他的粗暴对待和骚扰。“卡戎长了一个猴子的头!又有点像老虎的头!半虎半猴……”[7](111)希腊神话中,死者必须要交钱给摆渡人卡戎,才可以穿越冥河抵达冥界。“付费死亡”这一主题在塞利纳的作品中不断地重现。《分期死亡》的书名也出自这个典故。塞利纳在1960年对雅克·达理博奥德解释道:“对我来说,人们有权力死亡。我们有一个精彩故事可讲的时候,就可以进入死亡之地,我们交出这个故事,就可以踏入其中。《分期死亡》就是这样的象征。死是对生的奖赏……”[18]塞利纳在《分期死亡》的序言中说:“死亡可不是免费的!那是一块漂亮的、缀满故事的裹尸布,我们要把它呈给死亡女神。最后一口气是很有讲究的。”[5](40)塞利纳的作品中,卡戎是塞利纳笔下死亡幻境的核心人物。他在小说中以各种化身的形式呈现出来。“民众号”情节中的勒维冈和他的助手,都承担了卡戎的“生死摆渡人”功能。
摆渡人卡戎的船桨,是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工具与途径。“船桨”在法语中是“la rame”,这个词也同时具有“地铁列车”之意,是塞利纳“情感地铁”的列车。塞利纳像卡戎把所有旅客装载在“民众号”上一样,把他的读者也装载到了他的地铁上:“对不起!我把我的整个世界装进了地铁里!……自愿的或是强迫的……情感的地铁!我的地铁!”[19]塞利纳的地铁,既是《茫茫黑夜漫游》中将巴黎郊区的人们吞没的地铁,是开往黑夜深处的美国纽约的地铁,是《木偶戏班》中费尔迪南将米勒-帕特推下轨道的地铁,也是《北方》中主人公被希特勒主义者威胁的地铁。地铁之中存在着黑暗与死亡的威胁,而同时由于它的摆渡功能,使得地铁被赋予了一种连接现实与幻境的可能性:“那是时间和地点的混乱,见鬼!您知道,那是幻境……幻境就是这样……未来!过去!真的!假的!”[20]卡戎的船桨是从现实的时空到达幻境的摆渡工具,是生与死之间的摆渡意象。塞利纳通过一系列的“摆渡工具”,将幻境与现实连接起来;“卡戎”这一形象及其各种化身透过“摆渡功能”将船、通道、地铁等各种原本不相关形象连接到了一起,“摆渡人”与“摆渡工具”构成了塞利纳小说中的生死摆渡时空的整体。
结语
塞利纳小说中人物所生存的空间总是充斥着封闭的、令人窒息的危险,其时间则是现在与过去交错并存的错乱时间,逃脱封闭的空间与错乱的时间成了其笔下人物生存的本能。塞利纳通过大海(水元素)、地下空间等形象的反复使用构建出其小说空间的开放与封闭交错的特性:空间封闭,人物便面临威胁;空间开放,人物则被推向新的未知。塞利纳笔下的人物也由此不断游走在封闭与开放之间,挣扎在生存与死亡之间。“封闭”与“开放”交错的空间,展现出了一个充满威胁而永恒动荡的世界。空间主题与生死密切相关,构成了人物命运的图景,使主人公意识到“生命的真相不过是一种缓期的死亡”这一悲观思想。从时间角度来讲,塞利纳不断地通过回忆、狂欢等方式呈现时间,又将时间与战争的历史相结合,从而打破了时间的线性流淌,使其呈现出复杂性和模糊性。塞利纳在八部小说中通过回忆时间、交错时间、零散时间等非线性的时间将过去、现在与虚幻的时间联系起来,构建出一种融入了“大写的历史”的“个体时间”,最终达到了消解历史时间、重建小说时间的目的,从而构建出塞利纳自己的历史观。官方的历史是建立在“战胜者”对回忆的选择基础上,塞利纳在小说中强调要建立一种真实的、以个人经历为基础的历史时间,以“编年史家”和见证者的身份,重现两次大战期间充满恐惧与错乱的时间。塞利纳作为“编年史家”的创作目的得以达成,其小说更具有了“为被战胜者撰写历史”的意义。与此同时,塞利纳通过“幻境”这个特殊的时空展现了属于幽灵的安宁的空间与未来的时间。摆渡人卡戎这一形象将船、通道、地铁等一系列“摆渡工具”联系起来,通过这种联系,形成了塞利纳小说中独特的“摆渡时空”。两次大战给世界带来了痛苦的磨难与摧残,塞利纳通过小说的时间与空间主题重现了战争阴云笼罩之下的黑暗世界。空间中的开放与封闭、时间中的现在与过去,构建出一个使小说人物不断逃亡却无法逃脱的危险时空。塞利纳赋予小说人物的出口只有“幻境”,只有经历死亡,成为幽灵,才能逃出现实的时空,抵达幻境。“幻境”代表了小说人物向往的希望之地与自由之地,塞利纳将希望、自由与死亡联系起来,增加了作品的悲观色彩。
①《茫茫黑夜漫游》是作家的处女作和代表作,学术界对这部作品的研究要远远多于其他作品。《茫茫黑夜漫游》在1999年法国《世界报》评选的“20世纪百部最佳小说”中位居第六。本文中关于《茫茫黑夜漫游》原文的引用,均出自2007年伽利玛出版社的Folio 丛书。
②塞利纳应用“克利希广场”这一形象的目的,我们可以在巴黎地图上找答案:克利希广场旁边,便是巴黎最为著名的公墓——蒙玛特公墓。对于巴黎人来说,蒙玛特公墓即是死亡的代名词。也就是说,克利希广场的旁边,是一个死亡之地、幽灵之地,同样,在小说之中,“克利希广场”这一空间的出现,随之而来的,必定是一场通向死亡的狂欢。因此有人从巴黎十八区的艺术、精神、政治和社会生活角度,将塞利纳的《茫茫黑夜漫游》定义为“蒙玛特小说”。
③图卢兹的木乃伊地下墓室并非杜撰,而是确有其事。对于普通的死者来说,尸体会被换动位置,风干,变成干尸以便保存。在图卢兹,从棺材里移出的尸体,先会被放到钟楼的二层,而后风干了的尸体会被陈列在公墓里,公墓被用白骨装饰成洛可可的风格。或许正是因为对这些故事的了解,使塞利纳将图卢兹设为一个有地下墓室的死亡中心,而在后续作品中,塞利纳又至少两次重复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