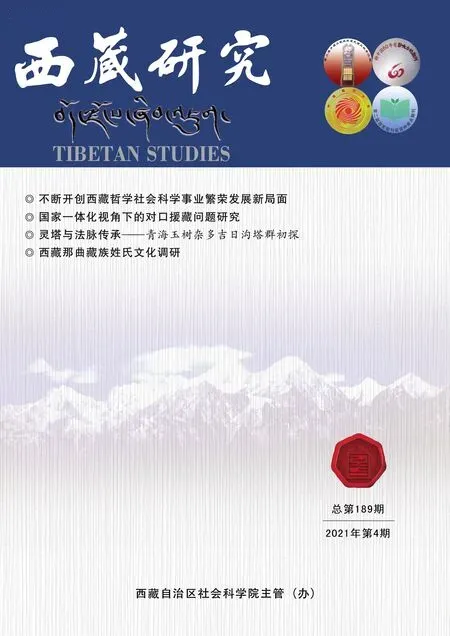表演与叙事:《格萨尔》史诗传播多模态话语阐释
王治国
(天津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天津 300387)
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兴起,由语言、图像、声音等构成的复杂多模态交际模式逐渐取代之前的单一语言模态。传统的戏剧、舞蹈、歌剧等表演艺术因其融合了大量诸如语言、音乐、身体动作等符号资源,在特定语境和文化中经过策划编导形成的表演,实际上就是多模态意义生成的过程。其他不太容易归类的与表演相关的活动,类似录制的表演(如电影与电视剧),艺术装置和自然发生的表演片段以及媒介录制的场景,同样包括复杂的符号模式。然而,如此复杂的叙事模态在学界尚未展开系统研究。本文以活态史诗《格萨尔》为例,尝试探讨活态史诗的多模态特征,并对多模态叙事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对“表演中的创作”活态史诗传播机制进行阐释。
一、史诗表演的多模态特征
符号学研究旨在描绘意义生成过程中不同符号系统所发挥的作用。学界对于每一种符号的功能有所了解,但是对于不同符号在文本和语篇中如何互动、如何结合却是着墨较少。无论是对单独一种符码(模态)意义的理解,还是多模态互动综合理解文本意义,都是对多模态文本如何传达意义的狭义解读。正如理解单独的文本符号不能全部解释意义如何源自某一文本,全部理解多模态符码之间的互动也未必能够完全解释意义的来源。因为,同样的信息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的交际目的,而正是语境影响着意义的最终确定。
多模态表演理论致力于符号资源的互动作用,类似语言、音乐、灯光、空间、举止神态、服饰等。该理论认为,表达语篇意义的手段和符号并不仅仅是语言文字、图像等,声音、动作等手段和符号同样能够传递语篇的意义[1]。所有语篇意义都是多模态的呈现。直到现在人们一直认为文本的言语部分是意义的主要承担者,其他因素则处于非中心地位,只起着辅助作用。然而有关视觉与言语关系的最新研究成果认为:图像可以是主导形式,文字起辅助作用,或图像文本共同决定文本意义。相对于图像如何辅助文字传递信息,该领域的学者更多地侧重于图像和文字的互动性[2]。Barthes(巴特)基于图像和文字在视觉与言语关系中的地位,提出二者之间的三种关系:1.依托:文字辅助图像;2.图解:图像辅助文字;3.补充:文字图像地位相当[3]。图像和文字两种模态相互交织共同建构了文本的意义。
显然,书面文本是永久的、可以追溯的、反复阅读的,而表演是稍纵即逝和无法复制的。表演的每一次演出也是独特的,语境也不同,听众的解读也不同。正如Birch(伯奇)所言:“不存在单一不变的文本。”[4]以活态史诗传播为例,其传播历程经历了从说唱艺人的口头说唱到书面语言文本传播,再到带插图的平面媒体,最后发展为集语言、图像、声音为一体的多模态影像传播。如此复杂多样的传播形态,单从语言角度无法全面理解活态史诗的意义构建。单一模态的传播分析,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活态文学多模态传播的需要。史诗的故事情节一样,但是每一次说唱艺人说唱的效果不一样,每一次说唱所引起的听众反应和感知反馈也是独一无二的,即确定中的不确定。确定的是故事情节,不确定的说唱艺人的个性化表达,而这种个性化表达恰恰是吸引现场观众的关键所在。即使一部史诗的核心内容是固定的、不变的,但是,每一次表演可能有所不同。正如一部文学名著改编为影视作品,观众聚焦的不是内容,而是演员的表演所带来的视听享受一样。作为多模态艺术品,史诗说唱与其他表演艺术一样,既具有稳定性,又具有变异性,在常规和变异中来回摇摆,即稳定性和变异性同在。
活态史诗《格萨尔》从藏族古老的说唱艺人口头演述开始,随着印刷术的传入,进入书面文本与口头演述并行的阶段,再经过带有插图的平面媒体,最后发展为集语言、图像、声音、动作为一体的多模态表演艺术。史诗演述过程中只分析说唱艺人的话语显然是片面的,说唱艺人的说唱声调、唱腔唱调、面部表情、手势、身体动作等对听众史诗赏析和史诗自身传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史诗说唱表演中的唱词,只是史诗传统表意的一部分,更为重要的是在赏析史诗《格萨尔》时,格萨尔图像占有重要的一环,在史诗传承和传播中同样作出了重大贡献。活态史诗自身的意义构建就具有多模态话语属性,是多模态综合艺术的典型体现。活态史诗凭借说唱艺人的说唱、唱词、声音、动作、曲调、服饰、场景、演述语境等多种表意符号的协同融合,构建活态史诗意义,制造出奇的活态文化审美效果,会赢得更多听众和读者的青睐。由于活态史诗天然具有的多模态话语属性,多模态话语分析对活态史诗叙事研究具有强大的阐释力,可以用来阐述活态史诗的生成机制与传播接受。
作为表演艺术的活态史诗,其多模态特征鲜明而丰富。实际上,口头文学的文本生成和传承机制非常复杂,除了说唱艺人的口头传承外,文本传播也为史诗基本内容情节的形成和样态传承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说唱艺人自身的知识结构、说唱技巧、表演语境与现场听众的互动等都是传承机制着力关注的重要环节。结合《格萨尔》活态史诗传播轨迹,可将活态史诗的多模态叙事分为三种,即,听觉主导的口语文化叙事、视觉文化的图像叙事和媒介融合的数字文化叙事。
二、《格萨尔》口头文本叙事
表演艺术长期以来固守于传统研究领域,重点在于某一具体的符号系统。然而,与歌剧、戏剧、芭蕾、马戏团、哑剧等类似,表演艺术同样离不开对诸如声音、身体活动、身体饰物以及有目的创造历史悠久的符号模态的掌握和理解。多模态视角研究表演理论,将传统的表演艺术(如戏剧、舞蹈、歌剧等)、活态表演艺术持续性的表演、媒介录制的表演(如电影、电视)以及社交媒体零星的表演片段等融合起来,进行多媒介传播。与传统书面文学作品依赖读者发挥想象力,浸入到虚构的文学世界中去感受、接受和赏析故事相比,多模态口头活态文学则“依赖其多模态诗学象似性,调用读者的多个感官,甚至会诱发读者的身体动作,令其得以在真实和虚拟、身体和认知之间的界面上感受文学艺术的审美效果”[5]。
人们通过一定场域空间内共同的社会习惯来联系和感知一种归属感,史诗演述传统更是如此。要描述同一戏剧在不同表演中语义交流的多样性,需要运用多模态符号学知识,将语言之外的符号互动交际阐释清晰。说唱艺人说唱的语境,以及随后作为舞台说唱的艺术设计、灯光、道具、动作、举止神态、身体姿态等等,都对史诗舞台艺术话语发挥着构建作用,达到意义增值的效果。艺术说唱的伴奏乐器和音乐、艺人声音高低、腔调的变换、曲谱等构成史诗舞台表演的综合艺术。McAuley(麦考利)指出:戏剧演出的视频摄录实际上已经是对该演出的一次阐释:包括一系列的选择,如摄录内容,摄录姿态,采取何种摄录视角,从而,表演的摄录结果就是一件新的艺术成品[6]。
实际上并没有任何绝对的分析框架和工具,对任何复杂的多模态艺术进行分析。史诗文本作为剧本,是以唱词和乐谱形式存在。也即是,史诗文本是一个由唱词和乐谱组成的一种潜在的意义构建活动,而这两者只有经过舞台表演才能得以呈现,才能例示、实体化。每一次表演产生一个新文本,每一个新文本需要重新进行研究,因为活态表演的本质是不稳定的,对于活态表演的文字重描是不可能的,而对活态表演的可复制性描述在多模态研究中又是非常必要的,从而为此目的生发出一系列誊写和加注符号。对史诗综合表演艺术的呈现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通过对文本和表演进行整合,分成宏观和微观进行分析多种模态之间的综合作用和交互影响。有鉴于此,多模式文本就是最终供舞台表演的书面文本(当然是为观众表演)。媒体、模式和符号系统之间的区别非常重要,就像认识到同一文本从不同角度出发(媒介、模式或符号系统)可以有不同的评估框架一样重要。同时,由媒体决定的文本,例如电影或电视剧,能够通过视觉、听觉以及不同的图像系统传达意义。考虑到这些方式的媒介融合与交融性,电影、电视、戏剧、歌剧或者漫画都处在多模态范围内。
对于活态史诗的多模态话语分析,尽管可以单独就每种模态对呈现史诗语境和文化内涵展开,以用于启发式目的的分析,但实际上,只能通过整合史诗活态表演事件中的所有资源和模态来理解史诗的意义。为此,不可能用抽象的术语来讨论活态史诗表演,因为每次表演都会创造一个新的文本,一次新的体验和一个新的事件。换句话说,即使同一史诗的某个章节部分,每位说唱艺人在不同语境中的表演可能被解释为彼此的“副本”,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每场现场表演都会产生全新的意义集合,因为“表演中的创作”,是活态史诗千年传唱的本质性规定。不同模态的相互作用产生了全新的意义,超过了单个模态所产生的意义总和。面对文字与图画的多模态文本时,不是仅仅从文字模态或图片模态来推断意义,而是综合文字和图画,因为意义存在于文字和图片的结合体中。
三、《格萨尔》视觉图像叙事
长期以来,格萨尔史诗就以口传、文字、图像等媒介载体在青藏高原流布。近年来,格萨尔图像引起了格萨尔学界的密切关注,学者们已经撰文对格萨尔传承的图像维度进行了解读。有研究者将格萨尔图像区分为史诗内容图说,史诗人物图像两类[7];有学者对格萨尔壁画进行研究[8];有学者对格萨尔唐卡进行研究[9];也有学者对格萨尔石刻进行研究[10];还有学者对格萨尔的面具(羌姆)研究[11];以及对格萨尔雕塑的研究[12]和手抄文本中插图的研究[13]。其中王田和杨嘉铭的研究具有代表性,他们归纳了传统格萨尔图像的四个基本特征:即,传统的格萨尔图像;寺院、经堂保存格萨尔图像的主要场所;格萨尔图像弥散出神圣性;传统格萨尔图像所保存的场地在室内[14]。这些研究基本涵盖了格萨尔传承的图像形式,反映出传统格萨尔图像的基本特征,也反映了格萨尔史诗文本传承之外的另一个重要的模态维度,即史诗的图像流传,实际上是勾勒出了格萨尔图像模态叙事的变迁态势。只是囿于传统文学研究领域,没有纳入多模态话语分析的范围。格萨尔图像模态本身自成传承体系,迄今出现的格萨尔图像模态表征类型多样,史诗以壁画、唐卡、版画、石刻、面具、塑像、手抄文本插图等图像模态与格萨尔文本模态并驾齐驱,共同传承着史诗的千年传唱。
新时期以来,格萨尔图像传承呈现出更多的样式和格局,可谓是异彩纷呈。众多图像模态传承带来了格萨尔图像景观化呈现的态势,表现在大量的大型户外格萨尔雕塑、以格萨尔雕塑为坐标的市镇格萨尔广场以及格萨尔图像展示场所与实践项目基地等,大大丰富了格萨尔史诗的图像模态传承。目前最大的户外格萨尔王雕塑位于青海省果洛州达日县城西郊卡热东那山上的玛域格萨尔林卡。除了大型、巨型的室外格萨尔雕塑外,还有一些地方修建了以格萨尔雕塑为中心而冠名的“格萨尔广场”,已经成为这些市镇的地标性景观。比较有名的是青海省玉树州府结古镇的格萨尔广场。此外在“世界高城”——四川理塘县城高城镇的岭·格萨尔广场也有格萨尔的户外雕塑。笔者有幸在2017年参加四川理塘举办的“四川·理塘首届仓央嘉措诗歌节”,期间参观了理塘岭·格萨尔广场。广场中心的格萨尔王威武雄健地骑在骏马上,整个雕塑极富动感和艺术张力。雕塑的基座正面用藏语、汉语和英语三种语言写着“岭·格萨尔王广场”,基座的右面同样是三种语言写着“岭·格萨尔王诞生一千周年纪念”的字样。基座的左面用藏语和汉语写有居·米旁的诗作:“三世怙主莲花生化身,悲悯光芒普照赡部州。祈祷雄狮大王格萨尔,庇佑众生吉祥功德满”,基座的后方注释了雕塑的建筑基本情况与竣工时间。显然,雕塑以及整个广场建筑是2013年纪念格萨尔王诞生千年的系列活动之一。广场周围的唐卡壁画中描述史诗里的相关情节以及藏民族的风土人情。格萨尔王雕塑的正后方是理塘县发展规划展览馆。围绕“康藏之窗,圣地理塘”为主题的岭·格萨尔广场构成了一道靓丽的文化景观。
除了雕塑和格萨尔文化广场外,藏族唐卡,尤其是成套的唐卡也是格萨尔图像模态传承的重要表征。作为一门古老的藏族绘画艺术,格萨尔故事与人物图像都是画师们绘制唐卡的重要题材。正如格萨尔雕塑从庙堂走出来一样,格萨尔唐卡现在也从寺院、经堂走出来,以艺术品的姿态出现在各类藏族文化展览馆内。目前规模最大的格萨尔唐卡是《格萨尔千幅唐卡》组画。从1997年开始,经过众多画师的努力,《格萨尔千幅唐卡》工程2008年上半年完工。它以连环画式的表现形式打破了传统唐卡的结构,成为举世瞩目的文化艺术产品[15]。藏族特有的唐卡艺术与活形态史诗口传艺术的相互结合可谓相得益彰,既可以通过唐卡图像模态了解《格萨尔》史诗,又可以通过《格萨尔》故事来了解唐卡图像模态,读者藉此可以多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地欣赏和领略史诗文化。关于当代格萨尔图像景观化的呈现,学者们分为三类:藏传佛教世俗化中的格萨尔图像;文化遗产化语境中的格萨尔图像;文化事业繁荣中的格萨尔图像[14]。虽然说格萨尔图像的景观化与20世纪5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以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和藏族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不无关系,但实际上也与活态史诗千年传唱中视觉与语言模态的各自传播进程密不可分,毕竟观看格萨尔图像与阅读格萨尔文本都是视觉体验,至少是一种补充的关系。正如有学者指出:视觉媒介强化了史诗的文化间性表达,从事实上建构了一个跨地域、跨文化的审美接受和互动场域[16]。
四、《格萨尔》数字媒介叙事
不同历史时期人类文化传播的物质载体各不相同。古代文化记忆的媒介以口头传说、神话、史诗和口承仪式为主。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文化传播实现的主要途径是口耳相传,在特定的语境空间中,很难超越客观世界时空的局限。文字出现以后,文化传播以文字形式记载,文本形式流传,人类的精神交往得以穿越时空。印刷机问世后,人类又进入本雅明所谓的机械复制时代,文化生产和文化接受在广阔的时空语境中进行。当然,除了印刷文本传播外,传统节日、文物、档案、建筑物等形式也是文化记载得以传承的重要载体。到了近代和现代社会,除了口承仪式、文字记载以外,大众媒体成为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当今的时代已进入了一个图像时代,即麦克卢汉所言的重新部落化时代:电影、电视、摄影、绘画、广告、美术设计、建筑、多媒体、动漫、游戏等正在激荡回流。无论是平面的静态图像(插图),还是超媒体图像(图像数据库),抑或是动态叙事图像(动漫)等,这些媒介都呈现出多维度融合的态势,即“媒介融合”。
媒介融合是指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泛指融合传统的报刊、广播、电视,以及基于数字技术的互联网、网络报纸、电子杂志、网络广播、博客、网络电视等新的信息传播渠道,成为建构媒介化社会的发展态势。人类媒介史的演进显示出了从硬媒介向软媒介,从原子材质媒介向数字媒介转变的嬗变趋势。科技发展到今天,已经出现了新媒介和新新媒介的说法。按照通常的理解和解释,目前新数字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新媒体形态有:数字杂志、数字报纸、数字广播、手机短信、网络博客、数字电视、移动电视、数字电影、触摸媒体等。新旧媒体的更迭是迭合、整合式的演进,呈现出媒介融合集成的多元并存、立体伸展的格局。随着印刷文字到数码以及数字媒介传播载体的转变,传统艺术发生了重大的美学转向,正如张耕耘所言:“一是艺术作品从过去以膜拜价值为主转向了以展示价值为主;二是颠覆了精英艺术的审美霸权,确立了艺术与普通大众的新型关系;三是艺术欣赏从个体性的静穆观照转变为群体性的随意消遣”[17]。
运用数字媒介手段来有效记录、保存和传播《格萨尔》史诗,创建《格萨尔》影像文化志是数字媒介时代为活态史诗传播带来了大好机遇,促进创建数字化储存数据预示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以前《格萨尔》史诗都是靠录音来记录和保存的,只关注声音的保存,而对于说唱艺人表演场面、动作肢体语言、图像等无暇顾及。现在完全可以应用数字媒介制作影像文化志,原生态地保存《格萨尔》史诗的原始真实资料,记录史诗传承的演述语境与传承概况。数字媒介既可以把诸如艺人面部表情、手势、身体动作及演述语境等等记录在同一画面,又能不间断地连续记录,把说唱演述的生态环境悉数记录下来,如此生成的影像文化志既拓展了《格萨尔》史诗的传播形式,又会超越时空吸引更多的受众。
五、《格萨尔》叙事的多模态话语阐释
文学传媒研究的成功实践,尤其是现当代文学传媒研究的丰硕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为从多模态视角介入活态史诗传播研究提供了参照。媒介融合视域下的活态史诗本质上是一种集民间文学与艺术创作为一体的活态文化形式。媒介融合视域下活态史诗的叙事研究旨在将史诗研究置于在跨学科视野下,综合史诗说唱艺人口耳传承与文本衍生的传播机制,为给传统社会流传下来的民族的、本土的文化寻找新的生存路径。史诗除了以故事本、绘画本、连环画、绘本画、漫画、舞台剧文本等视觉模态版本出版外,要加快利用文字、图片、录音、录像等手段和数字化信息技术对史诗搜集资料进行长期保存和科学使用,还要加快史诗影视改编、电视剧制作等艺术改编的步伐,对活态史诗演唱的语境与场景进行全方位呈现。
活态史诗的多模态叙事不仅仅体现在史诗口头记录本、文学再创本、改编小说、连环画、史诗儿童版等出版实物,还包括如将文字模态转换为图像、将诗歌改编为集音乐、图像、动漫于一体的多媒体数字文本等不同模态之间的转换与运用。多模态叙事借助影像媒体重现表演语境,将艺人史诗表演和多语种史诗版本进行数字典藏,通过音频、视频材料以数字文学形式欣赏史诗文本与说唱视频。通过兼容史诗图文、说唱音频、视频、网页等多媒体影像文化的多模态叙事,能够立体地重现史诗说唱全貌,使口语文化以新的数字形态得以传播。如此,多模态叙事将活态史诗的口头文本、视觉图像与数字媒介等维度融会贯通,能够相对完整再现活态史诗特有的语言诗性特点、体现活态史诗文化表征功能和重现口头表演语境视觉效果,通过重构史诗生发的语境来再现立体的史诗文化空间。
对史诗的多模态叙事探讨,有利于让中国活态史诗文化更好地传向世界。这一点,在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中,意义尤为重大。对于缓减在工业化和全球化语境中面临巨大挑战的活态史诗以及诸多民间文化形式多样化生存和发展危机,就要使这些文化多样性的个体继续成为满足人们精神需求不可或缺的宝贵文化资源。为此,不仅仅是将其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肯定其文化价值,更重要的是要延续其生命力,让其继续在当前全球化浪潮中继续在民众的生活中发挥作用,“使古老的《格萨尔》史诗在经历多重主体失落的同时又不断地被想象和重构”[18]。为此,“则必须深入到丰富而又活泼的民间文艺内部,了解并掌握它的内部规律,只有这样,它才有继续成为民众文化生活之一种的可能”[19]。
总体而言,多模态理论与表演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多模态视角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史诗的叙事传播途径;另一方面,它又帮助仍然存在的口头表演得以顺利完成。从多模态语篇分析角度对活态史诗传承进行描写分析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因为史诗传唱自身具有鲜明的多模态话语特征。基于影像文化志的多模态数字文本可以作为一种补偿手段,全景式地记录史诗演述的壮观创面,有助于史诗在更广范围内流传,为史诗他民族化提供了更加便捷的资讯平台和实现手段。当然,多模态视角只是活态史诗文学开展跨学科研究的一个方面而已,史诗研究还应该主动地与更多的学科进行交织,不断更新和建构更为合理的学术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