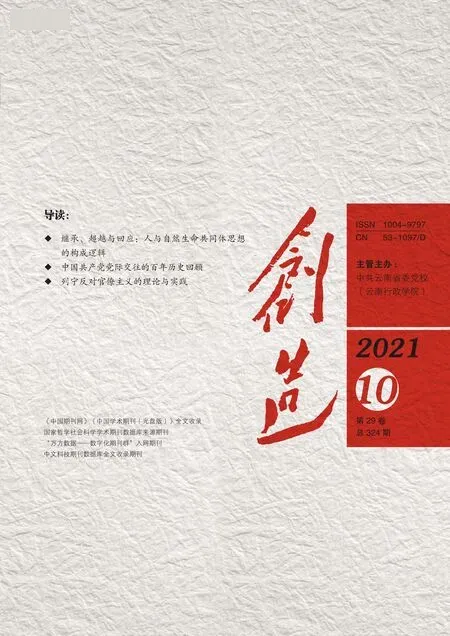云南易地扶贫集中安置点面临的变更风险及其治理
蒋 健
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奋斗的历史,是一部不断带领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历史。建党一百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对世界、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政治承诺,随着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困扰中国人民几千年的绝对贫困从此成为历史。在这场党带领人民脱贫攻坚的伟大战役中,全国共有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其中有960万农村贫困人口通过易地搬迁摆脱贫困,解决了“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困境,云南就有150万人(包括99.6117万建档立卡户),他们有的就地后移,有的离开世居的农村进入城市,成为新市民。这些环境、生活、身份等的变更,既为搬迁群众后续过上美好生活创造了条件,也让搬迁群众后续能否稳得住、能否适应新环境新生活面临各种风险考验。本文主要就云南19个万人以上城市化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面临的变更风险及其治理进行分析。
一、云南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的基本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云南的历史发展中,发生过两次重大的社会形态变迁。第一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11个少数民族一步跨千年,直接从原始社会形态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第二次是今天在党的领导下,近100万农村贫困人口直接从农村进入城镇,由农民变成市民,实现农村贫困人口的社会发展大跨越,一步跨进小康社会。
(一)易地扶贫移民集中安置基本情况
云南是全国重点易地扶贫搬迁省份之一,搬迁农村人口多达150万,占全国近1/6,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99.6117万人,约占全国搬迁总人口的10.4%,居第三位;全省共建设集中安置点2832个、安置房24.46万套,其中800~3000人的大型安置点有139个,3000~10000人的特大型安置点有14个,10000人以上的超大型安置点有19个,居全国第一。①数据来自调研材料。这些集中安置点,除昭阳区的靖安易地扶贫安置点属于新建城镇外,其余主要位于县城周边,同原有城镇融为一体,推进了当地城镇化的发展。
这些安置点,从安置类型来看,有城市化集中安置、乡镇集镇集中安置和农村集中安置三类;从搬迁安置移民来源来看,有跨县域集中安置(如昭阳区靖安新区移民来自6个县、鲁甸卯家湾片区移民来自5个县)、跨乡镇集中安置(如会泽县城集中安置点移民涉及本县22个乡镇)、本乡镇集中安置和本行政村集中安置四类;从安置点管理机构及区划设置来看,有新设行政区划组建新的管理机构的(如会泽在移民安置点新设两个街道办事处、7个社区)、有组建临时管理机构代为管理的(如昭阳区靖安易地扶贫安置移民新区)、有直接划归原有行政区划机构管理的、也有未改变原有管理机构的几类。
目前,在各级党委、政府努力下,搬迁群众已入住新的居住地,开启新的生活,除位于昭阳区的靖安扶贫安置新区外,其余所有安置点都并入或者设立新的实体性区划及机构进行管理。为让搬迁群众在搬得出的基础上实现稳得住、能致富,云南省于2020年3月印发了《云南省异地扶贫搬迁“稳得住”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从11个方面明确了未来五年的40项“稳得住”工作任务,并将每一项任务落实到具体责任部门。
(二)易地扶贫移民集中安置点的特殊性分析
通过对这19个万人以上超大型易地扶贫集中安置点的调查,发现这些新建的扶贫移民安置社区具有不同于原有社区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既为做好新社区后续管理提出了新要求,也使新社区存在或面临一些与老社区不一样的风险。
1.社区成员同质性强。具体表现为社区成员身份同质、收入同质和需求同质三个方面。从身份同质来看,这些社区的成员都是由农民身份转变而来的新市民,绝大多数属于建档立卡贫困户,只有少部分是随迁户。从收入同质来看,涉及收入低与收入来源少两个方面,属于刚摆脱贫困的低收入群体,他们进入新社区后的收入来源主要为打工收入,包括为居住地附近的种植业打工、扶贫车间打工,还有一部分外出务工,其收入大多数仅能解决最基本的城市生活需要,由于收入来源少,不少50岁左右的移民找不到活干,处于赋闲状态。从需求同质来看,普遍渴望就业和有活干,这些进入城市生活的新市民目前最关心或者最担忧的就是未来的生存发展问题,普遍感觉在这里生活不像在迁出地,所有生活必需品都要花钱,而收入来源又非常有限,担心一旦找不到工作,没有收入来源生活怎么办。这些同质性犹如一柄双刃剑,一方面,易于管理者找到社区群众的共同需求,有利于促进社区的管理;另一方面,也蕴藏着社会不稳定风险,一旦他们的需求得不到实现或者面临需求满足危机时,这些同质性的社区成员就会产生共同诉求,形成诉求压力,导致风险升级,甚至演变成群体一致的社会行动,对社会及管理者造成巨大的发展与维稳压力。
2.产、区融合。在原有城市社区中,社区居民生产工作地同其居住地是不统一规划考虑的,很少有两者在一起的,尤其是这些城市社区居民基本都不从事种植养殖业。扶贫搬迁移民安置区为解决安置点移民的生计问题,使其尽快适应新环境、新生活,多考虑让其就近就业,当地党委、政府均在这些超大型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及其附近规划建立了种植养殖业基地和扶贫车间,通过吸引企业进驻或由企业发展种植养殖业来解决搬迁群众的就近就业问题,从而形成了安置点生产工作地与移民居住区在一起的“产”在“区”边的“产、区”融合规划建设发展特色。
3.户、居分离。据调查,搬迁群众由于对扶贫搬迁安置政策不了解、不信任,担心迁户会导致附着在原有搬出地户籍及农村户籍上的待遇与利益会随着农村户籍转变为搬入地城镇居民户籍而被取消,多采取观望态度,不愿迁户,致使绝大多数搬迁户户口与居住地分离。现行政策对搬迁户的户籍迁移也是采取动员、自愿而不是强制的态度,如《方案》规定的“群众搬迁后原户籍地址实际不存在的,原则上应将户口迁移至新居住地”,仅是针对原户籍地址已经不存在的要迁移至新地址,而且是原则上而不是必须迁,其余的则是由“当地政府积极组织动员群众将户口迁移至实际居住新址”。造成安置点绝大多数居民“户、居”分离,不像老社区绝大多数居民“户、居”统一。
4.生存压力普遍大于原住民。这些新市民在迁出地普遍有林地、承包地和宅居地“三地”。在原住地,再怎么困难也不用担心生存问题和吃饭问题。但在迁入地,所面临的一切都是全新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居住环境都发生了变化,他们不仅要适应这些变化的环境及生活,还要担心未来的生存和发展。虽然对现在的居住环境比较满意,但大多对未来具有担忧与恐惧心理,担心找不到工作或者工作收入低难以支付迁入地的生活成本,甚至连基本的生存与吃饭问题都难以解决,心理压力普遍高于当地的原住民。
二、易地扶贫集中安置点面临的变更风险分析
风险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一定条件下,风险会演化升级、会转化为事故与灾难,造成难以弥补的生命与财产损失,因此,必须树立风险意识,加强对各类风险的辨识与管控。
中国现在已进入风险社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在国际国内面临的矛盾风险挑战都不少,决不能掉以轻心”①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防范风险挑战、应对突发事件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8.。确保扶贫安置点搬迁群众在搬入地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需要做好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后续管理,尤其是这些安置点的风险管理。要通过风险辨识、风险分析,了解安置点存在哪些风险和风险源,通过对这些风险的评估建立起相应的风险管控机制,维护好安置点的社会稳定,为群众创造一个平安、和谐的生活环境。
(一)变更风险的认知
“变更”一词最早出自《管子·法法》,“上不行君令,下不合于乡里,变更自为,易国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其含义为改变、更动。现代意义的风险概念则来自西方,最初主要是形容商船在频繁的货物运输过程中可能遇到的由触礁或海难等因素导致损失的危险。对风险的理解可以从客观和主观两个层面来认识,首先,风险是一种客观存在,是“关于不愿发生的事件发生的不确定性的客观体现”②王巍.国家风险——开放时代的不测风云[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14.,是“可能发生的危险”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330.。其次,风险也是一种主观认知,是损失的不确定性,其不确定性就是人的主观判断,不同的人对同一风险往往会有不同的认知,“作为一种可测定的不确定性,风险与人们的主观认识和预期联系在一起”④袁方.社会风险与社会风险管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37.。变更必然产生变化、更新,也就意味着产生不确定性,同时也因为人们对变化、更新的未来的不可知、不可测,变更就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这种因事物的改变、更动而产生的风险,我们就称之为变更风险。
在管理领域,变更管理是安全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管理者如果对变更管理不当就有可能因其潜在的风险因子引发重大安全风险甚至是灾难性事件,因为“变更过程是高风险的过程”①钟开斌.逆向变更风险管理——“12·31”外滩陈毅广场拥挤踩踏事件案例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06).。比如,2014年12月31日在上海外滩陈毅广场发生的拥挤踩踏事件,就是一起典型的因变更引发的重大安全风险,再加上管理者“预防准备不足、现场管理不力、应对处置不当”②钟开斌.公共场所人群聚集安全管理——外滩拥挤踩踏事件案例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3.造成重大伤亡和严重后果的公共安全责任事件。这起事件中的变更主要有:组织者变更,由原来的上海市政府牵头举办、上海市旅游局代表上海市政府主办变更为黄埔区政府和上海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活动地点变更,由往年举办的外滩风景区变更为外滩源,不说外地人,就是不少上海本地人都不一定知道外滩源在哪里,而将两者等同于同一个地方;公众参与方式变更,由过去的免费参与变更为凭票参与;参与人数变更,由过去的不限制变更为3000人左右参与。导致“原计划在外滩举行的跨年灯光秀活动变更为在外滩源举行不对公众公开的灯光秀活动后,相应的外滩安保措施等应急准备工作由市级管理降为区级管理”③钟开斌.公共场所人群聚集安全管理——外滩拥挤踩踏事件案例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45.。
变更都有其风险,需要管理者和组织者对变更产生的风险认真加以分析评估、研判对待。作为管理者需对变更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意外情况有清醒的认识,并运用风险管理与系统管理思想建立起应对变更可能带来的风险的变更风险管理体系,在对变更过程进行全面、系统风险评估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地应对和防控各类变更风险,避免和减少因变更产生的风险带来的突发事件发生。
(二)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面临的变更风险
通过对现有超大型易地扶贫安置点风险源、风险点及居民群众的走访、调查分析,目前在这些安置点主要存在以下一些变更风险。
1.政策变更风险。随着脱贫攻坚的全面完成,绝对贫困问题在我国已成为历史,脱贫攻坚时的政策将会被乡村振兴等其他政策所取代。虽然原有脱贫攻坚的一些政策内容在新政策中会有延续,而且国家对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后也明确还有5年的过渡帮扶期,但不管怎么说,对这些建档立卡贫困户原有的帮扶政策确实发生了改变,原有的一些优惠和帮扶将会逐步减少乃至取消。对于搬迁到安置点的群众来说,政策的变更既涉及个人,也涉及新居住区基础设施的后续完善问题,一方面,对他们还能不能适用乡村振兴的有关政策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说法,毕竟他们现在不是生活在农村而是城市,目前云南对他们的新政策是2020年3月印发的《方案》。另一方面,虽然集中安置的新居住点已经建成并完成搬迁入住,但在安置点仍有一些城市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需要完善,过去集中安置点的建设资金是精准扶贫政策整合和投入的专项资金,现在精准扶贫已画上了句号,后续的建设投入从哪里来,目前没有具体说法,而这些投入对承接安置任务的县(市、区)来说是其财力难以完成的(昭阳区靖安、红路两个安置点基础设施配套缺口资金达57031.97万元),设施的不完善会影响到安置点居民的后续生活,这些政策变更对未来安置点的社会稳定存在着风险。
2.身份变更风险。虽然目前在安置点生活的绝大多数群众还没有完成户籍迁移,还是农村户籍,但是,按照我国对城市居民的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分类统计方法,这些没有完成户籍迁移的安置点群众其身份应属于城市常住人口,而不再是农村人口。其身份的变更面临着既有城市人口对其市民身份的认同,也面临着他们自身对自己市民身份的认同。与此同时,身份的变更既有利益的获取,能够得到现有城市居民的保障及待遇,也潜在着未来附着在其原有身份上的利益失去和减少的风险,让这些新市民对其身份变更存在着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进而成为不稳定因素。
3.环境变更风险。人对熟悉的环境有一种天然的依赖感和亲近感,故土难离是这种依赖感与亲近感最直接、最生动的体现,对新的、陌生的环境往往会有一种排斥感、恐惧感。一般来说,人在对陌生环境熟悉与适应的过程中,适应期越短,潜在的风险就越少、级别也就越低,反之,适应期越长,潜在的风险就会越多,风险的等级也会越高。集中安置点的群众普遍都是离开曾经熟悉的、世代居住的环境搬迁到一个新的陌生环境中,这种陌生性既表现为对自然环境的陌生——农村到城市、山区到坝区、单门独院到单元楼房,还表现为人文环境的陌生,从传统的乡邻社会变更到陌生的城市社区社会,面临着由农村文明向城市文明的变更。由于周边大多数人都是新面孔,在熟悉和适应这种环境变更中,必然存在着不适应或者是排斥感,造成搬迁群众的不安与担忧。
4.生活变更风险。生活变更风险主要是指生活方式变更的风险。集中安置点的移民,一是生活来源获取方式发生变化,在原住地,搬迁群众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做什么、什么时候做完全由自己自主决定,不受或者少受他人影响,但在安置点则失去了自主选择的可能,更多的是被动接受;二是随着生活环境的变更,其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更,安置点的生活离不开各种电器,由于是单元房,出门要乘电梯、做饭要用电器、入厕就在家里,等等,都需要适应和改变;三是生活必需品来源的变更,过去喝的水、吃的粮食、肉食、蔬菜大都来自于自己——基本上是自产自销,尤其是蔬菜,没了就到自己地理弄,基本不花钱,现在所有的这一切都要到市场通过交易的方式货币式获取;四是生活习惯的变更。这一切,都意味着不可知和不确定。
5.职业变更风险。搬迁群众的职业身份将由农业从业者、家庭妇女变更为城市一产或者二产、三产从业者;职业生活习惯将由原来的相对自由、随性变更为受约束、守规矩和整齐划一;职业活动将由原来的独立与自主活动变更为多人的分工协作与合作,由强调自我到强调配合。
以上变更同时、集中出现,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安置点风险发生的概率和等级,而且这些风险的叠加又会加大安置点及其附近地区风险管理的难度,增加群体性事件发生概率。如果没有有效的风险研判与防控机制,当诱因出现的时候,这些风险就可能成为当地社会不稳定或者是群体事件发生的助推器。
三、易地移民集中安置点变更风险治理的对策
古人云,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要在危机中育先机,要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战。做好云南省超大型易地扶贫移民安置点的后续发展与管理工作,确保安置点群众稳得住、能致富,离不开对安置点的风险管理。防范和化解易地扶贫移民安置点的变更风险,避免风险叠加和风险演变升级,需要提前谋划,下好先手棋,打好风险防控主动战。
(一)树立系统治理理念,构建系统治理机制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197.防范和化解变更风险离不开系统治理理念与系统治理行动。系统论强调以系统为对象,从整体出发来研究系统整体和组成系统整体的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把握系统整体,达到最优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系统思维在深化改革和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系统意识,增强系统思维能力,提高应用系统思维解决问题的本领。2013年9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项改革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2014年初,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项工程极为宏大,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第一次将坚持系统观念作为“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发展原则。
风险的产生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不同的风险也会相互交织、互相影响。对风险的有效治理需要树立系统观念,运用系统思维从整体、系统的角度全面把握风险产生的各种诱因以及促进风险演变、叠加的各种因素,同时还需要掌握不同风险之间的相互影响。针对易地扶贫移民安置点各类变更风险的情况,防控和化解这些变更风险,要从整体的角度出发,系统分析考虑这些变更风险与安置点其他风险的关系,厘清上述不同变更风险的内在机理以及彼此之间的内在关联。一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个维度全方位系统构建针对易地扶贫移民安置点的管理、发展、认同、参与四条路径协同推进的变更风险防范化解的防控处置机制;二要加强移民输出地与安置点的沟通协调,构建移民输出地与安置点之间的信息沟通与协同共治机制。
(二)不断完善制度,建立安置点变更风险专职研判处置机构
在国家和社会治理过程中,制度是带有根本性的。我国现在已经进入一个各类风险高发、多发的时期,“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在国际国内面临的矛盾风险挑战都不少,决不能掉以轻心……如果防范不及、应对不力,就会传导、叠加、演变、升级,使小的矛盾风险挑战发展成大的矛盾风险挑战,局部的矛盾风险挑战发展成系统的矛盾风险挑战……经济、社会、文化、生态领域的矛盾风险挑战转化为政治矛盾风险挑战,最终危及党的执政地位、危及国家安全”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222.。随着时间、环境的变化,各类风险也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各级党委、政府要增强忧患意识,不断完善各项制度,应对处置各种风险。针对这些集中安置点可能存在和面临的风险,当地党委、政府居安思危,已建立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比如:网格管理、加强基层党组织领导、大力发展产业解决群众生计等制度和举措,取得了明显成效。
但仍需对风险防控做到关口前移,提前准备和防范。“‘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维护公共安全必须防患于未然,要坚持标本兼治,既着力解决较为突出的公共安全专项问题,又用更多精力研究解决深层次问题。要坚持关口前移,加强日常防范,加强源头治理、前端处理,针对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地毯式排查和立体化整治行动,什么问题突出就集中力量解决什么问题。要建立健全公共安全形势分析制度,经常评估、预判,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清除公共安全隐患。”①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防范风险挑战、应对突发事件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187.因此,当前和今后做好风险防控既要总结完善既有制度,让制度效用得到充分发挥,又要针对新情况、新问题,制定出台新的制度和举措解决这些情况和问题。
针对安置点面临的上述变更风险,需要在现有制度和机构的基础上,组建专门的机构或者是责成专门机构、人员专项负责,对安置点的变更风险及风险源进行持续跟踪监测、评估,及时了解、掌握安置点变更风险及其风险源的演变情况,定期或不定期地向当地党委、政府报送风险研判报告,为及时管控和处置风险提供第一手资料。
(三)聚焦源头治理,推进产业持续发展
发展中的问题要在发展中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风险要在发展中化解。超大型易地扶贫移民安置点面临的变更风险是在发展中出现的,很大程度上是由当地和安置点发展的不足以及移民群众对当前及未来自身发展信心不足带来的,化解这些风险要聚焦源头治理,找准风险产生的根源,紧紧抓住发展产业这个“牛鼻子”,通过产业的发展妥善化解移民进城后的后顾之忧,让他们有通过诚实、努力劳动获取养家并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产业平台与发展平台,让自己的未来能够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要让移民群众稳得住,在安居的基础上乐业,首要的是要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收入来源问题。为此,一要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推进安置点及附近产业可持续发展。要发挥好当地政府经济调节和公共服务职能,努力培育市场或者在一定程度上暂时替代市场,设置企业(产业)发展专员,一企(产)一员或者一企(产)多员专门帮助安置点及附近新建产业提供发展信息、化解发展风险、解决发展难题,帮助企业(产业)增强发展动力与发展后劲,促进其较长时期稳定发展,保障安置点群众有稳定的就业平台。二要继续完善现有政策,奖励、鼓励与激励企业积极吸纳安置点群众就业。三要多途径开展就业创业培训,提升当地群众城镇化就业、创业能力。做好就业创业服务,大力鼓励和创造条件帮助移民群众积极就近创业,化解其创业进程中的难题,通过群众自身创业来带动就业,在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与动力的同时,增强其对城市新生活的适应能力与融入能力。
(四)做好宣传教育,促进群众心理融入
如前所述,风险既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一种主观认知。安置点变更风险的产生既有物质与发展不足的客观原因,又有来自移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主观认知。做好变更风险防控不仅要提高安置点发展能力,还要提升安置点群众的心理适应能力,让他们尽快适应新居住地的环境、生活,从心理上接受和融入目前崭新的城市生活。一要避免过度宣传。要恰如其分地向群众宣传介绍安置点的情况,既讲未来发展愿景,也讲当前发展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党委、政府对待这些问题的态度与举措,让群众对安置点的新生活有正确的心理认知和态度,树立正确的心理预期,既对未来有美好的期盼,也对当前可能会面临的困难有清醒的认识,进而增强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安心接受和融入目前的城市新生活。二要抓好安置点学校软件建设,促进教育发展。孩子是国家、社会未来的希望,更是安置点群众对未来的希望,他们宁愿自己苦一点也要让孩子未来有一个比他们更好的生活,而且孩子的城市化融入也是家长融入的动力,稳住孩子就是稳住家长、稳住移民。稳住孩子的前提是提高安置点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让这些孩子通过学习获得改变命运的机会与能力,不仅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掘出潜力、激发出能力,为未来发展奠定基础,还能通过孩子的变化影响家长的行为,促进安置点社会稳定。三要多渠道、多途径、多主体关注移民心理健康,及时化解其心理问题。通过发挥安置点基层党组织、基层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党员、社会贤达等的力量,采取多种形式关心、关注移民的心理健康,化解其心理困扰,将诱发变更风险的各种主观因子及时消除在萌芽之中。
总之,安置点变更风险是多方面的,产生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对其治理应多方发力,多维度、多角度、多路径创新治理,不能有毕其功于一役的简单思维,要树立久久为功的坚定信念,通过发展来逐步化解安置点的变更风险,促进安置点社会和谐稳定与群众安居乐业。